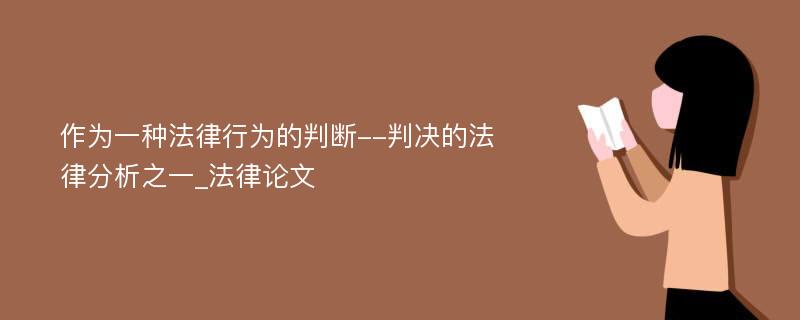
作为法律行为的判决——判决的法理学分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决论文,法理学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判决是审判机关以中立的立场对特定的社会冲突作出决定以求解决该冲突。在今天,因为社会冲突的不同而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注:社会冲突与诉讼间的关联性,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诉讼在今天并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判,而是“超司法”。见杨一平、俞静尧:《司法概念的现代诠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69页。);相应地,判决有民事判决、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就形式意义而言,判决是对特定的社会冲突作出相应的决定。对此,《牛津法律大辞典》写道:“法庭对由其审理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所作出的公布的有关争议问题的决定”(注:[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页。)。就实质意义而言,判决是对特定社会冲突的法律解决。对此,判决被认为是“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注:杨春铣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对特定社会冲突的法律解决指明了判决的功能所在。那么,判决为什么能对社会冲突加以解决?换一个角度说,判决与特定的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结因素是什么?在法理学看来,这一联结因素只能是立法者在诉讼法上以制度设计而赋予判决的法律上的力。诉讼法学将这一联结因素称为判决的法律效力。那么,判决为什么能具有法律效力?这可以解释为判决是由公权力机关作出的。但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与粗疏。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法理学的而不仅仅是诉讼法学的角度来探寻判决的内在规定性。
判决为法律行为
冲突当事人依据现行法而将特定的社会冲突提交作为中立的第三人的审判机关以求冲突获得法律解决,由此形成了诉讼法律关系。所谓法律关系,无非是法律化了的社会关系即采取了法律形式的社会关系。诉讼法律关系可以理解为为了使冲突获得法律解决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此中,冲突当事人为诉讼法律关系的一方,作为中立者的审判机关为另一方。既然“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是由行为作用的”(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那么诉讼法律关系也就必然是冲突当事人与审判机关之间的行为互动。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法律制度正是关于冲突当事人与审判机关之间的互动行为的法律规定,不告不理和告则必理是行为互动的典型。这意味着:第一,离开了行为则不存在诉讼法律关系;第二,必须着眼于行为,以行为为基本范畴分析与把握诉讼法律关系。
如果说,起诉、举证、申请执行等是行为互动关系中冲突当事人一方的行为,那么,判决——“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则是审判机关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一系列行为的核心。对冲突的受理、对冲突事实的发现与认定是判决的前提性行为,调解是判决的变通性行为(或称变通性形态),裁定与对制定法的司法解释是判决的辅助性(补充性)行为(注:“法官的这种造法职能被认为是附加于其基本职能的。”[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页。),强制执行则是判决的延伸性行为。这些行为围绕着判决这一概念而形成了诉讼法律关系中审判机关的行为系统,这一行为系统作用于特定的社会冲突,最终使冲突得到法律解决。因此判决是审判机关作为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并且,在诉讼法律关系的互动的行为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离开了作为法律行为的判决,诉讼将是没有意义的,冲突的法律解决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判决是审判机关的法律行为,它才受相关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规制——法律规范不可能作用于行为之外的领域(注:参见王广辉:《法律规范的性质与作用》,《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第9页。)。
大陆学者仅将判决界定为决定、判断等(注:参见柴发邦主编:《诉讼法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张仲麟主编:《刑事诉讼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台湾学者则是将判决界定为意思表示(注:参见胡开诚:《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1993年,第191页;庄柏林:《民事诉讼法概要》,三民书局1982年,第97页;张载宇:《行政法要论》,汉林出版社1977年,第487页。)。这些学理界定均隐含了判决为审判机关的行为的认定,可惜没有明确地将判决界定为法律行为,终究未能准确地揭示判决的内在规定性。少数学者认识到了判决实质上为法律行为,如“所谓裁判,乃法院或审判官对诉讼关系人所为之诉讼行为为意思表示之行为”(注:黄东熊:《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1991年,第453页。);“行政诉讼之裁判,乃谓行政法院就行政诉讼事件予以裁定或判断,依其意思表示之内容,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之行为”(注:管欧:《中国行政法总论》,台北1981年第19版,第550页。)。但是,没有指明判决在诉讼行为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也缺乏对判决为法律行为的学理论证。
以上的阐述仅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指明的是判决与冲突当事人的程序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做进一步的阐述,以指明判决与冲突当事人的实体法上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许正是这种研究视野的转换,形成了法理学对判决的阐述与诉讼法学的差异。
法律以行为为对象,是对行为的控制。就现当代法律运行机制而言,“行为的法律控制”经由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实现:一是针对普遍的与抽象的行为即不特定主体的行为,二是针对个别的与具体的行为即特定主体的行为。前者为立法,后者为司法,行政则兼具二种机制。法律控制不论是针对抽象的行为还是针对具体的行为,都应该并只能由法律行为来承担,否则就意味着纯粹的内心活动具有确认与平衡利益关系的功能。社会冲突是表现为特定状态的主体行为,因为“冲突的法学本质应当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冲突必须表现为主体的特定行为,非行为表现的对抗情绪不构成冲突”(注: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因此,以诉讼对冲突加以法律解决也就是对特定行为的法律控制,确切地说是一种个别化的法律控制。只有当判决是作为审判机关的法律行为时,作为特定行为的冲突才可能受到法律控制;如果否认判决为法律行为,那就无异于承认冲突可以不受判决的控制,这显然与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
法律效力是逻辑地与法律行为相联系的(注:详见李琦:《论法律效力——关于法律上的力的一般原理》,《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只有确认判决作为法律行为而存在,才能说明判决为什么能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确认恰是诉讼法学在理解判决时所忽视的。
综上所述,可以将判决定义为:法院基于审判权而对特定的社会冲突作出实体决定以使该冲突得以解决而在诉讼法律关系的互动的行为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行为。
利益指向
法律以人的行为为对象和法律以人的利益为对象的判断指明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实质上是统一的(注:参见姚建宗:《思考与补正:论法的调整对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26页;杨春福:《论法律的对象与对象化的法律》,《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86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践的合目的性说明了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动因无非是利益;另一方面,所谓利益,又不能不以主体对资源的竞逐、占有、支配等行为表现出来。行为受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仅仅在于与行为相关的特定利益需要受法律调整。社会冲突在形式上表现为主体特定状态的行为,在实质上则是行为主体之间利益的矛盾状态。因此,对社会冲突的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对处于矛盾状态的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调处。一项具体的判决总是针对着冲突当事人具体的利益矛盾,通过对冲突当事人具体利益的确认与保护或抑制与减损而使利益矛盾得到解决。
纳入法律解决机制的社会冲突可以区分为两种形态:发生利益争执和损害法定利益,审判机关对冲突的解决相应地表现为确认利益与平衡利益。当发生利益争执时,判决的功能是确定处于争执中的利益即不确定的利益的归属。如婚姻当事人的离婚诉讼是对与婚姻相关的利益的争执,准予或不准予离婚的判决总是确定了争执的利益归属于其中一方当事人;选民名单诉讼是对与特定公民的选举权相关的利益的争执,其判决则是确认该公民是否可以享有选举权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当侵权行为损害了法定利益时,判决的意义在于针对所损害的利益的不同而对行为人设定功利性补偿责任或道义性惩罚责任,通过行为人对相应责任的承担以使因侵权而失衡的利益关系重新处于平衡状态(平衡包括对受损利益的恢复或补救以及在无法恢复或补救时的道义性与精神性慰藉)。
很显然,判决指向的是冲突当事人的利益而非判决实施者即审判机关或法官自身的利益。这早已是一项公理性的命题了。这一命题决定于判决的特性——由冲突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以中立的立场对冲突加以法律解决。如果判决的实施者在判决中寻求自身的利益,那就意味着“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从而导致冲突得不到公正的和真正的解决(注:参见[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页。)。进一步说,判决指向冲突当事人的利益是就直观的与直接的层面而言的,在抽象的与最终的意义上,判决则是以公共利益为指向(迄今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
公共利益包含了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个体利益可以区分为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和个别化的个体利益。这源于个体之间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差异性。某种“个人利益具有社会普遍性,因而,这就成为社会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注: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54页。)。对自身利益的安全与可靠的需求以及在利益的安全与可靠因他人的侵权行为受到破坏时获得救济的需求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因此,当一项具体的判决满足了利益获得救济这一个体需求时,它实际上是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换一个角度说,诉讼机制中的当事人并不是以特殊性的、区别于他人的形态存在,而是以抽象的、与他人具有同一性的形态存在。正因此,诉讼机制才可能是一个为冲突当事人提供平等保护的、排除了特权的法律机制。受到诉讼机制因而受到判决的保护的冲突当事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作为普遍性个体利益即公共利益的直观形态而进入诉讼机制的。立法者在设计诉讼机制的时候,并不是针对个别化的个体利益,而是出于为普遍性的个体利益提供法律救济的目的。这是对法的普遍性原理的贯彻:“法律所设想的适用对象不是特定的个人及有关行为,而是一般的人和行为。”(注:东方玉树:《成文法三属性: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态》,《法律科学》1993年第5期,第36页。)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行政诉讼中使行政相对人胜诉的判决、全部的民事判决,均是以“普遍性的个体利益”这一公共利益为指向的。
个体的单独存在和由个体集合成共同体是人类两种有机联系的存在方式,因此,“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具体包括:1.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2.共同体的安全与秩序,3.共同体的尊严与荣誉。由于“社会作为个人的相互合作,是人的广泛的、持久的对象化活动所必须借以实现的方式”(注:万斌、薛广州:《民主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因此,在终极性上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可以并且应该还原为个体利益,但是,至少就法律形式而言,它是与以权利形式表现的个体利益明确地区别开来的。它的法律形式之一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尊严等。这说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具有对个体利益的抑制性从而使二者处于矛盾状态。这样的利益矛盾使公共利益可能受个体行为的损害,所以近现代法律制度中存在着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保障与救济机制,刑法和行政法即包含了这样的法律机制(它们被典型地认为是公法)。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行政诉讼中对被诉行政行为加以维持的判决,均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为指向的。
判决指向公共利益源于并表明了判决的手段属性。作为法律行为,判决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审判机关运用作为国家权力的审判权而实施的行为。国家机关是抽象存在的国家的直观体现,而国家,无非是“一种通过公共权力联结起来的,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处理公共事务为目的的综合组织体”(注:王振海:《论国家功能》,《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第61页。)。显然,作为人造组织的国家仅仅具有工具合理性。国家权力同样地具有工具的即手段的属性(注: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因此,审判机关与审判权就不能不具有手段属性了,而与此相应的判决亦不例外。就法律分析而言,法律制度是分配利益并为这一分配提供相应保障的统一。利益的法律分配表现为法定权利与法定义务的设定,对利益分配的保障是由资源增益机制和对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承担的(注:详见李琦:《利益的法律分配及其保障——对现当代法律机制的整体性描述》,《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两种保障机制的手段意义正在于使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使法定义务得到实际的履行(注:行为法学认为法律系统分为资源分配子系统与保护子系统两部分,这与本文的观点相近,见谢邦宇等:《行为法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判决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的与最终的行为表现。这表明判决作为公共利益的保障手段具有他种手段所不可替代性(行政权的运行即行政行为同样属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手段。但是,行政行为可能引致新的社会冲突。因此要有行政诉讼机制,以行政判决最终地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
上节指明判决因作为法律行为而具有法律效力,这是从制度设计层面所获得的结论。本节指明判决以公共利益为指向,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手段,这是从价值选择层面指明判决何以具有法律效力。
合法性与合理性
判决的意义既然在于对特定冲突做法律上的解决从而相应地对公共利益加以保障,那么为了使判决真正地解决冲突,就必然要求判决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判决的合法性更多地属于逻辑问题。判决乃是制度设计所创制的行为,与实体法上的行为大不相同。实体法上的行为离开了制度设计是仍然可以作为事实上的行为而存在的,如买卖、结成配偶、杀人、盗窃等。因而,实体法上的行为是法律化了的行为而非法律创制的行为。判决则是纯粹出于法律创制的行为,不可能离开了制度设计而仍能作为事实上的行为存在(注:学者新近认为:“按照规则所调整的行为是否可能发生于该规则产生之前,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调整性规则只是对已经存在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评价,并通过授予权利或设定义务来调整相关行为的法律规则……构成性规则是以本规则的产生为基础而导致某些行为方式的出现,并对其加以调整的法律规则”。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虽然此中未直接对法律行为作出区分,但显然隐含了与本文相同的观点。)。前文的阐述实际上已指明了法律为什么要创制出判决:创制一种法律工具。如果“以最小限度举出构成审判的三个要素”,那么它们是:“以社会上的纠纷为对象”、“须由有拘束力的第三者判定”、“依照法律规范的审判”(注:董潘舆编著:《日本司法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可见,合法性是逻辑地包含在判决中的。这并非指每一项具体判决必定是合法的,而是指判决逻辑地要求合法性——如同逻辑地要求由第三者作出判定。
判决必须依据实体规则固不待言,那么,实体规则对冲突的解决到底有多大功能?立法史上曾有认为实体规则能充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相应地采取严格规则主义以禁止法官越制定法之雷池的时代(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4页。)。然而,实际情形是,“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到的问题”(注:[美]梅里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另一方面,立法作为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内含着对差异的否定;而司法是从一般向个别的回归,必然面对差异并且必须对个案中的具体情形给予充分考虑。所以,“判决内容永不能由既存实体法规范所完全决定”(注:[奥]凯尔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这意味着,实体规则与冲突的解决之间只可能存在相对的对应关系。因此,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结合成为必然,法官对冲突的解决突得了自由裁量权从而判决成了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当判决作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而存在时,仅仅要求判决具备合法性也就不够了。为了使自由裁量的判决能够公正、合理从而有助于冲突的真正解决,就必然要求判决在具备合法性的同时还具备合理性。学理上正是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乃是在特定情势下对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权。这是设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目标”(注:杨开湘:《法官自由裁量权论纲》,《法律科学》1997年第2期,第13页。)。刑法学则更具体地指出,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要求法官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在法定范围内公正合理地决定刑罚(注:李志平:《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93页。)。判例法机制固然以重视法官的创造性为传统,大陆法系在今天也“并不否认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某种创造性精神”(注: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赋予法官创造性所表明的是对冲突解决的合理性的追求,“创造”一语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假使法官完全丧失了创造性精神,则他对法律的适用即判决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怀疑。
对判决的合理性要求源于判决的工具属性。推而言之,合理性是全部权力行为的要求。合理性要求也可以说是对作为工具属性存在的国家权力运行的一种控制方式。法学家们一向将合法性与合理性作为行政法的原则,以之要求行政行为。本文试图从学理上强调合理性要求之于判决同样为必须(当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时,判决的合理性就为立法的合理性所吸收,不再作为独立的问题而存在)。
判决必须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相比之下,合法性要求是判决较易达到的同时也是较为表层的要求,合理性要求的达到则更具难度并且是更为深层的。就合理性与合法性二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判决的合理性应基于合法性即以合法性为前提;另一方面,判决的合理性是高于其合法性的。合法性可能仅仅与形式正义相关,合理性则必定达到实质正义。“法律的武力强制的理由来自于法律的应当被服从性。”(注:北岳:《人类理性协议与法律规则的来源》,《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第11页。)只有判决具备合理性,才可能真正地具有“应当被服从性”。由此,判决的法律效力在直观的层面来之于合法性,实质上则由判决的合理性所决定:“司法判决之所以必须得到当事人的执行和尊重,不只是因为它是握有司法权的法官作出的,更在于其中的法律推理和原理阐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注:贺卫方:《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93页。)。正因为合理性乃是对判决的更深层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要求,所以当出于另一种合理性考虑时,合法的判决会被废止:例如,民事判决的执行和解、对已决犯的赦免。
必须指出,判决的合理性不能不是有限的因而也是相对的。这是因为:第一,再现冲突事实的相对性。再现冲突事实是将客观上的冲突事实转化为法律上有意义和能为法律所承认的事实,从而以之作为判决的依据。“尽管法律事实可能与客观事实近似,但并不是相等,甚至总是不能重合。”(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很深的哲学问题”。对此,可参见孙再思:《论法律上的真实》,《学术交流》1994年第4期,第63页。)因为法律事实“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构设出来的”(注:[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中译文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0页。因遵循证据规则、法庭规则等导致事实再现的相对性,可看作是形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抑制。)。既然判决基于具有相对性的再现冲突事实,那么判决的合理性就必然只能是相对的。第二,判决的利益确认与平衡是由法官做出的,必然地介入了法官的带有个性化的主观意志。因此,即使法官完全出于善意,也不能确保所认定的公正合理是全然与社会一般的正义标准相一致(注:学者指出:“职业教育经历较长的法官,其行为的理性化程度比职业教育经历短者为高”,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可见法官在把握判决合理性的个体素质上存在差异。作者还同时分析了法官的不同心理类型。)。又由于判决是针对具体的冲突当事人,冲突的真正解决尚须当事人认许判决为合理。当当事人以同样(甚至更)带有个性化的主观意志看待判决时,即使判决与一般的正义标准相一致,也未必能获得当事人的认许。基于法官的与当事人的二方面情形,虽然有上诉机制,但由于存在终局裁判制度,判决的合理性仍然只能是相对的(终局裁判制度无疑是出于诉讼正义而设置。由终局裁判制度而形成的对判决的合理性的一定限制可视为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间的矛盾)。
判决的合理性的有限性可以作为法律的有限性的一种解释。从中似乎也可以说明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秩序并且只能在于秩序,尽管理论上认为法律应该是秩序与正义的统一。那么,本文的最后结论是:作为法律工具,判决的功能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