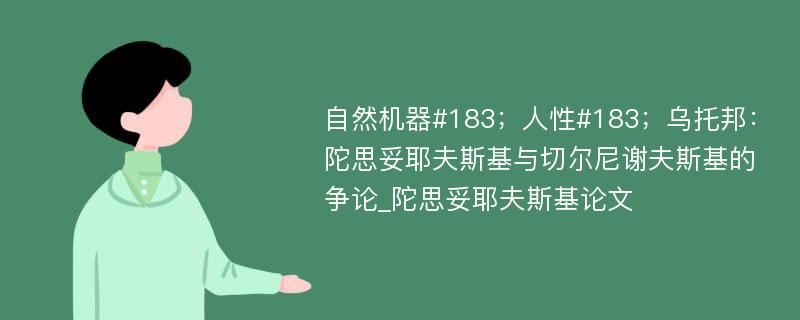
自然机器#183;人性#183;乌托邦: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乌托邦论文,之争论文,斯基论文,耶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1-0043-10
一、并不陈旧的故事
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步入思想相对自由的时期。圣彼得堡在地理位置和思想文化倾向上都是最接近欧洲的城市,在那里思想尤其活跃。1861年的9月1日,有一神秘人物快马疾驰在涅瓦大街上,一路撒下传单后消失。传单题为《致青年一代》,号召废止沙皇,民选政府。彼得堡人心沸腾。9月23日,大学生在涅瓦大街游行,过节似的高兴。接下来,仍旧是沙皇政府实施镇压、监禁、流放。而历史毕竟已经转了一个弯,变革的思想继续在彼得堡、俄罗斯各种各样的“地下室”里酝酿着。“地下室”也就成了当时变革思潮的一个比喻。
1860年代出现的一代知识份子,来自各种社会背景和阶层,类似法国革命前的第三等级,他们有意和1840年代的贵族知识份子的思想方式切割,思想更自由,想法更浪漫,也时常更盲目。当时许多人主张在俄国创造出一代“新人”。“新人”的理论多半依附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观和英国功利主义(启蒙思想在19世纪的延续);更有激进者主张虚无主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塑造的医科学生巴扎罗夫就是虚无主义者的塑像,这一代人因此被称为理性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未必就准确,也不妨称他们为超级浪漫者。欧洲启蒙本来就有激情洋溢、富有梦想的浪漫特征;急于改变落后现状的俄国人情急之下就以为欧洲现代化的一切都是先进、光明的,比欧洲人还浪漫,因此超级浪漫。如果给超级浪漫的俄国人一个具体的人格形象,那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沙皇政府不喜欢他,1862年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起初关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后流放到西伯利亚。车氏入狱后就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怎么办》,一部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出发设想人性和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小说。1863年《怎么办》出版,因为这本书正是超级浪漫者的所需,加上车氏的个人传奇色彩,小说很快风靡俄国,成为“新人”思潮的经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敬佩车氏不畏强权的人格,但是对车氏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的自然观、人性观和乌托邦设想却不以为然。陀氏有了同车氏公开争论或对话的意图之后,起初打算撰写论文,后来却写了小说,这就是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地下室手记》到了20世纪被广泛仔细地阅读,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书中的地下人这个原型在20世纪世界文学里还有不少的子孙。
这是一段陈年往事,然而意义并不陈旧。陀氏和车氏的两部小说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对20世纪产生了不同影响,至今我们还生活在这场争论提及的观念中。把陀氏和车氏之争当作进步和反动的争论,是历史造成的误区。首先,在苏联,因为列宁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己的书也起名为《怎么办》,所以早期的苏联把车氏的自然、人性和社会观奉为真理,甚至将车氏的某些设想转化为苏联建设的蓝图。于是前苏联阵营的国家一边倒地把车氏思想视为范式,把陀氏说成是反对进步的作家,这样的观点也影响到中国长期对车氏和陀氏两个人的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中国的具体影响很难评估,但是他的那种盲目浪漫对于几代的中国人都不陌生。即便没有读过车氏的小说,我们对小说中人物的想法、语言乃至说话的口吻都非常熟悉,因为见过,听过,是另一种的耳濡目染。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锋,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针对两件事:一是车氏的乌托邦思想,二是欧洲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这两者是因果关系:车氏的乌托邦来源于欧洲的现代性体系,是这个体系的延伸。乌托邦和现代体系都以某种理性为其骄傲,对人性的理解却很贫乏。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追问的正是:什么是人性?他要批评的,既是车氏乌托邦里的人性观,也是19世纪欧洲社会所认定的现代人性观。这种人性观既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又是乌托邦的。
从当代西方文论的角度评价陀氏和车氏之争,毋宁说这是发生在19世纪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后现代性也被称为“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也就是说这是与现代性体系相对位的另一种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地下室手记》是后现代思辨的先驱之一,虽然当时并没有“后现代性”这个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智慧,是他看到了车氏人性观和社会观之所以错,根源是启蒙运动产生的自然机器观或自然神论。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性体系当然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体系之所以为体系,因为它永远重复自己的真理,这样启蒙就变成了“启蒙的讹诈”,(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福柯指出启蒙的双重性时已经是20世纪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1860年代的俄罗斯,那时的现代性体系势头强大,他面对体系却表现出超常的勇气和智慧。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了“新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塑造了“地下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物原型,从中已能窥见两人的分歧。
作为“新人”思潮的灵魂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怎么办》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部小说冗长而情节松散,由拉赫美托夫、薇拉、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等一批“新人”榜样式的生活组成。这些“新人”都是道德楷模,他们正义凛然,充满乐观和理想。然而“新人”们的言行又都缺失了真实可信的心理基础,让人感觉他们是车氏的自然观、人性观和现代乌托邦观点的诠释。
小说中有这么一个“碰撞”事件:“新人”罗普霍夫某一天在彼得堡街头遇上一位有身份的人迎面而来,对方并不让路,因为在彼得堡谁给谁让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的潜规则。罗普霍夫是个地位低微的人,但是,作为“新人”他要挑战彼得堡的让路规则。于是他毫无顾忌撞了上去,还把这个上层人物提起来搁在水沟里,好好羞辱了对方一顿。这一段描写初看是痛快淋漓,继而就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小人物面对彼得堡的权力法则,会轻松到没有一点内心的冲突吗?像这样缺乏心理基础的描写,见于《怎么办》中所有的“新人”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新人”,却略去了人物的内心冲突、心理基础,抹去了人性的真实,也违背了文学虚构应该遵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法则(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的lawS of probability and necessity)。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些“高、大、全”的人物。“高、大、全”意味着后面还有一个字:假。罗普霍夫,假,其“新”也就没有根基。
地下人和“新人”最大的不同,是他曲折的心理过程全都呈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地下人,或幻想联翩,或真心忏悔,或幽默机智,或一筹莫展,表露的是生活中、历史中的多面的人性。
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罗普霍夫,《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也描写一个“碰撞”事件。有一次,地下人在酒吧里遭到一个军官轻视。他觉得忍无可忍,为了尊严和平等决心找机会在路上和军官相撞。就不甘受辱这一点,地下人和罗普霍夫是一致的,但除此而外,他们完全不同。有意和地位高的人在路上相撞,等于主动反击权力法则,在当时的彼得堡谈何容易。为了现实中的各种“谈何容易”,地下人苦思冥想,心里挣扎激烈,制定和放弃各种的幻想计划,曲折迂回长达数年,甚至于自己病倒,发烧,说胡话。最后,就在他放弃了计划的那一天,他在涅瓦大街上无意间和军官相撞。这样一段近乎夸张而又真实幽默的“碰撞事件”,揭示的是当时俄罗斯现实中的人性有哪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可任意杜撰。在陀氏和车氏之前,果戈理已经针对这些可能性做了文学尝试。基于对彼得堡自相矛盾的现代化的思考,果戈理把幻想和行动的冲突作为小人物的基本特征。地下人来自果戈理的小人物,但是比果戈理的小人物心理层次更深入。地下人的生病、发烧、说胡话、好幻想,要比“高、大、全”的“新人”可信可爱,因为他从19世纪的彼得堡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个人物,为的就是请车尔尼雪夫斯基们从空中楼阁下来,扎扎实实脚踏在彼得堡的街上。这是个文学问题,又不仅仅是文学问题。
地下室在彼得堡市区边沿一条不显眼的街上一座不显眼的房子里,地下人在昏暗的灯下伏案疾书,连贯成句成段,我们读出声来,就听见地下人心里的声音,那声调疲惫,却亢奋。他(小说中的“我”)不是对我们说话,而是讲给特定的听众,他称之为“你们”、“先生们”。“先生们”不在场,听不到他们说话,不过地下人一再模拟他们的话,重复他们的观点,很快就能猜出“先生们”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们。
《地下室手记》是中篇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下”,时间是“现在”(1860年代),四十岁的地下人随兴所至,有答有问,直指“先生们”的理性体系。这一部分有心理,也有许多论辩。第二部份“关于湿漉漉的雪”主要是故事叙述。地下人讲述大约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丽莎之爱。这一部分里,地下人吐露他苦闷的根由,也间接评判“先生们”的理论。读完第二部分后再读第一部分,读者可以体味地下人的心理经历同他的观点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这样,一场震撼现代思想史的论战便不是抽象的空泛之谈,而是引人入胜的现身说法。
地下人的直接寓意就是:上面的社会不把他的意见当回事,在“正常”情况下他没有说话的渠道;地下人于是写手记,希望他的声音有机会被听到;他是低姿态,从地板的裂缝对上面的“先生们”讲话。另外,面对现代体系的宏大叙述,地下人的叙述看似纤弱,而他偏偏以弱攻强,以小抗大,他甚至将自己最大的弱点在小说第二节丽莎之爱中和盘托出。读过《地下室手记》的人都知道,这人性中的最弱一环最感人肺腑,反而是小说最强的一环。
车尔尼雪夫斯基设想理性是人性的根本,他的理性观是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优先、理性至上立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理性是不受欲望和情绪等杂音干扰的逻辑思维,这和柏拉图将灵魂和肉体分开的哲学是一致的。从尼采开始到当代的西方思辨理论,都质疑这种排除意志、欲望、情绪的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19世纪对这种理性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一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理性,是非理性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反对理性。他的看法(也是地下人的看法)是:人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是人同时有欲望、冲动和意志力,而且往往先服从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所以人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理性行为(incapable of sustained rational behaviors)。地下人说:
您看,先生们,理性嘛,先生们,是极好的一件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理性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功能,然而意志力是所有的生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体现了人的所有生命力,包括理性,也包括所有的冲动。(Dostoevsky:25)
理性是逻辑连贯的思考和叙述;理性是必要的。但是,促使人进行理性思考和叙述的动力是某种欲望。理性优先论者说理性是客观的,其实是掩盖理性是由欲望驱使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抽象的理性、纯粹的理性。他在《冬天所记夏天的印象》里这样写:“抽象的逻辑不适用于人类,只有伊凡的理性,彼得的理性,居斯塔夫的理性,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理性,那只是18世纪毫无根据的空想而已。”(陀思妥耶夫斯:286)同样,以理性优先的眼光界定人性,等于将人性与抽象概念等同,必然无视欲望、冲动和意志力才是人的个性。地下人的复杂性格和“高、大、全”的“新人”对照,反映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人性观上的分歧。
和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一样,地下人是彼得堡灰色社会氛围里的求生者。社会地位的卑微、长期的地下室生活使他自卑,犹豫不决。他又不同于果戈理的小人物:他阅读甚广,智慧不凡,论辩机智,是社会底层的思想家。地下人极有自尊,对自己的思辨能力很有信心。可是他又很自卑。自尊和自卑使地下人常常自相矛盾。陀氏在小说结束时称他为“自相矛盾的人”(paradoxalist)。地下人的自相矛盾也表现在他的“过度的意识感”(hyperconsciousness)上。换言之,他想的过多。“过度的意识感”如双刃剑,正面:他比别人多想一步或几步,见常人不见,且善修辞,通逻辑,旁征博引(他的语言有互为文本性),聪明过人。侧面:想的太多则无法行动,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是一种病态。地下人毫不掩饰:“我向你们发誓,先生们,过度的意识感是个病,实实在在是个病。”(Dostoevsky:6)地下人的病,还在于不会与他人相处,心里渴望爱,但是不会爱。自虐和虐他倾向的并存阻碍爱的能力。不会爱,是地下人的致命伤。总之,地下人种种的弱点和曲折的心理剧情,使他成为人性的活标本。
我们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弱攻强、以小抗大的文学策略反而能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争论中胜出,原因在于他对人性的看法更深刻。
陀氏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代的思辨理论使我们能深层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地下人叙述风格。一个是巴赫金的理论。巴赫金认为,陀氏创造了对话性话语(dialogism),与单一性话语形成反差。比如地下人说的话是包括了别人立场的话语,是和他人互动的话语。当然地下人怕别人看低他,常把别人可能有的负面印象先讲出来。《手记》一开始地下人就说:“我是个病人……我是个有恶意的人。”这正是基于他的自卑,基于对上层社会可能这样说他的一种预测。在对话性话语中,“我”的差异和他人的差异相互联系,探讨的道理是具体的理,活理。相反,在单一性话语(monologism)里,理却是单一、绝对的理,即死理。对话性文体也体现了对话思维,即一个声音有多重性,多个声音呈复合结构。巴赫金称之为多声部文体、复调文体。复调文体的哲学涵义是: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包含了感性、理性、欲念、想象,而以意志力为综合特征。意志力以多种声音说话,抽象理性以单一的声音说话,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分歧。
德里达的解构也和地下人的叙述方式紧密相关。解构哲学有许多内容,我们说关键的一点:地下人对“先生们”的反驳并不是他提出了和“先生们”相对的一整套反论,而是他能“游戏”(freeplay)一番对方的词汇和逻辑,使人看到“先生们”体系的另一面。正所谓借力使力。基本策略:指出对方用的能指(signifier)和对方宣称的所指(signified)并不相等。换言之,对方说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未必就是那个意思,地下人挑战对方所坚持的所指,同时使能指活起来,呈现多义,以此“游戏”对方那个所谓的完整体系,使之变为开放性的、可以讨论的话语。这恰好是解构的基本内容。正是这种解构式游戏,使得地下人和他的作者一样具有“双重视力”,他能见常人之见,又能见常人所不见。(冯川:130—34)地下人熟谙逻辑,却时时指出逻辑理性的盲点,因而能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智慧高出单有理性视力的对手。
对话性话语和解构式游戏使《地下室手记》可以多点切入人性:从“先生们”的逻辑和比喻切入,从地下人和“先生们”对话的张力中玩味,也从他自己的矛盾人性中领悟。多点切入,等于变换视角来观察和思维,尼采称之为perspectivism。
三、驳乌托邦和现代体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样设想“未来”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俄罗斯将会把大片的草原变成可耕地(当时不会想到这可能是沙尘暴的起源),将会用玻璃和钢筋造成水晶宫(就像19世纪伦敦的Crystal Palace),电的秘密将被揭示而造福人类(和今天的科技发展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但是车氏是在1863年对科技做此预言的)。车氏还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艺术繁荣。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完美的世界由乐观向上、富有理性的男女组成,他们没有私利,因为他们可以在普遍的善(universal good)中找到自己的利益和福祉。这个梦“崇高而美丽”(地下人用语:sublime and beautiful),后来为之献身的人期然而不然,不期然而然了,也就不明白为何怨而怨,为何悔而悔。所以仔细研讨这个乌托邦颇有必要。
在上面的乌托邦蓝图中,“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车氏的人性观。这个人性观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科学立法的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 as codified by science),二是理想地反映了这些规律的“人”。这两个部分都不是车氏的独创,是他借来的,是源自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
第一部分,以科学为标志的自然规律(或法则)。车氏所说的“自然规律”来自以经典机械论(classical mechanics)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观。根据这个科学观,宇宙被看作一部机器,机器的各部件由因果链组合而成。宇宙或自然界既然是一部机器,它就一定遵循可预见的客观规律/法则(predictable and objective laws)运行。“科学”是什么?“科学”为人提供了手段和途径,让人可以“发现”这些规律,并用以改造文化和社会。依照这种科学理性,科学和自然规律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经常说的“自然规律”和“科学”也是这样的。人们自然会问: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个问题暂且置后,因为地下人有他的回答。
现代科学观其实是现代版的宗教。请看:只要把上帝摆在现代科学观的中心位置,这种科学观就变成了自然神论(Deism)。宇宙既然是一部机器,那么是谁创造并启动这部机器的?答:上帝。不过上帝并不负责机器的日常运作,只在机器出现大故障时才出面干预。依此推论,因为宇宙遵循客观规律运行,宇宙的秩序也就是理性的,上帝因此是超级数学家、超级工程师,为科学理性的最高象征。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试图发现自然界所隐藏的规律和秩序,也就是去发现上帝这个超级数学家的思路。牛顿正是这种机械论加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
现代化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秩序,却又把上帝科学化、科学上帝化了。人类匍匐在科学面前膜礼顶拜,新宗教名曰:“科学主义”(scientificism)。
车氏人性观的第二部分认为,以科学为准绳的自然规律(或法则)必然与人性是一致的。这也是现代思想体系的观点,即用来理解自然世界的科学理性和机械主义方法,也必须用于对人性、人类社会生活的解释。这样的人性观听起来逻辑性严密:自然是一部机器,宇宙秩序是理性的,科学是理性的;人要发现宇宙的自然规律、用科学规律来改善人的生存状况,人必须是理性的。再加一句:理性的人代表了自然规律。姑且不论自然是不是一部机器,试问:这样和自然机器的规律完全统一的“人”有吗?车尔尼雪夫斯基借用英国功利主义(“体系化的精神”在19世纪的衍生思想)想说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性是普世真理。
功利哲学认为,人和所有的自然界动物一样,纯粹根据自己的愉快和痛苦来决定行为。做合乎理性的事,可带来愉快,谓之“善”。做不合乎理性的事,造成痛苦,谓之“恶”。人是理性的,只要运用理性,必然选择“善”不选择“恶”,必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趋乐避苦。因此,理性的人是乐观的、愉快的。如果一个人受苦,那是他的无知所致。总之,人只要运用理性,一定可以幸福愉快。功利主义的口号是:“做对你有用的选择。”车尔尼雪夫斯基由此推断出理想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用上述功利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追寻真正符合自己的利益,那就是集体的利益,可以造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好处”,形成快乐的完美社会,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如果有人问一个人追寻的“善”或快乐,会不会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造成痛苦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一个人追寻的自我利益是基于理性的,他不会对别人造成痛苦。一个人如果抵触共同的利益,也许可逞一时之快,最终要遭受最大的痛苦。为了保护理性,共同的利益由法律保护。法律是理性的,理性的人因为守法,所以他的作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法律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假设所有的法律都代表着“善”是不对的。比如,曾经保护蓄奴制和种族隔离的美国法律也是按照某些人的某种理性制定的,那不是“善”,美国人经过了漫长和艰苦的争斗才推翻这样的恶法。卡夫卡常说反话,他曾经说:“善,无非是法律(法则)所言。”
从前面对车氏理论的简述中不难看出,其中的观念和价值已经渗透到现代的秩序,留在现代人的无意识里,在现代人的生活和判断中继续发生作用。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的方式近乎朴素。他是通过地下人、彼得堡的一个小人物做出回答的,再具体说,是通过地下人的对话性话语和解构式游戏提出反驳的。地下室里昏暗,思想的亮度却在地下人那里,他对准“先生们”的要害问题穷追不舍。他再追问的问题是:自然界是理性的吗?用“自然规律”可以解释人的欲望、人的心理、人的痛苦或快乐吗?现代科学等于人性吗?人是纯理性的动物吗?人性是什么?无论是问还是答,地下人都是以能指破对方所指的高手。
《手记》一开始,地下人就出言惊人:“我极其迷信,这么说吧,迷信到了足以尊重医学的地步。(我受过足够的教育,本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迷信。)……”好像是傻话,其实一点不傻。三复斯言,方可体味其中的“游戏”意味。其一,他抢先说出“先生们”对他的看法。您是科学的呀,那我当然是迷信的那一类。依此推理:您乐观,那是因为您有知识呀,我这么苦闷,当然是因为无知了。不麻烦您给我扣帽子了,我自己戴上给您瞧瞧。二复斯言:您不是说人不遵循理性必将是迷信的、必将回到科学前的迷信时代吗?我懂一些科学(如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照理我不应该迷信。可是,我迷信。我为什么迷信呢?因为我质疑你们的理性,你们认为这样质疑就是迷信。姑且同意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容易迷信,可是掌握了相当科学知识、受过相当教育的地下人,如果他质疑现代科学观,质疑理性,是因为他迷信吗?三复斯言:另一个想法呼之欲出:对现代科学观和理性深信不疑,会不会才是新的迷信?这里是地下室,是彼得堡的底层,地下人是假想着他有机会对“先生们”说话,自然可以任着性子说气话、反话、俏皮话。
“先生们”说,理性的人能按照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采取正确行动,这件事就像二二得四的乘法那么简单。地下人戏称这样的人是:“自然人”、“合乎法则的人”、“行动人”。他把“自然人”比作一头牛,大吼一声冲向前去(喻其敢于行动),但是在一堵石墙面前猛牛止步了。这石墙是什么?“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数学的结论”,地下人不无反讽地说。根据力学原理,头撞南墙要撞出个大包的。所以,牛也好,“自然人”也好,站在自然规律的石墙面前无计可施。地下人把自己比作一只老鼠,可以想见,老鼠碰到自然规律的石墙会绕过去,沿着墙边跑,见到墙上有个洞还可以钻进去。对付自然规律,老鼠机智得多,灵活得多。初看,理性优先的“先生们”面对“自然”气壮如牛,何等乐观;而地下人见了“自然”却胆小如鼠,岂不悲哀。但是,“牛”的乐观,恰恰排斥了生命意识中的最基本的悲观,而人类真正的智慧则是从这悲观中产生。
有“过度的意识感”的地下人争辩:二二得四是数学的法则,不是生命的法则。我们替他说下去:人类(包括在科学活动中)和自然规律打交道,时时在想:我怎么才能二二得五、得六?这是人性。但是,二二得三、得二、得零的事却是常见的,因为自然规律常让人类吃亏。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认为人用理性计算自然这笔“交易”完全平等,那是一厢情愿。理性的计算,算的是人自己的账,得了些蝇头微利,沾沾自喜;过后再细算,才知是亏了,亏大了。气壮如牛的若能顿觉自己愚笨如牛,那是大彻大悟。不过,整体看人类还是不顾一切地撞向南墙。
牛和鼠的能指再发挥一下,倒是可用在地下人自己身上。他在第二部分的碰撞和聚会两个事件里就是一头牛,不过那时他面对的是社会法则,不是自然法则。说得更准确一些,他面对社会法则时先是胆小如鼠(他属于彼得堡常被强权欺负的群体),然后变成牛,宁愿头上撞出包来也要维护他的尊严。这个先鼠后牛的地下人,却有可爱之处。
据说“自然人”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理性就能趋乐避苦,真是如此吗?地下人以牙痛做比喻,他说:牙痛可有不少的乐趣,痛起来的呻吟各有千秋。“呻吟表达的首先是你的痛毫无目的……当然,你对自然界整个的法律系统蔑视地吐口水,可是你照样受苦,而大自然却不受苦。”你看,牙痛不也是自然规律吗?您再理性,得到的还是和呻吟有关的那些乐趣。“先生们,我请求你们,有时不妨听一听19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牙痛的时候是怎样呻吟的……他可不是像农村的大老粗那样呻吟,而是像受了进步和欧洲文明影响的人那样在呻吟呢。”讽刺得深刻而且准确。
“自然人”自以为敢于行动,所以又是“行动人”。地下人这样回应:
我重复一遍,我强调地重复一遍:所有立即就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活跃,恰恰是因为他们笨,智商有限。怎么解释呢?这样解释:由于他们智商有限,他们把眼下的、次要的成因误认为主要成因,而且比其他人更快、更容易相信他们找到了采取行动的无可争议的基础,这使得他们挺自信。(Dostoevsky:13)
将地下人的话略加翻译、推衍:“自然人”乐观,其实是只问“次要成因”(secondary cause)得出的盲目乐观,而没有细想“根本成因”(Primary cause)。广义讲,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通常用“根本成因”指宇宙的“秩序”由哪里来,“次要成因”则指人类创造的“秩序”。人的理性也好、科学也好,只限于人利用自然为自己创造的那些成果。我们不必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指称宇宙的“秩序”为神的创造而万事大吉(如阿奎诺的神学),“根本成因”无非是人类以外的宇宙,或称宇宙意志。科学、理性对人类秩序中的各种因果是有所解释的(因为人是在解释自然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秩序的),换言之,人类秩序中的各种谜都有谜底。但是,宇宙并非为人而设,宇宙意志是没有谜底的谜。
再推衍下去,地下人的这一段也指出了现代体系所依赖的“科学理性”的局限。“科学理性”又称“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指那种依赖可计算性的逻辑的推理。工具理性的用处不少,它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所以它为现代社会所青睐,助长重物质实效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然而,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而且导致对美学思维的排斥、对人类生存所需的更深远的智慧的排斥。过于相信可计算的逻辑其实是人类的骄傲自大。许多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展望基于这样的想法:人的逻辑计算必然符合自然规律,人算等于天算。越来越多的事实是:人算不把天算放在眼里的时候,天算不动声色地惩罚人算。
因为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认为人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认为人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同时有欲望、冲动和意志力,而且往往先服从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所以人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理性行为。相比之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性观和依此设想的社会与此大相径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设想是:一个完美的体系里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必定一致,而且什么对个人“有利”是可以计算的。地下人回应说:“你们笑;笑吧,先生们,只要你们能回答我的问题:什么对人有利是可以完全确定地计算出来的吗?”对地下人而言,如果是以欲望和意志力思考人性,个性的差异才是人性,车氏的乌托邦社会并没有设想如何容纳个性差异。地下人问:如果你列出的利益清单符合你的利益,也符合我的利益,却遭到他的反对,我们将如何对他?去消灭他吗?地下人的意思很清楚:当然不可以。
我们从历史中看到,运用理性设计某个秩序的人多半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的欲望或愿望合理化,他所援引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侵犯另一部分人的借口。文明经常因践踏人性成为野蛮,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人太喜欢体系和抽象的推算,以至于他可以任意扭曲真相,可以为了证明他的逻辑合理而否定他的所见所闻。”(Dostoevsky:21)拿破仑一世和三世、征服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占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鲁士,哪一家不是以理性和有利于人类为名,结果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用最快乐的方法说,血流得像香槟酒一样”。(Dostoevsky:21)
在《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地下人特意提到英国人巴克尔(H.T.Buckle)的历史观。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的俄文本1863年出版,是当时在彼得堡时尚的观点。巴克尔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会变得更温和、更不愿意流血,战争将会停止。巴克尔显然是理性的、浪漫的,他于是理性地、浪漫地相信“崇高和美丽”。地下人这样回答巴克尔:“你们注意到了吗,最含蓄的刽子手几乎总是最文明的绅士。”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而指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不会停止战争,只会造出更先进的杀人方法。至于杀人的方法竟然会先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看到。这未必是他的遗憾。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乌托邦找到的象征是“水晶宫”(Crystal Palace),这也是车氏乌托邦和现代思想体系的联系的证明。
现实中的水晶宫是一座钢铁结构加玻璃表面的宏大建筑,由帕科斯顿(Paxton)设计,1851年建成后作为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的展馆。从工程学的角度,上过工程学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钦佩帕科斯顿设计的水晶宫。不过,水晶宫当时是一个更大工程的象征,即英国以此向全世界(尤其是它的殖民地)炫耀大英帝国的工业、军事、经济实力。世界各地的人汇集于伦敦的水晶宫,好像在赞美现代体系的完成。陀氏在欧洲旅行时看了水晶宫,他不无讽刺地写道:这是“圣经上的某种景象,关于巴比伦的某种景象,亲眼见到启示录的天启应验成为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272)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质问的,显然不是指帕科斯顿的建筑设计,而是作为现代体系象征的水晶宫。
《怎么办》的水晶宫出现在维拉憧憬未来美景的梦里。梦里,在花香四溢的田野的尽头,在高山脚下、森林边沿,有一座宫殿耸立,那就是水晶宫。因为是在梦里,维拉和她的同伴不是向宫殿走去,而是向那里飞去;水晶宫里有欢声笑语、有泉涌的美酒、有情人间默默的香吻。够浪漫吧?还有呢,有人即席作诗曰:自然界把秘密揭示给人类,还透露了历史的规律等等。(Chernychevsky:157—58)描写维拉的梦那一段里还有“啊,大地!啊,幸福!啊,爱情!”这样的字句。真的,都在那梦里。
车氏的水晶宫和伦敦水晶宫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标志着完美无比的结构,象征着可以一劳永逸的人类秩序。
地下人问“先生们”:在您的水晶宫里能让我吐舌头吗?意思是:你用理性建构的体系能够接受人性的差异和与你不同的理性吗?体系完美到了不容置一词?没有理由怀疑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善良的愿望,更不能怀疑他的头脑一定是理性的。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许没有想到,他的理性、完美的社会,理性到了不许任何人有悲观和不满。只有鲜花、阳光和音乐的世界在现实中常常是可怕的,是噩梦的表象。
设计再周全的秩序,也不可能是终极的秩序。如果人“就此止步不前”,以为“再往前走就没有路”,那也不符合人性。地下人关于人性说的另一段话可圈可点:“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人主要是创造性的动物,注定了要自觉地朝一个目标奋斗,要致力于工程性活动;也就是说,要永远地、不停地修建新的道路,无论这些路通向哪里。”(Dostoevsky:29)。人类需要不断创造,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却永远也不要一个终结的目标。
四、结束语
在小说下篇,地下人讲述十五年前的旧事,以人性的告白、以情的隐私回应上篇“理”的诤讼。这样情理交融的结构不仅是一个文学形式,它还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既是争论也是对话。对话一定需要真诚,地下人够真诚。
我们今天读《地下室手记》的优势,是历史给了我们后见之明。两三百年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现代性、现代化是有正负两面的。所以福柯主张,进一步的启蒙应该继承启蒙的积极价值,同时拒绝“启蒙的讹诈”。
对现代性体系的批评和思辨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形成后现代、后结构的种种理论,才在西方思想界形成一定的共识。从这个共识再回头看,思想史上的几页尤其重要:尼采从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出发,颠覆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知识传统——这正是现代理性传统的源头和基础;20世纪科学思想的发展(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资讯革命),已经使牛顿式的经典机械主义科学观解体;整个的心理分析学发展史不断质疑了人性纯为理性的看法;“知识”的后现代结构提出了现代思想体系没有回答的新问题;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在20世纪后期又领引了针对“体系化的精神”的解构哲学。
在这个思想史中同样不能忘记的一页是:1864年出版的俄罗斯小说《地下室手记》。
标签: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人性论文; 科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彼得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