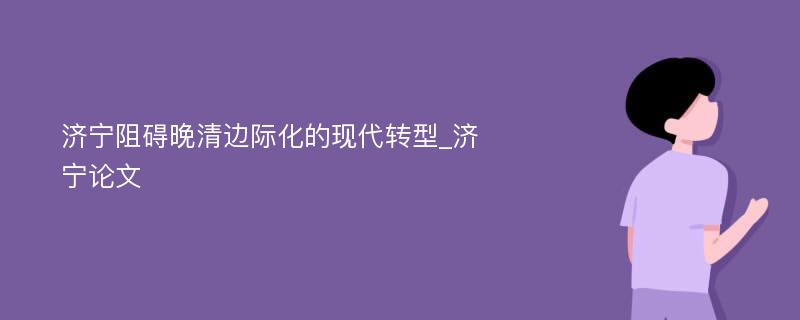
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济宁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由晚期帝制时代向早期现代转化过程中,1901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分水岭。这年7月2日,清廷颁布一道重要诏令,停止征收和转运山东、江苏、浙江等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征实物为征银。① 其实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清朝的财政运输体系就因太平天国战争瘫痪了,这种税赋折银的方式已经在长江中游各省试行,后来逐渐推广到中部和东部各地。② 1902年,清廷又诏令宣布裁撤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和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③ 至此,作为明清帝国的生命线的漕运正式谢幕。
漕运的终结首先在沿运河地区产生了严峻的后果。自15世纪初明朝重修运河以来,运河沿岸地区,特别是北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生产的商品化促发了城市化。然而,对运河沿岸的一些北方工商城市例如临清、天津和济宁来说,其崛起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几无关联;政府主导的漕运和私人的长途运输贸易直接启动了其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其持续性繁荣。④ 为了保障帝国的供给和安全,明清政府对运河倾注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严格周密的管理和监督。自19世纪中叶以来,漕运体制和运河基础设施迅速衰败,运河逐渐丧失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运河地区已不再是朝廷的中枢策略考量的对象,这是大多数北部运河地区经济败落、城镇凋零的重要原因。然而,北部运河城镇的经历不尽一致,在随后的现代转变中的机遇也各有不同,本文叙述的济宁就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案例。
在晚期帝制和近现代中国城镇史的研究领地里,学者们的兴趣点长时期集中在中国南方,如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在“走出上海”、“走出江南”的风潮中,不少学者将视野投注到北部的北京、天津,东北的长春、旅顺以及西南内陆的成都和南端的广州。具体到山东省,济南和青岛因其现代史上的角色受到了应有的关注。⑤ 相较而言,笔者所探讨的山东西南部城市济宁似乎是一个被埋没的名字。在晚期帝制时代,它曾经作为府、州和直隶州。特别是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作为直隶州,下辖嘉祥、鱼台、金乡3个县。今天,它是一个拥有10个县或县级市和2个县级区的地市级行政单位。无可置疑,在今天的山东,它的光环被省府济南、沿海城市青岛和烟台遮掩了。可是在明清时期,它是中国最重要的运河都市之一,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具有南国园林色调的文化旅游胜地,以“江北小苏州”而驰名。在明代以前,济宁或其前身任城大都是作为县一级的治所,虽久负文化古城之誉,但工商经济不彰。明朝前期运河重新修建、开通后,济宁在南北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枢纽作用,其工商经济也随之勃兴。在新旧交替、西潮东渐的变革时代,济宁开拓出一条独特的转换之路,其作为偏远内陆城市的发展,经验殊为可贵。
本文考察济宁在清代最后半个多世纪的遭遇以及转化的轨迹,通过对事实的梳理和分析,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鉴于晚期帝制时代中央政府长期依赖运河藉以维系帝国机器运转的惯性,何以在19世纪中叶以后陡然改变这一行之有效的战略?因为运河的使用促发和养育了运河流域尤其在华北平原的传统农业区的城市化,运河的式微对这些地区和城镇的后果如何,在济宁的具体情形又怎样?本文将展示,不再受到帝国政策的惠顾,济宁和北部运河城镇例如临清与天津都面临着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转换的挑战。在这一变局中各地出现不同的反应,并导向不同的现代命运。本文将集中反映济宁居民在时代大嬗变之初如何理解、回应这种变化和他们努力的初步结果;通过对在地方政治经济生活里若干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和现象的回顾并与其他北部运河城市比较,论证济宁开明的士绅精英群体的积极作为有效地抑制了城市的衰退。
一、大运河的衰败与济宁的困境
大运河的衰落不是一件突发的事情。清廷在1901—1902年的诏令不过最终宣告了运河作为官方漕粮和其他贡物的运输通道的结束。更重要的是,清廷逐步减少并最终放弃依赖运河的战略方针的过程,与在全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紧密相关。漕运曾在明清帝国政务中占据十分紧要的位置,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央政府作出一系列变应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济宁在内的沿运河地区。
(一)运河迅速衰败的原因
尽管存在体制上的弊病,运河在明代和清代的大多数时期运转基本正常。导致19世纪中叶以来运河衰败的有战争、动乱、环境恶化和漕粮官运方式的策略调整等诸多盘根错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首先,社会动荡使运河瘫痪。运河的命运系于国家政权的稳定,运河的正常运行也反过来支撑着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两者互为因果。在帝国的稳定时期,运河、黄河得到有效治理。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运河、黄河水利系统曾一度被废置。晚清此起彼伏的战乱使中央权力萎缩,社会失序,运河、黄河水利系统被严重冲击。太平天国极大地破坏了作为漕粮和田赋主要来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和生活;1853—1855年的北伐摧毁了包括临清在内的众多运河工商城镇,并点燃了此起彼伏的北方战火。太平天国平息后,捻军和其他暴动武装继续蹂躏大片北部运河和黄河下游地区。⑥
其次,生态环境的歧变严重瓦解了运河的运输和水利系统。北部运河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黄河水患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山东境内运河和黄河的基础水利工程要通盘考虑。1816年英国阿莫斯特勋爵(Lord Amherst)使团的随员克拉克·阿贝尔(Clarke Abel)记载了他对运河基础设施破败的匆匆一瞥,这与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二十余年前在运河航行中目睹的景象迥然不同:“在上次使团的观察里,运河的筑堤是由‘切成大块的大理石以铁夹加固而成。’今天,运道安然高于两岸地势的景观被洪水冲走了。”⑦该世纪中叶时情况更加糟糕。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运河、黄河水利工程中枢所在的济宁地区危机频繁,而乍起的战祸又加重了天灾的破坏力。
但运河运输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修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运河北部地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生态系统的改变——黄河因河道北移直接冲入运河的现状直接导致漕运的骤减。明清时期,黄河经常在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泛滥成灾,威胁运河。19世纪50年代初,固定在山东西南部长达700余年的黄河河道开始北移。至1855年,黄河终于一改从山东南部进入淮河水系入海的历史,经山东北部东流汇入渤海湾。尽管在政府内部发生过是否控制黄河移动的激烈争论,最后还是放弃了使黄河重返淮河水系的企图。⑧ 从此,黄河下游流经山东北部的局势延续至今,尽管它是在1875年以后才彻底固定在现今的河床上的。⑨ 这一大变化摧毁了庞大繁复的运河——黄河综合水利系统,造成济宁以北运河交通的瘫痪。⑩
除了简单的救灾赈饥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认真、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正像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所指出的,清廷正精疲力竭地与太平军和其他暴动者作战,“无暇、无钱来筑坝固堤以保护运河、黄河地区的农村”。(11) 1860年代末战事大体平息后,清廷尝试重开运道。运河漕运一度恢复,并断断续续地延至该世纪末,但规模大大缩小,漕运之外的其他运输和贸易也风光不再。1870年秋来自山东的一封奏折提到,因为黄河改道,运河航行艰难,到达京畿的漕船无法驶回。(12) 几个月后,同治帝要求山东官员紧急疏浚河道。(13) 但清廷一度想完全恢复漕运的设想由于各省封疆大吏的反对而打消了。因为资金短缺和社会动荡,沿运地方政府只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星工作而已。
政府不再关注运河和黄河水利网络,山东西部地区洪灾频仍。济宁地区的生态系统随着运河基础设施和航运的败落而恶化。大卫·巴克指出济宁——临清间航运特别困难,运河水位在两地落差之大造成1855年至1950年间的多数时期运河被堵塞、阻滞。(14) 周锡瑞认为1880年后山东西部的运河危机变得越来越险恶:淤泥不断冲积,升高河床,几乎每年都是洪水泛滥成灾。(15) 在中央权威更加衰微的民国时期,洪灾的后果更具有毁灭性。(16) 这些运河地区失去了在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战略重要性,其厄运已非中央政府的心头之痛。
面对国库的空匮、战乱对帝国粮仓制度的摧毁、货币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国经济中心的地理转移等新情况,清廷无法顾及庞大复杂的漕运系统工程。(17) 运河的颓势已无法挽回,清廷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雇用商船海运漕粮的设想出笼了。鉴于运河航运系统错综复杂,加之吏治腐败,河运成本极高,清中叶就有改由海运之议。同时,粮食的商品化发展和商人长途贩运的高效率对臃肿的漕运机制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海运于是在19世纪上半叶就被数次讨论和试行过。(18) 太平军占据南方各省、切断运河交通线后,漕粮海运便成了切实可行的应急之策。激烈争吵和深入探讨之后,1872年李鸿章关于海运取代漕运的奏请得到朝廷的批准。(19) 太平天国后期,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清廷很难恢复漕粮实物征收和转运体制。对漕粮过度榨取的普遍不满迫使清廷减轻税额;同时由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商品化,税粮折银的呼吁愈来愈强烈。李鸿章在1865年的一件奏章中指出,若回归税粮征实会加重农民负荷,修复毁坏的漕船和运道以及重新征召和训练运军、运工已非当时政府所能承担。(20) 基于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的共识,各省督抚大都主张田赋和漕粮折征银钱的办法。
从19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开始从内地的水利、水运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抽身出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废止漕粮的征收和转运。对山东西部沿运各地区来说,尽管日常的运道简单维护在和平时期大体上能持续下来,可缺少了原先来自中央政府的充足资金,地方政府无力有效地保证水源、控制水势,城乡经济迅速地走下坡路。
(二)大剧变中的济宁
19世纪下半叶,济宁没有直接遭受战争和动乱冲荡。凭据其坚固的城墙,政府军队和地方民兵有效抵御了太平军、捻军和其他武力的进犯。当然,作为全国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军事基地,济宁也承受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地方财源枯竭,无力从事大规模基础水利建设。如其他北方运河城市一样,运河的凋敝严重影响了济宁的生存和发展。
政府退出运河事务,时人有不同的观察和评价。因为北部运河地区担负更多的劳役,与此相对应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缴纳更重的漕粮和田赋;而政府的投入更多的是用于漕粮转运本身,并不顾惜沿河地区的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一些济宁人士甚至感到漕运废止对地方发展来说利大于弊。1905年《济宁州乡土志》的编纂者就讲到愈来愈少的权贵莅临济宁,官府可以节省一大笔用于接待的开销;往来运船递减,强制性力役也随之松缓。(21) 但地方精英的主要忧患则是家乡在国家整体战略地位的丧失,依赖运河取得辉煌的光景一去不返。随着运河的衰落,靠运输谋生的人口大量失业,济宁和大多北部运河区域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1927年私修方志《济宁直隶州拟稿》的作者李继樟这样总结运河起落对济宁的影响:“漕运既废,铁路贯通,此后运河兴替关乎全国微矣,而于济宁则犹切。盖得名、建治所由来,亦湮水沈田所独受也。地当南旺、昭阳两湖之间,汶、洸、洙、泗、菏、济诸水皆汇境内,为南下之尾闾。故河之兴也,受益最广;其废也,受害亦深。会通河成,南北通津,舟楫往复,商贩运输,丁壮庸食资繁庶者五百余年。咸丰后,寇起河决,运废船停,南来水手之不能归者聚哭河干,折卖船料以自治,壮者多流为捻匪。而东南近水之地,积水莫泄漏,西岸陆沉,济宁始受运河之害。同治后勉强复行河运,其时下游运河已堤坏,渠溢,不分水陆。南旺、马场两湖反以黄河而灌,渐淤成田。国家既无资重督修复,河工积弊已深,反藉口漕运,误徇己便,弗恤民艰。”(22)
运河衰落后,与运河相关的其他水利设施多被废弃,这造成了山东西部黄河、运河、湖泊聚集地区生态系统的严重恶化。(23) 济宁士绅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竭力游说官府重视当地的水利工程,于是在1891年东河衙门勉力拨出一部分经费,特设“河防局”,以应付紧急情况。(24)
不过相对而言,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运地区。尽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中断,济宁段的运河水资源还是十分丰富,足以支持局部性船运。事实上,济宁南抵江苏北部的运道一直畅通。因此,虽然济宁的地方经济失去了广阔延展的契机,但尚可以在相当的区域范围内往来循环。在1912年南北铁路大动脉及现代公路出现前,济宁段的运河仍是货运最主要的通道。
(三)帝国区域战略部署的变更及其影响
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里,漕粮征收、运河运输制度的衰亡是与清帝国的衰亡连在一起的。清廷竭力尝试不同的策略以在“内忧”和“外患”中苟延残喘,而正是与“外患”相关的空前变化的形势和机遇推动清廷逐步放弃曾作为帝国生命线的漕运。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关注点已经从内地转移到现代实业肇始的沿海及首都。其救亡图存的“准重商主义逻辑”(quasi-mercantilist logic)压倒了先前以富庶地区资助贫瘠地区为宗旨的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结构的维护承诺。治水预算被大大消减,省出来的款项用于偿还借贷、战争赔款、修筑铁路以及训练新军等“现代化”项目。彭慕兰认为,“对国际竞争的新的聚焦促使清廷从他传统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职责中退却:在包括黄河—运河地区在内的对生存和社会再生产关系重大的生态基础脆弱的区域予以财政资助和生态问题管理的监督”。(25) 因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原先作为政府投资和其他特殊政策的受惠者的全国核心经济区之一的内陆运河地区,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丧失使得北部运河地区在天灾人祸面前比以前更加脆弱。
《济宁州乡土志》的编纂者从现代全国格局的广阔视野讨论了在济宁发生的政治、经济巨变:
就东省而论,刘公岛、胶州湾租借于他族,而地势之厄塞全殊。然则济宁一邑,就使亢父之险依然,其扼西南而捍东北者安在也?加以漕运改途,河督裁撤,而济宁之运路荒,商贾之货路亦隘。于是向之所谓转输咽喉之要津者,亦失其所恃。(26)
随着受西方启引的新工商经济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崛起,运河为枢纽的经济范式被打破。与内地多数城市的衰退相对应,沿海城市迅速成长。烟台、青岛、龙口的开埠带动起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使之在山东省独占鳌头,并成为全国新的经济中心之一,内陆的运河地区则成了偏远的腹地。彭慕兰观察到:山东西部旧有的系于运河的经济纽带松落,进而有向沿海城市联系并汇入其市场体系的趋势。然而,被帝国政治经济部署所支配的旧经济格局的打破,并不必然在某些内陆地区被新式市场经济体系所成功替换,中断和裂变也是转型中的常态。彭慕兰认为山东西北部的运河地区比较容易地进入受沿海港口城市所牵引的华北平原的现代市场网络。(27) 周锡瑞把清末山东划分为6个社会经济区域,将富有活力的胶东半岛与迟钝无力的西部内地作了鲜明对照。但他认为济宁地区是个例外,因为该地区呈现出与沿海地区颉颃的竞争力。(28) 从总体上看,历史上以运河为贸易通道、向南方取向的山东西部经济,在从东部袭来的大浪潮下,正在发生结构与取向的变迁。山东省明清时期以济宁、临清、西部运河带为中枢的中心—腹地的层级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逆转。济宁不可避免地被排列到一个边缘腹地位置。济宁原来在全国作为一个经济枢纽的地位荡然殆失,其对山东西南部的经济辐射力也大不如前。正因为缺少一个可以整合、协调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山东西南部在东来以沿海为基地的现代经济的结构和环境里,变得支离破碎。
二、济宁阻滞边缘化、调整经济结构和取向的实践
边缘化成为北部运河区域的共同命运。但各地在时代巨变中做出的不同反应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济宁在全国市场循环体系中的没落无疑会导致经济倒退,然而在清末二十余年里,士绅、富商等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员合力制止这一倒退趋势,并开启了地方经济的现代转型。
(一)政府主导现代事业的开端
洋务运动阶段,山东的现代化建设是由地方政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主办的。因为山东西部在全国政务序列中不再具有战略角色,因此仅有零散的现代设施兴建起来。1881年,山东第一个电报局在济宁建立,以便于应付黄河和运河紧急情况的通讯之需。济宁的电信局则出现于1899年。(29)
庚子之变后,山东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在1900—1911年间先后八任巡抚的任期内,山东经历了激烈的变革。大多数巡抚,尤其是于1900—1901年在任的袁世凯,卓有成效地推行各种改革。(30) 1900年,以1894年成立的保甲局为基础,济宁在全州内(本州和附属3县)成立了巡警武装,标志着现代警察制度的创立。济宁在明清多数时期设有管理运河、治理黄河的机构,还是卫、所的驻地,这些机构互不统属,权能重叠交叉,不利地方统筹。1902年东河衙门裁撤后,济宁直隶州官员在境内施政的余地变大。1905—1907年担任知州的邓际昌(1856—1930)在济宁的革新成就赢得了盛誉。1906年,他开始推出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先后建立了一所师范学校、一所职业培训所、一所孤儿院、一所农校和政府雇员培训中心,还在监狱举办了就业培训项目。(31) 值得一提的是,邓际昌后来很快地适应了民国初年的政局演变。1912年他东调登州担任军职,两年后被提升为省政务厅厅长,1915年又重返济宁,担任山东4个道之一的、管辖南部和西南25个县的济宁道道尹,直到1922年退休。他在清末民初的勤勉工作、锐意革新带来的崇高威望和行政的高超技巧,降低了乱世对济宁的损害程度。(32)
(二)地方回应的策略和努力
大约从明中叶起,城市士绅在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公共空间的活跃是济宁地方政治生态极为亮丽的特色,有别于山东抑或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城市。(33) 但从清初之后,士绅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在全国范围内都趋于沉寂,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许多学者都指出太平天国事件的一个副产品是战争中获得军政权力的地方士绅所代表的地方主义的兴起,他们充分运用刚刚获得的权势在地方治安、社会救济、教育改革、工商实业和地方自治等广泛的领域雄心勃勃地一展宏图。于是,以士绅社会为内涵的公共空间迅速扩张,国家权力日渐萎缩。(34) 在济宁,地方主义的活跃发生在清末新政和民初兴办实业和社会、政治革新时期。
原来的名胜古迹、亭阁园林与运河一起成了明日黄花,济宁现代化事业的重心不再是运河景点,而是经济领域。士绅精英们认识到正在兴起的新式运输业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其时德国凭借特权于1904年修建了连接青岛—济南的长达394公里的胶济铁路,便利了山东境内沿海与内地的联系。(35) 济宁士绅期待自己的城市能跻身现代交通网络,投身于作为现代化经济基础设施的铁路和现代公路系统的建设。(36)
发生在1907—1909年的“争路风波”在济宁现代转型过程中最引人注目。从天津到浦口的长达1009公里的津浦铁路在1907年7月动工,1911年11月竣工。这一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由清政府从英国和美国贷款,雇用德国工程师修筑,有420公里的路段经过山东境内。(37) 早在工程筹划阶段,围绕在山东西部路线选址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德国由于享有开采沿铁路矿产的特权,迫使线路经过矿脉丰富的曲阜、滋阳城(兖州府府治)和邹县一带,这个方案忽略了长期作为区域中心的济宁。从1907年开始,济宁士绅和本籍京官不懈努力,争取主干线得以从济宁穿过。地方精英们认为铁路修建的唯一目的是发展实业,因此必须经过人丁兴旺、交通畅达、工商兴隆的都市地区,济宁则是当仁不让。几次上书不果后,他们在1908年春天组团进京到邮传部等中央部门游说,年轻的举人潘复(1883—1935)在这次请愿中一举成名,为他以后官场生涯奠定了基础(潘复在1927年担任北洋军阀时期的末代总理)。当时济宁籍的进士杨毓泗(1864—1921)任职翰林院,他联络同乡京官集体上书,争取济宁取代兖州为铁路通过之地。经过力争和协商,尽管他们没有如愿,但获得了修筑一条将济宁接通到津浦线的支路的承诺。1912年,穿越济宁的兖州—济南支线与津浦干线同时通车。(38) 兖—济线投入使用后不久,通过济宁的货运量每日可达700到800吨。火车站附近新起的市场不久成为山东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39)
同时,济宁士绅也没有放弃整治境内运河河段的努力。不过,比较富有成效的事件大都发生在民国初年。由于一些济宁籍人士在袁世凯及之后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担任要职,济宁及山东西南部的运河和黄河水利设施的维修和改造得到了相对充足的经费,而临清及山东西北地区则因资金短缺而承受水运、水利体系崩溃带来的恶果。1914年担任山东省实业局局长的潘复拟定了一个修整山东南部运河和湖泊的计划,并于次年在济宁设立公署处理水利工程中的管理和技术问题。尽管原来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完全实现,但部分措施还是取得了局部成效,而公署则发展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水利学校。(40) 1927年的县志描绘了济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河环绕济宁及其近邻,并南达江南;兖济铁路把济宁与津浦干线连接起来;长途公路西抵曹州。(41)
周锡瑞正确地指出铁路在中国北方对城镇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南方。济南就是个例子。尽管它是山东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其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在铁路贯通以后它的经济地位才得以提高,并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经济重镇。(42) 同样,较为优越的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加上可以局部使用的运河等水路,为济宁人改变地方经济取向、完成经济转型增添了希望和信心。
(三)地方经济取向的重新规划及其困顿
1892年,307000担进口机制洋纱从镇江运抵济宁,(43) 这是外国商品大宗运销济宁的较早记载。从19世纪末起,各种洋货从山东东部港口、北方的天津和江南的通商口岸源源不断地运来。这个大趋势肢解着传统的手工业以及市场秩序。从地理位置上看,济宁是一个北方城市,但它在明清帝国经济与文化的网络中的位置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南方化的特征。与漕粮转运的方向一致,沿运河北上的江南商品、资本、组织、机构、信息以及风尚,通过商业与文化的互动,成为塑造晚期帝制时代济宁城市南方品格的重要因素。现在,为了应对转化了的经济格局,地方精英全力把家乡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导向沿海经济中心。不过,在清季的最后二十几年里,这种转向还是局限于流通领域。如1927年的《济宁县志》记载,这阶段商业继续繁荣,但新式工业却尚未引进。由于没有足够的雇用机会,贫民大量流徙他乡。(44) 但与沿海的新型经济体连接的商业繁荣有助于现代工业的诞生。济宁商会在1908年成立,主要的宗旨是促进和协调新兴实业。商会里的领袖人物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的地方工商、金融巨头,他们积极从事外贸生意,其投资远至整个山东西部以及天津和北京等地。在1920—1930年代,济宁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工业局面。(45)
因为本地资本是晚期帝制时代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所以济宁也避免了现代转型之初北方运河地区普遍发生的外地商帮退出后无以为继的创伤。例如在临清和聊城,开埠后迅速衰微的晋商将资金撤离后,由于本地资本弱小,又无新资本进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46) 大卫·巴克在他对19世纪末山东各地商业的观察中,注意到外地资本的空缺。济宁也受到波及,但是处境要好得多,因为其区域内贸易和长途贩运大多由本土商人经营,而且不少富商本身就出自士绅之家。(47) 由此,济宁能够在外来经济因素的冲击下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彭慕兰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可穿透性”(impermeable)来定义济宁地区,以别于山东西南其他地区。山东西北地区则比较顺利地融入新的经济体系,接受新的行政和经济统合。(48) 这样的后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济宁主动进入现代市场体系,避免了被动进入可能带来的灾难——不少中国北方内陆地区因被动卷入现代市场体系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排拒性使济宁的经济体难以脱胎换骨。经济格局和经济取向的变迁给济宁带来了多项选择。由于运河水道可以南达江苏,济宁继续保持着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尤其在1912年津浦铁路开通后,济宁直接从上海而不是原来的运河都市扬州和苏州接受现代技术和资本。同样由于铁路的作用,济宁与正在迅速崛起的沿海城市天津、青岛、烟台的商业、社会联系加强了。曾同为运河城市的天津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现代工业、金融、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影响着整个大华北地区。(49) 在民国年间,天津成为济宁联系最为紧密的港口。(50) 庄维民通过资料详实的研究,认为济宁作为山东三个最大的商品区域集散中心,其市场取向、经济联系已从南方转向北方,济宁的进出口货物主要经过天津。(51) 济宁本土和济宁籍贯的著名工商、政治人士的活动舞台和迁居地也多在天津、北京、济南,而不是上海。(52)
三、清末时期的议会、自治实践和地方政治生态的演化
中国开埠以来,山东西部对外来文明的侵袭表现出反应迟缓的惯性,东部沿海城乡则利用地理优势尽情吸纳西方的商品、组织和观念。然而,济宁士绅的文化和政治心理习惯使得他们的表现非同一般。纵然革命、共和的理念没有多大市场,却存在对议会政治的热衷。山东各级咨议机构迄至1908年大体上筹办成形。(53) 次年10月,山东省咨议局正式成立,共103名议员,杨毓泗被公选为议长。(54) 次年,两位济宁的州县代表赴济南参加山东省自治研究所。1911年,州参议会和众议会成立,自治公所及其分支机构也在城区和辖县建立起来。(55) 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地方精英对这种渐进的议会政治的偏爱体现了济宁城市社会开通和温和的传统。东部沿海则在社会大转变中大踏步地前进,1910年对省议会议员的一则新闻评论折射出这种区域性差异:“东三府(议员)多主张激进,西七府(议员)多主张保守。”(56)
杨毓泗在济宁的自治活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他出生于城内一个下层绅商家庭,于1903年考取举人,次年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他被清廷派往日本学习宪政,冀以服务于新政改革。三年后学成回国,加侍讲学士衔,并加入了家乡使团来京争路请愿的活动。洋务时期的自强求富、新政时期的议会政治的观念贯穿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坚定奉行和风细雨的渐进改革。1909年,他响应清廷在各省建立咨议机构的倡议,回乡组织了自治研究会。(57) 稍后他当选为省议会议长,积极倡导“振兴教育”、“兴修水利”、“省刑薄赋”、“学习欧美创办实业”,成为西部保守派的领袖。后由于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萌生倦意,于一年后辞职返京。民国初年,他曾担任过若干军政幕僚之类的职务。1916年直到1921年去世,他主要住在济宁,成为士绅圈中与潘复之父潘守廉(1847—1934)齐名的领袖人物,广泛地参与地方公益事务。1914年,他创办并主持慈善事业因利局。在他的倡导或直接领导下,济宁一些颓废的名胜古迹如太白楼、古南池、浣笔泉等得到了整修。由于其在全省和全国的威望和人脉,他曾代表地方与先后统治济宁的当权者斡旋,保护地方利益。在他遗留的书稿中,有一部名为《世界经济政策须知》。(58)
19—20世纪之交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和欧美,他们学成回国改变了原先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结构,年轻一代知识精英更适应时代趋势和政治现实。(59)
四、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最初变化
与经济和政治领域相关联的是城市文化、生活领域的变化。不过,鉴于中国传统志书重视精英个体、忽略众生群体的传统,反映清末济宁城市生活的写实文字不多。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老人为当地《文史资料》撰写的回忆录大多是对民国时期的描述。然而,给生活带来波澜的新鲜事务还是十分令人瞩目的,成为隽永流传的地方记忆。其中,西方传教士和他们建立的教堂、医院、学校、图书馆和教友组织形成了济宁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另一种力量。济宁城市对多元、多色彩文化宽容、接纳的良好人文环境为西学、西教的锲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60) 这意味着济宁被吸入了国际化的浪潮中,人民拥有更多的生活、知识、价值和信仰上的选择。
现代观念的植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普通民众和士绅精英的认知系统。1905年《济宁州乡土志》“学校”编将士、农、工、商并列,“如国之四体”,还认为作为舶来品的“自由”,其实与中国古代的“自治”相通,民权既可发展,则“贵贱可以平等”。这种进步理念是自治运动的思想基础,但强调了中西观念的联系。新的政治改革理念与现代文化、生活观念互为促进。在跌跌撞撞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困扰着几代人。在外国人聚居的沿海通商口岸,中国的城市掌权者更倾向于西方化的市政建设和管理体制,市民沐浴欧风美雨,追逐时尚新潮。内地的精英则似乎更重视本土或更“中国式”的气质。与山东沿海城市相比,济宁的士绅在对待西风西俗上表现出一种中庸的态度,尽管存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从20世纪10—20年代作为济宁地方发言人的士绅领袖杨毓泗和潘守廉的身上折射出这一特点。前文已经对杨毓泗的生平作了简单的介绍,潘守廉也属同类人物。
潘守廉于1889年考取进士,之后长期在河南担任过知县和知州的职务。民国成立后返乡,凭借其仕途生涯、文化修养和其子潘复的影响,潘守廉在地方公共领域享有崇高声望。他主持了济宁州续志和县志的编修,两志均在1927年出版。他对基督教不以为然,但承认外来机器和技术的先进,主张用儒学去容纳西方物质文化。同时作为一位佛教居士,他力倡“儒佛合一”,还写了一首“劝人念佛歌”。(61) 这类努力的初衷是希望在大变局中维系地方和民族的认同。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和杨毓泗倡议、主持修复标志地方文化遗产的名胜古迹。所以,济宁在民国初年尽管历经兵荒马乱,依旧保持着典雅的名城景观,楼阁亭榭错落有致,尽管其黄金时代早已逝去。(62)
五、结语:清末济宁——处在内地边缘层级上的城市现代化转变的成功起步
在19世纪中叶以来时代巨变中,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在寻找其新的位置。处在江河日下的内地的济宁,似乎生存都举步维艰。纵然遭受区域性的沉落,其现代转型的步履也比东部沿海城市滞后,但与临清等大多数运河城镇的根本性衰竭不同,济宁滑向边缘位置的趋势被阻滞下来。在清末20余年间,富有实力和活力的济宁精英投身并领导起这个内陆城市的现代转型。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运河弃置的损失,经济结构和市场取向的调整带来了现代转型的勃勃生机,并进而奠定了民国时期竞争和发展的基础。民国以后,虽然政局更加动荡不定,战事、动乱连绵不断,济宁在1938年初沦陷于日军之前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中等现代城市。
当然,济宁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是在经济领域。与大卫·巴克所描述的济南的例子相近,而与沿海通商口岸迥异,作为内地城市的济宁代表了一种更“中国化”的现代化追求。这种追求建立在本地的需要和动机上,是基本自主型的城市改革,没有西方的强力干预。巴克对济南现代化过程和成就的某些归纳也很符合济宁的情形:“在1890至1949年间,济南经历了伟大的商业变革和一些工业化,但是国内及外来的政治上的因素瓦解了城市商业的进一步纵深发展,阻止了其全部经济潜力的实现,即使在一些和平时期也如此。”(63) 然而,济宁缺少济南当时所具备的优势:处在能吸引国内外贸易与投资的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的枢纽位置。济南作为省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有力地增强了它的经济地位;处在边缘化境地的济宁的成就则取决于其士绅和民众的主观努力。
关于济宁早期现代转化的轨迹的考察不可避免地需要评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中的位置和意义。当然本文只是一个时间、空间和视野范围都十分有限的个案研究。这里,我只是将此个案与相关重要课题联系起来。总的说来,虽然济宁作为一个城市个体并没有完全衰落,但它所处的山东西南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沦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在山东省、华北和全国的经济网络的层级结构中,沿海城市是中心,大济宁地区则在20世纪上半叶被边缘化为腹地。在济宁经济区域内,济宁与周边地区的城乡两极分化的个案也透露出中国现代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两难境地:现代市场经济富裕了城镇,却肢解了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掳掠乡村的物质和劳动力资源,从而加速了农村的破败,使社会紧张和对立更加严重。这种现代中国宏观政治经济构造的两分法也决定了济宁城市现代化的最终失败。而城市现代化仅仅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胡适意义上的社会改良的一剂温药。中国现代城市的命运无法自我决定,济宁也概莫能外。
(致谢:此文主要由我博士论文中的一章发展而来。除了感谢悉心指导我完成整个课题的导师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外,还要感谢先后对该英文稿或中文稿提供宝贵意见的下列先生:宋贻明(Michael Szonyi)、周岸瞩(Stephen Trott)、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吕士胜、王志明、冯刚、张自义、杜庆生、高建军等)
注释:
① 参见李文治、姜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79页。
② 在明清时期,南方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6省的部分州县提供“南粮”,北方的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州县提供“北粮”。参见李文治、姜太新:《清代漕运》,第11页。
③ 杨士骧等修,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1911)卷首:列祖训典八,第1册,第171页上。
④ 关于运河对明、清沿运地区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中外学者多有涉及。我对济宁地区做了专门考察。详见我的博士论文City,State,and the Grand Canal: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1289-1937(《城市·国家·大运河:济宁的地方认同和转变,1289—1937年》)第2章Canal-Oriented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多伦多大学,2007年。
⑤ 当然,许檀对临清的专门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又闻近年来国内有些年轻学者对烟台、周村、淄川等进行了若干历史考稽,但似乎还没有出现如许檀作品分量的成果。
⑥ 大卫·巴克(David Buck)谈到捻军起义平息后山东西部继续骚乱的局面:“当捻军在1867年被最后镇压后,几乎没有间断过的骚乱在半个山东持续了近20年之久。”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25.
⑦ 参见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New York: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1971,p.148。马戛尔尼1793年观察到,在山东西部沼泽地带的运河“被既高又厚的大块土墩构造的堤坝围起,远高于两侧地面”。他惊叹道:“试想一片洪流被人类的技能和勤劳制服、收拢在一条高于其原来的河床若干码的人工渠道里一直长行到与其它河道交汇的地方才调整水位。”参见George Macartney,An Embassy to China,New York: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1971,p.171。
⑧ 参见下列相关资料: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出版社,1982年,第348—358页;Jane Kate Leonard,Controlling from Afar: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1824-1826,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6,p.49; 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56,pp.19-23。
⑨ 陈龙飞主编:《山东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⑩ 关于黄河北移对运河的影响,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版,第339—141页。
(11) 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4-15.
(12) 参见《大清历朝实录·穆宗》卷二九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7、28页。
(13) 参见《大清历朝实录·穆宗》卷三○三,第67页。
(14) 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25.
(15) 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pp.14-15.
(16) 按照一位济宁老人回忆,1935年的黄河决堤造成包括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27个县的大片灾区,仅济宁县(当时的行政编制)的受灾面积就高达600多平方公里,80800亩地、500余村庄被冲毁,百余人溺死,受灾人口约有50万。参见郝子善:《一九三五年黄河决口济宁灾情的回顾》,《济宁文史资料》1987年第3期,第106—112页。
(17) 参见李文治、姜太新:《清代漕运》,第470—474页。
(18) 李文治、姜太新追溯了自1825年开始的海运酝酿和试行。参见李文治、姜太新:《清代漕运》,第432—434页。Harold Hinton的研究则显示,从长江下游海运漕粮得方案始于1846年,并在两年后实施。见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p.23.
(19) 参见《清实录·穆宗》卷三五四,第315页。
(20) 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卷五七,同治四年,引自李文治、姜太新:《清代漕运》,第470—471页。
(21) 参见王赓廷修、邓际昌纂:《济宁州乡土志》(1905)卷一,兵事。
(22) 李继樟:《济宁直隶州拟稿》(手稿)山川志上,运河。
(23) 吴琦引述岑仲勉《黄河编年史》的统计数据:在1863至1904年的42年间,黄河在山东境内49次决口。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9年,第83页。
(24) 李继樟:《济宁直隶州拟稿》山川志上,运河。
(25) 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155,159.
(26) 《济宁州乡土志》卷一,兵事。
(27) 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p.14。
(28) 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pp.7-13.他将山东分为东部半岛、北部坡地、南部山区、济宁、西南部和西北部。
(29) 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卷一,第12页下。
(30) 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960—1916》(上、中、下三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3),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初版,1987年再版,第268—285页。
(31) 参见《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卷一,第12页上—13页下。
(32) 参见袁静波:《兴学育才,力行维新:清末循良邓际昌》,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5册,1989年,第42—48页。
(33) 我在博士论文中用了两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济宁士绅在地方公共生活中的霸权以及与国家既矛盾又调和的复杂关系。地方精英的作用在明季臻至顶峰,但进入清代后其政治角色受到政权的压制。济宁的这种情形与江南颇为相似。国内外关于江南的士绅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可参见我翻译的卜正民教授论文《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4) 可参见玛丽·兰金的综述。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86,p.3.
(35) 参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5页。
(36) 之前贯穿山东东西的驿路已不能承担现代运输工具,至于全省的现代公路网路的建立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第133—138页。
(37) 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960—1916》,第485页。
(38) 这一事件参见潘复《争路小记》,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1927)卷二,第56页下—60页上。
(39) 参见袁静波:《“兖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筑小史》,济宁市工会编:《济宁工运史资料》第1集,1987年,第124—125页。
(40) 参见济宁市政协编:《济宁运河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59—60页。
(41) 参见《济宁县志》(1927)卷一,第2页上。山东西南部的两条主要长途公路分别在1923年和1924年建立起来。
(42) 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43) 以下这则史料反映了进口洋纱在19世纪末大宗进口到中国并用于北方作坊制造业与家庭副业的情形:“本口[镇江]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本口北方各境,尤觉棉纱销售兴旺。去年[一八九一年]此货进口仅二万七千担,今年[一八九二年]进口有八万五千担,比去年多三倍。窃恐通商各口,未必有多至三倍者。第以棉纱有本口转运而论,记运至徐州五万二千担,运至济宁三十一万七千担,运至开封六千余担,运至归德四千八百余担,运至兖州三千六百余担,运至沂州一千余担,可见新旧黄河腹内各府州县,系购洋纱自织矣。”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9—210页。
(44) 参见《济宁县志》(1927)卷四,第1页下。
(45) 民国初年的济宁出现了所谓的“四大金刚”。他们全都从事现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成为取代传统“绅商”的新式资本家。尽管在公众评价里褒贬不一,他们的故事至今在济宁流传。参见石贡九、骆绍康、袁静波:《济宁四大金刚侧记》,济宁市市中区编:《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9—50页。
(46) 参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第146—147页。
(47) 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32.
(48) 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p.10.
(49) 据贺萧估计,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对外贸易量已仅次于上海。参见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86,p.10。几种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依照刘海岩关于现代中国北方变化着的交通条件和区域城市重建的关系的研究,天津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为其成长为新的大区域中心开拓了广阔的腹地。相比而言,烟台对内地的较小影响与其不够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关。结果是,天津和青岛在内地竞争腹地。参见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城市史研究》第21辑,第24—48页。
(50) 此与天津在整个北方区域的角色有关。它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使得许多北方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成为它的腹地。参见Kwan Man Bun,Mapping the Hinterland:Treaty Ports and Regional Analysis in Modern China,Gail Hershatter,Remapping Chinese History: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6,pp.187-188.
(51) 参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第164—166页。另外两个中心是周村和潍县。
(52) 我在博士论文第8章Modernizing the Hinterland in the Early Republic里描述了这种现象。同时可参见彭慕兰的相似观察。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2:note 2.
(53) 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960—1916》,第433—467页。
(54) 参见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300页。
(55) 参见《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卷一,第13页上、下;卷五,第26页上、下。
(56) 参见《民主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转引自孙柞民:《山东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0页。东三府指登、莱、青三府;西七府包括济、东、泰、武、曹、兖、沂诸府。
(57) 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960—1916》,第793页。
(58) 参见《济宁县志》(1927)卷四,第55页下;卷三,第14页下—15页上。方伯廉:《才华名当世,落拓一书生——清末翰林杨毓泗》,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第31—41页。
(59) 在济宁籍的日本留学生中,李汝谦在清末民初成功的政治生涯很值得体味。他刚取得生员后,科举制度便取消了,于是远渡东瀛研习政法。学成回国后入仕,颇有一番吐故纳新的作为,不断得到升迁,1912年担任了民国肇始的首任泰安知府。在兵荒马乱的北洋军阀时期,与清高的旧士绅不同,他不断地寻求公共职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担任过黄县知事,也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供职过。其书画、收藏、烹饪闻名一时。参见孙嗣东的手稿:《李汝谦先生轶事》(未刊稿)。
(60) 一位名为Jaspers S.McIlvanie的德国传教士在1880年7月5日写给济南的同事的信中声称:“(在济宁)的公众场合的传教工作远比在济南要顺利得多。”藏于山东博物馆,卷宗号:J109—01—12。
(61) 潘守廉:《对凫缘景》(手稿本),北京图书馆藏,第29页上。
(62) 我在2002年访问当时已逾90高龄的刘子怡老人时,他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济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老百姓不偷不抢,商人不欺不诈。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大众的群体道德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济宁社会与许多北方贫瘠地区截然不同的温和城市性格。
(63) 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