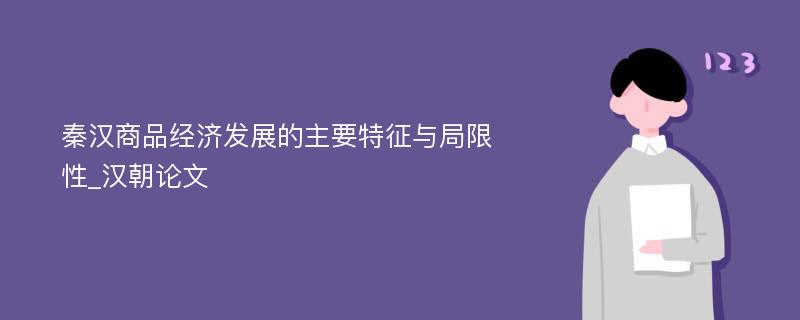
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秦汉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4)06-0014-05
随着封建地主制的确立与形成,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是,对其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在认识上则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当时商品经济有突出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表现为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以产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1]。但更有学者认为: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比先秦发达,但充其量是简单商品经济。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只能充当自然经济的婢女。不同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他们指出:对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宜估计过高,这时的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2]。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对之应作何等评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观史实,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和先秦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的主要表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数端:
首先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这和商品流通有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各地之间已有较多的商业交往。当时的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3],不同地方的物资,确实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流通。但由于受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其时的商贸往来主要是限于中原地区。时至秦汉,随着国家统一、关梁开放、交通开辟,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增多,市场广度空前扩大。当时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样是商人活动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之间也有汉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4](卷129《货殖列传)。由于东南西北中的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流动。其表现是:北方向南运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毡、毯、裘皮、筋角等;南方向北方运的商品,有犀牛、象牛、翡翠、瑇、瑁、珠玑、楠梓、黄金、锡、铝、丹砂等;东方向西运的商品,主要有鱼类、海盐、油漆、蚕丝等;西方向东运的商品,有竹木、旄牛、玉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乃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回外地的方物、特产。至于周边各族如西域、匈奴、羌人输入内地的商品,有名马、骡、驴、骆驼、毡裘、狐皮等;内地输出的商品,则主要是铁器和丝绸等。可见,秦汉时期,各地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明显扩大。
商品交换的主体,除商人外,广大“编户齐民”,特别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更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市场大量出现;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实现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进行经济运作的必然要求。三是豪商、高利贷者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记载可证,于此暂可从略。
特别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期,商业形态多样,商品流通渠道亦有了很大拓展。当时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如:秦有“官府市”,官府常将剩余物资或陶汰的旧物等在市场上零售[5]。汉初也然,如据《二年律令·金布律》称:“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又规定:“官为作务,市受租,质钱,皆为缸,封以令……”。手工业产品出卖的钱,必须“辄入钱缸中”[6]。到汉武帝时官府从事的商业活动更有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就是例证。官府不仅直接进行盐、铁的产销,还策划贩运业与屯积商业。尽管官营商业是国家操办的,其出发点和私营商业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为了牟利。但其商业形态或商品流通方式是大体近似的。就是说,不论官营商业抑或私营商业,实际上大都存在着直销、贩运、列肆或肆店等商品流通渠道。大量史事表明:汉时既存在自产直销的商业买卖活动;更有利用地区差价,贩贱卖贵的贩运商业;在全国各城市还有为数众多的肆店商业。这各种商业形态的发展,都为商品交换,互通有无,提供了方便。
秦汉时期,不仅商品交换的空间扩大,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普遍,商业形态多样,而且商品流通量也比较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有关汉简资料,当时商业行业不下二、三十个,商品种类多达三百种以上,而营业额也动辄以百、上千乃至万数为计。在“通邑大都”,一年出售“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此亦比千乘之家”[4](卷129《货殖列传》)。可见,当时商品流通量相当之大。所有这些都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我们对此确乎不容忽视。
其二,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市场的发育水平是衡量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又一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代,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稍大的市场。如齐国的都城临淄有“大市”、“中市”、“右市”,燕国的易都有“左市”[7]等。这些都会市场,虽然可以解决民间物资匮乏、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的市税收入等多种功能,但其规模和发育水平却不可和汉代相比。
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发展,交换频繁,各级市场蓬勃兴起。从京畿到郡国涌现了多层级市场,还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大的都会市场。例如:
西京长安,自高祖定都后,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长安城区商业市场日益发展,出现了“九市”。如据记载:当时“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又云:“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8]。东京洛阳,位居中原,“超大河,跨北岳”,处要冲之地。自光武帝在此建都后,规模扩大,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六里。据载:“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9]。又云: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10](卷191,陆机《洛阳记》)。长安、洛阳这样的京畿市场,既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又是著名的国际性都市,商品琳琅满目,来自各地的商人众多,不少国际商贾云集于此。故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繁荣。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对长安的繁华,都有生动的描写。不仅市场熙熙攘攘,人口拥挤,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而且各色商品,“求者不匮”。至于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4](卷129《货殖列传》,牛马车舆,填塞道路,资末业多,市场也是相当繁荣的。
除京城长安、洛阳外,区域性的都会市场,同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十余座卓然不凡的天下名都。其中最主要的有临淄、邯郸、宛城、成都等。临淄在战国时代就声闻远近。据称:“临淄之中七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击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11](齐策)。西汉前期,人口已达10万户,多于京师长安;商品交换频繁,仅市租收入竟达千金。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4](卷52《齐悼王世家》)[12](卷58《高五王传》)。邯郸地理位置重要。《盐铁论·通有篇》说:它“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战国时期,阳翟大贾吕大韦父子两代久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4](卷85《吕不韦列传》)。西汉时随着工商业迅猛发展,邯郸之地,“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13](通有篇),成为中原重要的商业城市。宛城地处南阳盆地,物产丰富,又有水陆四通之便。司马迁《货殖列传》称其:“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班固《地理志》有“南阳好商贾”之谓。桓宽更是将宛地商人置于周、齐、鲁之上。这里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工商业的发展使宛城跻身于天下名都之列。而成都,在秦时就“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14](蜀志)。
到了汉代,商业更加繁荣。左思《蜀都赋》称:这里“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市场欣欣向荣。要之,这些著名都会,往往成为区域性市场,是跨郡国的商贸场所,为各地商品对流提供了条件。许多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欲”,追逐“货殖’,周流于这些市场经商,因此,呈现出比较兴盛的局面。正因此,故王莽时期,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师[12](卷24《食货志》)。表明这“五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推动与核心作用。诸多史实说明,秦汉的商业市场,特别京畿、都会市场是比较发达的。尤当注视者:一是市场规划整齐。一般都设有阛阓、隧、廛、市楼等建筑设施。二是市内的肆店林立。其中有酒肆[15](卷52《崔寔传》)、屠肆、肉肆[10](卷828资产部,“肆”条)、药肆[15](卷83《逸民传》)、书肆[15](卷82《蓟子训传》),还有牛肆、马肆[16](《吾子篇》)革肆、帻肆、鱼肆、宿肆[10](卷828资产部,“肆”条)等等,各肆有一定的布局。三是商品种类很多,分类排列。司马迁说:当时“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薪蒿、车船、竹木、漆器、铜器、素木铁器、筋角、丹砂、细布、文采、榻布、皮革、盐豉、鲐、鮆、枣、粟、旃席、佗果等[4](卷129《货殖列传》)。还有犀象、瑇、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从中各种生活、生产资料均可买到。四是交换频繁,商贾济济。很多商人腰缠万贯。如“临淄姓伟訾五十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12](卷91《货殖传》)。商人们“东西南北,各用智巧”,目的是为了牟利。五是市内“都人士女,袨服靓妆”,“喧华鼎沸,则咙聒宇宙”[17],“既庶且富,娱乐无疆”[18],说明市场有娱乐场所。因此,秦汉政权为维持市场秩序,非常重视对商品质量、物价、度量衡、市税征收、市署、市籍和市场治安等方面的管理。这些市场管理立法的加强,可以说,体现了当时市场发展的文明程度。我们在讨论中,有人说,当时的市场是“虚假繁荣”。对此,诚乎还可商榷。
其三,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
货币是实现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战国时代,金属货币已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各国都有自己通行的货币。秦始皇统一后,规定以黄金和铜钱为法定货币,汉代沿用其制,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至西汉时期,黄金的流通范围较广,大量用于赏赐和馈赠等。据文献记载,从汉高祖至王莽时期,西汉对各级大臣、将吏共计赏赐黄金70余次,其中赏赐百斤以上者33次;赏赐千斤以上者18次。例如:汉高祖时曾先后给田肯、叔孙通赐金“五百斤”[12](卷1《高祖纪》)。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赐太尉周勃黄金五千斤[12](卷1《高后纪》,卷43《叔孙通传》),赐丞相陈平二千斤,赐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各千斤,赐刘揭千斤,赐灌婴千斤[12](卷3《文帝纪》,卷38《高五王传》,卷41《灌婴传》)。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赐窦婴千斤[12](卷1《窦婴传》)。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赐霍去病、卫青五十万斤[12](卷6《武帝纪》)。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赐广陵王千斤[12](卷8《宣帝纪》),后来,又赐霍光前后七千斤[12](卷68《霍光传》)。成帝永始中,赐史丹数千金[12](卷82《史丹传》)。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赐孝单于咸千斤[12](卷94《匈奴传》)。至于黄金用于馈赠方面,数量在百斤、千斤者也多有记录。如:韩信赠漂母千金[12](卷34《韩信传》)。刘泽赠齐人田生二百斤[12](卷35《燕王刘泽传》)。周勃赠狱吏千金[12](卷40《周勃传》)。陈平赠绛侯五百斤[12](卷43《陆贾传》)。韩安国赠田蚡五千金[12](卷52《田蚡传》),等等。不一一列举。据统计:西汉时期,仅皇帝赏赐的黄金数量有据可查的就达90万斤之多。约合今273.4吨[19](p70-71)。王莽灭亡时,仅集中在宫廷中的黄金就有70万斤[12](卷99《王莽传》)。这些数目之大,令人惊叹!与此同时,西汉民间的黄金数额也不可胜计,在不同场合下用黄金表示价值的记载多有,流量亦大。故有“汉代多黄金”之说。
至于铜钱,西汉前期曾改制4次,武帝时期又改了5次,最后确定以“五铢钱”为标准货币推行全国。汉武帝发行“五铢钱”的成功,是其强化中央集权的结果,也是商品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形式发展的产物。关于铜钱的发行量问题,自秦至西汉前期,史文简缺,难于稽考。但汉武帝收归铸币权后至平帝元始中期,全国统一铸造的五铢钱有个具体数据。如《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12]。在这120多年中,平均每年达二亿多,说明五铢钱的铸造量相当可观。由于铜钱较黄金使用方便,故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广泛流通,普遍用于市场交易、雇值支付、贳贷借债、财富计量、赋税征收、财政收支等各个领域。实际上,五铢钱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止,七百多年间一直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秦汉时期的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尽管还存在一些障碍。但就总体来说,当时的货币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战国时期。黄金和铜钱的货币职能显得很突出。它既是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又是支付、贮藏手段。货币发行量之大,流通速度之快,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的。这是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对加强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育及货币流通等方面,都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快速的发展。秦汉商品经济取得如上发展的原因出于多个方面。其突出之点是:与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有关。消费需求,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动力,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和国家的赋税也有关系。秦汉的赋税制度以税人为主,税产为辅,以货币为主,实物为辅。货币在赋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对商品经济有相当大的拉动作用,它不仅迫使农民将粮食和农副产品投向市场以换取货币,也迫使农民为了获取货币开辟新的谋生途径,甚至弃农经商,当时的赋税既提升了商品市场的丰度,扩大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容量,也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等。除这些之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当时铁器、牛耕的推广,有利于大规模开发土地,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从而能提供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同时,新兴生产关系确立,经济结构调整,使各种经济因素、经济力量从传统的束缚中得到解放,地主制经济比领主制经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加之国家统一等,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因此,窃以为秦汉商品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达到新的高峰,与多种因素有关,当是需求导向与生产导向合力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肯定秦汉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当看到它还存在着的历史局限性。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合符实际的价值评判,不宜任意拔高。
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和近代的市场经济相比。考诸史实,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研究商品经济不能单纯看流通领域,还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因为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秦汉时期的商品生产在总体水平上却还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当时,除官营手工业的规模稍大外,绝大多数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很小,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散、狭隘,工具简单,技术更新缓慢。官营手工业的许多产品主要是供国家或统治集团内部消费,通常不具备商品生产性质,只有部分产品当作商品出卖。私营手工业虽属商品生产,但小打小闹,产品数量有限。在农业领域,除林、牧、渔、园圃的专业农户和地主田庄的商品生产外,广大农民出卖的部分农副产品,其初衷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之目的,他们将农副产品投入市场是为了调余补缺,互通有无,或换取货币以纳赋税。故严格地说也不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至多只能是商品性生产,商品化水平很低。当时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尽管相当可观,但对一家一户的农民或地主来说,他们的产品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尤当注意的是当时商品生产的范围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的居多,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商品生产有明显的地域性,它主要集中在中原内郡,且发展不平衡,而边郡之地除方物、特产之外,商品生产相对疏落;再从商品生产的主体结构来看,私营往往受到官营和“抑末”政策的制约,私营手工业很难得到广阔发展的空间。在长时期内,国家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特别是盐、铁、酒类官营后,官营生产的总值上升,而私营商品生产便失去了销售市场。当时强化官营、限制私营的政策,必然会挫伤手工业主的积极性,使商品生产进入低谷。因此,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大多数私营手工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朝着曲折、艰辛的道路发展,一般不具备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再者,商品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不能只看市场上有多少商品,而关键点之一还要看市场机制是否健全,价值规律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市场法则支配、调节经济,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政府重视商品质量、平抑物价、划一度量衡等立法外,还必须有好的经商环境,必须有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官、商垄断,实现价值规律等。然综观秦汉市场的发育状况,在这些基本的方面确乎尚未达到此等水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4]。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范围的市场竞争情况。但更多的史实表明,当时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是十分有限的。例如:在国家垄断盐铁产、销期间,商品价格很难平衡供求关系。据《盐铁论·水旱篇》: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铁器产品质量很差,“民用钝弊,割草不痛”,而又价格昂贵,强迫人民购买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民争利”,“力排富商大贾”,私商是无法与官府竞争的。至于贵族官僚垄断市场的情况,汉代也非少见。他们中有部分人利用手中特权控制市场,辜榷为利。汉景帝时,赵王彭祖,“擅权,使使即县贾人榷会,入多于国家租税”。韦昭注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得为之”[4](卷59《五宗世家》及注)。西汉有不少“贵族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所谓“辜榷”,也是利用权势专断买卖[12](卷84《翟方进传》)。到东汉时豪商控制市场的现象也为常有。如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初置骎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15](卷8《灵帝纪》),使马的价格腾贵。诸多事例说明,在市场垄断多于竞争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很难形成的,价值规律受到很大限制。司马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4](卷129《货殖列传》)。这是否说明当时已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当时的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的基础上,同时商业利润长期偏离商品价值,看来,要形成“平均利润”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所反映的农工商业比较利益的差距,正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是符合史实的论断[2]。
此外,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统一市场,是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产物,也是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秦汉时期的市场虽然比较广阔,但它只是地域性市场在空间的拓展,是简单货物交易的大市场,当时“全国性统一大市场”并未形成。这主要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尽管中原地区市场联系增多,但周边地区经济落后,商品流通网络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畅通”,它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和分割性,因其“故俗”而治的各个“属国”,尤其如此。再是统一市场要有健全和稳定的货币制度。而秦汉的货币,只是对金、铜两种铸币材料做了统一,对其质量和规格并未一以贯之的完全统一。如秦至西汉前期及王莽之时,铜币多变,轻重无常;盗铸之风严重,劣质钱币充斥市场。这种情况,不仅有损于人们对货币的信赖,而且常常导致物重钱轻。加之黄金与铜钱无法定比价,交易不便等。故其时的币制,对商品流通是存在着一定障碍的,所谓“货币经济活跃”只是相对而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统一市场必须具备统一的市场价值,并使价格形成机制。然而秦汉时期的价格制度并不健全。据文献、简牍资料,当时市场上能看到的商品有二、三百种之多,除粮食、布帛、六畜、酒类、食盐、肉类、酱醋、竹木、漆、薪藁、轺车、笔墨和部分蔬菜、铜、铁器、珠宝等170余种有价格的商品可稽考外,还有不少商品包括各类农具,70余种鱼类及各种水果等,并未发现一一记价。就是记有价格的商品,有的往往与实际价值不符,是一种僵化的价格体制。至于市场上的不等价交换就更为普遍。诸多史实表明,在自然经济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不可能使各种生产要素都纳入市场,成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枢纽,使市场成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它只能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它的发展程度无法和后来的全国性统一市场相比。
标签:汉朝论文; 秦汉时期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经济论文; 秦汉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西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手工业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