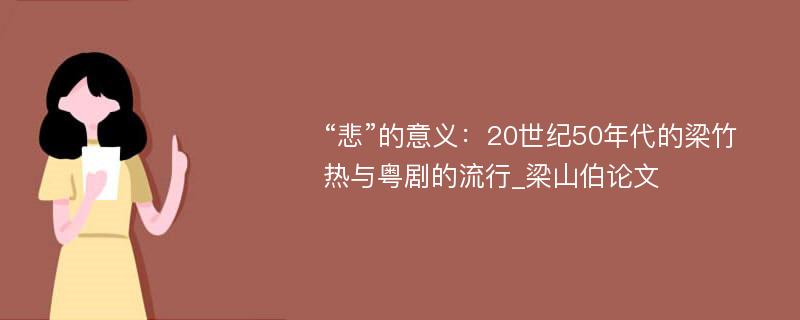
“哀伤”的意义:五十年代的梁祝热及越剧的流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祝论文,越剧论文,哀伤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六十年代,曾有一阵令人瞩目的梁祝热。目前研究较多的是1963年由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引起的“梁祝热”和“凌波热”,却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早在五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有另一拨更早的“梁祝热”,并直接对港台的“梁祝热”产生了影响。它涉及多种叙事形式,包括民间故事、小说、戏曲、歌谣、电影、小提琴协奏曲及其它艺术形式。在建国初期的地方戏曲改革运动中,1952年越剧的早期版本《梁祝哀史》获得了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的五项一等奖,被树立为改革的模范,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与梁祝有关的许多讨论。同时,在1954年出现了分别由张恨水和赵清阁改写的有关梁祝故事的通俗小说,并出版了梁祝的连环画版本及梁祝民间歌谣集,例如路工编辑的《梁祝故事说唱集》和钱南扬辑录的《梁祝戏剧辑存》各自在1955年和1956年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依据越剧版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在1954年的国际日内瓦会议上由周恩来作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介绍给西方世界后,又南下香港及东南亚,在华人地区刮起一阵“梁祝热”及“越剧热”。
要讨论50年代的梁祝热,不能不讨论越剧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在这个时期的崛起和流行。越剧事实上是梁祝故事在50年代最主要及最有代表性的传播载体。作为一种从南方来的地方剧种,越剧的柔美及抒情的特点与这个哀伤浪漫的故事最为吻合,而梁祝故事的普及也大大地推动了越剧在此时期的扩张。女子越剧① 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年轻的地方戏曲类型。它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开始快速发展并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仅次于京剧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剧种。它不仅北上到北京,同时还南下到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并且被介绍到海外而蜚声国际,形成非常值得深思的50年代的文化政治地形图。在建国初,关于梁祝故事的地方戏曲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越剧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一个是川剧版本的《柳荫记》。虽然川剧的泼辣和刚烈与当时宣传婚姻法的政治运动更能产生互动,新政府却在1953年选中越剧版本拍成彩色戏曲片,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本文将特别关注越剧这样一种以演绎婉约动人、哀伤柔媚的才子佳人故事见长的南方剧何以在建国初得到新政权极力支持并克服方言的障碍,被推广到全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文化因素。在梁祝的改编过程中,戏曲的改造者面对着种种双重的矛盾:其一是新政府需要突出梁祝爱情故事的悲剧来控诉所谓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但是对梁祝之间情爱的强调又很自然地会带出新意识形态所试图避免的颓废的及哀伤的情绪。并且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哀伤也并不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一味排斥的,如日内瓦会议上的新中国政府也会借用梁祝故事的浪漫及哀伤来建立超越意识形态限制的情感认同及向非社会主义国家传达自己“和平”的信息;另外“男扮女装”及“化蝶”等情节是梁祝故事之所以为“民间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两个传奇性的情节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新意识形态所不希望出现的情色想象及迷信与神话之间的纠缠。本文将特别关注这些双重矛盾中情感处理的部分,而且它会促使我们思考建国初革命通俗文艺的情感结构里经常不被注意的一个面向:女性化及柔媚化的一面。
一 五十年代初南戏北上:越剧的南方性和爱情的主题
有关梁祝的故事,文字记载最早可见于晚唐张读所撰写的《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②。这段材料已经包括了之后各种戏曲版本都有的基本要素如“伪为男装”和“跳墓并埋”。其中尤其以“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最为惊心动魄,祝英台之悲痛竟能大到地陷,足见哀之深,可与另一传统民间故事中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情节媲美。早在1930年容肇祖写的《祝英台故事集序》中就提到:“我以为祝英台故事在民间贯注之容易和通行之普遍,除了它有悠久的历史关系之外,故事的简洁而动听,自是它的存在和流布的原因;而悲剧的结局,更容易使人有惋惜的情怀和深刻的印象。”③ 另外从这段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整个故事的重心是落在祝英台这个女性人物身上。整个记载以祝英台开始,也以她被谢安誉为“义妇”为结束,两人之间的爱情似乎还不是关注的重点,而梁山伯、祝英台及马文才之间的门第高低及贫富的细节在此段文字中更无从推敲。
1950年7月,王亚平发表文章④ 解释了梁祝这个民间故事受民众的欢迎与这个故事所带有的悲剧性和传奇性两大特点密切相关:“故事性强,起始、经过、结尾,带有传奇性,又带有现实性,其中大部分故事是民众在爱情上可能发生的情节,这样的故事是他们所熟悉的,也就是被他们所喜爱的。”在文章的结尾,王亚平建议新政权保持这些最有价值的部分,并可以把它们改编成戏曲或诗歌,应该会很受观众的欢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也正是王的文章第一次用“封建婚姻的一幕大悲剧”来阐释这个民间故事。在此之前,如在二、三十年代,在走向民间的运动中,钱南扬曾倡导收集祝英台的故事,后来部分资料发表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93、94、95期合刊《祝英台故事专号》上,由容肇祖作序,但当时关注的重点多是故事版本的演变及地域的分布,而较少讨论梁祝故事发生的社会原因,即时有涉及,也多限于妇女的地位问题。可是在50年代,王亚平的“封建婚姻悲剧论”越来越成为政府推动这个民间故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如何突出封建婚姻的悲剧性也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阐释和改编梁祝故事的一个中心。在50年代,相对来说,原先二、三十年代民俗学家比较注重的由祝英台女扮男装出外求学而引发的传统女性地位及男女平等的主题反而在此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建国以后较早以地方戏曲的形式把梁祝故事重新搬上舞台的地方剧是越剧。在1950年的8月及9月,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越剧团之一“东山越艺社”受北京文化局的邀请到北京演出,并在怀仁堂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汇演。其中,《梁祝哀史》是两个重要演出剧目之一。整个演出获得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甚至有天津的观众坐车到京来观看,而且当时的北京《新民报》还专门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推介越剧及演出剧团的情况并发起了一些关于梁祝的讨论,例如有关梁祝剧本改编的问题。上海女子越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最大特点是其充满女性特质的柔美的审美特征:它吸取了话剧和电影中的导演制度,使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集体”,而不是“旧剧中的名角个人演技的炫耀”⑤;越剧音乐以“尺调”和“弦下调”为主腔,多使用乐调比较简单和优美的笛子和二胡等琴弦之类的中国乐器,特点是“唱腔曲调抒情优美、清丽婉转”⑥;从内容上说,多是演绎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在所有的地方戏曲中,它是较早地使用丝绸来做演出服装,增添了越剧流动的柔性美;服装和道具所使用的颜色也多是中间色,例如浅绿、粉红或淡蓝等,很少使用大红大绿的颜色。越剧的这些特征在北上演出的过程中,由“陌生”的北方观众所“发现”并被当时报纸媒体上的广告及报道进一步强化。1950年8月29日介绍大众剧场越剧上演预告时,采用了如下的词汇“江南地方戏剧”、“载歌载舞,推陈出新”和“首次由沪来京短期献演”。这是越剧第一次北上,来自江南的越剧对北方观众来说非常新奇,因此在当时的演出广告及报纸的文章中越剧的“江南性”和“新”两大特征被格外地强调和突出。例如,北京《新民报》就打出了“布景富丽,灯光新颖,服装鲜艳,唱工繁重,表情细腻”⑦、“轰动华东,连满九十场,十景十二场,缠绵曲折,民间故事,古装巨构”⑧ 和“四幕七场悱恻哀艳大悲戏”⑨ 等广告词,并特别标出了“十八相送”、“应梦”、“惊艳”、“访祝”、“楼会”、“送兄”、“归终”、“吊孝”和“哭坟”等著名场次。不论是题目中的“哀”字还是这里的“缠绵曲折”及“悱恻哀艳”等词都指向这个故事情绪上的伤感及情节上的悲剧性;而“民间故事”的定位使梁祝这个爱情传奇在五十年代初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流传更具有了政治合法性。这种“江南性”后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越剧版本制作成彩色戏曲片时有进一步被强化。对此我会在第二部分继续进一步讨论。
必须指出的是,越剧此次北上演出与当时推进的旧戏改革运动密切相关:“上海‘东山越艺社’这次北来,使江南地方戏‘越剧’(绍兴戏)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北京舞台上。这对于戏改工作经验的交流,特别是南、北地方剧改革经验的交流,是有它一定意义与影响的”、“他们这次北来,是为了观摩、学习,同时把越剧介绍给北方观众”⑩。50年代初的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此项改革,例如:巡回演出,出版刊物及推动对各种戏曲形式的学术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是举办一系列规模不一的地方及中央的戏曲观摩比赛演出。越剧版本梁祝的第二次北上是在1952年的10月6日至11月14日期间文化部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在这次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个重要的报告,总结了1949年以来新政府在地方戏曲改革上的成就与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会上,越剧和梁祝故事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剧本奖、演出奖,主演范瑞娟、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音乐和美术设计也都有获奖。越剧相对于京剧和昆曲来说是很年轻的剧种,而在这次大会上,它却被树立为戏曲改革的一个典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政府对京剧的小心及谨慎的态度。在周扬的讲话中,他明确地提出京剧要向这些地方戏曲学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他看来,京剧太模式化并多注重历史题材,而越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却相对地灵活一些:“带有较多的人民性,更接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语言,因而它们的内容就更生动活泼得多,形式就更自由、更新鲜。”(11)
二 眼泪的意义:《梁祝》故事改编与新婚姻法宣传
50年代的梁祝热也与建国初宣传婚姻法紧密相关,更准确地说,宣传婚姻法的政治运动为梁祝爱情故事的流行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在新婚姻法颁布后3年,也就是在1953年,中央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宣传运动,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这年三月,中央政府文化部要求地方政府指导并与地方剧团,文化站及戏院一起合作宣传《婚姻法》。一个重要的宣传举措是改编那些建立在民间浪漫爱情故事基础上的地方戏曲剧目,由此一批具有民间故事色彩的传统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织女》以及《天仙配》等,都被重新改编上演或拍摄成电影。
在这里值得分析的是越剧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对民间传说中梁祝故事的改编。越剧早在男班落地唱书阶段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在这个时候,围绕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的特殊情境而演绎的民间爱欲联想在这些片断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当时男班演的都是“路头戏”,即兴创作的成分很大,如“十八相送”这个片断,农村里常见的一些事物如喜鹊、樵夫、牛、鹅、猪、狗及和尚尼姑等都引为比喻,极富乡土性。越剧从农村进入上海后,为适应大城市观众的需要,经常以幕表形式演出连台本戏。当时在沪的男班名生王永春和名旦白玉梅,根据宝卷本《梁山伯祝英台》和唱本《梁山伯祝英台夫妇功书还魂团圆记》,形成了上中下三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19年3月15日第一次在上海第一戏院上演(12)。当时内容是说天上金童玉女因动了凡心,在蟠桃会上打破了琉璃杯,受王母责罚转世人间。玉女投胎成为祝英台,而金童投胎转为梁山伯。后面的情节如祝英台乔装打扮到外求学及与梁山伯草桥亭结拜为兄弟,与梁在书院一起读书互相情投意合都与现在相同。而有意思的是,戏中把山伯与英台同床三载不识英台是女扮男装的原因归于山伯在梦中被太白金星用“醐心酒”迷住心窍,又被摄去真魂。另外,在英台祷墓碰碑而入墓时马文才也随入。之后还有一段马文才向阎王爷告状的后续发展:说山伯、英台、文才入墓后,游地府告状,经十殿阎王一殿一殿审下来,方知真相,夫妻不能团圆是命中注定。而后,山伯与英台回归于天庭。此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从此梁祝成为越剧常演剧目。到了三、四十年代,越剧由“男班”发展到“女班”后,并且观众也主要是女性,女子越剧的早期名旦如施银花等从女性观众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剧本首先进行了改编。在这个基础上袁雪芬和马樟花对剧本的进一步提高和改造尤其值得一提。她们删掉了《游十殿》的情节和一些有关情色的暧昧部分,并将之改名为《梁祝哀史》。整个故事朝“纯粹”的情爱故事发展,马文才的戏份几乎消失,情节重心集中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身上,而且更突出“悲伤缠绵”的情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山伯这个角色的改变。从40年代起,越剧中的梁山伯主要由女演员范瑞娟来扮演。她很清楚地把梁山伯这个角色定义为“书生”(13)。而在早期的传说和戏曲当中,梁山伯通常是被描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呆秀才,有的剧种甚至由丑角来扮演,把造成梁祝悲剧的原因归于山伯猜不透“一七、二八、三六、四九”这个哑谜,以至于耽误了日期,祝公远才把英台许给了马家。如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越剧版本中,山伯在梦中被太白金星用“醐心酒”迷住心窍,又被摄去真魂,所以演出时,“饰演梁山伯的演员从《草桥结拜》后,精神面貌要‘瘟’一些,把书生巾戴得压住额角,两手下垂,举止迟钝,神态表现得淡漠些,还只能在英台身后跟着走……”(14) 然而,在后来的改编过程中,梁山伯越来越被塑造成一个痴情的、善良的极富悲剧性的才子形象。如在越剧版本的第二场“草桥结拜”中,祝英台之所以和梁山伯结为金兰是他在祝发表女子该读书时所显露出的非同一般男子的同情和主见;“十八相送”里,梁山伯虽经祝英台多次暗示仍不能领其意时,原因则被诠释为性格上的憨厚,被称为“呆头鹅”,是一种可爱的书生气;而在“楼台会”中,当他得知因祝父把她许配给马文才而两人不能成婚时,又极度伤心,以至于积悲愤成疾。范为了更好表达出梁临死前的悲痛情绪,在40年代为《山伯临终》一场还特别创造了“弦下调”唱腔,曲调悲伤哀怨、缠绵动人,在当时的观众中曾风靡一时。如姜进在分析上海女子越剧的发展时所提到的,越剧对“儿女私情”主题的凸现是与40年代流行上海的好莱坞电影及观众大部分是女性相关(15)。但耐人寻味的是50年代宣传新婚姻法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剧中爱情的主题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其中的逻辑似乎也不难理解,只有梁祝两人之间的爱情更深层缠绵,而之后被无情破坏的悲剧性才会更有分量,也因此更能突显消除旧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把越剧的舞台演出搬上电影银幕时显得更为鲜明和突出。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6) 由桑弧导演,袁雪芬、范瑞娟主演。不论在剧本的压缩改编及拍摄方式上,抒情性和诗意成为主要的特点。导演桑弧40年代初在上海文华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时,与张爱玲一起合作,曾经执导过《不了情》、《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和《哀乐中年》等。他非常擅长处理都市爱情悲喜剧的微妙之处,“通过大量细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示富有生命力的大众文化”(17),织绘“浮世的悲哀”(18),因此他的电影作品通常显示出比较浓厚的海派风格。在这部戏曲片中,桑弧也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来表达梁祝之间的爱情,对角色的内心转折处理细微。例如在学堂读书一场,戏曲舞台演出中多是用“同窗共读两无猜,志同道合相敬爱,光阴过去如流水,一年一年又一年”(19),而在电影里则改为“同窗共读两无猜,说古论今喜有伴,嘘寒问暖常关怀。冬去春来容易过,忽忽过了三长载”。配合歌唱的是梁祝二人学堂共同读书、树下一起下棋及祝英台帮梁山伯加衣等温馨的日常生活画面,两人的感情传达得丝丝入扣。而电影中最缠绵动人的场景是“楼台会”。原来的戏曲舞台演出中楼台会一场戏里有梁山伯“告状”争吵的部分,出现了“好气呀!果然负心祝英台,花言巧语欺骗谁”(20)等唱词,传达的是梁山伯气愤难耐的情绪。桑弧认为这与梁深爱祝的情感不连贯而将之删去,最终处理成两人共知婚姻无望,互执双手共诉衷肠,一连串的“我想你”唱得婉转悱恻,把全剧的哀伤情绪推向了高潮:“刀割心肠寸寸碎……”(21) 另外,在电影风格上,桑弧采取把纪录片及故事片综合在一起的拍摄方式,创造出中国文人式的清新淡雅、优美抒情的风格。例如电影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座精致的传统舞台,丝绒帷幕拉开以后,还有一层纱幕,透过它,可以隐约看到舞台上的祝家庄和秀丽的江南风景,因此整个画面制造的效果就如在看舞台演出一样。但是它又不是单纯的舞台记录,之后镜头就慢慢地推近到祝英台书楼的窗下,突然间那两扇窗门被推开,女主人公祝英台向窗外眺望,而画外音是优美动人的合唱的歌声。在这整个处理过程中,桑弧比较恰到好处地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象征风格及电影写实的优点,并充分利用像小桥流水、书院、柳荫、凉亭、传统书法、诗歌等中国传统符号,构造了一个极富江南风情的“文化中国”空间。在美术设计上,电影同时使用实景和绘景,建筑物基本上是写实的,但透过窗户和门阑所看到的自然风景却由有关江南山水的绘画所代替,虚实相间,诗意十足。
在戏曲片开拍的时候,有人曾建议在拍摄各个场景的时候,应该比较分析所有的版本而取之优。他举例子说川剧中的“英台骂媒”情节就很精彩地突出祝英台大胆的反抗性格(22)。50年代初,作为戏曲形式的梁祝主要有三个版本:越剧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版本的《柳荫记》和京剧版本的《英台抗婚》。在时间上,京剧版本《英台抗婚》比前两个版本要稍晚一些,它是由程砚秋根据川剧版本改编而来,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来比较越剧和川剧的版本。在川剧的版本中,新添了一个媒婆的角色和增设了英台骂媒的情节。当时艾青在仔细地比较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川剧《柳荫记》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假如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长处是缠绵、细腻,则川剧《柳荫记》的长处是粗犷、纯朴。从民间文学上来看,川剧《柳荫记》的文字,比较泼辣,有时出现一些对话和顺口溜形式的道白,俚俗得可爱。也就是说,属于劳动人民的东西更多。”(23) 相对于川剧版本及京剧版本,越剧版本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其对情感的细腻处理。川剧《柳荫记》的第一场“英台别家”并没有越剧版本中祝英台乔装打扮成卜卦算命者来说服父亲的场景,祝父强烈不同意她去读书,认为“女儿读书有何用”,并且“自古以来,女儿之家,应该谨守三从四德,岂能抛头露面,玷辱门庭”,从而突出祝父“封建卫道者”的形象;而越剧中的祝父在是否让女儿读书的问题上显得更为犹豫,更富人情味:“我有心叫她杭城去,怎奈是闺女怎能出远门?我有心不叫杭城去,又怕她病势转深沉。思前想后心不定。”另外从文字表达上说,川剧的版本对白比较多,而越剧则多由唱句组成,词句相对比较婉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川剧《柳荫记》第五场“说媒许亲”。媒婆邱嫂一上场,就作了如下的道白:“哈哈!做媒人,几张脸。心要狠,口要甜。不方要说方,不圆要说圆。每日街上转,到处把事编。到东家去骗吃,西家去骗穿。夸男像金童,夸女像天仙。好看不好看,出在我舌尖。蒙到两边谈,都要钻圈圈。说得心花溅,哪怕你鱼儿不上我的钓鱼竿。等你过门后,我的事就完。悬梁我不管,投河我无关,媒人不担担,保人不还钱,只顾我的包包满,管你冤魂升天不升天。”(24) 从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川剧的语言非常的口语化,并且口吻夸张,“一点点风雅的气息也没有,倒是粗俗的很”(25)。同时媒婆等人物的增添使故事情节支线增多,有时会显得过于零碎。总体来看,在川剧当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爱情的主线不如越剧清晰,并且父女的冲突及书馆里梁祝之间有关女子是否是祸水的争辩都比较鲜明地指向50年代有关“婚姻自由”及“男女平等”等意识形态话语,有时会破坏了情绪的完整性。也正因为此,当时有评论者就认为越剧版本相对来说悲剧气氛更为饱满:“川剧后部分量虽重,占五折,但许亲、思兄两折,是可以不要的场子,事实只有三折,在三折之中,又仅只有访友一折支撑全局,这样就不可能像越剧那样一步跟一步,一折悲一折,逐折加紧,把悲剧的气氛,完满的、有层次的造成和达到最高峰。”(26) 而且在川剧版本中,存在“不应有的诙谐对悲剧气氛的破坏”(27)。同越剧版本的优美抒情相比,川剧版本显得更为泼辣和粗俗,同时也似乎更能突出祝英台反抗封建婚姻的性格,但新政府最终选择越剧版拍成电影。
电影中最诗意的一幕其实是结尾的“化蝶”情节。电影制作者特别利用电影媒介的优势,用特技来呈现梁山伯墓在雷雨闪电中突然裂开及用制作动画片的手法来制造两只蝴蝶翩翩起舞向彩虹飞去的场景。在电影的结尾,还特意加上了两位演员在花丛中穿梭跳舞的曼妙舞姿。在50年代,当时一些改编者曾提出舍去化蝶的迷信结尾,以助于将祝与她父亲之间的家庭冲突改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如在1950年8至9月发表在北京《新民报》上的连环画版本里,故事结尾变成祝英台的父亲逼迫她用剪刀自杀。当时有人甚至建议梁祝两人参军入伍为自由婚姻作斗争。如何区别迷信和神话是50年代地方戏曲改革的争论焦点。在改革的初期,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判定一个剧本的好和坏。在1951年,马少波发表了一篇题为《清除舞台上的病态及邪恶形象》的长文(28)。文章中,他以举例子的方式来澄清哪些形象需要去除。对改革委员会来说更难的是重评那些总体正确却夹杂着少量迷信因素的剧目。马少波特别指出要区别神话和迷信,还批评了把神话当成迷信的现象。他举的例子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化蝶情节。在他看来,化蝶是神话,不是迷信。他认为试图寻找科学证据来区别神话和迷信是不必要的。神话情节存在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它的政治意图。周扬(29) 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清楚的澄清。他对神话作了一些定义并用一系列对比词汇例如积极与消极,反抗还是屈服来区分两者。他赞扬梁祝故事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总结这个时期的讨论文章来说,关于神话与迷信之间的争论转换成民间故事可以为政治的目的做多大的改变这个问题上来(30)。其实,最早的梁祝故事并没有化蝶的情节。在南宋时化蝶的情节开始被加进梁祝的故事,而直到清初才被介绍进民间版本的梁祝故事中。至于越剧版本,根据范瑞娟的回忆,1951年,东山越艺社50余人参加了华东实验越剧团,又排演《梁祝》一剧赴京演出时,按当时的团领导之一伊兵的建议,将原来的尾声舞蹈改为梁祝变成一对白色蝴蝶翩翩起舞。后来,周恩来观看此剧时,特别建议将白蝴蝶转化为彩色的。对于化蝶的被批判,在当时,更多的评论者却批评了这些武断地对传统民间故事进行篡改的做法。何其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31)。他以“浪漫主义”和“美丽的想象”为由替化蝶情节作辩护,并指出保持“民间传说原有的色彩和想象”是非常重要的,而改编“不是仅仅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能够胜任的”(32)。
由当时戏曲改革者及新政府选择缠绵悱恻的越剧版的制作成电影及对“化蝶”情节的保留中可以看出女性化及哀伤性的情感与政治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关系,相互之间甚至可能有互相加强的一种张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新政权对此面临着一种左右为难的情景:一方面,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依旧要保持,以便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同情从而能让他们更容易认同其中反封建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另外,又要同这种在当时被认为消极的悲伤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众多的青年读者和观众受其影响。1953年9月,当时一封题为“学生看越剧入了迷,妨碍了学习,怎么办?”(33) 来信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报纸《文汇报》上,作者是一位教师,他苦恼地提出当时的学生对越剧有一种超出正常的迷恋。他特别地提到一些学生居然能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大轴戏从开头一字不漏地唱到末尾,而且同时能表演出各种姿态和身段。在另外一篇文章(34) 里,作者提到当时许多年轻人通过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学会了互相如何谈情说爱,有的由于沉浸于其中悲伤的情绪不能自拔,夜不能寐,有时在梦里也能哭出来。有的甚至学习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例子自杀徇情。所以,在整篇文章里,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引导观众该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物形象。他用了很多宏伟的字眼来形容祝英台形象,称赞她的死是一个战士的死,是一个反封建及与旧社会勇敢做斗争的光辉形象:“她同梁山伯的死,都可以叫做被害。祝英台的死更是战斗的牺牲。实际上她是为她自己理想的婚姻制度——容许青年婚姻自主的制度——而奋斗牺牲的。她是具有,在当时说来是先进的民主思想,并且勇于实践的可敬的战士。”(35)
三 情的跨国魅力:戏曲片《梁祝》与新中国的文化外交
那新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有意识地凸显梁祝故事中的缠绵柔美?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宣传婚姻法的意识形态目的相关意图,当年在电影中扮演祝英台的越剧演员袁雪芬的秘书黄德君曾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在全国会演的剧目中看上了《梁祝》,觉得是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又是民间传说,如果拍成功可以用于对外宣传,可以反驳当时攻击中国好战的国际舆论。”(36)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推测居多还是史实居多,但在戏曲片制作完成以后,新政权确实成功地驾驭越剧版本的“悲”和“美”来跨越50年代冷战背景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界线,以“情”动人,成功地打“文化外交”的牌,利用越剧及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柔美和忧伤的特点来改变其在国际政坛上“冷硬”的政治形象。
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制作完成以后,1954年8月25日,上海市22家影院同时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1000余场,观众近155万人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37),而整个中国大陆观众人次和放映场次截至到1958年则为九千多万人次(38),风靡一时。梁祝热的一个高潮是1954年5月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选择了播映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来招待外国记者。日内瓦国际会议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它是新中国政府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亮相,也是中国通过国际会议尝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可能性的一次关键性尝试。“和平”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新中国政府如何赢得英法美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尊重也成为此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之前,周恩来与张闻天等先后两次非正式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等商议和协调中苏等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在1954年4月6日,张闻天就有关日内瓦会议上的宣传准备工作发电报给当时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提到当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提醒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应在宣传工作上下更多的努力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力,其中包括电影放映会、组织演讲、小型的展览及文化表演等(39)。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新闻处一共举行了三场电影放映会招待各国的记者,一场是放映电影《1952年国庆节》,而另外两场就是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电影《1952年国庆节》放映会结束后,有美国记者评论这部纪录片恰恰证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40)。为了抵制这种谣言,周恩来选择放映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来招待外国记者,并对如何向外国记者宣传这部电影做了如下的指示:“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它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41) 从这些建议中显然可见周特别强调此剧的“诗意性”和“悲剧性”对国外观众的影响力及政治价值,并希望用梁祝电影来建立中国“崇尚和平”的国际形象。事实上,周恩来对越剧的发展和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直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及心血。此片导演桑弧曾举过一个例子。原来的越剧长达三个小时,所以为了适合电影两个小时的长度,电影制作者删去了一些场景及将近一半的唱词(42)。1953年冬,当电影拍摄完成时,夏衍特别邀请了周恩来及陈毅审看样片。周恩来看完后建议,“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远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43)。从周恩来对“思念”这一场面的建议,一方面可见他对越剧的娴熟和了解,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对此剧情绪的连贯及饱满度的注重。《梁祝》在记者电影招待会上放映后,如周所愿取得了良好的响应。此影片引起了各国记者的共鸣:“映到《楼台会》一段时,在我身旁的一位法国女记者用手帕擦了眼泪。当祝英台奋身跃入梁山伯墓中时,一位日本记者禁不住哭了。在一个半小时中,观众的情绪随着梁山伯、祝英台的遭遇而起伏。当梁山伯、祝英台化为蝴蝶在万花丛中双双飞舞的时候,全场爆发了赞叹的掌声,直到灯光大亮,还历久未息。”(44) 而有的外国记者将之形容为“一首美丽的诗”(45)。
日内瓦会议以后,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放映,并且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刮起一阵“梁祝热”。而在这股热潮中,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尤其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卓别林时,还特别邀请范瑞娟作陪同。1954年,范随团参加了在捷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在电影节上,当穿绣花旗袍和高跟鞋及烫发的范瑞娟出现在外国观众面前时,结果“整个电影节都觉得很新奇,还有男演员冲她跪下,说要向‘中国女人和艺术’投降,因为她们能演男子汉让人完全看不出来。周围人则冲着范瑞娟大喊‘毛泽东、毛泽东’,那大概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中国人名字”(46)。把梁山伯的扮演者与毛泽东相连是外国观众在梁山伯形象与新中国之间建立的一种象征性联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在越剧版本里,梁山伯角色由女性来扮演,而且这个以悲剧结尾的爱情传奇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同的是梁山伯的过分“女性化”。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经常的故事情节是有情人历经磨难,最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而越剧版本里的梁山伯是一介穷书生,为爱而伤,最后也为情而死,一生未考取任何功名,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情痴”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雌化”的梁山伯形象很符合当时新中国在国际外交中所企图建立的崇尚和平和尊重传统文化的国家形象这个期待。
周恩来当时还组织上海越剧院到各个国家演出。1955年,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当时的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当时的《戏剧报》对此有图文并茂的介绍,并翻译介绍了苏联《真理报》上两篇观后感。其中一篇是一位名为胡波夫的苏联作者写的《高尚爱情的诗篇——为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访问演出举行闭幕式而作》(47)。作者用“浪漫”和“优美”等词来形容《西厢记》和《梁祝》中的爱情故事,而且文中还特别提起了演出中“艺术化的舞台装置”,并称之“出色地显示了中国色彩诗一般的情感以及中国建筑学上特殊风格的美观”。另外一篇是一位名为卡巴列夫斯基的观众所写的《古老文化的青春——为越剧在莫斯科作访问演出而作》(48)。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尤其对越剧的音乐部分作了非常仔细和专业的分析,并称整个故事为“意义深长的诗一般的剧情”。同时也对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作了高度的赞扬,称其为“天才性的演员”。最后,作者也对越剧的“艺术装置”赞不绝口,认为它“替整个戏剧的演出增色不少”,并特别指出服装及舞台装置“有绝妙的风格以及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综合起来,当时外国观众都是对越剧中的抒情性及由舞台装置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诗意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综上所述,五六十年代的“梁祝热”促使我们思考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观众对梁祝故事中情感内容的反应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感知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或者更准确地说“眼泪”在五、六十年代文学文化中的意义(49)。“情”这个含义丰富的概念贯穿了晚清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五四”及“后五四”的浪漫主义小说,而在50年代通过“反对封建婚姻”及革命浪漫主义等概念,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50年代的“梁祝热”提醒我们关注50至70年代中国情绪文化结构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层面:哀伤的意义,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一系列的改编过程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一直是处于加强的一种状态之中,这当然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婚姻法及新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特定的宣传目的相关,但“梁祝热”中女子越剧的中心位置也让我们重思这个时期梁祝文化热中的性别含义。通常此时期主要的文艺美学被定义为“崇高”(50) 和“阳刚”的男性美学,而女子越剧的流行却凸显了50到70年代文化美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根据姜进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越剧大多数的观众是女性观众,例如家庭主妇、女学生、工厂的女工及一些职业女性(51)。以此大概可以推测50年代的越剧观众绝大部分会是女性。这样一群女观众的欣赏趣味及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会促成以情爱为主题的传统戏曲片的流行。如我们在讨论中所提到的一些年轻的观众会把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成自己恋爱的榜样,沉迷于其中的哀伤情绪。这其实不仅限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像越剧的另一个戏曲片《红楼梦》及黄梅戏《天仙配》在当时也是风靡一时,票房很高。这是50年代初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文化现象。
另外,海派色彩甚浓的越剧在50年代的繁荣也促使我们思考海派文化在此时期的位置和作用。目前学界通常是认为在建国后,海派文化因其商业性和娱乐性处于一种被排挤和质疑的位置,而在当时以延安文化为代表的陕北文化开始逐渐超越地域,并在全国范围内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越剧在50年代的流行似乎又在提醒我们海派文化在被取代的同时,却还是可能寄身于地方性的民间文化继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如上海女子越剧对梁祝爱情传奇的演绎及我们上面提到的电影导演桑弧,建国之前主要以执导张爱玲编剧的都市爱情悲喜剧出名,建国后用同样细腻的手法来处理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爱情,缠绵悱恻。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左右,越剧热开始逐渐冷却,而在“文革”期间,女子越剧更被江青贬低为“堕落”。论及原因,女子越剧的爱情主题及其柔美的特点都是被排斥的理由。1963年4月,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召集上海越剧院的主要负责人,告诉他们“越剧的腔腔调调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抒情要抒革命、劳动之情,而不能抒男女之情啊!越剧要找条出路,先演出一些现代剧试试看”(52)。从此以后,上海所有的越剧团体,几乎全部演现代剧,而传统剧目则不再被提倡,直至“文革”结束。
注释:
① 关于女子越剧在1949年以前的发展及其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请参见姜进新近出版的英文书:Women Playing Man: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
② 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原载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93、94、95期合刊,1930年2月12日出版。现摘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页。
③ 原载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93、94、95期合刊,现摘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4页。
④ 王亚平《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原载《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现摘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38页。
⑤ 徐琮:《新越剧在成长中:介绍新越剧和“东山越艺社”》,北京《新民报》日刊,1950年9月5日第四版。
⑥ 钱雄:《浅谈越剧音乐》,朱玉芬、史纪南主编《漫话越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69页。
⑦ 北京《新民报》日刊,1950年9月13日第六版。
⑧ 北京《新民报》日刊,1950年9月5日第六版。
⑨ 北京《新民报》日刊,1950年9月3日第五版。
⑩ 北京《新民报》日刊,1950年9月5日第四版。
(11) 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52年12月《文艺报》二十四期。
(12) 丁一、孙世基:《越剧〈梁祝〉的由来与发展》,选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726—730页。
(13) 范瑞娟:《我演梁山伯》,选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160页,原载于《戏剧报》1961年第十五期至二十四期。
(14) 如上,第160页。
(15) 参考姜进新近出版的英文书:Women Playing Man: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第81页。
(16) 根据高小健在《中国戏曲电影史》中所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中国大陆观众人次和放映场次截至到1958年为九千多万人次(第134页)。
(17) 陆绍阳:《〈哀乐中年〉:经典中的经典》,《桑弧导演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18) 柯灵:《浮世的悲哀》,《桑弧导演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
(19) 《梁山伯与祝英台》,《人民文学》(1951年五卷二期),第18页。
(20) 如上,第27页。
(21) 《梁山伯与祝英台》,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
(22) 当时有一篇署名江灵的文章《祝英台的另一种性格》发表在《新民报晚刊》(1952年5月18日)。文章指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虽是一个,但是在不同的地区里,就又加进当地地方色彩了,因此我以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要把这传说改编为电影的话,顶好先广泛收辑各地不同的传说,加以综合、分析,再找出这传说中最优美、最富于人情味,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来。前些时我曾看见过越剧《梁祝哀史》,我觉得那里面祝英台的性格就不如川戏《柳荫记》里表现得泼剌,而省去‘骂媒’一场也是可惜的事”。
(23) 艾青:《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文化大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61页。文章原载《人民文学》1953年第二期。
(24) 《柳荫记》,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
(25) 黄裳:《〈梁祝〉杂记》,《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85页。
(26) 阿英:《关于川剧〈柳荫记〉》,《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156页,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12月17日。
(27) 卢耀武:《川剧〈柳荫记〉剧本的改编》,《新中国地方戏剧改革纪实》(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28) 《戏剧报》1950年3月。
(29) 《文艺报》1952年第24期。
(30) 关于这个问题,张炼红在她的论文《从民间性到“人民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里有精彩的论述。
(31) 何其芳:《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文化大观》,第39—50页,原载《人民日报》“人民文艺”第九十二期,1951年3月18日。
(32) 如上,第48页。
(33) 《文汇报》,1953年9月23日。
(34) 张真:《我们应该向梁山伯与祝英台学习什么?》,《大众電影》,1954年7月。
(35) 如上。
(36) 《越剧百年时尚化与人性慰藉:怎一个情字了得》,《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5期。
(37) 袁雪芬:《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38) 高小健:《中国戏曲电影史》,第134页。
(39) Ostermann,Christian F.,ed.,Inside China's Cold War(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8),P15.
(40) 如上。第678页。
(41) 如上。第680页。
(42) 桑弧在《谈谈戏曲片的剧本问题》一文中提到,《梁祝》的舞台剧本共有唱词732句,电影剧本则为352句,约占舞台本的50%。《桑弧导演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43) 桑弧:《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陈荒煤主编《周恩来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
(44) 孙承佩:《〈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1954年5月25日《文汇报》第三版。
(45) 如上。
(46) 《越剧百年时尚化与人性慰藉:怎一个情字了得》,《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5期。
(47) 《戏剧报》1955年10月,第36—37页。
(48) 《戏剧报》1955年10月,第38—39页。
(49) Lee Haiyan的单篇论文:“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no.1(Feburary 2005):35—65.对“情感”在五四时期民歌运动的发展与作用做了很细致的历史谱系学的研究。同时Lee的英文专著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对建国前的现代文学及文化中的情爱话语作了非常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50) 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对毛泽东时期的“崇高”美学有精彩的讨论。
(51) Jiang Jin,Women Playing Man: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P116.
(52) 袁雪芬:《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