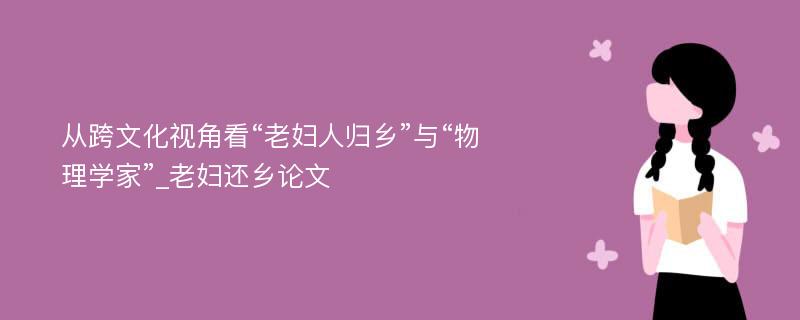
从跨文化角度看《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妇论文,物理学家论文,角度看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士德语剧作家迪伦马特(1921— )的《老妇还乡》(1956)及《物理学家》(1962)是与古希腊戏剧及中国戏剧颇有关系的西方现代名剧。
《老妇还乡》写了一个复杂的故事。45年前,居伦城发生一件冤案:一个叫伊尔的青年人欺骗了一个叫克拉拉·韦舍尔的少女,少女生下一女婴后即被伊尔抛弃。她上诉法庭,伊尔用一瓶白兰地买通两个粗汉作伪证,少女败诉,伊尔逃避了做父亲的责任。一年后,女婴死于救济院,克拉拉沦为妓女。伊尔娶了当地一家小商店的女人,当了小老板。
45年过去了,克拉拉已成亿万富豪,她还乡复仇,剧情便由此开始。奇怪的是老妇除随身人员外,还带来一口棺材,一只黑豹(45年前她把伊尔叫“小黑豹”)。她在市长欢迎宴会上把45年前法院的错判讲出。她带来了足够人证,证明伊尔才是罪人。她宣布:“只要有人把伊尔弄死,我可以给居伦城十亿镑。”
下面的故事就变得复杂了。结局是老妇叫人把伊尔杀了,装在棺材里带回去;小城因为得到了十亿镑而变得繁荣起来。
此剧实际上有三个故事:表面的故事是老妇复仇,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城市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再下面的故事是一个罪人因认罪变成另一个人。三个故事三个主题,即复仇主题、金钱主题、认罪主题。三个主题都有多面性的内涵,并且是转换推进的。
老妇复仇主题的多面性不仅在于她的复仇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合理的一面,还在于她的行动既出于报复,也出于极其自私的爱。她对伊尔说:“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于我的,永远属于我。”她要把伊尔的尸体装在棺材里运回她居住的岛上埋葬,永远陪伴她。金钱主题的多面性在于剧作家一方面批判了现代社会人欲横流及文明的虚伪,另一方面又认为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剧作家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全城的人像那位校长一样,慢慢在诱惑面前屈服的过程,但这种屈服是可以理解的。那诱惑实在太让人动心了,居伦城的穷苦的情况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1]认罪主题的多面性在于一方面伊尔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而甘愿被人杀死,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他发现居伦城人也都是罪人。他敢于认罪而居伦人不敢认罪,在人格上他高于居伦人。所以剧作家说:“而他在死去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所以在表演时,一定要让他的死带有某种庄严的气派。)”[2]
以上三个主题,包括它们的多元内涵,是不少作家都写过的,例如霍桑的《教长的黑面纱》、托尔斯泰的《复活》、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但是,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主题多半是单一地加以表现,而在《老妇还乡》中,则同时予以表现。由于《老妇还乡》主题的多元性、复合性、多层次性,就构成剧本与众不同的新意。现代社会本来就如此复杂,一件事物的本身,往往有多方面性。这样,读者(观众)的思考就不易简单化,少了些片面性,多了些辩证法。但是,这三个主题又不是平均展开,而是有主有次。剧作家在剧本中给予最有力的讽刺和批判的,还是金钱罪恶的主题。现代文明的法律、公正、人道、正义,在金钱的魔棒下一一现了原形。真实的情况是金钱支配一切,现代社会无法、无公正、无人道、无正义可言,现代文明是十分虚伪的。
这样说有剧本为证。剧本第三幕写小城开市民大会,表决接受或拒绝老妇的建议。剧作家让表决场面重复一次。请看:
市长——一致通过,接受克莱尔·察哈纳西安的赠款。但这决不是为
市民们——这决不是为了钱。
市长——而是为了主持公道。
市民们——而是为了主持公道。
市长——为了良心。
市民们——为了良心。
市长——因为我们决不能纵容罪恶行为。
市民们——因为我们决不能纵容罪恶行为。
市长——让我们除掉那个犯罪的人。
市民们——让我们除掉那个犯罪的人。
市长——从罪恶中拯救我们的灵魂。
市民们——从罪恶中拯救我们的灵魂。
市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最神圣的东西。
市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最神圣的东西。
伊尔(大叫一声)天哪!
(所有的人仍然庄严地举起一只手站在那里,可是正在这时候,拍摄
新闻纪录片的摄影机忽然不知什么地方卡住转不动了。)
摄影师——真要命,市长先生。光源的电线出了毛病。能不能请你把
刚才表决的那一段再来一遍?
市长——再来一遍?
摄影师——让我们能够拍摄下来。
市长——哦,当然可以。
摄影师——行了吗?
一个人的声音——行了。
摄影师——那好,再拍吧。
(市长摆出一副架式来。)
(以下重复一次)
剧作家让表决场面重复一次的目的有二:一是加强讽刺效果,起点题作用。剧本中有好几个主题,什么是主要的呢?剧作家在这里告诉读者(观众)了。二是为了最终完成伊尔的性格塑造,将他的一连串“发现”与戏剧高潮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发现”自己有罪,应该认罪,而且是发现全城人都是伪君子,全城人对他也犯了罪。这当然也起点题作用。剧本写第一次表决时他还惊呼一声,第二次便沉默了,不肯说话。剧作家留下“空白点”,由读者(观众),还有演员去补充。
迪伦马特把此剧定为“悲喜剧”,证明他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老妇复仇主题即美狄亚主题,从古希腊悲剧化出。认罪主题即“复活”主题,源于基督教观念。剧作家创作的重点不在“悲”而在“喜”,把老妇写成喜剧角色,强调其“恶”的一面。他说:“那个老太太的确是个恶棍。”[3]针对金钱的罪恶及文明的虚伪,他用夸张、滑稽、荒诞手法去写,深得阿里斯多芬喜剧的精髓。他不重笔写伊尔认罪,而是淡化其宗教成分,因为宗教已失去往昔的力量。这样就连伊尔认罪也是悲中见喜。剧作家把古希腊悲剧成分与喜剧成分揉合起来,着重以喜剧手法去处理悲剧题材。因此,古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大于希伯莱文化。
迪伦马特在处理情节、冲突、性格三者的关系上,又与古希腊戏剧有所不同而近似于中国戏曲。古希腊悲剧是“冲突”的艺术,从冲突到冲突。冲突的目的是塑造性格,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角色从顺境转入逆境,悲剧性格便塑造成功,如《俄狄浦斯王》。《老妇还乡》剧写法不同,第一幕“冲突”写得极好,迅雷不及掩耳,但这“冲突”快近结尾时才出现。在这以前,伊尔还处在顺境中,宴会还是一片狂欢气氛。因此,第一幕写法是从情节到冲突,并非一上来就是危机,就是冲突。剧本还有二、三幕,伊尔的性格发展,从第二幕才起动。他先从市民纷纷赊欠帐的怪现象发现老妇的建议正在深入人心,自己处境危险。后从警察局长、市长、牧师谈话中发现他们绝非自己的保护人,更加重了精神危机。继而发现家人也站在老妇一边,于是由害怕、恐慌、绝望、思考而认罪。然而在表决大会上,他又发现居伦市民并非因他有罪而判他死刑,而是为了要得到十亿镑而判他死刑,于是顿悟世界的不公道含恨而死。至此,他的性格塑造才最终完成。迪伦马特这种从情节到冲突、从情节发展中慢慢塑造性格的编剧法不是古希腊悲剧的编剧法,与中国戏曲的编剧法倒有几分近似。《墙头马上》、《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例子。
古希腊旧喜剧不以塑造性格见长。罗念生说:“希腊‘旧喜剧’没有多少性格描写。”[4]迪伦马特崇拜阿里斯多芬,但在塑造性格方面却不尾随前人。他的剧本不是如阿里斯多芬那样从情节到情节,而是从情节到性格。
《老妇还乡》除了在情节、冲突、性格三者关系的处理上近似中国戏曲外,其“假定性”的表演手法也近似中国戏曲。《老妇还乡》中的群众演员(市民)同时又是树、鹿、啄木鸟,剧情需要什么演员就扮演什么。如男女主角在林子里回忆往事,有风吹来,装作树木的三个男市民便一上一下地挥动手臂。女主角说:瞧,一只鹿。一市民就扮鹿向一边跳了几步。女主角说:瞧,一只啄木鸟,演员就拿一个钥匙在烟斗上敲着——这是啄木鸟在啄树。与西方写实的表演手法不同,此剧不把生活实景搬上舞台,只是虚拟、假设。剧作家说:“一个剧本的演出,首先应考虑的是舞台的限制和它可能被利用的程度。……因此,居伦城的人在这里扮演树木,这并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5]迪伦马特的表演美学与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是相通的。如果他像布莱希特那样熟悉中国戏曲,他也许还会在东方戏剧中找到更多更有力的论据。《老妇还乡》剧中的演员当众把道具抬上场抬下场,也近似中国旧戏曲中的“捡场”。
《老妇还乡》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表现为“围猎”的意象多次出现。第一次是在教堂左边,老妇在黑豹被市民开枪打死,伊尔却以为市民在围猎他。剧情如下:伊尔去找市长请求保护,逮捕老妇,被拒绝。他看见市长桌上有一把手枪。市长告诉他,老妇的黑豹逃走了,在教堂左边乱窜,市民正在追捕。伊尔又到教堂找牧师,说他害怕所有的人,他们把他当着一只野兽追捕。牧师劝他不应怕肉体的死亡,应怕灵魂的死亡。伊尔看见牧师也拿着枪,牧师说是提防黑豹。这时,教堂外边拿枪的人围成一个半园形,似乎向伊尔包围过来,伊尔以为市民要射杀他了,只听到两声枪响(黑豹被打死),伊尔瘫倒在地。
第二次是在火车站。伊尔决定逃到澳大利亚去,在火车站市民追上来把他包围住了,似乎是欢送,但又不让他走,就是不散开。“伊尔象一只被围的野兽恐惧地望着他们。”他慢慢跪了下去,终于双手捧着头瘫倒在人圈的中心。
第三次是在金使徒旅馆的礼堂。市民表决之后,市长命令伊尔留下,叫市民在礼堂排成一条小胡同,要伊尔从人群胡同里走过去。被老妇收买的体操运动员杀手已站在人群夹道的尽头。伊尔看到两排人向他围拢过来,立即软瘫下去。那两排人围成一团,乱了一阵,随即都慢慢地弯下身去(伊尔已被运动员杀死)。一片沉寂后,那一大堆人渐渐散开。只有大夫还跪在一具尸体旁。大夫站起来,从耳朵上取下听诊器说:“心脏衰竭。”
这是三次“围猎”的场面,第一次以黑豹象征伊尔。第二次写伊尔主观的感受。第三次是真的捕杀。三个场面构成了一个“围猎”完整的意象。
《老妇还乡》剧中“围猎”意象的构思及表现手法,对徐晓钟导演《桑树坪纪事》大有影响。《桑树坪纪事》中也有象征性的“围猎”意象。
例一是村民打死耕牛一场。公社革委会成立,要请县与地区的头头们吃上一顿,用40元硬买下桑树坪小队的耕牛。这牛是桑树坪的命根,村民连打都舍不得。但村民不敢得罪公社干部,竟迁怒于耕牛,便自己动手把牛打死了。耕牛惊惧不安地望着四周一改常态的村民们。最疼爱牛的饲养员李金明首先操起木犁向牛身上砸下去。灯光在音乐中逐渐变成了腥红的色调,整个打牛的场面也随即形成了震撼人心的程式化慢动作的“围猎”场面:村民们发疯似地围打着向四处逃窜的牛,牛躲闪着、翻滚着、哀哭着,突然,它猛地前蹄腾空,一声惨叫站立起来,痛苦而困惑地茫然四顾。一村民在疯狂中扣动了枪机,牛应声倒下,但仍支撑起受伤的身子,哀号着爬向李金明。牛死了,村民在音乐中仰天长跪,悲痛欲绝。徐晓钟说:“打死耕牛‘豁子’这场戏是全剧哲理和情感的高潮。”
例二是“围猎”青女一场戏。在小说(朱晓平作)中,一群愚昧的农民后生撩拨阳疯子福林当众扯下青女的裤子,以证明青女是他的“婆姨”。青女惊逃跪求,孤立无助,终于被福林当众扯下裤子,而村民则心满意足地欣赏由他们一手导演的惨剧。“可怜的青女,不哭,不闹,不感,不叫。精赤着那玉石一样的身子,呆滞的目光望着天空。”编剧者把小说这段情节改为“围猎”的意象,同样作了诗意的升华:
李福林残忍,但却天真无邪地带着陈青女的裤子,下。歌队——村民们在音乐中渐渐散开,一尊残破但却洁白无瑕的侍女古石雕出人意外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扮演许彩芳的演员将一条黄绫肃穆而凝重地覆盖在古石雕上。歌队——村民随着扮演许彩芳的演员,一起跪倒在古石雕的四周。
这还是“围猎”,只不过美化了青女与村民。如同围猎耕牛的最后,转化为祭祀。祭祀是从“围猎”化出的,“围猎”是基调,祭祀只是升华。
徐晓钟在导演《桑树坪纪事》剧时构思了“围猎”的意象,确实是精彩的一笔。“围猎”耕牛这场戏确实是《桑树坪纪事》剧的压轴戏,它大大加强戏剧的悲剧性,具有多元的内涵,发人深省。
这里着重谈的,是徐晓钟编剧法的灵感从何而来?试将《老妇还乡》的“围猎”场面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大胆下一个断语,他的灵感来自《老妇还乡》。
现在再谈谈迪伦马特的另一部剧作《物理学家》。这是二幕喜剧,讲三个物理学家被终身监禁在疯人院的故事。剧情如下:在一所疗养院(实为疯人院)的一个晚上,一个疯子(自称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一个女护士勒死了。警官来了。三个月前,另一个疯子(自称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也把一个女护士勒死了。警官传达检察官的提议:必须由男护士代替女护士。疗养院的负责人博士小姐只好同意。
就在这天晚上,就在爱因斯坦勒死女护士之后,疗养院第三个疯子默比乌斯把第三个女护士勒死了。因为看护他的女护士识穿他非真疯子,还爱上他。她向他告别,说明天将由男护士取代她。默比乌斯害怕她洩露秘密,便把她勒死了。
原来三个“疯子”都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牛顿是东西方派来的间谍,他们为了窃取第三个“疯子”默比乌斯的科学发明,装疯进入疯人院。他们另有真名,但自称爱因斯坦和牛顿,这是装疯的表现。由于情况发生了逆转,明天男护士将代替女护士,这两个间谍将出不去了。于是,就在这天深夜,他们向默比乌斯公开了身份,要他交出手稿,跟他们回国去。两个间谍为了争夺默比乌斯,彼此还掏出了手枪。原来默比乌斯是天才的核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能用以发明一切的万能理论体系。他害怕这一科学成果被东西方大国用于军事目的而导致人类的毁灭,便胡诌出什么“所罗门”向他“显灵”,装疯卖傻,抛妻弃子,躲入疗养院。他说服两个间谍留下来,因为“我们不住疯人院,世界就要变成一座疯人院。我们不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人类就要消失。”这两个间谍也有科学良知,便同意了。
这时博士小姐突然出现。原来这个50多岁的驼背老处女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她是个垄断资本巨头,有自己的特务机构。尤其可怕的,她有精神病,幻想统治全球。她宣布她才是“所罗门”的代表,“所罗门”派她来统治全世界。她已偷拍了默比乌斯万能理论体系的所有资料,建起一个强大的工业托拉斯,将夺取各大国各大洲及拿下太阳系,而三个物理学家将永远被监禁在这所监狱里。三个物理学家大惊失色,惊呼“世界落入一个癫狂的精神病女医生手里”。于是,一个又自称“爱因斯坦”,一个又自称“牛顿”,一个又自称“所罗门”,走回各自的房间。
《物理学家》剧受古希腊戏剧编剧法的影响大于《老妇还乡》。影响之一是“三一律”。迪伦马特是“三一律”的拥护者,认为它“来源于希腊悲剧,构成了戏剧的典范”。“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在戏剧素材的处理上需要最大的精确性,最大的节约和最大的简化。”[6]此剧的地点就在疗养院,时间就是一个晚上,情节也只有一条——默比乌斯的故事。在迪伦马特的剧本中,论“精确”、“节约”、“简化”,没有另外的剧本能出其右。所以此剧是现代戏剧运用“三一律”的典范之作。
影响之二是古希腊旧喜剧。迪伦马特说:“喜剧意味着一个正在建立而已经完全颠倒了的世界。”[7]这是从阿里斯多芬喜剧中得出的中肯结论。他又认为现代社会不可能产生悲剧,产生英雄。他说:“我们的世界就像引向原子弹一样地引向怪诞荒唐”,“我们的权利就是喜剧”[8]。剧作家的悲观观念在《物理学家》剧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物理学家》剧中,没有英雄。三个女护士是可怜的,可同情的,是男性的牺牲品。三个科学家也不是英雄,那两个间谍固然不是,默比乌斯也不是。他逃避斗争,躲入疯人院,害了妻子,勒死爱他的女人。莫尼卡护士临死前质问他:“您为您的信念奋斗过吗?”他无言以答。再问:“您为什么这样没有勇气呢?”他的回答更荒唐:“处在我这种情况下,勇气是一种罪行。”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伽利略传》的声音:“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三个物理学家不是悲剧性格最有力的论证在于此剧的结尾:在博士小姐的淫威下,他们不敢有一丝一毫反抗,连起码的愤怒和抗议也没有,如同三只小虫子,乖乖地爬回各自的房间。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反抗是无用的,世界本来如此。他们完全是喜剧性格,最后也真地在演戏了。在此剧结尾,剧作家用喜剧——甚至闹剧——手法塑造他们的意图最为明显。
迪伦马特用“三一律”去写喜剧,应说是创新。古希腊人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古希腊的“三一律”是用以写危机与冲突的悲剧的,但《物理学家》剧并无危机,亦无尖锐的冲突。本来可以有的,剧作家编偏让它没有。三个科学家勒死三个女护士,本来惊心动魄,但三个女护士服服帖帖地被勒死了。两个间谍向默比乌斯摊牌,本可构成尖锐的冲突,但矛盾立刻就解决了,没有冲突起来。博士小姐突然以真面目出现,本是最尖锐的冲突,但三个科学家立即“俯首就擒”,根本没有冲突。剧作家用“三一律”保证剧情处理的最大的精确、节约、简化,一句话,保证剧情的集中紧凑,而有意不写角色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把崇高、严肃、恐怖化为滑稽、荒诞、可笑,变悲剧素材为喜剧,“于是三一律再次得到了胜利”[9]——在现代喜剧中的胜利。
迪伦马特不仅写戏,还写戏剧理论。他的“偶然事件”论与李渔的“立主脑”说不谋而合,颇可比较。他在阐释《物理学家》剧的编剧法时说:
我不是从命题,而是从故事出发的。既然从故事出发,就不能不把它想透彻。如果故事的进展骤然间发生极坏的转折,那就必须把这个故事想透彻。极坏的转折并不是能事先预见到的。它是通过偶然事件发生的。剧作家的艺术就在于:在情节中恰到好处地插入偶然事件。[10]
迪伦马特不仅重视“三一律”中的一个故事,他尤其重视这一个故事中的“偶然事件”。他所说的“想透彻”,不仅指一个故事,尤其指一个故事中的“偶然事件”。他这段话的核心是在最后一句。如果剧作家能在情节发展恰到好处时插入偶然事件,就见艺术水平。
《物理学家》剧的“偶然事件”是什么呢?是换护士。由于两个“疯子”勒死了女护士,检察官便要求疗养院把女护士统统换成男护士。莫尼卡护士因此必须向默比乌斯告别,便引发默比乌斯勒死她的情节。两个间谍要出去,便向默比乌斯亮出身份,便发生了后来的剧情。换护士确实是“偶然事件”,是事先谁也料不到的。换护士这个偶然事件确实引起了情节“极坏的转折”,对推动剧情的进展举足轻重,确实要“想透切”,方能在“恰到好处”时插入。
以上说明,迪伦马特所说的“偶然事件”,非亚里斯多德的“一事”,而是亚氏“一事”中的一个关键情节。迪伦马特认为写好它乃写戏的决窍。
我们来看看李渔。李渔戏剧结构论的核心是三句话:“立主脑”、“一人一事”、“一线到底”。这里有两点宜注意。第一,这三句话是一个意思。李渔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止为一线到底,……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只有一人也。”第二,李渔的所谓“一事”,并非指一个故事,而是指一个牵动全剧戏剧冲突的关键情节,在《琵琶记》中指“重婚牛府”,在《西厢记》中指“白马解围”。“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11]如果没有蔡伯喈“重婚牛府”这个关键情节,《琵琶记》后来的故事便无从谈起。没有张君瑞的“白马解围”,《西厢记》就写不下去。李渔认为“立主脑”极重要,剧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否把主脑立好。李渔一再强调剧作家构思时一定要把主脑想深想透,创作时一定要使剧情紧紧围绕主脑展开。
李渔这些理论,与迪伦马特不谋而合。迪氏的“偶然事件”即李渔所说的“主脑”,他们都认为这非指一个故事,而是指故事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他们都认为这个关键情节是剧中人始料不及的,剧作家的本领在于擅长于在情节发展恰到好处时插入,以推动剧情的发展;他们都强调剧作家要想透、写好这个关键情节,剧本才能获得成功。迪伦马特从《物理学家》默比乌斯这一个故事中抽出“偶然事件”来大谈特谈,正如李渔从《琵琶记》、《西厢记》中抽出“重婚牛府”、“白马解围”来大谈特谈一样,都是独具慧眼,深知编剧法三昧。
所不同者,迪伦马特的“偶然事件”论建立在悲观的哲学上,他认为“世界只是个偶然事件”[12]。李渔的喜剧理论则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上,他并不认为世界是个偶然事件,他要用笔歌颂康熙的太平盛世,顺历史潮流而动。他说:“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
从编剧艺术的角度说,二人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迪伦马特是亚里斯多德的拥护者,是古希腊戏剧的崇拜者,他是在“三一律”的理论海洋中游泳,在写一个故事的前提下来谈“偶然事件”,可说是亚里斯多德“一事”论的发展。而东方的李渔的戏剧理论与亚里斯多德完全不同。李渔主张写多情节多线索的喜剧[13],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类似于写莎士比亚式的喜剧。他的“立主脑”说是如何写好多情节多线索喜剧的理论,他认为只要“立主脑”,则情节再多,线索再繁,剧本也不会如散珠碎玉,而能保持统一。
迪伦马特是西方文化圈的剧作家,东西戏剧分属两个迥然不同的体系,但因为都是戏剧,又并非截然不能相通。迪伦马特的“偶然事件”论与李渔的“立主脑”说都说了与亚里斯多德不同的话,在主要方面又不约而同,就说明这一点。
注释:
[1]迪伦罗特《老妇还乡》“作者后记”,黄雨石译,见《迪伦马特喜剧选》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迪伦罗特《老妇还乡》“作者后记”,黄雨石译,见《迪伦马特喜剧选》第315-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迪伦罗特《老妇还乡》“作者后记”,黄雨石译,见《迪伦马特喜剧选》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罗念生《阿里斯多芬喜剧集》序,见《阿里斯多芬喜剧集》第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迪伦罗特《老妇还乡》“作者后记”,黄雨石译,见《迪伦马特喜剧选》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迪伦马特《戏剧的问题》(1955),刘安义译,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7]迪伦马特《戏剧的问题》(1955),刘安义译,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8]迪伦马特《戏剧的问题》(1955),刘安义译,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9]迪伦马特《戏剧的问题》(1955),刘安义译,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迪伦马特《关于〈物理学家〉的二十一点说明》,叶廷芳译,见《迪伦马特喜剧选》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以上引文均见《李渔全集》第3卷《闲情偶寄》第8—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2]迪伦马特《戏剧的问题》(1955),刘安义译,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3]详见拙文《李渔的‘一事’并非亚氏的“一事”》,《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