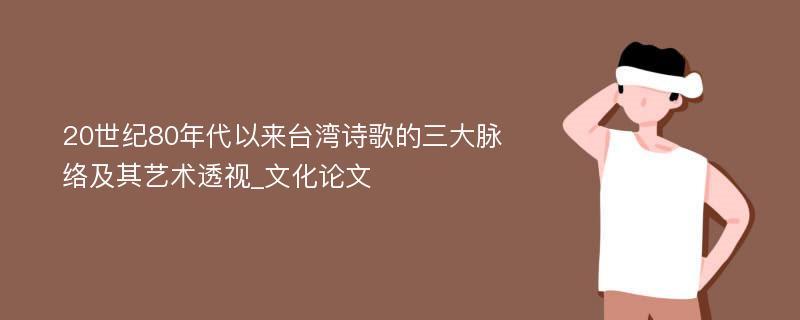
8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的三大流脉及其艺术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台湾论文,视角论文,年代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年台湾诗坛的三大群落,其观照视角可概括为“中国”、“本土”和“世界”的。“中国”视角者从新古典主义到“大中国诗观”的建立,其势方兴未艾。“本土”视角者从一般乡土情怀到承载特殊政治内涵的本土精神乃至台独意识的表现,总体呈衰颓之势;“世界”视角是资讯时代世界一体化趋向的产物,渐成诗坛主流。
关键词 台湾诗坛 艺术视角 中国 本土 世界
“乡土文学论战”后台湾文学呈现的明显演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首先是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瓦解,使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政治上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呈现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的一体化倾向。在中国国内,大陆方面继续推进改革和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这一切,必然对台湾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岛内政局发生的“强人”消逝等结构性变革,思想文化界也面临激烈的震荡。思想的纷纭,交锋的频繁,抉择的多样化,使文坛(包括诗坛)产生了多元发展的可能和必然。
文学的变化自然还取决于内部各种艺术因素的传承、超越关系。而8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的内部特点,即在于数十年来文学经验的共时汇聚。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观念意识,使同时汇集于诗坛上的各代诗人们更能容纳异己和吸取多方面的艺术营养。1981年痖弦在《联副30年文学大系》总序中,明确归纳出有关文学创作方向的几项意见: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精神;二、采纳世界性现代文学的表达技巧;三、掌握台湾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代意识。另一位诗人杨牧也称:“经过三十年的淘汰修正,诗人对横的移植、纵的继承已不再持排斥性看法,西洋的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以及早期台湾的历史风貌,均同时为诗人们所采纳运用,这是文学史上健康正确的发展方向。”[①]这些类似的概括,说明它已成为台湾诗坛一个广泛的共识。
在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下,不同的诗社、诗人延续着各自不同的诗歌脉流和理念加以发展,显示出形形色色的艺术追求和倾向。从宏观角度看,主要存在着三大群落,其各自不同的艺术观照视角和趋向,可简略地概括为:“中国”的,“本土”的,和“世界”的。
“中国”的观照视角
所谓“中国”的视角和趋向,是由一批亲历4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乱,后来到台湾的前行代诗人,如“蓝星”、“创世纪”诗人所主导。这批诗人在60年代为了表达内心“刀搅的焦虑”,向西方借来现代主义的表现策略,表面上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其实无法忘却民族的兴衰和前途。他们怀有较强烈的“中国情结”,从未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此时面对台独势力膨胀的客观现实,其诗作益发以“祖国”、“民族”为重要思考对象,以其认同的整个中华民族同胞的生活为抒写题材。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曾着迷于“横的移植”的现代派诗人,其中不少已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转向所谓“新古典主义”——或力图再续中国古诗抒情传统,或倾力寻求西方现代派与中国古典文学在表现方法上的契合之处。1980年前后,以古代圣哲为题材融入现代感思的诗歌创作一时蔚为风尚,主要作者包括余光中、洛夫、张默、彭邦桢、张健、管管等老一代诗人,也包括较年轻的罗青、萧萧、罗智成等。他们通过咏史叙事、写人状物,寄托情怀和心绪,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这一新古典主义的追求,由于结合了对所谓“现代化神话”的反思而增加其深刻性。这种反思使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叶维廉指出:“洋”的不一定不好,只是我们不能陷入殖民者制造出来的“现代化”的迷思,“基本上,这个神话化的说词,把原是模棱吊诡的现代化文化——亦即是既有解放作用亦具人性减缩宰制暴力的现代化文化说成人类福祉,看成最合理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西方霸权可以不费一颗子弹,利用全球经济整合的美词达到其目的:麻木民族文化的自觉、制造仰赖情结,透过文化工业把原有的文化力量消之无形,催生“轻文学”来取代台湾本有的严肃的文学;面对此,这阶段的重要任务即是摆脱仰赖情结,而这必须牵涉受过外来文化教育的精英分子“对自己已经不假思索地内在化的外来思想的反思”,即“不应该接受宰制者现存系统的模式,也不应该没有反思地回归过去的传统”。[②]正是在此认知下,这批诗人对于“现代”和“传统”的问题再次投以极大的关注。他们提出了吸收传统、反哺现代,把新与旧、现代和传统熔为一炉而冶之等方针。洛夫写道:“中国新诗的建立,必须承受外来的与传统的双重影响,偏于一方均为不宜,西方的肥料和栽培固不可缺,但无论如何,中国诗这株奇葩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始得以成长茁壮。”[③]他并以早期台湾诗坛未经批判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从而造成紊乱,直至70年代后受到强烈批评,才促使诗人们检讨和调整,并对传统的价值重加评估的经验教训,进行现身说法式的告诫。
1987年赴大陆探亲的开放,使这些诗人得以亲炙于中国万里江山和千年历史文化之中,了却乡愁而又开阔了文化视野。他们以“探亲诗”的创作赋予旧有的“乡愁诗”以新的内涵和境界,表达了自己与中国的难以阻断的血肉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所谓“大中国诗观”[④]。洛夫写道:“也许我们诗坛今天面对的是一次新的蜕变……进行这一辩证式的蜕变,一则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再则必须加入一些新的变数。在现阶段,我认为变数之一就是诗人至少应将一半的心思投注在对大中国的关怀上。台湾现代诗六十年代的主调在于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七十年代的主调在于表现社会的变化和对乡土的拥抱,八十年代的主调则转移对城市生活感受、生态环境与电子资讯的探索。我觉得台湾现代诗发展的轨迹丝毫未乱,问题是何以诗人愈来愈多,而读者愈来愈少呢?我想原因之一,乃在诗愈写愈冷。诚然,现代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情感的冷处理,但不能没有人味,不能不对大民族的忧患心存关切。”又称:“今后诗人是否应该调整音量,扩大而深入到大中国的心灵?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抉择,更是一项为了挽救现代诗的颓势而必须面对的挑战。”[⑤]显然,“大中国诗观”乃是当代台湾诗歌中的乡愁主题和“新古典主义”一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合乎情理的延续和发展。它将挽救现代诗的衰颓和对国家、民族承担责任的使命感相结合,因而具有深刻性和号召力。从“新古典主义”到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厘定再到“大中国诗观”的建立,代表着这批诗人不断演进的心路历程。
“本土”的观照视角
近年来台湾诗坛的第二个主要群落——标举“本土”的诗人群,主要由“笠”为核心而组成。李敏勇《台湾在诗中觉醒》一文写道:“战后的台湾,从农业性、乡村性的社会转变到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但是,农业凋疲,工业纷乱;乡村不满,都市不安;甚至形成乡村已消失而都市未真正形成的社会基盘崩坏现象。‘笠’穿越了变迁的时代,认识、记录、思考、批评了这样的现实经验。”“战后的台湾,在国民党类殖民统治的威权体制下,面对着血腥肃杀、白色恐怖以及各种的政治弹压、追求近代独立民主国家的政治改革运动,从未曾死灭的人民心灵燃烧出前仆后继的烙痕,寻求人权、民权与主权的憧憬。‘笠’参与了追寻的行列,也反映了这样的意志和热情。”[⑥]这两段话概括了“笠”诗人创作的两大主题。如果说前15年的“笠”更多地倾向于前者,那么近15年则更凸显了后者。或者说,这两段话勾勒出他们30年来创作发展的明显轨迹。一是在题材上,由反映一般社会、经济层面的现实向着更多地反映政治层面的社会现实的方向转变。二是在内在精神上,由一般地表现爱乡爱土的情怀,向着更强烈地表现承载了特殊的历史、政治内涵的本土精神乃至“台独”意识的转变。这种趋向和上述“大中国诗观”可以说背道而驰。
在80年代前期就已大量出现的所谓的“政治诗”,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狱中诗”,出自当过“政治犯”的诗人之手,正面或侧面地以牢狱生活为题材。它们与当时文坛出现的“牢狱小说”相呼应,将笔触直接指向统治机器的重要部位,将其压制民主,罗织罪名迫害异己的内幕曝光。二是以“二二八”、“高雄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揭露台湾当局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行径。三则是所谓“人权诗”,控诉当局以“戒严法”、“国安法”等严密控制并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乃至基本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或对政治高压下苟安退避、不思反抗的人权意识低落现象加以影射和批判。
8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诗”的一个明显的发展,是本土意识乃至分离主义意识的膨胀和浮上台面。名称由“乡土”改为“本土”,固然因乡村萎缩、都市膨胀,再称“乡土”已不确切,但其中也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在内。部分诗人在抒写因台湾人民的特殊经历而形成的历史的“悲情”时,不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立足于吸取历史经验,弥合历史伤痕,而是有意强调和加深所谓省籍矛盾,并片面宣扬针对中国的所谓“主体性”或“独立自主性”。更有甚者,他们在各种言谈乃至诗作中直接表达了追求台湾独立建国的论调。痖弦所谓文学发展三大方向之一的“掌握台湾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代意识”,其本意在部分诗人手里遭到扭曲。
与此相应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所谓“台语诗”的提倡。致力于此的除部分“笠”诗人外,还有90年代新成立的“蕃薯诗社”等。早些时候的“方言诗”乃是立足于乡土事物和情怀的生动表达,而“台语诗”的出现却具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某些人那里,所谓“台语”及其“文字化”等的提出乃是作为建立所谓“独立的台湾文化”的重要一环,而此“文化”的型塑又被视为所谓独立的“台湾民族”成立及其国家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当然,并非所有的“本土”诗人都持相同的观点。如杜国清指出,面临这些对台湾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抉择,每个人的看法甚至有着相当的歧异。对于文学创作者,“传统的重要,艾略特早就谆谆告诫。一个创作者的最大挑战来自传统,而他在创作上的评价,也只有与传统的伟大作家并比之下,才能定位。做为一个台湾诗人,只要在创作上使用的是中文,他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挑战。而他的创作成就,终将归入这个传统。”至于“台语诗”,杜国清也认为这基本上是政治影响下的一个问题,是台湾意识高涨,以及国民党当局过去对“台语”的压制而造成的一种反弹现象。他指出:“一个诗人的伟大,往往在于如何精练本族的语言,使之更加纯粹优雅。”“谁也不必否认,台语做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语言,有多么鲜活生动,可是,谁都不得不承认,台语做为一种文学创作的语言,有多么困难。……文学创作,免不了有地方色彩,如何提炼方言,使之加入、丰富、充实大家共通的现代汉语,我想才是创作者在有限的一生中,能够创造出优越作品的客观条件。基于政治压迫而造成反抗的理由,企图使用方言,以取代大家共通的现代汉语,由此而希望创造出大家都能接受和欣赏的作品,恐怕主观的愿望多于客观的可能性。”[⑦]这可以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所谓“台语诗”等的盲点。
应该说,本土意识如果作为一种认同生我养我之土地和人民的扎根的自觉,或者作为对抗战后新殖民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一种认知,应是无可厚非的。但在部分诗人那里,本土意识被严重地政治意识形态化了。这时它对诗创作就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尽管他们有时也强调政治诗的写作应注意艺术的经营,不可流于概念和口号,但由于其政治理念本身的舛误及过于急切的情绪表达,造成了普遍的艺术粗糙浅露的弊端。如发表于《笠》第182期上的《为台湾写的诗》一作,几乎就是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行列出。这类“作品”其实已经不是“诗”,至多只能算蹩脚的政论而已。由此可知,虽然“本土”取向的诗常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发挥了指摘时弊、攻击暴政的作用,但也有许多显示的是“诗”的倒退。
“世界”的观照视角
如果说上述两大趋向中,老一代诗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所谓“世界”的观照视角和趋向乃是由年轻一代(所谓“新世代”)诗人所主导。前两种取向的诗人都有着对民族、国家的复杂历史情绪和某种使命感,只是一者包容着整个中国,一者拘囿于台湾。但对年轻诗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试图超越所谓“中国”或“台湾”的政治争执,将其前辈对于民族、国家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心和思虑,或思考一些人生、人性更本质的东西。这种情况的产生,显然与交通、资讯的发达所带动的世界一体化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有关,也与台湾的日益都市化带来的政治力减退、经济力和社会力上升的情况紧密相连。当然,所谓“世界”的,并非排斥“中国”或“台湾”,而是纳其入内。一些80年代成立的新诗社常将“心怀乡土、献身中国、放眼世界”[⑧]作为其创刊立社的口号或宗旨,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具体而言,所谓“世界”的观照视角,并不仅在于取材范围从“台湾”、“中国”扩大到“世界”,更主要的是体现于视野、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上。
1979年12月成立的“阳光小集”,由于集合了当时台湾一批最著名的年轻诗人而成为诗坛承前启后的重要诗社,其主要倾向仍是70年代“承续传统”和“关切现实”两端。然而,也是这个“阳光小集”开始显露了新的观照视野和时代特色。由于“世界”视角的产生得助于资讯时代的来临、“地球村”的逐渐成形、多元化的都市社会的日趋成熟等,因此这种“世界”的视野,主要即意味着对资讯时代的一种感应,对多元观念的一种服膺。《阳光小集》第十期社论《在阳光下挺进》中表示:“不强调信条、主义,不立门派”,要在这“社会已趋多元化的时代”里,不求“纯粹”而求“不纯”地为大众提供一份精神口粮。除了诗人外,它还容纳了画家、歌手等,除了出版诗杂志外,还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活动,目的就在“以诗为中心,尝试各种媒体与诗结合的可能性”。显然,资讯时代的新理念已渗入诗社,后现代的多媒体创作和大众文化倾向,在此露出了先声。
1985年5月,诗坛出现了一个明确标举“都市诗”的诗刊——《四度空间》。创刊号上《80年代的诗路》一文,概括了他们的诗观和宗旨,主要有:一、除了直线的继承外,也要横向的融合,不盲目趋附,也不自我封闭,要延续传统新诗优点,又要融合更多前卫性思想,如此才能开创出中国新诗独具一体的高潮时期;二、现代人类大多生长在都市环境中,因此都市诗、社会诗、生态诗以及前瞻性的科幻诗,都是目前所应发展的重要方向,这样既不会被局限于狭隘的乡土观念,又可保有基本的本土意识。这篇文章提出了加强“横向的融合”,这对于70年代以来强调纵向继承、批判横向移植的潮流,可说是一个勇敢的叛逆。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为现代主义解了咒,堪称现代主义在80年代台湾诗坛复苏的征兆之一。
“都市诗”不以都市素材为界说,注重的是都市精神的把握。而在挖掘现代都市人的心灵特征方面,新世代诗人有着比其前辈更突出的表现。人际关系隔阂产生的孤寂,机械式运作导致的无聊,自我被撕裂的痛苦,表里不一、无法率性真诚的悲哀,社会角色被派定、理想落空的无奈,核战威胁的梦魇……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焦虑不安的集体潜意识,其恶性发展,便是普遍的精神畸变现象。这些都是林或、许悔之、侯吉谅等诗人经常表现的主题。这时频频出现的科幻诗,是都市诗的一个特殊种类。它作为人类遭受物质文明压迫的精神外射,常表达对科技文明的潜在威胁和人类集体自我毁灭倾向的迷惑和不安。如果说从乡村到都市标志着地域性的减退,世界性的加强,那科幻诗由于处理的常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更成为台湾新世代诗人扩展了世界性、宇宙性视野的最佳例证。如陈克华的诗作常展现一幅文明轰毁、人类灭亡,整个世界退回原始时代的图象,以此向人类敲响警钟。而林耀德的科幻诗同样具有涵盖世界、宇宙和人性本质的宽阔视野。
紧接着诗坛又出现的一面醒目旗帜是“后现代”。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学思潮是伴随着后工业社会而出现的。1986年,罗青以《后现代状况出现了》为题为“四度空间”五诗人合集《日出金色》作序,以其前卫诗人特有的敏锐指出台湾后工业文明状况的萌发,并在复刊的《草根》上进行“后现代诗”的理论建树和实践,为这一新兴诗潮推波助澜。罗青罗列的后工业文明现象,一是电脑、电视、电话、复印机等资讯媒体的发达,二是社会财富遽增而带来的消费膨胀,以及由此二者引起的其他方面的诸多变化,如社会整体的日趋多元无序状态,复制、假冒的盛行,精神分裂、理想主义消失等社会精神状态的弥漫。后现代的诗表现,除了对上述后工业文明状况的直接描绘、反映和省思外,还呈现两个重要的指向,一是对资讯乃至传播媒介本身可靠性的质疑;二是为适应大众消费需要和资讯时代人们审美方式而在艺术传播方式等方面所作的变革。这时新成立的一些诗社如“地平线”、“新陆”、“曼陀罗”等,一开始就表现出视野扩大、意识更新、多媒体应用、注重包装、与读者亲和等取向,都可说是感应着新诗潮而出现的。
“后现代”诗潮对于艺术方式的扩展,主要有拼贴组合、诗的多媒体化以及电脑诗、录影诗等的创作。如拼贴、组合等的大量运用,实际上是迈向世界一体化时代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审美经验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杜十三在《四度空间的历史社会观——浅谈资讯时代的艺术形态》一文中写道:“只有数十年时间,继飞机、电话之后,电视、电脑、传真机、镭射……等等高科技的迅速崛起,霎时间使地球变成了村庄,却又使电子变成了宇宙;使整个人类的历史压缩成为一个‘昨天’,却又使现代膨胀有如飘渺的未来……而我们活着,已然是活在一个包含所有人类呼吸,以及古人嚏声和来人胎动的历史社会里,是四度的,而不是三度的空间了。即将进入后工业时期的现代人,家里可能仍然摆着祖先的牌位,却又供着电脑的设备,早上在东京看朋友,晚上在家看杨贵妃……在这种‘时无定时’、‘象无定象’的空前的生活方式里,几乎一切即定的现象都可以用新的观点重新被‘解构’,依照个人的需求重新被组合,时间和空间,慢慢的可以当成生命的零件前前后后的加以利用,而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种没有秩序的新秩序,一种没有规则的新规则。”
后现代诗的得失和未来发展尚有待观察。它的理论和创作,无可否认地带着较浓厚的舶来色彩。它的出现表现了台湾年轻作家们的一个强烈愿望:面对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地球村”时代,他们尝试着借助对一个新的世界性文化潮流的同步或准同步引进,使自己尽快跻身于世界主流文化的行列中。因此可以说,后现代诗的崛起最有力地证明了新世代诗人放眼宇宙的视野,走向世界的急迫愿望和努力。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代台湾文学本来就包含着“本土”的、“中国”的和“世界”的等因素,并形成了具有排它性的发展脉络,先后在诗坛占据重要位置。而它们在80年代的同时凸显,与这一时期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相对而言,“本土”的视角由于其拘于一隅的偏狭性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舛误性而必然地呈现衰颓之势;“中国”的视角由于极大地扩展了以前被隔绝和阻蔽了的文化视野,力图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当前正方兴未艾;而涵纳了“中国”和“本土”的不再是照搬西方的“世界”的视角,由于顺应了时代潮流,更是大势所趋,已经或正在成为当前台湾诗坛的主流。当然,一个诗人无法脱离他立足的土地而升天,无法割断其文化的血脉而存活,也无法自我封闭而发展。也许,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综合的路线,才能为跨世纪的台湾诗坛开辟更坦荡的前景。
注释:
①杨牧:《谈台湾现代诗三十年》,载《创世纪》第65期,1984年10月。
②叶维廉:《被迫承受文化的错位》,载《创世纪》第100期,1994年9月。
③1988年1月30日洛夫致《诗歌报》主编严阵的信,载《华夏诗报》总第30期,1988年9月。
④洛夫:《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沉思》,载《创世纪》第73~74期合刊本,1988年8月。
⑤洛夫:《现代诗新的困境与蜕变》,载《创世纪》第77期,1989年11月。
⑥李敏勇:《台湾在诗中觉醒》,载《笠》第170期,1992年8月。
⑦杜国清:《笠·台湾·中国·世界》,载《笠》第151期,1989年6月。
⑧罗青:《专精与秩序——〈草根宣言〉第二号》,载《草根》总第42期,198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