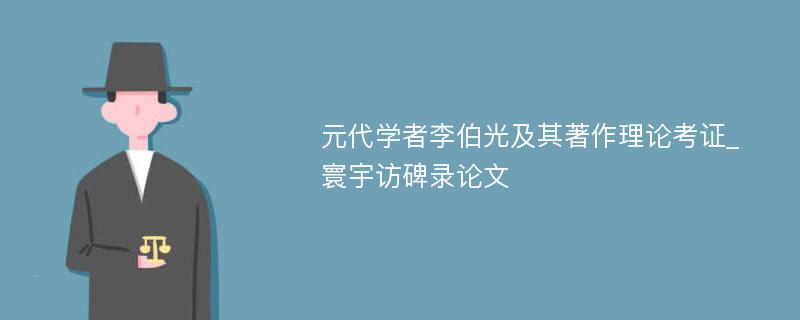
元书家李溥光及其书、论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家论文,溥光论文,论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4)05-0049-07 李溥光为有元一代著名书家,因善榜书大字而深享时誉,与赵孟頫名声相埒一时,所著《雪庵字要》专论楷书大字技法与审美标准,言简意深,颇具实践指导意义,在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后人对其人、其书、其论皆知之甚少,现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求资料的基础上成此拙文,以期最大限度恢复其历史真面,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李溥光的生平 李氏生平事迹正史不载,仅散见于元明笔记小说和诗文集中,方志亦只有寥寥数语之记述,所记不出名、字、号、里籍、历官、所擅、事迹等。 如元夏文彦《图绘宝鉴》载: 宗师溥光,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善真行草书,亦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俱成趣。[按,大同,地名,今山西大同市。辽为西京大同府,重熙十七年(1048)分云中县,置大同县]。 又明李侃、胡谧《成化山西通志》卷九载: 李溥光,大同人,号雪庵,自少为头陀,深究宗旨,雅好吟咏,喜与士大夫游。见闻日富,篇帙浸多,尤喜作大字,当时宫殿城扁皆出其手,寻为昭文馆大学士。有《雪庵长语》、《大字书法》等集行于世。 又清顾嗣立《元诗选·雪庵集》载: 溥光,字玄晖,大同人,自幼为头陀,号雪庵和尚。深究宗旨,好吟咏,喜与士大夫游。尤工大字,与赵文敏公孟頫名声相垺一时,宫殿城楼扁额皆出两人之手。亦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大德二年(1298)文宗(应为成宗)降旨来南阐扬教事,椎轮葛岭,后诏蓄发授昭文馆大学士,玄悟大师有《雪庵长语》、《大字书法》行于世。 此外,元陈基《夷白斋诗话》、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叶盛《水东日记》、陶宗仪《书史会要》等文献中对李溥光亦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内容均大同小异,使我们对李氏生平只能知其大略。限于资料,现对其生卒、交游及书艺等内容略加考述,以期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历史真面。 1、生卒享年 李氏生卒不见史载,只能征引相关资料作出大致推断。明徐一夔《始丰稿》卷八《题雪庵临兰亭帖》载: 雪庵昔在至元、大德间,以楷书大字名世,所书碑版至径寻尺,今犹有存者,而未尝见其小字。钱塘锡上人示余以所临禊帖,其后有宋牟大理巘、元赵承旨孟頫跋语。雪庵自疏云:“予书此帖时年七十有二,颇自诧其妩媚气”。大理公有文学重望,承旨与雪庵同朝,书法妙绝,名不在雪庵下,咸相推重。予不解书,窃谓雪庵字画譬如相马,不当贵肉而贵骨也。知书者以为何如? 据此可知李氏在元初“至元、大德间(1264-1307)以楷书大字名世”,享寿不低于72岁,但于其生卒年仍不可知。据《元书》卷九载,牟巘生卒年为1227-1311,享年84岁,湖州人,历大理少卿,浙东提刑,入元不复仕,有《牟氏陵阳集》行世。赵孟頫曾多次书写由牟氏撰写的碑志,二人最后一次合作撰书《湖州妙严寺碑记》在1309年7月31日前后,①是年牟氏81岁,距过世仅有两年时间,想必已年老体弱,不可能再提笔作文,为李氏作跋时间也不会晚于此。假定是年牟氏为李氏作跋,时李氏“年七十有二”,其生年可逆推为1237年。鲜于枢《雪庵像赞》中有“总角问道今白头,始知斗擞为清修”②的诗句。该诗作于何时无从得知,但最起码应在1301年(鲜于枢卒年)之前。若按李氏生年为1237年推算,此时李氏年龄为64岁,也应该“白头”了。若再上推几年,李氏“白头”则更合常理。又张雨《李雪庵学士写竹枝》中曾云:“昔我入朝皇庆初,及识此老苍眉须”。③按,皇庆间为1312-1313年,皇庆初当指1312年,按李氏生于1237年推算,此时李氏75岁,亦符合“此老苍眉须”的描述。下面再来推断一下其卒年。 明陶宗仪《辍耕录》卷四《前辈谦让》载: 延佑间,兴圣宫成,中宦李丞相邦宁使奉太后懿旨,命赵集贤书额。对曰:“凡禁扁皆李雪庵所书,公宜奏闻”。既而命李、赵偕至雪庵处,雪庵曰:“子昂何不书,而以属吾耶?”李因具言之,雪庵遂不固辞,前辈推让之风岂后人所可企哉。 延祐间仁宗当朝,在位时间为1314-1320年。上文称赵孟頫为赵集贤,说明此事当在1316年7月赵进拜翰林学士承旨之前,故此事当发生于1314-1316年。此间赵正仕于大都(1318年4月25日因管夫人疾作,始离开大都,一直定居吴兴,又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贤乐堂记》载: 延祐四年□月□日,诏作林园于大都健德门外,以赐太保曲。出且曰:“今为朕春秋行幸驻驿地”。有司受诏,越月而成……。命臣赵孟頫具名以闻,于是请名其堂曰:“贤乐之堂”……。即日命昭文馆大学士臣溥光书以赐之,太保公复俾孟頫为之记,以表上恩。 可见延祐四年(1317)李仍在世,且能书匾,表明身体状况尚佳。如按其生年为1237年推算,此时李氏已80高龄,垂垂老矣。若将其生年上推十年,此时李氏90岁,书匾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但85岁能书匾的可能性却还是有的,依此来看对李氏生年的推断误差约在五年左右。有关李氏活动有系年的记载止于1317至1322年)④,于时间、地点正相吻合。这说明李氏于1314-1316年间仍在世,其卒年或距此不远。保守一点估计,若李氏享年90,卒年最晚不过1327年。李氏与赵孟頫(1254-1322)、邓文原(1258-1328)、程钜夫(1249-1318)、鲜于枢(1256-1301)、李衎(1245-1320)、王恽(1227-1304)多有交游,与这些人年龄当相差不大。又张雨《李雪庵学士写竹枝》有“金色头陀去已久,献花还自有门徒”之语。⑤可知李氏在张雨作此诗时已去世有年,惜此诗作于何时无从可考,但还是可以张雨卒年(1348)作为参考。从以上种种材料来看,李氏卒年当不会晚于1327年。 2、何时被赵孟頫荐于朝并官至昭文馆大学士 赵孟頫是对李氏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可以说没有赵氏的奖拔荐举,便没有李氏的名垂书史,更不会有后人的津津乐道。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载: 李雪庵初为和尚,善书。赵文敏公(赵孟頫)一日见酒帘上书,以为胜己,询访知为雪庵书也,荐之朝,得官。凡宫禁中匾额皆雪庵手笔。噫!于此见前辈奖拔之美谊矣。世传李雪庵有摹榜书甚佳,未之见也。 又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载: 尝闻赵松雪过酒肆,见其“帘”字,驻视久之,谓:“当世书无我逮者,而此书乃过我!”问知为一僧书,则雪庵李溥光也。因荐之朝,累官昭文馆大学士。 以上两条记载均陈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李溥光因善大字曾被赵孟頫荐之于朝,并累官至昭文馆大学士。但二人何时相识,何时李被荐之于朝,又何时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等均未详。据明汪珂玉《汪氏珊瑚网》载,赵孟頫、李溥光曾在李衎作于大德癸卯(1303)夏四月的《墨竹图》后先后作跋: 仆观息斋墨竹多矣,此卷老嫩荣悴风晴,备尽意度,尤可宝玩。 吴兴 赵孟頫题 息斋画竹曰规模与可,盖其胸中自有悟处。故能振迅天真,落笔真妙。简斋赋墨梅有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余于此公墨竹亦云。 大德七年闰五月望雪庵道人溥光谨题 由“大德七年(1303)闰五月望雪庵道人溥光谨题”语看,李氏此时尚未被封官。赵作跋时间在李衎作图(夏四月)与李氏作跋(闰五月望日)之间,相隔极近,二人同时作跋亦有可能。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据此认为赵氏“时或识雪庵”。⑥但由鲜于枢所作《雪庵像赞》中“帝开昭文礼巢由,归来毳衣卧林丘”语看,李氏最迟在1301年(鲜于枢卒年)以前即已被赵荐于昭文馆。其具体时间可作大致推测,据清顾嗣立《元诗选·雪庵集》载:“大德二年(1298)成宗降旨来南阐扬教事椎轮葛岭(按,葛岭为山名,在浙江杭州西湖北),后蓄发授昭文馆大学士。”⑦可见1298年或其后不久,李氏己为朝廷所用,但封官与否尚不可知。按李东阳和梁巘所记,这应是赵孟頫推荐的结果。1298年春赵氏曾借入大都写藏经之机向成宗荐举了邓文原、金江正等二十多位善书者入京抄经,后皆赐得官。⑧这二十多位善书者具体是谁已无从可考,李氏因善书成为其中一员被荐于朝也是有可能的。鲜于枢与李氏曾于1297年为“二老亭”作图赋诗,⑨此间鲜与赵又来从甚密,⑩李、赵通过鲜于枢相识亦极有可能。至于何时累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可见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四载清黄本骥跋李溥光书万安寺茶榜: 元僧雪庵,俗姓李氏,至大初授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赠号圆通玄悟大师。其时,赵文敏书为朝野推重,而禁扁署书则以雪庵主之。所刻有万安寺茶榜在嵩山峻极院,字径三寸许。 按此说李氏于“至大初授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按,中奉大夫为元散官名,从二品。元陈基《夷白斋诗话》作“荣禄大夫”,为正一品,陶宗仪《书史会要》亦从之。李氏《大字说》中自署为“资善大夫”,为正二品,应更可信)。至大是武宗年号,其在位时间不过四年(1308-1311),而从李氏《字要》中《大字说》款识“至大元年(1308)菊月望日,圆悟慈慧禅师资善大夫昭文馆大学士李溥光雪庵书于翰林院文会轩”看,李氏是于至大元年(1308)被授昭文馆大学士的。明程敏政《题元李雪庵大字后》记:“(李溥光)凡有所书及著作皆不系衔”。(11)而独于此书署官衔,想必是得官之初意得志满心情的一种流露吧。 元太祖崇尚释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达二万四千余所,经登记的僧人有21万之多,其中不乏各阶层的文化人。(12)他们不但佛学学问精湛,诗文书画水平亦极高。中峰、大訢、惟则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僧人书家,李溥光亦是其中之佼佼者,其“为诗冲淡粹美,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13)“亦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14)李氏“总角问道”,自幼便遁入空门,“以淡泊为宗,虚空为友,以坚苦之行为头陀之首,盖数十年”。(15)从清顾嗣立《元诗选·雪庵集》、明叶盛《水东日记》和清《大同府志》中收录的李氏诗作看,其早年大部分时光在山西大同度过。《大同府志》载有他早年所作《初出云中》(按,云中即大同)诗一首,道出了他“乍出嚣尘”的喜悦畅快之情: 吟鞭驴背稳如舟,乍出嚣尘眼界幽。 宿雨洗开千里障,晴云卷出一天秋。 白鸥黄犊浑相识,绿水青山忆旧游。 莫讶旅怀还更好,道人心上本无忧。 当时僧人有与王公卿侯、文人墨客广为交流的风气,李氏虽迹隐空门,亦向往世俗的物质生活,“喜与士大夫游”(16),由其所书碑志及时人诗文所记知李氏在入翰苑前足迹曾遍布陕西、江浙、福建等地。对此与其“针芥缘相投”(17)的鲜于枢在《雪庵像赞》中记曰:“帝开昭文礼巢由,归来毳衣卧林丘。一朝泚笔赋远游,南逾五岭东闽瓯。涛江瘴海靡不周,会稽禹穴为少留。山君川后护驿舟,骏马方伯走群候”。李氏结交者均为当时名贤雅士,达官显贵,虽不无攀附之意,但广泛的交游确实使李氏“见闻日富,篇帙浸多”(18),诗书画艺渐入佳境。与李氏过从甚密者除前文提及的赵孟頫、鲜于枢、李衎、牟巘外,还有程钜夫、王恽、邓文原等人。因材料所限,不能详考,只有罗列几条文献以见一斑。 具一只眼然后能识,又须具一只手然后能临,今观此卷是能以一手眼化为千手眼者,兰奢兰奢(兰奢,华言好也)。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五《李雪庵临诸家法帖后》) 古今诗僧至齐已无本之流,非不工,而超然特见,高出物表,径与道合未有若寒山子之诗,雪顶敷之颂,得其旨者惟昭文馆大学士雪庵大宗师乎。师以淡泊为宗,虚空为友,以坚苦之行为头陀之首,盖数十年矣。适然遇会濡毫伸纸,发而为诗,有寒山之顶之高,无齐已无本之靡。不假徽轸,宫商自谐,得之目前,深入理趣,谓不足以流芳声于四海,振遗响于千祀,可乎?樵夫织妇邂逅一语,犹万世不可跂及,况衣道食德,遐观旷览若大宗师者耶?世欲知师之道,此因特其糠粃,然求其至亦不外乎此也。诗云乎哉,诗云平原政事张闾公、右丞曹公、参政李公得本于十二代宗师焦空庵,将刻诸样而俾予序之。延祐二年(1315)夏六月既望,广平程某序。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一《雪庵诗序》) 雪庵圆通士,我非方外人。每来扣禅扉,坐暖蒲团春。有时论书翰,两耳闻未闻。自笑以技进,断轮非郢斤。吾学师所知,师传吾所珍。擅书三十年,临池墨□沦。手提八阵法,论入三昧神。功多诚悬骨,劲擢平原筋。蹴踏龙严势,仿佛黄山真。何必山阴鹅,不计羊欣裙。兴来追醉素,堂堂张其军。惊蛇杂走虺,入草犹龙奔。纵横与捭阖,其积力可臻,具眼世所难,雪庵洞无垠。道存见目击,靉靆知见熏。孔窍洒有开,涤我胸中尘。十年风马牛,茅塞未易耘。去冬喜北来,将谓晤语频。远游久未归,此抱将何伸。怀人叙游艺,愧乏昌黎文。何如太行道,梯空下秋云。 (王恽《秋涧集》卷五《有怀雪庵禅师》) 公早业儒,交友皆当世名卿相,工大字,所谓技进乎道者。受知圣朝,位昭文馆大学士,而不炫智能,不着贪欲,故为诗冲淡粹美,有山林老学贞遁之风焉。昔高闲上人善草书,昌黎公言淡与泊相遭,若有疑于高闲者。然必先淡泊而后通变化,岂惟书哉?恃道亦由是尔。余曩在词林获接公风采言论,知公之为世贵重,不独深于诗也。故为序其编首而归之。 (邓文原《巴西集》卷上《雪庵长语诗序》) 二、李溥光的书法 李氏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与赵文敏公名声相埒一时,宫殿城楼匾额皆出两人之手”。(19)王恽《有怀雪庵禅师》称李氏“擅书三十年”。王恽卒于1304年,说明李氏最迟于1274年后即以书名世,鲜于枢《雪庵像赞》有“巨榜照九州,千金一字人争酬”之赞誉。元贝自强《大字评》云: 李雪庵大字,如玉佩金圭,绝无瑕尘之染,有规矩准绳之方,均停应和之妙,毫发不失,虽是筋骨未如朱、张、米公,然其法则出于朱、张、米公之上,可以为万世之法也。 明都穆《寓意编》称: 前元士夫多善书者,其大字独称雪庵学士为第一流。其庄重遒劲,如端人节士,莫可狎玩,真有得乎颜氏家法,后之作大字者见之,当不止于退三舍也。 李氏大字楷书“功多诚悬骨,劲擢平原筋”(20),“出于颜柳之门,脱变化,自成一家”(贝自强《大字评》),与唐张旭、颜真卿并驾,甚至凌驾于宋朱熹、张即之、米芾之上(21)。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颜柳之余,不得不生即之、溥光”。评价虽过誉美,亦可见成就之高,声誉之隆。据《书史会要》载,李氏法弟李溥圆、江浙行省丞相达实特穆尔大字皆学李氏(22),其大字楷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其大字楷书的不足,论者皆众口一辞。如明都穆《寓意编》云: 卖画孙生持示元李雪庵绢书唐人绝句诗四轴,其字大可数寸,似学颜鲁公,惜无神气。 又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云: 元僧溥光书茶榜……令天趣流动,而结习未忘,超洒不足。 据前人所记,李氏大字楷书以颜柳为宗,显然是以工夫胜,虽“法则出于朱、张、米公之上,可以为万世之法”,但难免为法所缚,规矩有余,神气不足。这既是时代所限,更是楷书大字的特殊审美要求所决定的。李氏在《字要》中认为大字要“如王者之尊,冠冕俨然,有威严端厚之福相”,在这一审美观念主导下,其题匾大字不能随意挥洒、逞才任性,必须以表现威严、端庄、雄壮的庙堂气象为准。由《字要》所附“十六字格图”来看,其笔画极为肥密粗壮,合于苏轼所说的“骨撑肉,肉没骨”。相应地结字则齐整紧密、匀称饱满,字字撑满界格,极富体积感。如此处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利于远观,还可与大字所处的高大建筑环境相和谐。这种正面示人的高大形象,在满足实用需求的同时又表述着书写者和使用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深层次的伦理教化意义,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基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就自然能够理解为何李氏大字楷书会“惜无神气”、“超洒不足”了。其实李氏不是不想写出神气和超洒,只是难于达到罢了。对此他在《字要》“大字说”中曾慨叹道:“至于筋骨神气,苍劲清古者,人罕能之。……此皆出于笔力自然至妙,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古云:明理难,学书亦不易耳。”李氏大字楷书至清已不多见,今更不见片楮只字传世,故难以做出较完整的评价,只能据前人所论予以想象。 对于李氏行草书历来评价较少,明陈继儒《眉公书画史》云: 至元大德间,有雪庵以楷书大字名世,其临兰亭为牟大理、赵孟頫所赏。 又王恽《有怀雪庵禅师》诗云: 兴来追醉素,常常张其军,惊蛇入杂虺,入草犹龙奔。纵横与捭阖,真积力可臻。具眼世所难,雪庵洞无垠。 李氏楷书大字取法唐人,立足于实用。行草书则重艺术表现,上溯晋人,纵横捭阖,尽展自我个性才情。其临兰亭能为当时名家牟巘、赵孟頫所激赏,艺术水准想必非同寻常。王恽更以李氏草书比之怀素、张旭,评价不谓不高,参见其晚年草书墨迹《石头和尚草庵歌》,可谓情驰神纵,一片神机。细品其用笔多为中锋,势疾力足,其放逸处颇似黄庭坚;结字以平正紧密为主,又能疏密有致,开合有度;章法上字密行疏,偶见数字一笔写成,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极为生动自然。在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风气之下,独树一帜,迥异时流,实为难得。能流传至今,足见其过人之处。若论不足,唯觉气格不够宏大,未免小家子气,个别处亦显零碎,用笔多有尖薄处,有损古厚之气。 李氏大字书法多题于殿宇楼阁之上,故保存不易,传世书迹几乎百不存一,其书名也随时代推移而渐为后人淡忘。据笔者所知,其墨迹仅存《石头和尚草庵歌》,其余碑刻仅能从前人金石著录与题跋中得见其名。存世与否已不可考,现整理如次: (1)《僧溥光绝句》至元三十年(1293)仲春作,行书,陕西鄠县。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望日上石,《寰宇访碑录》卷十二著录。 (2)《东塔寺八大人觉经卷》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二月二十七日正书,浙江嘉兴。据《辛丑销夏记》载知其为纸本,红格,高一丈二寸余,长三丈四五尺,每字大径三寸许,后有明万历辛卯壬辰二跋,清吴式芬《攈古录》卷十七、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十一、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四著录。《辛丑销夏记》卷四载有清钱载、钱樾、成亲王等人跋语,以钱载所言最为全面:“雪庵此卷自明叶藏东塔寺僧处,幸不饮人缸面酒,至今无恙,已刻石嵌禅室两庑向藏。初拓本携至京师,皇十一子见之深加叹赏,谓笔力破余地腕,有颜柳鬼,实出松雪翁上,宜当时之推重之也。今过僧庐纵观墨迹,正如亲到宝山得见真面目,何幸如之。”钱樾于观后记曰:“从来诗文书画皆不能囿于时代,此雪庵和尚八大人觉经追踪颜柳,无一笔涉元人蹊径,亦不蹈僧家习气,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者耶。” (3)《文始殿碑阴》全称《终南山古楼观大宗圣宫建文始殿碑阴》,大德七年(1303)九月正书“文始之殿”四大字,陕西鄠县,《攈古录》卷十八著录。 (4)《万安寺茶榜》至大二年(1309)正月十五日门资上座德严刻石于河南登封嵩山戒坛寺,李溥光撰并正书,《寰宇访碑录》卷十一、《攈古录》卷十八等有著录。王世贞《弇州山人书画跋》云:“元僧溥光书茶榜其词紫方袍底语耳,不得禅悦真味。书法风骨颇遒劲,略具颜柳及眉山、预章结法。”清叶封《嵩阳石刻集记》云:“为石四,与正刻凡八幅,今移立在城西峻极下院。按,王世贞跋云:‘元僧溥光书茶榜风骨颇遒劲,惜胸中无卍字骨,令天趣流动笔端,结习未忘,超洒不足。’又周叙记云:‘元雪庵所书茶榜字径三寸许,道伟可观,今观其书,笔虽过丰,而结体遒紧,有清臣诚悬之风。书史亦称其工大字,录之。’按,此书体大,装潢为繁,节录亦可。”孙礦《书画跋跋》云:“此茶榜刻,今世多以饰屏,字全师颜鲁公,虽天趣未流动,然亦有骨力,余曾见僧其它墨迹,颇遒劲可喜。” (5)《草堂寺诗》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望日上石,李溥光撰并行书,石存陕西鄠县,《寰宇访碑录》卷十二著录。 (6)《山名诗卷》大字行楷书,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称:“字大三寸许,每行二字,字体丰硕,结体道伟,笔法苍劲,得颜真卿、柳公权二家风规,是溥光书法代表作。”此作曾藏故宫博物院,现已不知去向,未见影印出版。 (7)《石头和尚草庵歌》草书,纸本,写唐释希迁(世称石头和尚)所撰《草庵歌》。凡42行,行字数不一,共229字。纵46.7cm,横605.4cm,无年款,自署“玄悟老人”,后有曹文埴识。按,玄悟老人乃李氏任昭文馆大学士时皇帝所赐之号,故知此作为其晚年任昭文馆大学士(即1308年)后所书。此作曾为近人叶恭绰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见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六)》、大地出版社1990年版《书法鉴赏大辞典》,现又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影印单行本行世,《中国墨迹经典大全》亦收入,并评曰:“字大如拳,笔墨浓重,结字紧束,不作姿肆之态,用笔极少提按顿挫,转折处多用圆法,浑然苍郁,古拙朴茂。在元代书家中独标一格。” 李氏以善大字楷书闻名于世,草书成就被其所掩而不被人提及,但有意味的是其楷书至今不见片纸传世,草书却能保存至今,其中原因颇耐人玩味。 三、李溥光的《雪庵字要》 《雪庵字要》(以下称字要),又称《雪庵大字书法》,是李溥光所撰专论楷书大字书写技法与鉴赏标准的理论著作,自序作于至大元年(1308)菊月望日。现对其版本、体例、内容及理论价值和影响予以阐述。 1、《字要》的版本、体例和内容 《字要》的版本就目前所见仅两种。 其一为《涵芬楼秘笈》本,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孙毓修等辑。《字要》收在第九集中。前有明永乐辛卯(1411)春当涂詹恩和宣德己酉(1429)立夏后二日南阳叶盛先后所作之序,卷后永乐八年(1410)秋九月詹恩和成化十七年(1481)龙集辛丑春三月望后一日琴川俞洪二人所作之跋。后另有戊午(1918)十月海监张元济跋语,谓是书乃著名藏书家毛子晋、黄尧圃旧藏。 其二为《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点校本(虽经崔尔平点校,仍有错讹),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8月版,所据为《涵芬楼秘笈》本。可惜的是收文不全,删去了最有实践价值的图谱和不太重要的《永字八法说》,使读者不能得窥全貌,极大地影响了其传播范围和力度。该书解题中称:“此处只选录该书之前四篇”,不确,实际应是收录前十六篇。 《字要》体例比较别致,前面文字内容除《捽襟字原》、《大字说》、《大字评》、《永字八法说》外均以歌诀的形式来表现,共有《把笔八法歌》、《用笔八法歌》、《把布八法歌》、《用布八法歌》、《捽襟五法歌》、《捽襟永字八法歌》、《永字八法歌》、《永字变化三十二形势歌》、《八善歌》、《八美歌》《八忌歌》、《八病歌》、《好恶一十六法去取歌》十三首。均为七字一句,用语通俗浅白,读来朗朗上口。文后附有“把笔永字八法法图”、“永字用笔八法图”、“用布八法图”、“捽襟永字八法图”、“永字变化三十二形势图”、“八病图”、“十六字格图”等图谱若干,具有直观、生动、形象、实用的特点。 《字要》共一卷,全文不到两千字,多为李溥光自撰,亦有辑录他人之作。如目录所示,其内容由二十二条组成,首为《捽襟字原》(他人作,雪庵所录),次《大字说》,又次为《大字评》(贝自强所评),又次为《歌诀》十三首,最后为《永字八法说》(前人作,雪庵录)。 2、《字要》的理论价值和影响 《字要》言简意深、图文并茂,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价值和独到之处,可从前人的几则跋语中略见一斑。明詹恩云:“得《雪庵大字书法》一部,何异饥渴而获膏粱琼液也。”又云:“是书之传,实学者之规矩也。”贝自强《大字评》称:“至元二年(当指后至元二年,即1336)春复任京郡,于奎阁中得受雪庵字法,见其言简而理明,观览捷易,遂作字评于右”。按,奎阁乃奎章阁学士院的简称。建立于天历二年(1329)二月,即文宗登基后的次年,至元六年(1340)改“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23)建立初衷为“延问道德,以熙宁圣学。又创艺文监,表彰儒术,取其书之关系于治教者,以次摹印”。(24)可见,奎章阁不仅是文宗召集儒臣考帝王之治,论祖宗明训,研究古今治乱得失的机构,又是内府中书画收藏鉴赏的雅集之地。《字霜》忝列其中,足见其价值和受重视程度。 《字要》所论重在笔法,亦涉及结字、章法等内容,其认为楷书大字重在体现威严雄壮、正大堂皇的庙堂气象,讲求均称齐整的秩序感和严肃性,看似有其特殊的一面,实则在当时乃至明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适于初学,对不谙大字法的名家高手亦不无借鉴与指导价值,对明人的大字书法理论更有直接的影响,如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即在《字要》“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形势”的基础上发挥而成。(25)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二称:“(《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所立名自不尚形容,务求浅显,胜于雪庵之巧立名目者多矣,诚习大字者之规臬也。”(26)高松《变化永字七十二法》亦“推广李溥光三十二势而成之者。”(27)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认为明初名士姜立纲的“七十二笔势”亦由李溥光“永字变化三十二形势”推阐而成,并称“在日本,宽文、元禄时期所流行的《内阁秘传乐府》以及这一系统的指导书,都是本子姜氏此说。进一步上溯,也可以说是出于李雪庵。”(28)在古代,用于题匾的大字书法虽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但往往因其别有功用,往往被一般书家所忽略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李溥光及李淳等人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榜书向社会的广泛普及。榜书的普及,使楹联匾榜、横幅斗方等各种作品形式遍布室内屋外,形成明清建筑装饰的整体文化风气。使贴学从案几清玩中解放出来,使书法从全面的庄严中走出来,成为人皆可用,可以亲和的艺术。(29)一般来说,榜书大字多用于摩崖、匾榜、碑碣,明清以来更广泛用于立轴、楹联等形式中,其书体多以正楷、行楷为主,风格更趋于一致。虽各有攸宜,却不离整饬、端严、浑厚一路,应该说这与《字要》的引导不无关系,最起码《字要》的先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字要》以发明精要为能,旨在实效。但限于歌诀这种文体的束缚,所言未能详尽深入,其中多有未显语处(尤其是捽襟法),“所立名目巧于取譬,意在明显而反涉于隐晦,”(30)是为美中不足之处。但《字要》所论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研究、教学和艺术实践都是大有裨益的,其中关于“捽襟法”的阐释尤为难得。因受当时条件所限,作榜书大字在没有大笔的情况下便捽襟代笔,把布作书毕竟不同于把笔作书,因布不具备毛笔“尖、圆、齐、健”的特性,所书之字难免粗糙不精。但若运用得法,想必会别有妙处,这种无奈之法无疑会大大丰富榜书的艺术表现力和内涵,给人以全新的审美感受。可惜此法已失传,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字书法创作仍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 ①详见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河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131页。(该书下文再次引用时,不再注明出版者) ②转引自戴立强《鲜于枢传世墨迹考释》,见《书法研究》,2000年第2期。 ③张雨《句曲外史诗集》卷三,上海函芬楼景印四部丛刊本。 ④任道斌《赵孟頫系年》,173—216页。 ⑤张雨《句曲外史诗集》卷三,上海函芬楼景印四部丛刊本。 ⑥任道斌《赵孟頫系年》,108页。 ⑦顾嗣立《元诗选·雪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黄惇《从杭州到大都》,见《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00年版,209-212页。 ⑨释大訢《蒲室集》卷十二,金华智者寺云屋禅师塔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戴立强《鲜于枢年谱》,见《书法研究》,2000年第3期。 (11)程敏政《皇墩文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楚默《元代的释道书法》,《中国书法》,2001年第6期,20页。 (13)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五,见《雪庵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李侃、胡谧《成化山西通志》卷九,民国二十二年(1933)景印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 (17)见《墨迹经典大全》卷十九,京华出版社,1998年。 (18)李侃、胡谧《成化山西通志》卷九 (19)王恽《秋涧集》卷五,《有怀雪庵禅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叶封《崇阳石刻记》卷下六十三,民国十二(1923)年,沔阳庐氏慎始基斋景印本。 (21)详见《雪庵字要》辑录贝自强“大字评” (22)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载:“李溥圆……于溥光为法弟……达实特穆尔……大字学释溥光。” (23)《元史》卷一四三,《康里夒夒传》。 (24)虞集《皇图大训序》,见《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二。 (25)明李淳于《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中云:“臣幼习大字,未领其要,所获儒僧楚章授以李溥光《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势》,宝而学之,渐觉有得。”(《明清书法论文选》66页)朱履贞《书学捷要》云:“至明景泰中,李淳进八十四条结构法,盖从李雪庵八法用笔及陈绎曾、徐庆祥书法增减而成者,此乃题擘窠大书法也。”(《历代书法论文选》,604页) (26)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7)同上 (28)(日本)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02页。 (29)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总论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0)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