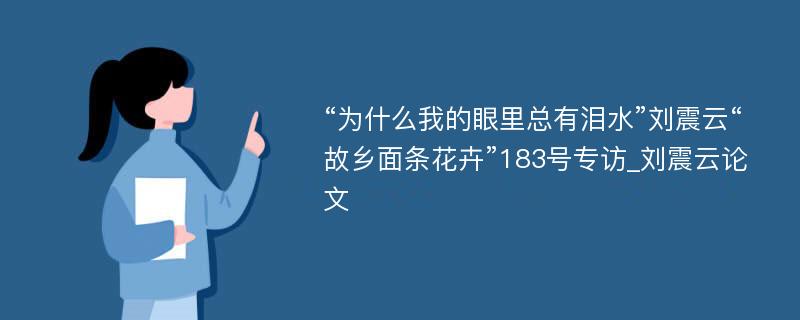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关于《故乡面和花朵》#183;刘震云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乡论文,花朵论文,泪水论文,眼中论文,刘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戎:首先祝贺你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创作完成并出版。很多读者都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你的这部长达二百万字的作品从创作到出版前后历时八年,这八年中你还写过其他作品吗?
刘震云:没有。一个人的能力、精力、体力是有限的。专心做一件事情往往还难以做好,何谈其他。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会写这么长,时间会用八年。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设想四年或更短的时间能够完成,四年下来我发现刚刚写了一半。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三十出头,写完这部作品已经快四十岁了。当一个人在屋子里关得时间过长再走出门,他除了感到强烈的阳光遮挡得他睁不开眼睛,还感到这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时候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首先不是感到满意而是产生怀疑,就好像我们掘地三尺终于挖出一个早年的陶罐会对结果感到匪夷所思一样。《新民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写这么长的东西,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傻子。我对这八年的体会是:世界变了,我的心态和对世界的态度也跟八年前非常不一样了。我感到我对世界所知甚少。这个所知甚少既包括对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及凌驾于内心世界之上人的情绪的翻腾和游走,也包括对那些永远不可触摸的万物生灵相对于人的情感流淌方式。这时你想起自己曾蜷缩在对世界的误会的自己的投影里沾沾自喜过,你除了感到无地自容更想做的是失声大号。同时在你对世界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开始动手写作可真有些盲目和憨大胆。
陈戎:我曾经听你在座谈会上说过,这部作品是你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写作的,给我们谈一下它创作的初衰好吗?
刘震云:开始创作它的初衷,主要是对之前我自己的创作有了极大的不满意。我以前写的一些中短篇譬如《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温故一九四二》和一些不太长的长篇如《故乡天下黄花》,主要打通的是个人情感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它主要写的是张王李赵起床之后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活动,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买菜、怎么骑自行车上班、上班之后在单位和同事发生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当然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恐惧、接受、占领、退让、忧伤和欣喜,变化之前的本相和变化之后的扭曲,他们在相对的镜子中飞快的退缩和躲避,我们能从这些闪烁不定的身影和心路轨迹中不时发现我们自己。但是我逐渐发现如果在“文学”中这么映照我们的每一天相对于“现实”来讲在时间的分配上还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我们只找到这么一个人生的支撑点是不够的。因为张王李赵在洗脸、刷牙、买菜、骑自行车和面对他们亲人和朋友的时候,他们脑子中思绪的翻腾和飞升往往并不固定在洗脸、刷牙和骑自行车这些动作本身上,当他们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全在我们身上而还会出现精神游走。譬如一个农民大哥在田里锄草,从早上七点半锄到中午十二点半,过去我们就说他在“锄草”,其实他在锄草的过程中,思绪早已经离开了锄草而想到了许多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连续锄草五个小时脑子不进行别的转动这种单纯的劳动他是坚持不下去的。越是繁重的劳动,他精神的创造就越是辉煌。过去我们只说他在锄草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在锄草,其实锄草和洗脸、刷牙和骑自行车或是面对亲人和朋友在精神的意义上只占到我们的时间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这种思绪的畅想和游走在时间的比重上却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过去我们将笔墨仅仅对准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以为是对准了生活的全部却将这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毫不在意地给忽略掉了,其实这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于支撑我们的锄草和面对却显得更加重要。同时我们在生活中往往还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我们似乎在多年之前曾经听到过,但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和地点和什么人一起听到过,我们一下却想不起来;我们看到一根花杆铅笔,这杆铅笔我们似乎也在多年之前看到过,但是在什么时候和地点看到过,我们一下子模糊起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形状、色彩、气味、河流的弯度和青草生长的样子,我们突然感到非常熟悉,我们似乎在今生今世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但在我们以前人生的历史
上,却从来没有踏入过这个区域。当然这些感觉都是转瞬即逝,我们刚要感动又觉得这是可笑的和不重要的而把它给忽略掉了。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觉得自己以前的写作只是刚刚接触到生活的一小部分而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全部,只接触了百分之二十和三十像瞎子摸象一样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这样下去是荒谬的,于是就试图接触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时间的比重上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情绪的翻腾和精神的游走也就开始了《故乡面和花朵》的写作。
陈戎:我在读“故乡面”的时候注意到,它和你以前所使用的文体有了很大的不同。譬如你过去写实的风格和白描的功力使作品出现了木刻和雕塑的艺术效果让人感动,也开创了“新写实主义”的先河。但是这些让人熟悉的风格在这部长达二百万字的作品中已经难觅踪影,更多的是采用现代派和后现代的手法使作品一直处于跳跃和动荡的状态。当你采取这种新的文体的时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或者说是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派作品的影响?
刘震云:文体的不同,是由于所打通的个人情感和世界关系的通道的不同带来的。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内容决定形式。过去由于重视的是“现实”和白天,所以结构的递进和语言的流淌就非常尊重现实时间的秩序。由于与时间的合拍,大家接受起来就有一种深入其中和会心相通的感觉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这次写的主要不是白天而是夜晚,前三卷用了一百五十万字在写成年人的三个大梦,这时再用现实时间的节奏和递进来表现它们就显得非常的苍白乏力、无从说起和勉强了。过去的形式已经撑不起新的内容了。纷至沓来和混乱无序的精神游走和灵魂飞升,需要用跳跃、动荡、破坏正常秩序的突进和倒灌结构和节奏来与其相适应。当然我学习过许多西方大师的作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创作上,总是受日常生活的启示要大于你曾经读过的书本。别的大师只是让你知道他对世界已经怎么样感觉和畅想过,告诉你这些甘蔗他已经嚼过了你再嚼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写作你应该去砍伐怎样的甘蔗。具体到“故乡面”的写作手法的运用上,你说它是现代派也好,你说它是后现代也好,其实仅仅因为写到了梦,所以它用的是梦的时间节奏和递进方式并没有有意为之要与谁等同和相通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意识的无控制流动和违反现实时间的情节和感觉递进首先不是存在于已经有的书本上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世俗生活中特别是他的夜晚。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在现实世界上是多么地高贵或是贫贱,白天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到了晚上他们会在一个事情上统一起来那就是做梦。当然梦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你梦到的是庄稼地和垃圾场,他梦到的是五星级酒店和歌舞场,但是到了梦的创造上,他们同样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现代派大师,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梦中的时间递进和现实生活都是不一样的。站在你面前的刚刚是这一个人,马上就换成另一个人;刚刚是这个场景,马上就是另外一个场景;何况梦还会出现这种创造——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的事情,在这里突然就实现了:我们见到了现实世界中再也见不到的亲人,亲人在梦中是永生的,梦醒的时候我们的泪打湿了我们的枕巾。于是“故乡面”出现和《一地鸡毛》不同的感觉和表达形式也就很自然了。其实在“故乡面”的整体结构中,这种跳跃和动荡的方式并不就是一贯到底,前三卷是三个成年人的大梦当然出现了这种形式,但是到了第四卷作为正文好像是一个铅砣要坠住天上飞升的三个大气球不使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飞开始出现一个少
年对一个固定年份的深情回忆和顾盼的时候,它在文体上突然又开始返璞归真和自然流淌了,就好像大戏过后开始抹掉脸上的油彩和卸掉身上的戏装一样。我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朋友的所作所为,都在教导我的写作并不仅仅因为知识和书本;第二层意思是:写作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事情没有必要故弄玄虚。
陈戎:说一说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首先这部作品和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叙述人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同时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如孬舅、冯·大美眼、瞎鹿、六指、小刘儿、白石头……等等,个个都是生生不死的,于是它在结构上就显得非常繁杂,场景和人物像走马灯和万花筒一样在旋转。我已经注意到一些评论家在谈论它的复杂结构和柱式结构,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刘震云:对事情进行总结我总显得很弱智。何况作者写一部作品的出发点往往源于情感而非概念。多重叙述人是因三个梦的相互干扰和渗透,朋友分别的时候有多种的嘱托和猜想这很正常。至于生生不死刚才我已经说了来源于我们梦中的挂念和寄托我们每个人也能感觉到。这是我们对生活依恋和热爱、恐惧和刺心疼痛的根本。就像对一部作品的完成一样——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问我八年完工之后是否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说恰恰相反,当我要和孬舅、瞎鹿叔叔和六指叔叔告别的时候,就像亲人在岔路口要各奔东西一样,我心中突然有了刺心的疼痛和无可告人的悲伤。当然除了这个层面上的意义我感觉更猛烈的一点是:这种梦中的挂念、寄托和创造对于你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每天醒来之后拍拍屁股就忘到了脑后提着菜兜就去菜市场买菜是不对的因为它也是支撑我们现实生活的另一根强大的支柱我们需要时间回味和畅想否则“故乡面”的写作倒是失去了意义。我赞成这样一种说法:文学代表着一个语种的想象力。当然,当我们在现实中坐在河边过于沉溺于幻想的时候,我们又会受到“现实”的压力,朋友又会赠送你两句话: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傻子。
陈戎:现在来谈语言。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汉语的使用应该规范。但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时常发现许多非规范化的汹涌澎湃和排山倒海的语言在泛滥和作祟。一方面,有评论家认为,《故乡面和花朵》的出现会给汉语写作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相对于大部分的非专业读者来说,这部作品新的语言的流淌和使用无疑会令他们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你认为这种陌生感会对他们的阅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震云:首先,语言的组接和排列形式是由于作品的内容和篇幅所决定的。一个大的长篇和中短篇或一个不太长的长篇比较起来对语言流淌速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三四万字的中篇或一个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可以看作是一段河流,河流的流淌总是要求河水的表面产生浪花这些时时的浪花用一个文学的词来概括就叫激情,它对语言的要求是明快,它对结构和节奏的要求是要经常显示出流动。这个时候短的句式、生活口语的使用就显得非常必要和俏皮。但是当你不是面对河流而是面对大海的时候,当你不是面对几万字和二十万字而是面对二百万字的时候,表面的浪花已经显得非常地不重要了。大海的表面风平浪静,而海水底部所汹涌的潜水或涡流是什么才决定着潮涨潮落及它和月亮和太阳的关系。如果说这部作品的语言或者说我对语言的把握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失误,关键就在于我对这种关系的把握。再举一个例子,语言的生长也有点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生长的植物和树木。一棵小树的表皮往往是光滑的、青春的、可爱的,但是当这个树疯长到几十年和几百年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棵树的表皮已经不那么光滑和可爱了,它的周身开始出现一年一年所积累下的伤痕累累的疤结。比这两个层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作品所写的内容并不“现实”而写的是非现实和精神飞升,于是它语言藤蔓的生长和盘绕一定会比明确的现实语言要盘根错节和节外生枝一些。语言总要跟结构的跳跃和动荡的情绪统一起来。评论家从职业阅读的习惯当然马上就会获得新鲜的快感,非职业的朋友可能一开始感到阅读的障碍,但是我相信他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过去的阅读习惯,三章下来一样会从容自如。这样说的前提是这些内容和梦幻对他们并不陌生恰恰是每天都可以遇到的显得非常家常,于是与其相适应的语言习惯下来马上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不要低估读者朋友的理解力,他们往往要比作者高明得多。
陈戎:在八年的写作中,你自己遇到的最大障碍和感到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刘震云:以我并不充分的生活准备和知识积累来讲,八年的写作可想而知会出现很多困境。最大的困境是当你展开精神想象的时候,你对非现实的专注程度和在细节深入上会在层次上出现差异。就好像声音是好描写的,但是当你给声音注入了催化剂,进行了混合和爆炸,声音宏观成了一个巨大的翅膀飞越了三山五岳或微观成一段越来越细的游丝渐渐地飘散或揪断这个宏大的飞越和揪断的过程就要求你第一天的写作和第二天的写作在情绪的深入上不能出现差池和错位。一个声音的细节描写是这样,二百万字的整体结构也要求你在情绪的深入和流动上从头到尾要保持平稳。这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当然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因为你常常发现第二天的写作和第一天的写作、下个月的写作和上个月的写作、第二年的写作和第一年的写作没有在一个情感层次上飞行。更大的困难是你不知道哪一层的深入是对的于是另一个层次是需要修改的。你的面前似乎总有一个身穿白裙子的影子在飘,你在夜晚的山路上精疲力尽还是赶不上它这时你就知道完美的艺术境界是多么地可望而不可及。同时你就明白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文学和艺术是悲惨的事业因为它相对于永无止境的生活中的精神想象你竭尽全力还是只抓到了它的一些皮毛。所以我除了二十多岁时的幼稚时代还有些自信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于语言和写作的陌生了。过去对另一句话也不太明白就是写作是一个修炼的过程现在刚刚咂摸出了它的一些甘苦和滋味。
陈戎: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你认为“故乡面”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占据什么位置?
刘震云:依然是一篇学习过程中的比较刻苦的作业。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就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从天资来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和悟性非常差的人。周围的朋友都比我要聪明。就文学来讲,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去考虑,许多聪明的大师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非常有想象力的作品,用这些作品打通了自己和世界的独特通道,而我到了三十多岁后,才知道一些肯定性的词语譬如“再现”、“反映”、“表现”、“现实”……等对于文学的空洞无力。当然这除了我本人的知识准备和教养不足之外,也和我每天说的汉语和汉语写作的传统和习惯对我的训练和深入血液的影响有关。在三千多年的汉语写作历史上,“现实”这一话语指令一直处于文字的主导地位而“精神想象”一直处于受着严格压抑的状态。而张扬一个语种的想象力,恰恰是这个语种和以操作这个语言为生的人的生命、生命力和活力所在。当然,在三千年的沉闷空气中,长着精神想象翅膀的创造像石光电闪一样往往也会偶尔划过漆黑的天空,但它们都是以短语和寓言的方式缩小着自己的存在。如“夸父逐日”,如“精卫填海”,如“黄梁一梦”,如“愚公移山”。有的是以脱离语种主流干脆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出现,如“白蛇传”。今年夏天我到杭州去过一趟,怎么也发现不了那里会是产生这么具有想象力的神话的地方。一个人和一条蛇发生恋爱,可见这个传统的创造者和流传者对现实绝望到了什么地步,就像孔子说出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话一样。到了大清王朝末期,统治这个社会和语种的人譬如慈禧太后,从她和身边人的关系来考察,她对宫女使用频率最高的汉语恐怕是“掌嘴”,就可见现实对于精神想象压迫和压抑之强。几千年的文明史发展下来,人对人的控制还要通过体力来实现,不能说不是这个语种和使用这种语种来进行正常生活的人的悲哀。如果她和宫女之间不是这样来体现她们之间的关系而是她在明朗的月光下拉着宫女的手坐在故宫午门外的台阶上告诉宫女“天上的星星数不清”,不知我们这个古老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推卸自己对汉语写作不努力的责任,而是说由于我的不努力过多地受到客观和历史的控制没有过早地觉悟当然这也是我稍稍悟出一些文学的真谛开始写“故乡面”的原因。
陈戎:接着我们再谈两个这部作品之外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你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刘震云:一,读者往往比我高明,写作和阅读通过书本是一种交流,就像两个朋友在灯下深入地谈心一样;面对面或通过电话和信件交流他们也教会我许多东西。湖北的一位朋友常通过信件对我进行哲学、宗教和古文化的指导;北京一位退了休的老校对常常夜里打电话纠正我作品中的错别字。特别应该感谢他们的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没见过面在这之前等于素不相识。二,读者朋友以他们的善良教我勤奋不怠和善良。就像我上个礼拜天到南京签名售书所受到的教育一样。据说现在图书市场已经非常疲软,那天天上还下着雨,日子到了月底作为工薪阶层钱已经快花光,“故乡面”由于二百万字和四卷的缘故定价到118元,但南京的读者朋友却给了我极大的爱护和关怀,雨中排起了长龙,两个小时签出去一百多套。许多朋友专程从泰兴和扬州赶来。大家经济都不富裕,这时你对朋友们花118元买你一套书到底值得不值得自己心里倒有些打鼓。回想八年的创作,其中肯定有许多肤浅和失误的地方,我应该找一个适当的场合向错爱我的朋友道声歉。还令我感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她很早就买完书但却不走,直到我匆匆要去赶中午的班机时她又赶上前说:你怎么看上去那么瘦呀?让我差一点潸然泪下。直到现在这个善良的大姐的面容还在我眼前晃动。这时你觉得你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微不足道,唯一能做的是在今后的创作中尽量将以前的失误弥补起来。
陈戎:最后请你谈一谈今后的打算。
刘震云:一方面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八年下来我体力和精神上都已经非常疲惫,起码一年半之内我不准备再写新的东西,主要用来读书补充自己。我在别的场合也曾经说过,一方面我准备集中读一下先秦的文学,那个时候的汉语放射出了丰厚的折射性的生活的光芒。秦灭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规,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汉语开始首先作为一种指令和肯定句式在现实中存在,流传到今天就像我们的长江和黄河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汉语也已经很累了。作为一个人在现实中生活囫囵吞枣它已经够用了,但是作为代表着一个语种的想象力的文学,要用现存的它来表现我们稍纵即逝和含混不清的情绪流动和飞升,有时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重新打理和发掘汉语的丰富性,词语连接所折射出的歧意和多重性,从指令和肯定还原生活的模糊或透明,让它重返青春和焕发朝气,就需要回头和溯流而上去找一下它的源头。另外我想集中精力学会一门外语。当你用一种语种写作的时候,你对世界上同时存在的其他语种一窍不通,不知道其他河流是以怎样的速度和节奏在流淌着,你对身边河流看似熟悉其实也同样是对面不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