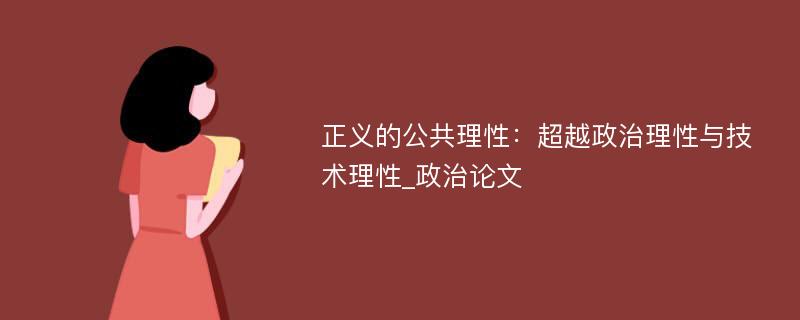
司法的公共理性:超越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技艺论文,司法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司法为民”切入
当下司法改革陷入瓶颈,如何挽救日益下滑的司法公信力成为法院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重拾延安时期“司法为民”传统和群众路线司法技术,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基本要求,摆出主动接近民意的姿态。但是,邓玉娇案、彭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吴英案等被“民意”改变的案件屡屡发生,暴露出司法价值取向与社会正义感之间的断裂,不断给跌入低谷的司法威信雪上加霜,与这些年来法院苦苦争取社会认同的努力很不相称。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公共理性的缺失是中国司法公信力低下的症结所在。工具理性“铁笼”为反思中国理性问题,揭示司法腐败、司法与民意断裂、司法公信力低下的根源提供有效分析工具。公共理性则为重树中国司法理性、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二、核心概念: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共同理性,是公民在讨论何种正义原则和公共政策(包括立法)可以接受时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是公民能够用其公共意识和公共理由达成关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共识的能力。公共理性意味着公民在那些事关支配自己社会立场的基本(或完备性)学说之间达成了“重叠共识”。①
哈贝马斯从商谈伦理学的立场,聚焦于理性的公共运用程序,认为公共理性是主体间性的理性,其运用需要通过自主的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商谈过程来实现。②在通过“交往实现正义”的法律程序主义中,衡量司法公正最为重要的指标不是某种实体价值,也不是不要任何实体价值的“纯粹的程序正义”③,而是商谈程序的合理性和理由的可接受性。其精义是通过程序产生实体,诉诸理由达成共识。同时,公共理性并不能经常导致各种观点的普遍一致,它也不强求如此。它的禀赋是“求同存异”。它的意义在于:当公民们在各种观点的冲突和论证中学习运用公共理由来进行论证,对于最后形成的结论少数人可以保留反对意见,但不能怀疑这种经公共论证得出的决定是理性的,因而承认结果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决定的论证理由的公共性与程序的民主化,使得最终的决定具有了正当性和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理性具有超越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公共属性,具有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沟通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能力。
三、司法的公共理性特质
公共理性理念首先适用于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中。不仅如此,公共理性理念的适用对于法官较之其他人更加严格。④
1.司法权的公共属性及其“用法律来判断”的本质,要求它体现公共理性。民主社会的法律本身就是公共理性的集合,是公众关于公平正义的重叠共识。司法权属于公共权力的一部分。每个司法裁判个案都是公共产品,是公共性再生产的过程,肩负实现法律价值、维系社会秩序与整合的使命。为此,司法裁判结论及其所依据的理由应当体现社会正义共识,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正是公共理性的表现,也是司法获取社会认同的基础。
2.司法理性是制度伦理的产物。司法公正是制度伦理的一种选择形态,它追求的是制度伦理,是一种整合性伦理,以程度较低的道德标准为基准,与多数人或普通人的道德水准相适应,以获得多数人的认同与遵守。其功用在于把制度所涉及的那些分散的个人的善、价值、目的和愿望整合为一个大体协调的结构或秩序。⑤所以,法官在作出判断和裁决的时候,不能以个人的道德偏好作为裁判的理由,而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评价标准。这恰是公共理性的本质特征。
3.司法克制是制度理论的题中之义。基于制度伦理的原理,司法需要恪守“浅”和“窄”的克制主义。“窄”是指法官只对案件作出判决而不是制定宽泛的规则。“浅”即尽量避免提出一些基础性的原则,而是试图提供一些就某些深刻问题意见不一致的人们都能接受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达致“不完全的理论化合意”(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⑥即便是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者也主张,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要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在涉及眼前需要解决的具体纠纷时,法院阐释此类命题的活动才有正当性,不能超过这个限度。⑦
4.沟通理性是司法应有的品格。司法对待民意的态度既非冷漠无视,亦非迁就屈从,而是公开交流、理性对话。法官能够在异质性社会中准确拿捏判决的度,不是靠其个人的智慧,而是经由司法与社会的沟通交流,在多元价值观中发现重叠共识,籍法律论证揭示于众。司法还应当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促使其裁判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共精神。这是司法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保证。
四、中国司法理性问题:政治理性VS.技艺理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司法为民”及其技术的内涵,可以发现其中围绕执政党政治需要确立司法目的、选择司法方法的特质,可谓“政治理性”。以司法专业化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一度推动中国司法技艺理性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反思和“能动司法”运动,又将司法的政治理性提到一个高度。尽管最高法院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主张表明其试图在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总体上看,中国司法的政治理性要强烈得多,表现为过于强调司法的政治功能,专注于“政治正确”:第一,以政治目标为司法总体目标,司法的中心工作是“服务大局”。第二,把“有效解决纠纷”作为诉讼目的。第三,主动服务政治需求,将司法内涵向社会管理延伸。第四,鼓励法官的政治和政策思维,裁判理由常用政策考量。⑧“能动司法”则更直白地要求法官成为“政治家”,鼓励法官“创造性”地解释法律和运用法律程序。⑨第五,司法对政治依赖度高,政治因素对司法的影响畅通无阻。因为调解一直被当作推行贯彻党的政策,实现国家治理目标、争取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司法结构中调解的兴衰几乎成为政治因素强弱的风向标。自陕甘宁边区时期至今,当代中国司法演绎了一个从“调解强判决弱”,到“判决强调解弱”,再到“调解强判决弱”的轮回式(或至少是螺旋式)发展历程,与司法的政治理性的强弱变化相映成趣。
五、公共理性缺失与工具理性铁笼
中国司法一直在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之间徘徊,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可以“得兼”、也应该同时具备的。能够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是司法的公共理性。这恰是中国司法所缺少的。表现为:(1)司法解释缺少公共理性。(2)司法裁判缺少公共理性,包括裁判无理由、用法律之外的理由作为判决依据和法官用个体经验与个人价值观为裁判理由。(3)司法缺乏沟通理性及制度化渠道。
缺乏公共理性的司法理性滑向“工具理性铁笼”。⑩中国司法的政治理性的结果是法律和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司法公正常被政治正确所替代。审判方式改革陷入瓶颈的根本原因是,大多数改革方案主要是从方便审判角度出发的设计。这样的司法技术也难逃工具理性“铁笼”,成为法官手中任意摆布的工具乃至寻租筹码。
缺乏公共理性的司法容易与民意发生断裂、隔阂。公共理性是一个包含时空元素的概念,它是身处同时代的、同一个地域空间内的民众的共识。熟知本国文化传统、了解当下民众价值观、洞悉当下的历史社会环境、体察本地风俗习惯,具有与民意沟通的意识和能力,是一个司法者必备的素质。缺乏公共理性的司法裁判不食人间烟火,裁判理由与社会朴素正义感相去甚远,容易招致社会反对。
缺乏公共理性的司法是空心的,无重心,禁不住舆论的批评而左右摇摆。这样的司法对民意表现出“专断”与“被动”两个极端——裁判时无视受害人和民众的意见与感受,闭门造车;当案件成为公共事件后又经不起舆论的拷问,随风而倒。中国司法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民意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司法,但会影响政治,政治再影响司法。如果法院总是“眼睛朝上”,眼里只有政治,在政治压力下才低头看看民意,那永远要面对政治正确而司法公信力消失的吊诡。
六、司法公共理性的培育
司法的公共理性程度受制于社会的民主程度、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法律的公共理性。而在中国,这三个条件均不成熟,尤其是立法的公共理性问题确实值得反思。但司法的公共理性可以起到修缮法律漏洞、填补法律公共理性不足、激发社会公共理性的作用。因此,培育公共理性是中国司法当务之急,不能坐等社会进步和立法完善。而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关键有三:
1.正确看待司法的政治理性。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不是简单地将司法“去政治化”,而是要将其政治理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追求政治正确到保障政治正义。司法需要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审视执政者的政治要求,为执政者提供一种制度化纠错机制,成为政治正义的再生产装置。
2.法官公共理性的养成。司法的公共理性最终体现在法官书写的一份份裁判文书中,法官的公共理性是司法公共理性的依托。作为公民,法官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将之融入日常司法行动中。作为法律人,法官的职业生命在于对法律精神和法律方法的把握,把法律当作其唯一的上司;还需要中国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将社会普遍的正义观与法律价值对接糅合,避免“精英”意识与民众观念的断裂。
3.司法公共理性的制度保障,完善司法的社会参与机制。改革完善陪审制的核心是祛除审判权本位主义的制度设计,将陪审制构建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通过改革陪审员产生方式,增加陪审员数量,规定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争议大的案件必须适用陪审制等渠道,让民众意见有序进入司法,加重司法论证负担,让司法有机会回应社会不同意见,在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发现重叠共识,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认同。
注释:
①[美]约翰·罗尔斯著:《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版,第225-226页。
②[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所做的调和: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谭安奎译;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375页。
③罗尔斯设计的“纯粹的程序正义”概念,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2页。
④[美]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理念新探》,谭安奎译,同注③,谭安奎编书,第122-123页。
⑤郑成良:《法律之内的正义——一个关于司法公正的法律实证主义解读》,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⑥[美]凯斯·R.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伟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⑦[美]艾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质》,张曙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⑧王旭:《解释技术、实践逻辑与公共理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解释考察》;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6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42页。
⑨公丕祥:《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能动》,《光明日报》2009年9月9-11日。
⑩即从行动主体单方面的目的出发,以自己的成功为指向,把一切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因素都视为手段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