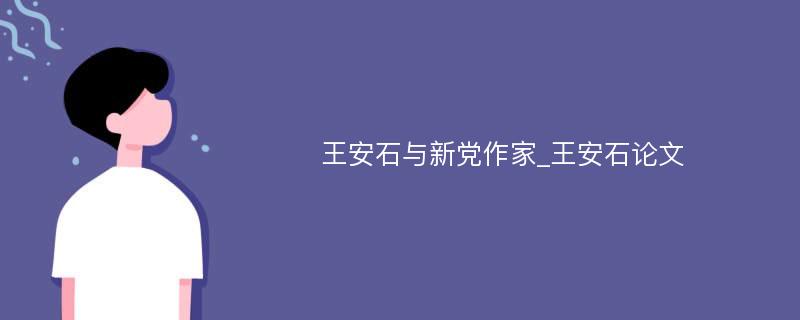
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安石论文,新党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在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后,罗列了一长串分别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交游和入“三氏门下”的作家名单,总结了庆历以后作家群的基本概况,也反映了北宋作家在崇儒重文的时代氛围中亲师取友的结盟思潮。不过,这种以师友为纽带而出现的作家群,并非仅仅停留在文学意义上的结盟。以欧阳修为中心的作家群是庆历前后诗文复古运动的主力军,在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中又多范党中人,而诗文复古运动则又是庆历政治革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以欧阳修门人王安石、苏轼为中心的两大文人集团,在熙宁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中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少还直接隶属于新党和旧党中人。不妨说,党争促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分野,又影响了其文学结盟,而文学上的结盟又反过来推进了政治上的结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北宋文学结盟思潮是政治上‘朋党论’的文学翻版,文学结盟是政治结盟的逻辑延伸”〔1 〕。这对成就一代作家、繁荣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北宋文学的发展与欧阳修、苏轼先后盟主文坛,切磋唱和、各逞才力密不可分;而北宋文坛一度出现的“弥望皆黄茅白苇”式的萧条景象,则与王安石和新党作家的结盟实践有着内在联系。在研究北宋文学时,总结作家结盟的成功经验,固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考察作家结盟的失败原因,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
新党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王安石之行新法,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纷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革新的旧党遂同时产生。作为执政党,新党在熙、丰期间主持新法,长达十七年之久。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嗣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了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废除新法,驱逐新党。为了彻底根除新党势力,元祐四年五月,左谏议大夫梁焘上疏开具新党人物的名单,榜之朝堂。疏云:
臣等窃谓(蔡)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吕嘉问、沈括、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2〕新党是个不稳定的政治集团,随着新旧党争与新党内部矛盾的激化,一些人或出或入,或同或异,或敌或友,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但就总的政治倾向而言,上列人物均属新党。他如王雱、韩绛、邓绾、龚原、李定、元绛、邓润甫、蒋之奇、李清臣、林希等亦属新党人物。而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擅长文学的,不少还撰有专集。据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等公私书目,新党主要作家有文集的,约21家,他们是:王安石《临川集》100卷;吕惠卿文集100卷(集名《东平集》,见孙觌《东平集序》),又奏议170卷;曾布集30卷;章惇《内制集》; 沈括《长兴集》41卷;陆佃《陶山集》20卷;元绛《玉堂集》20卷、《玉堂诗》10卷;王雱《元泽先生文集》36卷;舒亶文集100卷;龚原文集70卷; 彭汝砺《鄱阳集》40卷;李清臣文集100 卷(《直斋书录解题》作80卷, 集名《淇水集》),又奏议30卷; 张商英文集100卷;蒲宗孟文集70卷;安焘文集40卷;蔡肇文集30卷、诗3卷;曾肇文集40卷,又奏议12卷、《西垣集》12卷、《庚辰外制集》 3卷、《内制集》5卷;吴居厚文集100卷,又奏议120卷;韩绛文集50卷, 又《内外制集》13卷、奏议30卷;邓绾《治平集》30卷,又《翰林制集》10卷、《西垣制集》3卷、奏议20卷、杂文诗赋50卷; 蒋之奇《荆溪前后集》89卷,又别集9卷、《北扉集》9卷、《西枢集》4卷、 《卮言集》5卷、芻言50篇。凡21家。其中仅王安石一家保存完整, 沈括、舒亶、陆佃、彭汝砺、曾肇5家颇有散佚,其余15 家均已失传,其存零星篇章,今被收入《全宋文》、《全宋诗》与《全宋词》中。
由于新党作家的集子大多散佚不存,加上南渡以后对新党在政治上的全盘否定而以人废言,所以除王安石外,其他新党作家的文学业绩或沉没不彰,或很少有人齿及,给后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主要是政治人物,且多为奸佞小人,不擅长文学。其实,新党人物亦以文学、政事为立身之业。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指出:“李定、舒亶,世知其为凶狡亡赖(主要指炮制乌台诗案),而不知其皆留意文学者。”熙宁三年四月,司马光责问神宗“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时,神宗即以“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答之〔3〕。可见, 李定是以文学兼经术之长进入政府要害部门的。据《乾道四明图经》卷五,舒亶“博学强记,为文不立稿,尤长于声律程文”,以文学见知于王安石,“授太子中允、御史里行,累迁试给事中、直学士院,制命辞令,简重浑厚,有两汉风”。舒亶于诗、词、文均有创制。其词思致妍密,成就“不减秦(观)黄(庭坚)”〔4〕。 诗则清新隽永,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
七言绝句,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举。予每爱舒信道(亶)《村居》云:“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如此之类甚多,不愧前人。民国时,张寿镛辑有《舒懒堂诗文存》三卷、补遗一卷,收有舒亶古近体诗126首, 所咏全是有关鄞县山水风土,不仅近体“不愧前人”,古体亦不乏佳作。又吕惠卿,孙觌《东平集序》云:
观文殿学士东平吕公(惠卿)以文学政事,被遇神宗皇帝,于熙宁、元丰中,进居从官大臣之列。……公逢圣主,明道术于绝学之后,续微言于将坠之余,志合言行,应期而出,不数十年,遂参大政,谋谟讽议,劝讲论思,典册施于朝廷,乐歌荐之郊庙,扶衰救弊,尊主庇民之言,丰则裕固,治兵御戎之策,弥逢政事之体,不谬于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于今,声气相交,风动云兴,如虎吟啸,如凤鸣高岗之上,辞丽义密,追古作者。〔5〕
吕惠卿人品不足道,但孙觌称其擅长文学这一点是可信的。吕惠卿以文学先后知于欧阳修、沈遘和王安石。欧阳修称他“材识敏明,文艺优通,好古饬躬”〔6 〕,沈遘说他“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以过人”〔7 〕。吕祖谦《皇朝文鉴》选录其《建宁军节度副使谢表》,《谢表》结尾云:“龙麟凤翼,已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以“虫臂鼠肝”讥刺苏轼兄弟,苏轼阅后笑曰:“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八《经籍考》云:“考亭(朱熹)论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惠卿)而不取秦少游(观)辈,其说以为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这与孙觌所谓“辞丽义密,追古作者”之意相仿。李清臣亦享有文名,《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云:“欧阳公(修)爱其名,以比苏轼。”又如彭汝砺,王安石《赠彭器资(汝砺)》诗称其“文章浩渺足波澜,行义迢迢有归处。”并云:“我挹其清久未竭,复得纵观于波澜。”曹庭栋《宋百家诗存》卷一一谓彭汝砺“读书为文,志于大者,言动取舍,必揆于义,风裁卓荦,为时所重。”即便是蔡京,亦不失为一作手。崇宁蔡京擅政后,禁毁包括诗歌在内的所谓“元祐学术”,于崇宁元年十二月下诏:“诸说诐行非先圣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9 〕又于次年四月下诏:“禁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同月又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0〕尽管如此,蔡京本人却爱好和精通文艺。蔡縧《西清诗话》记其父京与他论诗语云:“汝知歌行吟谣之别乎?近人昧此,作歌而为行,制谣而为曲者多矣。且虽有名章秀句,若不得体,如人眉目娟好,而颠倒位置可乎?”同书谓其《春贴子》诗中“龙烛影中犹是腊,凤萧声里已吹春”一联,“荐绅类能传诵”。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载:
蔡元长(京)既南迁,中路有旨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来索也。元长作诗以别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饮食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稍息,元长轿中独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一诗一词,既有痛苦的回忆,又有失声的忏悔。写个人悲苦,却感情真挚,即如周辉《清波杂志》卷四“逐客”条所云:“放臣逐客,一旦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
除上述外,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凡150卷。录新党作家诗文320篇,其中王安石诗赋92首,文112篇;沈括诗赋6首,文4篇;林希赋1首,文13篇;张商英诗2首,文1篇;元绛文27篇;李清臣文12篇;邓润甫文9篇;吕惠卿文3篇;曾布文2篇;曾肇文32篇;彭汝砺诗赋2首;陆佃、蔡京文各1篇,蔡确、舒亶赋各1首。又南宋人编的《国朝名臣文粹》,所录新党作家的作品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亦可窥见新党人物的文学业绩及其擅长文学之一斑。
二
新党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且又是一个在政治上结党造成文人分野的环境中形成的作家群,其中不乏高明的作手;同时还具有不同于其他文人集团的文学思想,有着一致的文学实践。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云:
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二程以理性。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从整个文化的角度观之,“经术”、“议论”、“理性”代表了北宋儒学振兴后出现的彼此关联的三个层面;就单一的文学层面而言,它们则代表了彼此冲突、互不相容的文学思想。王安石“以经术”,就是以治教政令为文。王安石明确地提出了“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的命题〔11〕,主张以文学之文缘饰治道,使文学“务为有补于世”;在他看来,“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12〕;如果“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彩,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底济用,则蔑如也”〔13〕。“辞”即文;“理”即道。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主张两不偏废,但更强调道的作用;强调道的作用,就是为了“求其根底济用”即“经术”。王安石执政后,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以经义策论升降天下士,就是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式来实施这一文学主张,从而赋予了政治功利的性质而呈现出过于重道的倾向。但二程却唯“理性”是从,认为“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则不能然,是己与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启口容声,皆至德也”〔14〕。这就是对其“作文害道”〔15〕的思想的具体阐发,将文与道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此,尽管二程作有《论王霸札子》、《养鱼记》等清新可读之文,人们并没有视之为文学家。苏轼既不同于二程,又与王安石异趣。在王安石议革科举制度之际,苏轼便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罢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并指出在经学之士石介与文学之士杨亿之间,宁可取后者而不取前者,因为在苏轼看来,经学之士“迂阔”,文学之士“耿介”〔16〕。苏轼的思想在文学之士中颇为流行。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云:
窃有所疑者,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未知秘校所取何等文耳?若尧、舜以来,杨、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17〕吕南公于熙宁中试进士不第后,绝意进取,以灌园终其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耻于“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亦即“经家”王安石用以取士的经义策论之文。二程认为“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而不认为是重道之“经家”,苏轼与文学之士却认为王安石轻文艺而重经学。这就是陈善所谓三家“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的关键所在;而吕南公“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云云,就是指文学思想的分歧促使了政治上的分党,政治上的分党造成了文人群体的分野,亦昭示了政坛上的结党与文坛上的结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对于文与道或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正是促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形成的因素之一。
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和“济用”功能,是王安石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亦是他在变法过程中自为盟主,使之薪进火传,保持连续性和后继力的目标。不过,上述说明,王安石与其所结盟的新党作家在力图实现这一思想和追求中,并没有停留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上,而是采取了科举取士的形式,成了其变法的内容之一,从而将它转化成了政治思想和实践,即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式,将文学全面地纳入“务为有补于世”的“经术”轨道上来。
陈师道《后山集》卷一八《谈丛》云:
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董举子专诵王安石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教坊杂戏云:“学《诗》于陆师农(佃),学《易》于龚深之(原)。”盖讥士之寡闻也。“学究”即经生,“秀才”指文士,陆佃、龚原均为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章句”即指用于科举的教科书《三经新义》。“欲变学究为秀才”,将经生培养成为知“经术”的文章之士,使其人其文“务为有补于世”,担负起治国经邦之重任,是王安石以经义策论取士的用意所在。但事与愿违,结果却“变秀才为学究”,故更加遭致文学之士的强烈不满。而作为王门弟子或其他新党作家,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与王安石一样不乏纯文学上的成就,在政治实践中,却成了王安石以经义策论取士的有力推行者。如陆佃,诗文兼擅,其诗以七言近体见长。陆佃之孙陆游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亦擅长此体,故四库馆臣云:“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18〕但一方面,陆佃“受经于王安石”〔19〕,王安石以经术用之,兼侍讲,曾巩亦认为陆佃“好古知经,宜在此位”〔20〕,并对王安石经学有所继承,陈振孙谓其《尔雅新义》“大率出王氏之学”〔21〕;另一方面,正如教坊杂戏所云:举子“学《诗》于陆师农,学《易》于龚深之。”陆佃与同门龚原在推行王安石《三经新义》的过程中,用功甚深。《三经新义》是王安石经术之学的代表作,亦是用以取士的教科书。但除《周礼新义》“亲出于荆公之笔”,《诗经新义》与《尚书新义》乃“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22〕,其中还包括了王安石之子王雱、女婿蔡卞和妹夫沈括的写作。这就是说,《三经新义》不完全是王安石个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党集体思想的结晶。扩而言之,以《三经新义》作经义策论取士的教科书,从而求取文学的“经术”根底,发挥其“济用”功能,是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新党文人的主张,并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绍圣初,章惇、曾布、蔡卞等新党人物东山再起后,旋罢元祐党人所恢复的祖宗以诗赋、论、策三题取士之制,重新将被元祐党人废禁的《三经新义》播诸学馆,用以取士〔23〕,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主张以文学之文缘饰治道到以经义策论取士,王安石既实现了文学与经术的统一,又完成了从文学到政治的转化,从而使这一由诸多层面交织而成的结构体赢得了内在权力场域的支撑,亦使该结构体获取了外部权势上的结盟。换句话说,王安石与新党人物在共同交织这一多层面的结构体的过程中,实现并保持了既是文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结盟,取得了文学、经术和政治等不同层面或领域中的资本,确立了对在这些不同领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支配地位。终而通过他们自身的这种实践活动,侵蚀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元丰末年,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指出: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己,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脊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王氏之同也。〔24〕王安石论文亦主张自得其志,重性情之真,并体现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当他以其文其学“同天下”,“董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和权威时,便阻碍了文学自身特点的发挥及其自身规律的运行,给文坛造成了“弥望皆黄茅白苇”式的萧条景象。当然,对于这一景象,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是不希望出现的,亦是不愿看到的。但这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在“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的思想指导下,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与经术转化为政治与政制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在这一过程中构成的无法克服的一种逻辑发展。随着新党长期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和新党人物竭力推行王安石以经义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实施,这一逻辑发展愈陷愈深。至蔡京擅政,“专尚王氏之学,凡苏轼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25〕,并出现了全面禁毁政敌“文字”的局面,则不仅是以王安石的经术之学侵蚀文学及整个文化领域内的多样性和自主性,而且是用作践踏和毁灭文化的武器了。这更是王安石所不愿看到的,但其渊源,殆有所自。
从王安石以其文其学“同天下”,导致文坛如“黄茅白苇”,到蔡京以王安石学术为武器,进行全面的“文字”之禁,前后用意不能同日而语,性质亦迥然有别,但都是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悲剧。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王安石与新党集团将统一后的经术与文学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而形成的支配和控制文学、文化的专制集权。
三
王安石虽然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并在变法中自为盟主,使之薪进火传,但事实上,作用于王安石及其结盟的新党作家的,已非文学本身,而是政治;维系他们的文学实践的,主要不是文学自身的运行规律,而是政治权力。因此,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在文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不仅如此,张舜民《哀王荆公四首》其二、其三还云: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26〕王安石本欲继承乃师欧阳修提携后进的优良作风,使文坛保持连续性和后继力而广栽“桃李”,但所提携者多为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去来无情。王安石执政时,门庭若市,人人尽道是门人;罢政后,门庭冷落,“人人讳道是门生”,令人为之悲叹。其实,这与维系王门的纽带主要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密切相关,是王安石赋文学结盟予政治功利所使然。
同时,类似“江湖从学者”的品格在新党内部亦不乏其例。其中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吕惠卿小王安石11岁,自称“自少以来与安石游,凡有议论,更相是正”〔27〕。在王门中,吕惠卿的经术、文学与才干是王安石最为赏识和器重的一个。因有王安石的器重与提携,加之变法初期表现出来的异常坚定与积极,吕惠卿在政治上迅速发迹,史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安石力荐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惧安石去,新法必摇,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28〕。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吕惠卿信任之笃和吕惠卿对变法用情之专。然而吕惠卿任执政后,“得君怙欢,虑荆公复进”,故在王安石居金陵期间,施展手段,排挤王安石〔29〕。王安石复相后,吕惠卿又无事生非,与王安石产生磨擦,进而在神宗面前丑化王安石的形象,力图破坏神宗对王安石的印象,从而达到固宠保位的目的,最终发展到离心离德,反目相仇。这较之“江湖从学者”,更令王安石伤悲不已。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后,新党内部便有王党和吕党之说;元丰间,又有蔡确亲党之说;绍圣后,章惇、曾布、蔡卞、蔡京互相倾轧,各自为党。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亦验证了阿克顿的一句话:“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30〕。
总之,无论是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在文坛结盟,抑或为了推行新法而在政坛结党,其结果都是失败的。它不仅以政治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导致了文坛的萧条,而且在群体内部也因政治发生冲突与分化而缺乏包容性和整体性,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门与苏门两大作家群的鲜明特征。
注释:
〔1〕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2〕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一元祐四年五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甲申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6页。
〔4〕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词话丛编》本,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7页。
〔5〕孙觌:《庆鸿居士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欧阳修:《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一七,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894页。
〔7〕沈遘:《荐胡宗愈吕惠卿札子》,《西溪文集》卷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銍:《四六话》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9〕〔10 〕黄以周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崇宁元年十二月丁丑条、卷二一崇宁二年四月丁已、乙亥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第248页、第249页。
〔11〕王安石:《与祖择之书》,《王文公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2页。
〔12〕王安石:《上人书》,《王文公文集》卷三,同上,第45页。
〔13〕王安石:《上邵学士书》,《王文公文集》卷三,同上,第38页。
〔14〕《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道篇》,《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6页。
〔15〕《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程集》,同上,第239页。
〔16〕《苏轼文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4页。
〔17〕吕南公:《灌园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陶山集》提要,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3页。
〔19〕《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10917页。
〔20〕曾巩:《陆佃兼侍讲蔡卞崇政殿说书制》,《曾巩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7页。
〔2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22〕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四《荆公新学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9页。
〔23〕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经新义》被焚毁在元祐元年十月;据《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元祐党人以诗赋、论、策三题取士在元祐四年至八年。
〔24〕《苏轼文集》卷四九,同前,第1427页。
〔25〕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五靖康元年五月五日记事,《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张舜民:《画墁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条,同前,第2527页。
〔28〕《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同前,第13706页。
〔29〕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30〕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标签:王安石论文; 新党论文; 吕惠卿论文; 宋朝论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论文; 直斋书录解题论文; 苏轼论文; 宋史论文; 丛书集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