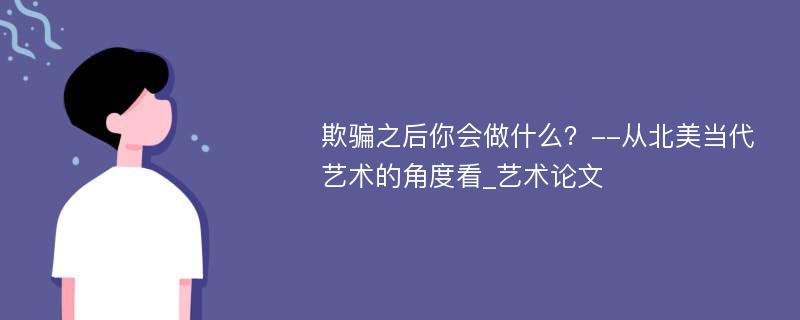
恶搞之后又干什么——从北美当代艺术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恶搞论文,当代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在蒙特利尔看了几个当代艺术展,有架上绘画、装置和新媒体作品。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这就是不少艺术家都偏爱“用典”的修辞手法,这让我联想到国内美术界时髦一时的恶搞之风。
“用典”原本是写作中使用典故的一种修辞手法,就是在自己的书写中化用或指涉前人或他人的书写,如宋词中大量化用并指涉唐诗的典故。当代艺术中的恶搞,在特定意义上也是用典,属后现代艺术的一种修辞手法,而近年成为江郎才尽和黔驴技穷者们的时尚。中国当代艺术的恶搞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例如周星驰的滥俗电影。由于中国文艺界过去的封闭和一叶障目,文化人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结果,当香港俗文化传入大陆时,举国上下欢呼雀跃,一片热捧,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连北京大学的“精英们”,也追逐时尚,不耻下问,将周星驰当作语言艺术家,聘为客座教授。中国文化的价值底线,就此面临着失守的危险。
在当代美术界,失去了价值底线的时髦艺术家们,经过后现代艺术的俗文化麻醉,也丧失了艺术判断的能力。一些当年具有强烈批判精神和深刻反思意识的优秀艺术家,例如那两个人气很高的兄弟,如今沦落为港式文化殖民主义的拾牙慧者。他们企图用周星驰式的恶搞,来颠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精华,并以此向西方策展人献媚,以求五斗洋米的赏赐。殊不知,这样做反而颠覆了他们自己当年辛辛苦苦获得的艺术成就。现在,恶搞者开始自食其果,恶搞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修辞语言,已经开始被人唾弃,周星驰之类滥俗表演的浅薄和庸俗,正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识破。
那么,在恶搞之后,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们,尤其是当代观念艺术家们又该做什么?
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我不打算去预测当代艺术的未来走向。我只睁开双眼四下观看。在西方,我看到当代观念艺术家们在经历了类似的恶搞之后,对自己的西方文化遗产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面对曾经恶搞过的西方经典,他们的态度有了微妙但清楚的变化。自从杜桑恶搞蒙娜丽莎以来,拾人牙慧的前卫艺术家们已经累得麻木了,他们需要新的刺激,或者,他们认识到了恶搞的浅薄和毫无意义,于是他们开始重新看待西方经典。
今秋在蒙特利尔当代美术馆,我看到眼下走红于欧美的巴西画家维克·穆尼兹(Vik Muniz,1961-)的作品,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用千奇百怪的材料重新绘制的西方经典绘画。穆尼兹1961年生于巴西圣保罗,后来移居美国纽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享有国际声誉。最近几年,他在西欧和北美举办巡回展览,其作品主要就是这类重画的西方经典。
在穆尼兹送展的作品中,有一组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大幅绘画,以色彩的强烈对比而具有撼人的力度。这种力度,来自作者对色相和色度的经营。例如,他给细小的软泥球涂上各种色彩,然后用来组合莫奈的风景,并用色相的对比和色度的变化,来发挥莫奈绘画的色彩力度。我认为,这是穆尼兹在形式语言层次上对莫奈的阐释,也即尝试“有意味的形式”。穆尼兹重画莫奈,就像钢琴家以自己的演奏而对肖邦进行阐释一样。
穆尼兹最被评论界称道的,是用食物绘制的两幅蒙娜丽莎。一幅的材料是果酱,另一幅的材料是花生酱,二者都是早餐时用来涂抹面包片的。穆尼兹用这样的材料,在早餐盘上涂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看似随心所欲或漫不经心,又仿佛是在制作视觉大餐。果酱是透明的,视觉效果像色层厚积的水彩。花生酱不透明,但泛着油渍,像是油画刀涂抹出的层层颜料。作者将餐盘上的“画”拍成照片,再放大制作为巨幅作品,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产生秀色可餐的联想。这些作品的制作相当简单,就是一个盘子、一把餐刀,再加果酱和花生酱,称得上极简主义。但是,既然是观念艺术,其要义便不在于制作。那么,作者究竟想借这看似简单的作品来说些什么?也许连作者本人都不一定清楚。因此,我获得了一个解读的空间,得以初步探讨穆尼兹对西方经典的重新绘制。
在视觉艺术之修辞语言的层次上说,重画经典的用典法,乃后现代主义的挪用或戏仿。但是,穆尼兹的重画经典,还有所不同。挪用一般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戏仿则有嘲弄的喜剧性,而穆尼兹却像临摹一样绘制,但最后的成品却与原作大异其趣,早餐盘上的蒙娜丽莎便是一例。
穆尼兹重画的莫奈风景和蒙娜丽莎,视觉效果很不一样。一是彩色泥球,远看像绒绣的壁挂,色彩丰富,近观却是一团乱麻;另一是果酱和花生酱的单色作品,虽似水彩和油画,却更像素描或木刻。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穆尼兹重画经典进行各种阐释,但是,我所看重的是他对西方经典的态度,这态度便是观念。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波洛克曾让人拍过一张工作照,他将画布平放在地,一手握笔一手拿着颜料桶,往画布上滴洒颜料。这是20世纪中期行动绘画的一幅经典摄影,穆尼兹用溶化的巧克力糖浆重画了这幅摄影作品,并将这巧克力画拍成照片送展。面对这幅大型巧克力画,我在展厅里看到的是具象和抽象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不再是对立或融合那样简单,也不是一句对立统一或互动转化就能说明的关系。无论二者的关系怎样复杂,我透过这关系看到了作者对波洛克的态度,一如他对莫奈和达·芬奇的态度,这就是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和心理状态下,用不同的材料来重新体验波洛克的绘画过程,来重新认识波洛克的艺术价值。
杜桑是偶像破坏者,尽管他是20世纪前期的达达分子,但却因破坏偶像而成为后现代美术的一个始作俑者。杜桑对西方经典的态度是破坏性的,穆尼兹却不是。在我看来,穆尼兹是在挪用和发挥杜桑的方式,以此来清算杜桑的破坏活动,也即对颠覆者进行颠覆。说不定这才是穆尼兹观念艺术的隐藏目的。
最近杨飞云有新作《三友行》在北京展出,看来这位一向以手绘技巧取胜的写实画家开始用脑子作画了。杨飞云身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环境中,积极介入了今日艺术市场,但他过去的作品却不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更不是观念艺术。然而,如果我们进行换位思考,从西方视角来看他的新作《三友行》,情况就不会那样简单。 《三友行》是杨飞云惯常的裸女作品,画了三个裸女相互牵着手,其图式是鲁本斯或马蒂斯式的。且让我假设这样一个情形:在欧美当代艺术圈的一次画廊聚会或展览开幕酒会上,来宾都是西方著名画家和艺评家,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看到了《三友行》,但并不知道作者是中国人。他们面对这幅画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是,这是一幅以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惠三女神为题材的拟古绘画。但是在酒会的杯盏交恍中再一留神,却发现作品明显违背了这个题材的传统图式,因为其中一位女神正转身离去,而传统图式则是三人围成一圈,或三人面朝同一方向,就像鲁本斯或马蒂斯的名画那样。于是问题便于此出现:《三友行》究竟是在质疑希腊神话,还是意欲解构鲁本斯和马蒂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宾们第三次审视画作,结果大吃一惊,发现画中的三女神竟是东方人而非西方人。于是他们一致认定,这件作品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解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具有后现代思想的观念绘画。在这之后,如果他们得知作者是中国艺术家,他们便有可能进一步说这是一幅后殖民主义作品,旨在颠覆西方的强势文化。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假设而已,其中不乏夸张和牵强之处,而且,我估计杨飞云也没有解构或颠覆的想法,他的画无非是一件商业性的裸女画罢了。上述假设的目的是想说明两点,其一,西方当代美术界涉及观念艺术时,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二,杨飞云在这件作品中的修辞语言是用典法,但他并不是要恶搞希腊神话或鲁本斯和马蒂斯这样的西方经典,而是以淡淡的幽默,及不带恶意的挪用和戏仿,是对重画西方经典的一种阐释性尝试。杨飞云对西方经典的这种态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提醒了我们态度之于观念的重要性。
对经典艺术之态度的转变,是北美当代艺术的一个新动向,这一动向涉及形式和观念的两极。换言之,在超越了跟风恶搞之后,北美当代艺术家们,更倾向于借助形式来进行思考,于是,他们的作品便产生于形式与观念之间。如果说穆尼兹是一个成熟的观念艺术家,洞悉了形式与观念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看新起的年轻艺术家的情况,看看他们在形式与观念之间都做了些什么。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当代艺术画廊,我看到了当地画家第尔·海德伯兰(Dil Hildebrand,1974-)的架上绘画。海德伯兰生于1974年,最近获得加拿大最高美术奖,称得上美术界的明日之星。
海德伯兰的作品主要是风景画,在这些绘画中,作者利用视觉错觉玩空间游戏,所玩对象是德国当代名家里希特。里希特有一件大幅仿摄影的风景作品,收藏于蒙特利尔美术馆,是当地美术圈中人眼熟能详的作品。里希特把玩的,是摄影和绘画之间的视觉错觉,是有关再现和写实的概念。海德伯兰作为后来者,站在前人的肩头,在空间关系上,将里希特的单一画面,发展为两个画面。例如,他仿画了里希特的风景,将里希特故意绘制得模模糊糊的画面推向极端,仿绘得更加模糊,制造出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使之成为第一个画面,即户外风景的画面。然后,海德伯兰又在这风景的画面上,绘制雨滴,形成第二个画面,即画布上的画面。于是,他的作品看上去就像是透过湿漉漉的玻璃窗所见到的模糊风景一样。其实,这种把玩双重画面的方法很老套,前人早就尝试过了,国内当AI写作实画家冷军近年也有类似的尝试。海德伯兰了解这一老套,于是他更多地关注两个画面之间的空间张力,并在这弹性的空间中制造多重视觉幻象,例如他送展的《无题》系列。在这些作品中,他试图发挥里希特的语言,以扩展语言的容量及其所承载之观念的深度。
海德伯兰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画家,他的想法和作品,都相对粗浅。不过,我欣赏他的态度,他没有去恶搞里希特,而是承认里希特的成就,并借助里希特的探索来进行自己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远离了杜桑的偶像破坏主义,远离了后现代的解构和颠覆,拒绝了盲目跟风,从而有可能以认真的态度去开发自己的艺术语言。
这种态度不仅表现于架上绘画,也表现在新媒体艺术中。加拿大著名女艺术家凯瑟琳·理查兹(Catherine Richards,1950-)是渥太华大学视觉艺术系教授,专攻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最近蒙特利尔美术馆有大型展览“电子艺术”(E-Art),她送展了一组电子装置作品,名《寻找爱情的方法与仪器》,由灯显文本和大型图示构成。这组装置中的图示,是一系列西方经典绘画的线描图,有点像中医的针灸穴位图。作者在图中人物的性感部位,标出神经元的位置,并以文字说明男女爱抚时该怎样刺激这些部位来获得性快感。这组装置初看有点反讽的意味,但读过文本之后,方知作者旨在通过解析西方经典中的情色绘画,例如意大利风格主义时期蒙蒂切利(Monticelli,1503-1572)的名画《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意》,来探索物理学、心理学、通讯传感技术与艺术间的关系。
理查兹的这件电子装置,既涉及了意大利的经典绘画,也涉及了杜桑的著名现成品装置《大玻璃》。于是,她得以将经典偶像和偶像破坏者的经典作品共置同一空间,用作自己作品的典故,以此而在形式与观念之间,为自己的新媒体艺术寻求一种亦庄亦谐的修辞效果,从而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个人化的探讨。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要提及加拿大年轻艺术家李斯特·勒米埃(Lisette Lemieux)的一件大型装置。他在画廊里做了一个装饰架一样的大架子,然后将黑色胶片卷成空筒,长短不一,密密麻麻地塞在架子上。架子后面的灯光透过来,使胶片筒呈现出达·芬奇的名作《人体比例》,也就是小说和电影《达·芬奇密码》一开始那位被谋杀者摆出的人体图形。由于灯光的巧妙使用,我猜测这件作品的用意在于探究文艺复兴的启蒙价值。在英语和其他主要的欧洲语言里,“启蒙”与“用光”字源相同,是照亮人之心智的意思。在此,作者利用视觉艺术与语言艺术的互涉关系,暗示了西方经典在今天的文化意义。
本文开篇说中国当代美术的恶搞,源自香港小市民文化的低级趣味,是被殖民者文化形态的一种犬儒主义表现。实际上,西方早有恶搞,而其理论阐释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解构主义理论“影响的焦虑”。西方经典对后人的影响,与西方殖民主义对香港俗文化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影响的焦虑”注重后人的揭竿而起,而港式恶搞则注重被压抑者的犬儒主义及其可怜的意淫。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恶搞之后,中国的当代观念艺术家们,应该对恶搞有理论的反省和历史的清算,否则,中国当代艺术的下一站便不知该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