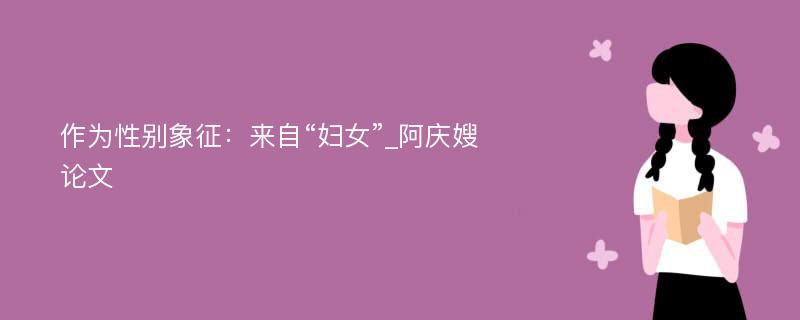
作为性别的符号:从“女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女人论文,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探讨文学语言中的性别问题,符号是一个重要概念与对象。因为符号不仅构成文学语言的有机成分,而且还构成其特定的修辞元素与意义。一个符号所意蕴的性别性,最终都被体现为文学语言的性别性。这种性别性出现在每一个具体文本中的具体形象上,并在融入被塑造或被接受的过程中而发生其不可思议的定向作用。
而要揭示符号所具有的性别性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女人”“男人”这样的符号与形象,在表征性别的意义上,不仅是首当其冲的,也是本源性的。日本的语言文化学者池上嘉彦曾指出:凡是人类所承认的“有意义”的事物均成为符号,人们不断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着这种类似“创造语言”的活动,现代符号学所关心的就是探讨这种活动的原型和本质。换言之,现代符号学关心的是人类“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①。因此,本文将借由对“女人”这个本源性的性别符号在文学文本中的形象构成,来探讨人类——一个由“男人/人类”(man/human)所构成的以男性中心的——文化,对男人—女人(man-woman)这个符号在文学中进行了什么样的“给予意义”的活动,它与性别刻板印象形成的关系与过程,而这个过程与结果又怎样反过来加固了性别符号的既定,以期揭示人类的性别歧视文化结构在文学语言结构中的投射、反映与功用。
1
众所周知,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为“符号”界定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择其要点阐述如下:其一是索绪尔经过一番慎重的比对与思考后,确定用“所指”与“能指”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符号的组成部分。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尔特评价说,在索绪尔找到能指与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意义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的能指相混淆,他认为索绪尔的这一主张至关重要,应时刻不忘,因为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作能指,而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双面的现实②;其二就是关于这个“双面的事实”。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要素都是心理的,它们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③。按巴尔特的总结是:在索绪尔的术语系统中,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是符号的组成部分。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或者说能指是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所指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再现。“索绪尔本人明确指出了所指的心理性质并称之为概念(concept)”④。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与阐述。但笔者在此想提出的一点是,也许索绪尔的研究是基于拼音语言文字之上的,故他对符号的“能指”面概念只能建立在音响形象之上,而对于如汉语言文字这样的象形文字来说,其符号的“能指”面可能不仅仅只限于其音响形象,应还包括其文字形象,即巴尔特所说的符号的表示成分。如果这个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索绪尔所强调的“能指”面的心理性质,应同样也是文字形象这一要素所具有的。
笔者以为,与索绪尔区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一样伟大或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语言符号的心理性质。这就为我们把对符号进行探究的视野从符号本身的结构,扩展到与人类文化结构的关联上,是特定的人类文化活动在人心理上的投射,造成人类心理在特定符号上的投射。这是我们能够洞察与讨论“女人”被作为一个性别文化的符号与文学形象的理论前提。
当代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用不愿“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妓态”⑤的表述,来表达自己傲然不流于俗的人格与个性。这个境界,是中国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人格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人格史上的主旋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说出来完全可以达到一呼百应、心领神会的效果——尽管在现实面前不知有几人存焉,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说自己“奴相”、“妓态”,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二个符号所指意指都甚为不堪。作家只在此使用了这两个符号,便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不仅是言简意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形神兼备的传达效果,从而不仅显示了作家的人格境界,同时也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文学修辞功力。这种效果无疑得归功于“奴相”与“妓态”这两个修辞意义极为强烈的形容性名词。而这个充满贬义不堪的修辞义,正是人类文化活动所赋予符号的意义。它们共同把这两种原本十分抽象的、既难于表述同时也难于理解的概念性“表达物”——一种人格状态,连带对这种人格状态的价值评判倾向,通过具有一定修辞意义的文学语言——一种符号,具体地、生动地、形象地表现出来,令人一目了然。试问谁愿为奴做妓,任人凌辱蹂躏践踏?被逼可谓惨,自甘则是贱,女人的别称是“贱人”,为人妻是“贱内”,从“贱人”的指事到“人格贱”的会意,于是,心领神会也好,一呼百应也好,人们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从这两个符号表示成份(能指)的“女之属”——一种屈辱的文字形象,到这两个符号被表示成份(所指)的“贱人”——一种低贱的人物形象,源远流长的性别等级制与性别歧视文化,已教会人们如何神速地读解出意蕴其内的含义。“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⑥,这个陈述就是“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妓态”的反比,同样经典。与“奴相”、“妓态”的“女之属”符号的负面形象与特征相反,它充满了男性化的正面形象与特征。顶天立地如松柏一样的形象,即是爹爹与共产党的男人形象,同时也是男性性特征形象,松柏成为能够标志男人精神气质与人格状态的符号,意蕴着顶天立地,意志坚强,光明磊落……阳性的褒义意象与色彩充满其所指,成为阳/男性符号的所指。而作为与阳性二元对立而存在的阴性所指,则充满了贬义意象与色彩,成为阴/女性符号的所指。
作为“女性”的另一个符号“阴”,也典型地反映出性别文化作用于符号结构的组成部分。其实,最早的阴,仅仅只是一个表示方位意义的词,如《说文解字》解:“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在清代的段玉裁注里,词义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扩充,意义更详细了:“阴,闇也,闇者,闭门也。闭门则为幽暗,故以为高明之反。”用以表示并形容阳光照不到的空间,即阴地也。但当“阳清为天,阴浊为地”,“阳在上,阴在下”,“男为阳,女为阴”成为人们的性别习得观念时,当阴阳二极同时也成为男女二性的性别符号时,阴阳二词的词义所指的不再仅仅是自然方位的结构,它承载更多的是人类性别文化的结构。从《说文解字》到《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是,从古代的“陰”到现在的“阴”,字形简化了,但意蕴则大大扩充了:阴沟、阴私、阴谋、阴险、阴曹、阴间、阴暗、阴沉、阴毒、阴风、阴魂、阴冷、阴霾、阴森、阴翳、阴雨、阴影、阴鸷等等,这里的每一个由表示方位同时也象征着女性性别符号的“阴”所构成的双音节词语,也都同时具有形容、比喻、双关等贬义修辞的作用——当它们进入特定语言陈述系统之刻,便也会是它们开始作用于这个陈述系统的修辞之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并感觉到的是,阳/男性符号中所蕴有的褒义性修辞有多么自然而深入人心,阴/女性符号中所蕴有的贬义性修辞也就有多么自然而深入人心。从“女”字屈膝跪伏的象形,到如“奴”与“妓”等“贱人”的意会,再到如“奴相”与“妓态”等“贱格”的意蕴,承载着阴/女性符号太多负面修辞意蕴的“女人”,作为文学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性别文化的符号,就这样产生:她被文化所文化,被符号所符号。
2
女,据《说文解字》解:为妇人也,象形。女人,据《现代汉语词典》解,有两个含义:一为女性的成年人,二为妻子。前者是对生理发育到一定阶段的女性的指称;后者是对处在一定人物关系状态中的女性的指称。如孙犁的《荷花淀》:
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成年女性)
水生的女人说:“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妻子)
以上这二种意义上的“女人”,可以说是“女人”这个符号的初始义。可以看出,“女人”在这里,还只是对处于“自然关系”状态中的女性的客观性命名,本身不含有来自于命名者的主观评价而形成的褒贬义。它与一指“成年男性”、二指“丈夫”的“男人”指称一样,同样是表示人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身份的词语,只是它们分别表示着不同的性别而已。因此,按理说,“女人”和“男人”这两个词语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可以用以区分成年人或婚姻关系人的性别,也只能起到区分性别的词语。但在文学语言中,情况却远非如此,它们不仅各自蕴有大大超越于区分自然性别与人物关系身份的客观性词义,而且二者之间还蕴有意义完全相左的、意味微妙的修辞意象,这使它们在文学语言的语境中,从词义到词意,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性,并发生完全不同的修辞效果。这种差异性与不同效果,可从堪为经典的戏文《沙家浜》“智斗”一场中的男女对话中,一窥其奥妙:
刁德一:这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德一与阿庆嫂是敌对的双方,当作者让刁德一用“这个女人”来指称阿庆嫂时,就完全可以把刁德一对阿庆嫂的敌对心理、敌对情态、敌对状态完全地、鲜明地刻画出来,表现出来。显然,“女人”在此,已不仅仅只是具有指称“成年女性”的客观性意义,它同时更蕴有某种可以与此表达情景相匹配的具有贬义性所指的主观性词义。或换而言之,是一种含有对“女人”这个性别群体具有约定俗成的、贬义性词义的所指,恰与刁德一所要表示的对阿庆嫂这个女人个体的敌意构成了一致性,才使“这个女人”指称,得以以最简约的话语形态,却可以最生动、最形象、最切合作者意图地,也是最能让读者迅速领会地表现出刁德一对阿庆嫂的敌意,从而达到最佳的修辞效果。
但是,有意味的是,在这同一个场景与情景中,阿庆嫂却不能以其道而用之,即用“这男人有什么鬼心肠”来替代“刁德一”这个个体男人的实名所指。如果从词义所含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所指来说(即成年的、女性的),按理说用“这个男人”来指代刁德一,就像用“这个女人”来指代阿庆嫂一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这里既不存在语法上的错误,也不存在词义上的错误。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作者使用同样的修辞手法来表达阿庆嫂的话——这种语言情景几乎也是约定俗成的,具有普泛性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不这样用,如果这样用,那么就会有种不得劲、不对味、别扭的感觉。这种不得劲、不对味、别扭的感觉,就是一个词语用在此时此地时所产生的修辞作用,它不是最贴切的与最恰当的,它所产生的修辞效果不是最理想的,甚而有可能是完全败坏的,是它构成了文学语言表述中的所谓“败笔”。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败笔”呢?也即作者为什么不能让阿庆嫂沿用刁德一的说法,用“这个男人”来指称刁德一呢?显然,问题就出在“女人”与“男人”这两个本应完全不带有任何主观性评价倾向的表示自然人的词义上。但现在,情况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果阿庆嫂也用了“这个男人”来指称刁德一的话,不仅不能产生如刁德一用“这个女人”指称阿庆嫂时所产生的恰到好处的、十分精妙的修辞作用与效果,而且还可能削弱了这种作用与效果。究其原因,奥妙就在于“男人”这个符号里,因为“男人”不仅没有“女人”这个符号中所蕴有的贬义性所指,反倒更多的是具有褒义性所指。因此,如果在贬义性陈述句中用了“男人”这个词语的话,那么,就会与贬义性的陈述句构成意义上的冲突与悖反。具体到阿庆嫂的这句话中,就是说使用它并不能起到阿庆嫂这个人物所要表示的对刁德一的敌意的作用,它不但不能与这种敌意构成一致性的语境,反倒会破坏掉文本所要营造的这种情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听众会听到刁德一唱“这个女人不寻常”,而不会听到阿庆嫂唱“这个男人有什么鬼心肠”的内在因素。
同理,作者也不会让阿庆嫂用“这男人倒是一堵挡风的墙”来取代“这草包……”的所指。因为,如果让阿庆嫂用了“这男人”,那么“男人”中所含有的褒义性所指的修辞作用,就会使这句话的意思和味道完全改变,它将不再是这个贬义性陈述句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了,它表现的也不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关系的情景。因为,阿庆嫂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利用明知是敌人的胡传魁缺心眼、头脑简单,即“草包”的缺陷,来为自己打掩护。也借此,作者在这里塑造了阿庆嫂形象中智慧的一面。但若用“男人”来取代“草包”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和所要表现的情景就会变为:因为胡是男人,所以他成为身为女人的阿庆嫂的挡风墙,这是符合男人保护女人、男强女弱的性别既定与公众心理的,那么,它所起的修辞作用与效果就可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歧义,甚而还可能接近褒义,这显然是不符合这个特定情景中的人物关系与情节关系的,不仅词不达意,而且不伦不类。可见,“男人”与“女人”,这样一个原来只是在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对人所进行的性别区分的符号,却也正因为其区别的恰恰是性别而不是别的其他,从而就被具有“性政治”意味的性别歧视文化,赋予了远远超出于生物学自然本义的,并且已全然不能对等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意蕴。如:
你是女人……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贬义性
你是男人……男人啊,你的名字是强者褒义性⑦
我是女人……做女人难,做名女人就更难否定性
我是男人……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肯定性
我们还可从否定式反证来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别看他是个男人,做起事来可一点都不……”因为不像男人,这句话含有对不像男人的男人的贬义;“别看她是个女人,做起事来可一点都不……”因为不像女人,这句话则可能含有对不像女人的女人的褒意。我们可以从类似上述的表述话语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语言心理现象,那就是人们不能像对“男人”这个符号那样来认同“女人”这个符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今天,男子是积极的和中性的人,意即代表着男性和人。而女子则只是消极的人,只停留于女性,每当女子作为一个人做出什么行动的时候,人们便认为这个女人和男人同化了”⑧。与之相佐证的,还有西美尔的发现:“在所有可能的领域中,凡有缺陷的表现都被贬为女性的,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称赞一个女人在同样领域内的成就时,就只能称之为‘简直像男的’。这一事实显然得归咎于文化客观因素的男性特征。这不仅因为男人的自大,好像‘男性的’是有价值的同义词。”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如果一个男人被比作女人,那是对这个男人极大的污辱;而一个女人若被比作男人,则多少含有对这个女人从个性到人格,从经验到事业的肯定与嘉许。“男人”的符号成为“女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的标杆,“男人”本身就被性别文化赋予没有缺陷的和有价值的符号,这就是为什么刁德一用“这个女人”的指称就可以到达他对阿庆嫂敌意的效果;而阿庆嫂若用“这个男人”的指称,则无法到达同等效果的原因。所以,作者只能让她选择避开“男人”符号而直呼其名或其类,比如草包、败类、孬种、恶棍等等。
3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是孙犁小说《荷花淀》中主人公水生夫妇的一段对话,也是最为人称道、引人入胜的文学桥段,它常常被引用来证明孙犁小说的美文特色,进而引用来说明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叙事特色⑩。而准确地说,这是孙犁式人物白描的最大特色:它不是通过对人物外形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人物对话间接来体现的。他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完全是在对话的场景中,被活灵活现地勾画到读者面前的。他的这种白描对话的手段,是文学描写中的经典。中国最为传统的女性形象与夫妇关系,与最富有时代进步(抗战)气息生活的融合,无疑是这篇小说叫好又叫座的关键。而其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孙犁内敛的、素朴的,但富有空间想象感的且充满韵味感的白描对话手法,与传统女性形象与夫妇关系的古典模式,形成一种天衣无缝般的诗意场景,是这关键中最为亮点的地方。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抽取了这部分对话白描精华,即使这篇小说写的题材有多么重大或应时,恐怕也难成为“荷花淀”派的文学气候与叙事标志。
那么,这个经典的对话场景体现了怎样的人物形象与夫妇关系呢?
在这个场景中,男主角水生作为男人,一名成年男性,在他作为“夫”的身份中,的确完全相应的显示了他作为成年男性应有的成熟与独立,他有独立的心智、人格、意志、思想与主事的能力。而女主角——水生家的女人,一名成年女性,则在她作为“妻”的身份中,非但丝毫没能体现出她作为一个成年女性也应有的与成年男性一样的成熟心智与独立能力,恰恰相反,它显示的是她完整的“没有”。女人的在场,先是只作为一个活动着的男人的沉默背景或活道具而存在,进而是作为烘托男人主事的形象而存在。男人女人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与尖锐的对照。有男人在,凡事有男人做主,女人只要听男人话的干活就是了。但现在男人要出远门了,女人就只好要男人的“嘱咐”——一种可以继续保存男人话语权在女人生活中的、保证男人继续对生活中的女人行使话语权的形态。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描写,才会把“女人”温顺听话的“正面”价值与传统形象,表现得如此鲜明突出。当然,与此同时的是,“女人”无主见的负面价值与形象便也相伴而生。于是,在这个场景中人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作为成年女性的女人/妻子,全面、完全、严重依附并依赖于作为成年男性的男人/丈夫的语言生活。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便在实质上被表现得完全不像是处于同一个“成年”阶段的、都具有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力的心智成熟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像是有思想能力的、知道做什么怎么做的、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与毫无思想能力的、不知道做什么如何做的、心智发育未成熟的儿童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这个动人的桥段还有涉及终极性意义上的生命权问题,这也是这一对话情境里最打动人的高潮:“女人”因其“性”属而绝不能被“敌人”——潜在的男人——所占有,在一系列温顺的“嗯”之后,最后还得流泪答应男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只为一个“男人”的性占有而活命的原则。很显然,女性在此关系中是毫无主体性而言的。人们,包括作者与读者,塑造与读解的是把性别文化中的“妻子”作为潜在标准而塑造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作为“女人”而塑造的女性形象。女人在此,完全剥离了作为“女人”符号的能指,男权制夫妇关系中“妻”的伦理内涵,成为“女人”符号的潜在所指。这种性别关系塑造的不平等要害之处在于正如劳拉·穆尔维所揭示的那样:“男人在这一秩序中可以通过那强加于沉默的女人形象的语言命令来保持他的幻想和着魔,而女人却依然被束缚在作为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制造者的地位上。”(11)有意味的是,作者并非是要在此小说中,着意揭示“女人”所具有的这种弱根性,而正相反的是,他完全是从审美的角度上来体现“女人”的这个“温顺如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读者都接受了这样的审美信息乃至熏陶:《荷花淀》能够以美文著称并流传于今,是与其中对“女人”的审美笔致分不开的。这也是笔者要在此举这个文本作为事例的意义所在。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符号是如何主导了作家的审美意识,这样,我们才可能切入其中的逻辑缝隙,揭示出被惯常审美表层掩盖了的深层悖谬。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如果把上述文本中的“女人”与“男人”的符号与形象互置,那么,文本会产生什么样的修辞效应呢?首先它应该会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因为它看上去是这样不真实与不合实际。如果硬要把它当作有意义的文本来看——犹如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女儿国”,那么它即便不是反讽的,至少也是荒唐与滑稽的。但是,如果这些表现是置放在“女人”这个符号下——犹如孙犁的《荷花淀》,那么,它不仅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还“看上去很美”。不仅如此,这“女人”被表现得越软弱和弱智,越没有主意与主见,越主动让“男人”对自己耳提面命,越使自己表现得俯首听命,那么,它的修辞效应就会越“美”越“正点”。因为这样的“女人”就越具有人们想象中的东方女性的“美德”,或者说是越满足人们对“女人”的想象——在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的历史(history)场景中,在与男性同化的艺术审美与社会价值观中。学者朱学勤曾针对性别问题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是男性文化,性别歧视渗透到最细小的一层文化细胞。女性如有价值,也只有美感价值,而且是生理性的美感价值,不是文化意识上的审美价值。”(12)这个见解固然精辟,但笔者还想说的是,男性文化不唯对女性“生理性美感价值”感兴趣,男性文化其实也“创造”了女性在文化意识上的审美价值。
对“女人”的这种审美价值观,直至今天,它依然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且很少受到其他包括政治、经济、职业、教育程度、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换而言之,在这世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存在太多的差异,但对“女人”这个符号的认知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举一个生活中的不乏典型性的例子:从事先锋艺术创作并以此标榜于世的某艺术家就曾这样表示:“我希望在女人身上看到我所没有的东西,包括她的幼稚、善良、她的容忍性。”(13)他认为这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如果不这样,就是“丧失了自己的天性”,他希望女人不要丧失了自己的天性。这番体现说话人女性观的话语反映了男权话语的显著症候:他没有的东西,即所谓“美德”,但却并不想让自己通过后天努力去获得,反而希望“女人”先天就为其所拥有。
显然,与其说这种“美德”是“女人的天性”,莫如说,是说话人通过话语权强加给“女人”的天性。当然,这种话不是某艺术家的发明,他只是在重复数千年以来反复被塑造的,而他信以为真的话,用他的话语权,再一次强加给“女人的天性”而已。他不是说这种话的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是身为男人的某艺术家才会这样说,很多生为女人者也会这样说。因为,这世上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习惯了对重复了很多次的语言信以为真,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思想。“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14)。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把这种事实叫做用语言新造出来的“再生性事实”。因此,他们绝对不排斥男人把什么当作“女人的天性”,女人就把它当作自己天性的事实,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语言中。
可见,作为表示人的性别成分的符号,“男人”与“女人”在文学语言中,除了它们的客观词义外,性别文化还赋予它们特有的意蕴。如果注意到索绪尔所指出的语言符号具有的心理性质,我们便可以理解这种语言现象或语言行为的产生:它的确不取决于被什么符号所标识,而取决于人们对被标识的这个符号的心理反映。正因为符号有这样的特质,它启发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这样的探究:即在文学语言的范畴里,具有特定意蕴的性别符号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作用的。一方面是性别符号在形象塑造时的作用,一方面是被塑造的形象对性别符号的固成或改变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8-13
注释:
①[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页。
②[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③[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g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0-101页。
④[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33页。
⑤贾平凹:《辞宴书》,《长舌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⑥引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⑦如果女人是强者,一般就会特指其“女”性,即“女强人”,在具体语言使用环境中,非褒意性更多,有另类之意指。
⑧[日]服部正:《女性心理学》,江丽临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31页。
⑨[德]西美尔(Georg Simmnel):《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⑩“荷花淀派”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流派,顾名思义便知这一命名源自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一般认为此派叙事的大体特征是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与乐观主义精神,语言素朴清新,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代表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
(11)[英]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编:《影视文化1》,周传基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12)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13)此段评述出于《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北京青年报》2005年8月15日。
(14)韩少功:《马桥词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