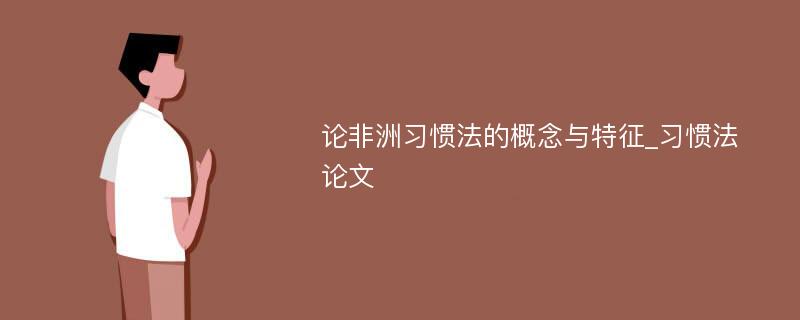
论非洲习惯法的概念与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非洲论文,特性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绚丽多彩的非洲传统法律文化中,非洲习惯法古老而又独具特色。而学术界对非洲习惯法的概念与特性分析多存歧义,这不利于有效地开展非洲法律文化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还非洲习惯法的本来面目。
一
在远古非洲法的起源时代,各民族国家法律制度一般经历了由习惯发展为习惯法,再向成文法转化的漫长历史时期。非洲古代国家形式的出现和发展相对缓慢,较其他大陆更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现象,从整体上看,北非的国家组织出现得很早,且一般比较发达,而越往南,国家组织则出现得越晚,且发展程度越低,直到公元15世纪前后,南部非洲很多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注:参见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因此特点,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法律状态还停留在习惯法阶段,只有少数国家如古埃及的纸草文书、铭文、图刻等考古发展反映出成文法存在的历史事实。古埃及的成文法典早已失传,难以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只能从保留到现在的一些写在纸草和石碑上的片言只字,以及一些残余的报道文件、契据和合同等项目中找到一些当时法律的痕迹”(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各国法律概况》,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因此,我们要了解的古代非洲法律, 通常指的是存在于古代非洲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法。
要探讨远古非洲习惯法,首先必须对“非洲习惯法”本身的概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学术界对此向来存在多种认识,例如,弗朗西斯·斯奈德认为“非洲习惯法”是近代的产物,是殖民时期的一种创造,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并与殖民国家有密切的联系。(注:弗朗西斯·斯奈德:《习惯法与经济》,载《非洲法杂志》(英文版),1984年第1、2期合刊,第34页。)西蒙·罗伯特赞成弗朗西斯·斯奈德的上述观点,他认为这种习惯法只是一种同过去有些联系的法,为殖民主义制度所支持,甚至被有些人喻为“创造出来的传统”(注:参见西蒙·罗伯特:《非洲习惯法的一些注解》,载《非洲法杂志》(英文版),1984年第1、2期合刊,第1~3页。)。西蒙·罗伯特进一步说,上述意义上的“非洲习惯法”被应用于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法院系统中,存在于移居国外的政府官员的头脑中,也广泛存在于非洲人的头脑中,这样,习惯法才可能流传至今。一些研究非洲文化的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他们的著作(特别是反映殖民时代的作品)中常常把存在于非洲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冠以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土著法”(native law)、“土著习惯法”(native customary law)、“土著法律和习惯”(native law and custom)、“地方法”(local law)、“部落法”(tribal law)等,而当旁注和引证是针对某一特定种族的法律制度时,就称之为“布干达人法”、“努尔人法”或“芳蒂族习惯法”,等等。在他们看来,欧洲基督教文明社会的法律居于支配地位,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是异教的未开化地区,这里拥有的不是法律,而仅仅是惯例。(注:A.kodwo kensh—Brown,Introduction to Law in Contemporary Africa,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6,p.19.)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是试图以欧洲法律种类的术语来重新解释非洲法律形式,将这种法律形式与西方殖民国家的法律形式相比较,因而称非洲法为“习惯法”。所谓“土著法”、“土著法律和惯例”、“习惯法”等术语,并非产生于名副其实的词源解释,而是产生于外国的种族主义偏见。显然,这代表的是一种殖民统治的观点。由于非洲本土习惯法普遍是不成文的,结果,许多非非洲(no—African )学生和学者据此认为,本土非洲法无资格称之为法律,在他们眼中,一种法律的存在只能通过对成文出版物的注释才能被确定。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传统非洲社会中并无专门法律职业这样的东西,正如阿洛特教授指出的那样,这儿的专门法律工作者极其稀少,培养律师的非洲本土法律学校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仍然没听说。法律“铭记在法官的心中”,它源于社会经验而非正规教育。(注:Ibid..p.23.)不过,尽管学者们对非洲习惯法的理解产生种种歧义与偏见,但从其法律的起源和发展进程考虑,使用“非洲习惯法”这个特别的名称仍有利于研究非洲法的过去和未来,况且,早在本世纪50、60年代,阿洛特等著名学者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并已开始了这个崭新的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注:参见西蒙·罗伯特:前引文。)与此同时,一些关于非洲法律问题的国际会议也曾对此展开讨论,如1959年12月28日~1960年1月8日召开的伦敦会议,即以“非洲法律的未来”为主题,部分与会者认为,尽管“本土习惯法”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但在当前情况下仍是一种使用起来最令人满意的表述。1963年9月8~18日,非洲独立国家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首次召开了法律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地方法庭和习惯法”。这表明,到1963年,“地方法庭”和“习惯法”已成功地取代了“土著法庭”和前面所提到的具有殖民色彩的分类术语。(注:A.kodwo kensh—Brown,Introduction to Law in ContemporaryAfrica,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6,p.21.)
不仅如此,一些非洲国家在采用“习惯法”这个用语的同时,还试图对它界定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解释。例如《加纳1960年解释法》第8条第1款将习惯法的概念表述为:“包含在加纳法律中的习惯法是由习惯形成的法律规则所组成的,这样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加纳的特殊社区。”(注:A.kodwo kensh—Brown, Introduction to Law
in Contemporary Africa,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6,p.20.此外, 伍德曼以加纳习惯法作为个案分析也下了一个十分相近的定义,参见戈登R·伍德曼和A·O·奥比拉德:African
Law and Legal Theory.Printed in Great Britan at the University.Cambridge,1995,p.36.)《坦桑尼亚解释法》第2条第1款表述为:“习惯法意指包含有某些权利和义务的任务规则或一系列规则,它建立在坦噶尼喀非洲人社区习惯的基础上,并具有法律强制力,而一般地被这些社区所接受。”1958年《尼日利亚联邦证据法》的表述是:“习惯法是一些在特定区域内由于长期使用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注:A.kodwo kensh—Brown,Introduction to Law in
Contemporary Africa,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6,p.20.)T·O·伊莱亚斯教授对习惯法的表述更具启发性,他认为:“习惯法是几代人生活经历的总结,它是一部深思熟虑的法典,是几代人用他们的经验和智慧通过一定的方法而制造出的一种联系。
”(注:
T.Olawale Elias. The Nature of
African
CustomaryLaw.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6,p.189.)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结合非洲社会的特点,笔者认为,本文中所讨论的非洲习惯法乃是这样一些行为规范,它是非洲各个传统社会中(主要指村社)属于各个族体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用来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且主要是在一套特殊的崇拜神灵、崇拜祖先等关系网络中,以口述方式被贯彻实施的。
二
非洲习惯法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形式上表现为“口传非洲法”。 与世界其他文化区相比,非洲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要借助口头语言、缺乏文字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注:参见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这种文化不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有典有册”,而是“有典无册”。也就是说,非洲传统文化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本,而是贮藏于人们脑子里的语言。对非洲各族黑人而言,语言不仅是日常的交流手段,而且是保存前人智能的基本工具和途径,所谓“先人的智慧蕴藏于基本言语,即口头传说中”,而口头传说“是保存和传播一代又一代非洲人民积累的社会和文化创造品的真正的宝库。”(注:J·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1卷,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84年版,第147、5页。)同理,属于各个族体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劳作中逐渐形成的非洲习惯法在形式上也相应地表现为“口传非洲法”(Oral African Law),因其形式是口头的而不是文字记载的,它活生生地存在于非洲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世代口耳相传,反复使用,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程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专门研究非洲黑人传说的当代马里学者A·哈姆帕特·巴认为:在非洲传统社会里, 深远而神圣的联系把人的行为与言语结合为一体,人们必须信守自己讲的话,并受其约束,他就是他的言语,他的言语就是他自身的证明。社会的协商依靠言语的价值和对言语的尊重。(注:参见J·基—泽博主编:前引书,第122页。)13世纪马里帝国宪法的制定就是最好的例证。据传说,马里帝国的创始人松迪亚塔在取得基里纳战役大捷后不久,召开了联盟军各首领参加的一次制宪会议,大会通过几项重要决定,如庄严宣告松迪亚塔为曼萨或马汉,意为皇帝,即王中之王;皇位继承依父系,采取兄终弟及制;皇帝必须从松迪亚塔家族世系中产生;同时还确定了各个氏族的权利和义务。此次制宪会议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将习惯法和禁律的制定归功于松迪亚塔,这些习俗和禁律至今约束着曼丁哥人各氏族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西非其他氏族的关系。(注:参见D·J·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4卷,中文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92年版,第109~110页。)此外,即使是在诉讼方式上,“口传非洲法”的特色也鲜明地体现出来。例如,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伊多马族使用一种传统的司法程序,即在一种基本上是戏剧性的场面中利用半合唱方式判案,把音乐与辩论结合为正式的司法体制。具体程序是,以合唱式应答为背景,争讼双方就像正式演员那样陈述各自的理由,审判过程持续两天以至一周。马里、几内亚等国的班巴拉人和东非的图西人也有与此类似的司法程序。(注:参见宁骚:《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3页。)
(二)精神上反映了非洲人特殊的价值观。受传统的多神宗教影响,古代非洲人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上帝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神灵,他是所有纠纷的最后权威。上帝之下是祖先神灵,他们总是受到敬畏。人是非物质本体和特质本体的复合物,肉体死后便分解,灵魂依然活着,因而死亡并没有结束生命,只不过是生命的延伸。人类社会就是由死者、生者和尚未出生者组成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家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意味着个人属于整个社会,个人权利的表现在于履行其义务,这使得社会成为一连串相互间的关系。(注:参见A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7卷,中文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91年版,第411~413页。)研究非洲宗教的非洲学者J·O·凯约德指出:“不细致地了解祖先崇拜,就无法了解人们的宗教信条,也就无法了解人们的生活,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 ——这些都是广义文化的内容。 ”(注: Kayode. J. O..Understanding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Ile —Ife: theUniversity of Ife Press,1984,p.70.)传统宗教是维护社会规范的强大力量,它要求人们依照神祗立下的准则,遵奉祖先的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在古代非洲人日常生活中具有权威地位的习惯法即源于这种特殊的价值观念。美国法人类学家E ·霍贝尔通过对加纳阿散蒂人的法律状况进行个案分析,充分证实了神灵、祖先及社会和谐在非洲人的习惯法观念中是何等的重要。E ·霍贝尔认为,在这里,所有法律问题都是“家庭的事务”,由不借助于物质力量的仲裁进行调整,通常是由受人尊敬的老者来执行。原告应当着族长和旁人向祖宗发誓,讲述祖宗的权利,族长们所进行的调整和劝导,都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祖先意志的体现,制裁也是祖先们的不悦和处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祖先们被认为是部落风俗和法律的监护人。阿散蒂人在约束自己的行为之前总是想着自己正在被祖先注视着,担心将来在天堂里相遇时会受到祖先的责难。这些思想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约束力,这些就是法律的基础,(注:参见E·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4页。)这说明,具有特殊观念的习惯法在古代非洲法律文化中处于权威地位,甚至深深地影响了非洲人的思维和诉讼方式。比如,解决争端重在和解,首先要能保证集团的一致和恢复集团成员间的协调与谅解。对个人而言,社会道德主张宽容和谦让,胜诉者常常放弃判决的执行。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与时间毫无关系的集团(部落、等级、村庄、家族等),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关心个人、夫妇、家庭这样一些不持久的因素。”(注: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添竹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也认为:“非洲人的‘概念的灵活性’的功能补充物是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它主要产生于亲属关系结构。在非洲人中,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取决于其在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身份。”(注: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在精神上,非洲习惯法最鲜明的特性就是尊奉神灵,崇拜祖先,尊重传统,注重集团本位,强调社会和谐。
(三)内涵上主要是民法方面的规范。 在非洲各传统社会里,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原则建立起来并得以维系的。这种社会组织同时也就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家庭、氏族、部落的建立、运行和维持都必须遵循一套复杂的原则与社会规范,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民事方面的社会事务,像如何划分亲属关系,如何处理家族、氏族内部成员相互关系以及继嗣规则、内部禁婚原则,等等。如在班布蒂人中,习惯法对集体生活的准则以及在赤道森林里生活如何保持生态平衡都作了规定;财产归集体所有,而在成员中分配食物的不公平被认为是严重破坏道德的行为;不许虐待孩子、殴打妻子或丈夫;不许滥杀动物和吃掉被认为是“生命幼芽”的蛋以及砍伐大树;不许盗窃和诽谤他人,等等。总之,这些社会规范在非洲各传统社会里强有力地制约着个人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奥德—布朗认为,非洲习惯法“与其说属于刑法性质的,还不如说是属于民法性质的,几乎所有最严重、最特别的犯罪都是采用类似于仲裁而不是惩罚的制度进行处理”(注:T. OlawaleElias.The Nature of
African
Customary
Law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56.p.115.)。这与英国著名学者梅因的观点相反。梅因认为,社会和法典愈古老,它的刑事立法就愈详细、愈完备。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开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他说:“这种现象常常可以看到,并且这样解释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由于法律初次用文字写成时,社会中经常发生强暴行为。”(注: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7页。 )而笔者认为,用梅因的这种“普适性”观点来看待非洲习惯法是不恰当的,因他并不了解古代非洲习惯法的特性,我们只有对此有一个清楚和全面的认识,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四)诉讼中通行神明裁判方式。 古代非洲习惯法带有较浓厚的原始部族痕迹,尤其与各部族中流行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图腾禁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也使司法诉讼充满神秘色彩。例如,中非一个奉青藤为图腾的部落,当发生有关土地、房舍以及杀伤、盗窃等较为重大的纠纷时,酋长就会召集双方当事者,摘来青藤叶子,让巫师念过咒语后请双方嚼吃。据说,心亏理屈者吃了就会死掉,临场怯食就等于认输。又如,在南非的巴罗朗部族里,如果发生纠纷,酋长就会拿出珍藏的图藤标志铁锤,让双方对着铁锤发誓,理亏的一方据说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注:宁骚:前引书,第138页。)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部落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是理性,而是神明。对部落而言,神明裁判是公正的,而理性裁判却是不公正的。在部落审判中,无须说明理由,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注: T.Olawale Elias, The
Natureof African Customary Law,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6,p.28 .)。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古代非洲人的习惯法观念,在概念内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与西方思想观念迥然不同,而与东方民族的法律观、价值观颇为相似。正如千叶正士所言:“如同日本的情形一样,非洲人的个人权利概念也是一个由法律公布的表面概念和当事人的社会身份这一隐藏观念构成的复合物。”(注:千叶正士:前引书,第26页。)但正是由于习惯法的权威性、独特性,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马达加斯加曾受习惯法统治达几个世纪之久”(注:勒内·达维德:前引书,第5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