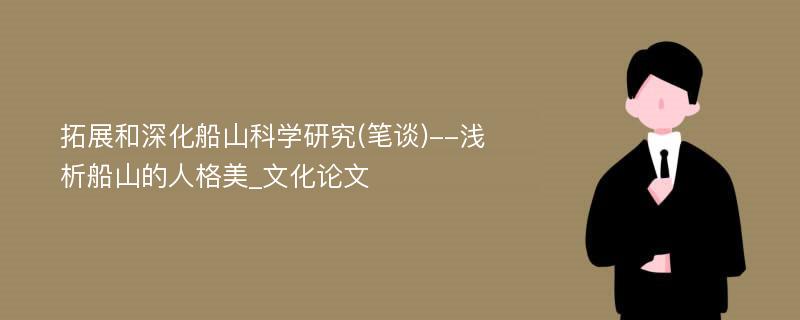
拓展与深化船山学研究(笔谈)——船山人格美浅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山人论文,船山学论文,格美浅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5)01-0001-11
一
船山一生,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的教养,学术道路的选择,都促使并激励着他始终执着子“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理想人格美的追求。
青年船山,倜傥不羁,十六岁学诗,“读古今诗十万首”;十九岁读史,“日成博议几千行”;二十四岁乡试,以《春秋》第一中式。诗与史,培育出一个忧时志士的倔强灵魂。
中年船山,出入险阻,投身时代激流,经受了各种复杂矛盾的严峻考验,终于在明清之际“海徙山移”的变局中,“寸心孤往”,“退伏幽栖”。三年多湘南流亡生活,所见民间疾苦,化为笔底波涛,从《易》《老》两大原典中汲取哲学智慧,披麻衣,拾破纸,在“厨无隔夕之粟”的艰苦条件下,写出了反映时代精神美的光辉著作。
晚年船山,潜隐著书,瓮牖孤灯,绝笔峥嵘。在学术自辟蹊径,精研易理,熔铸老、庄,出入相、禅,扬弃程、朱、陆、王而复归张载,“推故致新”,“破块启蒙”,别开新面;同时,搔首问天,以诗达志,续梦观生,“内极才情”,充分表露其“胸次”、“性灵”、“独至之微”,直至辛未深秋绝笔之作《船山记》中“赏心”、“遥感”的顽石之美,
船山自我鉴定一生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活动为“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这是理性的选择;而“芜绿湘西一草堂”的艺境诗心,却与“芷香沅水三闾国”的楚骚传统一脉相承。
二
船山哲学,首重“人极”,依人建极,主持天地。所谓“人极”,指人的类特性或文明人类的本质特征。故严于“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认为人的道德自觉和人格塑造有一个由禽到人,由夷到夏,即由野到文,乃至继善成性而超迈流俗的漫长过程。
由此,在天人关系上,反对“任天而无为”,而力主“竭天成能”,“与天争胜”,“以人道率天道”,成为天地的主人;在理欲关系上,反对“灭欲”、“禁欲”乃至“薄于欲”,而主张“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更强调“入天下声色而研其理”,“与万物交而尽性”,才算是“立人道之常”;在群己、公私关系上,冲破迷雾,否定“无我”,肯定“有我之非私”,且强调“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有了独立的主体或道德自我,长可能体现出“大公之理”的价值尺度。
因而,在人性论上,船山独树一帜,反对“复性”说,坚持“成性”论,且主张“习与性成”、“继善成性”、“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依靠主观努力与实践锻炼,人的道德、智慧、才情都在发展中日趋完美。“学成于聚,思得于永”,“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取精用物而性以成焉,人之几也”。船山的“成性”论,为其内在超越流俗,充分实现自我的人格美追求,提供了绵密的理论依据。
三
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又“思芳春兮迢遥”,乃船山心中最大情结。故甲申(1644)之后,仍以“续梦”名庵,且举兵衡山,奔驰岭表;庚子(1660)以后,“哀其所败,原其所剧”,居“败叶庐”,写《落花诗》:“旧梦已难续,无如新梦惊”,船山始终在寻觅着“新梦”。
船山特叮咛:“梦未圆时莫浪猜”,足见他确有欲圆而未圆之“梦”。企待后人理解。他曾“抛卷小窗寻蚁梦”,正当此时,写成《噩梦》一书,表明所寻之“梦”,并非虚无缥缈,乃是“苏人之死,解人之狂”的改革设计,并寄希望于未来。但“中原未死看今日,天地无情唤奈何”,有时“拔地雷声惊笋梦”,有时却“蝶魂入梦不惊霜”;有时“雨雨风风,消受残春一梦中”;有时又“青天如梦,倩取百啭啼莺唤”;还梦过“昨夜喧雷雨,一枕血潮奔”的奇景,更有过“眠不稳,梅花梦也无凭准”的迷茫。这纷至重叠的梦影,在船山诗中结成瑰丽的“情中景”。
船山诗境中最突出的还有一个“蟠藕修罗”的梦影。此典出于《观佛三昧海经》,谓阿修罗反抗帝释天,战败,暂时蟠身在污泥藕孔之中。船山早年自比修罗,“铁网罩空飞不得,修罗一丝蟠泥藕”,“扯断藕丝无处住,弥天元不网修罗”,把反抗者虽战败而不屈意志引为同调。晚年对镜,仍以修罗的坚贞自慰:“……别有一线霏微,轻丝飘忽,系蟠泥秋藕,一恁败荷凋叶尽,自有玉香灵透。眉下双岩,电光犹射,独运枯肠肘。无情日月,也须如此消受。”更有为而如长老所题“别峰庵”一联,妙契佛理,仍寄梦想于“藕丝香孔”里的修罗,说他终于会“摄尽万缘,神威自振,不教钓艇空归”。
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
四
船山之学,以史为归。“史”在船山,非记诵之学,而是可资能动取鉴的镜子。“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可能唤起和培育巨大的历史感。
船山早年“韶华读史过”,晚年“云中读史千秋泪”;衰病余年,奋力写出史论千余篇,全都是读史养志,“引归身心”的自觉实践。
船山善引庄子的“参万岁而一成纯”一语而为之别解:“言万岁,亦荒远矣,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乃数千年以内,见闻可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污隆治乱之数,质文风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这样不随风倒的独立人格,是以“笃实光辉,如泰山乔岳屹立群峰之表,当世之是非、毁誉、去就、恩怨漠於己无与,而后俯临乎流俗污世而物莫能撄”。这是基于历史教养而自觉形成的理想人格的崇高美。
至于这样的人格风貌所观照的祖国的山河大地、族类、历史、声教文物之美,及所预见的“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的光辉未来,则《黄书》七篇俱在,璀璨夺目。
五
关于人格美的自我塑造,船山首重立志和养志。“人苟有志,生死以之,性亦自定”。立志,就是确立坚定的、恒一的价值取向。强调要“仁礼存心”,超越流俗物质生活,超越个人得失祸福,卓立道德自我,纯化精神境界,实现真正的人的价值。“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可弗惧哉!”思想上界限分明,实践中长期磨炼,经得起各种考验。“衣、鼓琴而居之自得。夏台、里而处之不忧”。养志,就是要始终坚持贞一不渝的志向,并不断地“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怨艾以牖其聪明而神智日益,退抑以守其坚忍而魄骨日强”,就可以做到“堂堂巍巍,壁立万仞,心气自尔和平”,“孤月之明,炳于长夜”。
“在志者,其量亦远”。“量”,是具有一定历史自觉的承担胸怀。持其志,又充其量,就能够“定体于恒”,“出入于险阻而自靖”,面对“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不惶惑,不动摇,不迷乱,“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达到对执着理想的坚贞,在存在的缺陷中自我充实,在必然的境遇中自我超越。“此心一定,羲皇怀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万年不改其光辉”。对这一内在人格美的赞颂及其不朽价值的评判,船山曾以韵语托出,字字珠玑: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
潇洒安康,天君无系。
亭亭鼎鼎,风光月霁。
以之读书,得古人意。
以之立身,踞豪杰地。
以之事亲,所养惟义。
以之交友,所合惟义。
惟其超越,是以和易。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
深潭映碧,春山凝翠。
对此,我们也只能神交心悟,目击道存,如船山所云:“言不能及,眉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