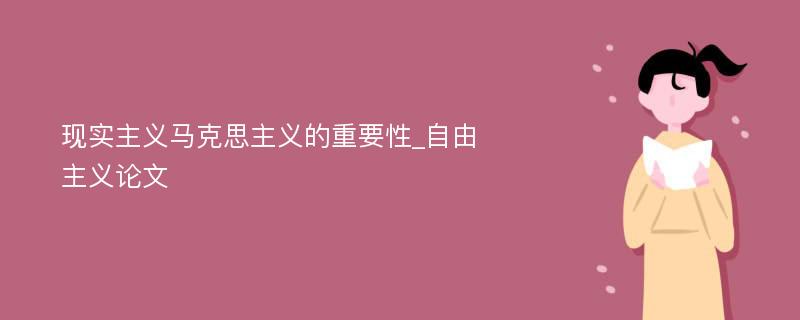
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重要性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希望这一近乎“狂妄”的讲演题目不致引起误解。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将尽可能客观地阐述我国政局的特点。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听一个刚从苏联来的人到西方谈谈时下的政治事件,而不是说史。
尽管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当紧迫,但是,在今天激荡的时代,如果没有理论,我们将束手无策,这是无庸置疑的。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theliberal intelligentsia)出现在人民代表会议的讲坛上、电视上和《莫斯科新闻》上。在他们看来,形势的发展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他们深信,无论形势怎样,都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驾驶自如,很自然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会无损丝毫,但社会将会如何呢?
从意识形态上看,Prestroika的头两年正是60年这一代人的结果。这一代人的代表不无期望地发现自己正处在最前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意识到手中有了实权。在苏联武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后,赫鲁哓夫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鼓舞与痛苦的过程,自由共产主义(likeral coimmunism)现在重又蓬勃起来。人们曾经一再相信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自由市场改革不过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再版,并且,在意识到自身历史责任的党的领袖们的指引下,将实现向民主稳健而平缓的过渡。进步的知识分子坚持这一过度应通过建议以及建设性的批评来达到。
遗憾的是,这种幻象注定长不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围绕“变革”这一总较量的后面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对立。当局推行市场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最现代的部分──技术官僚和混合企业(一些国际公司与传统官僚机构的联合)。当然,真正而积极的变化还是有的,例如,苏联人已能接触到仅在三四年前还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作品,这一事实不可小觑。这不仅仅对知识分子是相当重要的。此外,尽管有官僚操纵,今年年初的选举和随后议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召开都无疑刺激了政治生活,也出现反对的调子。但是,如果说到我们日常生活和每个人为生存而每天进行的斗争。perestroika对于人民群众则无足轻重。
60年代型的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守势。他们正被更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迫随者所替代。不管我们同意与否,后者的观念确实比自由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更富于逻辑。的确,如果你羡慕市场无约束的自由、财产多元化(pluralism of property),在实践中,则意味着在国有企业中造就私有成分和出售股份;如果你认为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而非劳动者阶级,如果需要商业化教育和医疗服务,总之,如果你象西方右翼分子那样行动和倡导,那么,讨论社会主义、回到“真正的列宁”(true Lenin)或本世纪20年代的经验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新自由主义者似乎在所有意识形态标志中,始终没有对传统与政治氛围负责,glasnost状况也仅是短短的一幕。60年代类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则不同,他们才真正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今天他们虽认为改革的支持者已言过其实,但意识形态的大权并非他们控制,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不出任何替代战略。这样,80年代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则就成为60年型自由主义者的正确继承者而显现于今日。
技术官僚的倾向
统治集团通过认同西方社会价值,正越来越走上一条技术官僚化的狭窄而陈旧之路。自由精英和官僚所憧憬的西方也并不是其三千年古老的文明,而是科技与消费。作为世间天国的一部分,这种憧憬产生了一种不顾我们的现实文化与经济水平、旨在抄袭西方的政策。今天,苏联的统治精英和目前西方国家的技术官僚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精英们实为一类。当然,他们正处于进退维谷之窘境,首先,Perestroika的意识形态构架就还需解释,戈尔巴乔夫等政治人物都欣然提出一些如“多一些民主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等口号,并指出自主管理和工人参与决策的益处。
现在,这都正成为过去。新意识形态优先权(new─ideological─priorities)正变成越来越明晰。最近,在官方报刊上已能够多次读到俄罗斯哲学家Berdyaev对他所不理解也不能认识的某些事情的批评,他被指责为不能认识“资本主义本质”,在他创造性的研究中,他不能完全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奥古纳克(Ogonek)及其他出版物则批评希布什维克在推翻俄国未代帝皇之后的错误行为。对托洛茨基及其主义(Trotsky and trotskyism)的批判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达到空前的规模。这决非多数主义(Pluralism)的显现或审查机构不灵的证据。审查者偶尔对真正危及现政体制的东西进行干预,记者们非常报怨89年底十分的严格审查。二十年前,伊萨克·德斯切尔(lsaac Deutscher)论及前共产党人(ex─communists)的良知,在抛弃斯大林主义时,前共产党人不仅为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且还以传统斯大林主义的偏激来辨护。这些前共产党人的良知完全变成某些人控制苏联官方媒体最具影响部门的一种集合体(collective identity)。
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茨普科(Aleksander Tsipko)的“斯大林主义的来源”一文于1989年在通俗杂志《科学与生活》上连 载。正如有人预料,作者在马克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者传统中找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源头。这对于西方读者是毫无新意的,茨普科基本是在重述海耶克、索尔琴尼辛、法国“新哲学家(new philosophers)以及其它作者早就进行过的争论(唯一不同在于茨普科的文采远逊于其先辈)。这篇文章使得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大为不满。奥托.拉奇斯(Otto Latsis)在一家很大的莫斯科杂志Znamya发表文章对垒,指出其文章中的多处纰漏──真正的错误和一处”误印”(诸如“热月”应为“雾月”)。这些让人信服。但拉奇斯的文章并没有、也不能引起同样的反响,这不是二者争论水平的高低问题,更重要的是茨普科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工作。这一难言之隐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茨普科只别具匠心地在布尔什维克的“老卫士”(old Guard)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方面谴责斯大林主义而不批评列宁。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众多的报刊、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传播,但是,它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社会学调查表明,大部分人象以往一样相信社会公正思想,并要求更大程度的平等。旨在引入市场政策的法案在那些似乎这种改革十分必要的地方也遇了阻力,七、八月矿工罢工已显示,工人的利益正慢慢地被意识到。可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却认为这是市场政策的巨大障碍,并引致其意识形态的骚动。他们在受到威胁与压力后,将意识形态的立场引向激进方向。茨普科的文章刊载不久,依古尔.克莱希姆金(lgorKlyamikn)和安德尼克.梅哥朗(Andranik Migranyan)的接踵而来的文章则以引入市场改革为由抛弃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主。他们认为,在实践中推进自由经济改革的主要意义在于创造出一个强硬而权威的集团而能够有效压抑人民的反对。
这对俄罗斯而言已不新鲜。西方化自由主义者向反民主方向的转变绝对是传统的和习惯的。在1905年革命后,一群左倾自由思想的著名思想家,如布尔卡柯夫(Bulgakov)、伯德叶夫(Berdyaev)、斯特鲁夫(Struve)等在《界标》(Landmarks)杂志上写到,与沙皇达成妥协和维护严厉而权威的政体以使受到教育的精英免遭群众的洗礼是必需的。
但历史经验的真理表明,这种保护是靠不住的。革命还是同样发生了,并且证明了比1905年当时任何人所预想的更血腥。俄国自由主义先驱者们──与《界标》同时代的君主立宪派曾与上述思想家们保持一定距离,可是革命爆发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竟在同一阵营。
西方主义的矛盾(The Contradicton of"Westernism")
历史是自身重复着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喜剧。自由公众对克莱姆金和梅哥朗的背信弃义表示了极大的愤概。但是,克莱姆金和梅哥朗还远为达到布尔卡柯夫和斯特鲁夫的水平,更不用说象伯德叶夫那样的杰出思想家了,而且,他们的批评相距当初团结了最优秀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1905年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则更远了。
同以往一样,西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可挽救的矛盾状态。在缺乏的西方式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的条件下,推动社会按西方方式变革的唯一力量即是实质上强制于社会演化的自然进程中专制而暴虐的政权,而这种政权与西方传统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政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官僚机构曾通过许诺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变革国家。事实上现在却转向资本主义的方式。这表明,旧的制度在历史与意识形态中已彻底破产,传统斯大林主义已彻底终结。只是这种政权转变为资本主义政权则不大可能。
我们正面临着后期政权(Post Thermidorian)的逻辑矛盾,斯大林的Thermidor,就象法国的thermidor一样,本质上是在革命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反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延续与完成。因此,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绝然划开的尝试就如同把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斯大林主义之先驱的尝试一样,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曾为了维护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公正而大加歪曲革命遗产的政府,这一次似乎也非常乐意抛弃这份遣产了,可它却不能这么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许诺即使与实践相矛盾。仍然是保持旧体制政治稳定的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并非西方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而是出现一种可怕的怪物──包含着东西方两种体制诸多最坏特征的消极集合体。我们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这怪物将证明,这样一种过程是多好的提示。它肯定长不了!
这种发展战略的沉默思考是完全传统的,少数人以群众的名义而合法地行使超越于群众的权力;财富、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的建立被视为进步的重要标准,如果说,当初布尔什维克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大工厂,那么,新自由主义则将社会与经济视为一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这种对称式的幻想与简单化的方式将今天的市场斯大林主义和20年代布尔什维克创立的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而这二者的核心是对激进主义和进步概念的歪曲:如果仅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话,这二者的逻辑推演则是危机深刻的证明,马雅可夫斯基在其诗中对专制主义和工业主义的颂扬激起了批评者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是马雅可夫斯基天才的堕落。但是,今天批评者们通过赞誉作为最完美的商业艺术和消费主义来荣耀他们的强权,这听起来是同样的荒谬。喜剧终究是喜人剧,在他们中间甚至还没产生新的马雅可夫斯基。
知识分子的危机已经出现。无论是党员和还活着的6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曾向往民主的美好和“大同”(common good)的理想,现在这些全被抛弃了──这意味:在实践中抛弃了知识分子本身及其作为伦理和政治价值的集体认同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俄罗斯的智慧被西方的所替代(只是没有西方的教育和能力)。俄罗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正在消失,而纯粹西方式的知识又没有,我们正处于覆没的危险之中,我们将一无所有。
左派替代者的形成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困境不是无可奈何的。自由主义者和政府官员对“左倾激进主义”(leftradicalism)适时崛起的不安不是没有根据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象他们30年前或100前的先行者们一样,在正在形成的体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新一代的反叛今天则用比文学更好的形式──摇滚乐来表达(尽管徭滚乐的文学质量正迅速改进)。很显然,我们已逐渐了解了新文学名称而非总是新政治口号。年轻的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并正迅速扩大力量,人们在经审查后的出版物中看到对自由主义者的神话的批评,而这已成为新Samizda的内容,一个左派替代力量正在形成。
我们正在准备的决定性战斗是6个月后将举行的市一级与共和国的选举。当然不排除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和共和国的一些成员将失去控制而落于“人民阵线”(Plpular Front)的手中。在俄罗斯,我们相信迫于人民阵线的压力,他们能赢得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多数;我们亦相信,人民阵线必定会有自己对日常生活问题、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的自治化和民主化的方案。
社会上需要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观念会使当局如此不安的原因。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比出版索尔琴尼辛的著作更难,当古拉格.阿奇贝拉古(Gulag Archipelago)正沉浸于畅销之中,而托洛茨基的著作却只能私下流传。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群众急迫地要求社会公正而非过往文化、经济和政治一简单替代物。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口号既非社会主义者也作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指出了人类对经济的简单依赖──这在马克思之前就已为人所知,而且还揭示了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之间的深邃关系。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改变生产过程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机械地在富人与穷人间进行简单的财产再分配。这一原则性观点常常被主张再分配社会主义(redistributive socialism)的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同之乌托邦鼓舞的各种激进分子所忘却。
我们必须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经济效益和群众要求更多的社会公正现实地结合起来。纠正“市场的极端”(extremes of the market)这一局部的要求在这里是无意义的。我们明白,唯一的道路是将包括市场关系整合到民主计划和自主管理(self──managemat)的整体结构中,并服务于社会利益。市场可以充当个人的保护人,但永远不可能权威地为群众利益服务,因此,它不能、也不会占据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地位而趋于民主与人道。每个人,不管他们才能、收入和运气,都有权过一种享有尊严的生活。能够把这个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的社会才必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将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人才必将是社会主义者。
今天,而不是以前的任何时候,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激进的价值体系。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掌握发展的辨证法,与过去的教条拉开距离,超越那种把进步仅视为物质价值积累的简单化观点。今天,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需要人辩证地思考,需要人关注人民利益并对人民寄予信心,需要人把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在继承了众多经典作家的丰富遗产,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新弗洛伊德主义、萨特的唯物者存在主义(materialist existentialism)、葛兰西《狱中笔记》中精炼分析、托洛茨基曾鼓舞革命的矛盾之后,马克思主义将被视为判断正确或虚假的综合体系。为如下目的我们需要检验:吸取并掌握其中的批判方法、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提供一种新的理性分析。而这也将是今天对所面临的问题的回答。
通向世界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通向欧洲文明和西方传统的道路,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经验的真正财富,而不是超级市场的货架。我们必须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抛弃夜郎自大式的地域主义,必须对世界开放自己,而不仅仅是西方。最后,我们必须完成俄国文化从欧洲主义和西方主义向世界主义的历史而艰难的转折。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将成为我们的动力。
(中国发展研究组译)
本文为1989年9月18日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稿。经作者同意,摘译刊载,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