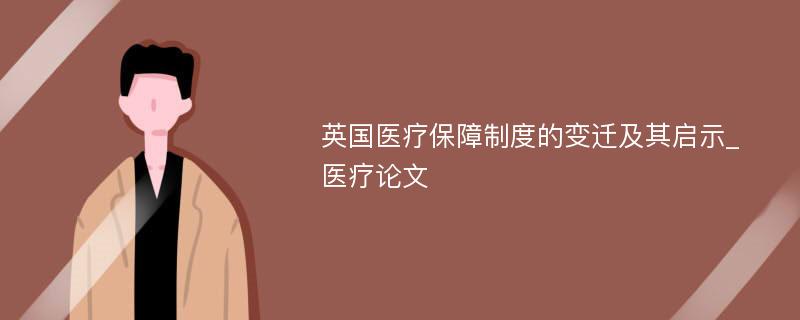
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保障制度论文,启示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宣布为福利国家。就医疗保障制度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后的产物,它为公民抵御疾病风险、增进身心健康、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一、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缘起
与养老、救助、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相比较,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相对比较滞后,最早建立的社会保障法案并没有包括为了应对黑死病以及民众健康所必需的医疗保障,从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劳工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该法律主要规定,所有“有工作能力的劳工”不得离开本教区,而必须接受任何雇主的雇佣;任何人不得向“有工作能力的乞丐”提供救济[1](p.87)。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不是为了防止民众因病致贫或者通过这个法律来建立医疗保障,而是为了防止黑死病流行以后劳动力外流的加剧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工业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都铎时代,随着“圈地运动”盛行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各阶层的日益分化,英国既产生了大批流浪者和乞丐,也诞生了产业工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健康状况极其糟糕。可是,此时的英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包括医疗在内的保障措施,而是制定更加严酷的法律禁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动。1531年,都铎政府责成市长与法官调查和登记教区中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与穷人,并向他们发放仅限于本教区有效的行乞执照,而对于没有行乞执照的流浪者或乞丐仍然处以严厉惩罚。1562年的《技工法》更是规定“12—60岁的失业乞丐被罚做奴隶”[2](p.15)。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时英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制定的相关法案都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促进工业发展,确保社会稳定。
真正将社会保障作为政府的责任首先出现在1572年。是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把“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同时,为了促进就业又于1576年规定,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前往“矫正所”工作,随后又设立“济贫院”收容无工作能力的穷人以及生活不能自立的人。1601年,英国政府汇总并正式公布了《济贫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政府在民众贫困以及失业方面的责任,同时规定了教区救助、征收济贫税等原则,从而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可是,总体上看,1601年以前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仅仅包括失业、老年人以及幼儿的赡养和救济等,并没有包括医疗保障。此后,无论是1696年英国政府颁布的《习艺所法》,还是1782年的《济贫法修正案》、179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斯品汉姆兰法》以及1834年的《新济贫法》等等,也只是提高了济贫税,扩大了济贫范围,使低收入家庭也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政府并没有注意到医疗保障。可以这么说,19世纪以前的英国尽管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以穷人养活其穷人”、“穷人懒惰”以及“惩罚穷人”的制度理念一直贯穿于各种社会保障法案之中。
尽管当时的政府没有重视医疗保障,但这并不等于说医疗保障就不是问题,就没有必要关注和建立。事实上,早在17—18世纪,英国就已出现了私人医疗保险和工人医疗互助制度,他们成立了“友谊社”、“工人俱乐部”以及“共济会”等民间组织,来应对疾病风险的挑战。因为在当时的英国,不仅产业工人及其家属随时都会因工伤、疾病等因素的产生而发生生存危机,其他社会群体也必须面对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生存风险因素,疾病风险又成为最为关键的生存风险因素之一。这样,这些民间组织的建立在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构成了英国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前奏。
二、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
不管怎样,英国依然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包括乡村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它代表了国家福利型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进程及其特征。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友谊社”、“工人俱乐部”以及“共济会”等民间组织已经逐渐发展成地区自愿性包括健康在内的民间自愿健康保险机构。它是由一些熟练工人组成团体建立起来的一种非盈利性社团组织,参加者缴纳一笔保险金,社团自己管理,成员生病时支付一定数量的救济金,有的社团还与医生签订合同。自愿健康保险实行到1908年,帮助产业工人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这样,医疗保障逐渐为英国政府所重视。于是,政府派财政大臣到德国学习该国医疗保险经验,并于1911年颁布法律,首次正式提出了“全民义务健康保险法案”[3](pp.18—20)。规定因疾病、生育不能工作者,给予现金补贴和医疗照顾。这样,政府民间自愿健康保险渐渐为社会医疗保障所取代,政府开始关注民众的健康保障问题。在1911年法律中,政府承诺国家在国民健康保障中的责任,规定医疗保险金实行三三制、按周计算原则:“国家出资2便士、雇主出资3便士、职工个人交纳4便士(其中女职员交纳3便士)”[1](p.93),16—70岁的体力劳动者以及年收入低于160英镑的患病男职员可以获得每周10先令的补助,患病女职员可获得7.5先令、患病残疾认可获得5先令的补助,而女工产前也可以获得每周30先令的补助。这是英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开始,国家负担原则也构成了后来其他国家所承认。
“二战”结束前夕,为鼓舞士气,战胜德国法西斯,英国政府承诺要变“warfare state”为“welfare state”。于1942年通过了以“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为支柱的《贝弗里奇报告》。在此基础上,于1944年正式提出“国民保健服务”方案,4年以后颁布了《国家健康服务法》。法律规定,英国实行惠及乡村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所有民办医院和市政医院都收归国有,健康保险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牙科和眼科。中央政府实行卫生规划,使医生在全国各地区均匀分布,地方政府则负责规划医院和分配预算的经费,保险经费不是来源于个人的保险费而是来自于税收,《国家健康服务法》和其他4个法律一起构成了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正因如此,英国首相艾德礼于1950年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1964年,英国又通过了《国家健康服务法》补充条款:任何一个国民生病,都可以找自己喜爱的医生治疗,所有的医生都实行免费医治,即便技术最为精湛、最有名的医生也不例外。“国民保健费用88%由政府支付,其余部分由医院承担。患者只需交付挂号费等等”[3](p.17)。
英国目前医疗保障制度主要依据197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以及1986年实施的《国民保健制度》。法律规定,受保人享受疾病补助的标准为每周可领取35.7英镑收入关联分级补助金,受供养人则可领取22.1英镑,至多支付28周[1](p.98)。英国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优点是医疗费用由政府预算控制,有利于战争结束后城乡全民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有力地保障了国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在医疗消费方面体现了相对公平原则。然而,经过几十年运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型医疗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医院运行效率低下。由于英国医疗在运行机制、管理模式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实行计划管理模式,医院属于国家,88%的经费由政府提供,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这样就无法调动医院尤其是医生的积极性,医院服务效率低下、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等现象普遍存在。据调查,英国门诊医生平均每天诊治患者30人左右,而日本为55人。也正是由于医生的报酬与付出没有直接联系,外科医生不愿多做手术,而全科医生则常常以预约已满为由而拒绝给予患者治疗,或者动辄就将患者转到上一级医院。由于这些因素,导致医患双方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据统计,“1971年英国登记等待住院的患者有60万,1979年达80多万,1989年则增至85万”[3](p.17)。
第二,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医疗费用上涨。由于英国医院服务效率低下,不少患者只好自费到私人医院去看病,这样又反过来促进私人医院的发展和壮大,使得私人医疗保险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种情况又带来了新的后果。一方面,私人医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必然导致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的变相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寻租”方式使国家医疗卫生经费不断地流入私人医院为个人所有。这样,就使得民众对政府的国民保健服务项目日益产生不满情绪。
第三,国民保健费用支出不断增大,给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据《不列颠手册》介绍,“1949—1950年、1959—1960年、1969—1970年、1979—1980年、1984—1985年以及1994—1995年,英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分别为6576、9829、17393、28353、36298以及61500百万英镑”[4](p.232)。其中,在1994—1995年615亿社会保障费用中,国民保健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362.92亿英镑,占据整个英国社会保障经费总数的59%,仅1978年的疾病保险津贴一项就达到6.88亿英镑。按此推算,医疗保障费用支出将占整个英国GDP的15.8%左右。可是,这种庞大的国民保健费用支出并没有收到预期效应,反而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失业人口的持续增多给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英国财政常年赤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这种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迫切需要改革国民保健制度。
三、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三届政府均着手进行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医疗保障而言主要有三点:一是确立国家有限责任原则,医疗费用实行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二是确保医疗服务公平原则,通过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障制度,防止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三是充分挖掘医疗资源,通过发挥私人医院在国民医疗保障中的作用,鼓励私人医院和国立医疗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同时,鼓励私人保险机构等开展国民医疗保障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提高国民医疗卫生水平。为此,1980—1981年度,英国政府将病人的短期津贴减少了5%,1982年1月,更是取消了与收入相联系的疾病短期津贴,同时,将原来向病人提供8周疾病津贴的责任转移给患者的雇主,雇主因此增加的支出可以通过减少其应交纳的社会保险费来补偿等等。在此基础上,1982年英国中央政策评估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削减政府公共支出的建议,其中也包括用私人健康保险制度代替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等[5](P.153)。1983年,政府认为,“国民健康服务的私有化减轻了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压力,私有化为国民健康服务制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选择,它表明在国民健康服务方面存在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6](pp.106—107)。
1983年,受撒切尔政府委托,英国健康与社会保障大臣福勒开始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调查,并于1985年提交了《社会保障改革计划》绿皮书。“绿皮书”指出,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明确国家与个人的作用和责任,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应该是个人与国家共同的责任与义务。“绿皮书”指出,自《贝弗里奇报告》以来,英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发展的主题与矛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这就要求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所有社会保障项目能够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然而,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原则仍是《贝弗里奇报告》所倡导的国家义务原则,这已不符合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必须加以变革。
“绿皮书”为整个英国社会保障改革规划了蓝图,也为英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和方向。1989年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医疗制度改革白皮书》,这也是英国免费医疗制度实施四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减少政府财政压力,提高国有医疗机构工作效率,确保医疗保障资源公平享用。它采取普遍性和选择性相结合原则,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强调公民有权自主选择医院,同时,也扩大地方保健当局权限等等。
1990年底,梅杰首相上台后,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人口以及民众对医疗服务制度不满情绪的增长,梅杰延续了撒切尔政府的医疗保障改革理念以及改革措施,继续实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力图既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又能够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此,英国颁布新的国民健康服务与社会关怀法。法律规定,医院和各类社会关怀机构应该从地方健康当局的直接控制下摆脱出来,建立起自主经营的国民健康服务公司,地方健康当局不再对其进行管理,只是确定当地健康服务需求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同时提倡企业以及其他“第三部门”自办医疗等保险,凡是有条件的企业,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可以自己举办医疗保险项目,鼓励效益好的企业为雇员设立更优越的医疗保险。法律还规定,从1993年4月起,“医疗保障制度不再对私人或志愿性寄宿医院的新增人员提供帮助,地方健康当局有义务确定此类需求人员的要求是否属实,并采取适当措施为其提供有效服务”[7]。
1993年以后,梅杰政府又“对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进行了重组”[8],首先将地区卫生局和家庭医疗服务机构合并,简化管理责任、消减管理费,仅伦敦就由12个减少到9个,每所医院根据就诊人数向政府提交经费预算。其次,精简医疗管理层次和管理人员,全国14个大区合并为12个,177个地区减少到77个,社区和通科医生管委会直接由地区负责。再次,医院和地区卫生部门签订合同,超支则减少人员乃至关门。同时,保持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的一致性,加强中央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总之,1991年以来的改革既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4年提高了1%),降低了治疗成本,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患者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是,医疗管理费用始终没有能够降下来。
1997年,工党领袖布莱尔出任首相后,提出了“新英国、新经济”口号。并在前政府福利政策基础上继续深化这场“福利革命”。新政府试图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前提下不降低国民的健康福利,发挥社区等“第三部门”在医疗保障中的积极性,努力在社会保障权利与义务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变原来的“消极福利”为现在的“积极福利”,强调“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针对80年代以来两届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里的改革过分强调压缩医疗保障费用、削减民众医疗保障待遇而忽视中下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情况,是年12月,布莱尔政府发布了新的国民健康服务白皮书,那就是,“增加医疗经费来源;明确病人权利和完善评价指标;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改革内部市场、代理和计划机制;降低管理成本;建立卫生服务地区。”[9]显然,布莱尔政府试图实行控制医疗保障费用和提高服务效果两大目标并举措施。即“在提高筹资来源、规模的基础上比以前更加突出卫生服务提供的公正性、可及性和效率”[10]。
但布莱尔政府的这场改革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关资料显示,到2002年3月底,英国有100多万病人在等候做手术,其中20多万人已经等了半年多。在英国,每1000个居民平均拥有4张病床,而在法国和德国则为10张。针对这种情况,布莱尔政府认为,既要适当提高医疗保障经费以保证必要的医疗供给水平,也要进行费用控制。为此,2000年1月,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财政预算报告中宣布,今后4年中,英国的全国医疗费用将由目前的不足500亿英镑增加到近700亿英镑,医疗卫生费用将增至国民生产总值的7.6%,以解决医疗供求矛盾问题。政府还规定,有些治疗项目所产生的费用必须由患者自己支付,如患者应当自己支付看牙或购买某些药物的费用。另外,患者生病时先找普通医生登记看病,然后才能被决定是否住院治疗或者接受专科医生治疗,以防止医疗资源的浪费。总之,英国医疗保障改革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改革效果正为人们拭目以待。
四、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反思英国医疗保障制度近100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有益启迪,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践:
第一,由于医疗保障主要目的就是解决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疾病风险问题,努力使民众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医疗保障项目及保障水平必须始终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医疗保障水平过低尽管可以减轻政府财政支出,但是无法应对不断增大的疾病风险,而医疗保障项目过多、保障水平过高其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因此,英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始终围绕着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前提下如何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增进民众身体健康,而并不是纯粹为了实现社会的理想性目标。因此,英国政府包括鼓励“第三部门”参与医疗改革、实行国家有限责任等等在内的所有改革措施,其核心就是要将国家投入的资金切实用于民众的医疗保障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这就告诉我们医疗保障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实现医疗保障资金(投入)与医疗保障服务(产出)的有机结合问题,真正降低民众的疾病风险。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医疗保障费用支出一直居高不下,一度占社会保障费用的59%,占整个GDP的15.8%,90年代仅英国每年的医疗保障行政费用支出就达到16亿英镑之多[11](p.73),布莱尔政府在改革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却在增加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的医疗保障水平以此来增强政府的信任度。可是,庞大的医疗保障费用支出并没有带来令民众满意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由当初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变成了现在的制约因素,民众对医疗保障不满情绪没有减轻。从英国医疗保障改革实践来看,政府强调国家有限责任原则,认为增加资金投入并不是唯一办法,只有改革医疗保障运行机制,努力调动医院、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医疗效率,同时发挥“第三部门”参与医疗服务,减少医疗保障资金非医疗性支出,逐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确保医疗资源的公平运用,以增强民众的满意度。
第三,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制定必要的医疗保障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尽量精简机构,把有限的医疗保障资金真正用到救死扶伤之中去。从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外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践来看,首先制定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做到依法办事。其次,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努力保证医疗保障制度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公平性。再次,各个国家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电子技术支持系统,实现现代化的管理,使各地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查询服务等,能够实行全国计算机联网管理,从而减少医疗保障实施过程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
第四,从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直到现在,无论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如何进行改革,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方向和制度理念始终未变。也就是说,尽管英国医疗保障财政支出不断增多,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府始终遵循医疗保障资源享用的人人平等原则,并没有采取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是继续实行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总之,强调政府有限责任理念、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这对于处于风险社会、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相对比较紧张的中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