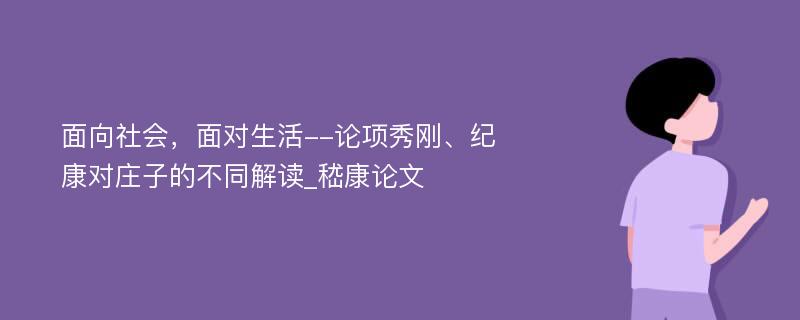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生命论文,社会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2-0033-07
在竹林七贤中,向秀和嵇康关系最为密切,但思想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他们的思想分歧不但表现在关于养生问题的论辩中,而且表现在对《庄子》的不同解读中。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需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1](P111)向秀和嵇康都极喜爱《庄子》,但竟有了“注”与“讵复需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庄子》有着十分不同的解读。
向秀是面对着“人间世”来读《庄子》的,他用头脑、用理性来分析、借用《庄子》的理论学说,紧密结合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对困扰人们的重大问题予以解析,试图协调尖锐存在的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为长久处于乱世的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向秀注《庄子》的目的是想借助于《庄子》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庄子》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借助,只是因为它更有利于阐发自己的思想而已,所以他必须注。
嵇康则是面对着生命来读《庄子》的。他用心、用悟去把握《庄子》的思想精髓,以庄周为师,抨击社会,超越世俗,努力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试图于混乱、罪恶的现实社会之上塑造出理想人格和自由的人生意境,在俗世红尘中建构一个精神家园,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在嵇康看来,《庄子》不是理性能够解说的,必须用生命去贴近、体悟,否则注亦不懂,所以是无须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注的。
向秀:面对社会的思考
向秀、嵇康等竹林士人生活在一个动荡、残酷的年代。由远而言,自东汉初平元年(189年)董卓乱京开始,东汉王朝已是名存实亡,军阀混战,狼烟四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由近而言,自曹魏嘉平元年(248年)正月的高平陵之变以降,司马氏父子便将屠刀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杀曹爽、曹曦,杀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杀夏侯玄、李丰,杀大臣,杀皇帝,“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2](P20)。人世间成了一个硕大的屠宰场,朝廷为之一空,天下“名士减半”[3](P759),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达到空前激化的程度。“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这是阮籍《咏怀诗》里的哀歌痛哭。社会的险恶,生命的脆弱,社会对生命的蹂躏摧残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在这带血的歌哭之中凸现出来,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
社会是一个残暴、虚伪、罪恶的存在,这在竹林士人那里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而如何去面对这一存在,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嵇康、阮籍、刘伶等人是冷眼相视,揭露抨击,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与之疏远,于俗世红尘中精心建构一个超越于世俗社会之上的、具有浓厚理想色彩的精神家园,进入其中逍遥遨游。向秀、山涛、王戎等人则不然,他们从人的现实性出发,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4](P1876)是人的自然本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进而论说道:“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者所欲得以财集人,此皆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不得相外也。”[4](P1876)因此,他们对于社会有一种深刻的依赖之感,要依附于社会,获取功名富贵,满足世俗生活的需求。所以,尽管他们也认为社会是一邪恶丛生、黑暗罪恶的存在,但仍然愿意密切同社会的关系,求得社会的接纳。于是,化解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而使之和谐一致,成了他们当时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山涛、王戎等人自觉而不声不响地投身于社会猎取名利、享乐之时,向秀则开始其哲学层面的思考,他要为这种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寻找一个理论上的依据,于是便有了《庄子注》的出现。也就是说,向秀并不是要去理解、阐明《庄子》的学说思想,而是面对社会现实,为努力解决时代赋予的沉重课题去注释《庄子》的。
在理论上,向秀是正始玄学的继承者,其《庄子注》依然坚持着正始玄学的“以无为本”的思想。但是,向秀在理论上又与正始玄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在“以无为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和发展。
众所周知,正始玄学的“以无为本”是有与无的统一。无是本质,是有存在的依据;有是现象,是无的表现形式。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向秀则不然,他说:“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5](P4)向秀承认在万物的背后有一个“生化之本”存在,这个“生化之本”则如道家思想中的“道”,正始玄学中的“无”,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但这个“生化之本”又与“道”、“无”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本质是“不生不化”,不能进入万物之中。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是由“自生”、“自化”,而不受“生化之本”的控制、操纵。也就是说,向秀否定在万物之中有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无”存在。这样一来,“有”与“无”便截然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存在。
向秀之所以要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生”、“自化”,将“有”从“无”的控制、支配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是有其深意的。他要将思与行、精神与肉体、超越与世俗分离开来,各守一域,避免其矛盾冲突。
行、肉体的生存和欲求,属于世俗生活的领域,是直接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一面。在这一面里,就应该遵从、顺应社会的现实存在,以一种“无心”的态度去行为。
社会的存在是罪恶但却强大,它倚仗着国家机器而随心所欲。所以,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向秀认为,个体应该作出妥协和退让,“达其心之所以怒而顺之也”[5](P58),即平心静气地承认、顺从统治者的意志行事,而与之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不思想,不抗争,“自然无心”,“与群俯仰”,随波逐流,“应世变而时动”,如此,则可以“得全于天”,尽情地拥抱功名富贵,满足世俗的欲求。所谓“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5](P72),说的就是这一意思。
在向秀的理论里,所谓“自然无心”、“无心以随变”,主要指的是要泯灭是非之心。因为,社会现实毕竟是一虚伪、残暴的存在,若是非之心存,则必然会与之疏远、对抗,结果只能是折磨和痛苦。所以,在他看来,面对社会时,其心要“块然若土”,作到“遗耻辱”、“忘贵贱”,是之与非,“混然一之”。
然而,人又毕竟有思想,若泯灭是非,顺其本能与时俯仰,则又与禽兽何异?这是向秀需要予以解答的。因此,在向秀的理论中,也就有了一个与“有”相对应的“无”,即人除了肉体、世俗的一面,还具有精神、超越的一方,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构成人的全部。向秀在谈到人与禽兽的区别时说道:“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唯无心者独远也。”[5](P49)具有“自然”、“无心”的一面且能够予以固守,则是人“相先”、“独远”、超出于其他“形色之物”的地方,也是人与其他“形色之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向秀的眼中,“无”是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本,尽管它不走进“有”的领域,但不可或缺。唯有固守着这个一成不变的“无”,才可能在应对千变万化的“有”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夫水流之与止,鲵旋之与龙跃,常渊然自若,未始失其静默也。”“虽进退同群,而常深根宁极也。”[5](P75)“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5](P73)所谓“静默”、“深根宁极”、“太冲之极”等,都是“无”的别一种表达,是“渊然自若”、“进退同群”、“玄同万方”的前提和依据。可以这样说,在向秀的《庄子注》里,作为“生化之本”的“无”的一面才是人的真实存在,而因时变化、升降,则是一种“无心”的表现,非真我之所为。在以下二则《庄子注》里,向秀将此说得十分明白:“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因,则为之非我。我虽不为,而与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应世变而时动。”[5](P76)“萌然不动,亦不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5](P72)
当然,所谓的“为之非我”,“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是经不起深究的。但是,正是这一自欺欺人的哲学,为士人在那一特殊的时代寻找到了一个心灵和性命的安顿点,同时也寻找到了一条与社会相沟通的渠道,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1](P111)
将“无”和“有”独立为两个不相往来的领域而又相辅相成,是向秀在《庄子注》中面对社会现实而建构的理论学说,同时也是他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具有二元论的倾向,但还不很成熟。如向秀在其《庄子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无雄耳。今吾与汝虽深浅不同,然俱在实位,则无文相发矣;故未尽我道之实也。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5](P71)就向秀的本意,大约是想说实与文、道与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样才和他在《庄子注》中阐述的整个思想相一致。但就这段文字而言,则很容易理解成实与道是本质,文与事为现象,这就同正始玄学的思想没有什么区别,而与向秀自己的“生自生”、“化自化”,无不进入有的领域的理论不相符了。又如在“贵无论”的思想里,向秀增加了“自生”、“自化”的新内容,但对于“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是如何成为“自生”、“自化”的天地万物之依据的,向秀则没有予以深究,因此留下了一个矛盾,留下了一个待东晋张湛去解答的难题。这理论上的不成熟,除了理论的发展本身有一个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外,更重要的是向秀的重点是要努力解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对抗,为久处乱世的士人寻找一个心灵和生命的安顿处,而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完备和完善。应该说,向秀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嵇康:贴近生命的诠释
嵇康、向秀等竹林士人亦生活在一个体意识觉醒、增强的时代。早在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一种以个体为基点的新的人生观念便通过诗的语言展现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随后的邺下城内、洛阳街头、洛水岸畔乃至皇家宫殿、士人庭院,随处都能见到这种新观念的丰富多彩的显现和蓬蓬勃勃的发展。人切切实实地是从群体的束缚和对社会的依赖中走了出来,焕发着亮丽的风采。
然而,真正对于人的真实存在予以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的,当是竹林时代的那一批士人,其中又以嵇康为杰出代表。
当向秀割舍不开对社会的依赖而殚精竭虑地弥合个体与社会的分裂,试图化解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时,嵇康则将审视的目光深情地投向人的自身,面对着珍贵、鲜活的生命,先后撰写了《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太师箴》、《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卜疑》、《琴赋》、《声无哀乐论》等等一批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理论著作,就人性、生命、人的真实存在、人生的超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予以论说,将人自身的思考和探索引向深刻。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4](P1321)这是嵇康面向社会的公开宣言。的确,嵇康的思想和人生都与老、庄有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这“吾之师”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准确把握老、庄的理论和将老、庄思想作为自己人生的指南去身体力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融合。
众所周知,在先秦百家学说中,大多以社会为思考的基点,由此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对于人的真实存在、人的真实本性、人的精神超越等关于人自身的问题则思考甚少。唯有道家,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杨朱、列子等,都对此予以深切的关注和思考,由此而形成了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特点,即对于人的注重。其中尤以庄子的思想最为深刻。他抨击社会,反对异化,追问、探讨人的真实,塑造理想人格,建构精神家园,这些都对嵇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嵇康则是庄子数百年之后的知音和思想的继承人。可以这样说,在古代思想家中,嵇康是真懂庄子的一位。他由生命的需要去读《庄子》,用心去贴近庄子而与其沟通、对话,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诠释、实践庄子的学说和思想。
“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4](P1336)将自然之性视作人之本性,是嵇康对于人性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很明显,这一思想来源于《庄子》。可贵的是,嵇康并没有在此打住,而是朝着如何拥有、固守着人的本性而不致丧失的方向努力发展,身体力行。为此,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4](P1322),对束缚、削割、打压人性的社会存在予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所谓“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并非要与汤武周孔几位历史人物过不去,而是要抨击、否定由这批所谓的圣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嵇康认为,正是由于它们的出现和发展,破坏了人类社会那种“不虑不营”[4](P1341)的自然和谐,并以此来迫害、蹂躏人的生存,扭曲和践踏人性。在《太师箴》里,嵇康揭露说:“下逮德衰,大道沈沦,智惠日用,渐施其亲。惧物乖离,擘□□仁,利巧愈竞,繁体屡陈。刑教争施,大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益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4](P1341)这是嵇康对社会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嵇康疏远社会,拒绝与其合作。当他得知好友山涛要举荐他入朝为官时,便写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自己同社会的对抗,用生命捍卫了理论的纯洁和神圣。
不过,在嵇康看来,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并不全然是由君权制度和礼法规范所造成,其中也有人自身的原因,这就是人们对于功名富贵等外在诱惑及声色香味等内在情欲,往往会着意地追逐和无休止地放纵。嵇康在《释私论》中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4](P1334)所谓“名教”,当然主要是指儒家的纲常礼法、行为规范。但在嵇康看来,“越名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中还应包括一切破坏人们顺从自然的外在诱惑,如名利、情欲等等,只有超越、摆脱它们,人的自然之本性才有可能显现,人生才能拥有真实的存在。“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这里的“从欲”是一种自然呈现的状态,不是刻意、放纵。“抑引”削割人性,刻意同样会导致人性之失,二者都是必须摈弃的。所以,嵇康主张“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乎所欲”,以一种静虚的境界去面对人生。《晋书·嵇康传》曰: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2](P1369)。《世说新语·德行》注引《康别传》亦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1](P10)可见,理论与实践在嵇康的实际人生中是完整和谐的统一。
生命是宝贵的,即便是“齐生死”、“一夭寿”的庄子,也割舍不了对生的执着。正是在他的手中,养生、养神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而继庄子之后在这一问题上作出重大理论与实践之贡献的,则是嵇康。
排除社会、群体而对生命作纯个体的思考是嵇康一生的执着,其《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是他这一思考的理论总结。在上述两篇文章里,嵇康以《庄子》的思想为指导,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认识,对生命、生命的真实存在、生命的超越之境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养生论》曰:“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着,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恕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4](P1324-1325)在这里,嵇康对这样几个问题作出了探讨:一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嵇康明确指出,神是形的主导,而形是神的依靠,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而划清了他的养生理论与宗教的界线。二是养生的关键是“修性”、“安心”,即自觉地拒绝外在名利和内在嗜欲的诱惑,保持一种淡泊宁静、少私寡欲的心境。这既是养生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生命得以延伸的重要依赖,亦是对生命自身的超越。三是作为辅助,指出了食药、吐纳等外在努力的重要。这一方面可以延年益寿,增加生命的长度,另一方面可以“使神形相亲,表里俱济”,即让形与神的关系更加和谐、紧密。据此可知,嵇康的养生理论并不只是在探讨生命如何长久存在,而是以此为基点,系统地阐述他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定位;精心地构筑起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进入其中诗意地栖居,作逍遥之游。在随后的《答难养生论》中,嵇康对养生与拒绝名利、嗜欲的诱惑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使对人生的思考获得了再一次的深入。
嵇康是热爱生命、深情于生命的。他“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3](P605),尽力排除外在诱惑,享受有限的人生。他养气于陋巷,采药于山泽,试图通过“呼吸吐纳,服食养身”的途径来增加生命的长度。然而,社会却不能容忍这位追求独立、自由之人的存在,罪恶的魔爪终于向他伸出。“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2](P1373)这是嵇康的狱中之诗,字里行间,弥漫、荡漾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
在深情于生命的同时,嵇康亦追求着人生的真实、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且视之比生命更为宝贵。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陈述拒绝入朝为官的原因时,列举了所谓的“七不堪”,归纳起来,无非是官场生活不得自由,失去真我,失去人格,人在其中遭到扭曲和异化。在《绝交书》的如下话里,嵇康将这一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晰明了:“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4](P1321)所以,嵇康甘心于远离功名富贵的清贫淡然的生活,因为那里面有人格的独立,有人生的自由和真实。“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4](P1322)这是嵇康理想的生存,亦是参透独立、自由、真实之后的一种人生境界。
嵇康生活在一个虚伪奸诈、黑暗残暴的社会里,但他敢于直面而不逃避,在一个罪恶的俗世红尘中执着地追寻、建造着精神的家园。他在《答难养生论》中说:“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4](P1325)这其中的“意”,即是一种意境,一种超越,一种世俗之上的精神追求,一种挣脱各种桎梏、束缚而归入自然后的人生大自由,是《庄子》中至人、真人、神人的显现。嵇康的一生都在努力地追求、实践、固守着这个“意”,固守着人格的独立和人生的自由。
吕安在读了向秀的《庄子注》后言:“庄周不死矣!”而我要说,真正使庄周不死的是嵇康,他用生命演绎庄子的思想,将鲜血注入庄周理想中的真人、神人的体内,使其化作一个能够亲近,可以触摸的真实。《晋书·嵇康传》曰:“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2](P1374)残阳如血,琴音若梦,而面对着死亡“手挥五弦”的嵇康却是一个真实,一个让《庄子》中的至人、真人、神人鲜活起来的真实,一个流传千古而不朽的真实。
一部《庄子》,让向秀和嵇康有着不同的阅读,不同的理解,这是历史之手的安排,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嵇康面对生命读《庄子》是个体觉醒后的必然,向秀面对“人间世”读《庄子》是社会现实之必须,二者同样承担着历史的使命。嵇康和向秀对《庄子》的不同认识、不同理解,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收稿日期:200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