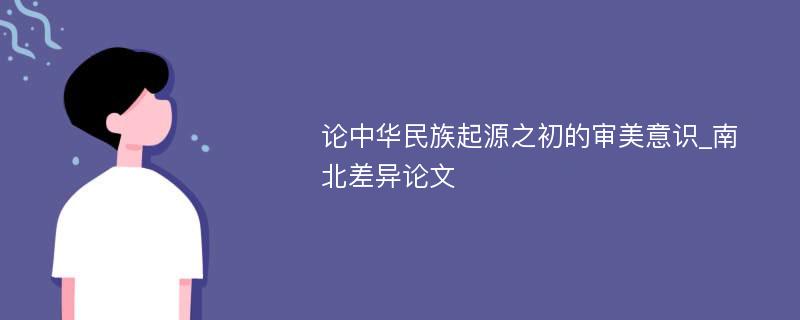
论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1-0005-06
审美活动是人类最为复杂也最具个性特点的精神活动。个体的审美心理总是千差万别的:相同的对象,在这个人看来是美的,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并不觉得美;即使是同一个人,此时感觉是美的东西,彼时也许并不觉得其美,环境或心情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他的审美判断。古往今来,美学家们不知给美下过多少定义,然而,直至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美的定义。现代心理学也曾试图揭示审美心理机制,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科学数据。
这样说来,美是否就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观感受了呢?其实也不尽然。且不说对于美丑,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们一般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也说明了审美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和时代属性。至于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他们对于美的感受和批判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以文学艺术为例,中国的绘画与西洋的绘画,中国的京剧与西方的话剧,在审美形式上的巨大差距,是一眼就能看到的。正是因为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才开放出姹紫嫣红的民族艺术之花。因此,承认不同民族审美意识的差异,正是为了肯定民族文学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审美意识的差异,他们的审美创造活动是无法沟通的,恰恰相反,审美意识的多样性造成了审美创造活动的多样性,而多样性的审美创造能够更进一步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正如不同的个体审美意识能够融入到民族审美活动的整体意识之中一样,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也能够通过相互交流与学习而融入到人类审美意识的全面发展之中。这正是我们探讨不同民族的独特审美意识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中国人的原初的审美意识的出发点。
1
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应该从中国人最初的精神模式子中去寻找。
法国的艺术哲学家丹纳在研究产生艺术品的规律时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P.76)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希腊的雕塑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例如,他认为希腊雕塑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他说:
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既没有巨妖式的喜马拉雅,错综复杂、密密层层的草木,巨大的河流,像印度诗歌中描写的那样;也没有无穷的森林,无垠的平原,面目狰狞的无边的海洋,像北欧那样。眼睛在这儿能毫不废事地捕捉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明确的形象。一切都大小适中,恰如其分,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培奥提,伯罗奔尼撒各处的山,高不过九百多公尺到一千四百公尺;只有几座山高达一千九百多公尺;直要在希腊的尽头,极北的地方,才有像庇来南Pyrenees(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大山)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高峰,那是奥林泼斯山Olympe,已经被希腊人当做神仙洞府了。最大的河流,贝南和阿基罗阿斯,至多不过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其余只是些小溪和急流。便是大海吧,在北方那么凶猛那么可怕,在这里却像湖泊一般,毫无苍茫寂寞之感;到处望得见海岸或岛屿;没有阴森可怖的印象,不像一头破坏成性的残暴的野兽;没有惨白的,死尸般的或是青灰的色调,海并不侵蚀岸,没有卷着小石子与污泥翻腾的潮汐。海水光艳照人,用荷马的说法是“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紫罗兰的颜色”;岸上土红的岩石环绕着闪闪发光的海面,赛过镂刻精工的一条边,有如图画的框子。——知识初开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与这样的风光接触。人看惯明确的形象,绝对没有对于他世界的茫茫然的恐惧,没有太多的幻想和不安的猜测。这便形成了希腊人的精神模子,为他后来面目清楚的思想打下基础。——最后还有土地与气候的许多特色共同铸成这个模子。[1](P.329~330)
这里主要谈到的是自然环境对形成民族精神模子的巨大影响。所谓精神模子,主要是把这个民族的思想方法、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当然也包括审美意识。尽管人们对于环境决定论有着这样那样的意见,然而直到现在,丹纳所作的从环境入手探讨希腊民族的精神模子从而揭示希腊雕塑的艺术特点的深刻分析和基本结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希腊雕塑艺术的最为精辟的见解,也为我们研究民族审美意识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从自然环境来探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要比探讨古希腊人的审美意识困难得多。古希腊仅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岸一带,面积不过十多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土地物产均有较大差异,形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反映在审美意识方面,南北文化也有明显的区别。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想》一文中说:“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2](P.33)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P.261)很显然,自然环境的确造成了南北文化形态及其审美意识的差异。
承认南北文化形态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并不表示可以放弃对中国文学共同审美理想的探寻,也不是说南北文化对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影响没有主次强弱的分别,更不是说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没有其同的精神之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南北文化所给予中国文化整合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后),北方文化表现出了比南方文化旺盛得多的生长力。从考古学界所发现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遣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析,“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期,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主要地区,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们都是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社会,不过狩猎和采集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采集鱼、蚌之类水生动物的比重,南方似乎多于北方;它们都使用角、骨、蚌等原料制作的工具,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这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都是大致相同的。在社会性质方面,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均处于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酋邦阶段。石家河文化的社会,也到了部落社会的晚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以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南北文明对铸造中华民族精神模子的不同影响。
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遗存,可以和古史记载相印证。龙山文化的居民逐渐以部落为主体,以城为核心,发展成古史中所谓的国或邦,与《史记·五帝本纪》所云黄帝有万国和《尚书·尧典》所云尧有万邦相一致。从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的序列分布及其相互联系来看,也与《史记·五帝本纪》所云“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记载相吻合。北方文化的整合过程,应该不是一种自发的演变,而是一种人为的强制。《史记·五帝本记》所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尧舜“流共工于幽陵”,“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应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正是这种文化的整合,表明北方正大踏步地走向文明社会的门槛。夏禹所建立的王朝,终于将中国社会推向文明。
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并没有像中原龙山文化那样发展。尽管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的文化互有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一种整合的趋势,仍然各自独立发展着,这说明它们没有整合的动力。因而,当中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国家组织已经高度发展以后,南方仍然徘徊在文明社会的门槛,需要借助外力的推动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南方社会后来的发展也是靠北方强力推动的结果,不仅殷商、西周均有征讨三苗、荆蛮的记载,就是使南方振兴的楚人其实也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
造成文明时代南北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童恩正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中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他指出:北方便利的交通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而较差的自然条件能够激发文明的创造(注: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所以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见《历史研究》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南方交通不便,生活资料易得,酋邦的出现即能满足社会要求,不必也不能自动地再向国家发展;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而南方是稻,粟是耐旱作物,可以单纯依靠扩大耕在面积而增加产量,而稻对地势和水源有较高要求,南方的山林不容易改造成为稻田,难以满足社会分工发展的需要;中原以北是蒙古大草原,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频繁,黄河流域早期城市的出现、政权的集中和阶级的分化,均与民族冲突有关,而南方族群分散在山林溪谷、河湖沼泽之间,没有经常性的外界威胁,缺少北方那样促进民族团结整合的力量;北方水患频仍,治理黄河需要有权威的集中领导,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有可能与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所以夏禹治水成为妇孺皆知的传说,而南方虽有水患,却山高土广,容易避免,除蜀地外,不存在大规模治水的传说和史实;北方存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比较容易联合而成更高级的政治团体,当这种团结出现以后,也比较容易统治与管理,南方则是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经济上的分散性必然影响到政治上的分散性,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文明的出现;北方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氏族意识浓厚,祖先崇拜盛行,如果这一氏族或家族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的统治者,那么他们崇拜的祖先就可能成为全政治团体的神,这种神灵崇拜能够增强这个政治实体的凝聚力,南方的宗教信仰与此不同,良渚文化的祖先崇拜没有发展到地区性的神灵崇拜或政治实体的神灵崇拜,反之,落后的动物崇拜和神鬼崇拜则长期存在;北方很早就出现尊卑等级和社会分工,中国礼乐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先秦北方学者都肯定国家管理、阶级划分、社会分工和礼乐制度,而南方在政治思想方面则比较落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基础,就是南方长期存在的分散的家庭经济,这种经济不但没有向更大的政治实体发展的要求,反而拒斥北方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就开始了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力图维护历史上形成的封闭、停滞的经济和政治局面。童恩正先生的这些认识是颇有见地的。
既然在进入文明的大门时北方的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整合而成华夏民族时,北方民族无疑成为了优势民族,而文明之初所形成的民族精神自然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模子。它给予后来的影响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北方,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寻找这个影响我们民族审美意识发展方向的精神之源。
2
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人的原初审美意识不仅应该有南北地域的差异,而且在不同的原始部落中也应该存在差异。例如在即将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有相当精致的陶器,蛋壳黑陶不仅胎壁很薄,而且磨制光亮,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陶塑的人头、羊、猪、鸟等,形象生动逼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随葬雕塑品,如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梳、骨匕、嵌绿松石的骨筒、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制作精细,造型优美,是颇具特色的艺术品;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中的雕塑则有双鸟朝阳象牙雕、鸟形象牙圆雕、双头鸟形骨匕、编织纹骨匕、木雕鱼形柄、圆雕木鱼、陶塑鱼、陶塑狗形器钮、陶塑人像,以及玉质的璜、管、珠等,制作之精美,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所罕见;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璧、瑗、琮、璜、珠、管、坠等玉器,这些玉器中有不少制品磨制细腻,雕刻精致,花纹图案精美,种类繁多,达到了制玉工艺的空前水平。所有这些雕塑制品,无疑体现了制作者的审美意识,它们造型上的明显差异,也无疑体现了制作者审美意识的差异。
然而,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这些颇具艺术特色的器物,究竟是人们审美活动的产物,还是原始宗教祭祀的副产品,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原始宗教活动中也可能伴随有朦胧的审美意识,况且由器物的造型和加工工艺来推断制作者的审美意识,很可能人言人殊,所谓的审美意识也许只是现代诠释者自己的审美意识而并非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不仅体现在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中,而且最直接最可靠地反映在能够概括其审美意识的观念符号中。事实上,新石器时代还没有产生反映人类认识的观念符号。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即使已经有了对美的一些认识,也不可能达到清醒和自觉的程度,而清醒和自觉的审美意识是在作为观念符号的文字产生以后才得以定型化并扩大其影响的;并且,任何器物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实用性常常会掩盖其观念行意义,只有当一种观念定型化并符号化以后,它才能不受时空的局限而凸显其意识形态意义,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直接地影响。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也是在其观念的形态定型化和符号化以后,才得到不断地继承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对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的探讨,可以从中国最早的观念符号——甲骨文入手。
美,按照甲骨文专家的意见,“象人首上加羽毛或羊首等饰物之形,古人以此为美……《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说文》以味甘为美当是后起之引申义”[5](P.416)。他们不同意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美的解释是美的原初义。然而,季羡林先生通过对西文“美”(Beauty)的语源和中文“美”的字义的考释分析后指出:
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所谓感官知觉,基本上只限于眼和耳,于是所谓美学也仅限于研究眼观之美和耳听之美。
……中国人讲“美”,是从五官中的舌这一官讲起的,讲的是口味之美。同西方讲美从眼和耳讲起,出发点迥乎不同。我近几年以来,总是到处寻求中西间的差异,而少谈其间的共同之处。吾非好辩也,只有寻出了差异,才能讲中国的特色,而差异又是客观存在,只是人们视而不见而已。[6]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对美及与美相关的古代文字和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后也认为: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起源于味觉,然后依次扩展到嗅觉、视觉、触觉、听觉;随着文明的发展,又从官能性感受的五觉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最后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扩展到精神、物质生活中能带来美的效应的一切方面。他说:
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或美观念是始于味觉美,“美”字的最早含义就是指味觉的美的感受。但是不久,“美”字也用来表达嗅觉以及视觉(严格地说,是视觉和触觉结合)的美的感受了。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明白中国人美意识的原初形态之一斑。简而言之,中国人的美意识,在其初级阶段,是直接从肉体感觉的对象中触发产生的,其内容是与味觉、嗅觉以及视觉、触觉这些肉体的官能的悦乐感密切相联的。而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美的感受的对象,即美味、芳香、美色等等,都与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与他们的生命的保持、永续,体力、精力的充实增进,以及伴随着这些的丰富深切的快乐、愉悦,有极深的关系,所以美味、芳香、美色等等,是官能感受的直接对象。[7](P.16)
不管《说文》所云“美,甘也”是否“后起之引申义”(注:从甲骨卜辞来看,“美”还只用于地名和人名,如“追貯其乎取美御”(郭若愚《殷契拾裰二编》七八),“美”为地名;“子美亡蚩”(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三四一五),“子美”为人名。至今还没有发现甲骨文中的“美”字指审美活动或有意识形态内涵,因此,现在下结论说“以味甘为美当是后起之引申义”为时尚早。),羊在古人的生活中的确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段玉裁注《说文》“美,甘也”云:“甘部曰:美也。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注“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云:“周礼膳用六牲,始养之曰六畜,将用之曰六牲,马、牛、羊、豕、犬、鸡也。膳之言善也,羊者详也,故美从羊,此说从羊之意”。从《说文》“甘”、“美”可以互训,“美”、“善”可以互训来看,说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从味觉开始是有符号学和语源学的依据的,同时也符合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羊是美味的食物。农业民族以谷物(北方主要是粟和麦)为主要食物,即使是贵族也不可能经常食羊,人们以羊为甘美之味自在情理之中。《吕氏春秋·孟春》、《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均有“食麦与羊”的记载。《吕氏春秋·察微》还载有鲁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宋华元率师迎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将战,华元杀羊飨士,羊斟不与焉。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于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华元杀羊飨士,是为了激励士气,说明羊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御者羊斟因未能食羊而怀恨,竟然在战场上将帅车驾入敌阵,其行为自然可鄙,这里面虽有争待遇的意味,但也说明羊斟对羊的美味的贪婪。(注:中国人有喜爱羊之美味的传统。陆游《老学庵笔记》记事谚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宋人也以吃羊肉指代优裕的生活。)另一方面,既然羊是美味食品,祭祀祖先当然应该敬上,因而羊又成了祭祀的牺牲。古代祭祀燕享单用羊、猪称少牢(见《仪礼·少年馈食之礼》注),后来专以羊为少牢(见《大戴礼·曾子天圆》)。人们以为祖先享用了美味的羊会赐福于后人,于是羊便具有了给人带来幸福的美意,羊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来。《论语·八佾》载云,由于鲁自文公以来不视朔,子贡便想废去告朔之羊,孔子不赞成,对子贡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以是否用羊为牺牲来判断是否爱礼,羊甚至成了礼乐制度的一种表征。当然,以上材料并不发生在中国文明的初始阶段,但一个民族的基本的文化观念常常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些材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何以产生以味甘为美的原初的审美意识。
正因为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从味觉开始的,所以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重在体味而不是重在观察,对气与神的把握胜于对形与体的关照。孟子有“养气”之说,庄子有“凝神”之论;书法有王僧虔的“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书法钩玄·王僧虔笔意论》)的书道,绘画有谢赫的“气韵生动”(《古画品录》)等六法;唐司空图论诗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表圣文集·与李生论诗书》),宋张戒论诗追求“意、味、韵、气”(《岁寒堂诗话》),元方回论诗主张“心即境”(《桐江集·心境记》),明谢榛论诗重视“兴、趣、意、理”(《四溟诗话》),清叶燮论诗本于“理、事、情”(《原诗》内篇),等等,都可以看到原初审美意识的影响。《孟子·告子上》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荀子·王霸》云:“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从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他们论人的审美感受也都是从味觉到听觉再到视觉。李泽厚总结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说:
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8](P.63~64)
这些论述,是符合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的客观实际的。中国文学不大重视对现实的摹仿,早期没有宏大的史诗,叙事文学成熟较晚,却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抒情诗特别发达,视文学为人的生命的表达等等,都与中国人的文学审美重视生命的体味和内心的感受有关。
我们说中国人的原初的审美意识是从味觉开始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审美始终停留在味觉的层面上。事实上,人的五官原本相通,味觉也会蔓延到嗅觉、触觉、视觉、听觉,只是由于感觉的原初基础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传统心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我国传统审美心理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提出的许多有关美的基本思想成为后来中国美学发展的基础,也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发展。
美与德的结合是春秋时期极有代表性的一种审美思想,如楚国大夫伍举所云“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固然意在批评灵王修建章华台劳民伤财、耻笑于诸侯,然而,这里涉及的审美观念也是不容忽视的。伍举认为,美不在于感官的愉悦,而在于道德的完善;审美不是对对象实体的把握,而是对对象实体的超越;只有在审美活动中贯彻社会性、伦理性原则,才能真正达到美的理想境界。伍举不以“目观”为美,强调以“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为美,这种重内心体味的思想继承的正是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注:其实,“德”之涵义便重在内心体味。《广雅·释诂》云:“德,得也。”《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注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左传·桓公二年》疏云:“德者,得也,谓内得于心,外得于物。”说明“德”重在体味,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重德倾向是中国人原初审美意识的合规律的发展。)。
与伍举对美的认识比较接近的还有鲁国大夫臧哀伯的“文物昭德”说、晋乐师师旷的“乐以风德”说等。臧哀伯在谏鲁桓公纳郜大鼎于太庙时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具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左传·桓公二年》)师旷在谏晋平公悦新声时说:“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也。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国语·晋语八》)《左传·宣公二年》还载有王孙满劳楚子回答楚子问鼎之大小时指出“在德不在鼎”,《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有魏绛辞谢晋侯赐乐时也说过“乐以安德”的话,《国语·周语下》所载单穆公、伶州鸠同周景王论乐也强调“乐以中德”。单穆公认为:“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昭德;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伶州鸠则说:“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总之,他们均以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是否有利于培养美德为审美活动的第一要务,有着十分鲜明的审判道德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得到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主流。由于论题所限,不再申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们之所以把审美活动道德化、政教化,一方面与中国原初的审美不重形式而重内在体验的民族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喜爱整体思维、类比推理,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常常运用象征主义方法有关[9]。应该承认,道德化审美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对合理性,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道德约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水平。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化审美的历史局限和对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由于古人将审美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将审美鉴赏与伦理教化同等看待,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不能脱离道德与政教的束缚,形成古代作家重德轻艺、重教轻文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固然有利于作者注重作品的道德作用和社会效果,对接受者的阅读心理也有规范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确有不少扬善惩恶、伸张正义、抨击时政、为民请命并且富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但也毋庸讳言,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大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阿谀之作和充满说教、毫无美感的陈词滥调,这是探讨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必须予以注意的。
收稿日期:2001-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