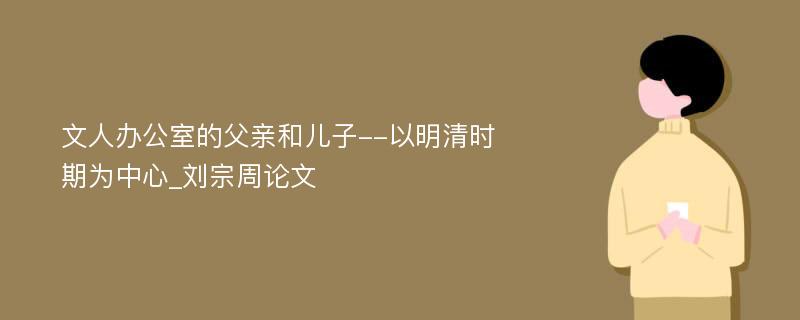
士大夫处父子一伦——以明清之际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明清论文,父子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2-0122-12 本文尝试以明清之际为时段,由有限的视角讨论古代中国士大夫的家庭、父子,探查知识人之间观念与伦理实践的歧异,呈现他们伦理生活的丰富性。 一、肃若朝典 古代中国被公认的模范家庭,有可能气象森严以至肃杀。 《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王夫之说:“《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节也者,礼也。……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礼行其间,庶几哉,可以嗣先,可以启后。”(《耐园家训跋》,《薑斋文集》卷三)[1] 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家训》:“曾大父平居,鸡鸣辄巾栉起。诸子必起居于寝,诸妇篝灯理晓妆。少迟,竟日不许见。先安人竟以劳病。”同书卷下《庭训》记沈镜宇节甫,“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子孙环列其父左右,“非问不敢发一语”,其父“不就寝不敢退”,皆“凛凛重足,肃若公庭”,[2]更像是对家人日常的折磨。张岱也记其曾祖父“家居嗃嗃,待二子、二子妇及二异母弟、二弟媳动辄以礼。黎明击铁板三下,家人集堂肃拜。……家人劳苦,见铁板则指曰:‘此铁心肝焉’”,“平居无事,夜必呼二子燃炷香静坐,夜分始寝”。(《家传》)[3]《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种描述尽管略嫌抽象,但由同书的其他章节获得的印象,此先师的确不像后儒一派俨然,尤其不像他的上述“之徒”,即使“燕居”也像是刻意令子孙不适。又,李颙称道曹端(月川)整齐门内,“言动不苟,诸子侍立左右,恪肃不怠,则是子孙化也;夫人高年,参谒必跪,则是室家化也……诸妇皆知礼义,馈献整洁,无故不窥中庭,出入必蔽其面,则是妇女化也”。(《四书反身录·大学》)[4]“夫人高年,参谒必跪”,最为不情。名儒之家,气象肃杀如此。 王夫之记其祖父:“出入欬笑皆有矩度,肃饬家范,用式闾里”,(《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薑斋文集》卷二)[5]似乎时刻意识到其道德形象的示范意义;更“居家严整,昼不处于内,日昃入户,弹指作声,则室如无人焉者”,(《家世节录》,《薑斋文集》卷一○)[6]入内室尚要“弹指作声”,其妇的紧张不难想见。陈确也曾记自己夜宿某家,那家有母妻子女共五六口,“鸡鸣起煮粥,竟肃然不闻一语,若无人之室”,不由得自叹弗如。(《暮投邬行素山居记》)[7]由今人看来,有人而肃若无人,那一家气氛之压抑不难想见。据陈的同门友张履祥说,陈确自己也“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机杼之声达于外。男仆昧爽操事,无游惰之色。子侄力行孝友,雍雍如也”。(《言行见闻录二》)[8]既“有法度”,又“雍雍如也”,与他所称赏的邬家相较,至少较近于人情的吧,不知其为何自以为不足。陈氏不纳妾,能善待佃仆,想来不至于一味“严”、“肃”。刘宗周所纂家谱,记某位前辈“居恒寡言笑,及对众吐辞确而厉,听者悚畏”,“门内之政肃然”。(《水澄刘氏家谱》四《世家列传》)[9]另一前辈“矜严好礼,出于天性,自少鲜戏言戏动,长而愈自绳简,规圆矩方不逾尺寸”,“视妻子如严宾,三子既老,犹出必告,反必面,不命之坐不坐,不命之退不退”。(同上)[10]刘宗周的儿子刘汋所撰年谱,关于其父,说:“其刑于家也,事亲极其孝,抚下极其庄,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11]曾师从刘宗周的张履祥,引其同门友祝渊得之于亲见的印象,也说刘氏“闺门之内,肃若朝廷”。(《言行见闻录二》)[12]但由刘宗周所整理的家谱《世家列传》看,他本人对于家族前辈的“坦衷和易”、不拘礼法,也颇能欣赏。如说某前辈“为人坦衷朗度,无城府,与人交,一见如旧好”,[13]某前辈“居恒不甚闲苛礼,而率真远俗,动铸天机,外泯圭角,亦不内设有城府”。[14]颜元自说“有志于礼”,其目标即“闺门之内,肃若朝廷”。(《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禁令第十》)[15]对弟子也说:“夫行乎礼,则闺门之内俨若朝廷,不亦贵乎!”(同书卷下《教及门十四》)[16]李塨所撰颜元年谱,记某日“门左演爨弄,家众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无闻”,颜氏喜曰:“谁谓妇女不可入德也。”[17] 上述事例在士大夫中普遍与否,难以断定。对此暂且置之不论。上述引文中“肃若公庭”、“肃若朝庙”、“俨若朝廷”云云,自可视为对于朝廷、官府的模拟,但仅此尚不足以为“家国同构”的佐证。王夫之的确说过:“圣人之于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于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道敦厚。”(《诗广传》卷二)[18]儒家之徒拟“齐家”于“治国”,无论父/子、夫/妇、师/弟,无不以君/臣之礼规范。类似的伦理实践,不难将家族秩序政治化。不能拟之于君臣的,则为朋友、兄弟。陆世仪说:“天下惟朋友一途最宽,不得于此,则得于彼;不得于一乡,则得于一国;不得于一国,则得于天下;不得于天下,则得于古人——惟吾所取之耳。”(《思辨录辑要》卷二)[19]至于兄弟,则兄友弟恭,虽有长幼之别却非从属、臣服的关系。朝不坐燕不与的儒士,以想象中的朝廷为模拟对象,构建其家庭、家族秩序,在今人看来无疑有喜剧意味,但相关的书写却一本正经。在当时的知识人,最为理想的秩序在朝堂之上,是理所当然的事。以朝廷为最高典范,对“朝典”、“公庭”的模拟,系对尊长权威、权力一再重申的仪式,亦系对家庭、家族秩序反复确认的仪式;既是管理手段,也是教育手段。而“肃”、“严”的达成,首在戒妇、子、仆,即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唐顺之说其妻始嫁,“见于舅姑,舅曰:‘所属妇者无他,第闺外不闻妇声,足矣。’自是舅往来闺外,竟廿余年不识孺人声。舅每叹以为能妇”。(《封孺人庄氏墓志铭》,《唐荆川文集》补遗卷五)[20]约束到了这程度,即夫妇间狎、昵,不消说也在所必戒。 拟“齐家”于“治国”,颜元的确是较为极端的例子。他说:“吾侪岂必作帝王,乃行夫子‘为邦’之训乎!如每正月振起自新,调气和平,是即行建寅之时矣;凡所御器物,皆取朴素浑坚,而等威有辨,是即‘乘殷之辂’矣;凡冠必端正整齐,洁秀文雅,是即‘服周之冕’矣;凡歌吟必正,‘乐而不淫’,是即舞舜之韶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法乾第六》)[21]以一介平民而坦然言之,并不以为“僭越”。颜元所谓“习行经济”,纵然无“经济”,也仍不妨习行夫子“为邦”之训。这一种思路,无疑将政治伦理泛化、日常生活化了。经了训练,颜元的妻妾已相当自觉。年谱记其家人(应即妻妾)收到颜氏家书,“相谓曰:‘不闻朝廷诏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宁以妻子异人臣?’相率拜受”。[22]这种景象,我于其时号称“粹儒”刘宗周、张履祥、陆世仪等人的文集中未曾读到,更不必说气象宽和的孙奇逢。年谱说颜氏“待妻如君,抚子如师”,[23]只是不像夫妇父子。① 顾炎武对东汉风俗,不胜向慕。其《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24]说东汉之世,“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25]《后汉书》李通传,记李通之父李守“为人严毅,居家如宫廷”。而李氏并非诗礼传家,倒是“世以货殖著姓”的。张湛传说张“虽遇妻子若严君焉”。东汉之世,颇不乏此等人物。同书樊宏传记宏父“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魏晋士人,在后人的想象中一派通脱,而“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世说新语·德行》)《晋书》卷三三何曾传:“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颜氏家训·序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明清之际的儒家之徒,对此却既有承袭,又有发挥。李颙推究《论语·乡党》“吉月,必朝服而朝”,说所谓“朝”,“盖在家望君之所在而朝,非趋朝而朝也”,理由是“君亲一也,遇朔望则宜肃衣冠以拜亲”。(《四书反身录·论语上》)[26]张履祥以为“朝夕袍褶,不为不敬”,而“朝夕具公裳以揖母”不免太过,“朔望则具公裳可也”。在他看来,“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备忘四》)[27]那何不将“朔望具公裳”也免了?无论李颙还是张履祥,均不以平民而朝服、公裳为亵,且李氏更认为非如此则不足以言敬。 儒者型范,是刻意塑造的。《周礼》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用之于塑造。礼的功能,部分地正在于此。孔子答子张问政,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解释“五美”之一的“威而不猛”,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子夏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亦可为“威而不猛”作注。相反的例子,《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仪式是达成秩序的必要手段。刘宗周为其家族所拟《宗约杂戒》中,有如下行为规范:“凡道路,祖孙行啣尾,叔侄行肩随,兄弟行雁序。”“凡语言,除序寒温外,尊长不举,子弟不先;若遇有启问,必屏息而待。”(《水澄刘氏家谱》六《宗约》)[28]如此等等。如被切实遵行,自不难“肃若朝典”。 不止男性家长,即女性长辈,也不难将其家治理得犹如官府、朝廷。孙承宗《翰林院检讨劬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志铭》:“孺人自公为诸生至官长,安操家政,如持大府之宪,厘然有条次。”[29]黄宗羲《刘太夫人传》:“夫人出自相门,自幼陶染诗礼间事,闺阁之内,肃若朝典。”[30]但女性长辈对其家庭角色的理解也互有不同。王夫之记其母对其父“如承严宾”,但此母也正是暗中改变家风的人物。“一庭之中,兄弟訚訚于外,妯娌雝雝于内,欢然忘日月之长。”(《家世节录》)[31]而对于家庭气氛的改善,其母与有力焉。“家承严政,内外栗肃者九代,自先孺人易之以和恺。”(同上)[32]明末忠臣温璜之母曾说:“家庭礼数,贵简而安,不欲烦而勉。富贵一层,繁琐一层;繁琐一分,疎阔一分。”(陈弘绪编辑《五种遗规》之《教女遗规》卷下《温氏母训》)[33]于此见识很明达。 由刘宗周所拟《证人会约》的《约言》、《约诫》,人们很难想象严厉之外,他会有别的神情。而据其子刘汋所撰年谱,他父亲于讲学之余,“间一命酒,登蕺山之巅歌古诗,二三子和之,声振山谷,油然而归”,[34]大约得自曾点自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子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启示——即使这偶一的优游,也是需要经典支持的。由刘汋所记其父母的日常相处,不难想见他本人的成长环境。但年谱记有其友人对刘氏的印象,说对刘氏一向仰视,“比朝夕聆教,始觉气宇冲融、神情淡静,又如春风被物,温然浃于肌理”。[35]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想必也为刘汋所认可。刘汋自己的说法是:“先君子盛年用功过于严毅,平居斋庄端肃,见之者不寒而栗。及晚年造履益醇,涵养益粹,又如坐春风中,不觉浃于肌肤之深也。”[36]应得之于切近的感受。 由士大夫记其祖父,记其父其母,确可据以考察他们本人早年成长的环境以及他们与家庭伦理有关的思路的经验背景。刘宗周记其父刘坡,刘汋记其父刘宗周,王夫之记其父王朝聘,均可供人们想象不同的家风。万氏兄弟八人中,斯大、斯同并以学问见称。由黄宗羲记其父万泰,亦可供推想其子早年所处的家庭气氛。据黄氏说,万泰“好奇”而“胸怀洞达”,较其好友陆符(文虎)“和易”。(《万悔庵先生墓志铭》)[37]这为父者有十足的名士习气,在使其诸子不免于饥寒的同时,也应放松了过度的管束。他那些儿子的成才是否与此有关? 士大夫家传中的此类文字,无论在今人读来如何荒谬,不合理,违拗人情,这种感受与撰写者的态度却不相干。还应当指出,尽管格于体裁,但无论写父、祖或其他先人,得之于切近的观察或家族中人的口耳相传,庄严的文体中往往不乏生动的细节,可据以想象那一时期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具体情境。后人不妨尝试由此进入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尽管有关的记述容或有夸张或渲染。 二、严、慈之间 周公之于其子伯禽,孔子之于其子伯鱼(鲤),被后儒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典范。《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对此评论道:“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尹氏语,曰:“孔子之教其子,无异于门人,故陈亢以为远其子。”[38]这“远其子”,似乎使后儒印象深刻。张履祥说孔门弟子之于其师,“虽孝子之于慈父,或未之有及也”,而孔子对弟子,“其亲爱之情,实有过于父之与子者”。(《与李石友》)[39]张氏言此,旨趣更在孔门师弟子之亲密,而对孔子之“远其子”,像是视为当然,不以为有阐发的必要。 《孝经》:“父子之道,天性也。”《荀子》有《君道》、《臣道》、《子道》诸篇,却未设专篇讨论“父道”。有“父慈子孝”的说法,即使不能读作条件关系——即“父慈”则“子孝”,却不便径以“慈”为“父道”。关于父之于子,似乎缺乏明确的规范,士大夫的伦理实践,通常也在“严”、“慈”之间。 《汉书·刑法志序》:“鞭扑不可绝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鞭扑”所及,无非子孙及僮仆。上文已引王夫之所说“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接下来更明确地说,父兄子弟间,要强调的非止仪节,“有精意存焉”。所谓“精意”,“夫之蔽之一言曰严”;更引《易》所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耐园家训跋》)张履祥训子,说“家长执家法以御群众,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训子语》下)[40]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写其祖父对于其父“严威,一笑不假,小不惬意”,其父即“长跽终日,颜不霁不敢起”。祖父“每烧镫独酌”,令其父“隅座吮笔作文字,中夜夔夔无怠色”。[41]而他自己的父亲有所不同。其父“严于自律,恕于待物”,对儿子却“以方严闻于族党”。只是这“方严”非即疾言厉色,倒是“恒以温颜奖掖”,甚至与其子对弈。(《家世节录》)[42]对儿子们另有惩戒方式,即“正色不与语,问亦不答”,能这样达“旬余”之久。[43]这种“冷暴力”,实在较呵责更可怕。与其以脸色施教,倒不如将那番训诫明白说出的好。该篇还说其父“大欢不破颜而笑,大怒不虓声而呵”,[44]“拥膝危坐,间终日而不一语”。[45]自控到这种程度,想必不难在家中造成隐蔽的紧张。我已在其他场合讨论士大夫的处夫妇,写到叶绍袁的寡母对其子、子媳的不情。冒襄笔下的祖父对其父也类此。冒氏说祖父课子“严切”,子、媳“结褵一月,即携去读书郡城者经年”。冒氏不讳言自己的态度,说“寒门家教最严,礼溢于情”。(《老母马太恭人七十乞言》)[46]这“礼溢于情”,非王夫之、刘宗周所能道,只不过在近人读来,仍嫌过于委婉而已。 却也有为人父而不如是者。由陈确晚年由子弟舁了去赏花,可想其人宽裕的一面,那是其师刘宗周所不能有的。花间的父子想必不至于俨乎其然正色相向的吧。陈确曾批评其时为人艳称的孝行的不情,对友人说:“尽父母之欢,尽人子之欢,便是太和宇宙在吾兄家庭日用间,何快如之,而当远慕高远难行之事乎?”(《答沈朗思书》)[47]所谓“道平易”,无非顺乎“天理人情”。陈氏上面的说法,与他论节义反对以惊世骇俗为标榜,有其一贯。不过“太和宇宙”云云,与上文所引他对邬行素家风的推许,又不尽一致。陆世仪的见识更称明达。他说:“古人云教孝,愚谓亦当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愚见人家尽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边。遇顽嚣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后,能有几人!”(《思辨录辑要》卷一○)[48]北方大儒孙奇逢为人和易,由有关的传记文字看,更像是开明家长。其人理学造诣似乎不便高估,却平实质朴,气象宽裕,是蔼然长者。由他本人的文字看,其处兄弟,待子侄,十足朴野的乡土气息,而少有刘宗周的那一种道学神情。由他的如下文字,不难想见其家庭气氛:“幸诸孺子,长幼成群。诵诗读书,膏续香焚,长枕大被,至性氤氲。兄弟而兼父子,眠食起居,随意适形,而绝不觉其纷纭。”(《榻铭》)[49]正是其乐融融。上文引张岱说其曾祖“家居嗃嗃”。他父亲则异于是,“喜诙谐,对子侄不废谑笑”。(《家传》)[50]接下来有生动的例子。《黄宗羲年谱》记天启三年黄氏随侍其父黄尊素在京,“好窥群籍,不琐守章句”。其父课以制艺,黄“于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其母告知其父,他父亲说的却是“亦足开其智慧”。当其时党争激烈,其父与同志者议论时事,独许宗羲在侧。[51]凡此,均可知黄尊素对他这个儿子不以凡儿视之。本来就有种种父,种种子,种种父与子。《礼》的规范性描述,或多或少限制了对于古代社会伦理状况的想象。 另有不便以“严”、“慈”描述者。颜元祭其六岁早夭的儿子,动情地说:“自汝之能举止记忆也,听我之训,每晨午饭后至我前,正面肃揖,侧立读《圣谕》三过……诵名数歌三徧,认字三四句,乃与我击掌唱和,歌三终,又肃揖,始退。”说他如此年幼的儿子,“于曾祖父、母称孝孙,于父、母称顺子”,“所欲为者,畏吾即止;所恶为者,顺吾即起”。(《习斋记余》卷八《祭无服殇子文》)[52]刘宗周有诗《哭招儿》、《哭亡女哀娥》。其《亡儿哀娥葬记》写的是女儿幼年即“听父母之训惟谨”,“每晨夕必朝于床下问安否,敛衽正容下气。不命之退不敢退,自坐卧饮食皆然”。[53]不愧为大儒之女。哀娥乃刘的长女,死于二十一岁。刘宗周、颜元未见得不慈,丧子之痛极其深切。称“哀娥”,也因了此“哀”。只是颜、刘上文所写的那一套规训,适足以戕害了童真,在今人眼里非但不情而已。 唐顺之说詹钿其人,幼孤,“自童孺时,已恂恂若老生”。(《俞孺人传》,《唐荆川文集》卷一一)[54]少年老成,不好弄,往往被作为“生而歧嶷”的表征。倒是王夫之,关于“蒙养之道”,说对儿童“若苛责太甚,苦以难堪,则反损其幼志”,(《周易内传》卷一下)[55]是很明达的话。陆世仪也说:“人当少年时,虽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终有畏惮,故法不妨与之以宽。宽者,所以诱其入道也。”(《思辨录辑要》卷一)[56]还说:“人少小时,未有不好歌舞者,盖天籁之发,天机之动,歌舞即礼乐之渐也。圣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礼乐,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今人教子,宽者或流于放荡,严者或并遏其天机,皆不识圣人礼乐之意。”(同上)[57]不唯对童子,即对成人也戕贼生机——这一层意思,陆世仪未明言,未见得不作如是想。黄宗羲也说:“尝见有名父之子,起居饮食之际,不稍假借,子视其父真如严君。而一离父侧,便无所不为,反不如市井闾阎不教之子。盖以父子之情不能相通,片时拘束,藏垢愈深,故孟子以‘养’言之,太和薰蒸,无不融洽。”(《孟子师说》卷四)[58]他自己所写《亡儿阿寿圹誌》,说自己“食与儿同盘,寝与儿连床,出与儿携手,间一游城市,未暮而返,儿已迎门笑语矣”,[59]父子间的亲昵有如是者!黄宗羲宗王(阳明),王阳明在“训蒙”方面见识通达,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批评“近世之训蒙稚者”,“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他所主张的“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均意在宣导,而非抑制检束。(《训蒙教约》,《五种遗规》之《养正遗规·补编》)[60]以王阳明学派宗主的身份,其上述言论的影响可想而知。王学知识人讲学场合令童子歌诗,以兴起众志,也应与此有关。陆世仪以为,“阳明先生社学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诗习礼,以发其志意,肃其威仪,盖恐蒙师惟督句读,则学者苦于简束,而无鼓舞入道之乐也”。(《思辨录辑要》卷一)[61] 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段,人们随处可读到患难夫妻、患难兄弟、患难朋友、患难师弟子。那本是一个非但忧患且危机深重的时代。患难父子,即如遗民傅山与其子傅眉,流人方拱乾与其子方孝标。患难中家人父子相拥取暖,使人伦的美好面尽显,也应当不是稀有的事实。 祁彪佳的如下一例与以上诸例又有不同。《祁忠敏公年谱》记崇祯九年祁氏的长子及孙子死于痘,而祁氏“色不哀”,有人“窃议其矫”,祁氏说:“人情于父母每患不足,妻子每苦有余,即‘矫’亦未为失也。”祁氏本人的日记,记当其子“疾转剧”,还询问自己是否用餐,“以此见儿之天性甚笃也”。儿子死后,自己“为之含殓已”,竟在当晚读完了一本“邸报”;还说自己曾和别人谈“哀而不伤之义”,觉得自己“于此尚有中节光景”。(《祁忠敏公日记·居林适笔》,崇祯九年五月二十九日)[62]理学家于“喜怒哀乐”已发、未发,反复讨论。祁氏在信仰层面说不上是儒家之徒,却正可证那一套论述影响于士人之深且广。王阳明《与黄宗贤》一札,说:“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63]这番意思,为后儒所乐道。他们倾倒于这种自我控驭的能力。明人记御史陈祚,说其人“面目严冷,虽家人亦不假辞色。宣德七年,进《大学衍义》,劝上曰:‘勤圣学。’上大怒,抄劄其家,并捕其子侄瑄等,同下锦衣狱,各不得见者三年,备尝苦楚。宣宗宴驾,释出。祚乍见瑄等,略无怜惜之意。偶都堂顾佐来访,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荫此辈,为祚累至此。’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归,不问其生理。其少恩如是。”[64]苛刻寡恩如陈氏者,也应当属于较为极端的例子。更常见的,应当是“远其子”的吧。 我在其他场合已提到了以夫妇而兼朋友,被士人认为理想的婚姻关系。却未见以父子而兼朋友这一种表达——或只是我搜寻未及。即使没有(或罕有)这一种说法,实践中却未见得没有与此相近的意境。古代中国的知识人,严于等差、伦序,却又不无变通,不乏欣赏融和之境的能力——是伦理的,又是审美的。清代关于人伦持论通达的俞正燮,对“严父”有别解,所引陆游诗,就有近似的趣味,尽管他仍然未用“友”这种说法。②古代中国处父子而近于朋友的,想必不止陆游父子。相信古代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开明的父亲,都有类似俞正燮的通达之见,尽管不便仅据若干条材料,抽绎出纵向演变的线索。所谓“一门师友”,家门之内“自相师友”,就有可能隐含了此种意境。这种家庭关系与严于父子、夫妇分际以至“肃若朝廷”的那种,可能都不普遍。庸常的,想来应当是虽不极端,却仍然暗合了伦理规范、至少不远于规矩的那种情况的吧。 已有对古代中国“绝对君权”的质疑。父权是否绝对,未见得没有讨论的余地。金声称颂王氏家规,总结道:“要之,民间断未有家用子弟为政,而得见淳风美俗、而得获吉祥善事者。”(《王氏家规引》,《金忠节公文集》卷八)可知也有“家用子弟为政”者。的确有极端的例子。太仆寺卿正霍子衡要儿子从死,理由是:“吾国之上卿,君亡与亡。吾今从君,汝曹亦当从父。”其长子亦以为“父死君,子死父,奚为不可?”[65]这种事例或也不多。由明清之际忠臣的传状看,该忠臣纵然以为妻妾应当从死,也有可能愿意给子孙留一条生路。 家训(尤其训子部分)一类文本对于本篇的重要性,在于其中较为直接表达的对于子弟、子孙的规训意图与成效期待。这种表达之郑重,自然也与其文体渊源有关。“训子”的经典案例,自然是上文提到的周公之于伯禽,孔子之于伯鱼(鲤);相信士大夫当训子之际,有可能因了上承这样的传统,而感受到其行为的庄严性。“训子”,对象明确,标准或系度身定做,即针对其子的条件,未必预设了普遍意义,与泛泛的道德训诫有别。这种有明确针对性的“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或竟是为父者对子孙后代的“遗训”。由士大夫的“训子”,固然可知该父对其子的期待,却也令人可据以推想那是何等样的父亲,这做父亲的如何处父子,承担“父”这样一种角色。为父者期待于其子的,未见得是“肖”。鲁迅曾提到阮籍、嵇康正希望儿子“不肖”;嵇康在《家诫》中教训儿子,宁要其“庸碌”,与他本人的行事风格全然不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66]杨继盛刚肠疾恶,为明代著名忠臣,训诫其子,无非庸德之行,庸言之慎,做世俗所认为的好人,这层心事,岂不也耐人寻味?③刘汋所撰刘宗周年谱,说他父亲撰写《做人说》、《读书说》,系因自己“气质庸暗”,其父以此“示警”,[67]则两“说”亦刘氏的“训子”篇。《做人说》对其子的要求,合情合理:宁为庸人,勿为恶人;由庸人而“积”为好人。即使庸人而庸学,其进境也有不可限量者。有趣的是,刘宗周对其子指点路径,所用的依然是讲学态度,或也如夫子的庭训,那口吻不大像父之于子;标题下虽注明了“示儿”,有特定的对象,内容却有普遍的适用性。可知刘氏进入某种角色之深。至于刘汋,则因常常出现在其父讲学的场合,惯闻其教,对此应当习以为常。刘宗周在三篇《做人说》后自注道,后两篇中的问答,“往往设为之。儿固不能作是问,余亦不能作是答也”[68]——的确是在做文章,不过将“儿”作为了假定的对话方而已。刘宗周对后人的要求,还可由《证人会约》的《约言》、《约诫》佐证:规范行为之严苛,法度之细密,正是严于修身的儒者本色。一度在刘宗周门下的张履祥,衰老之时训其幼子,由《训子语》诸目,可知为其子计虑之周详,唯恐有失,絮絮不已。(《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七、四八)张氏所训,多属世故谈、人事经验、庸言庸行之类,预先设想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教其子以应对之道,乃极实用的处世之道。由那文字看来,这做父亲的并不指望其子出人头地,只希望其循谨,“全身保世”,不“妄想”、“妄求”,务安其本分,“尽其职分”——既鉴于世道,也应当考虑到其子的资禀。 无论刘宗周、张履祥还是傅山的“训子”,均不落实于身份,所说不过是希望其子成为何等样人。傅山的训子侄,关心更在(不限于家学的)才华、精神的承传,内容集中于读书、著述,几无道德说教,且现身说法,口吻亲切,置于同时同类文字中,特具一格。他希望子侄完成自己的“著述之志”,(《家训·训子侄》)[69]故知傅山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至于读书,则“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同上)[70]并不异于常人,只不过较之张履祥那样的“粹儒”,所取较宽而已。同卷《文训》、《诗训》、《韵学训》,所训亦子侄。所传授者,为独家心得。如《文训》特重《左氏春秋》的文章技法。至于《仕训》,关系出处,是遗民家训中尤为重要者。傅山对其子傅眉的未尽其才、先自己而死,不胜痛惜。“尽其才”,或许也是他对于子侄的最大期待吧。《十六字格言》,乃教其两孙。傅山对其孙说:“尔父秉有异才,而我教之最严。”[71]此“严”,只能在上述文字外想象。上文提到士大夫的悼殇子(女)。傅山《哭子诗》十四首,悲慨淋漓。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生至痛,何况是一对在明清易代的动荡中“患难频共”的父子!④傅山对死去的儿子说:“吾诗惟尔解,尔句得吾怜”,(之三)以父子而互为知己;说“患难饱荼蓼,艰贞抱精神”,(之四)则以父子而同为遗民;“尔能饱暖我,我不饥寒忧”,“祖母不至饿,我每暗点头”,(之五)儿子不但是自己晚年的依靠,且“以孙为子”、代己尽孝;“尔志即我志,尔志唯吾知”,(之七)更强调以父子而同志。触物伤情,这组诗中如“架上之载籍,多尔细批点”、“晒书见诠评,仓皇掩其卷”(之十二)[72]一类句子,更令人心动。傅眉生前立身行事,正肖乃父。由傅氏训子侄及《哭子诗》,可知对其子多方面才华的激赏。至于评价中的过甚其词,不消说也出自慈父心肠。 王夫之说其父“尚不言之教”,(《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薑斋文集》卷二)[73]还说其父严于取与,不但与他人之间,即使对于已成年的儿子,涉及财产,也界限分明,并不以享用其子的供奉为当然——似乎较为少见。其父的理由是:“其人则吾子也,其物则非吾有也。”(《家世节录》,《薑斋文集》卷一○)[74]除了戒汰外,无非以此对儿子示教,出于极端的洁癖。王夫之本人的文集中,也没有题作“家训”的文字,而与弟侄、子侄的家书,却可以作家训读。王氏另有《传家十四戒》。“戒”与“训”,前者更有“命令”意味,有诸不可、不要(“勿”)之意。篇末却说“吾言之,吾子孙未必能戒之”,想得很明白。他寄希望于“后有贤者,引伸以立训范”;即使对此,也不敢期必。(《船山诗文拾遗》)[75]王氏在这种场合,也保有了一贯的清醒。由王夫之的文字间,不大能想象其是何等样的父亲,倒是一些似乎无关的小片段,引人遐想。即如王氏记自己“敕儿子勿将镜来,使知衰容白发”,(《述病枕忆得》,《薑斋诗集》)[76]就令人想见其衰暮之年颓唐中的幽默感。 我所读这一时期的家训尤其训子文字,对家人子侄的要求,似乎不如宋儒的苛细(参看朱熹《治家格言》、司马光《居家杂仪》、袁采《袁氏世范》等),亦未见如嘉靖朝浙江提学副使屠羲时《童子礼》那样,工夫细密到无所不至。未知可否据以想象“时代风气”的转移?据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77]以严格的父子为主体,是春秋时期以来封建崩解后家族结构变化的结果。⑤曼素恩则说:“自1645年颁布的圣旨开始,清朝历代皇帝有系统地将明代遗留下来的父子相袭的职业集团和地位集团逐步拆散。这些政策显然来源于由满族民族背景所促成的一些考虑,而这些考虑不可避免地又要渲染清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的同时带来的一些价值观念,尤其是他们对待社会性别角色的态度。”[78]梳理由春秋时期直至清代与父子一伦有关的变化,无疑是有趣的题目,却已在本篇作者的能力之外。 三、人子之事亲 正史孝义传中人物,往往是异人异行,反不若日用伦常、庸言庸行,更贴近普遍经验。传记文字中一再被提到的“孺慕”,或因稀有才被大加渲染。人子之事亲,出告反面、晨昏定省,不过常仪,属于“子道”的基本面,真的做到,已属不易;至于“奉甘旨”、“色养”,即今人也难以实践的吧。而古代知识精英所认定的人子事亲之道却不限于此,更在“不坠门风”,进而“克绍箕裘”、“继志述事”。这里的“继述”,非即“子承父业”之谓;较之承业,更要“继”的是“志”。“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宜传、可久的,毋宁说是“耕读”这种生活方式;更高的境界,仍然在借诸诗书的精神的“传”、“继”。 舜的处父子、兄弟,被赋予了经典意味。舜对后世的示范,或许不在“原则”,而在具体情境中的应对。但舜的行为实在难以复制——或许颜元等少数圣徒除外。《日知录》卷六“如欲色然”条:“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则其诚无以加矣。”[79]“慕”乃情感取向,非《礼》所能规范。至于不取“证父攘羊”之“直”,则出于儒家之徒的深谋远虑,关系世道人心。可惜这一层深意,今人已难以领解了。上文已谈到事君与事父之道的异同。除了上述引文提到的那些原则,士大夫还认为对父不可责善。黄宗羲阐发其师刘宗周对《孟子》“匡章”章的诠释,那说法是:“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难,即今吾之知善与不善,还是父母的,如何反责善于父?”[80]关于“君子之不教子”章,则说:“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从来弑父与君,只见得君父不是,遂至于此。”[81]刘宗周所纂家谱,记某前辈不见容于继母,诉讼中不为自己辩解,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水澄刘氏家谱》四《世家列传》)[82]家谱记某前辈说:“念中见亲有不是,讵特大逆之渐,直是大逆矣”;并非“亲”确有不是自己假作不见,而是杜绝此念,使自己相信亲“实无有不是处”。(《水澄刘氏家谱》六《祖训》)[83]却也有通达之论。王夫之就说:“后世子道之衰,岂尽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读通鉴论》)[84]那么,天下确有不是的父母。 至少在本篇所论时代如黄宗羲这样的士大夫那里,“忠”不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道德律令。那么“孝”是否绝对、无条件?这里我想说的是,“子道”之于“父权”,即便是微弱的制约,也不便无视,因其关涉士大夫的伦理实践有无可伸展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事实是,一个恪守礼法的儿子,除了指望一个开明的,得严、慈之中的父亲,也仍然有适用于“经/权”的有限空间。舜对于其父瞽瞍的小杖受、大杖走,就被作为经典性的示例。见诸史籍,君叫臣死,臣不妨逃亡。援此类例子,父要子亡,子亦可不亡。张自烈《与司马君实论从命书》:“比读大集,见执事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于君亦然。违君言不顺,逆父命不孝,人得而刑之。’仆谓此说尤非。君父之命一也,而治乱异。治命可从,乱命不可从,审于礼义而已。”[85]古代中国诸伦理规范并不止于相互补足,还互有辖制。至于儒家伦理系统中的破绽,或许正可理解为预留空间。屈大均《书叶氏女事》涉及反常事件。叶氏女以父命(“甥舅为婚”)为非礼。“夫女也,在家从父,而有时父母之命不可从,不可从而从,是为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罪人也。”[86]尽管屈氏评价此类事件,仍然务合于礼或“礼意”。仍然是王夫之,强调君臣、父子间的互动,亦即君臣、父子关系的相互性,说:“人伦之事,以人相与为伦而道立焉,则不特尽之于己,而必有以动乎物也。尽乎己者,己之可恃也。动乎物者,疑非己之可恃也:自非天下之至诚,则倚父之慈而亲始可顺,倚君之仁而上以易获。其修之于己者既然,则以立天下之教,亦但可为处顺者之所可率繇,而处变则已异致。”(《读四书大全说》卷三)[87]至于“遗民不世袭”,内含了对于父子伦理的理解,亦“继述”的限度。不对子孙作不情的要求,出诸遗民本人,更像是一种“解放”其子孙的姿态(关于“遗民不世袭”,参看拙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下编第七章)。纵然有诸种现成且公认的规范,生活世界中的人子之于其父(母),仍有伦理实践的个人性、丰富性。 “继述”往往是对于士大夫(尤其知名人士)子弟的特殊要求。这里“继述”固然是为人父者之于其子的期待,亦为人子者对于其父的责任,是更高境界的“孝”,更精神向度的“孝”。天启阉祸被难诸人父子,曾为一时观瞻所系。黄尊素之子黄宗羲的袖锥刺仇,以及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刺血上书”,为父报仇,就大为时论所称。孙奇逢致书魏学濂,说“尊公以一死完君臣之义,令兄以一死毕父子之情,痛定思之,是父是子,今古无两”。(《复魏子一》)[88]当然,后来的事情有点复杂。魏学濂之兄魏学洢之死,被认为无愧于其父,而魏学濂一度的附顺,则被视为门风之玷。忠臣子弟易代中的姿态,关系重大,已在通常人子的伦理义务之外。魏学濂因而难以为时论所恕。即使同为“东林子弟”的黄宗羲为其撰写墓志铭,对问题的尖锐性也无可回避。易代间“一门忠义”,最为人所艳称。鹿氏一门,鹿太公、鹿善继父子,就被奉为人伦楷模。孙奇逢、鹿太公,是其时被认为没有人伦缺陷的人物。鹿太公与其子若孙,孙奇逢兄弟父子,都令人可感北方式的淳朴醇厚;孙、鹿特具侠肝义胆,又非平世乡里贤人、善人可比,所拥有的似乎是完满的人生。 而如下“继述”,虽不轰轰烈烈,却更合于知识人的普遍期待。明中叶以降不乏理学家父子兄弟一门师友、子弟以传承父兄之学为己任的例子。名父之子尤有继述的压力。到本篇所论的时期,黄宗羲的《宋元学案》,由其子黄百家及全祖望后先修补。以整理遗编为继述的,另有王夫之之子王敔。这也是子对于其父的切切实实的纪念,尤其在明清鼎革尘埃落定之后。黄宗羲《黄氏家录》写其祖父逢其曾祖父之怒,“必伏地请扑”,而且说,自己“以大人释怒为喜,不以免扑为喜”。(《封太仆公黄日中》)[89]写其父黄尊素,使用的却更近于“正史书法”,全不及于家人父子之“私”,不大像儿子写父亲(同书《忠端公黄尊素》)——不私其作为“历史人物”、“公众人物”的父亲,倒未见得是在刻意隐藏个人角度。上文写到了刘宗周训子取讲学态度,与此相应,刘汋写其父,态度也更像仰慕、追随者,而不大像子之于父——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当然,日常相处中的刘氏父子,仍然不能仅据文字推想。刘汋之于其父刘宗周,不但辅助其讲学,阐明宗旨以开示后学,且在其父身后,撰写年谱,整理遗编。由传记材料看,刘汋为人较为谨愿,没有其父的气魄、锋稜。据其父的高足黄宗羲说,刘汋对其父之学,虽曰“墨守”,却“有摧陷廓清之功”。(《刘伯绳先生墓志铭》)[90]其立身的刻苦严毅,也正肖乃父。而王汎森所撰《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一文,考察刘门弟子间的严重分歧所导致的“蕺山学派”的分裂,及刘汋于其间扮演的角色,足以复杂化了通常对于“继述”的理解。[91]正是由继述的角度,刘汋对于其父遗编的整理、宗旨的阐发,当其世即有争议,更被后人目为明清间学术转向的一种征兆,具有思想史的话题性。所谓“继述”,又何易言哉!刘汋删改其父遗稿固不足为训,却也仍然应当说,倘不持学派立场,仍能由这种有争议的继述,体察到那一代人的严肃和对于继述一事的郑重不苟吧。 无论士、民,均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由其父看其子,以其父责其子,使得某些为人子者承受了较之常人更大的道义压力。易代之际的忠臣父子、遗民父子,清初的流人父子,均为特殊境况中的父子。患难父子、患难夫妇、患难师弟子,亦其时一种伦理景观。方以智于漂泊流亡中,似乎置妻、子于度外;他撰写的《自祭文》,“言自甲申之变后,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92]我在其他场合已写到流人夫妇。方拱乾的儿子方孝标,奉其父居宁古塔两年,后认修前门城楼工,奉诏赎还。江右彭士望说其人在宁古塔“自撕薪行汲”,(《钝斋文选又序》)[93]江殷道说其在宁古塔“搆屋三间,畜高丽牛二头,耕以养亲”。(《钝斋文选序》)[94]关于方氏艰难困苦堪比宗教苦行的“万里寻亲”,台湾学者吕妙芬有专文研究。⑥这里只补录该文未及的一个例子。清初陆圻的仲子乃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其父于庄氏史狱获释后,不知所终,做儿子的“万里寻父,不就职,竟以劳卒”。(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后丁绍仪识)[95]吕妙芬《明清中国万里寻父的文化实践》一文说,某些寻亲故事“透露出些许更复杂的讯息,反映着生命的复杂情境,甚至凸显了父子间的冲突与意志的角力”。陆圻父子的故事,或也可由此看取。寻亲以亲人的离散为前提。离散多因战乱,却也有出于主动的选择,因而非止明清易代这样的历史时刻,即平世也有。抽身而去,掉头不顾:寻亲故事与家庭破裂、破碎的故事互为上下文。 生养死葬,本是人子事亲之常。正史列传“孝义”一目下,却不乏为葬父而历尽艰辛、孝感神灵的事迹(参看《明史·孝义列传二》)。这种故事往往渲染苦情、悲情,赏玩的,毋宁说是寻亲者的自虐;愈多磨难,愈多挫折,愈可证孝思之诚。至于上述吕妙芬该文已写到的李颙为父招魂,更像当代传奇,由李颙本人、士绅与地方当局共同制作,充斥着灵异、人神(鬼)感应等因素,务求耸动,无非为了教化的目的。对于民众,这确是有效的教化手段,主题不消说是“诚孝格天”、“至诚之道通乎鬼神”、“仁孝格鬼神”之类。那寻亲故事也就被官、民大事张扬,演绎得轰轰烈烈。⑦至于更极端以至血腥的事例,如子报杀父之仇,则平世固有(参看《明史·孝义列传二》何竞、张震、孙文诸传),也以易代间更有轰动效应,呼应了嗜杀嗜血的社会心理,不难为舆论称快。如王馀严的歼杀仇家老弱三十口(《清史稿》卷四八○王馀佑传)。 此节的标题为“人子之事亲”,“亲”指“双亲”。但儒家伦理的子道,于父母向有区分。王夫之释《易》“家人”一卦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说:“‘父父’,不言母者,统母于父也。”(《周易内传》卷三上)[96]他说:“父生之,母鞠之,拊之畜之,长之育之”,鞠育之“地道”可谓“勤”矣。其勤却不过“承天”、“奉天之性”而已。也因此“母之德罔极”,“父之德尤罔极”,“古之知礼者,父在而母之服期”,无非“崇性以卑养”。强调父道之尊,在这一点上,王夫之与迂儒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他看来,母的鞠育既承之于父,也就“大有功于父,而德亦与之配”而已。(《诗广传》)[97]顾炎武推究礼意,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又说服丧“以父为重,以母为轻”。他以孔子之子伯鱼为例,说“伯鱼不敢为其母之私恩而服过期之服”。(《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98]在这里,又遇到了几于无所不在的公私之辨:父在,不可伸其对母的“私尊”,不可因“私恩”而延展对于母的服丧之期。顾氏更辨析《礼》母为长子服丧三年之文。这种在今人看来不情的礼文,确要顾氏这样学问家才足以揭示其精微。 妻子相对于父母为轻,母则相对于父为轻——对此一向有不谓然者。王文禄就说古人父重母轻,以制礼者乃男子,故为己谋,不免于偏私,清四库馆臣以其言为“不足训”。(《海沂子·敦原篇》,《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但引据经典固然有可能规范思想,毕竟不能“规范”普遍人情。⑧也从来有女性家长。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的杭州才女顾若璞,就被作为上流社会女性家长的范例。[99]另有我曾经写到的祁彪佳妇商景兰。至于天启党祸中,罹难诸公以东汉的清流自命,有拟其母于范滂之母者,也如范滂之母,备受尊崇。记述易代之际的文字中,人们一再读到“臣有老母,此身未可以许人”云云。不知何以总是“有老母”,而非有老父。即使父权制下,母在,也可以是拒绝以身许君的理由。当然,在不少时候,这一理由也被作为了逃避艰危以至避死的借口。 关于父亲的记述,或有记述者最深刻的早年记忆。我也发现,为人子者讲述其经验中的父子一伦,较之讲述其处夫妇更困难。相较于“夫”这一角色,“子”显然更使他们紧张、压抑。由冒襄兄弟的故事,也可察觉这一点:由父母所致的创痛,只能在讲述其妻时有所透露,闪烁其词,欲说还休。并非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无非在刻意避免对尊长的损害罢了。知识人与家庭有关的经验中的隐秘面,往往为禁忌所造成。某些禁忌至今仍在,只不过不再像对古人那样有效罢了。即使这一点变化,也得来不易。 注释: ①台湾学者吕妙芬论述清初北方学者的家礼实践,颜、李之外,也谈到孙奇逢,参看其《颜元生命思想中的家礼实践与“家庭”的意涵》,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奇逢固然有礼仪方面的实践,与颜元仍有显然的不同。 ②俞正燮说:“慈者,父母之道也。”说“严”乃“敬”,系由子的方面言之;将“严父”理解为父亲“严恶”,不过是误读了古语。(《癸巳存稿》卷四“严父母义”条,《俞正燮全集》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151-152页)他引陆游诗,说陆氏教子“主于宽”,其诗中的“家庭文章之乐,非迂刻者所能晓”。(同卷“陆放翁教子法”,同书第153页)关于师道,说:“圣人之教,其道尊而不严酷”;以“敬”解“严”,以“严师”为“敬师”。(同卷“师道正义”条,同书第155页) ③陈弘绪编辑《五种遗规》之《训俗遗规》卷二《杨椒山遗属》,写于临难之时,无一豪壮语;对其两个儿子所嘱,不出日用常行,不期其肖,也不期其不肖。处处可感为其子计虑之周:正是慈父心肠。遗嘱中说:“你读书若中举中进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按杨椒山,即杨继盛) ④据诗后傅山自记,傅眉五十六岁,“郁郁不得志,以积劳忧恨成病”。(《霜红龛集》,第393页) ⑤杜正胜该书引《仪礼·丧服传》:“昆弟之义无分焉,而有分者则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杜氏以为张载“异宫乃容子得伸其私”的说法“深获原始儒家的精义”,“唯有肯定父子之‘私’才能体会‘古之人曲尽人情’”。而程颐“轻视这点‘私心’,而谓‘亲己之子异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虽可为‘累世同居’张目,却与先秦经典不合。”(《家族与社会》,第82页) ⑥吕妙芬:《明清中国万里寻父的文化实践》,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二分。该文说,“就文献数量而言,万里寻亲的故事在明清之际有大量增加的现象”。该文还谈到,由宋元到明清,寻亲故事有寻母、寻父比例的变化;寻母故事反映“家庭生活中的母子之情”,而寻父故事“却鲜少以实际生活中的父子情感为基础,更多是奠基于儒家父系家庭组织的礼法名分”。佛教报恩故事“多强调孝子为报答母恩而有种种孝行,对于母恩之深重也有极多的书写”,而“万里寻亲孝子传并不强调‘父恩’或父子之情,而是以人子之孝思为出发,以人子充分实践儒家道德规范下为人子之责任为目标”。关于寻亲,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一书有深入的分析。《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⑦李兴盛《增订东北流人史》中记有赴戍所省亲、陪亲人赴戍以至“请以身代”的“孝义”事状,其中有寻亲故事的流人版,亦为时人乐道。与流人有关的,父子、夫妇的故事外,另有朋友的故事,均为患难中人,各有动人之处,见出那时代士大夫处人伦的至性真情。《增订东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⑧陶希圣《婚姻与家族》第四章《大家族制之分解》:“唐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武后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诏依行。明《孝慈录》更改齐衰为斩衰。父尊母屈的一尊主义显然衰落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92页)按《礼》,父在为母服丧一年;父死,服丧三年,齐衰。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译本第三章注82,依据别人的研究成果,说:“将为母服丧的期限改为三年是从明朝开始的,从此为母服丧的期限就与为父服丧的期限一样了,而且也同样称为‘斩衰’。而在古代,母死仅服一年(期年)丧。在唐代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也曾有将服母丧延长至三年的规定,但有一个特殊的名称为‘齐衰’。”(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