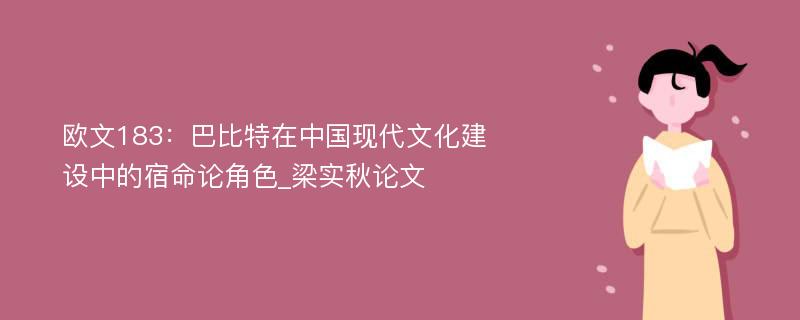
欧文#183;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宿命论文,角色论文,文化论文,欧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与中国现代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他以自己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一代中国文化青年,如汤用彤、陈寅恪、吴宓、梅光迪 、胡先骕、林语堂、梁实秋、楼光来、张歆海等,他们纷纷求学哈佛,投师其门 。白璧德以富有魅力的学识和人格深深影响了这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参与者,包括让本来具有浪漫倾向且对于白璧德颇有些不服的梁实秋彻底改变了自己,成为白璧德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是,学衡派文人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建设热潮中以传统文言形式标举白璧德,不仅使得国人望白氏之学而却步,而且使得白璧德人文主义蒙上了中国式守旧复古的面影。梁实秋虽然清楚地看到了学衡派对于白璧德的“拖累”,但他以白璧德所不屑的方式将白璧德学说用为苛刻论战的武器,轻而易举地将白璧德拖进了与鲁迅为敌的阵营,从而确定了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妖魔化角色。其实,白璧德的学说包含着鲁迅曾经主张过的理念,可正是受它的中国传人特定色彩与作派的拖累和影响,使其中所包含的积极价值始终未能得到弘扬、关注、哪怕是冷静的介绍。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给予白璧德带来的一种宿命。
一
在哈佛受教于白璧德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对白璧德保留较多的一位。他承认 曾“从游Biss Perry,Irving Babbitt……几位名教授,却增长了不少真学问”,不过 后来又“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甚至为白璧德的论敌斯宾岗辩护。(注:刘 慧英编《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9、80、81、80页。)但他依然 坚持认为“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够深速的”,(注:刘慧英编《林语 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9、80、81、80页。)有人说“就美国人而论 ,对中国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白璧德”,(注:侯健《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 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见余光中编《秋之颂》,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年, 第74、70页。)虽未免有些夸张,可不容否认的是,白璧德学说经过梅光迪、胡先骕、特别是吴宓、梁实秋的大力张扬和鼓吹,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思想资源之一 ,并且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漩涡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无法绕过 的精神现象。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现象?面目陈旧,色泽灰暗,以因循的固执拒绝时代的鲜亮。翻 开《青年杂志》及胡适的相关文章即能感受到,当新文化运动正以某种恢宏的气度冲击 着旧文化的黑暗而通向新时代的光明之际,与胡适展开论争的梅光迪及其所处身的哈佛 大学正体现着这样的灰冷与暗淡。翻开《学衡》及同时代的其它报章又能感受到,当新 文学正充满生气昂扬风发地向现代性表现的前景迈进的时候,《学衡》带着浓重的白璧 德观念背景乃至哈佛情结勇敢地挺身“搅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灰冷与暗淡。更不 用说梁实秋逆潮流而动,面对文学大众化的呼声申言文学从来就不是大多数的,针对无 产阶级文学的宣传提出文学应宣扬普遍而永久的人性,并且不断地抬出白璧德这尊西佛 ,陆续贩卖其关于文学学科训练的保守观点,与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思潮前道 而驰。哈佛大学本是一个充满进取心的一流学府,可经过它的中国留学生们的几度运作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影像立刻变得顽固而守旧;白璧德本是倡扬宽容之德的学界巨子 ,可经过他的中国信徒的几番装扮,在中国现代作家面前立刻变得诡奇而固执。吴宓、 梁实秋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界介绍并推举了哈佛和白璧德,但同时,也正是他们的 热心介绍和诚心推举,使得哈佛大学尤其是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色调显得过于 灰冷而暗淡。
白璧德及其文化思想最初登陆于中国文坛是由学衡派推进的,也同时被学衡派抹上了 灰冷和暗淡的色调。发现并揭示这一现象的恰恰是对白璧德爱之甚切的梁实秋。这位最 初正是通过学衡派了解白璧德及其思想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精辟地指出:白 璧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固有其因指陈时弊而不合时宜处,但其精意所在绝非顽固迂阔 。可惜这一套思想被《学衡》的文言主张及其特殊色彩所拖累,以至于未能发挥其应有 的影响,这是很不幸的”。(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见梁实秋等编 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4、3页。)实际情形 也正是如此。
1922年初创刊的《学衡》杂志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主办,尤以吴宓为自始 至终的中坚干将。该杂志第3期刊载的《学衡杂志简章》,阐明其主要宗旨是站在中西 文化胶合的视点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用力于国学和西学两方面,特别提倡“以 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这里说的“吾国文字”明确指中国传统文言。由此观之, 始终处在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对立面是其一大特点。《学衡》自第1期载梅光迪《评提倡 新文化者》起,至最后一期载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止,洋洋79期,悠悠10余 年,几乎从没有放弃过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抨击,从而坐定了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文化大 本营的位势。此一旗帜一展,各派旧式文人、守旧势力即以陈词滥调竞相邀集,从而使 得《学衡》客观上成了(至少在新文学家看来)群魔乱舞的诗坛,藏污纳垢的文场。别的 不说,那些惯于写作旧体诗词文赋的老夫子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一些获得旧 功名不合新潮流的遗老文人也纷纷联袂而至,那些年在《学衡》刊登过旧体诗文(或遗 文)的遗老文人中,光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出身的便不下于十数人。加之留洋归国的才士 俊彦专好“吾国文字”传统,以文言介绍外国人思想,翻译外国作家作品,如吴宓屡以 章回体笔法翻译外国小说,在第55期将萨克雷的《名利场》的开头处理成“楔子”和“ 第一回,媚高门校长送尺牍,泄奇忿学生掷字典”,俨然一副旧说部的作派。尤其是他 们尝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心态勉为其难地强用古文表述新鲜事物和异邦学理, 以至或穿凿附会,或半文不白,于是给新文学家留下了“乌托之邦”之类的口实。所有 这些都表明了学衡派文士甘愿冒当时中国文学界之大不韪,在锐不可当的新文学潮流面
前自觉秉持梁实秋所说的“特殊色彩”,呈现着僵死的灰暗,散发着陈腐的霉味。
令梁实秋十分遗憾的是,他们这种僵死陈腐的“特殊色彩”无可挽回地“拖累”了白 璧德,进而“拖累”了哈佛。吴宓等人不仅从来不讳言他们的哈佛“出身”及与白璧德 的师生关系,而且一有机会便炫耀这一出身及这种关系。他们曾在《学衡》杂志登载过 白璧德像和哈佛大学西华堂的照片。《学衡》插页很少刊载大学校景(似乎除此西华堂 之外就登载过牛津大学全景图),更不用说大学里的一座建筑物。他们选择的哈佛大学 西华堂位于魏德纳图书馆右侧,那里应是白璧德“生前上课”的地方,或有人译为“西 维堂”。(注:侯健《染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见余光 中编《秋之颂》,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年,第74、70页。)《学衡》插页上刊载的 外国文学家思想家的造像,也常体现出白璧德先生的好恶:白璧德推崇的孔子、苏格拉 底、释迦牟尼、耶稣的造像被置诸醒目的位置,伏尔泰的造像曾被刊载数次;卢梭的造 像虽然在第18期得以刊用,但在同期的《述学》中即有《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的译 文呼应白璧德对卢梭的批判,特别是附在这篇译文之前的“编者识”,乃与白璧德同一 声腔地声讨卢梭,说是“社会万恶,文明病毒”盖可由卢梭负责,“今世之乱,谓其泰 半由于卢梭可也。”刊登卢梭造像,似乎正是树立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当然,学衡派对白璧德最直接最严重的“拖累”是用陈旧艰涩的文言译述白璧德的言 论著作。吴宓等人在《学衡》上推介白璧德不可谓不努力,陆续刊有《白璧德中西人文 教育谈》、《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 、《白璧德释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 《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等译文,同时还分别译介白璧德学术同伴穆尔和谢尔曼(S tuart P.Sherman)的人文主义观点,在自撰的杂评述论中更是频繁征引白璧德的思想观 点,客观上造成了《学衡》是白璧德人文主义中国分店的一般印象。这种印象对于白璧 德来说带有一定的强加意味,因为他由此可能被中国人视为同学衡派一样的陈腐保守, 或者像梁实秋所担心并慨叹的那样,可能被当作学衡派“顽固迂阔”风格的精神导引和 思想源泉。
白璧德人文主义同文艺复兴时代及其后流行的欧洲人文主义相似,强调人性的完整、 发展的均衡、生活的常态和伦理的精神;但思想内涵比欧洲人文主义更开放,更有系统 性,也更注重人生的修养和节制。白璧德认为人生“含有三种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 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应该过分扩展。人性的生活 ,才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的生活当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强企求” ,因而人特别需要自我内心节制和宗教的调节。(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 想》,见梁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 、4、3页。)而内心节制和宗教调节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像儒家宣扬的那样为了推行“礼 制”,所谓的“克己复礼”,而是为了达到更高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有人认为意志自由 是白璧德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因为他“喜欢反复引用约翰荪博士的话:‘所有的理 论都反对意志自由,所有的经验又都趋向于它。’”(注:Frederick Manchester,ed.,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Odell Shepard G.P.Putnam's Sons,1941 ,p.77,p.110.)实际上,“白璧德将保守主义问题放置在自由秩序中。”(注:Richard Wightman and James T.Kloppenberg,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BlackwellPublishers Ltd.,1995,p.53.)另一方面,他虽然确实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思想 表述中常常显露出服膺古代圣贤的倾向,但从来反对拟古主义和泥古主义,在《论创作 》一书中提倡“一种包容着真诚创造的摹仿类型”,这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不是根 据事物的样子而是根据它应有的样子作摹仿”的法则的发展。(注:Stephen C.Brennan &.Stephen R.Yarbrough,Irving Babbitt,Twayne Publishers,1987,p.90,p.95.)
由此可见,白璧德人文主义的真髓不在于仿古复古,而在于更高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和 创造性摹仿,诚如梁实秋所指出的那样,“其精意所在绝非顽固迂阔”,它尽管“有其 因指陈时弊而不合时宜处”,可不少美国学者断言,其中含有现代主义的成分,甚至“ 只是许多现代哲学形式的一种”(注:Dom Oliver Grosselin,The IntuitiveVoluntarism of Irving Babbitt,St.Vincent Archabbey,Latrobe,PA.1951,p.117.): 白璧德与马修·阿诺尔德没有什么不同,其所以被当代人误解,不是因为他比他们少 现代一点,而是比他们更加现代。(注:George A.Panichas,The Critical Legacy of Irving Babbitt,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9,p.27,p.200.)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保守倾向的要害在于“将传统和历史记忆当作稳定社会和政治的力 量,反对乌托邦和改革者的影响”,(注:Richard Wightman and James T.
Kloppenberg,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 .53.)而不是在于回到传统形成的历史形态之中;这样一种富有深刻历史理性并包含一 定时代新质的人文主义(注:在本文中我倾向于避开“新人文主义”的概念,因为经过 考察觉得用比较通行的“新人文主义”概念指称白璧德思想并不恰当。据D.O.格罗斯林 介绍,在美国,神学人文主义一度被称为新人文主义,白璧德人文主义则被简单地称为 人文主义或美国人文主义;他还观察到,白璧德只是有一次用了“新人文主义”指称自 己的思想,那还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避免与科学人道主义相混淆(Dom OliverGrosselin:The Intuitive Voluntarism of Irving Babbitt,St.Vincent Archabbey,
Latrobe,PA.1951,p.5)。学衡派在20年代、梁实秋在30年代介绍白璧德学说时皆未用“ 新人文主义”概念,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前面冠 一“新”字,乃是后来“新教育”、“新自由”、“新批评”等一系列“新”字号时髦 催生的结果(Milton Hindus:Irving Babbitt,Literature,and the DemocraticCultur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3)。这就是说,“新人文主 义”对于白璧德学说而言其实不算是一个稳健的指称,故而对白璧德比较尊重的学者在 谈论白璧德话题时往往倾向于避免用“新人文主义”概念。1986年为纪念白璧德逝世50 周年,在美国出版过一本题为《我们时代的欧文·白璧德》的论文集(George A.
Panichas and Claes G.Ryn,ed.,Irving Babbitt in Our Time,The Catholic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86),收有正式论文9篇,只有Russell Kirk 的TheEnduring Influence of Irving Babbitt一文一次提到过“新人文主义的凄苦的希望” (第20页),另有Folke Leander的Irving Babbitt & Benedetto Croce一文讨论过“New Humanism”与“Neohumanists”的关系(第85页),除了诸如此类偶尔的现象而外,研 究者全部使用了“人文主义”或“白璧德人文主义”这样的提法。有鉴于此,我认为还 是用“白璧德人文主义”较为妥当,也较为明确。),却被白璧德在中国的学生学衡派 文士染上了“顽固迂阔”、灰冷暗淡的色调,在对白璧德爱之甚切的梁实秋看来,当然 是一件值得痛心值得悲哀的事情。
梁实秋进一步指责学衡派对白璧德及其学说的“拖累”:
《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 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璧 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见梁 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4、3页。)
《学衡》创刊之际已经是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像梁实秋这样的大学生 看了《学衡》的满纸文言也不由得望而却步,广大的文学青年和市民读者自然更会退避 三舍,敬而远之,白璧德人文主义纵然满是经纶珠玑,也激不起读者的胃口,于是学衡 派文士不管如何竭思殚虑鼓吹和兜售白璧德学说,他们所端起的文言架势、所板起的经 院面孔早令人避犹不及,人们对之只能取冷落甚至鄙夷的态度。
梁实秋振振有词甚至可以说是义正辞严地指出了学衡派“拖累”白璧德声名以及耽误 白璧德人文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大失误,作为一个同样“从游”过白璧德的哈佛生, 作为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另一个积极鼓吹者,他显然很满意于自己对白璧德思想在国内形 成影响所做的工作。这不仅是指他积极推动《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在新月书店的出 版发行,也不仅是指他对《学衡》在“拖累”白璧德名声和耽误白璧德思想影响发挥方 面的揭露和反思,更重要的是指他在与革命文学阵营的对垒中比较充分地实践了白璧德 思想,施展了白璧德学说的“威力”,并在与鲁迅等人的激烈论争中几乎是单枪匹马地 捍卫了白璧德和他的人文主义,这至少使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不再像《学衡》时代 那样遭受国人的冷落。
二
问题是梁实秋的努力减除了白璧德学说在中国被冷落的尴尬,却招来了白璧德在这遥 远的国度被嘲骂的麻烦。学衡派的文言“拦路虎”固然严重限制了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 影响,但在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形下毕竟没有令白璧德思想陷入被攻击的境地。与学衡 派文士相比较,梁实秋之于白璧德在中国的被妖魔化更难辞其咎。
最起劲地将白璧德当作“妖魔”的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作为革命文学阵营里的一个 中流砥柱式的作家,鲁迅与活跃在“新月”文场上的梁实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这 番论战有比较理性的争议,如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论争,基本上还展开于理 论层面,也有比较不讲理性的争执,例如对白璧德的评价或评估。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 中经常对白璧德冷嘲热讽,但很少涉及其具体的思想观点,鲁迅在《而已集·卢梭和胃 口》一文中承认,他没有读过白璧德学说的原文,对于白璧德观点的了解只是通过日文 资料的浏览,但凭此他便可以讽刺白璧德,因为梁实秋等人在“上海一隅”“大谈白璧 德”,显示了他们特有的胃口,鲁迅就是想让他们倒倒胃口。他没有认真阅读白璧德原 著却敢于对白璧德嗤之以鼻,甚至在一种强词夺理的语势下将白璧德算作新月派一分子 :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 ,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作在:徐志摩先生的诗, 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 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注: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198页。)
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理性论证之正道。但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放弃了理性的态 度。他曾说“像鲁迅那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过白璧德的作品”,——这姑且算是实情, 但紧接着鄙夷地说鲁迅“也绝对无法能读懂”,(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 想》,见梁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 、4、3页。)则基本上是意气之论。
既然双方围绕着白璧德展开的是意气之争,便有必要弄清引起这番关于白璧德争执的 起因。这起因恐怕在于梁实秋对白璧德卖力的介绍——鲁迅是冲着梁实秋们如此卖力的 鼓吹才与白璧德过不去的。鲁迅说过,“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 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 威,……”(注: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 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注: 鲁迅《大家降一级试试看》,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第547页。)鲁迅其实并不满意于这种意气之争,而愿意接触这些真正的西方理论家的 论述;他指责“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等因 为要兜售他们的“国货”而怠慢了原著的翻译。(注:鲁迅《读几本书》,见《鲁迅全 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70页。)这些个洋人都是因为他们在 中国的传人而成了鲁迅的讽刺之矢的,梁实秋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与鲁迅争执最为长久
也最为激烈的对手,鲁迅既确认了梁实秋作为“一个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注:鲁迅《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第285页。)的身份,白璧德也就首当其冲成为鲁迅讽刺的重点。
鲁迅与白璧德在思想观念上本不是天然的敌人,他如果较多地接触白璧德理论,很可 能还会引起某种共鸣。白璧德反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张以人文主义克 服这种科学自然主义,与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的见解非常相通;白璧德认为“东 西方的人文主义者,都以砥柱中流的少数的说法,反对民主的随波逐流的多数的说法” ,(注:白璧德《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侯健译,见梁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 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15页。)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任个 人而排众数”的观点,指责那种以多数的和历史的力量压制少数精英的现象,在这一点 上似乎也成了东方的一个人文主义者;鲁迅慨叹中国文化衰败的历史如由春温而进入秋 肃,同白璧德服膺古代圣贤的观点很相接近:他尊崇的是“趋于成为孔子所谓的君子或 晋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持身端严的人”,这恐怕也与鲁迅的“希英哲”的想法相合。当然 ,应该注意到鲁迅的思想观念有前后期之分,但鲁迅并没有像郭沫若他们那样有一个明 确的“方向转换”的运作,也没有像田汉那样宣布过对自己的批判,他对于来自异邦的 与自己曾经有过的观点颇相接近的学说,即使不引为知己之论,也断不至于视若异己之 论甚至敌对之论,一般而言,自然的亲切感是容易唤起的。至少在鲁迅那里,白璧德之 成为敌人乃是由于梁实秋的“拖累”和“牵连”。
当然,成为鲁迅的敌人并非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但鲁迅之于白璧德很少观念上 的批判,多的是一些无谓的攻击和讽刺,这对于白璧德而言无异于不白之冤,就此一点 ,梁实秋之于其美国恩师岂能自辞其咎?从白璧德那方面说,一日为师,虽不至于“终 身为父”,为自己的学生担待一些被攻击的责任似乎也是身为人师的应有之义。问题是 梁实秋与白璧德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有那么密切。
从种种材料分析,梁实秋在哈佛留学期间确曾听过白璧德的课,读过白璧德的书,与 白璧德有过偶尔的个人交往,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超出一般留学生与任课教授通常具有 的那种关系。梁实秋从记忆中所能挖掘出来的唯一的一点与白璧德直接交谈的片断,便 是白璧德如何指点和肯定他提交的英文作业《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而这一点恰好说 明他这个选课学生与白璧德关系并不密切。因为梁实秋明明知道白璧德素来不喜欢王尔 德等极端浪漫化的作家,却提交这样的读书报告,岂不是自寻尴尬?白璧德拿到论文, “他乍看到这个题目吃了一惊,好象觉得我是有意来捋虎须”,(注:梁实秋《我是怎 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载《中国时报·人间》1978年3月12日。)然后告诫他,对这 样的题目,对这样的研究对象“要使用无限量的小心”。(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 生及其思想》,见梁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 2、5、2、4、3页。)白璧德的这种惊愕的反应至少表明,他并不怎么了解“眼前”这位 倔强的中国学生,他的这番告诫也只是一个长者对于所有后学的一般关照。梁实秋为解 释白璧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多且偏爱甚深的原因,曾于30年代《现代》杂志第5 卷第6期发表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中如数家珍般地说是“其母生于中国之宁波” ,后来他又称“白璧德先生的父亲生长在宁波”(注: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5页。)。虽然说法不同,但显示自己与白璧 德大师家世非常稔熟的用心是很明确的。遗憾的是他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全都属于道 听途说。白璧德早年丧母,其母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其父也没有到过中国。在白璧德 的家人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乃是其妻道拉·梅·德娄(Dora May Drew),德娄夫人 的父 亲曾任职于中国的天津,其父母在中国的上海组成了家庭,德娄夫人出生于中国并在这 里生长过一段时间。梁实秋或许听说过白璧德与中国的这一番曲折的关系,便附会为其 母亲出生于中国或父亲生长于中国。其实,与白璧德过从甚密的人要举出白璧德浓厚的 中国兴趣的例证可谓毫不费力,有人就说过他家里有中国物件的布置:灯罩上绣有一只 中国龙,家里还挂着中国式样的丝绸饰品。(注:George A.Panichas,The Critical Le gacy of Irving Babbitt,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9,p.27,p.200.)梁 实秋似乎只能用道听途说的资讯表述自己与白璧德的亲密关系,可见这关系其实本是如 何疏远。
不熟悉外国教授的家世原不是什么问题,与白璧德关系疏远一点更是无伤大雅,但因 对方声名显赫,便煞有介事谬托知己,已于自己的人格有碍,而以传人自居,将一个不 相干的“白老夫子”卷进一场无谓的争执,客观上又有失厚道。
问题还在于,在与鲁迅的论争中以及在日常的写作中,梁实秋某些苛刻的言辞和甚至
堪称宵小的作为实在不能算是得了忠厚儒雅的白璧德的真传,而鲁迅等论敌却很乐意于 将这一切帐目都算到乃师白璧德的头上。这是梁实秋比学衡派文士更“拖累”白璧德并 使白璧德在中国面临妖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白璧德无论在他所处的哈佛以及在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孤独者,但他在坚持自己观 点并与异己之论作不妥协论战的同时,始终表现出与“新英格兰的圣人”称谓相符的宽 容大度。在哈佛大学,他的“学生并没有被要求赞同他的观点或反对别人,他们可以选 做热情洋溢的或是孤僻古怪的古典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自然主义者,或 者颓废派”。(注:Frederick Manchester,ed.,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Odell Shepard G.P.Putnam's Sons,1941,p.77,p.110.)甚至他的论敌如门肯在 《偏见集》中也真诚地认为白璧德很懂得“尊敬他的敌人”。(注:J.David Hoeveler,Jr.,The New Humanism: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1900-1940,The Rector andVisitors of the Vniversity of Virginia,1977,p.16.)不过同样写过《偏见集》的梁 实秋显然不屑于摹仿白璧德的这一番作派。他对自己的论敌如鲁迅可谓大不敬,不仅写 过《鲁迅与牛》这样有失厚道的文章,而且在青岛大学的课堂上当学生问起他与鲁迅之 间的论争时,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鲁迅与牛’”,引得学 生“莞尔而笑”,他则“神态自若”。(注:臧克家《致梁实秋先生》,见刘炎生编《 雅舍闲翁》,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5页。)更严重的是,他与鲁迅的论战 词锋之间常暗藏杀机,似有一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险恶。他每每攻击鲁迅等“到× ×党去领卢布”,正如鲁迅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从事这种带有政治报警性质的“批评” ,“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注:鲁迅《“丧家的”“资本 家的乏走狗”》,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梁实秋看到《萌芽》杂志上有人说鲁迅“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有嘲笑过一 个字”,便非常起劲地质问:“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 大概不是国民党罢?”(注:梁实秋《鲁迅与牛》,载《新月月刊》1930年第2卷,第11 期,“零星”第5页。)这正是在国共两党生死敌对的时代,为观念之争而不惜将对手往 死路上送,可就不是有失厚道的问题,简直真有点借刀杀人的意思了。(注:这里不是 危言耸听。须知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组织确曾想暗杀过鲁迅,并已经着手布置,后因故 中止。参见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5页。)如果当年因 少不更事,又激于鲁迅的冷嘲热骂而想到借助“伟丈夫”的宝剑加以弹压,虽有些歹毒 但尚算情有可原,那么,待到他垂垂老矣,鲁迅更早已作古的时候,他居然不讳言当年 的这点险恶,还兀自洋洋得意,说是鲁迅自己“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注:梁实秋《 关于鲁迅》,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4、3页。)那番自鸣得意又苛刻歹毒 的宵小心态更见恶劣。这样一个在言语行事方面都不以白璧德的宽厚品行为楷模,却被 普遍地视为白璧德的门徒的梁实秋,他以自己的宵小行径玷污甚至摧毁了白璧德原有的 道德形象。
鲁迅为人为文也很苛刻,对梁实秋和白璧德尤为如此,梁实秋说他是“‘刀笔吏’的 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等等,(注:梁实秋《关 于鲁迅》,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4、3页。)大致是不错的。但鲁迅虽然 然检讨过自己的苛刻,表示过“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注:鲁迅《鲁迅译作书目 》附记,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可从不 标榜自己的宽容与恕道,恰恰相反,他声言自己鄙视那种口称“宽恕”的人,在临死的 时候立遗嘱告诫亲属:“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甚至宣言对怨敌 “一个都不宽恕”。(注:鲁迅《死》,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第612页。)他的刻薄或苛刻,不管怎样,乃是实践了他的人格操守,尽管这 种人格操守对于每一个当事人都并不可爱。梁实秋则是一个以白璧德为榜样,以西式绅 士自许的人,他撰写文章表示要学习“绅士”的榜样,那便是“对于我们的敌人要如对 于好象是我们的朋友一般”。(注:梁实秋《绅士》,载《新月月刊》1928年第1卷,第 8期,“零星”第4页。)恰恰在宽容别人和善待对手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得最为差劲, 嘴上一套行动上又截然是另外一套,倘若白璧德有知,且白璧德也认他作自己的嫡传弟 子,那么这位哈佛老夫子一定非常失望,并一定会将他批评叔本华的话挪来批评这位梁 姓学子:这是“一个顽劣的家伙,他根本做不到自己所鼓吹的那些东西。”(注:
Donald MacCampbell,“Irving Babbitt,”in The Sewanee Review,April,1935.)
鲁迅的论敌们对鲁迅的攻击往往与“某籍”、“某系”相联结,梁实秋就曾在《关于 鲁迅》一书中讽刺其绍兴师爷的“刀笔吏”素质。而鲁迅对梁实秋的攻击甚至包括对学 衡派的批判都没有作这样广泛的株连,除了顺便讥讽了白璧德而外,他几乎从不提及他 们所由出的哈佛大学。哈佛仅仅是在与它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文人那里体现为一种心理情 结。作为他们这种哈佛情结的延伸,后来的子弟甚至总结出,分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和 革命文学运动中扮演重要反对派角色的恰恰是哈佛弟子,“包括梅光迪、吴宓、梁实秋 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对手”师承的又正是白璧德在美国的论敌,如胡适的老师 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如革命文学家欣赏的辛克莱。他还分析说,辛克莱的《拜金艺术》 (Mammon art)“这本书对白璧德的恶意攻讦,决不逊于鲁迅对梁实秋的谩骂”,又一次 将中美两对论敌划分成两个阵营。(注: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见梁实秋等 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9页。)这一番分析(特别是 将鲁迅同辛克莱处理成某种师承关系)虽然相当勉强,但特别有效地强调了哈佛大学此 一“系”对中国现代文化影响和作用的整体性。犀利苛刻的鲁迅没有抓住白璧德——学 衡派——梁实秋这一哈佛谱系及其在中国新文化运作中共同的反对派角色,那是因为他 从没有过他的论敌及其后继者所具有的那一番哈佛情结。
当然不单是信奉白璧德的哈佛学子才有这样的哈佛情结。曾公开表示对白璧德有所不 满的林语堂也有着同样强烈的哈佛情结。有学者分析说,林语堂“尽管从白璧德的影响 中获益较大,可还是不承认自己是白璧德门徒中的一个”,而只承认“白璧德仅仅是他 在哈佛的几个教授中的一个”,其原因盖在于白璧德未能获有博士学位。(注:OwenAldridge,“Irving Babbitt and Lin Yutang,”in Modern Age,Wilmington,Fall,199 9.)这样的说法将林语堂《八十自述》中的说法作了相当的夸大和曲折的引伸,林语堂 虽然说过白璧德是哈佛的那些教授中仅有的只获硕士学位的一个,但并没有轻视白璧德 的意思,相反,还对白璧德学识的渊博表示了由衷的尊敬。他之所以强调白璧德不过是 他所“从游的”诸多哈佛教授中的一个,原非为了贬低白璧德的分量。
上述中国现代作家对白璧德的推崇,不仅没有促进白璧德人文主义在中国流布或产生 深刻影响,相反,正是他们的特定角色、特有立场和特别的作派,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 界对白璧德人文主义作理性的分析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白璧德及 其人文主义几乎就带有学衡文士般的陈旧、梁实秋般的苛酷、还有林语堂般的狡智。这 样的印象对于白璧德学说显然并不公平,但白璧德思想既然是由这样一批作家充任传承 者,它的被误解、被搁置以及被排斥便注定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标签:梁实秋论文; 鲁迅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学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