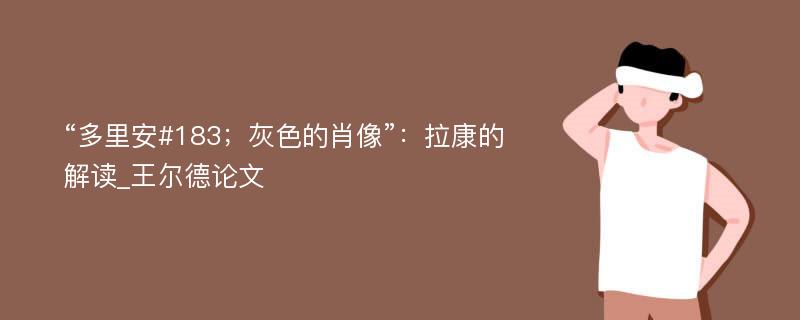
《道林#183;格雷的画像》:一种拉康式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像论文,格雷论文,道林论文,拉康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传世不多的唯美主义小说中的代表作。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为小说补写了序言来阐述他的创作观,这篇自序也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唯美主义文学的美学理想。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一个拉康(Jacques Lacan)式的深层结构,本文试着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阐释《道林·格雷的画像》,结合当时转型期的文化思潮,指出作品在“人”的塑造上是对西方文学“人”母题理解的深化。正如王尔德所言:“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认为的我个人的写照;亨利·勋爵在外界看来就是我;道连是我意愿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1]606 一、艺术与凝视 道林命运的转折,是从他看到画家巴西尔为自己画的肖像开始的。那一刻,他甚至没有理会画家和亨利勋爵的道谢与问话,“只在他的肖像面前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高兴得满面红晕,眼里闪出快活的光。”[2]69他继而顾影自怜,哀叹容颜易老,画像却青春永驻,并希望能够反转结局,将衰老转嫁画像,而青春留给自己,为此不惜出卖灵魂。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原则能够起到塑造“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所呈现的是一个不动的和连续的整体,并建构起一种完整的视像。这种视像与认为“存在”(being)是丰富的和同质的这一观念相符,能将观众塑造成一个先验的主体或想象中的统一体,并提供了一个有意向的客体,而这个客体既被它的观视主体的行为所暗示,也暗示着这个观视主体的行为。①这幅惊人的艺术杰作成功地诱惑了道林的凝视,使他“感到以前从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美在逐渐显露。”[2]69在拉康那,凝视是使观看变得可能/不可能的原因和机制,当观众在凝视的时候,其实已经携带并投射着自己的欲望进入一种镜像关系之中——将自我想象为他者,将他者指认为理想自我,而主体的建构就是从对想象中自我的指认开始。道林将画中像指认为自己,爱不释手,并坚持将画据为己有,他对于画像的狂热让巴西尔惊异,巴西尔以为道林终于开始欣赏起自己的艺术作品来了,道林对此的回答是:“欣赏吗?我是爱上它了,巴西尔,它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才是我的感觉。”[2]72道林因迷恋着画中像不能自拔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早在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暗示,靡菲斯特式的亨利勋爵从看到道林画像那一刻起就说:“他是一树水仙。”[2]48画像仿佛具有了魔力,这表现在:每当道林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时,画中的道林就日益变得面目可憎,而道林本人却青春依旧,此其一;其二,道林每次作恶后都会受到蛊惑性的力量影响去一窥画像的变化,尽管他对此感到惶恐不已。而在他印证这一变化后,尽管依旧恐惧与厌恶,却有一份欲罢不能的自足,仿佛他和画像之间的某种默契。根据文本的描述,发现画像变化的除了画家之外始终只有道林。直到道林死亡后,第三人才真正在场看到画像,而那时的画像又恢复往昔般韶秀俊美。这提供了一种解读路径:我们可以将画像的变化理解为一种隐喻,是道林在对艺术品的凝视中产生的幻想,是他出卖自己灵魂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是道林观念中的自我形象的变化在画像中的投影,“表面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跟他离开它时一样。那肮脏和恐怖显然是从内部透出来的。”[2]194他看画,也被画看,囿于看与被看的结构中。“看着那画的变化倒真有趣,它能让他深入自己的思想的底奥。这画会成为他一面最神奇的镜子。它已经向他揭示了他的外形,同样也能向他揭示他的灵魂。”[2]147我们还要注意到道林很快将画像搬进了抚养其成人但与他关系紧张的祖父用过的书房,那是一处道林不愿触及的地方,联系着他独特的身世与凄惨的童年。幽闭的空间、昏暗的光线、童年的某种创伤情境,这些因素正是诱发凝视的催化剂,因为当观视行为发生于一个幽暗的封闭空间,处于其中的观视主体,无论他是否意识得到(或者根本不去意识),都容易被视像俘获与征服。② 画家巴西尔是另一个看到画像变化的人,在道林第一次对变化的画像感到惴惴不安时,巴西尔已经有所预感,他闯进道林的住处,一是质问道林对其恋人西比尔之死的看法,二是坚持要看一看自己的杰作。在遭到道林苦苦哀求进而严词拒绝之后,巴西尔向道林坦露他创作的秘密:“我在画时每一笔色彩、每一层色彩都好像在揭示出我心里的秘密。我开始害怕,怕别人会知道了我的崇拜。道林,我觉得我已经表现得太多,放进了太多的自己。”[2]156那么画家的秘密是什么,崇拜的又是什么呢?“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你的美貌就对我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我的灵魂、头脑和力量都被你统治了。在我眼里你的美貌具体体现了还没有人见到过的理想,这种理想总像一个精美的梦似地跟随者艺术家们。我崇拜你,我想独占你……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也在我的艺术里。”[2]155这是与人告白,更是一份自我坦白,他已经成为道林之“美”的崇拜者,并借助艺术创作投射了理想自我——“每一幅带着感情作出的画都是画家的自画像……模特儿只是偶然的临时的东西。画家在色彩斑斓的画幅上揭示的与其说是模特儿,毋宁说是画家自己。”[2]51道林的青春容颜如精美的艺术品般诱惑了画家的凝视,画家在其中拓展着想象空间,并投射着自己的欲望。而画家在道林堕落后(两人在精神意义上的割裂),他的艺术生命也宣告终止。崇拜,除却虔诚之外也伴随着惶恐,那是一种理想自我破碎后的恐惧,打破了凝视与幻想的恐惧。因此,巴西尔对亨利勋爵的介入以及对道林的堕落引发的焦虑就可想而知了,他对还未曾见过道林的亨利哀求别把道林从身边夺走,在亨利和道林初次见面后便痛苦不已,倒在了沙发上。 对道林的命运产生影响的另一件艺术品就是亨利勋爵送给他的一本“黄皮书”。③书中的主人公玩世不恭、忧郁颓废的态度对道林有着致命的吸引,他仿佛是道林的倒影,延伸着道林的生命。道林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完成了对理想自我的另一次指认。在艺术与艺术品构成的“镜像”中,道林指认出了自己,他将自我一分为二,将自我当作客体来认识,这标志着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摆脱赤子(美少年)状态,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二、欲望与匮乏 艺术诱惑凝视,使主体逃离象征界进入想象界,并投射着自己的欲望,获得一种想象中的满足。但欲望总是指向不存在之物,指向永远的匮乏,它无法依靠现实的对象得到满足,“是不可能依靠结构上的必然性而被空虚之物充溢的。欲望指向的对象作为缺失者不在现实世界,但正因为它作为缺失而不存在,才被渴望。”[3]158因此,欲望在因寻找自身而不断置换着各种对象,或者说是欲望在寻找其对象的过程中得以维持。就像“能指的剑加在讲话的主体的肩上的标记。比起所指的纯粹激情来,它更是能指的纯粹行动。”[4]569换句话说,主体不断寻找其欲望对象,而这种寻找行为本身印证了欲望之不可得。 占有表象成为寻找欲望对象的最好注解。道林在被画像和黄皮书诱惑凝视后的人生轨迹就是不断占有美的表象的历程,他沉浸在唯美的艺术/艺术品中不断追寻欲望、占有表象,他也作为表象化的符号被他者占有。 王尔德曾说,“自恋是一生的浪漫故事的开端。”[5]489道林正是一树水仙,一个那喀索斯(Narcissus)式的人物。他的主体塑造始于发现自己的“美”:“好像是第一次认识了自己”;[2]69终于跌入“美”的深渊:“失去了美的外形……也就失去了一切。是你的画让我懂得了这一点的。”[2]70一生徘徊于混淆的影子与现实之间,“是他的美毁灭了他——他的美,还有他所祈祷的青春年少”。[2]259画像让他意识到自我之美,使他逐步开始对主体的建构,也使他以占有表象的方式来占有自我,当然那是一个虚幻的自我。他时常孩子气地模仿那喀索斯,“曾亲吻过(或是装着要亲吻)那此刻对他残忍地微笑着的嘴唇。他曾整个早晨地坐在那画前,凝视着它的美,有时觉得几乎爱上了它”。[2]147从此,道林与他者的联系,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也只剩下了表象。 道林对演员西比尔的迷恋,始终不曾指向西比尔本人,而是戏剧表演,是她在台上的一颦一笑与一招一式、行头打扮与美妙声音。道林指称西比尔的,也是剧中角色的名字,以至于他会为有人想在演出结束后介绍他认识西比尔而大发雷霆:“朱丽叶已经死了几百年,尸体还躺在维洛那一个大理石坟墓里。”[2]96他甚至将两人约会过程结构在剧本上:“罗瑟琳的双臂搂住了我,我亲吻了朱丽叶的嘴唇。”[2]118道林已经将西比尔牢牢地钉死在舞台与戏剧中,她不再是她自己,“西比尔”只是一个能指的符号。当西比尔坠入爱河,她选择演砸自己的角色以破坏戏剧舞台表演的规则,演得装模作样、矫揉造作,因为在她看来,这种令观众“出戏”的方式也能使她跳出道林所结构的莎士比亚式的“爱情戏剧”,可这对道林来说却是戳破了他的爱情表象,他大吼:“你杀死了我的爱情……现在你对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2]129西比尔因道林而死,道林为了抚平内心的愧疚,让巴西尔画一幅肖像作为纪念她的方式——他要把西比尔永远框在那镜像之中。道林所迷恋的只是爱情的表象与倒影、一道罗曼司程式,一旦戳破表象,爱情对他而言就不复存在,正如道林所言:“我从诗歌里找到了爱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找到了妻子。”[2]118后来,道林爱上了农村姑娘海蒂,初衷就在于她非常像西比尔,不过道林很快又抛弃了她。道林欢心地和亨利勋爵谈论他和海蒂的爱情,倒不是因为爱情的愉悦与悲伤,而是把这次经历当作一种行善的举动——在海蒂没有完全陷入爱情的时候离开她,“让她还像我见到她时那样美丽得像朵鲜花。”[2]249道林和海蒂之间的恋情又是一则“影恋”,首先是从相貌上,海蒂不过是西比尔的替身与影子;其次,他和海蒂的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初恋的搬演;再次,他把这次爱情的终结当作是一种“骑士行为”,是自己“行善的仪式”。道林再次心安理得地占有了恋人与爱情的表象,也是他自己“行善仪式”的表象——变得更可憎的画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本黄皮书的影响下,道林对表象的占有更加频繁。他一度对宗教与宗教服饰产生好奇,却又不正式接受任何信仰;他也学习过香料的制法,研究音乐与各式乐器并收集珠宝、手工艺品等等。“在他寻找新颖、愉快、具有离奇因素的感官刺激的时候,他常常要使用一些他明知与自己天性格格不入的思维模式,听任自己受到它们的微妙影响。而在抓住它们的色彩、满足了自己智力上的好奇心之后,便把它们随随便便地抛弃。”[2]171 占有表象本身并不能真正满足欲望,“并没有指向已被符号化的内容,而是阻止我们接近它,使人处于不可见的状态”。[6]109-110最能体现道林对表象占有欲的例证,莫过于占有艺术品的物质载体。道林专门请工匠把肖像装裱起来束之高阁,仅供自己观赏;他还从巴黎买来了黄皮书的大平装本九本之多,“把它们用不同的颜色装订起来,让它们跟他所喜欢的心情和他易变的天性里的种种幻想配合”。[2]167这是一种典型的恋物癖的表现,而恋物本身正是被掏空了的真实的填充物,最终只能印证欲望对象的匮乏。 如果说道林是迷恋自己倒影的那喀索斯,那么画家巴西尔和演员西比尔则处在迷恋那喀索斯的厄科(Echo)之位,他们分享的是爱的影子的影子,是自恋之爱的回声。于是,围绕道林和画像之间的故事也印证了另一关于“欲望”的精神分析式解读:凝视所投射的欲望永远是他者的欲望,即我欲望着他者的欲望。“凝视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是某个他人,因为我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他人凝视的对象。”[7]215凝视揭示了他人的存在对“我”的结构性功能,我“觉得”有某个他人在凝视着我,我在他人的凝视中发现了自己。这是看/被看、自我/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欲望的“他者化”是对欲望之匮乏的另一种注脚。 三、在场与缺席 道林不断在欲望能指之间游移、辗转,是他追寻欲望所指的努力与象征。根据上文所述,欲望对象始终是一种缺位,作为一种能指,指向“无”,指向永远消失的东西。欲望的结构中隐含了“存在/在场/满足”与“匮乏/缺席”的关系,“欲望是一种存在与匮乏的关系。确切地说,这一匮乏是存在的匮乏……存在就是据此而存在着”。[8]223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对欲望对象之在场的渴求同时也印证着欲望对象之缺席,这个一体两面的结构既是凝视存在的依据,也是对艺术的精神分析式注解:艺术占据了欲望对象的位置,却并非真正指向欲望,而是与欲望维持一种内在平衡,并分享着欲望对象的匮乏。于是,艺术审美是对主体凝视行为的“规训”,是“将凝视的目光变为一种了悟:了悟到欲望和匮乏的绝对”。[9]186它诱惑主体随时乘兴而来,又提醒主体适时尽兴而去,因为欲望永远在“别处”。 在此意义上我们便可重新审视道林之死。道林被艺术/艺术品所诱惑并产生凝视、投射欲望,即便对画像的变化感到无比惶恐,但仍不可遏制地甘愿被它捕获直至最后完全落网。道林对画像的变化感到不无得意的自足,并在自以为是的行善之举后去一窥画像的究竟——完全陷落在艺术/艺术品的“审判”之中。可以说,艺术诱惑凝视,令道林匍匐在艺术的“权杖”之下,将艺术指认为现实,混淆了缺席与在场之间的关系。道林陷落在艺术与现实、表象与真实、肉体与灵魂的多重镜像中不可自拔,由此建构了自恋/自卑的两位一体的主体意识。在此意义上,道林的死亡轨迹得以呈现:他试图越过缺席抵达在场,但抵达的只是“存在的匮乏”的情境。道林以为杀死自己的画像就能杀死过去获得彻底解脱,却打破了欲望与艺术之间的契约与平衡,他在刺向画像的同时杀死了自己,而画像却恢复了韶秀俊美。这是一个关于“谋杀/自杀”的隐喻:道林由于厌弃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而杀死一个想象中的他者/自我,这一戏剧化的刺杀行为,不啻一次仪式化的社会意义上的谋杀,同时也是一次想象中的自杀——借杀死他者/自我的同时宣布了所厌弃的“自我”的死亡,同时也是理想“自我”的新生,这是典型的镜像式心理症候、一次精神分析式的“死亡”。其实道林的死亡轨迹早在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道林与画像之间的关系始终被渲染上一层神秘、幽暗、恐怖的氛围。这种氛围表现在画像被“禁闭”着的幽暗空间、画像日益狰狞的面目,也表现在画家的偏执与对画像的觊觎,更表现在画像全知全能般对道林所作所为的“监控”与“审判”。尽管它处处不在场,却似乎又处处在场,使道林在想象中觉得有某个他者的凝视存在,有一道不可见的目光在引导与调节他对自己的“看”,从而被结构在“看与被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而这个他者的凝视却是被省略的,成为一种“全景敞视”视域,道林的恐惧感由此而来。这种被省略的凝视是一种潜在的权力,一种“符号化阉割”威胁,比现实性的威胁更可怕,“只有假借潜在恐吓,即是说,只有不充分行使权力,只有‘引而不发’,权力才真正发挥效力”。[6]119从另一方面看,画像作为“符号化阉割”威胁所发挥的功能,恰恰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抵达恐惧本身,因为它占据了恐惧客体的位置,从而消除了恐惧。因此,道林为了克服画像带来的诱惑/威胁而欲毁灭之,正是混淆了“在场与缺席”的边界。 画家巴西尔用自己的眼睛诱发了道林的凝视,并诱惑他试图越过缺席去抵达在场,这本是画家的“胜利”——他洞获某种“天机”,并向他人泄露“天机”。可惜画家为此付出代价并死于非命,死于他自己捕获的欲望对象之手。巴西尔和道林的死亡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相似的:道林是他的欲望对象,在道林身上,他维持着自己的欲望,分享着欲望与匮乏,这是他把道林视为他的理想与艺术生命的原因。当他去道林那强行窥视画像,追问道林的灵魂并努力加以感化,试图窥视表象后的真实,他也成了艺术与欲望的俘虏。尽管此时巴西尔还怀有某种天真的幻想,以为可以挽救道林的灵魂,但在道林看来,酿成他悲剧的元凶就是捕获他凝视的画家和他的杰作,道林选择了手起刀落,结束画家的生命。画家是另一个试图越过缺席抵达在场的以身涉险者,却死在了自己的欲望对象手中。 西比尔也曾困兽犹斗,她认为真爱把她的灵魂从囚牢里解放了出来,叫她“知道了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样子”。[2]128可惜她占有的“真爱”不过是道林的自恋之爱。她试图越过扮演的爱情之虚假程式而打破艺术与现实之间镜子,换来的只是破碎的水中花、镜中月,结束自己的生命似乎成了“最合理”的选择。在精神分析视野中,忘我的他恋与狂热的自恋内在地结构为一体两面,因为从恋人那获得的正是某种想象中的理想自我。在此意义上,疯狂的爱情神话总是潜伏着某种威胁:“就其内在结构而言,自恋之爱其实是一种欲望被爱。从爱的隐喻机制可以看出,自我如想成为被爱者,首先就得占据他人的位置,而占据他人的位置就是取而代之,就是置他人于死地,所以爱有时也是一种谋杀。”[10]57西比尔以为抵达了欲望在场,占有了爱情本身,却再次印证了爱情的匮乏。 欲望的在场与欲望对象的缺席,这是欲望本身的悖论,更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二律背反,“人的本心就是一个自身矛盾,因而是一种能动之源”。[11]41它说明了欲望的维持本质上是一种自欺,因此也就是一场“表演”。 四、表演与自由 一般认为,唯美主义主张追求艺术上的单纯的美感,即“为艺术而艺术”,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与表现力,而不太关注对“人”的理解和塑造。实际上,如果将《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人物形象置于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长廊中加以观照,可以发现其是对“人”的理解的深化,从而塑造了一种即将登上西方文学舞台中央的“新人”形象。就像王尔德的那句名言:“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5]348乍看之下,这段话表达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艺术观,不过如果结合文本与王尔德的现实生活方式来看,它倒一阵见血地指出了人生的“表演性”本质。这种“表演性”并不来源于自然,是无法纯然天成的,它源于“创造”,即人在自我意识支配下的人生体验,因为“一切体验都是对体验的体验,就像一个孩子把自己当做水仙花(或把水仙花当作自己)来体验,一个艺术家或欣赏家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角色作为自己的灵魂来体验一样。体验本身具有一种表演性结构。”[11]23王尔德认为:“一个人要么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拥有一件艺术品。”[5]488而在所有的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中,“唯有表演艺术最鲜明、最直接地体现了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即‘站出来生存’(Ekstase)……是最显现人的个体性、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艺术”。[11]215毋宁说,人生就是场一次性的表演,这种“表演”只有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特统合的人格之上,这正是文本通过道林的经历展现出来的。可以说,道林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品,也将自己变成了一件艺术品展示出来。如前所述,道林在“指认出”自己之前,只是一个(人格上)未长大的孩子,他没有“发现自己”,即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人格和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他对自我的认识是和他人“绑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林的人生还处在“混沌”状态,尽管那时的他纯洁得一尘不染。只有当他在艺术之美中发现了自己,才真正开始把人生当作了一件艺术,他的“欲望”、“疯狂”、“自欺”、“挣扎”、“忏悔”都是在表演着对人生的体验。正如他在与西比尔的恋爱中那夸张地形象化表现,对他来说,爱也是一种表演,一种痛苦却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艺术。他成了自我人生舞台中的“演员”,尽管还显“稚嫩”,却乐此不疲,并希望能够一直表演下去。他成了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即拥有了无限“可能性”(从这一点上说,道林颇似现实中装扮前卫大胆、举止特立独行的王尔德本人)。因此,对自由意志的“表演性”本质的形象揭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人之“主体性”认识之上的。 文本对于“人”的理解与生命体验的揭示并不局限于此,它更预示了一种“新人”形象的诞生。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准则看,作为“艺术家”的道林绝非一个正人君子,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作为亨利勋爵的信徒,他倡导的是反清教徒主义的享乐主义生活,也正因此,《道林·格雷的画像》也被斥为“邪书”,遭到猛烈抨击(这也符合王尔德倡导的,文学的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无关)。从道林的角度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自身自由意志之“逻辑”的,目的是建立新的“生活纲领”,把生活打造成“最伟大的艺术”,成为真正自由的“表演者”。道林(或亨利)不是用其他外在标准来衡量自身自由意志的善与恶,相反是用自由意志去衡量一切道德、善恶的真与假,由此,他将自由意志上升为自律。但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自律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自由,当“发现了自己”的道林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开始“自由表演”之后,常常挣扎在灵与肉、堕落与忏悔、自省与自欺的漩涡中。道林的挣扎和陷落,是其自由意志之逻辑发展的必然:当他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工具,他就是对自由的否定,反过来也就剥夺了自己的自由,这就陷入到“他人即是地狱”的困境中去了。道林与他人相互剥夺“自由感”在文本中呈现为:道林被巴西尔欲望,他在巴西尔的凝视中发现了自己;道林欲望着亨利勋爵的欲望,他欲望成为亨利欲望的对象——“当我们自以为在别人身上做实验时,实验正做在我们自己身上”;[2]102巴西尔和亨利欲望着被道林的欲望所承认——亨利试图从巴西尔手中抢走道林并改变他,而巴西尔在表达对道林的崇拜后表示,“本来就不是为了赞美你。那是一种自白。我作了自白之后它似乎就离开了我。”[2]157这些相互制约而又依赖的关系网是道林和其他几个主人公常常感到苦闷的原因。如果说“表演艺术是唯一没有艺术品、只有艺术本身的艺术,是唯一完全摆脱“在者”而只体现“此在”的艺术,也是唯一与艺术家本人直接同一、永远必须从艺术家自身的角度对之加以评价的艺术”。[11]215那么能够在表演的同时对自己“此在”的表演作出评价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对于道林来说,他恰恰体会到了自我的“分裂”——作为“表演的我”与“评价的我”的分裂。那逐渐衰朽的画像仿佛在不断地提醒着道林的自由意志与行动的后果,它是对道林这个“艺术家”的表演进行评价的自我之化身,就像他不由自主地去画像那验证行动的结果那样。而道林本人和自己画中象的相貌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他对于自己的画像嗤之以鼻乃至日渐恐惧,只有当其死亡(自由意志消逝)以后,肖像又恢复如初,这不啻作为一个失去了“自由感”的“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与异化的形象表达。因此,道林的形象正是近代晚期以来西方文学开始呈现的逐渐分裂的“人”的形象的新序列,也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极力描绘的自我撕扯的“现代人”的雏形。作为一个处在世纪末门槛上的作者,《道林·格雷的画像》对于近代以来“人”的自我分裂与生存境遇的异化的表达是敏感且深刻的,既超越了古板的维多利亚风格,又合乎当时正在转型中的西方社会思潮。 诚如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序言中所言:“艺术这面镜子反映的是照镜者,而不是生活。”③文本结构裂隙处的“凝视”、“欲望”与“自恋”等“路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论的解读路径。作品对美的迷恋、对艺术的崇拜以及颓废主义的生活态度都体现了王尔德式唯美主义的美学理想,回答了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作品对“人”的矛盾与悖论的揭示是站在西方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人”的母题的延伸,这种人文意蕴是不能忽视的。 ①②参见Jean-Louis Baudry.Ideological Effects of the Basic Cinematographic Apparatus[J].Alan Williams,trans.The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28.2(1974-1975):39-47. ③这本没有被王尔德点明的书乃是法国作家若里斯·于伊斯芒斯(Joris-Karl Huysmans)所写的《逆反》(ARebours,1884),此书对王尔德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参见[英]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序言),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标签:王尔德论文; 道林·格雷的画像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自由意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