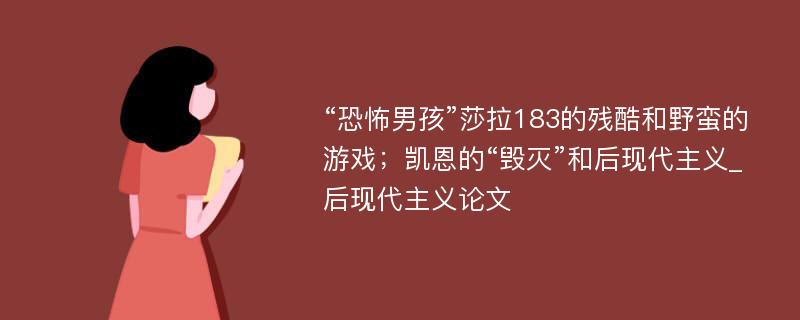
“惊骇小子”残酷而又野蛮的游戏——萨拉#183;凯恩的《摧毁》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惊骇论文,萨拉论文,野蛮论文,凯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萨拉·凯恩(Sarah Kane,1971—1999)被誉为当代英国剧坛的“惊骇小子”,她以其惊世骇俗的《摧毁》初登剧坛之后,立刻就在英国戏剧界、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四部戏剧《菲德拉的爱》、《清洗》、《渴求》和《4.48精神崩溃》也相继引起震动。戴维·格雷戈认为,萨拉·凯恩这五部戏剧由于剧作本身“极具爆发性的戏剧张力、抒情的诗意、激越的情感和悲凉的幽默”(《萨拉·凯恩戏剧集》“导言”1—2),成为后现代主义戏剧的范本。可以看到,萨拉·凯恩的这五部戏剧在直面戏剧和野蛮戏剧的表现方式下,无论在内容还是戏剧形式上,已经与现实主义戏剧彻底拉开了距离,并以后现代戏剧的认知进一步颠覆了人们对戏剧的认识。处女作《摧毁》尤其以主体性戏剧美学的衰落和碎片式的寓言,以及“性叙事”身体描摹的政治化,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戏剧的批判魅力。为了深入认识萨拉·凯恩的戏剧,我们有必要对《摧毁》进行深入解析,并通过该剧进一步厘清萨拉·凯恩戏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观照当代戏剧的美学倾向。 一、摧毁与建构:人性的普遍存在 《摧毁》之所以被誉为后现代主义戏剧,是因为该剧与“后现代主义一样是政治的”(胡全生6)。“话语、权力、权威和伦理”问题是后现代主义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胡全生6),也是《摧毁》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摧毁》以其当代政治的身体映射,使充满色情欲望的性行动成为政治隐喻的后现代投射。在《摧毁》中,戏剧叙事顺应时空逻辑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被悬置”(易杰16),但故事情节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支离破碎。剧本因此颠覆了所谓的真理性,“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Eagleton vii),以彰显小人物猥琐而可悲、可叹的困境,达到批判权力、暴力、战争中强奸暴行的目的。该剧的内容以色情、暴力、血腥、恐怖、恶心而著称,却以这一大胆的怀疑精神和不留情面的批判意识,对“普适性形而上的人性、情感”(王琼139—42)进行自我拷问,揭露出后现代社会政治机体与自然身体的缺陷,颠覆了宏大叙事建构的美好、爱情、善良等虚伪概念。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杰姆逊211)。《摧毁》通过建构这一从封闭到开放的暴力环境,拉近了舞台与社会的距离,对波黑战争强奸集中营中妇女所受到的暴力摧残给予关注(Saunders 48)。《摧毁》通过主体与他者、异性与同性之间的纠葛与强迫,以政治化的“性虐待”、“性暴力”隐喻人类精神的幻灭,以及残存的自我救赎希望。舞台上的《摧毁》有着后现代的真实化效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来,世界的非理性、人的非人性不再是不合理的,理性与合理仅仅成为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奢想。但在深入解读后,可以发现萨拉·凯恩虽持有后现代戏剧理念,但其叙事的落脚点仍然在于“关注人普遍的存在状态和死亡”(易杰5)。《摧毁》以性和暴力的呈现与批判为靶子,揭示了人们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迷惘、绝望和矛盾,显示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战争与暴力时的无望与无助。在萨拉·凯恩戏剧里绝望畸形的性虐行为之下,在剧作者惊世骇俗的背后,是凯恩通过“对本能、冲动和意志的解放”(凯尔纳17)来建构理想的希冀,舍弃绝望,放弃暴力与战争,关注人类生存。正如胡开奇所认为的,萨拉·凯恩以性为切入点,“她关注当代社会与人类的悲悯情怀,体现了她在信念上的坚持与执着,也体现了她创作风格上的多样与艺术表现上的创新”(《萨拉·凯恩与“直面戏剧”》303)。 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戏剧不同,后现代主义戏剧没有一个内涵确定、清晰的概念,但“直面戏剧”、“残酷戏剧”所显示的内容与形式却清晰地体现了后现代戏剧的基本特征,《摧残》正是以直面和残酷而著称。“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利奥塔46)。以这一说法来衡量《摧毁》,我们就会明白通过该剧中的性与暴力叙事,当下看待人类和世界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扭转。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而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人却并非如此。《摧毁》一剧表明,在后现代社会,因为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商品社会的特点,贫困并不是使人潦倒、堕落和羸弱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反而是在富足和现代商品经济的表象下,人们在心理上的羸弱、人格的堕落和行为上的非人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潦倒和绝望,即主体的消亡、混乱、颠倒构成了《摧毁》的后现代主义戏剧特征。《摧毁》就以其直面和残酷,呈现了超出个人心理经验的后现代叙事,深刻而强烈。《摧毁》打破了读者戏剧欣赏的期待视野,使观众不断感到作品在直面、残酷中的冷静与出奇制胜的力量。对于性的直面、性暴力的残酷、性虐待下人格的分裂与被摧毁,萨拉·凯恩在《摧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策略就是嘲弄“人”的主体地位,颠覆“历史”的必然性逻辑(陈晓明27)。《摧毁》不但反复嘲弄“人”的主体地位,而且人已经在性、权力、暴力、战争面前被彻底异化了。对于《摧毁》,凯恩这样表述她的美学思想:“所有好的艺术都具有颠覆性,或是形式或是内容。最好的艺术是形式和内容都具有颠覆性。而作品中最令审查者们大怒的则是它的形式……我推测,如果《摧毁》是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话,它不会受到如此严酷的责难”(转引自《萨拉·凯恩与“直面戏剧”》291)。在形式上,全剧毫无顾忌地通过肉身展示了性虐待、性暴力的全过程,剧中的“对话粗鲁不堪”,极其简短,“情景淫秽无定”(289),没有抒情描写,只有性与暴力一览无余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却反而促使观众意识到了这个“现代寓言”(292)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无情嘲弄、精神戕害,以及强烈的警醒、批判意义。例如,士兵毫无顾忌地描述他在战争中的犯罪: 冲进城外的一户人家房子里。人都逃光了,只有一个小男孩躲在屋角。一个哥们把他拖出屋去,推倒在地上,用枪扫射他的双腿。我听到地下室的哭声,冲了下去,里边躲着三个男人四个女人。我把哥们叫来。他们按住男人,我一个挨一个操那些女人。最小的才12岁。她没哭,就躺在那儿。把她身子翻过来就——。(凯恩44—45) 权力在奴役着人,主宰了人的身体,嘲弄着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使人失掉了自我,而主体究其实质则是权力的奴役。凯特、伊安被奴役是导致主体迷信的深层动因。在《摧毁》中,性变态、权力与暴力如影随形,粗暴地展示了“个人的疯狂经验”(杰姆逊111)。《摧毁》的叙事显示出,“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杰姆逊162),但在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和暴力面前都结束了。施暴者手中的枪和战争就是权力,是实施暴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象征。在这里并不存在“能够在合法使用权力与非法使用权力之间作出规范性区分的批判理论来调和”(朱立元747)的程序,一切以战争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喜好为转移。 如果我们给《摧毁》拟订一组涉及后现代社会的关键词,这就是:种族歧视、性歧视、同性恋、吸毒、暴力、战争、死亡的“爱与残忍相互交织”。在凯恩创作的过程中,战争恐怖控制着她的思维,她说:“对我而言,这是唯一能写的主题。它是人们商对的最迫切的主题。”(《萨拉·凯恩与“直面戏剧”》)《摧毁》对战争和暴力的残酷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在形式上,《摧毁》对戏剧内容和形式本身进行质疑、颠覆、解构与反叛;在内容上,突出表演,追求偶然、发挥即兴的表演效果;运用混杂、拼贴等手法,并以身体为一种具有渗透性的载体,再现身体如何“最终被禁锢在性别登记制与强制性的双性恋文化场的实践活动中……通过特别的话语被强制性地生产出来”(朱立元920)。凯恩期望借此达到批判的目的,但由于这一批判建构于性的直面和残酷展示上,因而并不能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宽容和理解,该剧引起西方戏剧界的哗然与惊骇也就在所难免。 三、自然主义与寓言叙事 后现代戏剧强调在精神领域内对社会的深入批判,其中包括对商品化了的文化与消费社会的深入反思与拒斥。在后现代社会“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杰姆逊162),但知识分子仍然对这种大众化、通俗化乃至庸俗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摧毁》的后现代美学旨趣“是指向通俗的,它注定要把那些‘可表现的事物’突显出来”,对世界和人生竭力进行反讽和戏拟,“对周围的一切均表现得冷漠和无动于衷”(王宁6),以此达到批判目的,并以文本的颠覆、舞台的残酷性和颠覆诗意表现社会与生活的残酷。《摧毁》在结构上,“前半为自然主义手法,后半则突转为象征及怪诞梦魇般的风格”(胡开奇,《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在该剧中,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些“原来美学范畴中的传统理论、判断以及推理从后现代主义中消失了”(利奥塔105),通过对世界的反讽、戏拟,通过后现代的无中心和意义游移,使观众看到了一种新戏剧内容的呈现及其新形式。尽管如此,我们在萨拉·凯恩颠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戏剧手法背后,仍然能够依稀感受到《摧毁》“是关于爱、生存和希望”(Saunders 26)的曲折表述。但是“凯恩戏剧中爱的概念超越了我们熟悉的爱情、亲情、友情,甚至爱欲的模式,表现出来的‘另类’情感具有隐喻的特征,探究的是在人类彻底超出了理性阈限,文化约束的情景下,真诚与爱成为人类自我救赎的可能性”(邱佳岭75—79)。在《摧毁》的性暴力内容和形式之下,作者仍然把眼光聚焦于当下社会中的人与人性,尽管戏剧美学范畴中的传统内容、叙事方式已经被颠覆了,但其批判锋芒与认识价值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使人们认识到在商品、经济交易背后被遮蔽的人的原始羞耻感。所以,萨拉·凯恩反复强调要真实。萨拉·凯恩在对一位排演《摧毁》的导演宣称:“凯特在晚上被强奸了……你不认为她应该,比如说把自己盖上……这只是与在任何时候的真实有关。”(qtd.in Saunders 26)即权力之下的性引诱、性暴力、性变态、性反抗应该以其真实的舞台呈现方式,去隐喻人在性暴力胁迫之下的本能反应。这种真实与舞台噱头是格格不入的,真实通过伊安与凯特之间特殊的性关系,作了“无为有时有还无”的人性呼唤。按照福柯的说法,“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转引自朱立元747)。在《摧毁》中,性究其本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成为引发权力压迫和暴力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处于性这个中间层面,在性之上是第一层面的权力压迫,而在性之下则是第三层面的暴力迫害。我们看到从第三场开始,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方位出现了跨越性的映射,在轮回的春、夏、秋、冬不间断的雨水中,战争中的暴力、强奸、同性恋、挖吃眼珠、吞吃死婴等场面交替出现,呈现出后现代戏剧叙事身体与政治的残酷与直面特征。观众看到的是,在权力和暴力胁迫下人对赤裸裸的“性”的无条件服从和毫无遮拦的展示,剧作家把“性”毫不回避、毫不掩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摧毁》给观众留下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中“性”预设的“政治”隐喻,也就无法解释该剧后半部分的寓言性叙事了。在剧中: 伊安(低头看自己的衣服。然后起身,脱掉全身衣服站在她面前,赤裸裸的。) [ 凯特瞪着他。然后笑起来。 伊安 不愿意?好。嫌我臭?凯特笑得更厉害。](11—12) 伊安把一只手插到她怀里摸着她的双乳。……凯特 我吻—吻—吻了你,只能这样。我喜—喜—喜欢你。(18) 在此,一系列性的叙事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政治信息,揭示了权力和暴力的无所不在,性的隐喻已经不单纯存在于两性之间,女性成为政治权力、性暴力、战争与占领施虐的对象,情节已不重要,而呈现的场景则是惊世骇俗的。在这里,情节的连缀,意象的表达,情绪的点染,通过性虐待被置换与戏仿。后现代叙事在性、权力、暴力的语境中构成了当下社会、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人与人性的“摧毁”。虽然后现代戏剧有时表现为嘻嘻闹闹,在《摧毁》中也是如此,但有时却在这种性嬉闹中隐藏了残酷的现实。在所谓真实的外表之下,《摧毁》在内容的表现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戏剧内容,不管是其中自然主义的描写,还是寓言式的拼贴,在代青体之外,凯恩在文本上为代言体的内容设置了大量动作性、心理性的叙事,而强烈的动作性恰恰构成了诗意被颠覆、情节被悬置的一种主要呈现方式,这既是作者与隐含作者对代言体动作的强化,也是观众通过代言体的表演,所看到的人物心理、情感被扭曲的现实。“后现代主义者追求一种欲望政治,艺术和欲望成了根本性的政治关怀和政治策略”(凯尔纳370),这甚至是《摧毁》文本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部分。人物的行动、心态、心理及隐含作者均在这里现身。如果说,《摧毁》在颠覆传统戏剧表现内容的同时,通过与传统戏剧表现方式截然相反的叙事,以寓言式的呈现,以对性、暴力、死亡的想象,为观众营造出被撕下现代化商品面纱后的后现代社会,那么,人性的变异动作性、心理性的叙事,既对代言体的表演者进行了强调,又自然成为代言体表演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摧毁》的文本中我们看到,形式上,《摧毁》中的圆括号为舞台提示,起着提示台词的作用,方括号中的词句不作台词,用于文本阐述,二者分别说明人物动作及心态和描述环境,如果离开了作者的“提示”和“阐述”,无论是导演还是读者都会陷入猜谜的境地。这就是说,无论是圆括号还是方括号内的文字,均特别对人物的动作、心理、情节发展给予了明确说明,显示出作者直面和残酷的写作态度。显然,在伊安与凯特的二人世界里,“我”与“他者”不仅仅是只有“我”才为主体,“我”与“他者”互为主体,互为台词与舞台提示、文本阐述,“我”与“他者”均为战争和暴力的牺牲品,以及作者创作意图的体现。尽管萨拉·凯恩对于性的描写有自然主义的成分,但仍然意在通过寓言勾画出现实的残酷之“真”,她着力呈现给观众的是“原封不动”的拼贴战争和暴力的“真”。在她看来,尽管这种“真”经过作者的过滤和淘洗,但仍然是毫不遮掩和赤裸裸的。西方戏剧追求纯粹的再现和表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事物的精神。《摧毁》中的“真”是一种直面而残酷的展示,例如:“伊安用枪对着凯特的头,掰开她双腿身体压上去……凯特大叫一声猛地坐起来”(29),“伊安高潮时的狂喜的呼叫突然变为一声痛楚的惨嚎”(32—33)。 后现代主义者对世界和人生竭力进行反讽和戏拟,对周围的一切均表现得冷漠和无动于衷;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自我意识是模糊的,其特征表现为主体的失落,对自我本质的探索也没有明确目的,“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倾向愈益明显(王宁6—7)。在《摧毁》中,这种赤裸裸的性叙事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动作,也因而具有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寓言式的叙事,已经显示出后现代社会对人生的反讽和戏拟。《摧毁》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戏剧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已经和寓言式的戏剧叙事一起,成为一种精神建构或手段模式。它以这种特殊的语言和特殊的文学代码,深刻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实”(佛克马5)。如此毫不遮掩地在舞台上展示性和暴力,除了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之外,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摧毁》中的“性”和“暴力”仅仅表明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现象,而隐藏在这一现象之下的则是普遍的精神扭曲和战争中人性的异化。例如:“可是当门外响起了奇怪的敲门声,一位端着自动步枪的士兵轻而易举推开门缴了伊安的枪。”(凯恩38)而士兵则描述了一幅更为恐怖的场景:“冲进城外的一户人家房子里。人都逃光了,只有一个小男孩躲在屋角。一个哥们把他拖出屋去,推倒在地上,用枪扫射他的双腿。”(45)人性的癫狂表现为非人性,并贮存于人的内心之中,在极端的环境中,爆发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士兵把嘴贴在伊安的一只眼睛上,吸出眼珠,咬下来吃了下去。”(51)“上帝存在没有理由只是有比没有好。”(56)“伊安吃着死婴。”(61)在《摧毁》中我们看到性与暴力总是随着权力膨胀起来,如影随形,正像权力无所不在,性、暴力、死亡、战争也无所不在。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清晰地认识《摧毁》后现代本质的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拨开后现代社会的商品、消费和现代化的繁荣之后,滤去感官挑逗的意味,所看到的是一幅更为真实、几近绝望的性暴力实施空间隐喻下的社会政治图景。我们可以这样说,萨拉·凯恩的戏剧与后现代社会的诸种特征息息相关,也是后现代社会战争与暴力无处不在的真实写照,即表现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凯尔纳164),体现出经验空间中的精神堕落与绝望。从凯恩的《摧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直觉或纯粹的精神表现。它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已经揭去了温情的面纱和人们浪漫的幻想,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和对整个世界的彻底绝望,摧毁的是虚伪的和平、爱与善良。 四、结语 《摧毁》覆盖的这一组关键词,构成了直面残酷人生和邪恶人性的“直面与残酷的戏剧”。该剧在“人所能想象的最低下的境遇”(Saunders 68)中,以反抗原意义中心、彰显新意义的自然主义手法和寓言式的“双连环结构”,冷漠地颠覆了传统理性的人文情怀,以性暴力迫害中施害者、受害者双方的心理体验来建构戏剧的张力。它“是暴力,是强奸,是在相知并显然相爱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萨拉·凯恩与“直面戏剧”》288);同时《摧毁》又以象征及怪诞梦魇般的风格,展现了后现代社会里饮食男女对性的态度,性和战争即权力和暴力。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认识,显然还不足以回答《摧毁》的深层意义。通过性叙事,《摧毁》以后现代社会的冷静觉悟呈现出来的是不安定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是人类社会目前尚没有解决的面对权力、暴力、战争等多种问题的困惑与无奈。《摧毁》赋予“性”某种独特的仪式,这是作家对受伤心理、政治厌恶的自我的救赎,也是对简净纯粹心境的皈依,从而在更深层意义上认识到后现代的某种绝望感。如何真实而客观地在戏剧舞台上展示性,这个难题不仅对导演、演员来说是一种实际而严苛的考验,对每一位观众和读者来说也是值得深思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