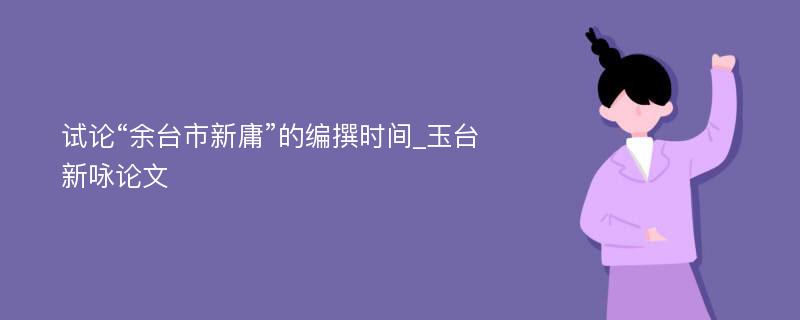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玉台新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3-0053-09
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兴膳宏教授和中国学者沈玉成教授、刘跃进教授为代表。(注:参见兴膳宏教授《〈玉台新咏〉成书考》,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沈玉成教授《宫体诗与玉台新咏》,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刘跃进教授《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载《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刘跃进教授新出有《玉台新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兴膳宏文章发表较早,1985年介绍到中国,沈玉成文章发表于1988年,二人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即《玉台新咏》一书编成于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二文论证详实,令人十分信服。但对这个观点,刘跃进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一文,却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根据版本调查的结果,认为兴膳宏仅据寒山赵氏复宋本所得结论并不可靠,因此提出《玉台新咏》可能编成于陈代,而非梁武帝时的中大通六年。笔者详考史料,并对各家所论重新调查,结论与兴膳宏、沈玉成先生基本一致;同时对《玉台新咏》相关的版本也都作过调查分析,对陈玉父本系统和明代通行本如郑玄抚、徐学谟等刻本系统也作过认真的比较,所得结论与刘跃进教授不尽相同,故认为这个问题仍有再讨论的必要。不过本文拟就《玉台新咏》的编辑时间作专题讨论,关于刘跃进教授的意见,将在《论〈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和《玉台新咏版本考订》中再作论述,但本文如有涉及之处,亦随作辨正。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和编辑体例论证该书编成于梁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一、从《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看编纂的时间
有关《玉台新咏》编辑时间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据此可以知道《玉台新咏》的编辑是在萧纲为太子的时候。除了这个记载以外,生活于天宝年间的李康成也说过类似的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其《玉台后集序》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目前学者基本都接受这个说法,但对萧纲晚年是否追悔,故命徐陵编书“以大其体”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今日流传的各本《玉台新咏》,题衔都有“陈尚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字样,似表明此书编于陈时,但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殆后人之所追改”,明崇祯六年(1633)寒山赵氏复宋陈玉父本《玉台新咏》,于简文帝萧纲题称“皇太子”,元帝萧绎题“湘东王”,可以证明。那么李康成、刘肃等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呢?如果可信,《玉台新咏》又编成于萧纲任太子时的哪一年呢?我们认为,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本书的编辑目的和编辑体例来说明,因为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不管承认不承认《玉台新咏》“大其体”的说法,它是一部艳体诗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简文帝写作艳体诗,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大家都熟知《隋书·经籍志》的论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又《梁书·简文帝纪》亦记他:“及居监抚,多所弘宥,文案簿领,纤毫不可欺。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些记载都表明萧纲的艳体诗发生在他作太子之时。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曹道衡、沈玉成师《南北朝文学史》考证,艳体之风,早在萧纲年少时就已形成,而对他造成影响的是徐摛和庾肩吾。[1](P237-241)据《梁书·徐摛传》载,萧纲出戍石头时,萧衍为他简选侍读之士,因周捨推荐,徐摛入萧纲幕府,其时是天监八年(509),萧纲七岁。从此以后,徐摛基本上一直随侍萧纲。《梁书》本传记:“后(晋安)王出镇江州,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又转平西府中记室。王移镇京口,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以母忧去职。王为丹阳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这可以看出徐摛与萧纲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萧纲受徐摛的影响是很深的。此外,庾肩吾也在天监五年入晋安王府[2](P372),任国常待,晋安王每一徙镇,庾肩吾亦常随府,他与徐摛一起都对萧纲写作造成了影响。徐、庾二人为文均好新变,如《徐摛传》就说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所谓“新变”,也就是艳体。本传又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是指萧纲入东宫以后的事,其实在此之前,萧纲的艳体诗风在徐、庾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徐摛既作艳体,当然会影响到萧纲,萧纲在七岁时就以徐摛为侍读,这个年龄正是学诗的时候,萧纲自己后来曾说:“余七岁有诗癖”[3](P109),正是指此而言。因此萧纲的写作艳诗,是长时间的事了。但正式形成一种诗风,恐还要到他镇雍州时。《梁书·庾肩吾传》说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高斋学士群的形成,说明了这种影响。
以上的事实表明萧纲从七、八岁时就已在徐、庾指导下写作艳体诗,从天监八年到中大通三年(531)入东宫之前,他一直在自己的幕府中写作并引导着这种诗风,与他不同,这时的京城内却由太子萧统提倡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诗风,即雍容闲和,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诗风。[4]萧纲对乃兄所提倡的诗风表达过什么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他们兄弟二人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差异是一个事实。在传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统写给湘东王萧绎的信,那是萧绎向他索要《古今诗苑英华》后写的回信,也正是在这封信中,萧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这说明萧绎一直关注着萧统的文学主张和京城内正在开展的文学创作。但同是诸王的萧纲却似乎没有对乃兄表示什么意见,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萧纲与萧统讨论文学的话题,也没有他向萧统索要《古今诗苑英华》以及其他萧统正在编辑的文集的信件,这个事实是否说明萧纲对萧统所提倡的文风并不十分赞成呢?当然仅仅根据这个材料得出这个结论,未免武断,但结合他中大通三年进京后不久写给湘东王的信,直斥“京师文体”的事实,再考虑这个结论,就觉得比较合于情理了。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病逝,萧纲继立为太子,这对他来说是飞来之福。因为,按照惯例,萧统卒后,本应立萧统的儿子萧欢,但萧衍却一反常例,废嫡立庶,让萧纲继位太子。这也许有萧衍的考虑,但却带来了萧统诸子们的不满,从而为日后的政治斗争带来了麻烦。事实上随着萧纲进入东宫,诸皇子之间顿时产生了非分之想。《资治通鉴》》卷一五九记载:“上(武帝)年高,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纶为丹杨尹,湘东王绎在江州,武陵王纪在益州,皆权侔人主;太子纲恶之,常选精兵以卫东宫。”这是中大同元年(546)间事,但积痈养疴,非一日所成,这一切都是因萧衍破坏常规带来的恶果。不管怎么说,这对萧纲说来总是好事,他也因此而踌躇满志。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太子之位有点不合正理,所以他要树立自己的形象,这也是他甫入京师,立刻就推广新诗风的原因。《梁书·庾肩吾传》说:“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转拘声韵,弥为丽靡”,既说明了这种诗风的影响,也说明了萧纲等人有意为之的行为。就在这个记载之后,同传记载了萧纲写给湘东王的信。这是一封公开发表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献,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要改变京师旧有的文风。他说:“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这个京师文体何指呢?我们认为,很清楚是指萧统所提倡的“丽而不淫,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5](P3064)文风。有趣的是,萧统和萧纲兄弟二人在作太子时所要发布的文学主张,都是通过给湘东王萧绎写信来完成的。
从以上叙述看,萧纲的艳体诗风形成时间较长,随着他被立为太子,他以这一诗风与故太子萧统提倡的诗风相抗衡,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是有着很深沉的考虑的。昭明太子在天监、普通年间提倡并形成了一种文风,还编成了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在这种情况下,萧纲要编一部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品选集,也是在其计划中的了,这大概就是萧纲编辑《玉台新咏》最初的目的。
根据这个目的,萧纲所要编辑作品集,应该是宫体诗,应该是以萧纲为中心的宫体诗人作品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玉台新咏》并非如此,而是上从西汉以来的历代有关妇女题材的诗歌。其实这个编法与萧纲等新变派诗人的诗歌观并不相符,因为宫体诗人对古体肯定不多,所谓“新歌自作曲,旧瑟不须调”[6](P53),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更明确说:“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这都是对前人作品表示不以为然。既然如此,为什么徐陵编辑《玉台新咏》要选录那么多古人的作品呢?根据明崇祯年间寒山赵氏覆宋陈玉父本,《玉台新咏》前三卷基本是魏晋作家作品(注:赵氏本卷三还录有刘宋时荀昶、王微、谢惠连、刘铄的作品,这不如明嘉靖间徐学谟海曙楼刊本全录魏晋作家合理。赵氏本有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后人刊刻时分卷的原因所致。),卷四是宋、齐作家作品,卷五至卷八全部是梁朝作家作品,卷九是历代杂歌,所录汉魏晋古歌及作家作品三十馀首,卷十录历代绝句、短制一百五十馀首,尽管重今轻古的倾向非常明显,但古代作品的分量还是很可观的。《玉台新咏》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刘肃关于“大其体”的说法,似乎是有依据的。据兴膳宏教授介绍,铃木虎雄曾提出《玉台新咏》可能是两个阶段成立的:最初只收梁代作品,而后将梁以前诸代的作品追加上去。对这个观点,兴膳宏教授表示不同意,但根据前文揭示的原因,我们以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大其体”的原因,是否因为萧纲后悔写作艳情的题材呢?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原因是,萧纲的父亲萧衍对他写作艳情并不满意。《梁书·徐摛传》有一则记载引起我们的注意:“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从这个记载看,徐摛被责是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后,而且是“宫体诗”已经产生了影响的时候,但实际上就在中大通三年,徐摛便因朱异的谗言而被外放为新安太守,这时恐“宫体”诗风还未来得及实行,更谈不上影响了。但是徐摛的外放,仍然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徐摛一直都追随着萧纲,担负着教导萧纲的责任,能够跟随这么长时间,除了说明萧纲对他的信任外,也说明萧衍对他的信任。古代帝王对于外放诸王的监督是很严厉的,诸王身边的人言行稍有不谨,马上就会受到处分。如果说萧衍不满于他教导萧纲写艳体诗,事实上这种诗风在萧纲七、八岁时就由徐摛传授于他了,萧衍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说明是认可了的。按照常理,萧纲继任太子,又对昭明太子诸子造成了伤害,因而政治矛盾激烈的时候,萧纲更需要得到徐摛的辅助,但就在这时萧衍却把他调离了萧纲身边,如果不是有很必要的理由,萧衍恐怕不会这样做的。尤其是这一次调离时间还比较长,自中大通三年外调新安太守,直到中大通六年萧绎撰《法宝联璧序》时,仍署“新安太守”衔,本传说他“秩满”才又调回为中庶子。结合前引徐摛本传的说法,我们以为,萧衍很可能就是从文风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情的。因为萧纲在雍府时,位为藩王,他从事艳体写作,在政治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当他继位太子,为一国之储君,太子在位养德,就不适合以艳情相煽了。尤其是萧纲的太子之位的确定,已经破坏了礼制,造成了诸王间的混乱(后来萧绎萌发野心,未尝不是在这个礼制的破坏中得到的启发),因此萧衍对萧纲身为太子还要写作艳诗,未免恼怒,而采取了将徐摛外调的措施。有一则材料可以作这种说法的佐证,《资治通鉴》卷一六二载侯景幽禁武帝之后,曾上书批评武帝,有一个内容便是指责他纵容太子萧纲写作艳情诗之事:“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虽然侯景意在纂逆,但从中也可见出当时朝野对萧纲的宫体诗风是有非议的。作为太子的萧纲对他父亲把徐摛从他身边调开,当然非常了解其政治意义,因此让徐陵编一部“大其体”的《玉台新咏》,表示这一题材的历史渊源。同时,对于徐摛,他是非常感恩的,但对他父亲的旨意,却也无可奈何,因此让徐陵编辑此书,也许含有安慰徐摛的意思。
以上我们根据《玉台新咏》编撰的目的,论述了它是有可能编成于萧纲任太子时期的,这个结论是否合于事实呢?如果合于事实,又大约编在什么时间呢?以下我们通过对《玉台新咏》编辑体例的研究,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论证。
二、从《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看编纂时间
《玉台新咏》编辑体例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从卷五开始的编排顺序令人不解。现行的几种版本,有不同的排法,一种是赵氏覆宋本以萧衍父子等作品排在卷七,卷八是萧于显等梁朝诗人,卷四、卷五、卷六则分别是宋、齐、梁三代诗人。一种是明通行本如嘉靖年间徐氏海曙楼刻本和郑玄抚刻本,以萧氏父子列在卷五,卷四是宋、齐诗人,卷六、卷七、卷八则是梁代诗人。
对于这两种版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赵氏复宋本比较可信,而明通行本明显增益作家作品太多,已失原貌。赵氏复宋本尽管也经过了陈玉父以及赵均的改动,但只限于个别篇目和字句等,总的变动不大。但赵氏复宋本以萧氏父子排于卷七的体例,却让学术界感到不可理解,似乎不如明通行本合理,因为它合于将当代帝王列于本朝作家之首的体例。关于这两种版本的体例,哪一种更合理,更合于原貌,我另撰有《论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一文,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赵氏复宋本保留了原貌(注:赵本基本保留了原貌,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受到后人的改动,但总的体例并未改变,个别的枝节问题,不会影响到该本的真实性。),而明通行本则是后人所改动。那么赵氏复宋本将萧氏父子排列于卷七,是出于怎样的体例呢?
学术界对赵氏本的疑惑是,根据古代总集编辑的一般体例,萧氏父子作为当代帝王,为什么会排列在梁臣之后,即卷五中的江淹、沈约、丘迟、柳恽、何逊等、卷六中吴均、王僧孺、张率、徐悱等,明显是梁代诗人,为何会置于萧氏父子之前呢?这个版本是否被陈玉父或者后来的赵均改动过呢?据前人的记载,似乎没有这个可能,这个版本,仍然保留了宋本的面貌。虽然据陈玉父跋文说,此本是由两个本子所合成,但据晏殊《类要》所引《玉台新咏》,一一都与此本吻合,同时,又据见过宋本的李维桢、冯班、纪昀诸人跋及校(注:见清叶万过录冯班等校语本及纪昀批校本,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皆未对赵本的顺序表示异议,可见赵本的顺序是和诸宋本一致的。对赵氏复宋本的体例,前人曾有过解释,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一《李延年歌诗》题下说:“此书体例,前八卷皆收五言,而长短歌词则皆入第九卷。”所以他怀疑这首《李延年歌》是后人所窜入。这个解释有道理,前八卷的确都是五言,杂言诗均入第九卷。但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萧氏父子会置于梁臣沈约等人之后。清初程琰《玉台新咏笺注删补》在卷八又有解释说:“三、四卷是宫体间见,五、六卷是宫体渐成,七卷是君倡宫体于上,诸王同声,此卷是臣仿宫体于下。”这似乎是按宫体诗的发展顺序来解释体例,但却不合于宫体诗的产生事实。作为独立的题材,宫体诗当然是以萧纲、徐摛等人为中心而开始的创作,是他作为提倡“新变”的产物,如果按照吴兆宜的解释,徐陵拱手把这个开创之功送给了前人,尤其是第六卷中的沈约、费昶、徐悱、张率等人,同是梁臣,按照吴兆宜的说法,变成了宫体诗“渐成”时期的作家,那萧纲的地位何在?仔细研究赵本的顺序以后,我们发现《玉台新咏》的编例其实与诗人的生卒年有关,徐陵其实是把全书分成了两部分,即前八卷以时代排列作家,后两卷以诗体排列。在前八卷的时代排序中,他又是按照已故作家和现存作家两部分排列的,即自卷一至卷六是已故作家,卷七和卷八是现存作家。以下我们先验证前六卷已故作家的情况。
前三卷分别收录了汉魏晋作家,其为已故作家是不须证明的,我们这里不妨对卷四至卷八作家作个检验。卷四共有十一位作家:王僧达(423-458)、颜延之(384-456)、鲍照(?-466)、王素(418-471)、吴迈远(?-474)、鲍令晖(不详(注:关于鲍令晖卒年,鲍照有《请假启》一文,是追悼其妹作品,据曹道衡先生考订,即指鲍令晖,则见鲍令晖比鲍照先卒。参见《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不过,史书于鲍令晖卒年没有明确记载,这可能是徐陵误排在鲍照之后的原因。))、丘巨源(?-484)、王融(468-494)、谢朓(464-499)、陆厥(472-499)、施荣泰(不详)。除了鲍令晖、施荣泰卒年不详外,其馀在宋、齐时均已亡故,是无可置疑的。卷五共收录12位作家:江淹、丘迟、沈约、柳恽、江洪、高爽、鲍子卿、何子朗、范靖妇、何逊、王枢、庾丹。其中除鲍子卿、王枢、范靖妇、庾丹卒年均不详外,其馀诸人的卒年分别是:江淹:天监四年(505);丘迟:天监七年(508);沈约:天监十二年(513);柳恽:天监十六年(517)。江洪和高爽具体卒年不详,但据《梁书》记载,高爽天监初出为晋陵令,坐事系治,后遇赦获免,顷之卒。则其卒年当在天监年中。江洪事例高爽之后,称他为建阳令,坐事死,是其卒年亦当在天监中。卷六共收录十位作家:吴均、王僧孺、张率、徐悱、费昶、姚飜、孔翁归、徐悱妻刘令娴、何思澄。其中费昶、姚飜、孔翁归卒年不详,其馀诸人的卒年分别是:吴均:普通元年(520);王僧孺:普通三年(522);张率:大通元年(527);徐悱:普通五年(524);何思澄:中大通四年(532)左右。这里有一个误入之人,即徐悱妻刘令娴。按刘令娴,据明通行本(徐学谟刻本、郑玄抚刻本)和赵均复宋本都加以收录,但通行本均录在卷七,共五首,赵本则在卷六和卷八两卷中都有,共三首。赵本以之录在两卷之中,肯定有误。依赵本体例,若录在卷六,表明徐悱妻已经在徐陵编集时故世,若录在卷八,则表明其时尚存人世。据《艺文类聚》载刘令娴《祭夫文》,其文写于梁大同五年(539),是徐陵编集时的确在世,所以不应列在卷六。故徐陵原本是将令娴编在卷八,但后人改动体例,遂将其移与其夫一卷。明通行本仍然置于卷八,保留了原貌。这个例子也说明,无论赵本,还是明通行本,都有保留原貌的部分,也都有受损害的部分,因此,在确定了徐陵基本体例前提下,应该结合两个系统的版本,讨论恢复原貌的问题。
以上是前六卷情况,其卒年最晚者是中大通四年的何思澄。从诸诗人先后排列的顺序看,基本按照卒年的先后,可见其为已故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与前六卷不同,卷七、卷八却不按照这个顺序,各诗人的卒年先后顺序与书中排列的顺序完全不合,显得很凌乱。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徐陵编《玉台》时,这些作家都还存世,徐陵当然不可能预见他们的卒年,从而根据先后顺序排列。这个凌乱的顺序充分证明卷七、卷八入选作家是还存活于世的人,由此可见,《玉台新咏》全书分为已故作家和现存作家两部分是确实的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该书的编纂时间了。在已故作家的前六卷中,最晚的卒年是中大通四年(532),而在现存的作家中,最早的卒年是大同元年(535),则《玉台》一书的编纂应该就在这数年之间。以下我们就验证卷七和卷八的情况。
卷七是萧氏父子,萧衍、萧纲、萧纶、萧绎、萧纪。其中萧衍卒年最早,在太清三年(549)。其馀依次为萧纲的大宝二年(551);萧纶的大宝二年(551)、萧纪的大宝二年(551)、萧绎的承圣三年(554)。这一卷排序与前六卷已有了不同。如萧纪卒年在萧绎之前,但却排在其后,这个排列不是偶然的失误,与卷六中张率排在徐悱之前不同,它表明从此卷开始使用的是新体例,而此点在卷八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卷八共收录21位作家:萧子显、王筠、刘孝绰、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徐君蒨、鲍泉、刘缓、邓铿、甄固、庾信、刘邈、纪少瑜、闻人蒨、徐孝穆、吴孜、汤僧济、徐悱妻、王叔英妻。其中除了徐君蒨、邓铿、甄固、闻人蒨、汤僧济、王叔英妻卒年不详外,其馀诸人的卒年分别是:萧子显:大同三年(537);王筠:太清二年(548);刘孝绰:大同五年(539);刘遵:大同元年(535);王训:大同元年(535)(注:逯钦立先生《全梁诗》记王训卒于天监十七年(518),当是误记。按《梁书·王训传》记训年二十六卒,考萧绎《法宝联璧序》载王训时年二十五,其序作于中大通六年,故知王训于第二年即大同元年卒。);庾肩吾:大宝元年(550);刘孝威:太清三年(549);鲍泉:大宝二年(551);刘缓:大同六年(540);庾信:隋开皇元年(581);刘邈:太清二年之后(注:《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载刘邈在太清二年侯景乱中为景所得,侯景攻台城不克,邈劝侯景气和全师。);徐悱妻:大同五年(539)之后;纪少瑜:大同七年之后(注:《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载纪少瑜大同七年为东宫学士。);徐陵:至德元年(583);吴孜太清二年以后(注:《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载吴孜太清二年为学士。)。从以上诸卷作家的卒年看,卷六之前的作家,最晚卒于中大通四年,而卷七、卷八的作家,最早的卒年是大同元年。同时,我们发现,卷四至卷六作家排列,基本按照卒年先后的顺序,但卷八作家排列顺序与他们的卒年先后并不相合,这足证《玉台新咏》是在卷八作家卒前编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说,《玉台新咏》卷一至卷八的编例是以已故作家和现存作家为区分而编排的,这样,根据已故与现存的人在卷六和卷八中的卒年分界,我们也就证明了《玉台新咏》的编撰时间,应该是在中大通四(532)年至大同元年(535)之间。
关于卷七萧氏父子排列顺序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很明显,这一卷与前几卷不同,不是按照卒年的先后排列,除了武帝萧衍和时为太子的萧纲外,其馀三位是以年齿排序。尤其要说明的是,排在第四位的不是后来的元帝萧绎,而是邵陵王萧纶,如果《玉台新咏》编在萧绎作了皇帝之后的话,萧纶无论如何不能置于他之前,反过来说,萧纶既然置于萧绎之前,就说明《玉台新咏》编成于萧绎未登皇位之前,因为萧纶是他的兄长,序齿排在前面。(注:萧纶排在萧绎之前是赵氏本顺序,但明通行本则排在萧绎之后,这是后人所做的改动。详情请参见拙文《〈玉台新咏〉版本考订》,待刊。)
以上根据前八卷的体例,推断出《玉台》的编纂时间,那么卷九和卷十是怎样的体例呢?,卷九、卷十的编辑体例与前八卷有很大不同,首先它不是按照时代分卷,而是采以文体区分,即卷九收录历代杂歌,卷十收录古绝句和短诗。其次,这两卷均以历代作家混列一卷,而不是如前八卷的据不同时代分卷。但是进一步检查,我们吃惊地发现,即使这两卷按照体裁区分,在作家排列的顺序上,仍然采取了已故作家和现存作家两部分区分体例。以卷九为例,萧纲之前是历代已故作家,从他开始则是现存作家。同样,现存作家中也以萧氏父子为首,由于此卷未录梁武帝萧衍,故首列萧纲。在对已故作家和现存作家的排列上,这两卷仍然遵守了前八卷的体例,即以卒年先后排列,虽然所选作家作品不多,但先后列的顺序仍然能在前八卷中找到相应的卷数。如第九卷,自《歌辞二首》(注:这两首《歌辞》,徐本作《古辞》,但时代绝非魏晋以前,故置于卷首,颇令人怀疑,如“河中之水歌”,《乐府诗集》作梁武帝,此或为误钞误刻所致。)至陆机《燕歌行》,时代相当于本书的前三卷;自鲍照的《杂诗八首》至陆厥的《李夫人及贵人歌一首》,时代相当于本书的第四卷;沈约的《杂诗八咏四首》,时代则相当于本书的第五卷;自吴均的《行路难》至费昶的《行路难》,时代相当于本书的第六卷;自萧纲的《皇太子圣制一十六首》至萧绎的《春别应令四首》,时代相当于本书的第七卷;自萧子显的《杂诗七首》至王叔英妻《赠答一首》,时代相当于本书的第八卷。所以兴膳宏教授说卷九、卷十的构成是按照卷一至卷八的方式压缩为一卷,前者根据已死者卒年的顺序,后半根据生存者地位的序列加以排列。这里要说明的是,本卷卷末所载沈约《古诗题六首》与前面重复,显然是后人附录,所以叶万过录校语称:“《八咏》,孝穆止收前二首,此皆后人附录,故在卷末。”
卷十与卷九相同,自《古绝句》至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时代相当于前三卷;自谢灵运至谢朓、虞炎,时代相当于本书第四卷;自沈约至何逊,时代相当于本书第五卷;自吴均至徐悱妇、王环,时代相当于本书第六卷;自梁武帝至皇太子,时代相当于本书第七卷;自萧子显至刘孝威,时代相当于本书第八卷。这个事实说明,《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在卷九和卷十中也是丝毫不爽的,所以虽然是在一卷之中,以梁武帝父子身份之尊,也只能排在沈约、何逊、徐悱等人之后。因为沈约等人是已故作家,而在现存的作家中,仍然是以武帝父子排在首位。这样,卷九和卷十在同一卷中排列历代作家,却以萧氏父子列于梁臣沈约之后,因而造成令人不解的现象,至此便完全清楚明白了。
以上所述可以见出《玉台新咏》在全书编排上的体例,那么在同一卷中,又是怎样的体例呢?对比下来我们发现,徐陵在一卷中的体例基本配合着全书的体例。即在前六卷的各卷中,编者以作家卒年早晚为序。这一点,兴膳宏和沈玉成先生都揭发在先。应该说这个体例在前三卷中贯彻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时代久远,不仅作者准确的卒年难以把握,即使是作家的生活年代也往往会发生错误,这在南朝一些选集和批评著作(如《诗品》、《文心雕龙》)中关于作家时代著录都出现过错误,可以证明。但从《玉台新咏》前三卷作家编排上看,基本上是符合这个体例的;而且是时代愈近,错误愈少。我们看第一卷的作家及其卒年:古诗、古乐府、枚乘(汉武帝初卒)、李延年(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苏武(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辛延年(不详)、班婕妤(汉成帝崩后卒)、宋子侯(不详)、张衡(汉顺帝永和四年,139年)、秦嘉(汉桓帝时人)、秦嘉妻徐淑(不详)、蔡邕(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陈琳(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徐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繁钦(建安二十三年,218)、古诗无人名为焦仲卿妻作。除了三首古诗外,作家的排列应该是很严格地遵守着卒年先后顺序的。因此跃进教授认为陈琳不该列在卷一的观点,其实没有考虑到《玉台新咏》从第一卷开始就贯彻了按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序的体例。相反,如果将陈琳和徐干列在卷二,就和这个卒年先后的顺序不符了。再看第二卷: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甄后(黄初二年,221年)、刘勋妻王宋(不详)、曹植(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阮籍(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傅玄(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张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潘岳(永康元年,300年)、石崇(永康元年,300年)、左思(晋惠帝永宁中,约302年左右)。此卷仅甄后例外,但编者以魏文帝列在她的前面,既是帝王,又是她的丈夫,这小小的例外不算破例。再看第三卷:陆机(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陆云(太安二年,303年)、张协(晋怀帝永嘉初年,307-313年)、杨方(曾为王导司徒掾,卒年不详)、王鉴(东晋人,王敦请为记室参军,不就而卒)、李充(东晋人,卒年不详)、曹毗(东晋人,卒年不详)、陶潜(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苟昶(宋文帝元嘉初人)、王微(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谢惠连(元嘉十年,433年)、刘铄(元嘉三十年,453年)。除了谢惠连略有不合外,其馀卒年先后顺序是很清楚的。和前三卷一样,四、五、六卷也遵循同样的体例,具体材料见前文所引。这六卷自西汉以迄齐梁,在选录的七十多位诗人中,徐陵对其卒年先后所作的排列,仅有极少的两三个人失序,对比《文选》在编辑体例上的粗糙,越发见出《玉台新咏》的精严。对这个事实我们是不应该再给予怀疑的。
前六卷每卷作家以卒年先后排序,但卷七、卷八本来是收录活着的作家,所以排列的顺序就改以按职位的大小。卷七的情况很清楚,尤其是邵陵王萧纶排在萧绎之前,最能说明问题,在卷八中,也是如此。由于古时作家彼此间职位的大小常常有变动,而且我们并不能确定本书编成于哪一年、哪一月,因此要作准确的说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幸好萧绎留下一篇《法宝联璧序》,序末排列了三十八位当时朝中显要人物,而这排列的顺序,萧绎明确说是按照爵位,这样我们可以用来与《玉台新咏》卷八所列作家进行比较。发现这个比较方法的,是日本的学者兴膳宏教授,这个发现真算得上是学术研究中的神来之笔。这篇序写于中大通六年(见《南史,陆罩传》),说明排列的顺序代表了这一年中各人的爵位。我们发现这三十八个人中有五位被选录在《玉台新咏》卷八里,他们是: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另有两位收录在别卷,如萧绎收在卷七,刘孝仪收在卷十。两相比较,结果令人吃惊,二者顺序完全相同!这也是兴膳宏教授认为《玉台新咏》编成于中大通六年的主要根据。这是兴膳宏教授根据《法宝联璧序》得出的结论,我们略为保守些,根据收录作家卒年的排列,认为在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间可能更为稳妥些。因为一部书的编辑,一年的时间似乎太短了些。
徐陵古今作品兼收,并以当代作家置于已故作家之后的体例,在现存总集中是没有先例的,兴膳宏教授认为这是他的独创。不过,清人梁章钜《玉台新咏定本》(注:稿本,藏湖北省图书馆。)说:“然考《汉书·艺文志》,惟《高帝传》十三篇,《歌诗》二篇,以时代最先冠于汉人之首。其儒家《孝文传》十一篇列于刘敬、贾山之间时赋家,武帝赋二篇列于蔡甲、兒宽之间,知帝王制作与臣下合编,乃自汉以来之旧法。至徐坚编《初学记》,始升太宗所作于历代诗文之上,则此例实改于唐,而此书编次,犹存古法,信非后人所能伪托也。其称梁武及诸王名,盖后人之所增改,与首署陈官同一例耳。”梁氏此说其实并不了解寒山赵氏本将萧衍父子列于卷七的原因,事实上在我们所理解的徐陵编例中,徐陵仍然是把萧衍父子置于本朝代作家之首的。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宋、齐、梁之间总集数量很多,其中古今兼收的也为数不少,如苟勖的《古今五言诗美文》、张湛的《古今九代歌诗》、萧统的《古今诗苑英华》等。古今兼收,势必涉及到对当代帝王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徐陵《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可能并不是独创,而是有先例的。
以上的结论,还须验证以徐陵的仕履,看他有无可能在这个时候为萧纲编书。据《陈书》本传记载,徐陵八岁能属文,普通二年(521)晋安王萧纲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引徐摛为王咨议,又引徐陵参宁蛮府军事,这一年徐陵大约十七岁。不过,据《南史·庾肩吾传》记载,萧纲在雍州置高斋十学士,抄撰众籍,徐陵并未预其中,似乎这个时候徐陵还未受到萧纲的充分重视。直到中大通三年(531),萧纲继萧统为太子,开文德省置学士,徐陵与庾信、张长公、傅弘、鲍至等充其选,似乎说明年轻一代文士已经成为萧纲东宫的主要侍从之臣了。《南史·庾肩吾传》所说“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的话,正是指他们围绕在萧纲周围,忠实地贯彻着萧纲的文学主张。但是徐陵在东宫的时间并不长,《陈书》本传说他:“稍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风闻劾陵在县赃污,因坐免。久之,为通直散骑侍郎。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又令于少傅府述己所制《庄子义》。寻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看来他很快就从东宫出来迁为尚书度支郎,又出为上虞令,因了刘孝仪的弹劾而坐免,又过了很久才改为通直散骑侍郎。萧纲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曾使徐陵为序,又令徐陵于少傅府为其所制《庄子义》作述。又不久,徐陵迁镇西将军、湘东王萧绎中记室参军。考刘孝仪作御史中丞时间大约在大同五年(539)到十年(544)间(注:《梁书·简文帝纪》载刘孝仪大同四年秋七月使魏,还除中书郎,累迁尚书左丞,长兼御史中丞。又据《梁书·张绾传》载绾大同四年为御史中丞,岁馀出为豫章内史,十年又复为御史中丞,则刘孝仪为御史中丞时间应是大同五年至十年之间。),又据《梁书·元帝本纪》载,萧绎进号镇西将军在大同三年(537)闰月甲子,五年秋七月入为安右将军,如果《陈书·徐陵传》所记不误的话,徐陵遭刘孝仪弹劾,只能在大同五年七月之前。在这之后,《陈书》本传说他:“久之,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又其后,太清二年(548),徐陵以通直散骑侍郎职聘魏,侯景之乱,他被魏人拘留不遣,从此再也没有与萧纲见过面。从徐陵以上仕履看,他从东宫出来的时间,关键是其为尚书度支郎的时间,这个“稍”字,到底有多长,如果是一、两年的话,则从中大通四年或五年至大同五年才出为上虞令,这中间相隔了六、七年,未免一官太久。据《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其郎中在职勤能,满二岁者,转之”,因此,徐陵从东宫出来任尚书度支郎的时间应该靠近大同五年,或者在大同二、三年间。这样,徐陵能为萧纲编《玉台新咏》的时间就在中大通三年至大同二、三年之间。至于《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时间上并不十分准确。但一种诗风的提倡、普及,最终造成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若理解为从中大通三年萧纲入主东宫提倡宫体诗风以来,至大同年间才风靡朝野的话,《北史》的这个评断还是合于实际的。说徐陵《玉台新咏》编成于此时,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此书著录刘孝仪之诗的疑问。据《陈书·徐陵传》载,他与刘孝仪之间原本不和,又在任上虞令时受到刘孝仪的弹劾,这个事件和刘孝绰与到洽之间恩怨相似。弹劾一事其实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件,当初到洽弹劾刘孝绰,刘氏兄弟联合起来写信骂到氏,并与到氏兄弟绝交。到溉初与刘氏交好,知道到洽要弹劾孝绰,曾含泪向孝绰道别。[7](P122)可见弹劾之事对人的伤害。刘孝仪弹劾徐陵,相信也会造成这样的伤害,但从现存几种《玉台新咏》(明寒山赵氏覆宋本、明徐学谟刻本)卷十都有刘孝仪的两首诗(《咏织女》和《咏石莲》,徐本更在卷入录有一首《闺怨》),这说明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当在刘孝仪弹劾他之前,也就是在大同五年之前,这就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结论:《玉台新咏》编成于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间,是完全可能的。
收稿日期:2001-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