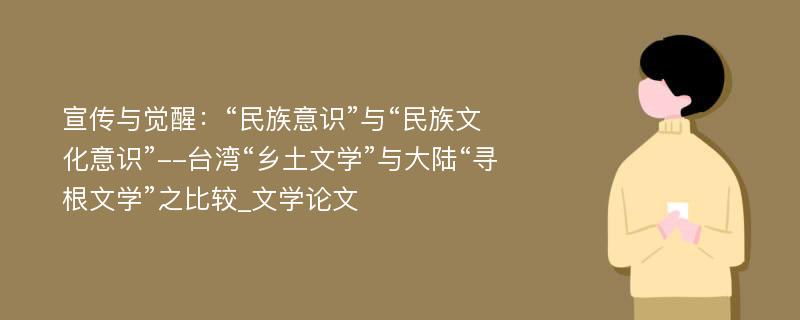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意识论文,台湾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主题词 “寻根文学” “乡土文学” 民族文化意识 台湾
Taiwanian ‘native literature’in comparison with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in Mainland China
Wu Yiqi
(College of Scientific Research,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is adopted to make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ian‘native literature’in the 1970s and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mid 1980s from various angl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imes,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and between literatureand culture.
Subject terms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native literature’cultural ideology national Taiwan
对“寻根文学”,尽管在80年代中期曾经为它的名实进行过一番颇为热烈的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来说,在当时它还是有着大体一致的指称范围,因而也并不妨碍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评述这一文学现象时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而对于“乡土文学”,我们就不免感到有些为难了,这是因为,虽然同样称之为“乡土文学”,但由于地域和历史诸种原因的不同,却使得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坛上呈现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而且,这里还存在着双重的困难:一是大陆文学界习惯上所认定的“乡土文学”与台湾的“乡土文学”各各不同;二是台湾的“乡土文学”本身也存在着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与70年代的“乡土文学”的区别。而这些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异,则使我们在使用这一名称的时候难免产生彼此相互混淆的麻烦。为此,我们的论述还得从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的渊源说起。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在20年代初期的北京,曾经聚集着一群为战乱所驱为生活所逐而离乡背井流徙北来的青年作家。他们没有像一代文学大师鲁迅那样以思想启蒙为己任,执着于国民性的探讨,没有像文学研究会诸君那样借“问题小说”以探索人生的意义,也没有像郁达夫他们那样在“身边私事”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写时代的流患和病态,而是在“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结合着自己的身世遭逢,将关怀的目光投射向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领域——故乡上去,用诚挚、伤感的笔触,真切地向人们展示出自己遥远故乡的特殊生活风貌。由于这些青年作家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倾向,也由于他们的作品所独具的乡土生活气息,从而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因而,鲁迅先生在为集五四新文学十年实绩之大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二集”时,就特意收录了这样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在该集的《导言》中将其称之为“乡土文学”并写下了那段著名的理论文字,这也是文学界、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文学”最早的理论阐释。正是由于这些青年作家的努力劳作,也是由于鲁迅先生的肯定和宣扬,“乡土文学”随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所接纳的,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并且以其独具的、顽强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地蕃衍影响至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陆本土文坛上,“乡土文学”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更而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变化,使得由鲁迅先生早先所给定的经典性解释也难以完全符合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它所具有的乡镇生活、乡土气息、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的种种特点,却仍然“秉性难改”地流传下来,也因此使得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乡土文学”无论是在作家对生活的取舍,作品的思想倾向或精神内涵等方面,较之于同一时期的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历史题材等)的文学来说,其间的政治性(相对于当时现实的政治要求而言)和民族性(相对于异族文化的同化方面而言)并不十分明显。或者,换句话说,40年来大陆本土的“乡土文学”并不像其它题材领域一样以政治的诉求或保持民族自尊作为它的终极使命,它只是默默地以其朴拙的乡野气息和强韧的生命力存在着流传着。然而,恰恰与之相反,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坛,现代“乡土文学”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政治意识和反抗异族文化同化的民族意识,而所有这些,则是由台湾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所决定的。
台湾历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可是由于其处于祖国的“东方前哨”的特殊战略地位,历史所赋予台湾的命运却是十分不幸的。早在17世纪初中期,台湾就曾沦为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直到1662年,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率领下,台湾军民奋起抗击,赶走了荷兰侵略者,台湾才又重回祖国的怀抱。19世纪末叶,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又使台湾成为远离祖国母亲的“孤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从1895年起至二次大战结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日本殖民者从它统治台湾的那天起,便有意地对台湾人民进行全方位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他们为了达到其长期霸占台湾,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更是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实施“皇民化”运动,强蛮地禁止台湾人民使用中国语言文字,规定日本语为台湾的“国语”,其狼子野心是十分明显的,即不但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制服台湾人民,而且还要从精神文化上彻底剔除台湾人民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从而“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化”了的“全新”的台湾。面对着侵略者野蛮残酷的政治军事压迫和阴险恶毒的精神文化统治,台湾人民也针锋相对地进行着两条战线上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抗争。而“乡土文学”就是台湾的文学知识分子从精神文化上反抗殖民统治的一面旗帜。从被誉为台湾“现代乡土文学之母”的赖和到杨守愚、杨云萍、朱点人,从自称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到吕赫若、张文环、吴浊流等等日据时期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他们不论是直接揭露控诉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残酷野蛮的统治,还是隐晦曲折地讽刺嘲弄统治者的贪婪嘴脸和丑恶本质,不论是描写反映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还是抒发台湾人民爱乡爱土的炽热悲痛情怀,其间所贯串始终的一条思想红线,就是对殖民统治者的无比憎恨和对家园乡土对祖国民族的深深挚爱。而实际上,他们这些作品中的“乡土的”“台湾的”,其实就是“民族的”“中国的”的同义词,只不过是逼于环境的险恶,他们不能公开地揭起“民族”的大旗去与统治者明白相对,只能隐晦地以“乡土”为号召罢了。可以这样说,日据时期台湾的“乡土文学”虽然也同样有着起源于中国大陆五四新时期的、为鲁迅所界定和评价过的“乡土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特点,但是,就其终极的文学旨归,也即是它的真正的文学使命看来,却显然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以乡土色彩民俗风情和“隐现着淡淡的乡愁”为其基本特色的“乡土文学”。它是由半个世纪以来惨痛的殖民经验所激发产生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色彩的文学,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反抗“皇民化”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民族文学”。从精神文化内涵上来说,则是彻底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本位观念的具体显现,是一个与殖民统治者所鼓吹的“皇民文学”绝然相反对立的民族文学的口号。而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正好在这一点上跟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精神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台湾70年代的“乡土文学”,正是日据时期“乡土文学”的精神赓续。
当然,70年代的台湾,是中国人的台湾,尽管国民党台湾当局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但是,台湾的国民党人也是中国人,台湾毫无疑问的是属于中国人所有的,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与日据时期的台湾的根本性区别。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在五六十年代期间,国民党当局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过分依赖,以及由这种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对西方精神文化的全面开放,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极大的附庸性。据资料统计,自1951—1965年的15年间,美国政府总共向台湾提供了12亿6千5百万美元的巨额经济援助(这还不包括比经济援助这一数字大得多的军事援助)。这15年的经济援助至少使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增长一倍,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7.7%,人均生产毛额成长率也提高了3倍,从而使1964年已达到的人均国民收入600美元的生活水平所需的时间整整缩短了30年。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美援,这15年间台湾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多点,而人均国民收入600美元的生活水平则要推迟到90年代初中期才能达到[①],美援对台湾经济的巨大激活、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与之相关联的是,台湾在接受巨额美援的同时又必然地决定了它的经济只能是一种基本上丧失了民族经济支配权的高度附庸性经济。依照政治经济学上的一般原理,这种经济上的附庸性必然地会影响乃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附庸性。因此,当美援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并主宰着台湾的经济命脉的时候,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诱惑和侵蚀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所以,尽管60年代初中期由李敖所推出的、以宣扬胡适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标志的“全盘西化”理论因为触及到国民党“法统”地位的敏感问题而被当局强压下去,败下阵来,没能获取理论上的胜利,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附庸性所决定了的不可逆原理,却使得“西化”在台湾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如陈映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30年来精神生活的突出的特点。这一认识使我们惊愕,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此无他,唯一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整个实际社会生活就是笼罩在别人强势的经济支配下的缘故。我们的附庸性文化,只是社会经济的附庸化的一个反映而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出现本身就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批判意义。从陈映真、王拓、杨青矗、黄春明、王祯和到洪醒夫、曾心仪、宋泽莱,从《炸》、《金水婶》、《望君早归》到“工厂人系列小说”到《看海的日子》、《莎哟娜啦,再见》、《我爱玛莉》到《小林来台北》到《夜行货车》等等一大批代表性作家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台湾处于经济附庸的状况下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生存生活情景和驳杂心态。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了蕴藏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的深切的民族同情心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的承续,而当我们得知所有这些作品都被称之为“乡土文学”的时候,便不由得恍然醒悟到:原来,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竟然与半个世纪前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同名同姓”!当然,这决不是历史的巧合或皮相的摹仿,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社会历史因素,尽管前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凭着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台湾,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而后者则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前提下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侵入”,但是,所有这些,对曾经几度离开祖国怀抱饱受殖民统治之苦因而也特别敏感的台湾人民来说,在感情上和在精神文化方面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叶石涛在分析台湾省籍作家作品为什么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性这一现象时就曾经这样说过:“省籍作家的小说特别富于坚强的民族性,这可能是由沦陷50年的惨痛体验所致。在那恐惧的日子里,本省的土地和人民被割裂——和祖国大陆分开,在异族的蹂躏之中备尝亡国的痛苦,这一惨痛的记忆永远提醒省籍作家唯有保持民族风格,才能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心灵和处境”[②]。也因为他们对外族的入侵有着难以忘却的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尤其不能忍受任何形式和名义的“殖民化”;所以,当70年代的这些作品以其对现实和乡土、传统和民族的回归为号召,以“不能永远寄养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做一个老站不直的中国人”的呼吁去反抗外来资本外来文化的“入侵”的时候,人们便有理由自然而然地将其与日据时期的那些作品等量齐观,并赋予其与前行者相同的名称:“乡土文学”!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起了王拓在1977—1978年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所写过的一篇名为《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除了具体详细地分析了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所由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乡土文学”改换名称。他在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
它(指“乡土文学”—引者注)不是只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文学。这样的文学不只反映、刻画农人与工人,它也描写刻画民族企业家、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教员以及所有在工商社会里为生活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来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而不是“乡土文学”;而且为了避免引起观念上的混淆以及感情上的误导,我认为也有必要把时下所谓的“乡土文学”改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
应该说,如果从文学取材的范围和描写的对象甚至是作家所遵循的借以反映和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方面着眼,王拓的看法是符合当时“乡土文学”创作的实际的,因而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从台湾“乡土文学”的固有传统,也即是日据时期“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历史承续关系,从而使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这一名称既有着历史的承续性,又有着现实的针对性这一点来看,他的改换名称的努力似乎就显得有点不太恰当了。在上面这篇文章里[③],王拓如果不是忘记了日据时期“乡土文学”的历史传承的话,便是有意忽略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如果说,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反映的是台湾人民惨痛的殖民经验和他们不忘祖国热爱乡土的悲痛深挚的情怀,那么,70年代的“乡土文学”所表现的却是对外国资本外国文化“侵入”台湾所带来的社会畸变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他们对现实对乡土的热切呼唤和关注。而建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则是台湾前后两次“乡土文学”运动高高飘扬的精神大纛。而这一点,正是台湾“乡土文学”不同于大陆的“寻根文学”的根本所在。
80年代初中期,中国大陆的改革运动正从广袤的乡村大地悄悄地向城市推进,并且开始小心翼翼地把试探的脚步从经济体制的外围领域伸向政治体制这个极为敏感的纵深地带。改革,在以前所未有的运动形式,给原来几近僵化的社会肌体注进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这时,人们所面临着的,再也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选择和争论,而是如何改革,怎样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是对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传统载体的“人”之间的矛盾的思考。或者,换句话说,是对当代中国人民应该如何调整、更新或者跨越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去参与和推动这场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改革运动的思考。而当这些思考上升为理论形式上的探讨的时候,又被抽象地归结到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这样的“老之又老”的、从近代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的“斯芬克司”之谜上去。当然,历史决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课题的重新提出,一方面说明了这一课题的理论难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代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大概在1983年左右,大陆的文化界学术界便渐渐酝酿兴起了一场持续几年之久且又颇具规模的“文化”研究的热潮。人们希图通过对上下几千年的民族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去获取解决、医治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疑难杂症和祖传痼疾的良方妙药。这种以“文化反思”为主要物征的文化研究热潮,也是80年代中期大陆上出现的一种十分突出且又极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或许正是受益于这一社会性的“文化反思”的影响和启迪,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在80年代中期前后形成了一股“渴望潜入历史文化的深层,为现代文明的重建寻觅可能性”(谢冕语)的“寻根文学”思潮。
然而,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的话,“文化研究”、“文化反思”的影响和启迪恐怕只是其触发产生的外部诱因,对前一阶段文学的重心过分横移的反拨才是这一文学思潮产生的更为内在的深层原因。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以保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的自我保护机制(有的称之为“内平衡机制”)。在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下,一切外来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不根本威胁或挤掉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否则,它将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以保护自身存在的优势。同样,一个民族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必然地具有民族文化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所以,在新时期之初,当以青年诗人为主力军的“朦胧诗人”和以王蒙等人为代表的“试验小说”,只是从形式上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拿来”借鉴,可怜巴巴地向当代文坛提出蜗居一隅的申请并为之进行申辩的时候,民族文学还能以其雍容大度的大家风范默许、接受它们的存在,尽管当时关于它们的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但是到后来,当这种借鉴“拿来”由开头的一二品种扩展到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曾经流行和正在流行的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全面登陆,尤其是当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剥离,开始由“穿中山装的意识流”向“中国式的现代派”转化,从而给人以企图借翻译作品来建立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④]的感觉的时候,当代文坛就再也无法保持昔日的衿持,自然而然地便有了“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不满和诘问。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一批青年作家,从文坛的发展态势和作为作家的深切体会中敏感地意识到文坛重心过分横移对民族文学的巨大冲击,意识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所造成的一代青年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欠缺,以及由这种欠缺所带来的当代文学的种种窘迫状态。他们似乎从拉美文学对本土文化的开掘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中得到启示:中国文学如若要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就必须把文学之根深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他们痛心疾首地反省着自己以往对民族文化的忽视,希冀借对民族文化的呼唤和补课填补当代文学中所出现的文化断层,借对民族文化的纵向开掘纠正文坛天平失衡的状态。
综上所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乡土文学”与“寻根文学”两者都是以乡村和乡村中人作为各自的主要表现客体,但是,“乡土文学”所着眼的是在外国资本外国文化的冲击下本民族生态(包括社会人生和自然环境)所受到的戕害及其所发生的种种畸变,而“寻根文学”所要追溯的却是当代大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的传统“神话原型”;尽管它们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现实批判倾向,但是“乡土文学”锋芒所向的是外国资本外国文化,而“寻根文学”所要探究、鞭挞的则是由“历史文化岩层”所积聚下来的民族劣根性;尽管它们也同样有着对当前文学文化过分横移的反拨功能,但是,“乡土文学”所面对的是强大的经济附庸下面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民族精神文化的被逼萎缩或自我弱化,它汲汲于要弘扬光大的是属于本民族自己的东西(当然包括文化在内,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文化上),而“寻根文学”所耿耿于怀的则是当代文坛所出现的文化断层,尤其是一代青年作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文化”的现象,它执意地希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掘去跨越或填补这一由社会、时代因素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从而使当代文学存在于一个巨大的文化包容中。由此,我们同样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概括,尽管它们都有着以“民族”为重的共同特点,但是由社会时代因素所造成的文学价值取向却又是各相迥异的:“乡土文学”深切关注的是受到伤害的民族利益和民族自尊心,而“寻根文学”所严肃思考的却是现代中国人的“原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失落。因此,在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方面,前者所侧重的是“民族意识”的张扬,而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注释:
① 上述数字均引自翁松燃:《美中关系四十年》,《台湾与世界》1986年5月;李非《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刍议》,《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1月。
② 叶石涛:《一年来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社1979年3月版。
③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在这篇文章里”,是因为我们认为,或许这样的理解更符合作者的初衷:他的这种提法只是因为逼于当时“乡土文学”论战的特殊氛围,为避嫌、也为“乡土文学”的生存计而采取的隐晦之略。因为作者在后来所发表的文章及讲话中,都曾多次明白无误地提到70年代“乡土文学”对日据时期“乡土文学”的历史承续关系。
④ 这里及下面所引的有关“寻根文学”的观点及话语,均出自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义和郑万隆等人的文章,因其早已为文学批评界所熟知,恕不一一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