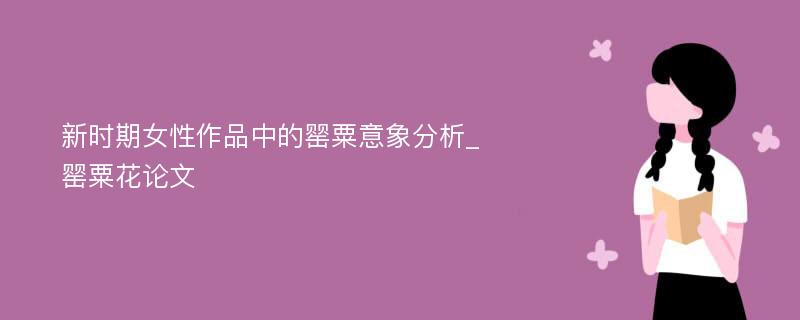
遍地罂粟——新时期女性作品中的罂粟意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罂粟论文,探析论文,意象论文,新时期论文,遍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84(2005)03-0081-05
花,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大意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花”的意象常常是指向同一向度的,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感受。罂粟是一种很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它的壳能入药、敛肺、止痛,主治久咳久痢诸症,它的果可取汁,制作为鸦片,鸦片主要含吗啡,亦为人间奇药的一种,有镇痛、镇静、止泻之功效;而罂粟花在开花时艳若朝霞、美丽非凡,可供观赏。但由于其物质属性和与中国历史的特殊关联,在民族记忆中,却并非如此单纯。在近百年间,关于“罂粟”的文本几乎是一片空白。罂粟一直以“禁忌”的姿态在社会中处于隐性、边缘地位。
直到新时期,罂粟作为花的形象出现。“五百年前三生石上的精灵/一只美丽的蝶/为寻找灵魂/已幻化成一朵罂粟花/鲜艳的,火一样燃烧的罂粟花/为寻觅前世的情缘/将自己开放在陡峭的悬崖/——;”①“——,在天气明朗的白昼里/闭上双眼想象雷声滚动/在粉红色的罂粟花丛中滚动/后就使罂粟看上去愈来愈鲜艳/——”②;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这里的罂粟更接近于“花”的形象最先出现于诗歌中的起兴、陪衬地位,体现了普泛的“花”的还原、纯净的意味,罂粟本身并没有可资陈述的特殊意义。
1979年开始,张抗抗首先推出了“罂粟系列”——《白罂粟》、《红罂粟》、《黄罂粟》,以后有海男的《箱子里的罂粟》、《鼓手与罂粟》,张欣的《遍地罂粟》、文夕的《罂粟花》等,199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集当代22位女作家作品推出一套丛书,取名为“红罂粟丛书”,在这些作品中,罂粟突破了“花”的意义,美丽/邪恶,良药/毒品,诱惑/抗拒、亢奋/死亡……这些相互对立的代码,使得罂粟的意义在重重撞击中,呈现出立体复杂的蕴涵。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罂粟意象日渐繁盛的趋势。
一、世纪末都市的喻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道德准则已经消失,社会文明的衰落、道德伦理的危机日益凸现。从价值观的困惑到不失温情的双重性格、复杂都市,直到欲望横流、尸横遍地的末世寓言,都市小说中罂粟意象喻示意义的不断扩展,也正反映了个人日益分裂、都市日渐颓废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繁华而危险的都市在文本中的影子愈来愈强大,人物逐渐趋于符号化,罂粟意象直接地指向人的生存环境——繁华都市。
张抗抗的《黄罂粟》第一个将罂粟与都市联系起来,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普通市民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时在价值标准取向上的困惑。在张欣的《遍地罂粟》中,年轻的转业军人夏媛蓓坚强地顶着压力投身于经济大潮中,并试图通过个人努力——包括利用情感来拯救受冤下狱的父亲及即将崩溃的全家:她牺牲了真正的情感,却并没有获得成功。罂粟在这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表面美丽而内在邪恶,诱惑人又毁灭人的罂粟与繁华而复杂的都市、与矛盾而狂躁的都市人形成了同质关系。张欣的都市小说题目常常是她的抽象观念的表达:《爱又如何》,《恨又如何》,《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那么,“遍地罂粟”也是她为都市、都市人设置的又一个代码。如果说,由于张欣“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③,《遍地罂粟》中的都市和人还都残留着脉脉温情的话,20世纪90年代末期,文夕的《罂粟花》则彻底撕去了温存的面纱,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示了世纪末颓败都市的景观。这个故事讲述了年轻美丽的女子米霜儿独闯深海市的遭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金钱、情欲弥漫的都市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深海市——很明显是化用了深圳、珠海,因而也具有了泛指的寓言意味:香车宝马、火树银花、物欲横流的世纪末现代都市。文夕作品中的女性置身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中;从江浙封闭落后的村野乡下到都市中金碧辉煌的豪宅别墅、灯红酒绿的宾馆歌厅;从黑暗腐败的官场到尔虞我诈的商界……作品以女人们飘零沉浮的命运为轴心,辐射出千丝万缕的关系链,由此牵引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围绕她们,演绎出一幕幕千奇百怪的俗世众生相。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文夕亦浓墨重彩地写出了一个物化时代里,一张巨大的光怪陆离的都市生存网络中,人们集体拜金的丑陋与疯狂,欲望与罪恶被袒露得纤毫毕现,淋漓尽致。
从罂粟意象的使用手法来看,在《黄罂粟》中使用了大量语言来描述罂粟特性,而在《遍地罂粟》和《罂粟花》中很少正面描述罂粟,却不约而同地将其设置为标题,其内涵更为抽象,也更为丰富。标题也罢,人物也好,成为一个个具体的能指符号,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统一的能指——欲望。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受着欲望的驱使,欲望就像个拿着皮鞭的魔鬼,鞭策着在世的每一个人朝着它希望的方向前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潜伏的沸腾的激情,当它一受触发,就会如火山般喷射出来,不管是以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形式。”④这里的“激情”就是欲望,人有了欲望以后,就要发泄出来。而在这香车宝马、火树银花、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中,什么人生的价值,意义、抱负,形而上的终极追求——精神的意义——都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死心塌地的拜金,牟取暴利与向上的职位,都市成为一片精神的“荒原”。在这种情况下,欲望鲜以正义的形式释放,种种非理性控制了人的生存,现代的都市中所囊括的是在奢华的外表下一颗颗受欲望驱使的不安分的灵魂,这里的人已失去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诗意生存”,全然陷入了“此在的沉沦”,流光溢彩的现代都市成了这些不安分的灵魂扭曲的狂欢舞蹈着的一座“欲望之都”。
二、迷狂艺术的镜像
“禁忌”和“矛盾”之外,罂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致幻效果。1992年的春天,女作家海男参观了云南第一戒毒所。在那里,她见到了一个鼓手。“他的第一阵鼓声就把我给震撼了,咚咚的一阵鼓声,令人迷乱,那时他好像正淹没在一种半透明的气体里,我知道这种气体是跟粉红色的罂粟紧密相联的”。“虽然我同他之间什么话也没有讲,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人,但我好像已经同他交谈过了,了解了他灵魂的痛苦”。⑤海男在一个素昧平生的鼓手身上感到了深刻的震撼和恐惧,并由此创作了中篇小说《鼓手与罂粟》和长篇小说《歌手的衰亡》。《鼓手与罂粟》中,鼓手欧利和画家南西在罂粟的迷狂中,创造出了最为辉煌的艺术作品,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歌手的衰亡》中,摇滚歌手阿南在布满罂粟的舞台上达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也在此刻死亡。“罂粟引起世界的失败,语言的溃散,引起纷纷扬扬的血迹斑斑的故事的重新虚构。”⑥海男在文中一次次地重申她对罂粟的读解:创造与毁灭,高潮与死亡,罂粟与艺术在这样的基点上不谋而合。海男说,“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过程”(同注释②)。由于她的理解和默契,由于她小说中强烈的体验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几乎缩小为零,她在文中的描绘让人身临其境,投射了自我的影子。事实上,海男在访谈、散文中一再表达了对罂粟的迷恋。她在访谈中说,“对于这种东西,我确实有一种要体验一下的欲望。”(同上)在散文中说,“我被吸引了,如果漫山遍野都是罂粟,那就是说漫山遍野都弥漫着粉红色的香气。”⑦另一篇类似于寓言的短篇小说《箱子里的罂粟》中,海男一反华丽、飘忽的语言习惯,有意使用简短朴素的语言和叙事突出日常场景的平淡、乏味、重复,而带来神秘、灾难、诱惑的罂粟作为“缺席的在场”,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反拨,其诱惑姿态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可以说,乐手故事中,作者与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为认同的。
在海男作品中的艺术家与作者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为认同的,事实上,从亢奋与幻觉、创作与毁灭的意义上说,乐手故事可以看作所有这些困惑、焦虑的作者的原型。这种困惑与焦虑,既源于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也受到了当代社会纷纭的语境的强化。如何摆脱这种困惑与焦虑?写作成为一种途径。弗洛伊德的艺术与白日梦同构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幻觉中的虚构。而当这些作家们选取了罂粟意象时,罂粟所带来的特殊的致幻效果使这种幻觉得到了最大的强化。在海男的文本中,通过体验化的叙事,几乎是再现了毒品带来的感觉——这种幻觉是审美的,同时也是生理的。但在一种强烈的刺激之后,不能不说同时感到了审美和感官的疲惫。
通过对戒毒医院的深入采访,1998年,毕淑敏推出了长篇小说《红处方》,以写实的笔调再现了毒品的危害,发出了严肃的呼吁;海男的《鼓手与罂粟》也源于她的一次戒毒所之行,却是以审美的方式将毒品化为美丽的花朵,表现了它的诱惑和毁灭,以及迷恋。海男曾说:“如果有一天我不打算再活下去了的时候我也许也会吸吸毒的,以体验一下这个东西是怎样的把我的生命一点点的毁灭掉的。”⑧这只是宣称而已,而到了更年轻的一代作家那里,罂粟已经消失了,其最初的来源“吸毒”二字已经堂而皇之进入文本中。比如棉棉,作为20世纪70年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频繁地出现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青年亚文化幻觉状态,直接在毒品中获得陶醉。“酒精和毒品让我们的生活飞入极限,生活的画面处于不停的变化中,这刺激,我们暗自喜欢。”“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海洛因最大的好处是让我没完没了地进入令人眩晕的虚无,我从里到外空荡荡的,时间开始变得飞快起来,生和死同时成为高悬在我头顶上的两座宫殿,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这其中尴尬的徘徊。”⑨棉棉的作品具有一种半自传式的“现场感”,她对吸毒的毫不隐晦的张扬或多或少暗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场景。
从毕淑敏到海男到棉棉,不难看到一个对毒品由抗拒到迷恋到认同,由审美到行为的过程。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作了深入剖析。他认为60年代生成了一种新型文化,即幻觉文化。与之前的自由主义者仅仅在艺术和想像方面的赞同相比,这种文化试图把有个人自由、极端体验(“刺激”与“亢奋”)和性实验的种种说教推向生活方式的高度。中国则有论者指出,新生代小说的另类写作展示了“一种在酒吧这棵树上生长出来的爵士乐、大麻、朋克、同性恋、迷乱的欲望的,舞蹈的、失控的东西”。⑩——很多人把中国新生代中的另类创作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从这两段描述的相似性看,不无道理。如果说,罂粟所具有的禁忌、悖论的特征使其最初的出现推动了文学意象多元空间的开拓,其致幻效果在文本中推动了文学的感性表述,那么到了后来,伴随着人性的日益分裂,都市的日益颓废,艺术的日益迷狂,价值观日益模糊,非理性日益扩散,则对这个幻觉时代起了推动作用。从审美走向行为,从对僵硬理性束缚的突破走向幻觉的泛滥,这是在罂粟最初出现时所料不及的。其实正如池莉在《愿做罂粟》中所说:“人类不肖,贪图过量的鸦片,这是人类自己的毛病,如何迁怒一草木?”
199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女性文学“红罂粟丛书”,池莉在为此书作的序言《愿做罂粟》中写到:“由于偏见,而使我们讳言这美丽非凡而又生命力强健而又充满个性的罂粟花。你是小草,他是松柏——而我,倒情愿是罂粟。罂粟集美丽的花朵治病的良药和诱人的危害于一体,我以为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而另一位女作家林白的《猜想〈红罂粟〉》中这样写的“我第一次看到罂粟花是在云南的云贵高原,在蓝天红土之间,层层薄如蝉翼的花瓣在明亮的阳光中跃动、漂浮和闪烁,红的无比妖娆,夺人心魄,它们就像一些在天堂和地狱都熔炼过的花朵,这个世界最精美最深刻最神秘最不可理喻的东西都以气体的形式抵达这些花朵,我们都能看到这片花朵在太阳底下散发出漫天的红光。”这套丛书的热销,也多少与“那种美丽的外表之中蕴含的怪诞和可怖对读者的刺激特别强烈”有关。从这里,也可看出人们对于罂粟从抗拒到认同的变迁。
此外,罂粟意象的崛起也缘于一种陌生化效应。罂粟意象的兴起也反映了一种美学观念——“变态美”的崛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花”的意象常常是指向同一向度的,它们一直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感受。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张辛欣在《疯狂的君子兰》中以“疯狂”修饰一向高贵的君子兰,来映衬现实世界的物欲横流和人们的焦躁不安;而在铁凝笔下,“玫瑰门里不玫瑰”,“在毒水里泡过的司猗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在庄家盛开着。”……总之,在悖论中形成强大的张力,用“恶”对“美”的突破表达复杂的心态,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罂粟意象本身已经具有了“悖论”的修辞学意义,为以上的干涉性方法提供了现成的工具。直接说,即“美”与“恶”的统一;笼统地说,则是异质共生,这成为罂粟意象的重要美感来源。如同罂粟对于“花”的突破,美与恶共生也是美学风格上的反拨。在人类文明史的源头,真、善、美往往是相生相伴的,它们形成一个和谐的圆。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美与善逐渐剥离——或者说,美与道德开始分裂。如果说,美与善的统一是“常态美”的话,美与恶的统一则是“变态美”。从这一意义上说,罂粟意象的兴起,也正反映了“变态美”的美学观念的崛起,它是中国多元、喧哗的文化氛围下的必然产物。
总之,罂粟的禁忌、悖论、致幻的特质是其意象发展的基点。正面一端是美丽、良药、亢奋、诱惑,负面一端是邪恶、毒品、毁灭、死亡。在这样的正负两极中,任意的排列组合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新时期罂粟意象的繁盛,带来的不仅是对于罂粟禁忌的解冻,相伴而来的,还有我们在分析罂粟的文化意义时所发现的原欲、颓废、死亡等禁忌的突破,反映了20年间文学从突破禁忌开始,至多元喧哗而终的总体态势。罂粟意象的文化意蕴的不断沉积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诸多要素不断被发掘的过程;罂粟意象在意象感觉化叙事方面的进展,也与中国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体验化探索同步;而其“变态美”则反映了新时期以来美学风格的变动和追求,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提供了一个新的镜像。
[收稿日期]2005-07-01
注释:
①曾梦莹《罂粟花》,《散文诗》2004年第五期,第36-37页.
②海男《危险啊危险》,《坦言》,作家出版社,1998版,第280页.
③张欣《深陷红尘 重拾浪漫》,《小说月报》1995年第五期.
④叔本华《人生的智慧》,张尚德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⑤张钧《穿越死亡,把握生命——海男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二期.
⑥海男《私奔者》,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⑦海男《生命圣经》,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⑧张钧《穿越死亡,把握生命——海男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2期.
⑨棉棉《糖》,《收获》2001年第1期.
⑩葛红兵《关于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十五条札记》,《花城》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