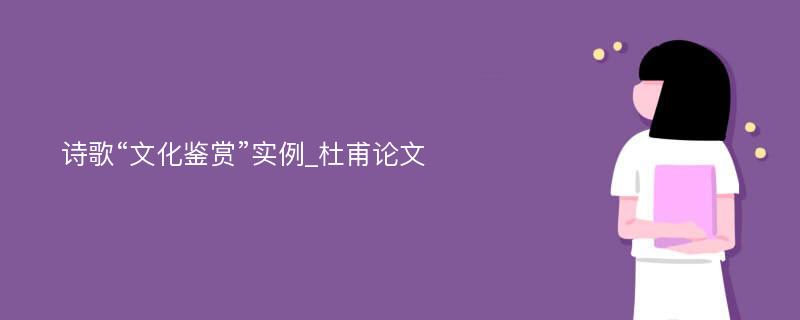
诗词“文化欣赏”举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诗宋词之美臻于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但唐诗宋词何以为美,我们似乎一直不甚了然;古代评点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哪些诗词是美的,却没有分析美的内在原因。当然,对某种事物的美感本来是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但当我们专门“欣赏”它们的时候,就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尤其对于被我们民族视为美的典范之一的唐诗宋词,就更应该追询其美之为美的内在原因。现在通行的所谓“艺术特点”、“写作技巧”之类的分析、总结对于提高我们审美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帮助,甚至“艺术特点”与文学的审美本质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联系,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文学之美——尤其是传统文学之美——与传统文化之间血浓于水的联系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传统文学之美是从传统文化的底蕴中生长出来的,离开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感受,对传统文学之美的体味恐怕只会流于表面。没有感受的理解是不真实的,没有理解的感受是不深刻的。这里从传统文化中选取了几个与唐宋诗词有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命题,以此为视角来“欣赏”几首唐宋诗词,希望有举一隅而三隅反的功效。
一、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追询——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孟浩然《宿建德江》“文化赏析”
陈子昂是初唐提倡风雅,进行文风改革的重要诗人,而他最为人们熟悉的乃是《登幽州台歌》。当时,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谙军事,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致使屡屡失利,他心情颇为抑郁,想起当年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参照《蓟丘览古》七首可知),于是吊古伤怀,故有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般的读者,极少会有人知道到陈子昂写此诗的前因后果,但还是一读之下,便被感动,这说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所谓“时代背景”的东西,而不受时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艺术品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时代背景”时,对它的感受反而减淡了许多,因为我们通行的“时代背景”解读法限制了人的超时空的审美想像。
从超越时空的意义上看,《登幽州台歌》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怀古意义,而是表达了深沉的悲剧意识,从中透显出了人的“觉醒”:当一个人独立于天地之间、直视生存真相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正处于空虚与惶恐之中,你会询问你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古人”和“来者”似乎皆不足为凭,过去和未来似乎也难以为据。那么,人难道就在这种困境中绝望了吗?不,个人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你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中,你就会在“悠悠”的天道中获得永恒。
这是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社会集体、道德本体、永恒天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道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自然本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虽然其中都不乏对建立高大人格的祈向,但始终缺乏要将个人从集体、社会或自然中独立出来的取向。所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与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吻合,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相吻合。
《登幽州台歌》同时还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方式。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对自己价值依据的追询开始的,只有走过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历程,才意味着人的“觉醒”。接下来的“涕下”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在觉悟了“天地之悠悠”——即获得价值依据之后的感动。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感受到《登幽州台歌》的文化底蕴。这种感受,相对于六朝人来讲,昭示着初唐时期的一种新的人格的降临;相对于中国人来讲,都应该会引起内心的感动,每一次阅读,都会使人产生一次思考价值、追询价值、确立价值的冲动和渴望,中国人的价值感便是在这种无数次的冲动和渴望中积淀而成的。
《登幽州台歌》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与西方悲剧意识相比,中国的悲剧意识并不仅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更不仅仅为人描绘出一幅绝望的前景,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弥合困境,在彰显出绝望时又指引了出路。中国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既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也与执着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形上与形下统一的体用不二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情节中感受“天道”,或者说是在“天道”的观照下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情节。这样,人生困境的暴露与弥合就在一首短诗中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对精神家园的追询和价值的建构。诗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中国人没有外在而超越的价值观念,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生来便被道德本体放逐,所以,在古典诗歌中,孤舟、漂零等有关的意象才那样的浓密。“移舟”二字将孤舟和漂零之意囊括殆尽,况且所泊之处还是“烟渚”,家园迷茫,无可求索。那么,为何“日暮”就“客愁新”呢?“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那日暮人归的图景,它在初民那里原本是极普通的,可数千年来不断地打动着我们的心?今日读来,犹使人在沉醉中挟有绵绵的心痛?那不是梦幻,而是一种虚灵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原型,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是对失去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是再也回不到故乡的永恒的伤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靠每人在生命的历炼中不断体味的,精神家园是在不断的呈现中存在的,追询的过程便是呈现的过程。所以,每当象征家园的日暮来临时,无所归依的游子便要起家园之思,等待着精神家园一次又一次的新鲜的呈现。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人与自然亲合的图景,是精神家园呈现的物化形态,为前面的追询提供了归宿。所以,这首短诗概括了我们民族追询精神家园和家园呈现的情绪流程。
二、在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之间——杜甫《登高》、《秋兴八首》(之一)“文化赏析”
杜诗的艺术特征是由其文化内涵决定的,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进行深入的把握。杜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沉郁顿挫”,杜甫自己在《进〈雕赋〉表》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此处的“沉郁”,是指学养深厚,“顿挫”是指节奏的抑扬缓急,后来的含义有所不同,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感,忧国忧民的价值关怀,浑融含蓄的气象,抑扬顿挫、回旋张驰的节奏。例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首联起句突兀,如狂飙来自天外,将全诗笼罩在沉郁悲壮的气氛中,但又透显出大化流行的刚劲和廓大深邃的情感追求。颔联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它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个体的生命也许没有希望,但天道是永恒的,只要将个体的生命与价值融入永恒的天道,个人也就可以获得某种永恒。此联在暴露人的困境的同时又弥合困境,使人在超越中得到归宿,但这种超越又不是廉价的,往往要在“艰难苦恨”中完成,所以,在颈联和尾联中,杜甫尽情地抒发了个人的悲剧感。然而,因为有了首联、颔联的铺垫,杜甫的悲剧感便获得了审美性的超越,他的“悲秋”、“多病”、“苦恨”、“潦倒”也就成了超度他的梯航。从“沉郁”来讲,全诗表现出一种儒者式的悲剧情怀;从“顿挫”来讲,不仅音韵上抑扬顿挫,结构上有着内在的回旋张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一种历经痛苦而走向超越的祈向,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对含蓄和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的追求相契合。
其实,“沉郁顿挫”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是对现实中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表现以及对理想中天道与人道的亲合的追求,只有在这种表现与追求的张力中去理解“沉郁顿挫”,才能把握其真正的韵致。在传统文化中,天道与人道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关系,即疏离与亲合。所谓疏离,即天道永远高于人道,在现实的层面上永远无法达至天道;所谓亲合,即天道不仅出自人道,还要还于人道,即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这是从心理体证或形上意义上讲的。现实中的疏离和理想中的亲和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上述的“沉郁顿挫”正典型地概括了这种张力的诗性特征。
再如《秋兴八首》(之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如果说上一首更多地表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话,那么,这一首就更多地表现了二者的亲合。首联从自然运转、山川气象着眼,而秋霜化为“玉露”,枯树变作“枫林”,在德配天地的仁者的眼中,秋天只能徒增凝重与爽厉之美。颔联则通过对“波涛”和“风云”的描写透显出大化流行的气势与厚重,在前两联的映衬下,颈联更是将一般思乡之情演绎成了漂泊的游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尾联是对普通人事的描写,但在“暮砧”的敲打声中,你不更加容易趋向心灵的家园吗?全诗以天道始,以人道终,天道与人道首尾相接,合二为一。
从“艺术”上看,诗作前四句沉雄俊厉,可谓“沉郁”之极,但不仅在“玉露凋伤”中就将严酷内化为道德,更在“孤舟一系故园心”中将前四句化作了追询精神家园的外在契机,且在尾联中落实到现实的家园,使其过程变得十分“顿挫”。沉郁顿挫之美是一种浑融的美,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
疏离是现实状态,而亲合是一种冥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境界。在由现实的疏离走向心理冥证的亲合中,其“沉郁顿挫”之美才能得以更好地显现。
三、彰显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昌龄《出塞》“文化赏析”
苏轼处在宋词发展的关键时期。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主要在于所谓的宋世风流。狭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浅斟低唱、歌舞宥酒的都市生活风尚,广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汉唐政治本体意识的消解,宋学与禅学的入世转向相融合,政治—文化政策和经济—商业政策的宽松,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的融汇,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这样,“主情”的宋词便必然要在“言志”的唐诗之后大行其道。
然而,词是“诗之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与诗争衡的俗文学,如何使词上升到雅文学的殿堂,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古人早就论及了这个问题,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题酒边词》),况周颐说:“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其实这说的就是苏轼对词的雅化。雅化的实质是将词变成了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使宋代的世俗精神雅化了,即使执著现实走出了感性享乐的泥淖,把现实生活提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世俗精神也就上升到了形上的高度。这样,苏轼的词就有了厚重的文化意蕴。
苏词在很多情况下将在过去只有诗才可负载的文化意蕴纳入词中,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以诗为词”。如人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此词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它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相吻合。中国人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因此英雄梦便是生而有之的理想。此词开端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唤起了人的英雄梦想,深契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给人以无限的热情和向往;然而,苏轼在唤起人的英雄梦的同时又打破了人的英雄梦,他以自然与历史的永恒和人事的虚幻与英雄的无奈相对照,传达出深沉的悲剧意识,也激发了人们对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与追询。可以说,只此一句,就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流程。下面的描述无非是为了说明和论证开端的一句而已,起到的仅仅是例证的作用,但自“故国神游”以下,则转入了对上述悲剧意识的消解。中国人传统的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有仙、酒、自然、梦、女人等,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数句中,除“仙”之外,其余诸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居然都包含其中。从慷慨壮志到悲剧意识的消解,正体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暴露”与“弥合”的双重特点,也概括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流程。
再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前人说:“此词一出,其余中秋词尽废。”那仍然是因为它描绘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句,代表了自屈原《天问》以来的中国人以诗性的方式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追询。苏轼超越了现实功利的拘囿,以一颗自由的心灵来贴近自然和宇宙,但心灵的超越不可能在瞬间构建起新的价值观念,所以必然要在一定意义上返回现实,所谓“高处不胜寒”,正是在进行价值追询时的心灵感受和无奈的结局,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理过渡。至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则是苏轼追询之后得到的现实答案。然而,这种形上追询—心理过渡—现实答案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历程决不仅仅是一种无谓、简单的重复,苏轼最后虽然仍旧落脚在现实的伦理道德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这已经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伦理道德,而是心理本体化的伦理道德,即以一种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命,已经具有了对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突破的意义。
人的心灵需要不断地洗礼,才能保持新鲜。词的上阕是心灵的询问,也是心灵的洗礼,洗礼过后,人们就会以新鲜的情感来感受以下阙为代表的现实的生活和生命。因此,此词以富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典型的意象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民族文化心理,使之深合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并在结尾处激发了人的超越性的美好情感,充满了传统的生生不息的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出塞》也同样彰显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起句铺陈时空,将人的思绪引向浩远的历史背景,在秦月汉关的映照下,人们会自然生发出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追询;第二句则从历史回归现实,从背景聚焦到人物和事件:边塞战争古今一贯,略无停歇,但“长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如此多的艰辛与死亡?这种平易直白的陈说却恰恰使诗作的悲剧情怀落于眼前;三、四句是在悲剧情怀中透显出希望,但这种希望决非廉价的,“但使”二字透显出现实的艰难性,从而完成了由悲到壮的情绪转换,也使“秦月汉关”和“万里长征”有了超越性的意义。全诗虽然只有四句,却极为精到地概括了我们民族对于战争以及历史的悲—壮—希望的心理流程和情感态度,这是其备受推崇的内在原因。这里可将王昌龄的《出塞》和王翰的《凉州词》加以比较,后者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虽有疆场生活的豪迈、慷慨,甚至还有对待死亡的洒脱,但毕竟缺少了对价值的追询和超越性的希望,所以不能深度契合民族的文化心理,受到的推崇自然也就不如前者。
四、体味仁德——杜甫《望岳》“文化赏析”
泰山是五岳之首,其性主仁德,孔子当年“登泰山而小天下”,历代封建帝王对泰山的“封禅”,都为泰山规定了这样的品格,似乎是无庸置疑的,但如何表现泰山的“仁德之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难题。杜甫的《望岳》似乎是迄今为止的最好的一篇“泰山游记”。
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使诗歌与传统文化的主流发生了内在的关联。忽视了这一点,就很难读懂杜甫的一些富有文化意味的诗歌。《望岳》这样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深入品味,我们会在杜甫的诗中体会出那股潜隐其中的深厚的“仁德”味道:五岳之首的泰山是怎样的呢?啊,原来她在青翠无垠的齐鲁大地上拔地而起。这青青未了的齐鲁大地,不正与人的自然而然、无边无际而又生生不息的“恻隐之心”相通吗?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涵孕出泰山般的仁德之心。这分割阴阳昏晓、是非曲直、仁与不仁的泰山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造化的钟爱。造化为什么钟爱泰山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造化只钟爱哪些仁德之物,只有道德自觉,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其实,这上天或造化就是道德自觉本身,它内在于我们的心中。登上泰山,是怎样的感觉呢?那在胸前荡漾的层云啊,仿佛要让人凌空而起,但脚又踏在坚实的泰山上,这也许就是那种执着而又超越的感觉吧!再加上归巢的鸟儿,仿佛都归入了我的眼睛和心灵,天地万物就都摄入我的胸怀了。在现实中体味超越性的意义,“万物皆备于我”,正是仁者的胸襟和情怀。最后一句说,当人登上绝顶的时候,真正体会到了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感觉,可以自由地俯瞰万物了,就获得了自由而超越的人格,也许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吧!可以说,《望岳》一诗形象地展现了由葆守恻隐之心而达到道德自觉并进而体味道德的各个进阶的全过程,当然也正是我们追求自我提升的全过程。
仁德在体味中呈现和建立!当然,这样感受杜甫,有所谓的“比德”的意味,甚至有以朱熹之法解诗的嫌疑,但不这样理解,读《望岳》时的那种深挚的感动就无法解释,《望岳》何以成为名诗,也很难理解。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带着近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形成的某些偏见来看待传统诗文的话,我们还是会承认《望岳》的确显示了儒家成仁思想的基本理路和对仁德的体认与感受。也许,无论是杜甫当年写《望岳》和我们读《望岳》时都没有想到这样多,但这些又确实是隐含在我们心里的,并以潜在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如果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望岳》以及许多著名的诗词就是所谓的语言的空壳!
如果一定要说唐宋诗词是一种“形式美”,那这种“形式”就是传统文化艺术的外化形式,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形式美。事实上,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的情感的发展史,当然,人的情感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的发展史。我们既不能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同样也不能忽视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人的情感的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人的情感又是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是被抛到历史之中的,是在以某些文化母体、传统观念为前提的情况下感知、运思和生活的。因此,如果能在文学和文化的张力中感受文学,考察文学,那又将是另一番不同的情景。
标签:杜甫论文; 文化论文; 泰山封禅论文; 登幽州台歌论文; 读书论文; 出塞论文; 天道论文; 望岳论文; 泰山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