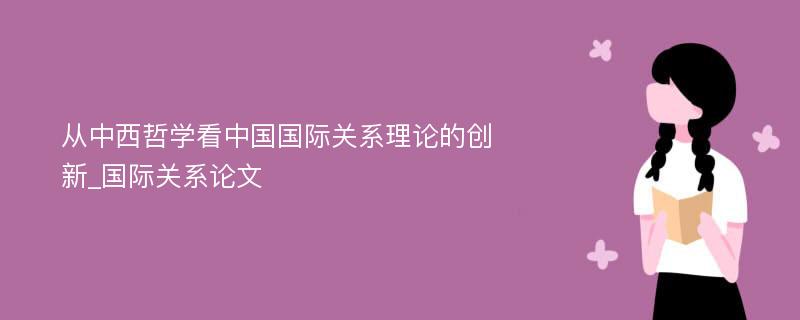
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中西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直为欧美学者所主导创生并为欧美哲学和政治理念所浸染,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进步主要体现为欧美学者之间的学理论争和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扩散传播态势,中国、印度、埃及和巴西等国一些别具特色的理解被遮蔽或湮没在欧美话语体系之下,原本因现实政治需求不同和各自文化差异而呈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日益演变成为欧美思维与方法一统天下的知识格局。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化进程压力所致一些国家本土精神的觉醒和本土文化的复兴,以及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带来国际力量中心和意识形态的变动,还有诸如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对国际政治运行规则的改变,使得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式思维路径和话语主导权备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的非西方路径与非西式理解日趋活跃,并发展成为国际学界的呼声。 有中国学者主张: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本土问题、凸显本土需求,反映本土视角。①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果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非西方视角和非西方路径,那么,中国学界应如何创生自身的核心概念体系并勾勒自身的理论特征?本文试图通过中西哲学对比,阐明客观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若隐若现的本土思维痕迹,以及这种思维之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概念重构意义。 一、国际关系研究西式思维困局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一直被牛顿经典力学和笛卡尔“心—物”二元论所左右,而作为社会科学谱系中新近才发展成形的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学更是深陷牛顿经典力学世界观的影响之中。概括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国内”二元分立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基础。综观西方国际关系文献,绝大部分理论普遍预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是不同的:国内政治有权威、有秩序,而国际政治无权威、无秩序,以致无政府状态几乎成了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公设和逻辑起点。②虽然对无政府状态的含义理解有所不同,③但这些理论普遍假定了牛顿力学原则之于该状态下问题解决的启发意义,即力的平衡与约束。④迄今为止,西方战略界所能够想到的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不外乎权力平衡与建立集体安全架构。18世纪、19世纪,自卫(self-help)或结盟以抗衡强者是西方各国战略文化的主导层面;进入20世纪,面对集团对峙所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各国转而寻求建立区域或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先是国联,而后是联合国、北约和欧盟,所有这些和平设计思路与安全解决方案,均未超脱牛顿世界观的机械力学束缚。透过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特别是以沃尔兹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了一个“原子世界”。在这个“原子世界”里,各个国家是分立的实体,彼此之间基于力学原则而互动。⑤ 第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疏离是西方国际关系思维的主导特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自我”和“他者”通常被描述成彼此分立且对立的实体,有时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被单向性地想象成一种生存意义上的“零和竞争”关系。例如: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刻画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对抗,⑥而以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倡导被压迫者、被遗忘者对现存秩序的颠覆。⑦当然,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对立的言说,卡尔·施密特和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最为世人所知。前者指出,一切政治的真谛在于区分敌友,无政府状态总是内生于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划分,⑧任何一个自我身份的形成都必然是排他性的,即自我通过贬抑、排斥他者并将他者标定为“敌人”或“对手”而获得自我身份之确立;后者则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的冲突性极易建构群体间冲突,一旦陷入不仅难以摆脱而且兼具进化性质:先是文明断裂带之间的对抗,然后蔓延至由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发展成为“亲缘文明集团”之间的战争。⑨凡此种种,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维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第三,寻求基于实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因果解释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宗旨和兴趣。虽然最近一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围绕着本体论和认识论而展开,但辩论的结果至今没有解决“物质与理念谁更重要”“结构与施动者谁更优先”“理解和解释谁是更适宜的研究方法”等问题,⑩仿物理学因果解释进行经验观察和规律总结仍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宗旨和兴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11)及“复杂系统理论”(12)的兴起,基于国际关系“原子论”主张的还原主义解释开始备受冲击和挑战。(13)还原主义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然后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也就是说,在还原主义看来,各种现象均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孤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然而量子论的崛起和复杂科学的诞生却说明,还原主义的解释不仅割裂了人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还忽略了行为体的能动性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最终朝向线性思维和机械的决定论主张。(14)及至最近,当温特宣布“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时”,(15)其欧洲的同行和批评者们认为“温特已经和他的批评对象们处于同一阵营了”,(16)决定主义和确定性分析已然侵入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 概言之,在这种“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世界通常被划分为两两相对的论题,譬如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民主与威权、开放与封闭、自我与他者、敌人与朋友……这些相互对立的命题往往无法自我证成,也无法相互证否。在现实决策和经验观察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这种“二元分立”的方式简化我们对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认知,以致在日常实践中,我们不自觉地建立起一个二元疏离的世界,而我们的思维则不停地在寻求分立的平衡感,譬如恢复势力均衡和重塑心理平衡等。 二、重塑观察世界的角度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以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迷恋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组成部分并不足以引导我们理解整体。1991年,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奥多·贝克尔在其编著的《量子政治学:量子理论的政治应用》一书中写道:“旧的政治运行连同政治科学太过附着于牛顿物理学的启示。而如今,随着整个科学界正在远离机械论、原子论和决定主义转而追求新的世界认知范式,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到了不得不如此跟进的时候了。”(17)为此,他组织了一个九人政治专家小组进行“思想实验”,以求能够凭借量子启示超脱于牛顿世界观的政治思考之外。1996年,《科学美国人》杂志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总结道:“在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下,科学已近终结”;“有关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来自哪里的知识探索,已经进入一个报偿递减时代”;“将来的研究已不会有多少重大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除非我们拥有新的世界观的指导”。(18) 在物理学领域,人类观察世界的传统认知模式最先受到挑战。1905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冲击了牛顿绝对时空观,有关物质世界的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解释开始备受质疑。之后,量子力学的勃兴尤其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与哥本哈根诠释,更是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有关自身及客观世界的确定性理解。透过量子力学的哲学透镜,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颠覆,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非实在性、世界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日益被科学研究所强调。当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有关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应照搬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这已为诸多国际关系文献所阐述。然而,若要放眼当前的国际政治运行和国际关系研究,二元分立的简单世界划分、线性工具主义的还原解释及源自牛顿经典力学的平衡原则仍是我们目前的主导思维方式。未来,还原主义、机械论和二元分立哲学能否继续指引我们认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自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范式革命问题。可以说,我们所处时代远不是“科学的终结”,而是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甚至超越于“二元分立”思想的新的世界认知方式。(19) 有不少学者指出,以强调整体演进、对立统一和不确定性、复杂性为特征的“二元互补”哲学,或许能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新的见解;(20)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理念和历史文化积淀的二元互补思维,或可超脱于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哲学之外,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视角和人文关怀重新审视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二元疏离世界。继而,有学者强调指出,中西学者之于国际关系思考皆可有自身的独特视角,中式辩证法与西式辩证法存有大不同。西式辩证法注重实体思维,是对世界的分离性想象与建构,人自身的存在被不自觉地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人之于这个观察世界的价值不是被忽视、遗忘就是被遮蔽在工具主义的物化影响之下;而中式辩证法则强调过程建构、阴阳互生、祸福相依,是一种关于世界及人本身存立的互容互补思维,在互容互补思维下“天人合一”,主观不是对立在“客观”之外,人只有在与自然、与周边世界同体共存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21) 中式互补概念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得即失”、“非生即死”的线性零和思维,而是一种“A可以非A”、“在与非在共存”的过程流变思维。(22)换言之,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过程与行为体互补共存、相互建构,对立的二元命题总是共存于同一过程之中并相互容纳、相互转化。有关这一中式思维的形象表述,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东方文化中流传已久的太极阴阳图。(23)这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工具思维和理性因果思维,而是一种圆的存在与整体演变启示。这意味着,“在国际社会里,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过程而天马行空,也没有任何过程可以没有国家而以空中楼阁的形式存在”。同理,物质与观念、主观与客观、激情与理性、自我与他者也不应当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这些对立的命题是同体共存的。 有关中式互补思想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汉学家李约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在过去2500年中,人类科学与文明始终存在着相互独立的两大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思想内核是机械还原论,后者的思想内核是互补整体论。他强调:“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阔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服从于其自身的内在支配。”(24)而如今,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瓶颈”问题,新科学的崛起则与古老东方思维的互补理念不谋而合。 三、基于“互补原则”的中国式概念诠释 尼尔斯·玻尔的量子理论指出,波粒二象性是物质的本来存在形态,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无法将我们的主观意识排除在外;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可还原、可分割的机械原子论世界,而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量子纠缠世界;以至于我们对某一现象的解释通常会用到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一对属性概念,譬如粒子概念和波概念。(25)虽然认知多有差别,但源自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互补理念,则同样强调世界的整体存在性和物性的对立相反且统一,有关事物的性质表述,中式传统思维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26)“万物负阴而抱阳”,(27)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反且互补的“阴”“阳”物性,绝对不存在分裂对立的孤阴、孤阳现象,阴阳不是形式互补关系,而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质。(28)就此而言,互补理念与传统分析哲学强调二元疏离、矛盾冲突不同,它主张二元同体共存、对立统一。本文认为,这一思想之于当前的国际观察而言,具有概念重构和理论重建之意义。 (一)“结构”的再定义:物质与观念的同体共存 按照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划分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两大阵营,且两大范式之间因核心立场的不同而在理论上相互攻讦。物质主义认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性特征主要是指以经济和军事实力衡量的权力分布状态,体系中行为体的偏好及其行动原则遵循物质实力的约束性要求;(29)理念主义则认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性特征主要是指体系中主体间所共享的观念结构,行为体之间的身份认知界定彼此的利益,进而决定各自的行为。(30)也就是说,物质主义强调“结构”是物质性的,观念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体系结构呈“孤阳”状态;而理念主义则认为“结构”的主要成分是观念性的,如果没有观念赋予物质实力以具体的意义,物质力量的作用发挥就无从谈起,体系结构呈“孤阴”状态。 而根据量子互补原理和阴阳互补理念,二者虽有差异,但均强调物性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无论是物质主义的“孤阳”表述,还是理念主义的“孤阴”阐释,都不足以描述现实中“结构”的完整存在状态,长期盛行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系方法需要被重新审视,“结构”概念也需要在互补原则下重新被理解。按照“阴阳互逐、互补共生、同体共存”的中式互补理念,国际关系行为体所置身于其中并在其中运行的体系结构是一种复合结构,即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在具体历史时空下的同体共存和相互建构,物质与观念皆是“结构”的存在描述。在大部分国际关系状态下,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并不单独存在也不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合二为“一”、共体共存,共同发挥作用且二者无主次之分,其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时而因果约束,时而社会建构,或兼而有之;只是“一”的概念与形式,或因物质因素的改变或因观念因素的重构而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状态朝不同方向演变,或进化冲突,或进化合作。 就此而言,所谓的“结构选择”不是指单纯的物质力量约束,也不是指单纯的观念力量建构,而是指不同的观念结构(政治认同)与不同的物质结构(权力受控)之复合结构选择,(31)行为体会基于特定权力关系与特定认同关系的流变,选择或适应不同的社会化方式,内化和遵循不同的体系规范,从而建构和加强不同的偏好取向。根据物质与观念的互补互构原则,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选择”至少应具有以下四种典型含义: 1.低度政治认同与高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定通常被放置于生存意义上来考虑,物质实力的意义在二元分立的话语系统中常常被朝向负面建构,以致权威强制型社会化是此种“结构选择”的必然逻辑,譬如罗马帝国、蒙元帝国及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对被征服地区和国家所采取的强力民族同化政策或殖民政策。当然,帝国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地方及边远地区所采取的强制性文化统一,如中国秦汉时期的文化大一统政策,也可视为典型经验案例。权威强制型社会化的实现条件是:暴力使用或暴力资源被绝对性地垄断和控制在某个政治行为体或政治集团手中,同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的分离性认同状态。 2.低度政治认同与低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无政府状态是体系结构的主导特征鉴于并不存在着一个可以垄断和控制国家间暴力使用的超级权威,也不存在着一个可以创制和强力推行某些适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中心机构(如帝国或世界政府)。“以力假仁者霸、以仁假力者亡”,利己主义较利他主义更易为体系行为体所学习和内化、生存竞争更有利于那些类属身份和团体身份再造型规范的扩散与传播,(32)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的天下失序与春秋战国争霸、1648-1945年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程及1946-1990年间的美苏对抗与东西冷战,均可看作是此种效率竞争型社会化的典范。在这样的社会化过程中,权力是决定“谁的规范将被遵守和内化、谁的规范将被排斥和抛弃”的关键性因素,生存竞争的目标在于消除他者的类属身份和团体身份。 3.高度政治认同与低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无政府状态(即国家之上无更高权威)依然是体系的主导特征,但权力的影响被逐步弱化,而规范的作用日渐崛起。自我已不再经常性地将他者看作是己方身份和利益的威胁者,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日益转向和集中在“如何使国际关系更加良性运行,如何使体系进程更趋和平与繁荣”等原则性问题之争上,商谈和妥协日趋演变为国家对外行为的首要偏好,进而体系整体的道德规范也将朝向和平主义演进。 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尽管并不存在着一个垄断并合法化使用暴力的超国家机构,也不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设定并强力推行体系规范的社会化行为体,但自1945年以来北欧各国已很少相互为敌,彼此之间有关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倾向于诉诸协商手段而不是暴力解决或以暴力相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已成为进化合作的典型样板,堪称世界“和平区”(Zone of Peace)的典范。 4.高度政治认同与高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复合结构下,行为体自我身份基于集体认同而确立平等协商、理性沟通、论争说服逐渐成为解决矛盾和协调利益的主导方式。各国之间不仅诉诸战争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而且在心理上相互为敌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反常现象。友好交往、坦诚相待是该结构的主题。 也许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朝向这种理想世界建构的最大胆想象,不幸的是都不怎么成功。因为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国联和联合国的设计缺陷既无法阻断暴力的合法使用,也无法有效规范体系行为体,使之建立起“天下无外”的集体认同。相比之下,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这种复合结构的样板要成功得多,因为欧盟既试图集中控制暴力,使得暴力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同时又试图为欧盟各成员国建章立制,并推进欧洲整体层面的集体认同,使各成员国尤其是法德在心理上不再相互为敌。 简言之,在不同的物质与观念结构复合形态下,行为体会基于特定的权力关系与特定的认同关系,选择不同的规范加以内化和遵循,从而加强或弱化权力政治的影响,此即基于“互补原则”的“结构”概念再理解与选择性社会化进程。 (二)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再审视:进程的重要性 进程是结构与施动者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层次,但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轻视或忽视了。进程是不断流变和演化的,但进程并非总是不断进步的,有时它具有可逆性,(33)而决定体系进程究竟是朝向进化冲突还是朝向进化合作演进,关键取决于体系复合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物质与观念复合结构下,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不仅会建构彼此间不同的身份认同,而且也会导致行为体优先选择内化某些规范和观念,同时拒斥另外一些规范和观念,从而对行为体持久偏好的形成和结构的物化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行为体所处互动情势——物质与观念的复合形态——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导致行为体互动模式和社会化机制的改变,随后导致行为体身份与偏好的转变,进而诱发体系进程转向或转轨,并最终带来体系结构的变革。 具体而言,进程是对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互动之描述。过程既是互动关系的复合体,同时也是互动关系得以运作的时空境域。(34)行为体与结构同存于进程之中,并因进程的改变带来二者之间关系及二者本身存在性质的转变。正如太极图所示阴、阳、圆三位一体并同体共存那样,结构、施动者和进程也是同体共存的。进程是对结构和施动者关系的整体描述,而结构与施动者则是对进程的阴阳分形的阐述。脱离了结构与施动者,进程则不存;脱离了进程,结构与施动者则无时空寄存。互补理念揭示了结构、进程与施动者的任何一方既无分析上的优先性,也无本体论上的原初性,对三者关系宜做整体论理解。 (三)结构的双重作用 互补理论强调阴阳互逐、祸福相倚,即对立的双方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缔造体系的整体存在状态。就此而言,施动者的施动性和人的意义应当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应回归到对人及人类群体间互动的分析,亦即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应是有关人自身存在、人际关系和人的能动性的研究,人对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理解不应被忽视,施动性也不应当仅仅限于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既是结构又是行为体的“结构化施动者”(structural agent)或“施动性结构”(agentive structure),(35)这类行为体的意图、能力和活动方式也应当被予以充分重视。 譬如,国家相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它可以被看作是施动者;而相对于国内行为体而言,它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系结构;(36)再如,欧盟相对于世界体系只是一个施动者,但相对于欧盟成员国则变成结构。(37)概言之,国际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体,基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它兼具施动者与结构双重身份,因而在关系互动和体系进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具体而言,此类“结构化施动者”或“施动性结构”不仅具有控制体系暴力、限制行为体行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同时更具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社会化行为体,使之不断为社会整体所接受而不被认为是体系中的异类之作用。进而,拥有特定身份并知晓其利益的施动者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会反过来再造、加强或改变体系结构和体系进程。 简而言之,在互补理念下,不仅人对意义的需求和理解、人的施动性可以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而且结构和施动者的关系也将得以重塑,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同体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性质描述,从而国际关系研究不必为了简化体系分析而抛却施动者及其施动性,也不必纠结于“结构与施动者谁更具有分析上的优先地位”等问题。整体而言,互补原理将提供一种不同于“二元分立”哲学的国际关系观察角度,其实质是整体论对还原论的质疑和挑战。 四、个案研究:互补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 古老中国的互补思维与西方的“二元分立”哲学存在大不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两种思维方式在东西方世界各自流行且并行不悖,尽管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元互补思维的光芒一度为二元分析哲学所遮蔽,但作为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互补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世界格局论 与西方分析哲学还原论对世界的描述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对国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认知更多是采纳了一种基于互补原则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可以简单称之为“世界格局论”,即中国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描述不仅是一种互补性概念的结构阐释,同时也是一种强调事变时移的过程流变思维。所谓的“世界格局”是指力量的对比与政治倾向的匹配,譬如: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8)之后,邓小平于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39) “三个世界理论”表明,国际关系世界不仅是按照物质实力排序的,同时也是按照政治倾向划分阵营的。就此而言,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虽然物质实力较弱,却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由此决定了中国应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中不可动摇的力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它们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人使用的“世界格局”概念更多体现为一种物质与观念相匹配的互补思维,而不是二元分立哲学,这在根本性质上与西方所惯用的“体系”概念和“结构”概念存在天壤之别。按照沃尔兹的解释,“国际体系”是指功能相似和相同的国家按照一定的物质实力排序所形成的结构和互动状态,因而所谓“体系变革”也主要是指国家间物质实力的增长及其对比状态的变化,(40)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定义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主体间理解和主体间共识的“文化结构”,任何体系的深层变革都必然是指体系的文化观念变革,比如从“霍布斯文化”进化为“洛克文化”进而“康德文化”。(41)如果说沃尔兹对国际环境做了物质主义的“孤阳”表述,那么温特则走向了二元分立的另外一个极端,对国际环境“结构”做了观念主义的“孤阴”描述,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环境认知之于外交决策都是有明显信息缺失的,不利于明智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二)和平发展论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全球热议话题。在诸多西方学者看来,一个在政治理念、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的古老中国之崛起,必将给现行国际关系体系带来冲突和挑战。然而,若是根据中式互补理念加以思考,中国崛起之于世界的意义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对自身发展及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是二元互补型的,既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也强调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二者共存共生、共荣共损。在这一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人认为自身的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冲突,反而会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会给当前国际关系运行中的权力分配和观念分配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效应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关键要看中国所要选择的发展道路:如果是一种物质实力的增长与冲突、掠夺型外交理念相结合,那么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则是危险的;但如果是一物质实力的增长与和平、合作的外交理念相结合,则中国的发展则是惠及世界的,不仅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带来世界的和平。幸运的是,中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看世界是互补共荣而不是分立斗争的,这种文化基因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不应仅建立在二元分立哲学的基础之上,古老的东方思维也应有贡献于国际关系研究。一个二元分立的世界是零乱、冲突的世界,一种互补型思维方式也许并不足以将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但至少可以提供某种别样的思考和启迪。无论是量子政治理念还是关系本位阐述,都应当被视之为对还原论世界观和牛顿力学原则的超越,从“二元对立”到“二元互补”是国际关系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二元互补”思维方式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将不再是一个二元疏离的世界,也不再是一个类似于弹子球的机械互动世界。互补思维告诉我们:世界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自然与社会、物质与观念、结构与施动者、建构与解构、解释与理解等命题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很多时候它们之间存在对话和融通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聚焦客体和结构,同时也不应忽视施动性和过程。 注释: ①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苏长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第47—55页;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34—40页;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32—66页。 ②有关“国际/国内”二元分立的经典表述可参见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Y:Alfred A.Knopf,1948;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而有关“国际/国内”二元分立认知的批判则可参见Colin Elman,“Horses for Courses:Why Not a Neorealist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6,No.1,1996,pp.7-53; Peter Gourevit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0。 ③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相关阐述和批评可参见Josh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pp.485-507;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 Barry Buzan,Charles Jones,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④牛顿力学有三大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此处专指牛顿第三定律,即力的作用与平衡。 ⑤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0页。 ⑥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Systems Analysis:An Introduction,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Columbia University,1992; 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Iver B.Neumann,“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2,1996,pp.139-174. ⑧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6. 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Vol.72,No.3,Summer 1993,pp.22-49. ⑩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次大辩论,可参见Emmanuel Navon,“The‘Third Debate’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4,2001,pp.611-625; Tanja E.Aalberts,Rens Van Munster,“From Wendt to Kuhn:Reviving the‘Third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6,2008,pp.720-746; 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p.235-254。 (11)Robert Hariman,Post-Realism: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Vol.50,No.2,1998,pp.324-348. (12)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David Byrne,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Routledge,1998. (13)有关还原主义的批判可参见David Alberts and Thomas Czerwinski,eds.,Complexity,Global Politics,and 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1997; Fred Halliday,“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New Reductionism?”in M.Ebata and B.Neufeld,eds.,Confronting the Politic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K:Basingstoke,2000,pp.47-71; Neil E.Harrison,ed.,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14)Alexander Wendt,“Flatland:Quantum Mi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Hologram,” in Mathias Albert,Lars-Erik Cederman,and Alexander Wendt,eds.,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Palgrave,2010,pp.279-310. (15)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4,2003,pp.491-542. (16)Stefano Guzzini,and Anna Leander,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 (17)Theodore L.Becker,ed.,Quantum Politics:Applying Quantum Theory to Political Phenomena,NewYork:Praeger,1991. (18)[美]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跋。 (19)[比]伊利亚·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 (20)Liu Xiaogan,“Taoism,” in Arvind Sharma,ed.,Our Religions,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3,pp.229-289; Nicholas D.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China Wakes: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China,London: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1999; Daniel A.Bell,“Just War and Confucianism.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Daniel A.Bell,ed.,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226-257; Amitav Acharya,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Taylor& Francis,2009. (21)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69—86页。 (22)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23)同上书,第49页。 (24)姜岩、朱清时:《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25)[英]曼吉特·库马尔:《量子理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世界本质的伟大论战》,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六章。 (26)《易传·系辞上》。 (27)《老子·四十二章》。 (28)吴全兰:《阴阳学说的哲学意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55—58页。 (2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30)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31)在这里,所谓的“观念结构”指的是施动者之间的政治认同性质(聚合性认同/分离性认同)及其强度;而“物质结构”则是指体系力量对施动者之间相互使用暴力的控制程度和垄断程度。 (32)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将身份区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集体身份。其中,前两种身份是行为体的自组织身份,对应行为体的生死存续和类型转换,如国家本身的消失和政权类型的转换;而后两种身份是社会建构身份,依托于共有观念和共享理解,只存在于交往互动和文化传承过程之中。相关论述可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90页。 (33)此处的“可逆性”主要是指随着某些新的国际规范和体系文化的确立,国际关系由好到坏、由合作到纷争、由有序到无序的演变态势。 (34)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76页。 (35)“结构化施动者”或“施动性结构”概念本质上源于如下互补主张,即结构限制社会交往互动,同时又为社会交往互动所建构。较早使用这一概念或思想架构分析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的作品可参见Andreas Gofas,“Structure,Agency and Intersubjectivity:Re-capturing the EMU Policy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ist Realist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workshop of the European Political-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May2002; Ian Manner,“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2,2002,pp.235-258; Michael Alan Brittingham,Reactive Nationalism and Its Prospects for Conflict:The Taiwan Issue,Sino-US Relations,and the‘Role' of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6。 (36)相关讨论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3,1994,pp.241-251; Colin Wight,“State Agency:Social Action Without Human Activ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2,2004,pp.269-280; Jonathan Joseph,“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Scientific Reali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No.1,2008,pp.109-128。 (37)Richard Whitman,“The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EU:Instruments as Identity,” in Alice Landau and Richard Whitman,eds.,Rethinking the European Union:Institutions,Interests and Identities,Basingstoke:Macmillan,1997,pp.54-71; Ian Manner,“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2,2002,pp.235-258.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39)《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人民论坛》1994年第10期,第15页。 (40)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1)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Ⅵ.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牛顿力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