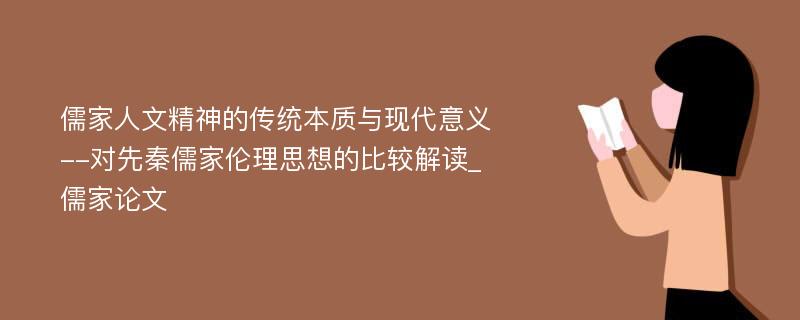
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试以先秦儒家伦理为例:一种比较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先秦论文,为例论文,伦理论文,本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文精神”之所谓
迄今为止,“人文精神”似乎还只是热门话题中的一个高频率用语而未能获得严格的概念界定,这无疑有碍于有关人文精神的深入讨论。因此,在具体展开本文主题的讨论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作一番必要的概念梳理,以期为下文的铺陈设定明确的论理界限。
要明确“人文精神”之所谓,似当先了解“人文”之所指。汉语中“人文”一词的原始意义与“天文”、“天运”相对应。《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有云:“舍诸天运,征乎人文。”由此识得人文二义:(1)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2)与自然物事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就第一种意义言,由于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之文明化的基本标志首在文化学识,且最初的文人学识主要集于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科目,故所谓“人文”者主要指包括上述科目在内的“人文学科”。就第二种意义言,因天人关系或人自关系是人类(不只是中国先民)早期认识的最基本主题,“人文”一词因之获得与“物理”、“天道”相对应的“人性”、“人道”意义。
汉语“人文”一词的原初意味正可参西语中同一语词的内涵,这是翻译家们用它来转译西语同一语词的基本依据。西语中的“人文”源出其母语拉丁文中“humanus”,引为“humanitas”(人文学科),为14—15世纪意大利世俗“异端”文人(如“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用以标异于正统经院“神学研究”(studia divina )的世俗“人文研究”(studia humana)。这一世俗人文化趋势正是此时在西欧(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和中心点)所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标志,其内容是通过世俗文学、诗歌、绘画艺术等方面向古希腊、拉丁(古罗马时期)语言、文体和方法的传统复归方式,创造一种别于(或毋宁说一种足以对抗)教会神学体系的新文化,并以这种新文化为思想载体,宣传和确立一种以人为思想中心和价值本位的新时代理念,而这一新时代的理念便是尔后西方史学家和思想家们所称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译“人道主义”)。
可见,所谓“人文”,即是所谓“人文研究”(anthrop- centredstydies)或人本之文化学术。在这里,所谓“人文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复兴传统的学术方式,不如说是一场现代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学术研究的复古兴趣是表面的、形式的,而其思想启蒙的开新目的才是内在、实质的,因而也是更为根本的。用梁启超的话说,人文主义者的真正意图是“以复古求解放”——使思想从宗教神学的一元化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求得人与文化的世俗自由。由此引申,用独立的世俗文化和学术方式,来创造和表达人性化的自由生活理想和价值理想,就是人文或人道的基本生活理想、价值理想和文化理想,亦即“人文精神”之所谓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且必须梳理出以下几个不同的概念范围和观念层次:
第一,“人文精神”最初是被后来称之为人文主义者的特殊学者或文人群体在其文化学术研究中所表达的一种与正统宗教神学相颉颃的世俗人文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精神。对中世纪以前古希腊罗马之俗文化资源的诉求,对人文学科之独立品格和世俗化样式的自由要求,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世俗教育、人文话语、古典文化艺术等诸传统的诉求,虽然是“人文精神”的外在表达形式,但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构成性意义。易而言之,即使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是所谓人文主义,也不能简单地撇开其原始表达形式来谈思想观念。这正标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与尔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前者的言说方式是文化学术的、间接的、美学层面的;而后者的言说方式则是思想理论的、直接的、哲学的甚至政治层面的。或者说,在前者,人文精神是通过丰富而曲折的人文学术方式来呈现的,是表达性、理想性的;而在后者则是以直接的思想理论方式来标志的,是论证性的甚至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如卢梭之与法国大革命)。了解这一差别很重要,它使我们既不失却对“人文精神”的思想性把握,又不至于将其直接化约为一种单一的思想观念或政治观念,因而给予它以本色,恰当、丰富的文化理解。
第二,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特定的宗教神学背景所致,所谓“人文”、“人文学科”有其宽泛的历史内容,在当时它甚至泛指一切与神学教会相对峙的世俗文化形式,包括世俗的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等等)。这一特定的历史意味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因为,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弱宗教文化或强世俗化文化,不存在一种连续性的宗教神学与世俗化的内在紧张,所以,其“人文”和“人文精神”的特质具有更为鲜明连贯的人生哲学内涵。就此而言,只能从世俗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人文精神”,理解其内在精神价值和文化理想的意义。具体来说,中国的“人文”或“人文学科”,有较文艺复兴时期更为严格的限定;它不仅与自然天道相对,也与那些具有工具性价值特征的学科或知识系统相别。这种传统的特征,正是我们习惯于把所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别开来的原因之一。当然,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发展和分化,西方文化中的这种学科群分类也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
第三,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构成性因素和“人文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分辨清楚。这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明在构成形式上的高度世俗化和精神气质上的突出伦理化特征所致,传统中国的“人文”不单有其完备的观念智识系统,而且有其普泛而深厚的典制结构,许多方面都有着充分制度化的具体表现。如,近乎法规的或准法制化的道德法典(monal code)、家族伦理礼仪、教化方式、教育制度以及“人文化”(“成人”与“成仁”、文化德性教育与政治成才或达德与达官)程序……等等,都构成了中国人文这不可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具体体现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特质,这一点又超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但是,我们的探究主题所关注的是各种人文观念和含摄于各种人文制度的精神特质,而非这些人文制度或物化产品本身,这点是应该清楚的。
二、先秦儒家伦理:中国人文精神的经典表达
明乎上述概念梳理和限定,为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限定性视点。但是,完备地揭示中国人文精神仍超出了本文所能承担的范围,况且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有待界定的庞大系统。由是,我谨选取儒家伦理之一面,对之作一个案性阐释。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伦理不仅是一个成熟而完备的价值理念系统,也是中国人文精神最经典的表达。若从人文的视角观之,儒家伦理的确不啻一种“哲学的人学”,一种“为人之学”、“君子之学”。它的基本理念至少可以分梳为“仁学”道德本体论、人格理想论和“成人”功夫论或修养论三个主要层面或方面。
把儒家伦理、尤其是作为其奠基理论的孔子伦理学看作一种“人学”或“仁学”,已是中外儒家研究的一种共同理解。儒家伦理之为“仁学”,首先在于它始终而彻底地坚持从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和人生观立场出发来看待世界和人生。与古希腊文化由自然宇宙论进入自然科学,进而进入人生哲学的进路不同,先秦儒家的创始者们从一开始就把思想的触角牢牢地拴在人间事物上〔1〕。在孔子的思想视野内, 最重要的是人事和“事人”,甚至只是现实的或现世的人事。《论语·先进》记言:“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弟子季路所问的“事鬼神”是指当时祭祀鬼神一类的宗教性活动。在孔子看来,这类事远不如“事人”重要,因此“事人”绝对优先于“事鬼”。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所谓“事人”是指侍奉父母长辈的伦理化的人本立场。显而易见,在孔子那里,人事和事人优于鬼事和事鬼;生优于死;道德的人事优于非道德的人事。这一价值秩序无疑有着深刻的人文意味:它不仅表现了孔子和儒学鲜明的人学主体性特征,即把人视为一切事物的价值主体(这一点还可从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一语中找到有力的印证),而且也表明其突出的伦理“仁学”色彩。
因此有其二,儒家伦理之为“仁学”,还由于它所追求的“人”、“仁”同格同位的道德主义人文理想。尽管学界对“仁”与“礼”两大范畴在孔子思想中的中心问题仍有歧见〔2〕, 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仁”的范畴更突出地标志着孔子乃至整个儒家伦理的人文性质,也更充分体现着儒家伦理的“内在超越”性特征。一方面,孔子教导:社会的文明安排和治理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相对。见《论语·为政》);仁人之行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另一方面,他似乎更重视社会国家之文明治理的“仁政”境界,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均从不同角度说明达致这一境界的艰难与可贵;更强调人之为“仁”的内在根本意义,即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在孔子的社会政治观中,道德的价值标准和理想是在先的、根本性的;而在其道德观中,人之为“仁”又是最核心的和最高的。这种将“成仁”、“为仁”作为一切人事之基本坐标的“仁人”学说,正是孔子和儒家伦理的道德主义人文精髓所在。
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伦理不单为社会和个人设定了“为仁”、“成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为仁和成仁之道,即所谓“仁之方”。简要地讲,这种“仁之方”也就是所谓“忠恕之道”。它具体有两个基本方面:从积极方面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后来孟子将之概括为“仁者爱人”,宋儒则更为确切地概括为“推己及人”。从消极方面说,所谓“仁”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还须提及的是,尽管在先秦时期有荀儒一系以“礼”释“仁”以及尔后宋儒的以“理”、“义”释“仁”等诸多语义、语境的变异,但总体上看,无论是孔孟还是后世儒家,“仁”一直都具有着“全德之名”、仁学之本的核心地位。这不单是我们把儒家伦理看作是一种“仁学”或“人学”的充足理由,也是其道德主义人文精神的主要见证。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儒家伦理尤有特色的道德人格理想论和道德修养论(功夫论)中,我们的这一判断就可以获得更为强劲的支持。
在本文特定的视阈内,我们可以把儒家伦理的人格理想与其所设置的达成这一理想的修养教育方式看作是它独特的人文化(或更准确地说,是人之德化)范式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为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谈。
儒家伦理对道德人格有很丰富的表述:孔子有“圣人”、“仁人”、“君子”〔3〕诸说;后孟子增说“仁者”、“大丈夫”;荀子还有“至人”说(与道家之“至子”概念的内涵不同)。先秦以后的儒家诸系虽对此亦有增益,多未脱先秦原儒之义。“圣人”无疑是儒家伦理之道德人格理想的最高化身。但考虑到三个方面的理由,以“仁人”、“君子”来讨论其道德人格说似乎更为合理。这三个理由是:第一,儒家及其伦理学是最典型世俗主义类型的,它所关注的人格理想和人格形象也是现实可见的或实际可达的,而绝非某种宗教性的超现实或非实在的人格影象。所以,虽然从孔子到宋明后儒都谈圣人,但他们实际最为关心的还是具有普遍可行意义的“仁者”、“贤者”和“君子”一类人格塑造。“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这一感叹可作为孔子在人格完善问题上持守平实态度的显证。第二,在儒家这溜人格虽有境界等级之分,但无实践通达之碍。从孟子“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断,到明儒王阳明等“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都可证实这一点。第三,儒家伦理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判断,并非空洞的假设,而是基于坚实的人性论确信作出的。无论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还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抑或其它形式的人性假说,虽有起点预设之不同,但最终都没有脱离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基本预制:即,人性相近,人性可变,因而人之可塑的预设本身深含着一种平等自由的人文价值观取向——人性相通且人性可变之前提预制,正是我们确信人类在根本上平等可善的基本依据之所在。这种内涵着深远而现实、积极而理性的人性学说本身的意义,决不仅仅在给儒家伦理的道德人格提供了一种合理可依的理论前提预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儒家伦理所蕴涵的具有某种普遍性意义(人性平等、人格自由)的人文价值精神。这一点似乎是我们长期未能充分认识并给予恰当评价的。
现在,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儒家伦理的理想人格观念。就我所知,这一观念的内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首先且始终是道德的。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几段代表性论断表明,自孔子始,“仁人”或“君子”首先是以“安仁”、“取义”、“德(得)德”来安身立命的。人格的道德理想化固然不能表征人文精神的健全理性的人格观念,但由马克斯·韦伯和J.R·列文森等人的观点识之, 却又恰好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所在。因为在韦伯和列文森看来,所谓人文精神的实质内涵乃是对人格理想的终极目的性价值追求,而不是对某种人事之工具价值的追求。正由于此,儒学作为一种典型的世俗道德学说,才因其缺乏对工具理性或工具价值这种为现代社会之合理化过程最为急需的价值观念,而难以独立开出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较高较先进的社会形态)。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纯目的性的、道德化的,甚至是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人才”理想相对立的、具有“业余风格”的文人儒者〔4〕。韦伯、列文森等西方汉学家们的这种批评虽然含有典型的现代主义“启蒙心态”,但也不失为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伦理“十足纯粹”之“人文主义的本质”〔5〕的反证。
第二,尽管儒家伦理的人格理想自孔子起即带有鲜明的泛道德化倾向,但无论是孔子本人的学说,还是其后诸儒的学说(甚至被看作儒家道德主义极端性代表的宋明理学),从来都没有将其人格理想同化于纯粹的道德人格。换言之,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全面型的而非(道德)“单向度的”(马尔库塞语),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孔子有关教育的基本理念来加以诠释。教育是人格完善的基本途径。任何一种人格理想的观念或学说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理念作为其实践操作性解释系统;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种完备的教育理念都或明或暗地以某种人格理想观念为其目标设置。在此意义上说,人格理论与教育理论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毫无疑问,孔子的学术人生堪称这一方面的最高范例。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与作为整个儒学之创造者的孔子都是中国文化或文明史上的最高丰碑。他最早创立了中国民间世俗化教育的基本模式,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限制。按其对教育模式的基本设置来看,孔子并不把人之文明“化”的理想人格的培养看成是一件纯道德的工作,相反,他创立了一个十分完整周备的教育理念体系和体制:在教育理念上,孔子坚持“文、行、忠、信”(即所谓“文学”、“德行”、“政事”、“言语”四科,参见《论语·先进》等篇)并举、“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孔子设置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图式和言传身授的传授方式。孔子的这套教育思想和体制构建是否合理姑且毋论〔6〕。我们所关心的是, 它对孔子和儒家伦理的人格理想观念有何作用?显而易见,孔子对教育内容和方式的设置都是较为完整规范的,它囊括了德、智、技、艺、言、行等多方面。按照这一理念所培养的人才显然不只是道德上的“谦谦君子”,而毋宁是知书达礼、文行合一、智德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它所内涵的人文要求就不只是道德的、价值理想(目的)的,同时也是普遍文化的、“智(知)的”、甚至技术工艺的或“实用理性”的。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理念及其体现的人文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资源意义,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罗马的道德文化传统。
不独如此,儒家伦理不单完整地设置了其理想人格及其教育模式,而且详尽指出了通达这一人格理想的实践途径,这便是其卓越的修养之道。可以说,儒家伦理不单具有强烈而纯真的人文理想精神,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化实践精神,这一点构成其完备人文精神的本色。
关于儒家伦理的修养之道,先秦孔、孟、荀三家及稍后《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书作了经典性概括。孔子提出以“志”、“学”、“思”、“行”为基本的修养之道,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所谓“躬行君子”(《论语·述而》)等等,都是这一主张的具体阐释。孟子根据其性善论和心性说,从内在超越取向上发展了孔子的修养理论。所谓“存心养心”、“存心养性”、“尽心知天”、“养心寡欲”(详见《孟子》中《告子》、《万章》、《离娄》、《尽心》、《滕文公》诸篇)诸多表述,将孔子“为仁由己”的原则性观点具体化为丰富多面的心性修养学说,最为系统的当为《大学》中所陈述的八条目,即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经宋儒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家扩展充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的内涵有了更为严格系统的阐释,构成儒家伦理乃至整个儒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总体看,“八条目”典型地反映了儒家修养论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内圣外王”之道,但其内向超越的特征确实是最主要的。余英时先生甚至认为,这种强调内在修养工夫的内向超越构成了儒家伦理之人文精神的具体特色〔7〕。
毋庸赘述和旁骛,仅仅先秦儒家的“仁人之学”或“君子之学”以及与之关联的人格理论和修养理论,虽不足以呈现儒家伦理(更不用说整个儒家学说)之全部,却足以显示其人文精神的精髓:以仁化人,以道教人,以德立人,是儒家伦理之将人“文”化或以“文”化人的根本精神之所在。这种人文化的理想既是凭文化教育而别天道自然与人道人性,以“文”培“质”或与“质”配“文”而无过与不及,使人首先达于“文质彬彬”的“成人”君子境界;也是由学习“诗书礼乐”、“格物致知”进而“正心诚意”、“成仁”、“成德”的道德人格理想;亦是一种基于人之本性可塑、有教无类的普遍化人文主义立场来追求人人“知书达礼”的人文理想。而其中所体现的以人文知识之“形”托人文价值理想之“实”,将世俗文化、教育、道德、人格和社会(或国家)的多重理念与理想融为一体却又不失主体价值精神(非宗教性、非外在性)的基本特征,正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困顿:“内在紧张”
“五·四”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整个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受到空前严厉的挑战。迄今为止,这种挑战虽有形式变化,但其思想冲击力仍未减弱。就本文主题而言,这种思想的冲击集中表现在针对儒家文化伦理传统三种常见的诘难:
(1)儒学及其人文主义本质上是传统的, 其伦理观无西方基督教伦理的超越世俗合理性价值的终极品格,也没有超出“文化人”以自我人文为目的的传统心态,因而无法形成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紧张)——从韦伯到列文森似乎都持这一观点。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作出了这样的学术判断:“儒教所欲求的‘救赎’仅仅是使人摆脱缺乏教养的野蛮。作为美德的报答,人只期望今生今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死后流芳千古。这和真正的希腊人一样,缺乏一切超越的伦理寄托,缺乏一切超世俗上帝与物质之间的紧张,缺乏一切超向彼岸的取向,缺乏一切根本性的罪恶观念。”〔8 〕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主张,韦伯比较道:“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缺少的伦理品质是:彻底贯注于上帝制定的各种目的;无情而实际的禁欲主义伦理的理性主义;生意管理上注重方法的实际观念;对非法的、政治性的、殖民性的、掠夺性的及依赖于君王庇护和不严肃者、反严格法律以及不利用日常企业的理性能力的垄断型资本主义的恐怖;对最佳技术方式、实际可靠性的和方便的合理算计,而不是对技艺传授或古老手工艺产品的美妙精巧所抱有的传统主义的自乐心理。还必须加上劳动者虔诚的工作意愿。无情的在宗教中系统化了的功利主义特属于理性禁欲主义, ‘在’(in)世界中生活,而不是‘隶属于’(of)世界,这一点有助于产生优越的理性欲望并由此产生职业者的天职精神,但这却是儒教所否认的。这就是说,儒教的生活方式是理性的,但却是被决定的,与新教不同,它是由外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内在所决定的。这一对照可以教育我们懂得,纯粹的节制和节俭与对财富的获取和尊重的结合,远远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精神’,也远远不能释放‘资本主义精神’。在此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在现代经济的职业者身上发现的。”〔9〕
进而言之:“儒教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新教的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新教徒与儒教徒都是‘节制者’(sob-er men),但新教徒的理性的节制存在于儒教完全缺乏的那种强有力的热情之中。而这正是激励过西方僧侣的热情。西方禁欲主义对世界的否定不可消融地与它的反面——即它想支配世界的热望相联系着。”〔10〕韦伯通过对儒教与新教的宗教伦理特性的异同比较,指出了儒家伦理顺应现实的世俗理性化之人文精神的局限,并明确将这一局限确定为:儒家伦理之人文理想缺乏超越目的性且不能培养出现代职业者或专门化专家,而只是以非职业专门化的雅儒为自己最高人格价值理想。所以他的结论是:“对儒教来说,专门化的专家并不能提高其真正的正面的尊严,无论其有用性如何。决定性的因素是‘文化人’(雅儒)‘不是工具’;也即是说,在他对世界的适应和他的自我完善中,他是一个趋向他自己的目的,而非任何功能性目的的手段。儒教伦理的这种核心观念否定了职业的专门化,否定了现代专家官僚和专业训练,而首先,它否定了追求利润的经济学上的训练。”〔11〕显然,韦伯的批评根本上是针对儒家伦理取向的世俗合理化(与宗教超越性相对)和人格理想的非技术性业余化(与现代职业的专门相对)的人文精神的。在他看来,正由于这两个方面的限制,使儒教伦理难以形成现代类型的“工作伦理”或“职业伦理”,而只能产生传统意义上的“责任伦理”;只能培养出学究式的通儒或“文化人”,而不能培养出现代类型的“职业化技术的专家”和具有强烈实业功利热情的现代商人〔12〕。
韦伯的这一批评在现代西方界影响巨大。著名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韦伯的这一批判思路。他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人文文化所能造就的文化人或知识精英只能是以“业余风格”(amateur)为基本“人格特性”的文人,而不可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专业化人才〔13〕。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目的与手段相互割裂的内在矛盾。迨至现代,这一矛盾仍然以所谓“体用”之争的形式而继续加剧着,无法真正彻底地消解。他说:“革新了的体用证明暗示,中国文明的心脏、它的精神价值,在纯实际生活领域——西方人已在这一领域捷足先登了——将受到中国‘自强力量’的捍卫,而不能让它遭受危险。然而,这种心理上的诉求方式并未如愿以偿。决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能将文化之物质部分与精神部分划分开来,而现代体用的两分对所有传统儒教门徒来说,实际是对根本性改变和传统日见衰微的一种掩饰。”〔14〕列文森的这一分析虽未像韦伯那样直接道明中国文化的“心脏”和“精神价值”所存在的目的性与手段性之内在张力的软弱,但他同样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由此对儒学的现代命运下了悲观否定的结论。
(2 )对儒家伦理之人文精神的第二种主要诘难是:作为一种人文价值理念,它的基本立场是私人本位的或家庭本位的,至多也只能是家族本位的,但即便是它内涵着强烈的“家族伦理本位”和家国一体式的整体主义道德精神,也无法从这种人文价值理念中开出现代公共理性或健全的公共观念。这是因为,基于自然化德性的私人或以血亲为基本纽带的宗亲关系,无法建立真正普遍的信念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韦伯谈到,宗教伦理特别是新教伦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以其“信念共同体”观念打破了“亲族血缘的束缚”,并由此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共同伦理生活方式”,它为公共商业伦理乃至公共社会伦理的建立奠定了基本的信念基础。而这一点恰恰是儒教伦理所不能突破的〔15〕。易而言之,在儒家伦理传统中,由于其人文价值的位格首先定位于个人自我的美德完善或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圆满上,因而既缺乏一种完整独立的个人之价值意识,也缺乏一种真正的“公共”价值意识,以至于连梁启超、孙中山和鲁迅等现代思想家也对此深有感触,伤感不已。梁启超指摘在传统道德中“私德占十之八九”而“公德不及十分之一”。孙中山和鲁迅也痛感中国人“一盘散沙”,导致中国人“心力”虚弱,民智低下。对这些论断,学界多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由于过于倚重家庭伦理的自然魅力和“公共”观念不足,儒家伦理的人文精神中确乎缺少一种内在的“公”“私”紧张,反倒是洋溢着浓厚的忠孝不二、家国一体的自然主义的暖味性伦理情感。这一特性极大限制了儒家人文精神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价值维度的社会化作用。
然而,对上述批评,学界不是没有异议的。譬如,列文森就侧面谈到。儒家对家庭伦理(“孝”)之优先性的强调与其“忠”的观念实际有着潜在的不协调性。因为儒家的忠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纯粹的道德行为,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帝国的要求”,是“强加给皇帝的”,所以忠孝两个道德概念在儒家那里还是有分别的。这一点也许是儒家的教育制度得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能够与封建社会的政治官僚制度既相互融合又相互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16〕。
列文森所谈到的儒家文化教育的目标制度与社会政治官僚制度之间的关联,实际暗示了儒家“士”的观念与“仕”之行动目标之间的复杂联系,但这也许并不是证明儒家伦理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孝与忠、私与公、内与外之间内在紧张的充足证据,更不能消除儒家伦理缺乏充分的公私区分和解释张力的实际困顿。但在传统文化的解释框架内,我们似乎也不能够要求儒家伦理自身向我们提供某种对充分个人化与普世化之内在张力的充分解释,这种理论要求是超时代超历史的。实际的事实是,在传统的、被列文森称之为“人文中国”(literati china)的历史情景中,儒家伦理已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由内(心、性、情、意诸方面)到外(齐、治、平等层面)、由知而行的德行之路。所不足者,是它未能像中世纪基督教伦理那样,将其人文话语的霸权扩张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层面,更没有建立自己“政教合一”式的社会政治霸权,而甘于自身对封建皇权的依附地位,甚至乐于自身自由人文者的“业余风格”。很难说,这种历史文化的角色究竟是一种文化的幸运还是一种历史的不幸。当然,从现代立场看,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之间的明确分别以及它们各自的充分自由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之文明程度和合理稳定性的重要标准〔17〕。就此而言,儒家伦理的人文精神的确面临着一个如何面对现代化公共领域,实现其自身向普世社会伦理转化的现实课题,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3)与第一种诘难密切相关,对儒家伦理的第三种诘难是, 虽然儒家伦理具有一种现世的或世俗的乐观主义人文精神,但它究竟只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世俗学说,因而既难以形成一种超越的形上学的终极关怀,也缺少人与神、世俗与天国、道德要求与宗教理想之间的内在紧张。仍以韦伯的观点为证:一方面,他认为,“儒家彻底的世俗乐观主义体系成功地消除了世俗与超世俗的个体命运之间的悲观性紧张”,这一历史的成功是基督教所无法达到的。另一方面,他又抱怨:“在儒家伦理中完全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的缺陷、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世俗行为与彼岸赎罪、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力量通过各种内在的摆脱传统和习惯的力量来影响人的行为。”〔18〕
回应这一类诘难是十分困难而又必要的。关键在于:首先,我们如何界定并在什么范围和层次上来理解“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如果本文第一部分的概念界定是合理的,且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近世人文主义是在与宗教神学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事实,那么,韦伯的批评及与之类似的指摘就难以成立。作为宗教神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当然是非宗教神学的、世俗的,因而对儒家伦理提出超世俗关切的价值要求就是不恰当的或额外的,也许,有意义的提问只能像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教授那样,探询儒家伦理是否能够、或若能够又在怎样的程度上摆脱“内在关怀”(内圣)与“外在关怀”(外王)之间的摇摆心态〔19〕?或者,如人们通常所指出的那样,儒家伦理的人文关怀能否或如何解决好现世关切与终极关切之间的矛盾?
进而第二,如果这一诘难意味着对道德与宗教之间相互关联的思考,那么,这一问题实际已经超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主题范畴,也不是评价其人文精神的一个合适标准。当然,我们已注意到,无论是韦伯,还是列文森,甚或某些国内学人,都倾向于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宗教。儒家学说(包括其伦理学说)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这是本文范围以外的问题。但由于它牵涉到对儒家伦理之人文精神的评价和认识,似乎有必要表明哪怕是最起码的倾向性意见。我的理论直觉是,儒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即令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汉唐)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性来看,儒家学说确实承担过西方宗教所担负的文化使命,那也最多只能说它具有某种宗教的文化特性,而难以将之直接归于宗教之列。当然,这还要看我们所持的宗教概念如何。著名汉学家尼德汉姆曾经合理指出:“假如你把宗教定义为某种包含着神圣感的东西的话,那么儒家就是一种宗教;……但如果你认为宗教只是一种超验的创造者的神学的话,那么儒家又不是宗教。”〔20〕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伦理的确缺乏目的价值与工具性价值、道德人格与公共社会化、世俗主义与宗教超越等“内在紧张”。从社会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视角来看,这些“内在紧张”也的确是传统社会和文化之现代转化所需要的“必要张力”。由是而观,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伦理及其人文精神之现代意义的局限性。然而,必须记住:在人类多元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任何自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进入现代社会而获得自我延伸。而且,现代性的标准也并不是我们用以评判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绝对价值圭臬。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是连续性的,一如流水;而所谓现代化或现代性也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历史概念。因此,本文的初步结论是,重要的并非用某种现代性概念来“透视”(在尼采的语义上)儒家伦理的人文精神,而是了解其传统本色,并由之揭示它在现代生活中可能产生的精神资源意义。
注释:
〔1〕马克斯·韦伯认为, “尽管儒教学派发展出一种宇宙起源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缺乏形上学的兴趣。该学派的科学主张仍只是素朴的。”(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Taoism,Macmilliam Publishing Co.1964,P.154。)
〔2〕参见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3〕余英时考释:“君子”一词在孔子以前并无特殊道德含义。经过较长时期的文化演变后,在孔子这里终于赋予较为完整而明确的道德内涵。见其文《儒家君子的理想》,收入刘述先主编的《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年出版。
〔4〕Cf.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and Taoism,and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Modern Fate,Vol.1,University of Coliforia Press 1958.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第95页。
〔6 〕我有另文《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及其限度》讨论这一课题。该文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7〕参见其著:《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3~34页。
〔8〕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Taoism,P.227~228.
〔9〕〔10〕〔11〕Ibid.P.247,248,246。
〔12〕对此,余英时在新近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见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原载《知识分子》杂志,第2卷第2期,1985年冬季号。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似仍有存疑。参见杜维明《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一文,载台湾《九洲学刊》,1986年第1卷第1期,以及余英时致该刊的长信《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洲学刊》编者》,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3〕Cf.Joseph R.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Modern Fate,Vol.1,P.16.and Vol,111,p.108—109.
〔14〕Ibid Vol.1,P65.
〔15〕Cf,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and Taoism,P.237
〔16〕Cf.Joseph R.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Modern Fate,Vol.1,P.16.and Vol,11,P.30,P77.
〔17〕新近,《公共论丛》在“公共论坛”专栏就此类问题展开了讨论,可资参阅。见该丛刊第二辑《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18〕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Taoism,P.235—236.
〔19〕Cf.JosePh R.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Modern Fate,Vol.1,P.16.and Vol,11,P.51,and so on.
〔20〕Joseph Levenson,Within The Four Seas, London,Allen Unwin,1969,P69.
标签:儒家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人文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教育的目的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韦伯论文; 论语·述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