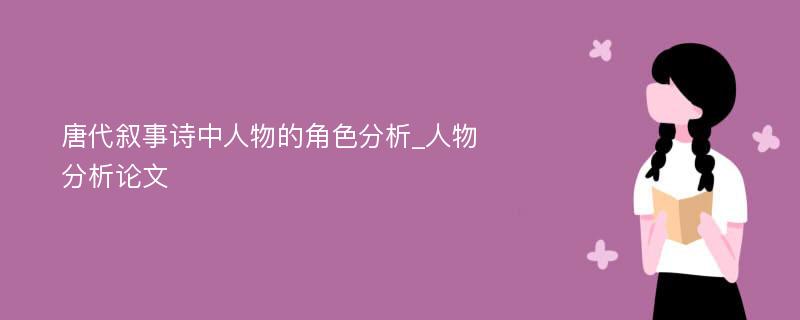
唐代叙事诗人物作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事诗论文,唐代论文,作用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3-0133-03
叙事诗以故事为中心,但故事的展开过程必须有人物参与,换言之,即人物串连故事,并引导情节的展开。这里所说的人物并不仅限于人,它可以包括一切人化和拟人化的寓言诗中的主体形象,如元稹《大觜乌》与白居易《和大觜乌》中的乌鸦、刘禹锡《聚蚊谣》中的蚊子、韩愈《双鸟诗》中的双鸟。西方叙事学对人物研究颇为深入,围绕人物的本质属性提出了多种人物理论,形成了不同的人物概念和分类方式。综合查特曼、福斯特、尤恩、格雷马斯、巴尔特等人的人物理论,人物在叙事作品中的作用主要是“角色”和“行动元”。所谓角色作用,指的是人物的性格特征造成其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在故事中给读者以鲜明的形象性和独立审美价值的作用。侧重这种作用的作品,人物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行动只是人物个性的表现;而所谓行动元作用,是指叙事作品中人物作为一个发出动作的单位对整个故事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侧重这种作用的作品,行动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人物受其动作的制约,读者往往注意其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试从“人物作为角色”、“人物作为行动元”、“人物既作为角色又作为行动元”三个角度来分析唐代叙事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一、人物作为角色
唐代叙事诗作为古代叙事性作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一大批人物类型,如美女怨妇、侠客少年、边臣武将、道士和尚、农夫商贾,他们多半无名无姓,其言行仅显示人物的身份;有的虽有姓名,但个性并不凸显,表现的只是他所代表的群体的性格特征。与此相对,少数的一些作品也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他们以其独特的言行和性格特征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依据人物性格塑造的这种差异,我们分“观念型”“特征型”两类角色来作些探讨。
(一)观念型人物
观念型人物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思想创造出的一个或一类人物。这种人物通常具有人们所熟知的某种性格特征。唐代叙事诗中的侠客和商贾形象就是较突出的例子。
侠客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其文学形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早就存在,并已成为传统。《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有相当篇幅描述这类具有侠义性质的人物。如《游侠列传》中叙述了朱家、郭解等闻名天下的“布衣侠士”的事迹;《刺客列传》叙述了聂政、荆轲等为报知遇之恩而视死如归的英雄传奇。司马迁还对他们作了一番概括性极强的性格描述:“今之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之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番描述成了后代侠客形象类型化的性格特征。
唐代是个尚侠的时代,任侠风气颇盛。唐传奇中塑造了不少著名的侠客形象,如李公佐《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薛调《无双传》中的古押衙,杜光庭《虬髯客》中的“风尘三侠”,袁郊《红线女》中的红线女和裴铏《昆仑奴》中的磨勒等。唐代叙事诗中题咏侠客的诗篇更是代不绝书。在以“少年行”“从军行”等古题所作的乐府诗中多出现这类侠客的形象,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行》、王维《少年行》四首、崔灏《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顾况《从军行》、戎昱《从军行》、李益《从军有苦乐行》、张籍《少年行》、李贺《啁少年》、李廓《长安少年行》等。这些诗中的侠客形象在唐前后期历史上稍有变化。大致说来,由初唐入盛唐任侠精神多与建功立业、拯物济世的人生理想相结合,如王维《少年行》四首: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到了中唐,任侠精神开始衰减,往往转型为个人的特立独行、奇操异节,甚或放荡不羁、玩世不恭。试对比李贺《啁少年》:
青骢马肥金鞍光,龙脑入缕罗衫香。美人狭坐飞琼觞,贫人唤云天上郎。别起高楼临碧筱,丝曳红鳞出深沼。有时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飞鸟。自说生来未为客,一身美妾过三百。岂知劚地种苗家,官税频催勿人织。长得积玉夸豪毅,每揖闲人多意气。生来不读半行书,只把黄金买身贵。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荣枯递传急如箭,天公不肯于公偏。莫道韶华镇长在,发白面皱专相待。
但总的来说,这类形象的固有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大变化,大都好勇尚武,如崔灏《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诗中有云:“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重诺轻身,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行》诗中有云:“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英雄仗义,如张籍《少年行》诗中有云:“独对辇前射双虎,君王手赐黄金珰”“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等。诗人们不管是对古代或现实生活中的侠士和侠义行为进行赞美,还是以侠士自命,侠客的性格形象显然非其笔力所系之处,他们只是要通过对这类人物的描写来表现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为国为民、除暴安良的审美观念,寄托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改造现实的强烈愿望。这类形象还进入了寓言诗,如杜甫的《义鹘行》,义鹘其实就是鸟类英勇仗义的侠客。
唐代由于运河开辟,南北交通便利,促使都市繁荣,商业发达。发达的商业造就庞大的商人群体,因而在唐代叙事诗中,对商人形象也往往有较多的描述。如《贾客乐》: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
此诗真实表现了商贾的生活特点和性格特征,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利轻别。这一点其实也是该群体类型化的特征,很多同题材的叙事诗对此都有表现。如刘禹锡《贾客词》(并引),其小引云:“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诗中有云:“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元稹《估客乐》:“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白居易《琵琶行》诗中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粱买茶去。”因商人重利轻别,所以表现商人妇的诗中往往要代抒或自抒她们在漫长等待中孤苦无依的怨情,如刘采春《罗贡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对商人和商人妇的描绘,一方面可以看到诗人们对社会新人物群体崛起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重农轻商思想的严重。正由于诗人们表现这一人物群体的落脚点是重农抑商,因而在塑造他们的时候常常作为苦难农民的比较对象,仅沿袭其固有的性格特征,而很少增添新的性格元素。
(二)特征型人物
如果一首叙事诗塑造的人物具有个性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这一个”而不是别的,那这样的人物可称为特征型人物。其特征并不体现于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上,而是落实于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甚或侧面的某一性格元素上。按诗人创造人物特征在构思表现方式上的差异,特征型人物可细分为:聚点式、变点式和多点式。
1.聚点式
这种人物的构思特点是诗人只突出刻画人物的某一性格元素,而且这一性格元素已经定型,其诸多行为都围绕它来安排。如李白《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两篇,题材类似,都写勇妇复仇的故事。宋长白《柳亭诗话》评前者说,其“秦女休一篇,曹子建、左延年俱有此作,是咏古迹而非述时事”,写的是历史人物;查慎行《初白诗评》论后篇云:“必实有其事。”写的是当世人物。前篇借重用典,以典故中的多个烈女衬秦女;后篇着意铺张,也用对比,描写细腻。虽则人物情况有别,手法也不一,但诗人执着一点,把“勇”视为两个人物核心性格的构思特点却是一致的。
王建《羽林行》也表现出这样的构思特征:此诗塑造了长安恶少的群像,其突出特征就是“恶”。首句括其要,点出“恶”;次九句细述其“恶”之表现:百回杀人、混迹军旅、改姓重出、殿前射禽,真是气焰嚣张、肆无忌惮!因古典叙事诗体制所限,篇幅短小,难以铺展,故聚点式构思方法为经常之选择,聚点式人物也颇为常见。如杜甫《戏作花卿歌》中勇猛的将军,崔灏《赠怀一上人》中高逸的法师,柳宗元《咏荆轲》中愚勇的荆轲等都是这类人物。
2.变点式
诗中只刻画人物的一个性格元素,当这个元素在全篇作品中只被凸现而不发生变化时,那么这种人物就是前述之聚点式人物,如果它发生变化,那么这种人物就成为变点式人物。如韩愈《病鸱》中的病鸱这一寓言形象,当其得意时,“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风恣追随。遂凌鸾凤群,肯顾鸿鹄卑”,狂傲纵恣,目中无人;而当其失意困顿时,“青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君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饱入深竹丛,饥来傍阶基”,表现出一副卑怯不胜的落魄模样。全诗仅截取鸱鸟穷达两个片断,却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官场中那种得志猖狂、失意失志的风派人物特点。鸱鸟这种性格元素是从一个点变为另一个点,具有质变特点,体现了性格变化的动态感。由于唐代叙事诗刻画性格普遍的单一性,基本就限定了这种带质变的变点人物多在一个性格侧面上进行变化。但也有例外的,如韦应物《逢杨开府》,自述人生变化:“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少年时横行乡里,无赖放荡,射猎赌博,偷香窃玉,无所不为;一朝省悟,性格大变,读书学诗,廉洁从政,高洁耿介,长风浩荡。诗本身虽欲表现从政不得志的牢骚,但诗人自身性格前后迥异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多点式
在唐代,有少量叙事诗不是写人物一个性格元素或其变化,而是写两个以上性格元素,甚至是两个以上相互矛盾的性格元素及其变化,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在古代人物画廊里十分引人注目。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描写叙述了一个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其中唐明皇和杨贵妃就是这种多点式的人物。诗中写唐明皇至少写了三个性格侧面的三种性格元素。其一是风流倜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他不仅重色,而且才情飞扬,高雅浪漫:“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其二是多情伤感。军士哗变,杨妃香销玉殒时,“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是夜,他无限伤感,“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回至长安,更是茶饭不思,寝卧不安,情到深处,帝皇无异百姓。其三是坚贞专一。在“寻觅”一节里,他为了求见心爱的女人,让方士殷勤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今生不能相守,魂也要相伴,梦也要相见。这三种性格元素统一到唐明皇身上,使人物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杨贵妃的性格也非单一,她不仅娇媚温柔,多情多才,而且对爱情坚贞如一。当故事进入最后一节,她已是仙界神女,一听得唐明皇来访,“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从外形到内心,传神的细节使人物个性鲜明如见,宛然如出。后世以李杨爱情故事为题材的诗词曲赋、小说等不断强化人物的性格,使李、杨的艺术形象越千年而不衰。
柳宗元《韦道安》也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之云:“毙群盗为勇士,辞师昏为义士,后顾义引刃,又为忠贞之士矣。”勇义、忠贞这些性格侧面统一在韦道安这个人物身上。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那位美丽、天真、多情、勇敢的少女,孟简《咏欧阳行周事》中文弱却勇敢的书生欧阳詹、热烈而痴情的行营歌妓也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二、人物作为行动元
在唐代叙事诗中,也有不少诗歌虽描写了人物但并不重视其性格的刻画,仅仅以他们为媒介来表达诗人某种政治见解或个人生活的感慨。这些人物显然不是以角色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或为故事中的人物,或作为内在叙述人,基本起着展示生活、见证事件的作用,并以此推动故事的发展。换言之,他们的行动本身就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就他们的行动方式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展示,一类是述说或见证。
(一)生活展示者
这类人物多出现在中唐乐府诗中。中唐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乱连年,苛税繁兴,民命不堪。承袭杜甫新题乐府记录时事的笔法,李绅、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写了大量真实反映人民深重苦难,揭露统治者残暴的讽喻性诗歌。如白居易《杜陵叟》写农民受灾后,地方官员还要敲骨吸髓,横征暴敛以表政绩;元稹《织妇词》写织妇整天织布,以应官税,忙碌得不仅失去嫁人机会,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些人物多为下层劳动者:农夫、蚕妇、织妇、水夫、卖炭翁、采蜡者、宫女等。诗人们在他们身上倾注笔力并非为创造角色,塑造性格,而是通过展示他们的苦难来抨击时弊、讽谏帝王。简言之,诗人重视的是人物的生活而非人物本身。因此,在这些人物身上不仅不具有个性,也基本不具有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如张籍《筑城词》: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著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土坚、吏鞭、口渴、身累,写尽了被征筑城农夫的辛酸血泪,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中人物既无名无姓,也不具备外在特征的典型性,展示人物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向读者表现这种情感的震撼力量。如果这首诗里有故事,那么人物的生活就构成了故事的全部。
(二)事件见证者
与作为生活展示者的人物情况类似,事件见证者也非诗人关注的对象,其存在价值是叙述或见证。事件见证者常以叙述人的身份出现。以杜甫《兵车行》为例,此诗是一首反对玄宗发动不义战争的政治讽喻诗,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年)。《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云:“天宝十载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将兵八万,至西洱河,大败,死者六万人,制大募两京及河南,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女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钱谦益认为此诗即为此事而作,颇可信。诗首段以“道旁过者”的视角写出被强征的士卒与家人分别的痛苦情景,二三段又以“道旁过者”与“行人”对话的方式交代事件之来龙去脉。“道旁过者”对诗中故事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也就是一个事件的见证者。
事件见证者作为内叙述人往往是故事中虚构的人物,由于他已经进入到故事的层面,不像叙述人那样独立于故事之外,故称内叙述人。事件见证者的叙述模式大体是:A遇见B,听B说故事,是一种典型的“借口叙述”。如元稹《连昌宫词》、郑嵎《津阳门诗》、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等俱是。以《新丰折臂翁》为例。本篇为白氏新乐府第九首,原序云:“戒边功也。”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与天宝十三载(754年)两次大量征兵,征讨南诏,均大败而还,伤亡惨重。诗歌通过一位当时以自残避免兵役的幸存者的叙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唐宋诗醇》云:此诗“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车》、前后《出塞》等篇,借老翁之口说出,便不伤于直遂。促促刺刺,如闻其声,而穷兵黩武之祸不待言矣。”不仅指出借口叙述的特点和好处,而且追溯了这种写法源头所自。《元白诗笺证稿》则点明此诗对《连昌宫词》的影响及两者的共同特点:“此篇为乐天极之之作……后来微之作《连昌宫词》,恐亦依约摹仿此篇,盖《连昌宫词》假宫边老人之言,以抒写开元、天宝之治乱系于宰相之贤不肖及深戒用兵之意,实与此篇无不同也。”前人虽非有意从叙事学角度探讨唐诗,但对该诗的分析表明他们已经明确意识到故事叙述的层次和事件见证者的作用。该诗正是借助老翁的叙述,完成了故事的基本构架。
三、角色兼行动元
在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些自传性叙事诗中,发生的是二重叙事。作者一层,叙述人(有时也是内叙述人,如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中借以叙述的“贱子”)与故事人物一层。叙述人与故事人物的二合为一使诗中人物作用变得相对复杂,不但以自身行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往往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光彩照人,成为后世了解作者本身经历和思想性格的主要依据。(实际上作者和叙述人是两个概念,但古典叙事诗一直处于史叙事笼罩下,作者和叙述人往往等而观之,不作区别。)显然,这里人物所起的作用既有行动元作用,也有角色作用。如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宿五松下荀媪家》,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彭衙》、《北征》、《羌村》、《逼仄行》、《壮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琵琶行》、《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它们多以仆仆行旅中记述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故事主要框架,通过叙事、抒情、议论三者结合的方式,凸现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
以李白现存诗作中最长的一篇《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为例来说明叙述人在故事中的作用。安史乱后,李白应聘做了永王璘之幕僚。李璘乃玄宗十六子,肃宗李亨惧其夺帝位,便杀害了他。李白因此事受累,流放夜郎,未至,遇赦,由巫山东归。途经江夏,李白写此诗赠给江夏太守韦良宰。诗中详细描述了叙述人(或故事人物)从入长安前后到流放夜郎遇赦东归这段时期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全诗共166行,结构上采用倒叙追溯方式,以人物的经历为线索贯串了五个主要情节:当年离开长安与韦良宰分别的情景→与韦良宰异乡重逢的情景→安史之乱→加入李璘幕府,再到流放夜郎→遇赦于江夏与韦良宰再度相逢的情景。叙述人生活经历的变化,即与韦良宰分别、重逢、再分别、又重逢的情节构成了故事主干,在此,人物起到了行动元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物在叙述展开过程中又不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他胸怀大志而时运乖蹇(如“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句)。放达洒脱而慷慨激昂(如“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句)、重友情(如与韦良宰分别时感叹:“歌钟不尽意,白日落昆明”)、有先见(安禄山拥兵自重,企图叛乱,他“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忧国爱民(如“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句)。这些性格特征使人物的形象丰满,具体可感,成为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角色。在这里,人物所起的又是角色的作用。
综合起来看,在这类诗中,人物作为叙述人具有引导故事发展的作用,作为故事中人物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人物的这种双重作用使读者与故事中人物失去距离感,常常把虚构的事件坐实,把故事人物的性格等同于历史人物的性格,从而堕入其叙事圈套之中。这类被读者视为诗人自传的诗常常出现误读的情况,就可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