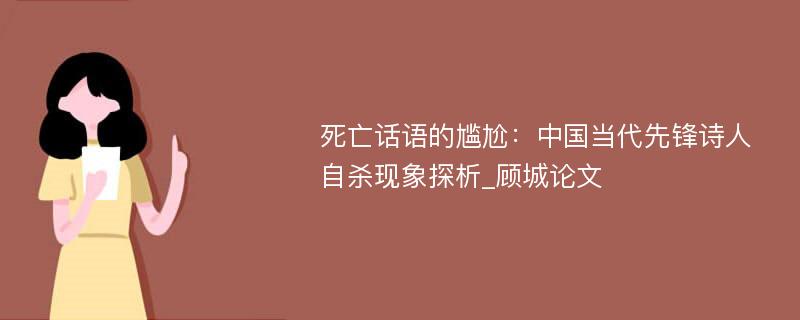
死亡言说的尴尬——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自杀现象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诗人论文,尴尬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先锋诗人如海子、戈麦等相继自杀的现象(我这里的先锋诗人所指范围包括朦胧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中的诗人),特别是1993年10月8 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以其惨烈的杀妻自缢的方式结束了两个年轻的生命,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文坛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失衡现象的体现,有人认为这是先锋所固有的“死亡情结”的必然归宿,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辉煌的”“最后创作”,是精神的最后一次飞扬……我认为以上种种看法虽然也触及到了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有些甚至是重要方面,但由于缺乏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广分析,其结论常予人以牵强之感。我这里想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在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文化语境和生存文化语境三个层面展开,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我认为它是诗人的生命境遇在以上三个文化层面处于深度尴尬状态的必然归宿。
尴尬之一: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交锋中的堂吉诃德
从政治文化语境来看,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自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就以边缘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在与主流文化交锋中处于不利境地。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耽于幻想,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现实“大风车”作战,这注定了他们“活着是个疯子,死了是个智者”(《堂吉诃德》结尾语)的悲剧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期间,文化的冲突、思想的互渗、观念的碰撞、价值的并行,构成了思想文化上空前未有的多元景观。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是以两大政治文化话语系统为轴心的——即以官方主导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为主体形成的主流文化话语与以扮演历史批判者角色的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边缘话语。
在主流文化话语中,官方主导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的话语系统,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强制性。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具有一定的宽容性的文化话语系统。大众文化是与商业功利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化。从文化类型来看,它是一种幻觉文化,因而具有非现实性、想象性、做作性的特征,它反映了人类审美心理中规避现实的一面。在中国古代这种文化虽然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但它却一直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从未铺展开来,更很少与主流文化话语沾上边(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曾一度跃居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自80年代以来由于推行市场化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使大众文化第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开始时由港台文化充当上阵的急先锋,而后本土制作的影视、音像、文字作品便如洪水泄闸,汹涌而至,构成20世纪末中国空前的文化时尚。一时间,琼瑶、三毛、金庸、梁羽生席卷神州,《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流行于街头巷尾,《废都》《大气功师》被炒得轰轰烈烈……大众文化第一次有幸参与了主流文化话语的建构,得到了官方主导文化的认同。由于官方主导文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模式而构筑的。大众文化又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的,因而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休戚与共,密切契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话语系统。
作为边缘文化话语的精英文化(或知识分子文化)是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道德追求的一种文化。它以站在每一个时代最前列的姿态,以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气概,以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识以及现实的批判者、民众的启蒙者和历史引导者的角色,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因而它是最不入流、最尴尬的一种文化形态。一方面,它总想以自己的人文理想引导着主流文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并不时地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甚至不惜充当御用文人的角色来实现自己的一点社会理想,但另一方面它的人格理想,它的现实批判者的角色注定了它很难真正介入主流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它们常常被挤出圈外,成了愤世嫉俗的看客。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正具有这一特点。自80年代以来,人文学者们曾满怀激情地预言历史新纪元的到来,那就是世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经济现代化及其导致的物质生活的空前富足与舒适。并斩钉截铁地宣布:中国的文化必然也实现现代化,其标志是融入世界文化主流。那时,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被走马灯似的宣讲与演练,似乎只要再努一把力,精英文化便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科技、经济和消费的现代化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出现时,他们所憧憬的“文化现代化”却以十分世俗的方式抢占了大部分精神阵地。面对着大众文化的汹涌来势,他们感到了一种严重的被抛弃感和愚弄感。他们原本打算用理性话语来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的图谋,被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以及商业巨子等“现代派”所取代。正义、价值、尊严、理性等美妙高雅的理想已日益被社会所淡忘。他们感到焦虑、压抑、躁动不安。同时,物质生活处境的窘迫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也让他们感到惶惑。面对着下海不几年便腰缠万贯学者文人的富傲姿态,目睹着鳞次栉比的商店代替了高等学府的围墙,耳听着教师们做生意的吆喝声,他们日益感到生活处境的窘迫与惶惑,难道这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
在这两大文化话语中,中国当代先锋诗人当之无愧地充当着精英文化急先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交锋中他们向当时僵化的主流文化的冲击时表现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果决,并得到了全社会的首肯,被冠以“崛起的诗群”,“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代表等尊崇的名号,在诗坛内外展开的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广泛的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时成为社会思想启蒙的警句名言,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主流文化的变异,先锋诗人所面临的政治文化语境已不复存在,到第二次交锋时(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就变成了大战风车的当代堂吉诃德,成了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多余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追逐的是赤裸裸的金钱,是带有享乐主义特色的文化快餐,他们不再需要诗人了,甚至连正宗一点的小说家都不需要了,诗人顾城写道:“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注:顾城《光的灵魂在幻影中前进》,《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3期。 )其实不止顾城一人如此,几乎所有的先锋诗人都面临着这种尴尬。这种尴尬处境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愈趋激烈(因为他们正处在由政治型文化人向市场型文化人角色转换的阵痛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部分偏激、敏感的先锋诗人在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中日益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他们不能认同这种扼杀诗意的社会现实,痛苦中他们力图在诗歌里构筑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国,但愈是如此,他们就愈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发言权,像堂吉诃德一样,他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嘲弄,当他们被看作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一群傻瓜时,他们对生活彻底失望了,渴望解脱的心灵冲动最终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死亡之路,并认定这是抗拒现实政治的一剂良药,是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尴尬之二:西方话语与东方话语夹缝里的迷途羔羊
从文学文化语境来看,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从一出现就生活在西方话语与东方话语的夹缝里困难地呼吸着。他们就像那迷途的羔羊,在两大文化话语的夹缝里左冲右突,彷徨无奈。
出于对文化现代化的紧迫感,我国当代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采用了鲁迅“拿来主义”的方法,在改革开放政策刚出台后就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译介。哲学上,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索绪尔、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等一个个轮番上场;文学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一个个都被奉为“新潮”不停上演。就诗歌自身来讲,一个个西方诗歌流派也被奉为圭臬,不断地在诗坛介绍,如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美国战后崛起的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后现代诗……这些西方文学流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既有对西方现代社会危机进行深刻批判的进步流派,也有表现西方落寞、颓废情绪的腐朽流派。他们在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与参照的同时,也给我们以负面的消极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些现代派诗人极端自我。他们自狂、自大、自私,由反传统发展至目空一切,称王称霸,贬低他人。其二,有些现代派诗人极端“弗洛伊德”,沉沦于颓丧、情欲、潜意识流中,有些严重的脱离现实,沉沦于绮梦、怪梦的幻景,甚至神经分裂,发疯或自杀。其三,有些现代派诗人的死亡情绪很重。“视死亡是一种美好的艺术”,或视死亡如游戏,视死如归,勇往奔赴死亡的宴会。而后者往往容易令那些神经相对脆弱、敏感的诗人心动。更可怕者,这种轻视生命的现象还不仅仅停留在生活与艺术感觉层次上,它被某些西方理论家总结上升为一种奇怪的理论高度。被视为存在主义大师的雅斯贝斯就认为伟大艺术家的生存是“特定状况中历史一次性生存”,在现代社会荒谬背景下,“优秀的艺术家认真地按独自的意图做出的表现,就是类似于分裂症的作品”,恰恰是凡高和荷尔德林这样的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照耀了存在的深渊”,而其他无数艺术家的平庸实则是因为他们“欲狂不能”(注:转引自张清华《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诗人产生精神分裂,抑郁、孤独、发狂乃至于自杀是一件并非痛苦,也非耻辱的事情,相反它倒成了一种高尚的行为,是用身体在“写最后一首诗”!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文学的家园在哪里?无人回答。他们也不屑于回答“这么一个陈腐的不识时务”的问题。
如果说在西方话语中找不到文学的精神家园还留有救药的余地的话,那么在东方话语(即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文学精神家园寻找中他们的无知和虚无主义态度则彻底把他们推进了文化精神的泥潭,并最终为他们挖掘了一口口通向死亡的陷阱。中国当代先锋诗人,无论是早期的朦胧诗人,还是“后朦胧”诗人,“后新诗潮”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文学传统抱有偏见,他们既不满意于中国古典文学,认为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与他们先进的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又不满意于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传统,认为那只不过是政治强权下的没有个性的文学话语,他们不屑去浪费时间指望能从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种观念上的拒斥态度,使他们找不到创作的参照系,于是他们只好将搜寻的眼光转向西方,从西方的各种现代派诗歌中吸取营养,但汉语诗歌内在的要求使他们从西方诗歌中找不到真正的诗的感觉。骨子里的汉民族思维习性也使他们很难真正逃出东方话语的语境。这使他们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因而极难找到诗歌创作的精神渊源,不时有创作枯竭之感在寂寞的诗魂中游荡。于是,他们逐渐退出了诗坛关注的中心地位。“据说,在欧洲的一个国际诗人节上,一位朦胧诗的重要代表诗人曾当面严肃批评了顾城近年的诗,顾城听后大哭了一场”(注:转引自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于是在彻底“疲倦”和“衰老”中, 他们就痴迷于死亡解脱,不断地咏叹着“死亡”主题(杀人和自杀)。顾城从1983年起,就一直在写着“死亡”的诗歌:
在这坚实的地上我们还能站多久
我们的小岛屿,我在浅海投下影子
花朵吃力地抬起头来
花朵在星云中紧闭着泪水的双眼
午夜的酒气弄湿了旗子
午夜的刀紧贴着陌生的额角
在这土地上,迭放着芳香柔软的尸体
那芳香正一阵阵蓬勃地展开——(《静静的落马者》1983年创作)
花儿
你的人在树上
离地十五尺
跳北房
高级老头
一枪一个
花 头朝下 脚朝上
——(《香港文学》1993年6月)
“死亡”在海子的诗歌中也似乎无处不在,他甚至把死亡本身看作存在的显现,看作是关于存在的经验的唤起。他在《九月》中写道: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终的选择,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他们的精神早已先他们而死了。他们的生命受到魂灵的折磨,没有力量也不能安宁,“我的脑子一直在走,无法停止。东方也罢,西方也罢,百年千年的文化乱致一团……我不自主地在这个旋涡中回转,最后是达到一个疯狂的境地”(注:顾城《从自我到自然》。),“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注:顾城《剪接的自传》。)。他们感到“江郎才尽”的痛苦,出于一种路已走到尽头的感觉,所以才用身体的语言写下最后一首诗歌——“死亡之诗”。
尴尬之三:理想风帆与现实幕墙叠合下的影子先锋
从生存文化语境来看,中国当代先锋诗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对世俗的生活有着本能的厌恶,他们幻想着在诗歌中建造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们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因此,当他们理想的风帆一碰到苍白无聊而又厚实无比的现实幕墙时,他们的先锋性就只剩下一个孤独落寞的影子存活于心灵的一隅。
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几乎是一切当代文化精英的共同信念,它表现了困惑之中的现代人对生命价值探寻的努力。海德格尔就对自己生活在一个“众神离开”、“上帝缺席”的“贫瘠时代”感到痛苦不堪,所以他推崇诗人荷尔德林,认为他不是一般地为诗,而是以诗寻索生命的本质存在,追寻永恒的“神性光辉”,并认为他是“诗人中的诗人”。中国当代先锋诗人的对理想境界的执着也毫不逊色。如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出于对理想的耽爱,出于对世俗生活的厌恶,他很早就离开了直接观照社会现实的立场,在诗歌中以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他一首诗歌的题目)的固执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正如舒婷写给他的《童话诗人》中所描述的: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地方
出发
在他看来,“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的,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他表示“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表现那“纯净的美”(注:见《诗探索》1980年第1期《请听听我们的声音》。)。他不仅在诗歌中去营造这种美, 去建立一个“天国花园”,而且还在现实中去实践这种美,真的去营造这一“天国花园”,但这样一块理想的净土在中国没有找到,在欧洲美洲没有找到,最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才似乎找到了。到达激流岛的第一天,他就对妻子谢烨说“这是我找了二十年的地方。从我十二岁离开学校就开始找了。”他以极大的毅力,亲自动手,寻找木柴、食物、修补房屋,挖化粪池……他说“我要修一个城,把世界关在外边”(注:转引自吴思敬《〈英儿〉与顾城之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除顾城外,其他自杀的先锋诗人也都堪称理想主义的殉道者。如海子,他诗歌中的三大母题:神启、大地和死亡,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了其理想主义的追求。
然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生存境遇如何呢?现实总是那么苍白、琐碎、枯燥,毫无诗意可言,到处是“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充满了名利之争的庸俗气息和柴米油盐的琐屑无聊。作为诗人,他们并不能获得理想的现实生活,他们大多是生活的弱者,缺乏楔入主流生活的圆滑,甚至缺乏独立生活的自理能力。顾城写道“我和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就象一个小虫子在瓶子里碰撞,就象孙悟空被扣在一个瓶里,想逃走……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我没有办法对抗现实……我没有办法改变世界……我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注:顾城《从自我到自然》。)。于是他听到《滴的里滴》的声音:
脚伸过去 里
看
鱼
锅里
雨
整个下午都是风季
盘子讲话 盘子
盘子
盘子
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
一
滴
门开着门总是轻轻摇晃……
(刊《香港文学》诗页:“滴的里滴”)
这类似疯狂的诞语,实际是他对生活无奈的慨叹。在现实中他陷入了生命的极度矛盾和冲突中,他无法、也无能突围,他已濒临于精神上的崩溃和疯狂状态。当他精心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构筑的“天国花园”被变得实际多了的情人英儿携英国老头出走这一现实撞缺四角的时候,他精神生活的支柱被彻底摧垮了;而当他的妻子因不能忍受他“设计”的太累生活决意离他而去,他最后一线生机也断绝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这唯一的“诗意”出路了。于是,他主动奔赴死亡,投入死亡女神的怀抱。生活中的海子、戈麦、骆一禾等无一不是同顾城一样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只不过冲突的方式、程度因各人的个性不同而略有差异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当代先锋诗人的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更不应用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等去忙下结论。它应被看作是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在现时段为寻找生命意义而焦虑痛苦到极端的反映,是他们处于文化语境深度尴尬状态而又无从解脱的必然归宿。它以殉道的方式启迪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可以预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大众审美趣味的提高,他们的这一幕死亡悲剧的出演,必然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虽然不一定能达到屈原那样崇高的境界,但也决不至于被人们看作是一场无谓的牺牲。
收稿日期:1999—04—27
标签:顾城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死亡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