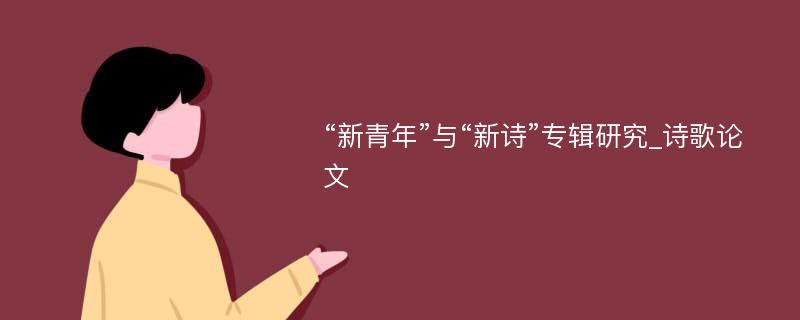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新青年论文,专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16-07
别辟路径地从现代期刊媒体审视诗歌生产,从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方法、文化体制诸多方面观察诗歌原生形态,当可获得崭新的文化认知和学术意义。作为《新青年》(沈阳)附刊的“新诗歌”,显示了地位相对独立和专业色彩鲜明的特征。
一、“新诗歌”专辑刊行缘起
始于1935年的《新青年》(沈阳)的诗歌生产,是与其创刊同步而行的。创刊号即设置“诗”专栏,刊有骧弟(金音)的《雨》(外二章)、可钦的《暮》(外二章)等。但此后其诗歌作品的刊行多呈不稳定状态,时多时少,且有时不见诗歌栏目。《新青年》包括诗歌生产在内的整体大起伏的运行状况,作为诗人的金音那时就有所不满,其在《关于成弦》一文中说道:“《新青年》印到我入XX①第二年,似乎不见起色,不,不是不见起色而是已退色……我既不大高兴写什么,你(指诗人成弦)也离开那里。”[1](P177)
其实,《新青年》诗歌生产的衰败之象,是这一时期前后东北诗坛的缩影。黄汉曾不无痛心地说:“过去的诗坛,虽然是歪曲的生长,但至少是流动着,是变化的,可是现在已经陷于静止的状态里了。”“我们现在很可以找到千篇一律因袭的滥调,把几个固定的名词反复运用着,无疑的满洲诗坛是将沉入死亡的深渊里去了。”[2]
为改变诗歌创作的颓势,《新青年》决定于1940年4月号起发行附刊《新诗歌》。《新青年》1940年4月号封面醒目地竖排印有“特辑新诗歌第一号”字样。该期有两个文件值得关注,其代表了《新青年》诗歌生产的编辑意向。
其一是刊载于广告扉页上的《本志附刊由四月号刊起〈新诗歌〉》,内容如下:
诗在今日正被唱着悼歌,几乎它趋近于宿命的灭亡。我们不甘于默视,要从新的角度上站起来,重新建设一下诗坛,这里没有意见,也没有主张,只有工作。倘严格的向我们要求意见,那意见只是热烈的要求着,写诗的人应该起来援助我们去突破那诗在现实的宿命。
这一短文,针对诗坛“今日正被唱着悼歌”、“趋近于宿命的灭亡”的现实,鲜明地表达了《新青年》文学编者“不甘于默视”诗歌创作现状而欲重振诗坛的意愿。
其二是刊于“新诗歌”封面的扉诗《牝牛》:
镰刀舐过的荒野上
再不会有草叶的飘摇了
人们不再把牝牛赶去了
不再被牝牛爱顾的草呵
像牛乳管一般的丝线
你不得不柔软下来了
不知儿女的牝牛
你有什么早饭呢?
有的仅是草上的牛乳呵!
呵!牝牛前的草呵,
牛乳前的孩子呵!
诗作从生物生态链的角度,诗意地描画出牝牛及其后代的生存状态。尽管牝牛“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但是若失去了青草又从何处觅奶,没有奶又何以使牝牛世代繁衍?编辑的意图十分明显,以此喻义当时诗坛的荒芜与凄凉,并预警着诗歌创作失去本源后的消亡。
《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是东北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独特现象,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惜迄今学界尚无人对此做些许言说。本文试以“新诗歌”第一、二号为文本进行研讨,旨在为日后的深度阐释尽奠基之力。
二、“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
《新青年》对东北沦陷区诗歌颓势的评估,绝非是一时即兴之见,缘由在于诗坛不景气由来有时。在1940年“新诗歌”专辑出版之前,《新青年》曾于1938年7月号(通卷第77号)推出“新诗特辑”,初显了《新青年》诗歌编辑为振兴诗坛而做出的努力,鉴于本文的“新诗歌”专辑研究主体,且“新诗特辑”与“新诗歌”专辑血连脉通,笔者姑且称“新诗特辑”为“新诗歌”专辑的一种前征象。在对“新诗歌”专辑进行文本阐释前,对这一“前征象”进行解读是必要的。
“新诗特辑”束集了七位诗人的十一首诗。其中衣冰(夷兵)四首、山军二首,其余里雁、也丽、寂秋、蕾、迟夜各一首。衣冰是当时诗坛极为活跃的诗人。仅据1938年《新青年》不完全统计,就刊有《绿色的笑脸》、《回归之歌》、《一样长短》、《寻》、《期望着的春天》、《复活》等多首诗歌。
“新诗特辑”中衣冰的诗,多以故乡为主题。《乡愁》再现的是思乡之景,呈露的是怀乡之情。《单恋者》则抒发了对故土的爱恋和思念:那里有“苍老的山坡”,“没葬的骷髅还披着饥荒”,这情景在我“一颗中病的心”里,“印住了社会的模样”。诗人悲哀于自己是故国的单恋者,但却拒绝单恋者的称呼;虽然“国土的泥香和我疏远了,/然而我有不变的心情”。《归去乎》中,“我”向往着故乡甘果的美味,可惜“没等红透了青心”,就有“狂风把我卷去了”!“离乡后的日子”令“我”“嚼着不适味的苦果”。“我”期望清鲜的世界,然而,“有一片沉着的心情,/才会担重我的希望”。对故乡美的期冀与现世狂风的凶残杂糅其中,展现着一种独特的思乡情怀。里雁的《志所闻》以“所闻”命题,记述的是一个他人言说的故事。其所以能得到诗性传播,动人心魄的悲剧情节是始动之源。“全靠蛮力”吃饭的“汉子”,“勉强着抛开了孩子的纠缠”,“两只脚迈上征途”而“不敢回望故乡的天”。“一身疲倦一头汗”地在异乡拼命劳作,“受尽了苦痛与灾难”。尽管如此,只要“想着快要长成的儿啊!/两只枯瘦的手掌就生些工作的热”;忍受着“想要归去不能飞过山阻水隔,/六七个年头忍着没处诉的苦楚”。然而就在此时,“从东风里面飘来一纸家书”,传来“如一把利剑,一只箭镞”的噩耗:“无故葬埋了十三岁的孩子,/在故乡时常采野花的那个岭南山麓。”靠蛮力生活的“汉子”的人生“幻灭了”,“破裂了”,世界“渺茫”而“没有一些声息”,时空中唯有传来“那么微细,那么哀凄的音声,/‘好苦的儿啊!苦的儿。’”《志所闻》冲破了新诗的抒情性规制,将一个离家外出卖苦力的“汉子”的生活遭遇原生态地再现出来,融悲凄、哀痛于质朴、平实的语言中,复沓性的回环境象加重了全诗的哀冷氛围。
“新诗特辑”所刊诗篇虽难说皆为佳作,特色也并不十分突出,但篇章之众却前所未见,《新青年》诗歌编者复兴诗坛的雄心于此可见一斑,它为此后出版“新诗歌”专辑的挽救新诗行动做了很好的铺垫。
三、“新诗歌”专辑文本阐释
从笔者能寻觅到的“新诗歌”专辑中,我们可以窥见比较强大、整齐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第一号中,首篇诗作者是当时被称颂为“给满洲新文学中的新诗,开辟一条动人的路径”、“在技巧和形式的创造上,在内容的主张上,都有相当的贡献”、有着“一个人灵魂之真实的独唱”的知名诗人金音。[1](P270)其他还有陈英、蓝苓、信风、杨野、田兵、罗绮等“各具特色”、“东北新诗的历史会一一记着他们”的诗人,组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此外,还有洪光友的译诗《我们自铁中出生》、《无题》等,形成了展示外来诗歌的另一特色。
“新诗歌”专辑中由金音领衔的《车中吟》令人瞩目。此作包含《奉天行》、《辽阳行》两首诗歌,前者1940年2月15日“成于由辽阳赴奉车中”,后者“成于归辽车中”,均于“二十三日在齐齐哈尔抄就”。②根据作者诗末所言,此二诗当作于1940年2月春光初泄之时,首句“疑此春光是秋光”当为实指。全诗是对“秋”之意境的歌吟。诗人无疑对车外“秋光”充满喜爱;“白云在天”,“满树银霜”,充满着一种参差美和图画美。如果说《奉天行》中的“秋光”还只是一种朴素的画面绘描,那么,《辽阳行》则显示出强烈的色彩对比:红日、落烟、青草构成了一幅“生命的远景”。然而,《车中吟》并非只是对“秋光”的吟诵。诗人虽以“秋光”中的“白云在天”喻“人生冉冉”,然而却又从“霜满枝头”的画面中联想起人生中的“谎言”;当云烟散尽,人们无言地步出月台,已“脸前秋光不在”。其实,“秋光”的“在”与“不在”,既有实指在,又有虚指充盈其间。作者正是在对“秋光”的“实”与“虚”的描摹与幻绘中抒发“秋光”不再的人生哀叹。《辽阳行》则全篇都是对这种落寞情怀的展示,而这种展示是在一种强力比较中进行的:
眼望红日落
烟中有人走过,
如走过一声嘘叹。
归来时
满树银霜那里去了
斜阳照
冻冬 衰草……
哀此大地无梦似有梦
——梦中烟云
一片空
望生命的远景。
烧焦的野地一片
片啊,今年
依然是草青青
青青草。
走出月台的无冠者
秋光是开在灯光中么?
“红日落烟”中有人走过,“如走过一声嘘叹”;满树银霜业已失落,斜阳下唯有冻冬和衰草;“无梦似有梦”的大地,终来还是“梦中烟云一片空”。如此,诗人不禁问道:“秋光是开在灯光中么?”《车中吟》通篇是对秋天意境的展现。其中,诗人运用了树木、白云、红日、烧焦的野地等多种意象,表达出一种对虚空人生无边的怆伤、悲催与恻婉。
思考人生,显然是金音这一时段诗作的重要主题特色。1939年8月初,金音在《暗窗回梦录》中这样写道:“二三年来我想更明白一点‘人生’的事,便如傻子一般想去发掘‘人生的实在’。苦与快,爱与憎,苦快爱憎以外的东西。我因为感到虚空——认识与感觉的虚空;便切念扩大自己。任我‘生活’范围太狭窄,我会继续去生活,去体认。但‘感觉’的狭窄却不能仅持‘生活’可以拯救。所以我去读哲学,纵令更多的疑难愈法临近我。”[1](P171)如果说“冷雾”时代的金音是基于“年轻灵魂的闷气”、“处理为‘现实’蒸发的‘感情’”而创作诗篇[1](P171),那么,随着“生活换了形质”,金音“体认了一个新阶段的‘现实面’。开始了新的生活的体会”[1](P172),诗风有了别样的变化。此时的金音力主诗歌创作“不要凝固于独我的感情范围内”,而应“从‘变动’的意识写出”[1](P179)。《车中吟》无疑是金音于生活之“变”后的作品。早在1941年,吴郎便将《奉天行》中“人生冉冉,白云在天”视为其“创造的人生”之所在。[1](P260)如果说人生“当然离不开梦的”,那么,这种情绪又与金音另篇诗作《纪梦》中的“以海水喻梦”所表现“平和的飞翔”的梦境相吻合。[1](P262)就“人生冉冉,白云在天”句而言,金音当然是在追求一种“理想人生”、“美丽的生命”。其实,自然与人生的相融与互喻,是金音诗歌的典型特征。《塞外梦》中有“望见命运极光亮的一闪”。又有“生活相同用铁锤锤肉身,/免脱的少数尽是遍体金纹,/没有幸免的是背离阳光的大群”。《比邻》中有“生活不是朵朝须花”;《我的感情》中有“人生是开花落叶落叶开花的果物园”;《蔑爱》中有“相聚的苦难结在灵魂的树上”;等等。吴朗曾引金音所言,“诗是诗人全生活的经验,但必得是由这经验中提炼出来,而成为有独特性格的不同于不是诗的东西”[1](P269),正是对金音诗作最好的证说。
金音的另一首诗《音》刊发于《新诗歌》第二号。此作与《车中吟》迥然有别,显露出十足的现代派诗歌味道:
时间的足音 沉 沉如秋海
从来访的八月睡眠中 走来
从零落槐叶的窗边
淋雨中走远
如新病老人扪须长叹
把淋雨的窗子关了
枕着漂流远方人
留下的旧枕。听
窗外的雨;回忆如
无言的诗文,听
时间的足音 沉
沉如新病老人一声“咳”
跌入八月的秋海……
“时间的足音”连接着“秋海”、“槐叶”、“旧枕”等诸意象,展现了一种别样的时间意境特征。其一是时间足音之“沉”。诗人对时间的想象充满了历史感,它成为可以体验和认知的因素。诗人对时间足音之“沉”的形象表征的描画是流动的:它“从来访的八月睡眠中走来”,又“从零落槐叶的窗边淋雨中走远”,这种时间意识的艺术生成,有着足够客观和科学的基础。诗人对时间足音之“沉”的形象表征的描画又是瞬间静止的:沉“如新病老人扪须长叹”,“沉如秋海”。时间足音如此之“沉”显示了诗人时间观中的发展与转换的沉暮之感。其二,时间意识的循环复往。关上“淋雨的窗子”,“枕着漂流远方人留下的旧枕”,“听窗外的雨”,忆“无言的诗文”,时间足音依然“沉如新病老人一声‘咳’”,“跌入八月的秋海”。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时间“周流”说尚不一致,其更多的是对时变而道却不变的无奈与尴尬。
金音刊于“新诗歌”专辑中的两首诗显示了不同的风貌。《车中吟》表露出中国古代词赋的格样,具有鲜明的传统诗文特征;《音》则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派诗歌风采。这不仅说明金音诗歌创作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表现出其诗歌本土与西方的双重印记,还体现出金音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向选择与探索。
东北沦陷区严峻的生活境况和精神束缚,无疑是诗人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新诗歌”专辑当然无从逃脱这种影响。以对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是“新诗歌”专辑的突出特色。
女诗人蓝苓的《追求》是一首仅有三节十四行的短诗,却意义鲜明:“我”“徘徊在十字街头”而不知何往。夜空里动荡着一个声音:“来吧——渡过了小河,/就达彼岸。”然而,彼岸依然“是一片荒凉的沙漠”,“驼铃声是那么遥远”,“在修长暗黑的旅途上,/我作着长久的跋涉”。诗作虽题曰“追求”,却表达了一种人生无望的情怀。
相比较而言,倪南彦的《悼——寄死灵魂》则呈露出一种较为明朗且极具感染力的意绪,激愤之情充盈全篇。诗作中的“你”是诗人谴责的对象。这是一个口言“善良”却梦想“老虎和羔羊的握手”、坚信“善与恶的糅合会开出圣洁的花朵”之人,纵有“火焰般的呼吸/蚱蜢般的脉膊[搏]/奔马般的血流”,但灵魂却已丧失,何以说“你还活着”。你虽有双腿,却“走不上自己的路”;“你大大地张开了嘴”,却“说不出自己的话”;“你本当哭泣”,却反而“呵呵地笑”;“你应该悲叹”,却“死劲地狂嘈”。诗人继而写道:“你用你的两只手/帮助贼奸把弟兄打哭了,/你却窃喜自己/是多么样的机巧!/你用你的款待/放纵奸夫把爱妻奸污了,/你倒对她赞扬/她是如何的美貌!”灵魂的丧失也如同肉体的毁灭。诗人终于判定:“你算死了!”诗作在激愤之情四溢之际戛然而止,诗人跋曰:“我因为过于悲哀了,就是想再多说也说不出来!就此中止了吧!”今读此诗,当然无法确定作品是否有所确指,但其在客观上审视沦陷时期异族当道之时而呈谄媚之相助纣为虐者,确有警醒之意。全篇句式简短,节奏急促,既无修饰,亦废典喻,明晓酣畅、疾风迅雷般的慷慨抒情,显现出一种别样的人格力量。
具有“私语”意味的是杨野的《夜的吟哦》和田兵的《偶歌》。前者是对暗夜的低吟。“想自己对自己说那么多的话,/可是却说不出一句话。”无言的暗夜使“生命的脚步”失去了方向;即便有以稍具方向感的“流星逃跑的轨迹”,也使人感到那是“有吟诗的鬼魂来访”;而寻觅到的亮源又只是“焚翅的灯”,哪里是“理想的天国”的闪亮。饱受孤独、压抑和狂躁的“我”不禁直吐胸襟:“夜啸一声吧!我太悲哀了!”暗夜之感于“我”也许是一种精神视觉,无怪乎诗篇结尾句写道:“我如今丧失了时刻知觉!”黑夜全然笼罩了“我”的精神世界。田兵《偶歌》的“私语”特征,发散出某种哲理的味道,全篇仅八行:
我愿在酒后里说话
因为那时我能忘掉了四周的恐怖
我愿在海岸上歌唱
因为它能给我和声的伴奏
酒和海是我生之灵魂
但它俩偏要离开我
我愿酒在海里
我又愿海在酒里
“我”分明生活在充满恐怖和没有歌声的世界。尽管无忧与快乐是“生之灵魂”,“但它俩偏要离开我”。诗人在尾句无奈地表达了所向往的社会意愿:“酒”与“海”的相汇与互融。这无疑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典型心态。
罗绮的《一条小黑狗的死》是一首具有叙事特征的百余行长诗,其独特性在于,通过对狗的通性品格的赞扬,宛曲表达诗人的人生喟叹。诗人娓娓讲述自家豢养的小黑狗的一生经历,诗里行间,流溢着对小黑狗的爱怜与喜爱之情。当然,诗作的立意不仅于此。作者在对小黑狗生活故事的平缓追述中,突出歌颂了它的忠诚:无论是饥饿、孤独或是被抛弃、遭蹂躏,忠贞是它唯一的选择。然而,当它“没有声息没有呼唤”地“悄悄的死去”,却“并不曾博得一些哀悼”,唯有“我在一个冷清的早晨/带着忧郁”去寻访那“作了你的天国”的城壕。然而,那里只有白雪,“寒风不会温馨了古老的记忆”,“孩子时的梦已无从认取”。忠诚与忠贞的凄凉、寂寞结局和后果也许就是诗人的悲哀所在。语言平实,形式自由,具有鲜明的大众化、写实化和散文化倾向,于沉重中呈现出浓重的乡土色彩和沧桑意绪。
信风的《黑色列车的犯罪》同样是一首长诗,但与《一条小黑狗的死》相异的是,它并不以叙事为唯一特征,而是于叙事和说理中凸显出浓烈的抒情性。如果说中国诗歌的抒情多以含蓄见长、深婉曲折方式为著,那么《黑色列车的犯罪》则反常规地现出激愤格调,寓情于理而直抒胸怀。列车本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一种现代交通工具——“人间聚散的牵引者”,“一身满驮了/嫁女的轻愁/和两地人将要重逢的喜悦”。它命中注定要在规制中行进,沿“法定的距离去散步”,在“被指定的空间/做着有限制的动转”。“偶尔地,虽则它感到了一份/说不出的窒息”,也只是“烦闷地泄出/一声哀吼,/慢腾腾地,/吐出一口闭在心脏里的黑烟”,“算是它向天空表示了/内在的一种抑郁的愤懑”。然而,一旦“神经质的黑色列车”爆发出“心脏里的恨怨”和“复仇之火焰”,则呈现出“脱轨”后异常恐惧的场面:“混乱,腥臭的血泊里,静静地,/安息了整千整万的旅人。”而列车却“并不显现出一种内疚与忏悔”。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发明和使用无疑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方便,但相伴而来的是其不可排除的负面效应。诗人将列车脱轨视为它的“犯罪”,表露出某种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忧患,揭示出工业文明人性理念的丧失。
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是“新诗歌”专辑的另一特色。泛西的《一个平凡的女人》创作于1940年3月14日,是东北沦陷时期少见的以塑造普通女性形象为主题的新诗。诗中的“她”“已经丧失了生的意识”,“盲目地/蹒跚在生活之阴暗的角落里,似一个无声蚯蚓,/宿命的挣扎和劳苦麻醉了她的感情,/从贫困和疲乏里葬送了青春”。这是从人生哲学视角的审视。“生的疲乏已为她罩上白发和皱纹,/灰颓的脸上失去了少女的光辉和颜色,/她已经无形地苍老了,/在那所古屋里。”这里对人物外在特征的描摹。“许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他们所要获得的了,/但她却是空的,/她有的是永远灰色的生活,/永远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走,/如一颗失去了阳光的秋日。”这是从人与人对比中得出的识见。“那些缺乏对命运反抗的力量的人,/只能甘心抛却人生之幸福的权利。/像所有在这大地生长着的人一样,/除了屈服,她不了解痛苦以外的人生。”这是从人生路径的思考中获得的认知。全诗篇幅不长,但却将身处底层、生活于“古屋”社会的“平凡的女人”的形象鲜明、活脱地展现出来,是东北沦陷区妇女形象群体真实生动的写照,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典型性。
罗绮的诗作《题画——写在一幅木刻的背面》,名曰“题画”,意欲以语言再现木刻画面,但诗意也许不止于此。诗人笔下的场景是凄惨、悲凉的,隆冬黄昏,“低矮的土房”摇曳着“蓬乱的,如疯人的长发”的房头草,“两扇破纸窗”装点着“密密的窟窿”,寒风“威武的,打着呼哨”,“粗犷的喘息”着的怪兽挨近了土房;在充满“阴冷,腐草气息”和“土鼠尖叫”的暗屋里,孩子在低泣:“妈呀,我冷——”妈妈说:“孩子,你别哭呀!/听,好像脚步声,/不是你爸爸回来啦——”。“尾声凄恻的,夹杂着颤抖,/一串泪,滴落在孩子冰冷的手上。”作者所题木刻画貌,今人当然已无从可考。但作者用诗句呈现出的画面却栩栩如生。对苦难的书写,无疑是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缩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题画》是诗画互构之作,也是诗对木刻重构的产物。诗人对作品情境的再造,使其平添了故事的情节性,生出一种动态的想象特征。
青扬的《鸩酒之歌》是一首充满激愤情怀的诗。鸩酒者毒酒也。诗人之所以为其而歌,是因为若那“浓烈的鸩酒/能够毒尽我胸中的激情”,也不惜以“广阔如俄罗斯的土地”或“尊贵如罗马的王冠”换取。激愤之烈可见一斑。这种对生命的不惜,来自于对生存尊严的考量。何以至此?盖因“而今的苦难已甚于炼狱”。为深掘这人类难以忍受的“炼狱的折磨”的意蕴,诗人设置了两式责问:“谁填平了沙漠的绿洲/使羊群觅不到水草而悲鸣/谁践踏碎了河山/使农民丢失了耕作的田园。”这里的苦难显然已远离了“自我”的个体,关涉着人类与自然生物的“大我”,融入了政治、时代和集体主义的内涵。在“群我”苦难的激励下,诗人回答道:
我预约下一纸空白的祭文
我含泪将它密密封藏
只要我的子孙不是聋盲
迟早他总把会③这纸空白填上
在“新诗歌”专辑中,如此刚烈、硬朗的诗篇并不多见,展示了诗人对民生苦难的无限忧虑和对“大我”利益的孜孜追求,它远离了沦陷区诗坛风行一时的“自我”吟哦与“私语”式诗歌体式,显露出对人类生存命题的庄严审视和独有的思想力度。
对外国诗歌的译介,是“新诗歌”专辑的另一显征。两期专辑中各刊有一首译诗:《我们自铁中生出》、《无题》,译者署名洪光友、光友,笔者主观臆测似为同一人。《无题》作者James Thomson(1700—1748),通译詹姆斯·汤姆森,18世纪苏格兰著名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很早就曾被翻译到中国,迄今仍源源不绝。《无题》比较明朗地显现了詹姆斯·汤姆森注重自然景物书写的诗歌创作特色,对乘坐在疾驶列车上观赏自然景物的动态视觉场面有生动的映现:
当我们突进,当我们突进乘在列车
树木和房舍回转着向后倒退,
但那平原之上的星天
飞驰地奔来和我们站在同一行轨。
“倒退”的树木、房舍与“飞驰地奔来”的“星天”,形成了巨大的方向反差和瞬间的相向而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强烈动感。这当然不是孤独者的感受,“满天美丽的星群”下那“夜林中的银鸽”,“在黑暗的大地之上群集飞翔”,成为“我们队伍中的同志”。“我们”已然成为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集合。就总体而论,詹姆斯·汤姆森的诗作有些伤感情绪,但《无题》中却有激越的律曲融会其中,且显示了某种特定的英雄情结:“我们将永久向前突进没有惧色,/鹄的要远,飞行要迅速!”有“天空伴着我们前进”,“大地滑过在我们的脚度”。这分明是一个顶天立地者的形象。《我们自铁中生出》则以拟人化的口吻,抒发了支撑高大建筑的钢铁制作的情怀和对建筑工程的铁样的成功信念,展现了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客观地说,“新诗歌”专辑的译诗生产,扩大了诗歌表现题域,开阔了诗歌创作视野,对于促进本土诗歌发展有所裨益。
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文化文本是一个存储媒介。更准确地说:通过‘文化文本’这个接受框架,文学这个符号体系的文本会被作为文化的功能记忆的存储媒介来接受。并且正如对于这些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存储媒介具有代表性文学这个符号体系的文化文本,在它的记忆文化中也拥有一个被阐释的状态:它们是记忆的媒介,同时也是集体记忆回忆的对象。”[3](P239)《新青年》中的诗歌文本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储媒介,无疑是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当下,它也必然成为“被阐释”的“集体记忆回忆的对象”,显示着无法掩盖的价值。
注释:
①原文如此。
②见金音附于《车中吟》诗末的说明,《新青年》1940年4月号,通卷第98号。
③原文如此,疑应为“会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