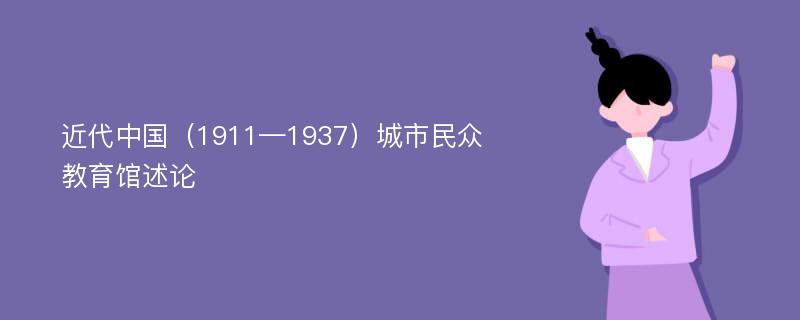
毛文君[1]2002年在《近代中国(1911—1937)城市民众教育馆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论述近代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的产生、发展历程及其开展的主要活动,借此以窥近代民众教育馆与中国城市民众早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全文共分叁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近代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历程、近代民众教育馆的行政组织与活动、民众教育馆存在的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近代民众教育馆萌芽于甲午战后之办报兴学,自是而后,至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结束,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1896—1911年)、初步发展时期(1912—1927年)、繁荣时期(1928—1937年)、曲折发展时期(1938年—1949年)。每一时期民众教育馆基本都是围绕着讲演、阅读书报、出版刊物、举行各种比赛等活动展开的。近代民众教育馆的设立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民众的文化素质,普及了现代知识,增加了城市民众的现代性,培育了城市民众的公共精神,向各界人士提供交往的空间和机会;促使城市中传统的休闲娱乐形式与现代休闲娱乐形式并存,而后者渐有取代前者的趋势;同时也促使近代城市文化向大众化发展。 城市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尽管有一定的成效值得肯定,但是由于民众教育馆发展中基层政府和一般民众对创办民众教育馆存在认识偏差;地方势力插手民众教育馆人员的任用;民众教育馆分布和发展不平衡;民众教育馆活动组织不佳;民众教育馆职员待遇较低等问题,使近代民众教育馆所发挥的作用离社会教育人士的主观愿望和城市民众教育馆在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应发挥的作用还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张鹏[2]2008年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9-1937)》文中指出20世纪20至30年代,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教育思潮风起云涌,民众教育思潮是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的民众教育运动不断发展。山东省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一直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山东也受到民众教育思潮的影响,民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实施民众教育最重要的中心机构——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应运而生。1929年至1937年,山东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这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这一时期,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并开展了各种民众教育活动,并设立了民众图书馆、电影院、运动场、民众茶园等重要的民众教育设施,同时,出版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民众周刊》、《民众教育周刊》等民众教育刊物。另外,该馆在乡村进行的实验和辅导活动也推动了农村乡村教育的发展。因此,对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进行全面研究,对于把握近代山东民众教育的发展规律,探寻民众教育的作用与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民众教育馆的兴起。对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民众教育运动展开论述,介绍了山东在这一时期民众教育发展的概况以及民众教育馆建立的客观条件,并对与民众教育有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民众教育馆概况。主要从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历程、组织及职员、馆舍、教学事业、临时活动、附属团体等方面展开。重点梳理了民众教育馆在山东近20年的发展历史。第叁部分,董渭川与民众教育馆。董渭川在任该馆馆长期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对他在馆内的活动的详细论述,总结并论述了其民众教育思想。第四部分,民众教育馆的主要设施。重点论述了图书馆、运动场、电影院、民众茶园等民众教育馆内设施。对这些设施经营状况以及意义进行了探讨。第五部分,民众教育馆的出版编辑事业。详细阐述该馆出版的定期刊物和不定期刊物,重点对《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的发行以及影响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民众教育馆的乡村实验区。详细阐述了民众教育馆在祝甸乡进行乡村实验活动的背景、行政组织、活动原则、工作演变等内容,重点论述民众教育馆在实验区进行的各项活动。第七部分,民众教育馆的第一民众辅导区。主要论述了第一民众辅导区建立的背景、组织、工作路线以及工作状况,重点阐述了工作路线以及在乡村的实际工作状况。第八部分,民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与存在问题。首先从民众教育馆对近代山东民众教育、对各县民众教育馆的指导、对山东区域现代化以及山东文化生活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然后主要从经费、人才、活动效果以及城市到乡村路线等四个方面阐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系统分析了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和解决办法。
吴善家[3]2014年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众教育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逐渐酝酿兴起的一场教育启蒙运动。20世纪20至30年代,民众教育思潮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民众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行民众教育的综合机关——民众教育馆也应运而生。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产生发展是近代民众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囿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方面的限制,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发展远不能和江浙、山东、河北等民众教育发达的省份相比。但是作为后起之秀,我们更容易从陕西民众教育馆的发展中,窥探近代民众教育馆发展的始末。本文分为以下几个步分:第一部分,结合民众教育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对陕西民众教育的发展进行概括。第二部分,对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组织构成、施教机关、人员构成及主要运动进行梳理介绍,并对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职员选择标准进行分析。本文认为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职员来源是多元化的。民众教育馆馆长的任用标准是高学历和年富力强。第叁部分,分析了民众教育馆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及其取得的成就。第四部分,对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尽管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在当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对陕西社会的近代化而言作用尤为明显。尽管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将其放在近代民众教育馆和近代陕西的发展中来看,我们还是要肯定民众教育馆所起到的作用,它能我们今天社会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民众教育馆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结果。民众教育馆的开办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对“启迪民众”、“塑造现代公民”有着重要的作用。
孙语圣[4]2006年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个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天灾人祸交织纷呈。本文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1931年大水灾是民国灾荒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创伤和全方位的社会震颤。此次灾害,无论从自然与人为的致因,还是直接的危害与深远的影响,都极具典型性,在民国历次自然灾害中最为显凸。并且此次灾害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期、裹夹于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其间、纠缠于国共武斗和国民党内部裂晋纷争的困局。在灾害救治中,因其“百年不遇”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因此有着“解剖麻雀”的标本意义。社会化是贯穿全文的经脉和主干骨,是笔者自我解释的一个中心名词。本文认为,灾害救治社会化,即是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国民国家社会意识的增强,在灾害救治中,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的动员与交流,特别是民间社会的响应、主动、自觉。民国时期,民间慈善传统的承续、近代经济的发展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大众传媒的强力助推和交通通讯的发展、近代国家思想的播扬与政府的无奈让渡等,使灾害救治社会化的动因与条件初步具备。社会化救灾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制度化的社会设置,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灾害救治的组织、立法等方面的社会设置是比较健全的。官民合作的救灾理念非常清楚明了。在1931年水灾救治中,采取了特殊的赈灾路径,即官赈义赈化的取向,政府抛却其原有一套赈灾机制,在赈灾方针、赈款筹集、赈灾办法与程序、组织机构、人事任用等方面,全面援用民间义赈、特别是新型民间义赈的机制,使得社会化的立论更有依据、更经得起推敲。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是本文的主体内容。社会各界对灾情与灾因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办法;政府与民间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救灾人力资源、物力、财力资源的进行全社会的动员;救灾信息资源也得到一定的传播布达;社会化的监督方式,使得救灾的成效得到尽可能的保证。最后,本文对灾害救治社会化进行绩效分析,运用大量具体数据量化分析社会化的成绩与不足;并指出救灾社会化中的困境与异常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财力汲纳的乏力与结构畸偏、外患不断的侵扰、内乱频仍的蹂躏耗损、奢靡的社风等所造成的动力不足和代食品现象、米禁与禁止移境就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空间挤压的冲突等异常问题。结语部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隧道,进行比较对照,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指出两个时期在社会化救灾方面各自的成功之处和缺陷所在,认为解决现今救灾主体的稀缺、救灾物质资源来源的单一化、人力与智力支持网络不够宽阔、监督机制不健全、救灾立法滞后等问题,才是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并且指出,社会化灾害救治是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机内涵之一。
万妮娜[5]2011年在《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综述》文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以科举考试为人才选拔方式,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的,以儒学经典为核心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培养行政管理人才。而针对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则因缺乏体制与经费的支撑十分不发达,更多的是通过乡绅等民间办学、官学和书院的途径,普及文化和进行道德传播,以达到维持社会和谐
张研[6]2007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社会教育》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从广义上讲,凡是社会活动,对个人的身心产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影响的教育皆可称为社会教育;从狭义上,主要指学制系统以外,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私人和民间团体推动为辅,为了提高失学民众以及全体国民的素质,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教育主要是指社会教育的狭义形态。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产丰富,尤以人口居全国之冠,故历来养兵之多,无与伦比。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四川省处于拯救民族危亡,实行持久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在1937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他认为在对日战事中“就是只剩下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可见蒋介石对四川在抗战中的作用的信赖与倚重。四川不仅人口多,面积大,物产丰富,而且地理位置介于西北陕、甘、宁、青与西南滇、黔、湘、桂诸省之间,位居中策应和控制南北之枢纽。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业和教育机构也随之内迁,其政治地位亦不断提高。四川成为国人期望的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与战时的后防重地,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全面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和使命,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唤起这七千万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动员他们为抗战服务,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成为争取抗战胜利之紧要任务。对广大民众实行普及教育,仅依赖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资源尚十分紧缺,不具备实行大众化教育的条件。因此,以全民为对象的社会教育,便成为抗战教育,民众动员的重要途径。鉴于四川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财力上给予川省社会教育以极大支持,教育部又先后颁布十余个社会教育文件给予政策上的指引,以期全面促进四川社会教育的迅速发展,在战时起到支援民族复兴,动员民众的重要作用。四川省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发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将社会教育的行政地位独立确定,1941年四川省社会教育行政从第叁科中分化出来,由省教育厅成立第四科专门掌管社会教育事宜。为配合抗战建国,四川省教育厅重新制定了战时各县市民众教育的新目标,一切活动,均以激发民众抗敌情绪,培养民众抗敌力量,发挥战时服务精神,赋予社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指导全省社会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促进全川社会教育事业的全面开展和对民众广泛的抗敌动员。抗战为四川社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由于以上各方面因素,四川省的社会教育在抗战时期得以稳步前进,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发展的顶峰阶段,为全国抗战胜利做了充分的民众思想动员工作,同时对四川社会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四川社会教育实施途径众多,在文中一一展述又是不太可能的,而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活动几乎囊括了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因此本文选择办理规模最大、最具成效的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为中心进行研究。抗战时期,政府对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的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经费数额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尽量完善社教体制,以保证社会教育事业正常有序的开展,从中我们可以透析出四川社会教育的运行机制。为配合抗战建国,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在政策方针的指引之下,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教育、展览教育、社会活动六个方面,以宣传抗战为中心展开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社会教育事实的分析,总结社会教育的发展,民众素质的提高与抗战建国、社会进步的直接的联系。政府竭力提倡四川社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动员和鼓舞川省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使国民素质得以提高,改善了整个社会风气,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增强了爱国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注意到,由于战时社会的不稳定,经济的崩溃,人才的缺乏等原因,社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是总体上,在抗战时期,四川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徐冬[7]2012年在《民国通俗讲演所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通俗讲演所是当时以“通俗讲演”为主要方式对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及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对其研究,除可以对近代以来的“口语”启蒙状况和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效应有所了解外,还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住近代思想启蒙对象下移、社会文化变迁大众化这一重要历史脉络。“通俗讲演”即用浅近的语言向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文盲、半文盲民众)发表意见、阐释观点。以“通俗讲演”作为社会教化的手段,古已有之,其目的无非是把上层统治者外在的压迫奴役内化为下层民众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造就出千千万万驯良的帝国子民。时至近代,随着思想启蒙对象的下移、文化变迁的平民化倾向以及社会教育的兴起,“通俗讲演”被赋予了“启迪民智”的新的时代职责而得以发扬广大,其相应的机构设置也纷纷兴起。清末宣讲所的创办在1910年代盛行一时,为日后民国通俗讲演所的运行积累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操作经验,提供了第一助推力。满清覆亡,民国肇造。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崩溃,为社会教育事业的纵深发展扫清了巨大障碍,通俗讲演所事业也随之得到长足发展。民国通俗讲演所的人事设置虽十分简单,但却有着极其缜密严谨的运行准则,在人事选拔、人事培养、讲材编订、讲演程序及讲演技巧等诸方面均有章可循,这保证了其运行的较高质量。作为官方设立的正规社会教育机构,通俗讲演所的开办及维持经费主要由政府在社会教育经费项下拨给,同时,各地民间资本也给与了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却对整个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有褴褛筚路之功。北洋政府成立后,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推进、规范通俗讲演所事业。北洋政府统治前期,尤其在1915至1918年间,由于各级教育部门大力推进,再加之全国政局相对安定,各地通俗教育讲演所数量增长较快,出现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黄金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国内文盲遍布,人民知识水平落后、素质低下的严峻现实,遂积极推行民众教育,大力创办社会教育机构,促使通俗讲演所事业进一步得以发展。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至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突飞猛进,步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黄金期”,进而达到巅峰。民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使得通俗讲演所的讲演内容极其丰富多元,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思潮均有所涉及和体现。进步方面的讲演内容可主要分为鼓励爱国、培养公德、普及法律、振兴实业、发展教育、革除陋习、灌输常识等类别。此外,通俗讲演亦含有复古、反共、奴化教育等消极乃至反动的内容。但从整体看来,通俗讲演所所宣扬的进步思想理念仍据主要方面,这也是把其定位于启蒙教育机构的最基本依据。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迎合救亡图存、启蒙求新的时代潮流,向下层民众大力灌输新观念、新文化、新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觉醒,确实在民众爱国热情的激发、民众先进价值观念的培植及民众传统生活陋习的革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效。但是,由于外在经济支撑的乏力、社会动荡的干扰,再加之讲演内容的鱼龙混杂、讲演员自身素质的低下、民众对讲演的漠视、抵制心理等一系列内在因素,使得通俗讲演所事业的社会启蒙效应受到极大制约,与其所标榜的“启迪民智”的崇高目标还相差甚远。与同时期的其它思想启蒙及社会教育事业相比,通俗讲演所事业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首先,这一事业在启蒙实践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是“口语”,而不是文字;其次,这一事业把受众定位于下层社会的文盲、半文盲民众,实现了辐射范围的最大化;再次,这一事业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促使民众心理嬗变的“隐形”层面,而不是立竿见影、直接可用以改造社会的“显形”层面。民国通俗讲演所运行的历史经验,为当前加强基层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文化教育工作者素质以及转变基层文化教育工作活动形式等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杨才林[8]2007年在《“作新民”、“唤起民众”》文中研究指明百年中国近代史,救亡图存是首要问题。变革教育,培养“新民”是挽救危亡的要略,国人认识到此并付诸实践,可谓抓住了国家的命根。清末以来,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和启蒙大多在知识界、政界发生效力,普通国民知觉甚少。民国时期,在诸多教育界人士的发起和推动下,在政府的多方支持中,旨在面向广大国民的社会教育持续进行了叁十多年。民国社会教育史的研究是近十年来一个学术成长点,以往论述罕有概观,可钻研的空间很大。本文力图爬梳史料,勾要提玄,搜求各类事业的内在关联,提炼宗旨,概括阶段特征,做出总体评价。本文研究的是狭义的社会教育,即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普通学校教育以外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共产党的社会教育和日伪政权的社会教育不在本文研究之列。笔者认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皆属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名异实同。社会教育是就施教的范围而言,民众教育是就施教的对象而言,是一个命题的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名称较为适宜,因为它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序列。本文出现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概念,得以统合为社会教育的范畴,不是依赖抽象的逻辑规定,而主要是用问题去统摄。这个问题就是“新民”的培养问题。第一章论述社会教育从清末继续推进到民国的根由。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作新民”与“唤起民众”,这也是社会教育从清末继续推进到民国的根由。民国初期,晏阳发起平民教育运动,以“作新民”为宗旨,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四力兼备谓之“新民”。“唤起民众”的口号出自孙中山《遗嘱》,晏阳初说,平教会所努力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唤起民众”的工作,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也解释民众教育即是“唤起民众”。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的“救国新民”主张,进而晏阳初“作新民”和国民党“唤起民众”的口号,其培养新国民的思想一脉贯通。新式学校教育有很多成绩,同时不可否认产生了不良结果,主要表现有叁:新式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模仿外国,由此造成事事不如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学校教育缺乏中国化,所教所学与社会需要脱节;普及教育远远不够。民国所需要的教育,尤其是面向广大国民的社会教育,除了为民众自身解放外,更需要昂扬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起民族自觉,使广大国民都能起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新民”的口号更多体现了社会教育的价值理性,而“唤起民众”的口号则更多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工具理性。两者都弥补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不足,其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民,最终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这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发展进程。通过对民国学者社会教育分期的总体纵向考察,得出两点依据:一是根据政权更迭,二是根据社会教育的突出特征。据此,笔者将民国社会教育史大略分为四期:1912-1918年,社会教育的确定时期,因为此期特别注重通俗教育的推行,也称通俗教育运动时期。1919-1927年,社会教育的发展时期,因为此期平民教育盛行,也称平民教育运动时期。1928-1937年,社会教育的全面扩张时期,因为此期民众教育的提法盖过社会教育,也称民众教育运动时期。1938-1949年,因为此期处于全面抗战继而全面内战,所以称战时社会教育。对于中间两个个时期社会教育的内容,以往论着叙述较多,笔者重在概括其阶段特征。对于通俗教育和战时社会教育,以往论着涉及极少,笔者尤为着力,进行了详细论证。第叁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行政。社会教育行政包括制度的建设、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培养、经费的筹措划拨。对于前两个方面,以往论述较多。后两个方面尽管材料稀少,笔者作了简要梳理。第四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设施。民国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可分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属于学校式的社教机关与普通学校的设置不可相提并论,在教育对象、教材、课程、上课时间、目标诸方面多有不同。属于社会式的社教机关,如各类场馆等。除此之外,1940年代各级学校也成为办理社会教育的地方。其中,民众教育馆是综合的施教机关,民众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为单一的施教机构,设置遍及全国。科学馆、礼乐馆的设置虽属个别,但具有特殊性和极大的象征意义。所以笔者择取以上六类设施集中论述,分析了以往论着不曾涉及的一些问题。其中博物馆、科学馆、礼乐馆叁项,以往论着中未见。第五章论述民国主要社会教育事业。民初社会教育以通俗演讲最为突出,平民教育运动初期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后期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增多,1931年教育部关于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报告中列举叁大类58项,几乎囊括普通学校教育外的一切教育活动。笔者主要择取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以往论着很少论及的通俗演讲、识字教育、通俗读物、生计教育、社会体育、电化教育六项事业进行了论述。第六章分析民国社会教育的演进特点、成效、弊病及其制约因素。民国社会教育的演进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由观览施教而入于分区实验、由农余补习而入于乡村建设、由补助的附属机关而入于正式的学制系统、由单纯的识字教育而入于全民的救国教育、社会教育学术化和组织化。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思想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设施为后世继续沿用,有关规程制度也是后来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的张本。成绩并非斐然,然决不能谓之无用。不能否认社会教育有若干收获和成就,但也不能不看到它曾遭遇了若干内在的和外在的困难和阻碍。民国社会教育理论的提出和实施,本在纠正学校教育之弊,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距,反生其弊,主要表现为:社会教育理论尚未系统化;社会教育事业“全面开花”;集中在城市,忽视乡村;实施方法多有不当。成效不彰,为国人所诟病,主要制约因素有叁:社会经济方面,民国经济困难,财政吃紧,民众忙于生计,无暇受教。社会政治方面,民众与政府隔阂很深,社会教育若不借助政权就无力推广。社会心理方面,教育界多数人士囿于教育即学校的偏见,对于社会教育不独鲜见积极赞助,甚且消极地施以诽谤;社会教育人员残留士大夫意识,不屑与民众为伍;民众对社会教育多持怀疑、顾虑和敷衍心理,并未自动的求教育;社会教育是出于教育家的满腔热忱和国家的政策所需,并不是应着民众的要求,乃是施教者为主动,民众为被动。结语得出四点史识。从臣民到新民、公民,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高端目标;民本观、民力观是深藏在社会教育运动中的思想基础;民国社会教育发展历程的重心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并未以”民众自身解放”为本位;民国社会教育属于改良范畴,但与革命一样,构成历史合力,同样促进了社会发展。
黄国庭[9]2005年在《江苏公立民众教育研究(1927-1937年)》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教育运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该教育运动中由着名社会团体举办的民众教育试验已经作了较为充分深入的研究,而对于这场民众教育运动中由国民政府各级教育管理机关,特别是各省教育厅发起、推动的公立民众教育部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本篇论文选取当时公立民众教育兴起得最早、也是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省份江苏省,作为探究公立民众教育的对象。本论文主要考察走在全国发展前列的江苏省公立民众教育,如何在江苏省教育厅的主导下,在没有国内外相应制度可资模仿、借鉴的情形下,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逐步完善,又如何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不得已做出相应重大变动的过程。本论文不仅考察江苏省民众教育系统演变的过程,而且还着重考察每次重要规程制度变更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并检验这些规程制度在实际中的执行状况。在论文最后,作者还将江苏省的公立民众教育与私立的民众教育实验进行比较,从中归纳出公立民众教育的优点与缺点。 在研究资料来源方面,本论文与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着作稍有不同。后者以民国时期出版的研究着作为主要参考资料,还未能充分利用那一段时期的民众教育期刊。而本篇论文则主要参考了两份发行自江苏省的权威民众教育刊物,再辅以参考当时出版的相关着作,在参考资料来源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林星[10]2004年在《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近代福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福建这个独特的区域内,以福州和厦门为龙头,以开埠为契机,福建城市开始了百年缓慢而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全文以城市近代化作为主线,力图全面深入地反映近代福建城市经济的成长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探析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导论部分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进而说明本文的相关概念、研究框架、理论方法和基本史料。 本文试图对福建近代城市的历史作多角度的长时段的分析,将分段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时间为顺序,以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中华民国建立和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切点,将近代福建城市历史分为叁个阶段,主要从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角度阐述城市发展的概况。各章之中分节讨论贸易商业、金融、工业、城市建设等。上篇包括以下几章: 第一章是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主要探讨生态环境对福建城市的影响和古代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和特点。第二章是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时间跨度是1843年开埠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这一阶段是福建城市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起步时期。主要叙述开埠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初步近代化。第叁章是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时间跨度是191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阶段是城市初步发展时期。主要阐述民国建立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是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即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这一阶段福建城市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沿海城市发展滞缓,内地城市有了一些发展。 下篇是横向的专题研究,选择一些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力图从多层面反映城市的变迁。包括以下几章: 第五章是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探讨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以及城市和附近乡村的互动关系。第六章是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城市中的外国人,以及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第七章是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讨论的是近代教育的发展、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第八章是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主要阐述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婚丧嫁娶,闲暇生活等方方面面风俗的嬗变。 结语部分是对福建城市发展的整体考察。着重对福建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近代化成效及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 近代中国(1911—1937)城市民众教育馆述论[D]. 毛文君. 四川大学. 2002
[2].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9-1937)[D]. 张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 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研究[D]. 吴善家.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D]. 孙语圣. 苏州大学. 2006
[5]. 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综述[J]. 万妮娜. 理论与现代化. 2011
[6].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社会教育[D]. 张研. 四川大学. 2007
[7]. 民国通俗讲演所述论[D]. 徐冬.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8]. “作新民”、“唤起民众”[D]. 杨才林.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9]. 江苏公立民众教育研究(1927-1937年)[D]. 黄国庭. 华南师范大学. 2005
[10]. 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 林星. 厦门大学. 2004
标签: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