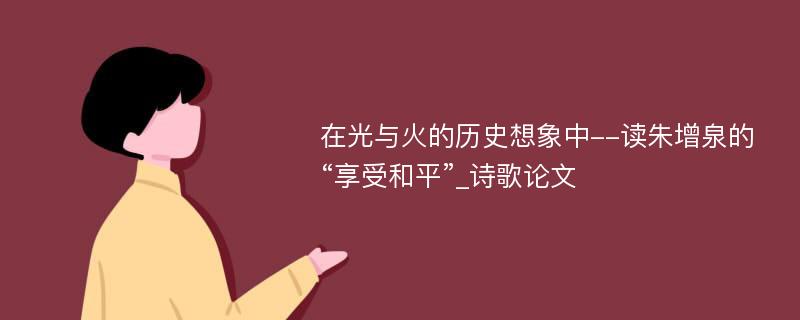
在光与火的历史想象中——读朱增泉的《享受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历史论文,朱增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第一部诗集《奇想》问世,朱增泉的名字似乎一直都与硬朗苍阔的诗歌质地扭结在一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璀璨一时的军旅诗空中,朱增泉游走于悲壮的在场与厚重的历史之间,言说了一种特殊的存在高标。从“踏着地动的脚步走来/沉重的脚步里随烟尘腾起/和着悲壮哀哭的啸啸号声”的《猫耳洞人》到“点点浓墨——蘸取四溅的硝烟/纪录下生命与战争的撞击”的《迷彩服》;从“分娩灵魂,一次血光照耀的大典”的红色辉煌到“一个个年轻战士/在生命之光爆发以后/收缩成一个个灵魂的黑洞”的《黑色辉煌》;从“骑上思想的奔马/去穿越历史的荒漠”,“决心去做一次/灵魂的远征”的《出奔》到“沉重的历史是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的《星空》……英雄气质和历史追寻构筑了朱增泉诗歌无可怀疑的价值指认。一九九九年八月《地球是一只泪眼》出版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这位将军诗人在军旅诗坛上鲜露其颜而是专注于军旅散文的钻探和经营,这固然一方面与诗人的兴趣相联,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诗歌创作整体的沉寂和消落。所以时隔八年,当朱增泉的第八本诗集《享受和平》出版发行,不得不让人充满期待,这是一种努力,也是一份难得的惊喜。
当诗歌进入“消费”时代,诗人的良知、作品人格所形成的文化人格首先或者不自觉地开始坠入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泥沼,历史语境化为虚幻的背景,支撑人类的文明支离破碎,这是一种整体的尴尬境地:现实表象细节的过分关注、蹈空凌虚的内心矫情、不痛不痒的书写、麻木不堪的灵魂,“大众狂欢”是一块刺眼的遮羞布,既蒙蔽了缪斯神性的身躯又灼痛了历史饱经沧桑的双眼。然而当我们阅读《享受和平》时,却不得不接受心理突变的状态,重新生成我们已经陌生很久的承受之力。斯蒂芬·欧文说过,“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使我们摆脱所承继的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和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诗歌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在过去和未来的向度上具有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力;诗歌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在共时的状态中抵达人类整体的共鸣和感怀。在《享受和平》中朱增泉将我们重新引领到了宏大恢阔的历史语境之中:
……荒原
你如此旷远
我因想起那支古歌而怀念历史
琐碎和平庸永远会令人窒息
——《荒原》
朱增泉从来都无意于在语言学的多维空间中展开文本的零度写作,没有历史所指的能指和没有个人的情怀的语词永远都是这位将军诗人不屑所为的。朱增泉曾经反复强调“我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诗人”,他不会吟风弄月,更不会无病呻吟,军人的思维维度决定了朱增泉的诗歌所指必是历史的刚硬和阔大。茫茫草原,千里绵延,让朱增泉首先“想起厮杀,怀念英雄”,“天边/山峦横卧连绵/如人马簇拥的营地/山岩的姿势和色调如此悲壮/如出发前的一片躁动和纷乱/如激战刚过古战场一片狼藉”(《荒原》);乌伦古河的流水古老苍凉,在朱增泉眼中幻化而成的是“悲壮”,是“铁骑飞奔剑戟铮铮火光四溅”,“边关的冷月凝成的霜花被马蹄踏得粉碎/血流成河”(《乌伦古河的流水声》);大漠孤烟,边陲戈滩,让朱增泉遥想起“狼烟——边报如飞”,遥想起“噶尔丹——骄横的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奔跑的黄羊在朱增泉看来“如古战马幽灵般出没/一缕黄尘孤魂般旋起/看草尖仰天长啸”(《边陲》)……在朱增泉诗歌的历史语境中,战火与光焰是意象,是场景,也是存在敞开的所有可能性。
在光与火的境界中,历史大开大阖,容不得半点的扭捏和造作;在光与火的境界中,历史至大至刚,容不得半点的暧昧和矫情。在光与火的境界中,朱增泉往往倾向于历史恢阔宏大的公众事件的书写,这是朱增泉诗歌区别于当下大部分诗歌的显著特点。毫无疑问,用无边的“我们”话语统摄整个诗坛是一种非常态的叙事,然而只是顾及追逐琐碎的尘世和封闭的内心,不吝将诗歌逼仄到另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也是这位将军诗人无法忍受的。朱增泉一直试图努力营造一种具有整合能力的诗歌,这种诗不仅具有诗歌的自足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将历史和时代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记录了新中国辉煌昌盛的起点,数十年后朱增泉遥望想象,激昂、感慨,“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海啸/最响亮的就是这句口号——‘人民万岁!’/那个时候/共产党最讲认真/老百姓的心情很好”(《人民万岁》);二OOO年八月十二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舰艇在巴伦支海域演习时因鱼雷爆炸沉没海底,与“库尔斯克号”一起消殒的还有一百一十八个鲜活的生命,几年之后朱增泉仍然震惊、痛心,“这些军人死在没有战争的日子/他们是为了战争而死的/大海在永不停息地咆哮”(《库尔斯克号葬礼》);甲午战争中的“一只锈红如血的大铁锚”牵动了朱增泉敏锐的神经,也将读者带到了血雨腥风的历史在场,“一只北洋水师的大铁锚/在海底凝结的百年老锈/像风干在战尸上的暗红血迹/看它一眼/就想哭”……
在朱增泉的诗歌中,历史不是破绽百出窘态毕露的待剖析之物,朱增泉无意逼问历史叙事中的文本想象;历史也不是在边缘缝隙之处设置曲折诡谲的迷宫,朱增泉无意于在历史的枝端末节做精雕细琢。朱增泉惯常于屏息凝视大历史的悠久深远,并在这种屏息凝视中寄寓人类生存困境的当下追思。正如有评论者指出:“他的思想视野却不仅限在刀光剑影,他从火光与鲜血中看到军人灵魂的辉煌,看到人类怎样艰辛地耕种着历史。他的诗情宏阔、联想丰富、气势磅礴,并且富有深邃的哲理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他以独特的方式和形式,思考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① 如果说光与火的历史境界和阔大恢宏的历史命题奠定了朱增泉诗歌凝重醇厚的底色,那么朱增泉在这种凝重醇厚的底色之上处理的是关于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喷绘的是一位将军在和平年代里对于民族和人类深沉的忧思和企盼。
和平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然而人类又在不断地破坏和平,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悖论。种族纷争、局部战争、核大战的威胁,始终就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掉下来将人类和地球劈得粉身碎骨,人类在脆弱的承诺和互为人质中艰难地前行着。遗憾的是,这又是一个充满了遗忘的时代。戏谑和荒唐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的无聊闹剧,鲜花与和平成为熟视无睹的存在,一切都在变得轻佻和浮飘,捏一把空气似乎也能感觉到某种惶惑与无措。我们遗忘了历史,我们遗忘了曾经的道路是怎样一种实实在在的震撼。然而历史似乎又总是喜欢在冥冥之中做出补偿性的置放:遗忘同时承担;沉醉同时清醒。毫无疑问,朱增泉将军就是这样的承担者和清醒者。
朱增泉既为现代文明将人类迎纳进了一个自由奔腾的时代而欢跃,“火焰将人们的眼睛照亮,将胸膛照红/火焰菠人们的额头放光,将人的精神照耀得焕发/火焰永远以升腾的形态提示人类:向上,向上”(《喷射的火焰》);他也为共和国五十年的花团锦簇和万民同乐而欣喜:阳光、白鸽、迎考的学生、晨读的老人、雍容的女人、欢快的小狗,青青的草叶尖上“每一滴露珠都在滋润着和平”(《享受和平》)。然而作为一位将军,更多的时候他为和平年代里所潜存的种种危机而忧心忡忡。他为世界的和平格局而忧,“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尚存,战亡者的白骨尚存/从集中营中生还的人,心灵的伤痕已不可能抚平/今天,战争的恶魔又在时时向我们逼近/科索沃远在欧洲,却有五枚精确制导炸弹/突然钻进中国人心中爆炸”(《享受和平》);他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忧,“中国在海上白白流失了六百年岁月/比流失岁月更重要的/是流失了郑和的济沧海精神啊”(《凭吊郑和》);他为世界上人权的不平等抱不平,“满街西方游客/一个个挽着泰国应召女郎/满街游荡/泰国本国的男青年/却一个个被阉了,做人妖/为了求生/夜夜为游人卖笑/风景宜人,风气不宜人/人权与人权,彼此不平等”(《帕塔亚景观》)……他更为当代社会价值信仰的沦落和迷失而忧。这是一种双重悖论:现代文明的发展刚刚把人从禁欲的前门解放出来,官能享受的泛滥又把人从后门交给了魔鬼。市场经济和商业化为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也无情地瓦解了当代历史建构起的包括情操、道德、信仰等文化观念;“解放”的同时意味着放逐,无所皈依的“游牧文化”收容着新一轮的荒芜和苍白;人们丧失了方位和目标,但每个方位都成了目标。信仰的迷失和精神的沦陷导致了整个社会心理出现浮轻的趋势,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存在不能承受之轻》中写道,“我大步地走在灰扑扑的卵石上,承重着我生命中横朦空虚之难以忍受之轻。”
当原罪开始覆盖世界的时候,朱增泉以自己的方式执著地顾惜和守护着人类精神的永恒存在:他不像怒发冲冠的战士那般嘶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思想家那般哀鸣。他以将军的气魄和风度,俯瞰众生,不动声色却万事了然于胸:他感慨曾经剽悍的蒙古雄性文化的消失,“在古代,在草原上的五名剽悍骑手/足可发动一场千里奇袭/去投入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如今,他们学会赚钱/一次又一次将游客团团围困”(《五个晒太阳的牧人》);他悲哀现代文明人的退化和无知,“这五位牧人/用几匹老得不能奔跑的老马/驮着一群群进化得不会骑马的游人/游客们嘻嘻哈哈骑马拍照/在照片上把自己打扮成纵马驰骋”(《五个晒太阳的牧人》;他在泰国鳄鱼湖边感叹现代人的无聊和乏味,“人们生活过于安定/便觉乏味/都来鳄鱼湖观光/花钱买些心惊肉跳”(《鳄鱼湖的观光客》),“如今,人间已经把丑陋当稀奇/动物的凶残/也有人崇拜”(《鳄鱼皮制品》)……一个伟大的诗人应该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圣哲,将人们引渡出情欲的苦海。朱增泉也试图以一种精神的高度和信仰指引芸芸众生,“我在此仰望雪峰,感受到清澈、高远/也感受到强烈的紫外线,感受缺氧/感受到一次高海拔的人生仰望/人生不可没有仰望/如同江河都向往海洋”(《仰望雪峰》)。
《享受和平》中的诗作于近几年,朱增泉的诗写得越来越深沉,也越来越具象。朱增泉将往日金戈铁马任我行的激昂豪迈和肝胆峥嵘隐于风高月清和宁静悠远的思索之中,这是诗人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也是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扭结在一起的产物。朱增泉,这位从老山前线猫耳洞里走来的将军诗人,一直让我们惊喜不断。作为一位职业军人和军旅诗人、军旅散文家,在“英雄”和“战争”渐渐成为面目模糊的存在的年代,朱增泉在诗歌中并没有去诉说一种被迫承担的现代文化焦虑,而是以将军的气度徜徉于历史长河的钩沉和现实生命的关照之间,探寻着人类精神的诗性特质。这也许是朱增泉给予我们的又一种奉献吧?
注释:
①张同吾:《耕耘历史与放牧灵魂——朱增泉和〈世纪风暴〉》,《文艺报》1995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