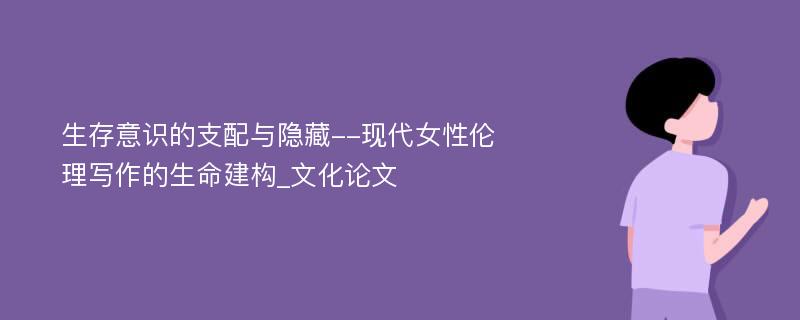
存在意识的显性与隐性——现代女性伦理书写的人生营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隐性论文,伦理论文,现代女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存在”可以囊括生命和生存两大方面,二者特有的规定提供了作家思维的内质和审美指归,个体的主观性和民族的社会的文化思想意识等等。说到生命伦理(bio-ethics),我们就没有办法不谈到生和死,如果说生命是一个问题,那么死亡就是一份答案,二者之间的往来归逝成为人世沧桑之起始终结,死亡与爱情、战争共同构成文学的血脉和精髓。从上古的生命崇拜到中世纪的死亡神秘到现代的生死朴素;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困惑到“好了歌”好即是了,了才能好的告白;从海明威作品只有一个死亡主题到鲁迅小说结局的共同点往往就是关于死,文学表现了最丰富、最精细、最生动的死亡意识,它在向人类展开它艰涩困顿的同时又促使人类揭示它的奥秘、洞烛它的幽微,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及对生命价值的创造。中国是个宗教氛围并不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的亚宗教性质承担了人的终极关怀使命。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所以何必“悦生恶死”?(《庄子·知北游》)生,“时也”;死,“顺也”(《庄子·大宗师》)。在此类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她们价值观中的生命就是意义——每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无论大小,都因得之不易和必要战胜苦痛,自有其自足的存在意义。
一、生命体验的浑融:“造命”和“不胜幻灭之悲哀”
诚如拉伯雷所言的要寻找一个尚属疑问的伟大命题,世纪初的女作家们在经历了“五四”的震聩,“人的觉醒”的阵痛之际,勇敢地走出深闺后宅,冲破三纲五常,去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生和死。她们的精神影响了此后数代女作家。正如当代作家铁凝所说的:“文学……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自身以获得灵魂的提升”[1]。历来被视为只会创造生命的女人将一向抛远的目光收回,“自我”由边缘走向中心。女性不断摆脱“自然生命体”,趋向“超生命体”。对死亡的关照由自发到自觉、生存到信仰、感性到理性,精神理念的创化充满了艰辛困苦。
价值信仰取向
“五四”的喧哗散尽后,“知识女性”仍然孤寂如初,“艺术化”生活何以实现?生命化成问号,答案的模糊始料未及。“知识误我”、“读书自苦”,向何处行的迷惘远不如沉醉来得轻松。“从超越蒙昧糊涂始,到回归和难得蒙昧糊涂终,从反传统始,以皈依传统终,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转着一个又一个思维的怪圈,永远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循环”[2](P151)。将死视作人生悲凉的终结,这是像庐隐、石评梅、白薇、冯沅君等浪漫主义“新女性”发出的人生碰壁后的哀音。她们把死想得很美好,认为它可以解脱一切缠绕;将死视为完全的终点,由之返生则一切皆无意义。她们也不乏“勿宁死”的战斗精神,但只空有形而上追问的意念与实验,而无途径与能力;只知人之必死,如何生都是这个终点,而不知生命的价值在于竭尽所能取得最后的辉煌,来彰显死亡。
冰心是属于望死亡而“微笑”的另一类作家。她附着于客观人生,宁静思虑,用爱来承受、化解死的苦难,万全之爱无生死,万全之爱无别离。正如云格尔在面对宗教时的箴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南归》中她把母亲的死表现得朦胧温馨,让母亲在病榻上尽享天伦。她的本意是拒绝来世,如果来生与今生不同,为什么要等待来生?如果来生与今生相同,今生就已足够。冰心将爱当作枢纽贯通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个体与群体,成为泰戈尔所说的“艺术的宗教”、“艺术的生活”的升华。陈衡哲将“命”区分得很清楚:“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我幼时求学的经过》),公然反驳了历来对女子“妇如影响,焉不可赏”的限定。这“造命”的生命意识是对女性价值的高扬,也是女性生命主体对自身命运的强调。丁玲以她坚韧刚毅的生命感同身受数十年沧桑,悲欣交集。早期的莎菲、梦珂是因欲爱不能欲罢不甘想“悄悄的死去”,可时代的冲击对丁玲的影响是巨大的,“倾向”成为实际行动。“苇护”是开始,“母亲”是深化,“水”则以苦难大众的群像浮雕在天灾人祸中述尽生死之值。“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风雨中忆萧红》)。
宗教精神烛照
自然生命个体必将消亡,但若面对宗教,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超越会成为永恒。对于生存的意义、人生的苦难、死亡的忧虑、灵魂的归宿,文学表达的是经验情感,是陷入历史社会的困惑。宗教则肩负着思考和救赎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终究是因为我们还微弱,它是文学的起源和避难方舟。宗教对女作家的“精神烛照”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直接的,比如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走向基督教,或是寻找寄托和依赖,或是探讨“爱”的宗教照耀社会和个人的“慈悲的光”;其二是间接的,它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其作用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被激活。
基督教伴随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虽从16世纪开始,但在“五四”时期形成多元文化渗透,它不仅仅是上帝和《圣经》,更是西方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情感方式。基督教超越死亡有两种方式:灵魂不死、死而复活。冰心“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是耶酥的人化,用他的精神之光温暖别人,是兰气息玉精神的灵魂监守;庐隐的《余泪》写修女只身奔赴战场,以自我的受难牺牲拯救他人,兼具超世与入世,既立足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追寻,又表现出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思索。
佛教追求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在看似万物皆空的气氛中表达出对真理、对人性的苦苦思寻,有着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又不乏进取牺牲。佛教的死亡观是:人不仅有一“生”,而且有无数循环之“生”,“死”是轮回的“生”的中介,一心向佛则可从红尘的因缘和合悟到宇宙万物尽虚空的超脱。宗教更多的是作为审美心理机制潜存于作家心理深层,作用于认知和表述,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永恒的宗教情绪。比如禅宗文化,虽不是土生土长,但由于官方的大力倡导,对女作家来说,其“缘起”、“因果”观已成为“先验”的遗传。但是这种“乐天知命,故不忧”的生死观也会演变成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像《生死场》中“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十年如一日”,“糊里糊涂地生长,乱七八糟地死亡”,“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二、生存体悟的孑然:“兰气息玉精神”和“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中国式的伦理是建立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之上的源远流传,盛主于宫廷,制约于民间。儒式伦理在历经了孔儒的发轫、汉儒的推崇、宋儒的深化和成体系化之后,逐渐形成了其效忠当世、完善自我的传统。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强势伦理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束缚和羁绊,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它那以“仁”为中心的学说,以积极入世为指归的能动精神在现代社会的30年代,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对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策动和勃发。女人不需要有亡国之忧,衰国之恨,尽管她们试图反驳“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鹧鸪天》),怎奈这种声音在宏大话语中显得微乎其微,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到底是将女儿身披在了戎装之下。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P70),随着娜拉离家时摔门的巨响,第一批知识女性要走向社会,她们参与社会的态度还比较暧昧,有的甚至希望以改良或人的良知的自觉,来推翻旧道德的痼疾。
革命的生存
“五四”时代的“社会”的生存与那一代女性所倡导、要求的社会的生存是很难划上等号的,或者不如说后者仅为她们精神形而上的一种美丽设想,是在为离开家的女性的措手不及寻找一条路径。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文化对民族传统伦理的复归和“引用”,不仅仅是重提,更是超越。当然,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倒退。中国传统以群体本位为核心的儒式伦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使命感,使本就张力不足的“个性”在这个阶段不留痕迹,“存天理,灭人欲”使义务、责任、服从则由自觉到自律地控制着每个人。第二代女作家已经习惯了将自我隐匿,去塑造一些毫无性别意义的工人、农民,这也就回复到了“第二性”的历史确认中去。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仅有的女人参与政治的书写中,女性的身体符号或多或少地指向了殉节、联姻或女扮男装。现代社会对历史传承的反驳之一便是女性直接以“女”字的身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与上一个10年相比,此期的女性在“离家”之后多有了明确的前路指向。如丁玲的《苇护》、《某夜》、《奔》,草明的《解放区散记》,白朗的《我们十四个》等,都是对革命和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武将军”的礼赞。
民族正义是对传统的继承,《左传》中便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中国文学感时伤怀、忧国忧民的传统得到了继承。这一段书写中,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对女性参与革命的书写往往是理论先行,先在的既定的理念要大于性格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女性参政的颂扬是以女性异化——外在赋予的质变为代价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丁玲的个人表述的激情转变成了革命洪流的汹涌,《苇护》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交接点。革命与爱情,江山与美人,政治与个人的冲突使文本所凸现的社会意义极大地超过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冯铿在《红的日记》所塑造的马英“眼睛里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在她眼中,个人的生存已经坚定地融入进了民族的生存之中,女性特有的生存模式已趋向中性,“铁娘子”的定位锁住了三四十年代解放区妇女的角色。
本色的生存
庄子曾有言:“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中华民族若干年的沉潜笃实,使所谓的“陋”由不知变成了耻于示人。因生活经验的贫乏和参与条件的限制,“五四”一代对生存百态、人心向背的揭示未免显得流于表面,隔靴搔痒。随着革命浪潮的席卷,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丁玲则大胆直率地指出了:“我自己是个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她们不会是超时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4],清醒而极具自审意识。 她的“霞村”妇女跟萧红呼兰城小团圆媳妇婆婆的街坊邻里,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封建残渣最顽固的维护者。自主自强的都市女性苏青承认自己“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坦露了传统伦理道德在内心最深处的挣扎。萧红、张爱玲、苏青、梅娘、杨绛等对人性的自私、虚伪、冷漠,都给予了讽刺和挖苦。
罗淑的《生人妻》和冯铿的《贩卖婴儿的妇人》,直接从劳动妇女最底层的生存揭示了她们无路可走的现状,女性的屈辱和原始的反抗交织在一起。30年代四川沱江流域败落凋敝的农民生活,尸首都见不着的井工和吃死牛肉被开除的井工的儿子,牛比人值钱的潜台词是80年代“桑树坪”的前言。萧红《生死场》是作为“奴隶丛书”出版的,她在写民族自救的同时糅进了大量人性/女性生存方面的经验描写,以另一种姿态对抗了红色/革命叙事,性别的生存常常会压倒民族的生存。女性的苦难和民族的苦难交织在一起,以第三人称“讲述”的视角切入,却是以切身的体验、关怀打碎了男性作家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文化想象与异性关怀。萧红写出了女性对自身生存的关注与关怀,身体的痛苦扩大为生存的痛楚是经验式的而非编码式的。她指出了农业文明统治下女性的真实生存,受制、受压、没有自我、没有未来。在她们身上找不出翠翠的美,也找不出祥林嫂的力,与《八月的乡村》中英雄的慨然赴难相比,她们更多的是愁肠百结、蓬头垢面,反而“知不可而安之若命”。《马伯乐》的笔调已经完全殊异于“苦菜花”式的“受罪”,而是接近于“阿Q”的全面翻版,对洋人的尊和大与对国人的轻和贱纠缠在一起,并时时拌着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的口头禅,可怜又可悲。
张爱玲更着力于都市女性在生存中暴露的人性真实,她笔下的女人津津乐道于服饰、化妆品、舞会等奢华的主题,生存是带着霉味的香气,人生的悲剧不仅是外部环境的重压,更是人性中非理性的弱点与渺小所致。男女情爱的青涩与美好,在她那里成了生存必须的勾心斗角。不论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曹七巧还是白流苏,传统女性的畏父兄、畏人言的恭谦,“和羞走,倚门回首”的含蓄已游走殆尽。“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谈苏青》)。苏青,无论从文本还是从创作主体,都逃离了“三从四德”的限定,怨妇、弃妇的称谓被她改写为坦然面对婚姻失败的自主女性,独立而清醒地写出了《结婚十年》。与男性相比,她们似乎更适应城市的绚烂,而少了那种对乡村、乡土的眷恋,没有人自诩为“乡下人”,也没人去刻意寻找城乡间的反差,都市也不是30年代“新感觉派”们“建在地狱上的天堂”。城市为女性提供了除土地、牲畜外的更广阔的空间。因其历史时间的短暂与生存空间的宽阔,更加有利于女性拓展自身和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同时期的罗洪的《践踏的喜悦》以女性作者少有的冷峻,嘲讽了事态的炎凉,将践踏和喜悦合而为一,女性心底的自私自贱可憎可鄙。她说:“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鬼影·序》)。
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汲取了老庄道家思想的有利资源,或者从反面批判了都会生活的异化与人性的扭曲;或者从正面建构了一种优雅从容,闲静自适的日常生活图式;或者从乡间田野寻找到了原始雄强的人性理想模型。埃莱娜·西苏说:“我不是那种喜欢黑暗的人,我只是身处黑暗中,通过生存于黑暗、往返于黑暗、把黑暗付诸于文字,我眼前的黑暗似乎澄明起来……”(《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海明威说死亡自有一种美,女人书写“死亡”之所以具有审美功能,是因其展示了较生命更为可贵的真与善。一方面,通过艺术的媒介可化死亡之丑为艺术之美,比如将生命化给自然。另一方面,通过艺术的筛滤和抽象,可以进一步强化死亡先已具有的审美功能。林徽因是美的象征,视生命为至美,视死亡为至善。在《深夜里听到乐声》中她写道:“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对个体生命而言,永恒是谎言,但若推到宇宙的大视角,这生死的变换又不得不显得伟大了。
生存并受制其中的女性写作,绝非仅是对以男权统治为中心的伦理体系的揭露和呼喊,而是她们自身对自我的认知与定位,对社会的参与和改造,以女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生存本真与生命感悟来反抗“被书写”的命运。“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 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5](P797)。女作家们已不再满足在既定的权力密网中写出“越轨的笔致”, 而是大力张扬她们精神的独立和创造的意识。中国现代女作家在经历了人与非人、集体的人与个体的人控诉的漫长朝圣后,终于走向男人与女人的目的地,在“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对生命压抑、伦理强加、物化语境的合力冲破,至少导致了在男性霸权文化体系内“女性主体”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