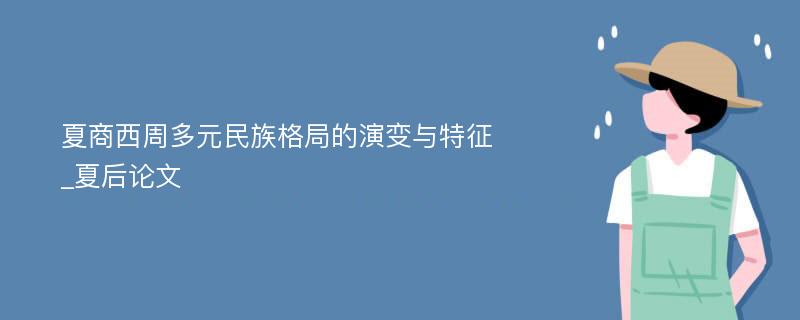
夏、商、西周一体多元民族格局的演进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格局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5)03—0129—10 自1901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忽忽百年,国族建构仍在进行之中。①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随即撰文《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予以全面回应,由此造成国族建设路径的两端,即顾文着重之一体与费文强调之多元。②此后,围绕中华民族的建构路径,产生一系列的讨论,但影响最大者仍是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对20世纪30年代末那场争论的再思考,是“民族识别”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综合。它的提出,构成我们今天继续探讨国族建构的基础。 费孝通认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是汉族出现,因此该格局的酝酿不能早于春秋战国之时。③这种观点与史学界关于封建社会诞生、统一国家形成以及民族关系主要类型出现所指向的时间节点是一致的。④然而,中华民族的演进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⑤这个“独特的社会条件”,不是单由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规定的;它之所以被称为“独特的民族”,因为它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副产品。中华民族的独特逻辑在于政治早熟,即使在社会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之时,政治意志仍要求克服多元而趋于一体。这里的多元和一体,并不固指野蛮与文明,贫弱与富强,边疆与中原,游牧与农耕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和一体的指向不断变化,唯其背后的机理保持不变:即一与多的新陈代谢,以及基于政治早熟的一体对多元的不断克服。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梳理先秦一体多元格局仍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恰是在夏、商、西周这样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低下的时期,我们才能看清楚早熟的政治如何推动一体多元格局演进并赋予其特点。⑥ 一、在多元中震荡:夷夏东西之争 炎黄夷联盟原是为了对付黎苗系的进攻,随着黎苗的衰退,北方部族的联盟需求逐渐消失,为维系和扩大联盟,部族联盟首领的人选从黄帝嫡系后裔扩展到外族。帝禹时,既是黎苗最终屈服,也是部族联盟首领人选向夷族扩展的时代。夷族最有名望的政治家是皋陶,其次是益。《史记·五帝本纪》说:“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益主虞,山泽辟。”⑦皋陶和益在舜时已是重要政治人物,和禹共同辅佐帝舜。皋陶的实力不如禹,但禹之后,皋陶便是联盟首领的第一人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可惜皋陶早死。禹退而求其次,推举益为继承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史记·夏本纪》)⑧,于是禅让制就在夏启手中破坏了。 至此,炎黄夷系联盟正式瓦解,面向黎苗的南北之争转为夷夏东西之争。这个斗争贯穿夏、商两代,实际上是炎黄夷系一体化机制瓦解后,诸族争夺霸权的内部斗争。随着禅让制的衰退,中原亟须新的机制进行整合。夏后氏就是在与东夷的反复较量中诞生、壮大和消灭的。 夏启践位引发东夷不满,他被迫放弃离东夷较近的阳翟,西迁至大夏,建都安邑。首先起来反对夏启的是有扈氏。有扈氏与夏启同宗,因不满夏启破坏禅让制度,起兵攻夏,兵败族灭。《史记·夏本纪》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⑨ 随后起而与夏争霸的是有穷氏。有穷氏是东夷的一支,其首领即后羿。后羿之时,夏后太康无道,发生武观之乱,后羿乘机西向,一举攻陷夏都。《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⑩ 后羿是上古武功卓著的英雄,但用人失察,他所信任的寒浞是一个“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的阴谋家。羿的政权被寒浞篡夺,羿自身也落得“家众杀而烹之”的下场(《左传·襄公四年》)。(11)寒浞出身东夷的伯明氏,他对夏后嗣进行追杀,夏后相因此被杀。相的遗腹子少康任用夏臣靡,联络夏后旧族,“收斟寻两国余烬,杀寒浞,灭浇于过”(《史记·夏本纪》),(12)从而取得少康中兴的局面。然而夏后氏和有穷氏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少康的儿子杼,“后杼灭豷于戈”(《史记·夏本纪》),(13)夏后氏才最终战胜有穷氏,重新树立霸主的地位。 帝杼是中兴夏后氏的重要人物。据说他改良了甲兵,《世本·帝系》曰:“杼作矛。”(14)他又向东扩展,使很多东夷部族臣服于夏,《国语·鲁语》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15)从帝杼开始,夏的统治趋于稳固。帝泄时东夷部族受夏爵命。由夏启所夺取的帝位,至此才为东夷承认。帝胤甲之后,夏后复衰,东夷的一支商在东方强盛起来,夏不敢向东方竞争,终于为商汤所灭。可见,自启至桀,夏后氏一直在东西之争的背景中生存,“夏都经常迁移,或东进或西退,说明姒姓势力与东方夷族势力的消长。”(16) 夏代是中国古代有史可考的第一个朝代,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王朝。如上所述,夏后氏在中原地区的优势是不稳定的。夏的建国,与其说是区域性统一,毋宁说是从基于禅让制的部族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夏后氏不仅要与东夷争霸,还得应对同宗其他部族的挑战。夏代历史展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即基于禅让制的旧式一体多元格局瓦解后,在多元占优的境况下缓慢生长出新的一体的雏形。新的一体多元格局的萌芽、发展和成熟,是贯穿夏、商、西周的重要线索,夏代则是孕育这一新格局的最初阶段。总体而言,在该阶段,随着旧式一体多元格局的瓦解,多元因素得以释放,在大体相当的多元力量中重塑一体的雏形,必然掺杂着偶然的成败和激烈的碰撞,无序和反复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最终脱颖而出的夏后氏,以不稳定的优势奠定新的一体的雏形,也因此被赋予正统王朝的名义。夏代整合诸族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在下一阶段,我们将看到一体化的因素大大增长了,虽然仍有其弱点,那就是殷商重建一体的尝试。 二、重建一体的尝试:殷商的进取和弱点 我们通常认为,夏代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以周秦以后的情况反推,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夏代在政教文化的整齐性上与后世相类。实际上,夏后氏仅仅是当时中原诸部族中较强的一支,它的统治区域盈缩不定,它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的贤否。整个夏代历史,就是在与东夷的争霸斗争中展开的。将夏后氏奉为中国历史的正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讲的。 商比夏强大,在国祚、幅员和武功等方面都有较大进步。《孟子·公孙丑》曰:“自汤至于武丁,圣贤之君六七作。”(17)这既是说商代多出贤君,也说明有效集权是商代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通典·礼五》云:“武丁时编发来朝者六国,自是服章多用翟羽。”(18)商代幅员的扩大,主要是靠武力征服得来的;能保持武力强盛,既是殷商政制的优点,也在王朝后期成为它致命的弱点。 商强于夏的原因有三:一是生产力发展。范文澜先生认为,“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随着商业的进展,交易的货物必须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用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夏朝兴起的形势。”(19)在古典政治学的言辞里,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以“修德”的面目出现。《史记·夏本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20)表面上看,战争成败以“修德”与否为标准;实际上,“修德”的实质是“裕民”,战争成败的根本是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管子·轻重》也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21)由此看来,汤武战胜夏桀的关键是经济实力的胜出。 二是殷商的尚武精神。有殷一代,武力强盛,与其保持半游牧生活息息相关。汤武以其尚武,“号曰武王”,(22)武丁“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史记·殷本纪》),(23)这种尚武精神是贯穿商代始终的。至其末期,这种粗朴的尚武精神才逐渐堕落为酗酒乱德。《淮南子·泰族训》说:“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矫之具,简氏族,习御射,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24) 即使殷亡之后,其遗民的好勇斗狠也使周初统治者大为头疼。武王封纣子武庚而设三监,周公封微子启于宋以分殷民,建国齐鲁以莅殷旧地,封康叔于卫以镇成周,都是防备殷遗民武装反抗的措施。 三是殷商的继承制度。商以兄终弟及为主,父终子继为辅,从而保证长君继位。这既是由于征伐频仍,也是立君以贤的现实需求。对此,王国维先生曾评论道:“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多非兄之子,而为弟之子……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25)有殷一代,多出贤君。《史记·殷本纪》曰:“雍己立,殷道衰。大戊立,殷复兴。河覃甲时,殷复衰。祖乙立,殷复兴。帝阳甲之时,殷衰。盘庚之时,殷道复兴。小辛立,殷复衰。武丁立,殷道复兴。帝甲淫乱,殷复衰。帝乙立。殷益衰。”(26) 但殷商并非没有弱点。生产力进步、尚武好勇和贤长继位,在一定意义上是殷商王朝维系不坠的保证,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成为其覆亡的诱因。夏、商之时,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奴隶的使用。殷商一代武功彪炳,战俘奴隶大增,生产力较之夏代进步很大。然而过分依赖奴隶劳动,不仅逐渐造成效率低下,更引起奴隶反抗的严重问题。后起的周受奴隶制束缚较少,它将部分人身和财产权利授予土地奴隶,使之转化为效率较高、稳定性更强的农奴,从而为夺取天下奠定了物质基础。对此,范文澜先生有很好的总结,“到了商朝,出现了助法,封建制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不过比起奴隶制度来,它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还不能改变奴隶社会的性质。至于商朝末年才兴起的周国,原是一个受戎狄压迫、奴隶制度很薄弱的小国。因为奴隶制度很薄弱,社会的衰朽力量也较薄弱,而自由民的反抗力量却相对地强壮起来,这就使得周国统治者,比商朝更不能完全剥夺自由民的身份及其生产资料,而只能实行较轻一些的剥夺,这也就使得在商朝已经形成但不占主要地位的助法,在周国取得了主要地位,成了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27) 在漫长的古代史里,富与强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正比例关系。烂熟的文明导致腐败,富裕、奢侈和糜烂如影随形。如何在文与质之间保持平衡,是历代政治人物关心的核心问题。殷商尚武已如前述,但尚武也可能走向其反面。尚武的反面有二:一是无序,二是黩武。无序是尚武精神的矮小化,它往往发生在屡战屡胜而民力耗竭时,《尚书·微子》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28)这正是过度消耗导致社会混乱的明证。黩武则在“资辩捷疾,材力过人”(《史记·殷本纪》)(29)的帝辛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左传·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殒其身。”(30)武丁之后,唯帝辛纣有文武才,凭着他的努力,殷商不断进攻东夷,部分恢复了武丁时代的幅员。但纣征伐不休,国势陵夷,且专顾东向,对周在西面的蚕食视而不见,终于在主力东征时被乘虚捣入,纣王“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31)帝辛纣不是简单的无能之辈,而是想在太短时间里做成太多事,从而导致最终的失败。诚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纣之百克而卒无后。”(32) 西周用父死子继之法,成为后世继承的定制。西周以前,继承并无一定之规。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实际上是在禅让制和世袭制之间采取折中。兄终弟及制在建国初期有保持政策连续性并防止国祚潜移的功效,但长此以往则容易造成继承纠纷,这也是殷商屡盛屡衰的一个原因。《史记·殷本纪》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3) 大同时代一体多元格局的维系,在内部靠禅让制团结诸族,在外部凭黎苗系给予压力,它的弱点是缺乏决定性的支配力量。新格局区别于旧格局的关键是有一个支配性力量长期存在。在夏代,我们看到这种力量的萌芽;在商代,这股力量是大大加强了。殷商对外开拓的基础是内部的常态军事化。这从它的奴隶政策、尚武精神和继承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殷商在生产阶层和战士阶层间有明确的区分,前者依附于后者,后者则发展出一种独立和尚武的精神。这种尚武精神在上层表现为贤长继位,这既是战争频仍的表现,也是军事指挥的要求。然而,殷商在常态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全不注意休养生息,生产者拖垮了,战士不足用了,还要用奴隶充当战士,终于被较弱的姬姓消灭。通过殷商的教训,西周统治者看出,重建一体多元格局既要求支配性力量的长期存在,也需要对无法直接控制的诸族加以羁縻、规范和建构。西周在两者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这源于它对封建制的创造性运用。 三、从羁縻到建构:封建制的起源和演变 黎苗系衰退以后,禅让制迅速消亡,北方部族联盟瓦解,中原事实上长期处于诸族争霸的状况。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原远非政教划一,而是由政教风俗殊异的诸族并存着的。尽管三代以降,由于战争和社会经济交往,各族间的融合日益加深,但仍不能改变众多族群竞争并立的事实。夏、商是中原诸族中的强支,长期处于霸主地位。夏、商两代能够影响诸族,但不能取消诸族,当时的技术水平远没有达到使中原地区政教划一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夏、商都无法仅靠一国之力量整合诸族,而需要区分敌友,树立屏藩,形成以一大族为核心、众多小族为外围的政治军事联盟。这种继禅让制之后有效整合中原诸族的变法,就是封建制度。 关于封建制度,历代褒贬不一,争论不休。赞成者视之为周代享祚七百年的原因,如班固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对封建制的评价:“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34)反对者则斥之为割据混战的祸首,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李斯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35)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范畴内讲,上述争议是儒法之争的命题之一。然而儒法之争发端于周秦政制比较,对于封建制度在夏、商、西周的实际意义,多有扭曲。若按历史主义的观点,封建制度源于诸族竞争并立,其旨在于有效整合诸族,随着诸族融合,封建制度不断发展,终成为郡县制之前中央集权的特定形态。 既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封建制度,须首先承认封建制度不全是人为理性的设计。后世文献对封建制度确有一些井然有序的描述,但实际上,封建制度是根据时势逐步发展起来的。诚如缪凤林先生所言,“封建之制,儒家以为起于王者之公天下,然邃古之诸侯,皆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出于帝王之封建,而起于事之不容己。”(36)封建制度起源于夏,发展于商,变革并鼎盛于西周,三代封建制度的内涵和意义大不相同。夏、商封建主要是对异族的羁縻。西周初年兼并无数,封建制度遂发生大变革,分封同宗以树屏藩,授土勋旧以拓疆域,封建制度成为周王室推行中央集权的重要方法。至西周末,封建集权成为当时技术条件下全国统一的特定形态。以下我们依次来看夏、商、西周的封建制度。 夏代已有分封,但数量较少,《史记·夏本纪》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37)这些封地分散各地,阻隔遥远,没有形成合力。《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38)将少康后裔封在会稽,与夏的统治中心相距过远,除为祭祀禹帝外,很难发挥别的政治军事作用。 商代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则有分封权,《史记·殷本纪》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39)商代与夏代相比,分封数量并无多大变化,但封建关系的内容已开始明晰化。尽管王室与各封建国间的权利义务不尽相同,但一般性描述仍是可能的。范文澜先生说,“他们都服从商王命令,或奉命出征,如呼雀伐猷;或互通聘问,如往雀,越来归;或助祭宗庙,如井方用彘来祭汤;或做王官,如鬼侯鄂侯周侯为纣辅佐。这种制度为周所承袭,并进一步确定诸侯对王室的关系,即大小封建领主对最高领主纣王的隶属关系。”(40)这种一般性描述是封建关系趋于稳定和集权的明证。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变革时期,也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王国维先生曾言,“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41)西周的封建制度,可从政治、宗法和社会经济三方面讲。 首先讲军政方面,西周封建以同宗而主,功勋为辅,其范围远近、结构严谨,远非夏商两代可比。《荀子·儒效》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42)这样的形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帝辛纣以及殷遗民的反复较量中形成的。与商相比,周是一个小国,虽然乘纣的主力军东征时攻陷殷都,但并未触动殷商实力的根本。因此,武王对殷遗民采取怀柔措施。为分化殷商统治集团,他拉拢纣王的反对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荣之闾”;为争取人心,他一反纣王的高压政策,“释百姓之囚”,“括鹿台之财,发讵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史记·周本纪》)。(43)对殷人的统治,武王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他没有掠夺殷人充当奴隶,而是“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遗民”。为监视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在殷商旧地周边设置军事据点,“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史记·周本纪》)。(44)这样,殷遗民就在自治名义下被牢牢监控起来。 然而殷遗民终究起来反抗了,武庚之乱给周室再次东向的机会。尽管战争十分艰苦,但战胜殷遗民及其率领的东夷部族后,周获得了彻底铲除殷商东方势力并重组中原的机会。《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45)《逸周书·世俘解》也说:“武王以降,灭国者九十九,归者六百五十二。”(46)封建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变化的。武庚失败后,殷商势力被摧毁,其旧地被彻底分解,周公封微子于宋以分殷民,封康叔于卫以镇成周,迁齐、鲁至奄和薄姑以莅殷旧地,剪徐夷、淮夷以平东土。至此,殷遗民再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史记·鲁周公世家》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47) 在此基础上,成王“封叔虞于唐”(《史记·晋世家》),(48)建立晋国作为北方的屏藩;又“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49)稳定南方汉江流域。南北的封建国,与其说是意在对外拓展,毋宁是守卫边疆,为融合殷遗民和东夷诸族提供时间和空间。 应当说,经过周初的斗争,周的统治不仅稳定下来,而且通过封建制度大大拓展了势力范围。周代封建之所以谓大变革,不仅在于多封同宗,且在于封建关系的井然有序。由于异族融合,同质化因素增长,周代封建的羁縻性质大为弱化,成为团结宗族和勋旧政治力量的有效形式。封建不再是对外族和异己力量的承认和联合,而是对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规范。如何使诸侯层层隶属、最终统摄于周天子,并建构起明确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这是封建制度的宗法性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讲宗法方面,西周封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国、天下的合一。夏、商之世,诸族并立,封建关系无法深入异族。家、国、天下,越向上一层次,政治联络的纽带就越松弛。降至周初,诸族或融合或消灭,异族林立的状况大为改变。姬姓诸侯在此基础上大为扩张,遂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50)的形势。宗法就是将宗族的规则延伸为治国与治天下的方法。诚如周谷城先生所说,“把君统变为宗统,把政治组织套在家族组织之上”,(51)这符合当时诸侯多出自姬姓的事实。 关于宗法组织的一般形式,《礼记·丧服小记》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祢也。”(52)《礼记·大传》又说:“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53) 这种宗法的组织方式,推广为治国与治天下的办法,就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政治军事网络。这张网络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财产分配,二是权力隶属,两者都是比照宗法关系自上而下展开的。对于封建制的宗法性,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滕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份,不同于农奴身份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性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54) 复次讲社会经济方面,封建制度是商周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封建制度不仅涉及军政、宗法,而且指向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关系。通常我们把封建解释为封土建国,从军政和宗法层面考虑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推进,“封建”一词越来越指向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变革,即将物化的奴隶劳动转变为生产积极性更高的农奴劳动。范文澜先生指出:“周国原是一个受戎狄压迫、奴隶制度很薄弱的小国。因为奴隶制度很薄弱,社会的衰朽力量也较薄弱,而自由民的反抗力量却相对地强壮起来,这就使得周国统治者,比商朝更不能完全剥夺自由民的身份及其生产资料,而只能实行较轻一些的剥夺,这也就使得在商朝已经形成但不占主要地位的助法,在周国取得了主要地位,成了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55) 这种农奴的劳动,虽然受封建关系束缚,但比之奴隶的生活实有较大改善。《考工记·匠人》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56)此外,封建的土地制度还有寓兵于农的效果,《周官·大司马》曰:“会万民之卒伍,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位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57) 封建的土地制度将奴隶转变为农奴劳动。尽管有附加于土地的封建义务和公田管理的繁难,农奴毕竟开始享有土地的部分权利。这在太平日久、工商业发展、人口增殖、私田膨胀的情况出现前,是很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和争取人心的。应当说,封建土地制度是西周初期最重要的“裕民”政策。土地意义上封建关系的演变,是军政和宗法意义上的封建关系变化的前提。封建土地制度为西周的文治武功提供了根本保障。 四、一体多元的新格局:西重东轻与封建集权 三代之中,以西周疆域最大最巩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熟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不仅整合了夏、商传统的中原地区,而且在抵御和征服异族过程中,大大拓展了周的疆域。《左传·昭公九年》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8) 西周的疆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两百余年历史中逐渐取得的。周起源于西方,曾与戎狄长期斗争。太王古公亶父时,戎狄势盛,古公无力抵御,“与私属去幽,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王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国势稍振。文王“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记·周本纪》)。(59)这样惨淡经营三代之后,周始称霸于西方。武王伐纣,周的势力只是触及东方。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周的势力始能植根东方。《史记·周本纪》曰:“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60) 但这只是就殷商东夷旧地而言,周在江汉流域很快遭到荆楚的抵抗。“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61)就是周室向汉水流域拓展的一次重挫。实际上,终西周之世,江汉流域和长江下游并不在周王室的有效控制范围内。穆王内文外武,周室复兴。经共王、懿王而传至厉王,西戎对周的威胁加剧了。面对外部压力,厉王本想有所作为的。他想整顿财政,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理财家荣夷公,但征敛过度;他要统一意志,压制反对派,“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却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外患未除,内乱先发动起来,贵族率领城市平民起来反抗,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称共和”(《史记·周本纪》)。(62) 继厉王之后的宣王是西周最后一位贤君。和厉王一样,宣王面临异族进逼的困境,但他对内取消专利,对外用兵有方,从而成就西周最后一次中兴。宣王分别向东、北、西三面用兵,虽然都获得了胜利,效果却不全相同。总体而言,对东面的用兵最为成功,其次为北面,再次为西面。先看东面。宣王命召穆公伐淮夷,大辟疆土,《诗经·江汉》曰:“王命召虎,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63)宣王又自率师伐徐戎,吞并成功,《诗经·常武》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64)宣王之后,殷商东夷故地再没有大的战事,民族融合迅速展开,平王东迁后,该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中心。次看北面。宣王命韩侯北伐,虽然战胜,但不能消灭当地土著,《诗经·韩弈》言:“王锡韩侯,其追其旄,奄受北国,因以其伯”,(65)就是将之纳入周天子封建秩序的意思。再次看西面。西戎是周王室最大的对手,双方交手各有胜负,宣王与南仲共伐严允,是西周最后一次对西戎用兵成功。《诗经·出车》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严允于夷。”(66)显然,即使是这一次大胜利,也只是击退西戎,俘虏甚众罢了。按当时的形势,尚不能将西戎纳入封建秩序,遑论兼并和民族融合了。 宣王用兵不已,虽有成功,国力耗损。他拒绝虢文公的建议,忽视农业生产,“不修籍于千亩”(《史记·周本纪》),(67)在南方败给姜戎。他又不听仲山甫的谏言,“料民于太原”(《史记·周本纪》),(68)进行超常规征兵,大大消耗了西周社会的元气。到宣王末年,西戎的势力已逼近镐京。幽王继位后,抵御西戎的形势更加严峻。此时又发生了“三川竭,岐山崩”(《史记·周本纪》)(69)的自然灾害,西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动摇。这时最需要政治上的稳健和团结,幽王却草率易储,自乱阵脚,终于成为西周灭亡的导火线。《史记·周本纪》载:“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俘褒姒,尽取周赂而去”。(70) 纵观西周分封布局和发展态势,其封建的意图和效果在不同区域很不相同。首先看东面。西周分封的重心是殷商东夷故地,其初衷是包围和肢解殷商残余势力,受封者多为宗室和勋旧,握有军政重权,对王室也承担较充分和明确的封建义务。其次看南面。西周在江汉流域的封建国可分两类,一类承担着较明确的封建义务,如周南、召南等;一类表现出更多羁縻性质,如荆楚。前者与王室关系密切,但实力不足;后者尚武多力,但与周王室之间缺乏持久规范的封建关系。再次看北面。西周在北方的封建国负有两种任务,一是控制和同化东夷和殷遗民,二是抵御北狄。前一种任务完成得较好,奠定了春秋伯政的基础;后一种任务执行不力,燕、晋、中山等国不仅屡遭狄人侵袭,还有融入狄人的危险。最后看西面。西周的实力根植于西方,西周最大的威胁也来自西戎,抵御西戎无须也不能以封建方式组织力量;因此,西方没有重要的封建国,王畿成为抵御西面异族入侵的首要堡垒。作为一体化的核心机制,封建制在东面表现得最为成熟,其次为南面,再次为北面,而使该机制运行正常的关键是西面王室力量的维系不坠。封建制的分布和发展态势,反映了西周族际政治的基本关系,也决定了新一体多元格局的具体样态。 新一体多元格局历经夏、商两代,至西周完全成型。新格局有两个特点:一是西重东轻;二是封建集权。先看第一个特点。通观西周一代,其用力最多的是殷商东夷旧地。成王之后,东夷虽时有叛乱,大势上却是与周融合。北方建燕、晋等国,勉强捍御北方异族,为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西周在江汉流域不甚成功,虽有周南、召南等老牌封建国,但优势大抵在荆楚一边。关左陇右是周室故地,周正是在与西戎北狄的长期斗争中壮大起来的。灭商之后,屏藩多树于东方,但周室实力的根本仍植于西方。镐京是西周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第一军事堡垒。夏、商以降至于西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格局大体成型,即西北抵御,东南浸润。真正能够威胁姬姓天下的力量来自西北。周室以镐京为都,实际上是将全国精锐集中于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对东南则文武兼用,意在融合。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西周各族间战争,主要是华夏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71)西周抵御西北异族的成功,为东方诸族融合提供了可能,齐、晋、宋、楚等春秋时代的大国,正是在周室的卵翼下,逐渐融合东方诸族而形成的。实际上,春秋伯政之出现,既是对周室实力衰退的填补,也受惠于周室对西北异族的长期抵御。 次看第二个特点。封建和集权,初看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实际上,若存在一个巩固的支配性力量,封建和集权是可能互为助益的。在周祚未衰前,封建制极大拓展了王室的统治范围,使周的疆域远远超出它能直接控制的领域。由于王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诸侯大体形成一个互助而非互戕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诸侯受到庇护而专力经营一方,王室借封建法权从地方提取资源。当封建和集权良性互动时,新的一体多元格局曾发挥出很大威力,这是西周的疆域和稳固程度远甚夏、商的根本原因。 然而,新的一体多元格局并非没有弱点,它的问题仍在一体方面。无论是西重东轻的格局,还是封建和集权的良性互动,都取决于一个共同前提,即一体的支配性力量长盛不衰。然而,政治和人一样,少年时一往无前,壮年时审慎进取,老年时腐化昏聩。当周王室走向它的老年,这个扩大的一体多元格局必将反噬其曾经的领导核心,并寻求能承担一体化任务的新力量。因此,春秋至于秦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重建一体的支配性力量,如何使支配性力量超越或部分超越人性的弱点,走出兴衰治乱的循环。秦汉以下专注于一体方面的维系,引发周秦政制的深刻裂变,这既是出于对三代一体多元格局的反省,也是因为秦汉以下一体、多元所指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那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 ①梁启超.中国史叙论[N].清议报,1901,(91). ②关于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产生的学术争论,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辩论的考察[J].民族研究,2007,(3).又见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又见郝时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N],中国民族报,2012—04—13. 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④按照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封建社会诞生、统一国家形成和民族关系主要类型出现的时间节点都在秦汉之际。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诞生及其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意义,参见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关键何在[J].历史研究,1957,(8).王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J].历史研究,1980,(5);关于统一国家形成的时间节点,参见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J].历史研究,1959,(4).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J].历史研究,1980,(1).关于民族关系主要类型出现的时间节点,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1).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史上的几个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6). ⑤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J].历史研究,1954,(3). ⑥笔者将“多元一体”改为“一体多元”,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费孝通先生认为多元和一体是中华民族分别在两个层面上的表现,笔者以为多元和一体是在一个层面上的;第二,费孝通先生认为多元和一体的结合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健全,笔者以为这种竞合是基于政治早熟的中华民族独特发展逻辑的。 ⑦[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32. ⑧[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1~62.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2. ⑩[西晋]杜预.左传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7. (11)[西晋]杜预.左传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8. (1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4. (1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5. (14)[东汉]宋衷.世本八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8:89. (1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0. (1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 (17)[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56. (18)[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35. (1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8. (20)[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5. (2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18. (2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0. (2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6. (2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673. (25)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5:46. (26)[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6. (2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 (28)曾运乾.尚书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4. (2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6. (30)[西晋]杜预.左传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37. (3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9. (32)[西晋]杜预.左传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86. (3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74. (34)[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81. (35)[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70. (36)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9. (37)[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66. (3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21. (3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80. (4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 (4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5:48. (4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78. (4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92. (44)[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92. (45)[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155. (4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彚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75. (47)[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71. (4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51. (4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89. (50)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335. (51)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3. (52)[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52. (53)[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83. (5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6. (5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 (5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8. (57)[清]乾隆.钦定周官义疏[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5:359. (58)[西晋]杜预.左传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20. (5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83~84. (60)[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97~98. (6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98. (6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2~103. (63)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83. (64)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87. (65)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81. (66)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246. (67)[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4. (6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5. (6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5. (70)[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7. (7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