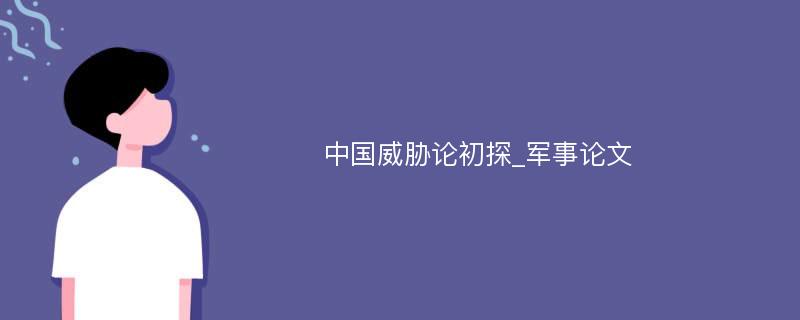
“中国威胁论”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威胁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本文对“中国威胁论”的各种观点及其形成原因与实质作了深入剖析和有力驳斥,并提出了相应的外交对策,对我国外交方针、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 形成原因 实质 对策
“威胁”一词就其字面含义,即是逼迫或恐吓。《史记》中云:“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1〕“中国威胁论”是就中国对他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影响状态的一种议论,即所谓中国对他国“构成威胁”的一种说法。自该论提出以来,“畏惧中国”已逐渐成为冷战后西方世界热门话题之一。虽经国内外学者再三著文予以反驳,但时至今日,它仍然颇为流行。本文试图对“中国威胁论”的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动机,及其负面影响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以求消除该议论的消极影响。
一
关于“中国威胁”一说从时间上看,最早由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所提出。1990年8 月日本《诸君》月刊刊登了村井的《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一文。该文从国力角度推论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一个“潜在威胁”。〔2〕随后,1992年9月17日美国学者罗芒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撰文《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面对中国经济上升之势而惊呼:“自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在预言,一旦中国龙觉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该文称:“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显示锋芒的道路,而这的确在亚洲和全世界引起反响。它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影响是巨大的。”〔3〕1992年底至1993年冬,系统的“是中威胁论”逐渐形成, 其中较具典型意义的为1993年冬美国《华盛顿季刊》和《外交季刊》的两篇文章《东亚新安全议程》和《中国的崛起》。它们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威胁”的理论。
综观西方学者的各种论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传统威胁论,即利用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其陆上和隔海相望的邻国达20多个)及由此遗留的历史积怨和分岐,而推导出所谓中国对他国(尤其是亚洲国家)构成“威胁”的一种理论。
其二,现实威胁论。该论包括经济威胁、军事威胁和污染威胁等论点。
(1)、经济威胁说。第一个把中国认定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2年11月28日该刊在其《中国特辑》上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其公布的数字超出中国官方数字 2倍。1993 年4月,美国兰德公司率先运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 Parity)这一在经济学界颇存争议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它又将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确定为世界第三位。〔4〕该评估结果立即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肯。同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在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美国占22%、日本占7.6%、中国6%、德国占4.3%。〔5〕。该刊评估结果引起美国政府决策部门的密切注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不仅援引了以上数据,而且将其推而广之,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的实际数目,事实上比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超出7倍还多,〔6〕这就意味着1元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与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持平。前《美国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尼古拉斯·克里斯朵夫在《中国的崛起》一文中称:“93年的世界银行用了两种‘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结果分别是:人均1680美元和2040美元”。依此计算,12亿人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究竟有多少亿美元?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这类按汇率法计算的方法是否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就其估算的结果而言,已十分明显地背离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超出了纯经济统计学的范围。西方世界有意夸大中国经济实力的目的只不过暗喻中国的军事威胁。
(2)、军事威胁说。西方一些人士依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而推论,中国必然有能力增加军费、扩充军备、购置先进武器及其生产技术,进而从事军事扩张,以填补苏东解体和美国军事力量收缩后在亚太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克里斯朵夫指出:“在过去的5年间, 当绝大多数国家正在削减军费预算时,中国却在利用其经济腾飞的实力来大幅度扩充军备。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正在追求作为军事大国的实力。自1988—1993年的5年内,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加了98%,共计净增75亿美元,而同期通货膨胀率为32%。包括一般军事开支在内,1993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已达180亿美元,按国际市场价格衡量,约合900亿美元。”〔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数字又与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1994 年中国国防费63.9亿元,仅相当于美国的2.3%,人均国防费用只有5.36美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院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8〕)相去甚远。
(3)、环境污染威胁说。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大部分动力来源于含硫量很高的煤。他们推算,仅在1991年中国便释放了11万亿立方米的废气,160亿吨的烟尘。“煤中排放出的硫酿成酸雨飞越国界, 破坏了西伯利亚和韩国的原始森林”。他们宣称,中国必须对全球的温室效应的日益恶化而负责。“中国燃煤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反常,甚至是引起孟加拉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沿海地区发生洪涝的关键。”〔9〕
其三,潜在威胁论。该论也包括三方面的论点。
(1)潜在经济威胁说。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及其经济发展规模的假定,是此说的切入点。1993年2 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特辑》首次提出“大中华经济圈(Greater China)的概念。该刊预测, 到2020年以大陆、香港、台湾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实力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10〕数月之后,克里斯朵夫又将该时间表提前了18年,称:“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02年‘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口额将达到6390亿美元。按照可比国际价格推算,到2002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8亿美元;同期美国是9.7亿美元。”
(2)、潜在粮食威胁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郎博士在《地球白皮书》(1995年版)中撰文《谁来养活中国?》,提出了中国的粮食需求对世界构成潜在威胁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大陆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已达到12亿之多,占全世界人口的21.4%。“中国政府在‘九五’计划中强调要在世纪末之前将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但是依目前中国人口以每年1300万人的增长速度推算,到2030年时,中国人口“无论如何”都将超过16亿人。由此他认为,“随着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也在普遍增加。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趋于多样化,对动物性蛋白质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然而,为弥补粮食缺口这一矛盾,中国再开垦新的耕地之潜力不大。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2.16亿吨至3.84亿吨。到时候中国将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可是届时就算把地球翻个底朝天也无法提供这么多粮食”。他的最后结论是:“粮食需求量与供应量之间的差距将会导致国际社会混乱、粮价上涨,为争夺粮食而引起激烈冲突和战火也是不难想象的。”〔11〕
(3)、潜在能源危机说。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将导致中国的能源危机,从而形成对全球能源的“潜在威胁”。他们认为中国的能源十分短缺,据统计,1991年每个中国人的能源消耗量为602公斤石油,而同期美国人均耗量是7681公斤石油。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后”,倘若其人均耗能量能赶上韩国人现有的水平,那么,“中国总的耗能量就远远超过了美国”。到时候“中国将变成纯粹的石油进口国,那时就迫使中国不得不将其目光瞄准南海石油”。因此,石油危机很可能“导致中国对南亚诸国使用武力,以确保它对南沙群岛单独拥有主权。”〔12〕
不难看出“潜在威胁论”的重点似是涉及经济领域的问题,但由此引发的粮食、能源等问题则无一不导向“中国潜在军事威胁”这一结论。对于所谓的“大中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在军事战略上的上述估计,揭示出“中国威胁论”提出的复杂的国际背景。
二
“中国威胁论”的形成并非西方文人们的一时之作,乃是昔日冷战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继续。究其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意识形态上看,冷战的突然结束,使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一场随传统的敌我界线的迅速消失而可能产生的对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得以相互补充、共存或共同发展的观念加以认同的危机。在长达几十年的冷战中,固定的信条对国民循环反复地灌输,将某种判断标准积淀于西方人的价值观中,它不仅成为西方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而且形成了在政治观念中一整套自我否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模式。
冷战结束,继苏东巨变之后,西方舆论曾一度认为,在西方的“以压促变”的政策下,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步苏东之后尘而发生类似的情况。然而,时过境迁,西方所企盼的“多米诺现象”却迟迟未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将出现,势必引起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谋士们的极度不安。
其次,从世界格局上看,中美之间失去战略合作的基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随之大为降低。然而,苏联的解体使得西方一些人急于寻找“新敌”取代苏联以维持原有的世界格局,及为自己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言:“美国40年来的目标一直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但是现在没有了目标,美国失去了敌人了。”〔13〕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也在其代表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后起大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引起所在地区力量结构类型的变化(渐变或突变)”其危险在于,由于它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在国际体系中所得到的利益和地位则较低,故而它将急于改变现状,“取代正在下降或增长较慢却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而后者则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加强对原有的国际体系加以控制,从而加剧与后起大国的政治冲突乃至军事对抗的危险。”〔14〕吉尔平这一观点得到美国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普遍认同。
1995年4月9——11日,始创于70年代初的北美、西欧、日本三边委员会在东京召开年会。会前,三边委员会指定三方专家花费了一年时间,精心撰写了一份题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正在上升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迅速崛起的前景,此乃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最重要的趋势,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它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十分强大的国家,它的崛起将促使亚洲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它提醒世人注意,“从历史上看,新的大国的崛起往往给原有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对原有的国际体制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引发了国际上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二战后苏联的兴起也曾打乱了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15〕三边委员会虽说是美日欧三方的非官方论坛,但该论坛与会者主要由政界、商界、学术界的要人组成,所以其评论则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再次,从西方某些国家的利益需要上看,一些西方人士提出“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之一在于排斥新的商业上的竞争对手,限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护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帕麦斯顿曾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从本国利益出发来决定国际事务及评价他国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西方一些人的思维定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曾说:“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有决定意义。”〔16〕美国一贯主张“要以我国的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17〕。这里所说的“利益”更多地则重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追求超越国界的物质利益往往成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矛盾的诱因,和国际政治活动所要达到的一种重要目的。
本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于低谷中徘徊,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6.7%,西方则为3.3%,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18〕近年来,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超出美国与西欧国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话说,“对美国利益而言,没有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的地区了。”〔19〕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正持续不衰,由此将可能引起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使国际经济格局出现较大地改组。这对于那些习惯于将世界认作是美国的世界的西方人士来讲,无疑是极不舒服的。
总之,“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西方某些人士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及意识形态的需要,“试图以冷战的思维,采取冷战的语言和手法,目的在于在亚太地区挑动新的冷战。”〔20〕
西方舆论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后果是恶劣的。它突出反映在对于中国的周边国家的心理压力上,使得久存的一些历史积怨重新开始蠕动。
苏联解体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南亚各国相继走出了“苏联南下、越南扩张”的阴影。它们根据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特点,开始重新调整各自的国家战略,本能地考虑新的“威胁”来自何方诸问题。在它们的心目中,经济腾飞的日本毕竟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其绝大部分工业原料依赖进口,大部分工业产品要靠国际市场消化;在人口结构上,日本老龄化程度居世界之首,劳动力结构已开始失衡:日元不断升值,使得许多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资本;冷战后全球贸易集团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趋势的日益加重,将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局面难以长久地持续下去;加之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性的不稳定限制了日本政府可能产生的对外采取冒险军事行动的意图,况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还不可能摆脱《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这一防务准则。于是,一些周边国家便将视角转向经济蒸蒸日上的中国。“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恰恰迎合了这种防御新的威胁特点的民族忧患意识,加之中国国内的某些单位和个人好大喜功,利用各种大众传媒所做的不切实际的宣传和报导无形中给“威胁论”提供了所谓的“佐证”,更是加重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畏惧感。它直接影响到中国与邻国的外交、贸易等关系。如,每当中国与某一邻国开展正常的友好交往,尤其是遇到高层互访时,总会引起其他相关国家的猜疑。个别国家已从官方角度对中国产品进口采取限制措施,或对欲往中国投资的本国华人设置障碍。
这里,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对这一恐惧心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5年,中国出于自卫目的进行核试验之后,日本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宣布“大幅度冻结对中国的无偿援助款项”。〔21〕日本参、众两院行动之快、调门之高、态度之烈是近年来少见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转移世人对日本政府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关注及解除邻国对日本近年来致力于军备竞赛“逆裁军”行动的趋势的不安和反感。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相悖,近年来日本不断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1993——1994年间,其军费开支已由美元337亿增加到420亿,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现有装备精良的24万人组成的国民自卫队、170架F—15战斗机、90多架P3C反潜巡逻机、1200辆现代化坦克。〔22〕其军事实力早已超过了本土防御的需要,给亚太地区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目前“中国威胁论”对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尚未起到质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远未达到促使其改变对华战略的程度,但它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有损于中国形象,而且破坏着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正是这样,这种论点的渲染足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
三
“中国威胁论”的提出从本质上看,与以往美国等西方舆论中的人权、西藏、武器扩散、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同出一辙,均出于“新冷战”之目的。冷战后美国虽然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经过长期冷战的拖累,其国力早已今不如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屡屡失误使之霸主形象大打折扣,它对“中国威胁论”的一再渲染只是其一贯对华政策的延续。说到底,只要中国一天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便一天也不会停止对中国进行攻击,对此我们应保持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就“中国威胁论”本身而言,对于其中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制度、国家主权的内容,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同时,我们又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无须将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所有不友好的言行,诸如美国提高台湾地位,批准李登辉访美、享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等问题都归之于“中国威胁论”而加以痛斥,从而使问题复杂化。尤其是对美国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时刻认识到我们的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应该围绕这一中心。
“中国威胁论”的提出反映出西方世界于世纪末面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的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危机感。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开始彷徨犹豫,他们提出的种种外交思想、政策建议自相矛盾,其理论依据也常常漏洞百出。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一基本的事实决定着它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规模的特点:中国要以占世界7%的可耕地来解决占世界22 %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它的经济上任何迅猛增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化解下都变得远远不足以解决历史所遗留下的贫困问题。虽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西部不少农村地区至今尚未彻底脱贫,数以百万计的文盲、残废人、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需要社会的援助。“希望工程”在中国各地的兴起很能说明中国的经济现状。这些问题及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汇集起来的“民工潮”等问题的解决将造福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贡献,而它的实现没有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是根本不行的。
像其它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的安全。中国近年来的军费预算虽有升高,但是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后,它的实际增长幅度并不高。至于核武器试验,中国已经公开宣布同意在《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生效后,全面停止核试验。况且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和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23〕
几年前,西方舆论曾大肆攻击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只字不提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如今“中国粮食威胁说”对中国政府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缄口不语,并无视所谓“超级经济大国”与“粮食威胁”这两个命题之间本身所存在的悖论。
诚然,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士都赞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在这一论点提出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都提出异议,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将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排除在外,世界的前进是无法想象的。对于美国舆论中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美国国内的学者和政治家历来持有批评的态度。美国前国务卿享利·基辛格博士曾直言不讳:“很少有一天(美国)国会不对某一外国指责一番,很少有一天(美国)政府不对世界各国内政说三道四。”他问道:“难道我们真的能永远扮演对世界各国内政进行训导的校长角色吗?难道我们什么都懂,有资格对从亚洲到拉丁美洲各国内政问题给予指导,甚至把意见强加于人吗?”他指出,照此下去,“美国就可能成为一个整天责骂世界的泼妇,同时丧失影响世界的能力。”〔24〕对那些“中国威胁论”者而言,细想基辛格博士的这番话,也许是十分必要的。
收稿日期:1996—01—24
注释:
〔1〕《辞海》(缩印本),第1655页。
〔2〕〔3〕〔8〕葛易:《浅析“中国威胁论”》, 《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第56—57、58页。
〔4〕〔5〕〔6〕黄仁伟:《“中国超级大国论”及其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
〔7〕〔9〕〔12〕Nicholas D.Kristof,"The Rise of China,"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3版,第63、65、67页。
〔8〕〔23〕《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人民日报》,1995 年11月17日。
〔10〕"News Week"(U.S.A),Feb.20,1993,P7
〔11〕《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第32页。
〔13〕《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第50页。
〔1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3页。
〔15〕陈启懋:《中国发展规模被西方夸大》,《解放日报》1995年5月12日。
〔16〕S·霍夫曼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7〕《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4页。
〔19〕参见1993年11月5日《新华社通讯稿》第7页。
〔20〕《人民日报》1995年12月28日。
〔21〕《瞭望》1995年第39期第11页。
〔2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15页。
〔24〕转引自《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第7页。
标签:军事论文; 中国威胁论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