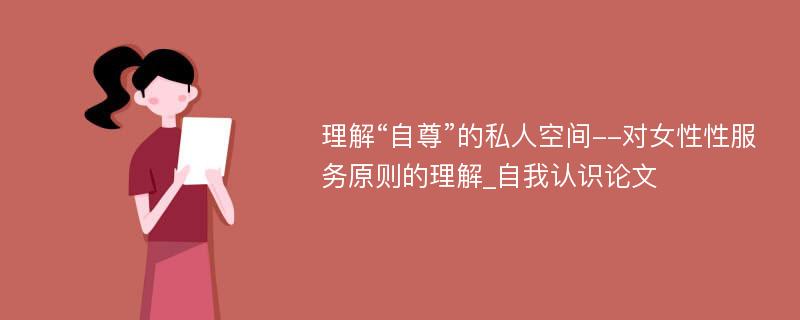
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对性服务妇女服务原则的一种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私人论文,原则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2)04-0011-13
在这过程中,最大的满足是自尊心的满足。因为我在以前那些男朋友这里,都很颠倒的,没什么自尊可言。就是很迁就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定要想办法办到,就是这样的。在客人这里就不同了,客人有求于我,我就是很高傲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总觉得自己,反正他有求于我,我肯定高他一等……基本上就是我摆平他们的。
——快快①
1998年7月,在某省妇女教养学校进行当初没想到会历时10年(1998—2008)的“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赋权性服务妇女”②项目的个案访谈③中,我听到了被访者快快这段话,心中大吃一惊。因为这完全溢出了我们一直认为的“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丧失尊严”的常识,也与众多的研究中有关性服务如何自轻自贱的论断相违背。
我并不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为这段话在整个被访者的叙述中逻辑很完整,更何况,“丧失尊严”是一种主流用语,在劳教中的性服务妇女大多习惯于用这一词来表明自己的悔过自新,快快不会故意以反社会的表述来加大自己的被惩罚风险。那么,如何在被普遍认为是“丧失尊严”、“自轻自贱”的性服务过程中,快快会认为自己最大的满足是自尊心的满足,她在性服务过程中收获了自尊?她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尊、满足自尊心的?而事实上,被访者中论及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自尊或得到自尊者几乎占到总人数的1/4,这进一步提示我这一个案并非孤案,有可能是具有某种常见程度性的常见现象。
快快以其个体化的自我叙述在常识和学术研究论断的华丽皮袍上划开了一条大大的裂缝,由此,性服务妇女的自身经验通过自身叙述进入了有关商业性性交易的论述之中,他者的视角和他者的话语被暂时搁置于一旁。而基于“自尊”一词内蕴的高尚、神圣、道德之意义,处在常识和原有研究论断与事实和新的可能性的夹击中,我陷入了学术焦虑之中。这一焦虑直到遇到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才逐渐减缓。开始认识到也许可以由此展开一种新知识的认知之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出:“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法,那么这种用法一定像‘桌子’、‘灯’、‘门’那些词的用法那样平凡。”“私人体验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本,而是没有人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这个样本或者其它东西。这样一来,就可能作出这样一个尽管无法证实的假设:一部分人对红色有一种感觉,另外一部分人有另一种感觉。”“清晰的表达能导致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出联系’。”“只要我能够把我的目光绝对清晰地对准这个事物,把它置于焦点之上,我就必定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1](PP66~13)
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我梳理出对“自尊”一词的新的理解:(1)在日常生活中,“自尊”只是一种对“自我尊重”的肯定性表述,并未被形而上学地赋予德性的意义。(2)对于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的“自尊”,每个人的私人体验不尽相同,并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事先就知道别人的“自尊”私人体验,甚至即使知道了也无法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自尊的拥有和满足、实践和实现、知晓和理解的私人体验有较大的差异。(3)“自尊”的私人体验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现实。因此,它与其它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之间有着一种必然联系。我们对于自尊的私人体验的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看出其中的联系和能在多大程度看出其中的联系。(4)只要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光绝对准确和清晰地对准“自尊的私人体验”,把它置于分析的焦点,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把握包括性服务妇女的自尊在内的自尊的私人体验这一事物的材质。
根据对自尊的这一新理解,我们不得不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否在主流和公共的场域之外存在着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进而有了自尊的私人体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论及词语的意义时有一段引用语:“某种红色的东西可能被毁灭,但红色是不可能毁灭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一词独立于红色东西存在或不存在的道理。”[1](P41)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将之推论至“自尊”,即:自尊本身是不可能毁灭的,只可能失去了持有者。因此,失落或被剥夺了自尊的人,是可以也能够重拾自尊并加以安放——拥有具有个人、私人特质的自尊体验的。那么,在职业、教育、婚姻、家庭等主流和公共场域之外,对于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者,如性服务妇女来说,是否还有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
第二,如果有,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实践和实现的?有没有某种行动策略?其结果又是如何?“自尊”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私人体验,对边缘和底层者,如性服务妇女,边缘和底层生活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私人体验,这两种私人体验之间是如何被打通,使边缘和底层者在被常识认为是无自尊和反自尊的生活中捡拾和安放自己的自尊?
第三,一种关于自尊的私人性空间的社会研究能否成立,其意义何在,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者来说?边缘和底层者的自尊以私人体验的形式掏空了“自尊”原有的德性的意义,使之回归平凡;破坏了“自尊”原有的社会范式,使之成为一种私人体验;挑战了“自尊”原有的公共空间类型,使之具有了私人空间特有的张力。由此,怎样才能理解这一溢出原有知识范畴的“自尊”,发掘出个人叙述所具有的社会指涉(social signifing)的意义,使之从经验上升为知识,进而进入知识传承体系?
要解答以上问题,诠释学的方法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而作为边缘/底层人群中的“底边人群”,④其对性服务地点、时间、对象、方法等的选择和性服务对象的对待,在为我们打开认知和理解“自尊”的私人体验之窗的同时,也成为适宜的分析对象。
一、为什么要以诠释学为分析方法
“文本(text)的诠释起源于希腊的教育系统,但是诠释方法的发展与初步形成要等到宗教改革时期对于教会垄断圣经解释的攻击。”[2]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至今诠释学发生了由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由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由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向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三次大转向,至少具有/已被赋予了六种性质:(1)作为圣经注释理论;(2)作为语文学方法论;(3)作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4)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5)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6)作为实践哲学。⑤由此出发,诠释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具有某种语言中介作用,而当语言的转换是基于理解和解释之上时,诠释学也就首先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转换,具有某种话语中介的作用,从而成为伽达默尔所说的“一切思想的使节”(Nuntius für alles Gedachte)。[3](PP11-27)
人生活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并划定了自己的生活疆域,搭建起自己的生活边界。于是,诠释学得以作为“一切思想的使者”穿行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中,去了解、理解、解释和实践。恰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理解是这样一种能在之存在,这种能在从不缺乏作为尚未现成的东西,而是作为本质上从不是现成的东西而随着此在之在生存意义上去‘存在’。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它对这样去存在或那样去存在总有所理解或无所理解,此在作为这种理解是‘知道’它于何处随它本身一道存在,也就是说,随它的能在一道存在。……只因为此在理解着就是它的此,它才能够迷失自己和认错自己。……从而此在在它的能在中委托给了在它的种种可能性中重又发现自身的那种可能性。”[4]就任何人而言,“能知”之存在使之能基于“不知”之存在,通过诠释,穿越“无知”,达到“知”之彼岸——了解、理解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研究者亦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研究者会进一步借助/应用相关的理论,对他者的生活/生活中的他者作进一步的解释,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概念或观点。这便是本研究选择以诠释学为研究方法的理由。
“理解”是诠释学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在本研究中,“理解”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对自己“能知”和“此知”的了解、检验和批判,一是对研究对象“能在”和“此在”的知晓、感知和了解。“理解的行动总是牵涉了将理解对象的陌生性加以克服,并将之转化成为熟悉的事物。”“文本与诠释者有其传统与视域。……在视域的流动中,我们意识到视域的存在。但是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视域呢?我们已经知道,跳脱自己的立足点以进入他人的视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存有是植基于我们的处境与视域之中。”即“所有人的理解都植基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没有外在历史与语言的阿基米德点。”因此,理解实际上是“借着视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来达成”。而也正是在“诠释者与文本的互动过程中,第三个语言形成了,而他们的视域也得到融合与转化,变得更为丰富。”[5]也就是说,正是通过与性服务妇女视域的融合和转换,本研究才得以理解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自尊、自尊体验、自尊空间的“能在”和“此在”,进而能够探究一种自尊的私人空间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存在的话,性服务妇女所进行的个体和私人性构建的策略。
二、是否有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性质空间?
自尊的本质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基础是自为的实践和实现——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践行与达致,而对于自为的实践/实现与否和程度,自我决定权和自我选择空间为一大决定性因素。由此,一直被视为、事实上也是更多地受控于他人/社会的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就在分析是否有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中具有了典型的意义。要回答是否在主流和公共场域之外,有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性质的空间,可以以最遭否定的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自我决定权/自我选择空间为切入点。
所谓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自我决定权/自我选择空间,指的是性服务妇女在从事性服务中的自愿性和自主性的实践和实现——基于个人意愿和主体性的对服务对象、时间、地点、方法、报酬、后续行动等原则的确定和实施(自主权)以及确定和实施的程度(自主空间)。对于性服务妇女的服务行为,人们有很多想象,并在想象之上搭建了诸多的共识。如“给钱就行”、“昼伏夜出”、“灯红酒绿”,等等。然而事实上,性服务妇女的“工作场景”是溢出主流、正统、中产阶级思维的想象力的,任何不站在当事人立场的描述、叙述和分析难免会有误解、偏颇和盲点。而性服务妇女的“工作场景”之所以会溢出常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性服务妇女对于服务行为原则的确定和实施是十分个体化和差异化的,并与底边生活相伴随,具有“底边人群”的特征。
1.对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一
WHY:我跟社会上的老板这些人关系不太好的。我看不惯他们,他们有点钱就很了不得的,我最不喜欢跟这些年纪大的人相处,因为他们都是这样一些人,我不喜欢跟他们打交道的。
WTF:一般跟我接触的人,都是二十七八岁到三十二三岁,也就是35岁以下、25岁以上这段年龄。在这段年龄我跟他们接触的,我觉得他们这年龄段经济上也比较有钱,比较成熟,有素质,修养这方面比较好,一般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男人。像这些流氓一样的小男孩,我觉得一起逛逛公园、逛逛街是没关系的,真的叫我跟他们玩啊,我觉得没必要,他们要钱没钱,是不是?
PLL,B:我一般是这样的,看看这个人还顺眼,比较舒服一点,干净点的,如果脏兮兮的……我最讨厌那种农民企业家,感觉上就给人很不舒服的。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的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一是个人及其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如,绝大多数性服务妇女对来自农村的客人,尤其是自称或被疑为“农民企业家”者抱有反感,不愿向其提供服务,或在服务中尽可能地“偷工减料”。这实际上是阶级/阶层偏见与对抗的一种反映。
2.对性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二
HXZ:年纪太大的话,我不喜欢的啦,年纪太小的,我也不喜欢。为什么?太大嘛,我怕有病,心肌梗死,我听了很多这种谣言。年纪太小的嘛,到时候纯粹是为了钱,感情根本谈不上的啦。年纪太小的,没什么钱的。
HLJ:客人大多是采购员、厂长什么的,我喜欢熟客,好像认识了,讲话嘛,好像也很随便的,那不搭界的,有时候,熟客的话,他钱多一点给你们,那有的时候,我也不问他们拿钱,这样子。
DXY:像我们在桑拿浴室是这样的:反正一出去的话,肯定是有钱的才跟他们出去,像现在玩玩的哪里有很多有钱的,实在有钱的,一个月两三个,也就算是最好的。带出去肯定是钱比较多一些。
WSH:反正有职业的人,我一般就不玩的,反正一般的女孩子就有职业什么也玩的,那我不玩的。我心里就这样想的,像他们,就是工资,有多少的。那我这样想,他如果就是靠外快,也没有多少的。捞也捞不到多少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给他拿一点钱,肯定很心痛的,是吧?我这样想的,好像没意思的。那我一般玩,就是喜欢做生意的。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二是:个人的心理偏好。如,有的人倾向接待中年人,认为他们有安全感,有温情;有的人倾向接待年轻人,认为他们有激情,会玩;有的人愿意被包养,认为这样省心省力,收入可靠,安全系数大;有的宁愿做“散户”,认为这样独立自由,没有做“第三者”的内疚。这种心理偏好大多可在对其社会化过程(包括紧张性事件)的追溯中找到根源,即,这实际上也是个体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之一。
3.对性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三
服务收入不低于500元的IJF:地点都是客人安排的,一般都在宾馆里。
每次服务收入在200—300元的HXZ:我一般把客人领回自己家里,安全一点,到宾馆里很少的。
每次服务收入在100元左右,最低为50元的LWY:我租了一间房子,在舞厅找到了客人就带他到那里来玩;除了到自己家外,有时男的也带我到他家去。其他地方也去过的。我们LS外面有一条瓯江,到那个江边上,有滩的,草泥地上。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三是:个人在本群体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在性服务妇女内部,也是分为不同的层次的,⑥而相对于每个层次,每一位性服务妇女不仅都有自己的定位,也依此层次,给本群体中的其他人定位。就一般而言,每一层次的人都有属于自己这一层次的、相对固定档次的服务对象、地点及价格。如“国家队”的通常不会到小客栈为过路的长途汽车司机提供服务,即使客人高额付费;“街道办事处”也不太会接“老外”到宾馆去“办事”:⑦不完全是事关“抢生意”,因为中国大陆的商业性性交易群体目前尚未进人严格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严密的团伙领地,不得抢占别人地盘的黑社会阶段;这更多地是由于对于居于较高层次的前者来说,这属于自我定位及其由这一定位产生并反过来支撑这一定位的自尊——她不愿“掉价”,事实上,她也不能“掉价”。一旦她“掉价”并让他人知晓,她的内心就会接受“掉价”,她的“队友”们也会以此讥笑嘲讽她并在客人中传播,自我排斥和他人排斥会使之在原层次上难以为续,进而下滑至另一层次,这无疑是较高层次者的大忌。而对于居于较低层次的后者来说,且不说她是否能接到“老外”,更主要的是“老外”、“宾馆”作为一种符号,不仅显示着豪华、享乐、有钱、舒适,也指向陌生以及由陌生产生的危险感。如果说,小客栈中的长途汽车司机对于“国家队”来说也意味着陌生,但“屈尊”的姿态能使“国家队”的心理危险感大大弱化的话,那么,“宾馆”中的“老外”对于“街道办事处”来说则是一种“攀上”,自卑心理加重了由陌生产生的危险感。因此,“街道办事处”们一般不去“勾引”“老外”,对于“老外”的“勾引”大多也或心有所甘或心有所憾地婉拒——她们不敢逾越自己的位置。从阶级/阶层分析的视角看,这一根据个人在本群体阶层结构中的位置进行服务对象的定位,实际上是性服务妇女基于群体外的阶级/阶层的分层和定位之上的群体内部的阶级/阶层再分层和再定位:在阶级/阶层社会中,商业性性交易不可避免地亦是一种阶级/阶层的生产机制,它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阶级/阶层的再生产。
4.对性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四
LWY:这个事情也要看人的……实在是很蛮的,我也不会跟他去的,怕的,一般看上去很诚实的样子,才会跟他去的。
CL:出台一般都到宾馆里干这种事,一般是妈咪介绍的宾馆,或者是妈咪给我们安排好的。嫖客选择的,我们不去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出事的,妈咪很有主见的,她给选择的地方一般不会出事的。她在那里是一路通的,特别是那里的保安,她都搞定的,她只要一个电话过去就行了。
JMC:反正我都是白天的,晚上我自己不要去的。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怕派出所的人会跟踪来。
WHY:我带出去的时候很少的,我从来没有陪过夜,因为我跟不熟悉的人在一起的话,是睡不着的,即使他们出得再高一点,我都不喜欢的。
快快:客人中,香港人、台湾人是有的。这种华侨是很多,但是,外国人有是有,但是我不接客,我就陪他们唱歌什么的。我怕艾滋病的。
WTF:我如果跟这些客人上床的话,那我都会拿避孕套给他们的。不愿意的话,我就不做嘛,一般他们都是钱先给我的。如果生客的话,他也不会,不过有时熟客的话,我对他印象如果好一点的话,那他说不用,那我也没有关系。
WSH:那我上次碰到过一次嘛,那他说要什么动作。什么东西呀,那我就是小费扔给他,扔回给他。我说不玩了,我就走了。那后来他把我拉回来,他就说算了,算了,那就是……我看到这种东西,我好象觉得很厌恶一样的。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四是:个人对于安全的把握。这一安全不仅是指不被逮捕,还包括避免性病艾滋病的感染、防止服务对象的性虐待或难以接受的“变态”行为,以及获得理想的收入。当然,对于什么是变态行为,各人也有各人的界定。
5.对性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五
LWY:最少的是50块,记得有一次是200元。一般这些男的也知道的,他看到心里不满意,就会加一点。一般都是给你50这样子。他如果给30,看到我不满意,他就会添点,凑你半张这样子。有的人不凑半张会凑整张,有些人凑80这样子来的。
GL:固定的,给几千几千的也有的。一般的话,都是800—1000元,一般档次很低的我不玩的,一般都是比较有钱的。
DXY:一次就算一次的钱,一个晚上就算一个晚上的钱,不跟他讲几次那个。我说要么都价格高一点,我做的两个是一千块,她们做五六个才一千块,这样我是不干的。
LX:我有两种定位,一种是偶尔在一起,完事马上就走的话,我就少一点,但不能少于500元;要是过夜的话,最少不会少于800元。如果说客人不出这个价钱的话,也可以转身就走的。但如果说我看这人很好的话,或许会降一点。但是,我最低就在这个层次了。对于熟客,我们并不是说只拿他一点,像我们现在的房子、电器都是他们买的。房子也是他们租的。我们找一个地方,他们出钱。曾经我也有过一件事情,他给我租了一年的房钱,几千块钱,我一个人住。但是,我另外还有一套房子,我就把这套重新租掉,租给别人,然后,我就说你这房子不好,另外找了一套,但他来的时候,我还是让他另外开宾馆。……所以,我们脑筋也要想一想,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怎么才能赚得到钱。
快快:到深圳去,就是想找找有没有老板包的机会。但很多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价格不是很高啦。有一次过去么,这个老板出12000块,而且有个房子,三室一厅的房子,房子给你弄好的。我说这么低的,我就不愿意了。他说你这个人这么笨,他说给你12000块钱的是个底价,他说另外东西我可以给你买,我就是,我不肯。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五是:个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需求。这是人们常常论及并遭到更多抨击的一种原则。尽管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性服务对于利润的追求原本是应有之义,人们对这一商业行为本身有着更多的道德评判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并且,事实上,性服务妇女在从事性服务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收入而是安全问题——只有在确保或自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她们才会“做生意”:生存状况的危机四伏使她们较之常人更明白一个浅显的真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对性服务对象的选择原则之六
DXY:我做是一次性的,我是不喜欢下次来找我的。因为觉得,第二次见面,看到,脸上都不好意思。生客反正都这样,大家都不认识的。
WTF: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房间,我们都住在宾馆里、酒店里的,也很少出台。后来认识这些客人多了,也不愿意上班了,三天两天两头串台。他们有时打我手机,打我传呼,今天晚上哪里熟客很多,生意很好,我马上就到那家酒店,就这样的。没有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就是串台子的。
HXZ:我的定价一次最低不低于500元,他们说这么贵的?有这么贵,最起码陪我一夜。那我就说,市面上这种价格你应该知道的呢,你也是这种玩玩的人。如果你不给到,我也要翻脸的。
WHY:我最不喜欢的女人就是不管多少钱她都会去做,而且做的方式都很恶心,就是换花样、口交什么的。这种女人我店里有过一个,她长得很漂亮,但智力不太好的,她赚钱养男人的,她男朋友叫她做这事的,每天晚上一回去,她就把钱交给他。她生意好的话,一个晚上接七八个。这种女孩子我也不喜欢的。她回来以后,我就不要她了。我就讽刺她,你跟你老公到深圳去。其实,我是不会讽刺任何一个做这事的女孩子的,因为我曾经也这样过,我也从来没说过看不起做“鸡”的。她用这种方式去做“鸡”,觉得太恶心了,所以不喜欢跟她在一起,好像跟她同吃一个碗的饭都有一点恶心。
从中可见,性服务妇女选择性服务对象的原则之六是:性服务所在地一般的“服务规则”和/或所在同伴群体的行事标准。这一规则和标准包括价格的确定与浮动、地点的选定、对象的选择等;也包括服务的方式。
也许是多此一举,但为防止误解又不得不说明的是,性服务妇女在实施上述六大原则时,有时较为单一,有时较为综合;有时是主次分明的,有时是主次难分的;有时是有前后次序的,有时是前后不分较为杂乱的。而无论如何,性服务妇女都是在性服务过程中坚守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则的。
三、在私人次空间中实践和实现自尊的策略
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营造了一个可以捡拾和安放自己自尊的私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她们又是如何实践和实现自尊,或者更具体地说,她们在性服务过程中通过/运用什么策略实践和实现自己的尊严?
在主流社会,年龄、容貌、健康、出身家庭等等是个人自尊达致的先赋条件,教育、职业、婚姻等等是自尊达致的后赋条件。而性服务妇女中的绝大多数原本处于社会的底层,⑧所从事的性服务使之处于污名之中,她们所在的亦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因此,主流社会获得自尊的手段与方法对于性服务妇女的适用性较低。
进一步看,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自尊的捡拾和安放是必须以性消费男子的存在为前提的。以性服务妇女的性服务原则之一:个人对于经济的需求为例,个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需求可以追溯到当事人个人和/或家庭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如,多数绝对贫困者、相对贫困者来自贫困山区/农村,或城镇中的贫困家庭,但除了这一初始化的贫富差距外,性服务妇女个人的经济收入更主要的是由其“工具化”身份被男人认可、接受的程度所决定的。这一“工具化”主要是“性工具化”(不仅是性交工具,包括作为性观赏、游戏、情感慰藉的对象),也包括“家务劳动工具化”(即被包养者提供全套服务中的保姆、厨娘之类的家政服务)——被男人认可、接受程度越大,男人支付的服务费用越多,性服务妇女也就收入越多,在性服务提供中的经济迫切性越低。排除了性消费男子这个“他者”,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的自尊行动无法实践,自尊体验无法实现,自尊的私人空间也无法营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营建的自尊空间也是一个次空间:它并没有自身独立的空间,只有在他者存在之时和浪迹之地,它才能够存在和得以存在——它才显现自己的“能在”和“此在”。也正是由此,性服务妇女捡拾和安放自尊的行为从客体性的反抗进入到主体性的对抗,不再是一个工具——客体(性服务妇女)对使用者——主体(性消费男子)的剥削行为的一种反对式的抗争,而是成为两个主体(作为性服务妇女)的自我和作为性消费男子的自我之间的一种实力抗争式的对抗。恰如著名的女性主义政治学家莎伦·马库斯在《战斗的身体,战斗的文字:有关强奸防范的一种理论》一文中的名言:“要建设一个我们不再会有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把强奸吓得魂飞魄散。”⑨这些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建设了一个自己不再被歧视、拥有自尊的私人空间,任何进入这一空间的性消费男子,在进入之初就会遭到贬低与矮化,不再成为自尊的主体。妇女对于性服务原则的确定和实施表现出她们在这一服务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自尊空间的“此在”和“能在”是对商业性性交易中男性+阶级霸权的主体性抗争。但是,这一自尊空间的建立和抗争行为的实施又是以性消费男子对于性服务妇女的工具化身份的认可和接受、将性服务妇女工具化为前提条件的。这似乎是一种悖论,而性服务妇女又是通过何种实用性策略消解了这一悖论,进而成功地营建起自己的自尊空间的?
1.分离策略
LJF:我这个人虽然是在社会上混的,但如果碰到要求口交的男人,我还是要翻脸的。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要不高兴的。虽然在你们看起来,我们是在卖淫,给别人当玩物,其实我脑子里不是这样想的。他不尊重我的话,我拿起包就走的,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既然出来了,就要赚点钱回去什么的,不会强求自己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PLL,A:客人要求其他姿势,那我不高兴,我说,你要那个的话,我不高兴的,烦也烦死的,快一点好嘛,还有什么这个姿势、那个姿势的,那我说,那你去找别的女孩子好了。
WTF:那我看到这个男的不顺眼的话,我有时候就好像,就希望他快点了事。好像是说我跟你是没有感情的,和你是做交易的,我只要你的钱,你也只是要得到你的性欲的满足。那我就拼命地催,希望他快点走掉,就是很讨厌他。有时也很讨厌这种生活,但我就觉得被生活所逼一样,觉得没办法的,我就这样想的,我就希望他快点下去。
CL:只要你能够放得开手,我可以,但如果你很小气的话,那对不起,我不愿意干的。我交换意识是很强的,如果说你今天只能给我300块,叫我陪一夜是不可能的。我一次最起码500至800块,而我的价钱真正算是高的。
就总体而言,性服务妇女的自我工具化/被工具化和主体性抗争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有的更具自我工具化/被工具化的倾向,有的更具抗争性倾向;就性服务妇女个体而言,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两种倾向,但在具体的性服务过程中,这两种倾向并非是同时共地存在的:有时/有的场合会具自我工具化的倾向、更多地接受被工具化,有时/有的场合更具抗争倾向。用她们的话来说,个体间的差异就是:“他们(指性消费男子)玩的是别人,而我是玩他们”;时间/场合的差异性就是:“该低三下四的时候就低三下四,该搭架子的时候就搭架子。”
性服务妇女的这一策略可称之为“分离策略”,其中包括将自己与本群体中的他人分离和场景分离两大类型。通过这一分离,这些性服务妇女或划出了自己与“自轻自贱”的“别的”性服务妇女之间的疆界,或划出了自己“自尊自重”之时之地与“自轻自贱”之时/之地的疆界,使这一自尊空间具有了自有和私人的特质。
2.非工具化的策略
PLL,A:我没有感到他们看不起我,我也从不说钱,都是他们自己放的,算算上次放的钱差不多了,他们就会问是不是要付电话费、电费什么的,就拿我的包,放个几千块钱进去。
WTF:他们都对我很关心,我年纪小嘛,他们把我当妹妹一样,到时候就会来问问我,身体好不好啦,心情好不好啦,什么的。不是每次来都要发生性关系的,发生性关系这种事情不多的。
LJF:我实际上不是跟那些卖淫的一样,很低档的,给你几百块钱就行了。我一般跟的人就像是情人一样的关系。
WPR:我不像卖淫妇女租一间房子,我一般都是为了散散心,交交朋友,既然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也就顺其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乐趣是身心愉快,很放松,除此之外,还能得到钱。起先,不做这种事情,不自豪的,那时整天为家忙,烧饭工作,后来卖淫后,打扮一下出去,有时三四个男的围牢,为了我吵架、打架的也有,我想想很开心的。这时,我觉得很浪漫,有点骄傲,有点自身价值。
一般认为,商业性性交易就是钱物与性服务/性服务与钱物的交换;而在这一交换中,作为以性服务交换钱物的一方,性服务妇女被认为是性消费男子的性工具和某种赚钱工具,而这也正是最遭社会谴责之处。但从访谈资料可见,一些性服务妇女将自己与性消费男子的关系或整体或部分浪漫化为一种爱情/情感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双方的感情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性服务与钱财则被置于次要乃至无关紧要的位置。这一浪漫化的建构消解了性服务妇女最遭社会诟病的“工具性”,将冷冰冰的商业性的交换转变为温情脉脉的情人关系、兄妹关系,将赤裸裸的性服务——钱物的交换行为转变为两性之间柔情绵绵的关爱和慰藉,性服务过程由此不再是工具被运用的过程,性服务妇女由此成为性消费者的情人及关爱和慰藉的对象。
性服务妇女的这一策略可称之为“工具的非工具化”策略,其中包括自己不再是性服务的工具和不再是赚钱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的非工具化”策略,这些性服务妇女将自己从某种工具的定位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作为工具的自卑和自鄙,性服务过程或整体或部分地成为一个体验自尊的空间,其在主流社会丢失和流浪的自尊在此得以捡拾和安放。
3.服务对象工具化策略
DLL:我跟客人之间并不是一种交易,我只想去伤害他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很会演戏,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喜欢很容易的。……然后,我再把他甩掉,我就很开心,我就是为了报复男人才去做的,玩他们,用他们的钱玩他们。
JMC:碰到我心情不好时,我要骂他们,我不要跟他们,就是他们来找我,我要给他们骂走的。反正我就是感觉到心里很烦的,我就是要骂人。
WSH:怎样多拿小费?就骗他嘛,骗他说,想和你晚上玩什么的……说等会出去和你吃夜宵。吃夜宵肯定是陪他的了,实际上是骗他的,等到夜宵吃了一半就溜掉了。还就是有的时候小费先拿到手,那等到下班了嘛,就跟老板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就走掉了。叫他自己回去,就这样的。客人不会不再来,越是这样,他越会来的。你好像钩子一样的钩牢他嘛,你就是好像走掉了,说我身体不舒服,你要来就是过两天再来啊。就这样说的嘛,那意思好像是女孩的事情,就是见红的意思,就是说身体不舒服。
XJ:当我走上社会赚钱,我就脑子里想牢这个目的。我对男的从来没有感情,而且我是必须赚钱,不可能对他们有感情。……我这个想法就是无非为了赚钱,好像说舒服不舒服,你玩为了舒服怎样,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和这个客人做好一次生意,我钱一拿到手,我就必须马上就走的,我也不和他谈任何事的。
QLX:丈夫,他一下就没有了,然后就自己睡觉。……那时我感到很痛苦,想,为什么?……以前他们说过性生活很满足的,我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尝到过,他(性消费男子——引者注)说你在上面试试看,我在上面很舒服,跟丈夫从来没有过的。
JRAY:掌握到这些规律后,我一般会有目的地接触从政男人,因为他们只有权没有钱,所以跟他们更主要是彼此相互利用式的接触。比如,有一个相好三年之久的当官的,他很有实权,我就去找他办表弟调动的事。⑩
在进入性服务之前,不少性服务妇女已把自己的服务行为设定为实现自己某种目的、满足自己某种需求的方法或途径。所以,在性服务过程中,尽管性消费男子力图将她作为服务的工具,但她却尽可能地利用性消费男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求。由此,在更大程度上,她成为性交易的主体,而性消费男子则转化成为她的工具,为服务对象的服务转化成为服务者的自我服务和目标达致,这一转化甚至延伸到了性服务过程之外,如事后的索要金钱和利用资源。
性服务妇女的这一策略可称之为“服务对象的工具化”策略,其中包括将性消费男子工具化为报复的工具、出气的工具、性工具、赚钱的工具、利益实现的工具,等等。通过这一“服务对象的工具化”策略,这些性服务妇女实践着并实现了对那些原本以强者、尊者、优势者身份出现的性消费男子的操控,使之弱化、卑化和劣势化,最后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被性服务妇女掌控于手中的工具乃至玩弄于手中的玩具。而也正是在这一掌控和玩弄中,性服务妇女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尊——一种非当事的在场者难以体验到的一种私人体验,在自卑的自我中生长出自尊的自我,在男人面前的自卑、自弱、自鄙、自贱等等开始成为过去,一个自尊的新空间诞生了。
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在论及西方后现代妓权主义时曾提炼出两个概念:“亲性后现代女性主义”(pro-sex postmodern feminists)和“反性价值观”(anti-sexual values)。其中,前者将“卖淫妇女视为有力量的性主体”,将“卖淫视为是一种提供有滋养的、赋予生命力的性服务”,是妇女以性为基础的抗争;后者则认为性服务妇女并不是为自己的性需求,而只是把性服务作为一种抗争的手段。[6]借鉴这两个概念,本研究所访谈的性服务妇女的基于自尊的抗争也可以分为“亲性抗争”(如QZX)和“反性抗争”(如DLL、JMC、WSH、XJ、JRAY)两大类,并以将性服务作为抗争手段的“反性抗争”为多数。而正由于这些性服务妇女或是将性服务作为一种抗争手段,或是将性服务作为满足自己性需求的主体性活动,作为服务对象的男子只是工具或玩具,性消费男子的满足,无论是性满足还是情感满足逸出性服务妇女的视界,以他人为对象的为顾客服务最终转变成为以自己为对象的自我服务——性服务妇女成为性服务的主体,并通过服务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尊体验。
四、认识一种自尊的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
让我们再回到日常生活的“自尊”。在日常生活中,自尊的含义只是“自我尊重”,这是一个十分私人化和个体化的命名。但一旦脱离日常生活,上升到意识形态,被类型化为上层建筑的一大构件,它便更多地与较高的社会美誉度相关联,被赋予了德性的意义,成为“高贵”的伴随物。于是,更多地居于/属于底边社会,从事着被高度污名化的性服务劳动的性服务妇女不仅难以在主流社会中与他人共享自尊,也难以在自尊的公共空间中落脚,在被轻贱化/卑劣化的过程中,她们的自尊或丢失了,或浪迹天涯。
只是性服务妇女毕竟是人,即使是作为从事着被认为是高度失尊、无尊的性交易的“经济人”,其最本质的要素依然是“人”,人之所以作为人的自尊无疑也是性服务妇女希望获得和拥有的。她们的居于/属于底边社会使得她们难以通过具有较高美誉度的公共途径,如升学、就业、提职、婚配等获得/拥有与“贵”相伴的、具有德性意义的“自尊”时,“自尊”便回归了它的原始意义/本义,由意识形态回落到日常生活,成为性服务妇女一种私人体验和个体体验——“自我尊重”。而也正是因为这一“自我尊重”只是一种自我体验而非他人认同/社会认同,性服务妇女得以/能够在被社会/他人高度轻贱化/污名化的性服务中心安理得地、理直气壮地捡拾起在公共空间丢失的自尊,公然声称自己在性服务中获得了自尊——在性服务中营造起属于自己的自尊空间,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自尊体验。
JMM: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就是好像害怕什么的。但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害怕失去这个那个的。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失去他们我无所谓。
WHY:背地里都骂他们牲畜,他们走了,就说牲畜走了。接待客人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猪什么的。
WTF:后来在我自己犯罪的道路当中,男人很少让我看到顺眼的,让我看到有好感的。我觉得你们男人在外面、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但是在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至少好像是要听我的,而且你要给我钱,而且要听我的。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不是男人啦,根本就不配做男人。在女人面前还不是像一条狗一样,我觉得。
快快:那些男人,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他们很虚伪,反正这些男人没得到你的时候,就求死求活,跪在地下啊,哪怕是哭啊,笑啊,反正想尽办法,都会来的。像狗一样,我觉得,真的。外面么,看上去冠冕堂皇的,都穿着西装怎么样,说起来还有的是经理啊,有的是什么当官的。哦,想想他们在床上这些,真的……基本上就是我摆平他们的。
谈论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自尊”,“自尊”就只能是——也必须是一种个人对于自己是否尊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它是如此高度私人化的,或者说是具有如此高度的私人性,乃至任何他人不是站在当事人立场上的评判都有可能是对“自尊”的曲解乃至亵渎,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曾认为并继续认为性服务妇女就“失去尊严”、“没有尊严”的妇女,性服务妇女的性服务过程就必定是“失尊”、“无尊”的过程,没有认识到或全然不理解有的性服务妇女其实有强烈自尊感的妇女,有的性服务妇女就是在性服务过程中获得了自尊、强化了自尊。
性服务妇女在性服务过程中营建了一个自尊的私人空间,体验着属于自己的“自我尊重”,这无疑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即:(1)这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一种自尊。这一自尊甚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2)这是一种职业的自尊。这一自尊可以追溯到性服务妇女是唯一职业妇女的古代。(3)这是处于妇女性别群体中的下层/底层者的一种自尊以及抗争。在此,阶级/阶层的对抗打碎了“姐妹情谊”之类的女性主义神话。(4)这是作为劣势性别群体的整个妇女群体的自尊以及抗争。在此,作为进行性别压迫和剥削的优势性别群体——男子,遭受到妇女针对男子的挑战和反击。(5)这是阶级/阶层的自尊以及挑战、反击和挤压。这一阶级/阶层除了个体自身所属的外,也包含着家庭的阶级/阶层归属。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对某些性服务妇女而言,性服务也内蕴着某种自尊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
性服务妇女的这一自尊空间所具有的如此高度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使得我不得不以“次空间”加以命名:它有别于主流认同、可以共享共有的公共自尊空间——“主空间”,是遭主流排斥、十分个性化的私人自尊空间:“次空间”。借助于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和加塔里(Felix Guattari)在《卡夫卡——迈向一种次文学》一书中对次文学特点的界定,[7]作为一个理空间的性服务妇女的这一自尊“次空间”至少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这一次空间并非建构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是由少数社群/个体在主流社会中营建起来的;第二,主流、公共自尊空间与社会认同相关,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次空间则基于个人的私人的感受,只接受和安放具有主体性的自我尊重体验;第三,这个次空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凝集成集体空间,从而具有某种集体价值。只是这一集体只是存在于主流社会,并不属于这一或那一主流;第四,相对于主流自尊空间而言,这一次空间是一个他者的空间。作为两两相对的他者,没有主空间就没有次空间,它在他者之地是生存,在他者之地流浪,在无价值之中显现自己的价值,“他者化”就是它存在意义;第五,这一次空间只属于个人和私人,只属于隐蔽/非公开和自我,一旦它成为公共体验,它就消融为公共空间——主空间而不复存在;第六,这一次空间并非无中生有,它诞生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并以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主空间内部实施着抗争和革命。
从将“自尊”视为一种个人的、私人的、自我的心理体验出发,认识到日常生活中自尊次空间的存在,一种关于自尊的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由此得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具有了社会议题的涵义,生长起社会研究对象的理论价值:对于自尊的研究将不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而落地成为对日常生活的探讨,深化为对个人的非公共/公开的自我心理的探索。这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原本更受忽视和被曲解的沉默者(如底边人群)和沉默的声音(如边缘人群的话语)当是更为有利的。
进一步看,当“自尊”重新认知为日常生活中“自我尊重”的一种私人体验时,对于上流社会中尊贵者们的某些越轨乃至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有了基于当事人立场的新的解释。以屡见不鲜的官员性消费为例:当这些官员只有在性消费而不是官场的权力运作中才能获得自我尊重的私人体验(如雄风犹在、宝刀不老之类)时,性消费作为他们营建的自尊私人空间的重要性难免大大提升,而主流社会自尊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则降低了。可见,有关自尊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的研究是可以推广至所有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只要个人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这双重属性,个人的自尊就必然具有公共体验/公共空间和私人性体验/私人性空间这双向维度;只要社会具有集体性和个人性这双重意义,自尊的公共空间中必然内含自尊个人空间,个人的自尊空间必然社会的自尊空间中凝集和实施自己的张力。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认为:“一切行动都有从其自己本质而来的它的方式和方法;每一生命行动都有它自己的原则……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进入一个陌生世界……这些原则将成为最迫切需要的。如果我们自己能构造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将——虽然只是逐渐地和困难地——领悟陌生现象,理解陌生精神的世界和推测它们的深层意义。”[8](P1)以对性服务妇女性服务原则的确定和实施为切入点,本研究在对自尊的私人空间和私人体验的探究中,所遵循的一大基本原则就是当事人立场。即,通过换位思考、开放心理疆界,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原本隔离的两个心理空间之间搭建一座对话的桥梁,并努力以当事人的思路来感知、了解和理解当事人的理念,进而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作出尽量接近当事人生活世界和生活原则的解释。而这一原则对于非主流人群(如边缘、底边人群)非主流行为(如违法犯罪)、非主流化生存(如底边生存状态)等溢出主流社会而存在的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当具有较大的适用性和阐释力。(11)
当然,也恰如弗里德里希·阿斯特先生进一步指出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任何精神性东西的原创统一和等同,没有所有对象在精神内在的原始统一,那么,所有对陌生世界和‘其他’世界的理解和领悟完全是不可能的。”[8](P2)用弗里德里希·阿斯特先生这段解释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如何理解古代精神的论断,对作为“他者”的我们若要理解和领悟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人有关自尊的心理空间或“他人”的世界——他人对于“自尊”的私人体验,也必须要有与研究对象在精神上的内在原始统一,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这一精神上的内在原始统一又需是“精神性东西的原创统一和等同”。
于是,诠释学作为一种认识和理解陌生世界/他人世界方法的终极关怀成为本研究最后的一个关注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人类的生命存在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生命个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而生命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又必须/不得不以表达(包括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为唯一途径。“表达与被表达者的关系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表现的多样性与作为这种多样性之基础的内部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使我们去考虑不断变化的环境。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从个别生命表现到生命关系总体的归纳推理。”[9](PP93-109)“生命存在于体验表达的本质中”,“表达将生命从意识照不到的深处提升出来”,通过表达,“在知识和行为的边缘处,产生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生命似乎在一个观察、反省和理论无法进入的深处袒露自身。”[9]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精神,正是这一原始精神将研究者作为他者和性服务妇女作为自我的“自尊”这一生命——生活体验和生命——生活表达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认识论上的“内在原始统一”,使有关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成为可能。而也正是从这一原始精神出发的对他人生命——生活及其表现/表达的尊重和理解,使研究者能够突破自身“此在”和“此知”的疆界,进入研究对象,尤其是底层和边缘人群的“自尊”的“此在”和“此知”之中,被研究对象的心理空间接纳,认识和了解/理解了有关自尊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的“能在”和“能知”。
通过对他人生命——生活及其表现/表达的尊重和理解,研究者挣脱了“他者”的桎梏,跨越了主流思维的局限,以当事人的眼睛,认识了一个底层人群用于捡拾和安放自尊的次空间,领悟到一种底层人群有关自尊的私人体验。从此,任何他人对于当事人“自尊”的评判或多或少都具有强权的含义,而当事人将成为自己自尊与否或多少的裁判。
本文在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获一等奖。
注释:
①个案受访者。她告诉我,她出生时,父母希望她一生快乐,所以给她取了“快快”这一小名,她希望使用她的访谈资料时,用“快快”之名标示姓名。
②对于以性服务交换钱物的妇女,常见的称呼有:“娼妓”、“妓女”、“暗娼”、“卖淫妇女”等。我认为这些称呼是一种道德批判先行、具有性别双重标准的称呼,也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和结果。由此,我以“性服务妇女”这一名称对这一人群进行重新命名。拙作《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的命名》一文(《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对此有较深入的分析。
③本文所用的访谈资料基本来自于该项目。该访谈在1998年7月进行,被访者为以年龄、职业、婚否、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指标选择的不同类型的因从事性服务而被送教养、愿意接受访谈者,计41人;访谈者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
④借用乔健教授有关“底边阶级/社会”的概念。在乔健教授的概念中,“底边阶级”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及边缘的群体,他们所属的社会便是“底边社会”。底边阶级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构成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阶级体系的一种重要基础。不了解它们,便不能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全貌、不同阶级间的互动以及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http://www.ncp.com.tw/product_show.php? sid=1189062753.
⑤洪汉鼎:“编者引言:何谓诠释学?”载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原注:R.E.帕尔默(Palmer)在其《诠释学: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美国西北大学版,1982年)中提出诠释学的六种界定:1.圣经注释理论;2.一般文献学方法论;3.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4.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5.存在和存在理解的现象学;6.重新恢复和破坏偶像的解释系统(中文读者可参考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附录)。我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诠释学的六种性质规定,与帕尔默的差别主要在于最后一种规定。帕氏主要根据保罗·利科尔的观点,而我主要依据伽达默尔的观点,我认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应当说是20世纪诠释学的最高发展。
⑥如,一位被访者告诉我们,在她所在的城市,性服务妇女就分为“国家队”(以境外人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省队”;“市队”;“区/县队”(分别以外省、外市、外县来该市经商、旅游、出差、途径者等为主要服务对象);“街道办事处”(基本以低收入者、无业失业者为服务对象,并且,与前四者的服务地点基本或大多为宾馆、旅社、出租房、舞厅/歌厅等室内,每次服务收入在200—800元不同,这一层次的服务地点不少为公园、路边树丛等室外,每次服务的收入为20—100元,故被称为“街道办事处”)。
⑦在20世纪80年代初,商业性性交易在中国大陆“死灰复燃”时,“买方”和“卖方”均处于无序状态,大多是具有随遇性的“引买”、“引卖”,较少有某种层次的划定和规定。到80年代中期,“买卖”双方开始逐渐层序化,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性服务妇女与服务对象间实现某种层序化分层。
⑧诸多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性服务妇女来自社会阶层中的底层,包括出身于底层和处在底层:其地区身份以农村人为主,职业身份以服务员、农民、失业者、无业者为主。对性服务妇女的这一人口学特征,笔者在《新生卖淫妇女的构成、特征及行为缘起》(与徐嗣荪合作,《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和《商业性性交易者的性别比较分析》(与高雪玉、蒋明合作,《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两文中也有详细的分析。
⑨莎伦·马库斯著、朱荣杰译:《战斗的身体,战斗的文字:强奸防范的一种理论与政治》,载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个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需求可以追溯到当事人个人或/和家庭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如,多数绝对贫困者、相对贫困者就是来自贫困山区/农村,或城镇中的贫困家庭,但除了这一初始化的贫富差距外,性服务妇女个人的经济收入更主要的是由其“工具化”身份被男人认可、接受的程度所决定的。这一“工具化”主要是“性工具化”(不仅是性交工具,包括作为性观赏、游戏、情感慰藉的对象),也包括“家务劳动工具化”(即使包养者提供全套服务中的保姆、厨娘之类的家政服务)。被男人认可、接受程度越大,男人支付的服务费用越多,性服务妇女也就收入越多,在性服务提供中的经济迫切性越低。
⑩该访谈由本项目组成员、四川社会科学院的马林英副研究员在四川进行。
(11)在对被拐卖/拐骗妇女——底边生存人群之一进行的研究中,我运用了这一原则,从而提出有关被拐卖/拐骗流出的新观点,以及有关“打拐”转型为“反拐”的对策建议。详见王金玲:《地方性行为、当事人立场与公共政策指向》,《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