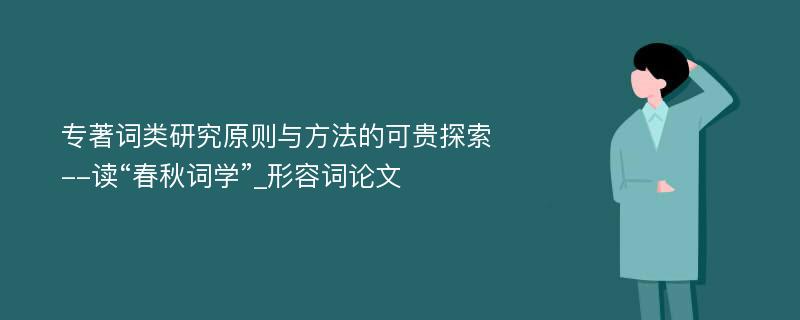
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的可贵探索——《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类论文,可贵论文,春秋论文,读后论文,吕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 (2001)01—0055—08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殷国光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现在在国内古汉语界从事专书语法研究的学者很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而对专书的词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这却是第一部。由于词类问题是专书语法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尚缺乏可以借鉴的先例,因此这本书对古汉语语法学界有着普遍的参考价值。它所提出的关于专书词类研究的一系列原则、方法,乃至具体操作,都具有启发作用和创新意义。
本文想通过讨论该书的特色,着重探讨该书所运用的原则和方法。因为我觉得这样更便于参照,便于借鉴。
一
作者善于运用穷尽的量化的方法对词类的性质与功能特征进行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下文简称《吕》)词类系统的框架,本书并未另起炉灶,而是沿用了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分类及名称。这种沿用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对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进行了严格的检测。为了进行这种检测,并在检测之中确定《吕》的词类系统,作者采用了穷尽性的、量化的研究方法,对该书5153个词一一归类,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数量统计。书中的各项结论都尽可能以量化的语言材料作为依据,再配合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将在下面讨论)综合进行研究。考察结果表明,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是符合上古汉语的客观实际的。
通过作者的上述检测,使人们对词类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上都推进了一步。比如作者把《吕》的词类划定为11大类,其中实词7 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虚词四类: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关于作者对实词和虚词的分类大家是否同意自然可以讨论,但这总算是一家之言。这11类词在《吕》词汇总量中各占数量多少?相互比例如何?出现频度又是怎样?(注:频度指单词平均出现频率。)知道这些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各类词在词汇总量中的位置和作用。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全面的统计,通过下面这样一张表格(该书p21),一目了然地告诉了读者:
统计内容词量① 占总词量频度
(出现频率)百分比
名词
3369(26027)
59.5% 7.73
形容词 571(5572)10.1% 9.76
动词
1418(23994)
25.0% 16.92
实 数词 24(1646) 0.4% 68.58
词 量词 21(105) 0.4% 5.00
代词 40(6176) 0.7%154.40
副词133(7160) 2.3% 53.83
介词 22(3237) 0.4%147.14
虚 连词 35(4772) 0.6%136.34
词 助词 23(9793) 0.4%425.78
叹词 7(27)
0.1% 3.86
①兼类词按类分别统计,故表中总词量为5663个,超出数字为兼类词重复计算部分。
由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吕》的实词占词汇总量的98.5 %, 频度为12.68;虚词占词汇总量的1.5%,频度为204.93。明显地表示了实、虚词在数量和频度上的巨大差异。同时通过这个表格,我们不仅全面看到由各类词编织成的词汇总体,同时也看到各类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只是《吕》一本书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何况在同一时期更多专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就能看到这时期词类的比较清晰的全貌。若没有专书语法研究,这一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又如:名、动、形三大词类充当句子各种成分时的词量、频率、占该词类总数百分比的统计(该书P28),使我们对这三大词类的特点、 性质、功能有了远比过去具体、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举这么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者在穷尽性、量化的基础上,对各类词的性质和功能都有进一步的剖析和刻画,决不仅是照搬前人的框架而已。作者善于运用计量语言学这一工具去解释语言现象,由于书中的各项结论都以量化的语言材料作为依据,因而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二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着重描写词的大类内部存在的语法功能差异和语义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着眼于同一大类的词在入句之后呈现出的不同变化。在这方面反映了作者在词类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较强的语法观念,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下面我们举例来谈:
2.1 名词
(一)作者提出名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征是“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能力存在着差异”(P37), 这是作者在对名词各小类的修饰语进行穷尽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的。作者先分别举例以说明问题,然后对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情况作了全面统计,列了一个很清楚的表(该书P40):
修饰语类别 名 词代 词数词
形容词
名词中心语小类
普通名词 名[,普/专/方/时] 代[,人/指/疑]70 111
160(1396) 72(371)
(713) (1170)
专有名词 名[,普/专]代[,指]6(7)5(6)
121(265) 3(3)
方位名词 名[,普/专]代[,人] 0
0
14(118)
1(1)
时间名词 名[,专/时]代[,指] 8(162)
10(84)
7(35)
4(121)
修饰语类别动 词 数量短语
名词中心语小类
普通名词
6513
(190) (38)
专有名词
0 0
方位名词
0 0
时间名词 3(5)
0
统计结果表明,普通名词可自由地直接受各小类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词、数量短语修饰;而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则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仅反映在直接修饰语的类别上,而且也反映在频率上。作者把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和他类词语修饰的能力排列如下:
普通名词>时间名词>专有名词>方位名词(>这里读作“优于”)这就使我们明确了名词内部各小类在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异;反过来看,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是区别各小类的一个条件。
(二)在分析名词主语与谓语的关系时,作者指出,名词各小类作主语,对谓语的选择存在着很大差异:普通名词、专有名词作主语,充当谓语的可以是名词、形容词,也可以是各小类动词,如动作动词、心理动词、关系动词等。而方位名词、时间名词作主语,其谓语不能是动作动词、心理动词;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方位名词就临时转类为普通名词。如:
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淫辞)高诱注:前人倡,后人和。这表明,方位名词、时间名词作主语,其谓语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方位名词、时间名词作主语是不自由的,而普通名词、专有名词作主语是自由的。
2.2 形容词
(一)形容词活用作动词的考察
作者首先指出,《吕》中,状态形容词不能活用作动词。(注:状态形容词表示情状,带有明显的描写性,如:逍遥、殷殷、苍狼等。)性质形容词活用作动词的共71个(139例), (注:性质形容词单纯表示属性,如:大、小、深、浅、坚固、安宁等。)其中复音词仅见1 例。通过穷尽的分析和统计,作者指出,“形容词活用作动词以使动用法最为常见,其次是意动。还有少数既非使动,又非意动。(注:如:太公之所以老也。(正名))”这使我们对形容词的活用在量上有了一个总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多数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只有一种语义(或使动,或意动,或其他);但有少数形容词(共14个)活用作动词有使动、意动两种意义。如:
高:高节厉行,独乐其意。(离俗)——使动
虽死,天下愈高之。(离俗)——意动作者指出,形容词内部活用的差异,大体可描述为:
活用作名词:复音性质形容词>单音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
活用作动词:单音性质形容词>复音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从而看出,活用作名词,复音性质形容词最占优势,而活用作动词,则首数单音性质形容词。
(二)形容词兼类的考察
作者在穷尽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状态形容词未见兼类现象。性质形容词兼他类词的(共183个)约占形容词总量的32%,比名词、 动词兼类词所占比例都高。(注:名词兼类词占该词类总量的10%左右;动词兼类词约占26%。)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颇有独到的见地:“无论从历史的来源看,还是从共时的功能看,名词和动词都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犹如两极,而形容词正处在两极之间,既有与名词相通的功能,如直接充当定语,又有与动词相通的功能,如充当述谓中心语。因此在汉语的历史演变中,处于两极的名词、动词,其词义易于向中间地带引申,引申出形容词词义。反之,处于中间地带的形容词,其词义也较易于向两极引申。这种历时的演变反映在周秦之交的汉语层面上,就是形容词一词多义现象较为普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词多类现象较之名词、动词更为普遍、更为突出。这也形成周秦之交汉语形容词的一个特点。”(该书P108—109)
2.3 关于动词, 我在这里只想举出作者对动词的一个小类“兼语动词”及内部差异的分析作为代表,因为我觉得这种分析细微深入,很能说明问题。作者指出,《吕》中能充当兼语结构中动1 的兼语动词共9个:请、使、令、趣、劝、召、命、谓、有。 他们的内部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大部分兼语动词(请、使、趣、劝、召、有)处于“动1 ·名·动2”格式中动1的位置时,只能构成兼语结构;小部分兼语动词(令、命、谓)处于“动1·名·动2”格式中动1的位置时, 除能构成兼语结构之外,还能构成非兼语结构。
(二)兼语动词对动2的选择范围大小不同。据此, 兼语动词可分三小类:(1)“请”、“谓”、“劝”、“召”、“趣”5个词构成兼语结构时,动2只能是表示动作变化的动词。(2)“命”构成兼语结构,动2可以是表示动作变化的动词, 也可以是非表动作变化的关系动词。(3)“使”、“有”、“令”3个词构成兼语结构时,动2 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
(三)兼语动词所带的兼语位置固定在兼语动词之后,唯“请”的兼语偶尔移至“请”之前。
(四)兼语动词未构成兼语结构时可以比较自由地受否定副词的修饰,一旦它们带上兼语构成兼语结构之后,兼语动词受否定副词修饰的功能则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反映在三方面:(1)出现频率极低, 《吕》中兼语结构共出现417例,兼语动词受否定副词修饰的仅见7例,不到总数的2%。(2)否定副词仅限于“无”、“毋”、“不”3个, 都表示禁止之义。(3)受否定词修饰的兼语动词仅见2个:“使”(6 例)、“令”(1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在对各类词内部存在的语法功能和语义上的差异上下了很大功夫去发掘和描述。其中对各种句式从多角度进行比较、观察是很重要的方法。此外,还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如:名词活用的考察(P66—68),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的比较(P77—95),数词计动量两种位置的比较(P200—203),量词对数词的选择(P226—229),数量短语与指称计量对象的名词的位置及结构关系(P233—236),对[B之谓A]与[B,A之谓]的比较(P356—358)等,不及一一详述,请大家自己去欣赏。
三
在词类内部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再分类,逐步深入地探讨其特点,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在这一部分,我想以作者对动词的分析作为代表。
正如作者所说,动词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再分类。首先,作者从宾语的语法意义的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由高层次向低层次对动词进行分类。先把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大类:不能带宾语或只能带准宾语的是不及物动词;能带真宾语的是及物动词。(注:准宾语包括关系宾语、非关系宾语(使动宾语、意动宾语、主题宾语等)。真宾语主要为受事宾语,此外,还包括准宾语之外的其他宾语(存现宾语、等同宾语、似类宾语等)。)
接下去作者又对不及物动词进行再分类:不可带宾语的动词为真自动词,可带准宾语的动词为准自动词。准自动词根据所带宾语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类:甲类,只可带关系宾语;乙类,只可带非关系宾语;甲/乙兼类,既可带关系宾语,又可带非关系宾语。甲类准自动词根据所带关系宾语的语义又可再分为三小类:甲1类只带处所关系宾语;甲2类,只带对象关系宾语;甲1/甲2兼类,既可带处所关系宾语,又可带对象关系宾语。
对于甲1类和甲2类准自动词,作者又运用变换的方法加以区别:甲1类的宾语只能变换为介词“于”、“乎”的宾语, 变换后的介宾短语的位置只能在动词之后,如:
谏静郭君→谏于静郭君 [谏于简公。(慎世)]
畏鬼→畏乎鬼 [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用众)]而甲2类准自动词的宾语,少数还可以变换为介词“为”、 “与”的宾语,变换后的介宾短语的位置在动词之前:如泣之→为之位;盟之→与之盟。
同时,对于乙类准自动词,作者根据非关系宾语与动词间的不同语义关系,把宾语分为使动宾语、意动宾语、主题宾语三类。据此,又进而把乙类准自动词分为四小类:乙1类,只带使动宾语;乙2类,只带意动宾语;乙3类只带主题宾语;乙1/乙2兼类,兼带使动、 意动两类宾语。这三小类内部的相互差异表现为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变换:
乙1类:[动·使动宾语]→(致使)·兼语·动
乙2类:[动·意动宾语]→(意谓)·兼语·动
乙3类:[动·主题宾语]→主·动
在对不及物动词进行分类后,作者又对及物动词进行再分类,根据所带宾语的差异,分为二类:只带真宾语的为真他动词;在同一义项之下,既可带真宾语,又可带准宾语的为准他动词。
根据真他动词与宾语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又可分为4小类:(1)只带受事宾语;(2)只带非受事宾语(包括存现宾语,似类宾语, 等同宾语等);(3)只带处所宾语;(4)兼类真他动词,可以带上述二类宾语。
准他动词既具有及物动词的特点,可以带真宾语,又具有不及物动词的某些特点,可以带准宾语。据此,作者把准他动词又分为二类:一类准他动词,可以同时带两类宾语,构成双宾形式。第二小类准他动词,可以分别带真宾语和准宾语,但在《吕》中未见带双宾语。(注:这类准他动词存有带双宾语的可能,有些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带双宾语,如:“予、语、食、衣”等,但大部分在先秦其他文献中也未见带双宾语。)
在作了以上分析后,作者好似作总结一样,对《吕》动词的层层分类作了一个总表,逐层都有统计数字和例词,使人一目了然(详见该书P136)。
然而,对动词的分类并未到此结束,除了从宾语的语法意义的角度分类外,作者又从宾语的语法性质的角度把动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体宾动词,共786个,只带体词性宾语:一类是谓宾动词,共137个,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作者拿它们与从宾语的语法意义的角度划分出的动词小类进行比较,发现两套分类之间有某些对立互补的关系。(详见该书P138—139)
在讨论了动词不同角度的再分类之后,作者又在“关于几个特殊的动词小类的探讨”大题之下深入讨论了双宾动词、兼语动词、助动词、关系动词。
通过作者对动词所作的多层次的再分类及从多角度所作的讨论,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着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作依据,有着新鲜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十分注意不拘一格地借鉴前人的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有选择地加以运用,从中显示出在方法上的向前推进和个人特色。
四
作者如何判定在《吕》中出现频率极低的那些词的词性?
在专书研究中,自然应当把该书的词类系统看作一个穷尽类系统,该书的全部词都应包括在这个系统之中。因此,作者必须判定《吕》中每个词的词性,将它们一一归类,这在具体操作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低频词的归类问题。因为考虑词的归属首先需判断该词在《吕》中显示的意义是该词的基本词汇意义,还是临时意义?该词在《吕》中实现的语法功能是该词的常功能,还是暂功能?这本来主要是靠数频显示的,因为数频常常为我们提供可以把握的相对稳定范围。但对那些出现频率极低的词,就难于判定了。作者为解决这一难题,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以与《吕》时代相近的先秦其他九部文献作为参照、比较的依据。(注:九部文献是:《论语》、《左传》、《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公羊传》、《谷粱传》。)比如“轮”、“豆”、“弁”在《吕》中都只出现1例:
天地车轮。(大乐)。高诱注:“轮,转。” 大庖不豆。(贵公) 庶人不冠弁。(上农)从句中用法观察,“轮”、“豆”、“弁”都用作动词。作者考察其他九部文献,“轮”共出现34例,均为名词用法,义为“车轮”。“豆”共出现19例,其中名词用法18例,义为“食器”;动词用法1例, 义为“以豆祭祀”。“弁”共出现8例,其中名词用法6例,义为“皮冠”;动词用法2例,义为“加弁”。通过以上考察, 作者判断“轮”的基本词汇意义是“车轮”,“轮”的名词用法是其常功能;“轮”在《吕》中的“转”义,只是它的临时意义,它在《吕》中这一动词用法只是它的暂功能。作者根据划分词类以词的常功能为标准的原则,把“轮”一词归入名词;同理,“豆”、“弁”也归入名词。
这样归类,虽然有少数词的类别与在《吕》中的表现不一致,但作者认为:1、这样归类是以先秦文献的语言材料为依据的, 符合作者坚持的划分词类以词的常功能为标准的原则;2、 这样归类以语义为基础,更符合人们对“轮”、“豆”、“弁”诸词心理上的认同;3、 对于它们在《吕》中的不一致的表现,可以用词类活用给以解释。
五
提出区别兼类与活用的可供操作的标准。
关于兼类与活用,这是进行专书词类研究无法避免的一个重大问题。作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形成一套原则和方法,可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作者认为,区分词的兼类与活用的标准有二:一是频率标准,一是意义标准。
关于频率标准。作者指出,在言语中“词的临时活用→兼类”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其间的界限显然不大容易把握。既然称“活用”,当属偶然的、临时的语言现象,其出现频率必然不高;反之,出现频率高的“活用”,就该看作是该词的常功能,当属“本用”。如何判断频率的高或不高呢?为了对《吕》的词类系统作量化的研究,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以区分词的兼类与活用。如何确定这一标准呢?作者认为应依据以下原则:一要以《吕》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必要时参考先秦的其他文献;二要考虑到人们语感上的可接受程度;三要从词类系统总的格局考虑。如果把标准定低了,比如以出现1次或2次作为活用的标准,那么,人们在语感上已经认同的一些活用现象,如“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知度)中的“耳”、“目”(在《吕》中作动词各有4次), 便会被排斥在外。如果标准定高了,比如超过10次才不视为“活用”,就又很难自圆“偶然”、“临时”之说。因此,通过对《吕》语言材料的通盘考察、全面衡量之后,作者把出现频率5 次作为区分“活用”与“本用”的标准。也就是说,凡一词的某一词类用法,出现频率达到5次者,就不视为“活用”。这一标准是否带有普遍性,尚有待更多专书研究者进行检验。但必须有这么一个标准,作者才能把《吕》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现象加以量化和区别,并在运用这一标准的过程中检验它的合理性。
需注意的是,当遇到出现频率在5次以下的低频词时, 上述频率标准就无法操作;同时,必须明确,“活用”既然是偶然的、临时的语言现象,其出现频率必低;但不能反过来说,词的某一类用法频率低的就一定是“活用”。因此,同时还必须使用意义标准,并须参考先秦其他文献。
关于意义标准。什么情况下属于词的“活用”现象?如何具体掌握?作者也尝试提出一套标准:由于词类活用是一种共时的语言现象,当一个词(主要指名、动、形三类)在言语中活用作它类词时,该词的意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也随之发生位移,位移后的词义与该词义之间应存在着直接的、有迹可寻的联系,位移的具体情况如下:
指称事物→表示以该事物为对象(或工具等)的动作。如:桑,用作动词,义为“采桑”;耳,用作动词,义为“用耳听”。
指称事物→表示以该事物为量度单位。如,以“鼎”、“镬”之类的容器作容量单位。
表示性状→指称具有该性状的人或事物。如:良,用作名词,义为“良人”。
表示性状→表示使客体具有该性状的动作。如:洁,用作动词,义为“使清洁”。
表示性状→表示认为客体具有该性状的动作。如:拙,用作动词,义为“以为拙”。
表示动作→指称动作者,或动作涉及的对象。如:逃,用作名词,义为“逃亡之人”;亡,用作名词,义为“灭亡之国”。
上述这类位移发生在同一意义层次之上,它们是同一义位的临时变体。如果一个词的词义与其用作它类词的词义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超出了上述词类活用时词义变化的范围,就应考虑排除活用的可能,而把该词归入兼类词。
作者进一步指出,一词多义,乃至由此产生的一词多类是汉语发展至周秦之交的特点,是汉语历时的发展在共时平面的反映。因此区分词的兼类与活用,必要时还得考察词义的历史发展。如“寇”,依甲骨文字形,象一个人拿着棍棒跑进他人的屋内去击打主人的头。本义是动词。《诗经》中“寇”出现7次,6次作动词,义为“抢劫”、“掠夺”;1次为名词,义为“盗匪”。从《诗经》的情况看, “寇”用作名词应看作是活用。《吕》中,“寇”出现27次,26次用作名词,指入侵之敌;1次作动词,义为“劫掠”(贵公)。从频率看, “寇”用作动词又像是活用。作者认为,从词义的历史发展看,“寇”的动词义项是它所固有的,不是在句中临时取得的,因此,“寇”宜看作是兼类词。
作者提出的上述原则和方法都有待在更大范围里实践,检验,讨论。现在还不宜过早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最重要的是作者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这些可供操作、可供讨论、可供修正甚至推翻的模子,为推进专书语法研究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做出了极有意义的贡献。
六
在专书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加以吸收借鉴,或进行讨论、修正扬弃。
作者这种精神和作法在全书随处可见,如在考察方位名词两两连用的组合顺序时,借鉴了陆俭明的《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中国语文,1994.5)。
在对《吕》形容词进行分类时,采纳了陈克炯“非定形容词”(指不能直接作定语的形容词)的称名,(注:陈克炯《〈左传〉形容词的考察和非定形容词的建立》,载《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出版社,1995。)分出非定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
作者以专书研究为依据,也对前人的一些观点提出讨论。如动词章的助动词小类中关于“可”和“可以”的讨论。作者指出,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中说,“可以”和“可”有两点不同:(1 )“可”字后的动词是被动意义的,“可以”后面的动词是主动意义的;(2 )“可”字后面的动词不能带宾语,而“可以”后面的动词经常带宾语。(注:详见《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P339。 )作者考察了《吕》的实情之后说道:“可以”和“可”的区别大体如此,但并非完全如此:(1 )“可”字后面的动词可以是主动意义的(17例),如:“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长见)(2)“可以”后面的动词偶而也可以是被动意义的(6例),如,“黔首之苦不可以加以矣。”(振乱)(3 )“可”字后面的动词也可以带宾语(92例),如:“今可得其国。”(高义)
以上这些与时贤的讨论,无论采纳时贤的结论也好,对时贤观点进行修正也好,都很有价值。只有深入进行专书语法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提出这种有力的论据。
七
本书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区分词类的标准。作者提出“以语法功能为标准,以语义为依据,二者不可或缺,这是我们划分词类的基本原则。”(P11 )但在作者的具体讨论中,没有使人感到“以语法功能为标准”和“以语义为依据”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可以把语义也作为一个标准呢?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有的大类的再分类缺乏科学依据,最明显的是副词,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在研究方法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较多笔墨用在词类内部差异的探讨和描述上,但缺乏一些必要的理论上的概括和阐发。看得出来,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也努力作了一些尝试,但总起来看还显不够。
总起来说,这是一本很有意义并有学术价值的好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专书词类系统的著作。作者对专书词类研究的原则与方法作了可贵的探索,其中颇多启人深思的地方,作者有不少新鲜看法,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