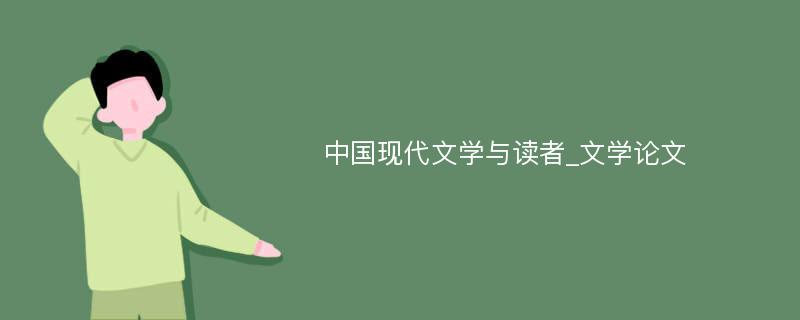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读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读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1—0074—08
尽管自80年代以来就有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倡导和实践,文学史研究因而重新发现了许多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遮蔽的盲点,但总的说来,文学史的重构仍然着重以艾布拉姆斯四元素图式当中的作品、作者和世界三维为考察标准。并不是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读者和接受维度缺乏应有的热情,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但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处理文学史的尝试却显然由于具体阅读接受事实的浩如烟海和随即的湮没无考而难以为继。因而,抛弃纯粹接受资料的堆积,改用某种基于文学与读者交流模式的理论概括之上的历史考察,在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视野中展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景观,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之事。
一、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中的读者
中国近现代文学读者的产生是与近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断裂同步产生的。而这一断裂又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空前变局直接相连。戊戌变法遭到扼杀以后,一部分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创办洋务和维新运动先后失败的经验中,痛切地感受到开启民智的迫切需要。“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随后的“小说界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产生的。这场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和大众思想启蒙的功利目的的文学改革运动,由梁启超在赴夏威夷的船上发端,由于恰好处在20世纪前夕,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象征性起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初的文学观念,其中自然包括全新的读者观念。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以诗界革命为先锋,是否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诗歌仍然据文学的正宗不得而知,但传统士大夫对于诗歌确实是以风雅相标榜,只求在士子阶层里彼此唱和,得一、二知音赏识即可,圈子外的读者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这种贵族取向的趣味以及作者到读者的自我封闭显然无法适应开启民智的需要。因此尽管梁启超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初始,似乎尚未自觉地意识到开拓新的读者群体的必要,但思想启蒙的明确意图,却内在必然地决定了他对读者维度的自然关注。“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 是最可恨也”[1](P189)。诚然, 这无疑是指斥传统诗歌题材与内容的陈陈相因,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痛恨了无新意的诗歌对读者阅读兴味的败坏。读者对作品所展示视野的过度熟知,意味着诗歌发展的停滞与僵化。传统诗歌园地的地力将尽,要想营造新境界更新读者的阅读感受,就必须发现诗歌的新大陆。从文学史看,宋明诗坛以印度意境、语句入诗,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然而,当时的新境界于今又为旧境界矣。梁启超以简约的文字直觉地叙述出文学史中读者视野更迭嬗变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再次构造诗歌新境的必要。而这一次的新大陆却是欧西意境,即为改良现实政治所急需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化精神。
在几天后的同一篇《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在设想中国“文界革命”的图景时,又再次提到了欧西意境,只不过是以日本的德富苏峰为范例。梁启超这样表达自己阅读德富氏的著作所获得的启示:“其文雄放俊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P191) 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清晰路径。同时参考读者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就终极意义而言,梁启超他们提倡文学改革的理论资源源自欧西,但由于在学习西方、向西方求取富民强国之策的路途中,业已存在一个功绩非常显著的先行者——日本。再加以地缘因素,日本成为梁启超及其同志的长期流亡地,耳濡目染,在语言方面沟通无碍,在情感方面认同直如第二故乡。这样,改革的倡导者就更情愿、更容易吸收从日本转口的、似乎已经通过日本现代化实践检验的欧西思想和理论。在这种理论以及文学的旅行和国际贸易中,梁启超们可谓一身数任:他们首先是西方与日本文学的阅读者,然后才是向国内介绍外来文学的输送者,进而成为新式文学的倡导者和创作者。身份的多重性导致了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多重性,简言之,即外国文学之于作为读者的梁启超与作为作者的梁启超的作品之于国内读者。在这两个层次读者的阅读中,由于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为对现代化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期待所遮蔽,他们真诚地自动压抑甚至清空自然存在于他们心中的,由传统古典文学模塑出来的期待视野,对外来文学或改良文学虚怀以待。正常接受中所应有的读者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互交流、相互妥协的过程,被限制在最低限度。也许从读者接受的主动低姿态中,我们更容易解释晚清以后翻译事业的空前兴盛与迅速发展,以及梁启超“新文体”风靡一时的魔力。
梁启超最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思想恐怕要数他不遗余力地抬高小说的地位。小说取诗文的主导地位而代之,几乎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文学领域必然出现的通例。因为,小说所表征的平民化和世俗化趋势相对于贵族文学的等级制而言,具有无可否认的颠覆和革命力量。因此,小说又称“资产阶级的史诗”。改良派的中坚梁启超对小说这一文体情有独钟的事实,再次显示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存在对应关系这一历史的无意识力量。当然,在梁启超的意识层面,他之所以推重小说,却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对读者拥有其他文体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洞察到小说对他们改良群治的事业产生巨大助益的潜在可能。而这种洞察是基于他对读者厌庄喜谐这一人情大例的深刻洞察和体认,基于对读者群体知识水平的估计和判断。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重复了乃师康有为的断言:“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但只要识字的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可以说,小说较诸其它文体具有最广大的读者普及面和影响力的辐射面,因此,小说在中国“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2](P37)
写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3](P3—8)是梁启超在域外政治小说的直接触发下酝酿而成的“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更是同一时期论述文学与读者关系的纲领之作。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梁启超的观点,我们也不得不惊异于梁氏理论的概括力与丰富性。除了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中心主张,强调小说为改变世道人心、移风易俗的必由路径已尽人皆知以外,梁启超的论述涉及小说与读者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已经不满于仅仅用厌庄喜谐这一心理的共性来解释小说感人至深的力量,他认为小说感染读者的深层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小说经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即小说能拓展读者的视野,满足读者超越日常凡俗经验的愿望。其二,小说能将一般读者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处境纤毫毕肖地描摹出来,使读者既产生于心戚戚的认同感,复惊叹于作者完美表达的精湛技巧。能将此二者“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诸文体中,小说为最上乘。具体而言,小说作用读者的方式有四,即熏、浸、刺、提。前两者形象地展现了小说对读者的陶冶之功,读者浸染于小说的意境之中,年深日久,潜移默化。刺着重于表明文本对读者的强烈冲击引起读者情感的激烈变化,变化强度与文本作用力的大小和读者受体的敏感程度相关。提实际上论述的是读者与小说主人公认同的审美现象。读者在阅读想象中与作品主人公合二为一,从而与身处现实的读者主体发生分化,其分化越深,表明读者受感动的程度越深,接受作品的影响亦越大。一般人皆知梁启超夸大小说作用不遗余力,但往往容易忽略他对小说的批判同样不遗余力。因为小说与社会风习、国民性格相表里,故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弊端丛生罪推旧小说,而中国国民性的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缔造当寄望新小说。罪之、贬之,抑或功之、褒之,犹如一币之两面。认识到读者的审美感受具有双重性,对梁启超而言殊为不易,但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亦遍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全部,其偏颇实种因于该理论对文学社会功利作用的片面强调,和对文学审美本质的忽视。自此文既出,后之的种种有关小说的论说,都只是对梁的观点的花样翻新而已。
时时刻刻以对读者进行启蒙的普及为思考的轴心,梁启超在文学形式方面的追求自然以传情达意、通俗平易为鹄的,于是就有诗乐合一和“歌体诗”的主张,以及“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的实践。核心意图就是要冲破中国文学因言文分离而给普通读者设立的接受障碍,努力以言文合一达到文学与读者交流的畅通无阻。
梁启超论述文学之感人常喜用一形象的熏炉之喻。人脑亦类似于熏炉,只不过是一高级熏炉,其区别就在于人脑“能以所受之熏还以熏人,且自熏其前此所受者而扩大之,而继演于无穷。虽其人已死,而薪尽火传,犹蜕其一部分以遗其子孙,且集合焉以成为未来之群众心理”。[4](P510—511)以此来比喻五四前一代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对国内读者进行启蒙,即学即用,且影响连锁扩散的情形,亦未为不妥。在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吹下,诗、文、小说以及当时被包括在小说名下的戏剧,都比照着西方的标准迅速地进行了传统模式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型,形成了创作的全新格局。尤其是在这一变革过程当中取得“最上乘”地位的小说,更是呈现出翻译与创作的全面繁荣。尽管这一近现代文学史的拓荒期主要功绩在于筚路蓝缕、开辟榛莽的奠基工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但在当时,文学作品从主题题材到写作方式的全面更新,却对读者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强烈的冲击。那些固守自己原有的期待视野、不愿作任何调整与更新的守旧之士,面对新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惊为“野狐”,但终究由于其与新的审美感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而遭到历史淘汰。而对于大多数对时代审美潮流采取顺应态度的读者,新文学向他的期待视野提出的挑战越大,他所获得的审美享受就越大,新文学越是展现出鼓动群伦、震惊四海的魅力。“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5](P648) 从对新文学的具体实践持保留意见的严复对梁启超的“新文体”的评论中,我们约略可以窥见当时文学与读者交流顺畅之一斑。新文学的产生培养了新文学的读者。在这些迥异于传统接受者的读者群中,一些年龄更轻的读者将在即将爆发的五四文学革命中扮演主角。他们是周氏兄弟、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文学革命的健将。当时,他们有些已经开始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的尝试,像鲁迅和周作人就是当时译者群体的重要成员,陈独秀和胡适也偶尔向报刊投稿进行文笔的操练,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林译小说以及各类新小说的热心读者。正像有论者指出,前五四文学的一项重要功绩就是培养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6](P5)
当然,理论的设想与具体的实践总不免存在着差距,当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之时,他心目中的理想无疑是有益新民的政治小说,但现实却是重在娱乐的市民小说的喧宾夺主与空前繁荣,梁对之痛心疾首。他在1915年的《告小说家》中说:“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来增加蓰什百”,但“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2](P511)栽下的是丁香,收获的却是洋葱。这是历史的诡计。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小说的主要接受者市民阶级不完全等同于西欧的市民阶级。第二,新小说接受的时代风尚急速转变。当最初的政治热情很快消退以后,读者原先主动抑制住的对旧小说消闲娱乐功能的期待就获得复萌的机会。当然,小说挣脱人为的预设,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并不意味着梁的倡议完全告吹。事实上,即使是哀情小说如《玉梨魂》者,其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控诉也为五四新文学的读者接受主张婚姻自主的小说提供了情感准备。
二、文学启蒙对读者的影响
今天我们重新对比1917年发端的文学革命与世纪初的三界革命,自然会发现在提倡白话和输入西方新思想方面,两者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精神血缘。但当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除了承认少数几部实写社会情状的晚清白话小说以外,其余文学遗产皆被目为封建谬种,归入应被扫除之列。这其中除了五四一代强烈的弑父意识外,还由于晚清文学的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过渡形态也确实容易遮蔽自身蕴涵的革新因素。尤其是新小说堕入鸳蝴一路、文明新戏蜕变为庸俗闹剧之后,晚清文学在后继者眼里也确实乏善可陈,需要另起炉灶别创一个具备更完整的现代形态的新文学了。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是以这种面对废墟的姿态部分重复着前人的文学主张,破梁启超之所破。仔细分析著名的胡适“八事”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有几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以彼此补充而阐幽发微。首先,陈腐的古典文学与迂阔的国民性相表里,因此,就服务于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言,文学革命的发生势所必然。胡适认为,传统文学中无论老少强作悲音的无病呻吟造成整个民族暮气沉沉,使作者“促其寿年”,读者“短其志气”。陈独秀则曰,古典文学内容“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以及个人之穷通利达”,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其次,古典文学体式僵化,导致了阅读感受的麻木。胡适深恶古典文学专以模仿古人为能事、满纸滥调套语,因而大声疾呼“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竭力捕捉、赋形时代新鲜的审美感受。陈独秀则强调文学要“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此外,两人都从读者的角度着眼,认识到文学语言平易畅达的必要。陈独秀断言艰深晦涩的古典文学“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胡适罗列不用典的原因之一就是“僻典使人不解”,文学的抒情达意“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7](P262—267)
当然,五四一代重新清理地基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准备对前辈的业绩进行扬弃与超越。在梁启超他们开一代风气的基础上,五四一代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在深入和准确两方面均达到了前辈无法企及的高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是欧风美雨的直接沐浴者,因此他们对创建现代新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体裁形式方面,都有了更清晰的设计和理想。相对于梁启超一代的普遍不谙外语,以及对文学实际功用由于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而造成的无限夸大,新一代的文学革命者在保持大众启蒙维度的前提下,侧重于文学本体特点,校准了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的目标。同样是认识到中国文学“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五四一代在引进西方思想和文学样式的过程中却没有了前辈那样的不加选择和生吞活剥,提出了“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8](P318),取法乎上。换言之, 五四一代仍然是以西方为自己的参照系,但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接受过程中,全新的接受视野已经使他们拥有足够开阔的胸襟和气度采取“拿来主义”。
鲁迅的“拿来主义”典型地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阐释学立场。“第一要义”是存国保种,这就为文学革命的先驱阅读、选取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话提供了现实的标准。具体而言,外国文学的译介,旨在帮助读者认识现实人生,因而当务之急不是文学史式的系统介绍以供研究之需,而是移译贴近读者现实人生因而“不得不读”的近代作品。其中,俄国与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由于与我们的反抗和呼叫同调而尤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正如茅盾所言:“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不过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9](P67—68)着眼于前一半的目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将西方历时数百年发展产生的文学流派共时地引进来,广泛借鉴,为我所用。立足于后一半,他们秉承梁启超的“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的精神,引进“科学”、“民主”的观念,在用人道主义“辟人荒”的基础上,大力宣传平民精神,提倡个性主义。
形式和内容兼备现代特征的新文学由于“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10](P22),激动了一代青年读者的心。从而也发挥了影响读者、 模塑国民性的现实效能,起到了为新文化运动引导先路的作用。“读者的文学经验成为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的组成部分,预先形成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从而对他的社会行为有所影响。”[11](P177)这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文学对社会的造型功能或曰“审美向习俗的流溢”,它通过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和谐”,分别从审美和伦理两个方面作用于读者和社会。在审美方面,文学“通过为首先出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新经验内容预先赋予形式而使对于事物的新感受成为可能”,“预见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为新的欲望、要求和目标拓宽有限的社会行为空间,从而开辟通向未来经验的道路”;在伦理方面,文学可以通过对读者期待视野中关于生活实践及其道德问题的期待作出新的回答,从而强迫人们认识新事物,更新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把“人从一种生活实践造成的顺应、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11](P179)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通过狂人那一固执的发问“从来如此便对吗?”对读者期待视野中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期待发出强烈的质疑,从而用现代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取代了吃人的封建道德。对现代文学的读者而言,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的新经验,是在一批像鲁迅的《伤逝》这样的作品中首先赋形的;强调个性独立不羁、自我空前膨胀的新感受,是在创造社作家的诗歌和小说中较早获得表现的。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问题小说直接从易卜生的问题剧获得灵感,与读者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未来可能性,从而开辟走向未来之路;自叙传小说借鉴日本的“私小说”,大胆袒露作者的“病态心理”,对传统道德的矫饰习惯进行挑战,同时又为其后的“莎菲”们自剖女性心理拓宽了狭窄的社会心理空间;乡土小说则通过对农村几千年积存下来的落后风俗的展示,让读者清醒地看到习焉不察下的骇人听闻。文学启蒙的传统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被一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不合时宜地继承下来,在40年代的国统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自由主义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的那些全方位、全景式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各地域、各个社会阶层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都得到了全面的探讨。综观整个现代文学的30年,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典型地体现了“审美向习俗的流溢”。当接受了新思潮洗礼的现代女青年渴望冲出封建家庭、追求个性和妇女的双重解放的时候,娜拉出走的文学经验就转变成了新女性们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的一部分,成为她们选择、设计自己道路的第一参照。庐隐的海边故人、丽石,丁玲的莎菲,都是现实的娜拉们在女性作家笔下的投影。这一投影甚至延续到《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的出场。正是出于对这种“流溢”的负面影响的警惕,鲁迅先是在讲演中探讨娜拉出走以后的可能,继而在小说中演示出走的续集。娜拉流溢到男作家手中,就演变成了或颓唐或昂扬的曾文清和高觉慧。
三、革命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中读者的嬗变
从20年代开始,紧接着文学革命,现代文学史上又出现了革命文学运动。就文学功用的现实指向而言,革命文学与前两次的文学革命一脉相承,但显而易见大大加强了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他们的感情,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12]革命文学的鼓吹者大多不是文学家,而是革命者和理论家,现实社会的激荡使他们不满足于文学精神启蒙的长远功效,转而追求文学修辞作用的立竿见影。对于这种工具论文学观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倒退和偏差,历来文学史家多有检讨。有意味的是,这种带有明显偏差的文学观在现代文学史上却屡屡由于现实的合理性而延续不断。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救亡文学、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蔚为传统。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考察,这种文学的现实合理性也许就表现在读者与这些作品联想式认同的交流模式上。殷夫的代表作《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联想式认同交流模式。“我突入人群,高呼/‘我们……我们……我们’/呵,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那种个人融入集体的狂喜并不仅仅限于作者一己之感受,而是作者召唤读者共同参与到庆典般的仪式中,成为阶级和民族解放庆典中的一个角色,彼此心心相印。联想式认同的交流模式最利于文学在那些民族伟大和苦难的时刻发挥出团结人们和衷共济的作用。在这些时刻,作者和读者都不会或无暇苛求文学自身的纯粹性。正与联想式认同交流的原始范本远古集体歌舞歌诗舞乐混融合一相似,革命文学在形式上也体现出诗、歌、话剧等多种文学样式相互渗透的特点,如提倡“民族化”,创作歌谣化的“大众合唱诗”和街头剧等,目的皆为增进文学与接受者交流的效果。
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这一文学传统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又直接指导、规定了其后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它也是专门论述文学与读者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献。因为它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学“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即文学与读者的问题。当然,它的不可动摇的前提是工具论和服务论的,文学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讲话》关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论述至关重要的有两点,其间表现为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一是普及与提高。文学作品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向他们普及文学艺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二是要求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作家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立场进行艰难的调整与转变。之所以要求文化程度高的作家一方趋近文化程度相对低得多的读者一方,大概因为只有从立场感情一直到语言习惯都彻底全面地“大众化”[13](P370—385), 才能完全保证作家经由作品与读者的交流,有效地获得化成一片的联想式认同效果,从而也从根本上确保文学艺术这一“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恰如其分地平稳运转。当然,具体的创作总是比理论主张更为丰富和复杂。在赵树理那些从语言到思想情感都与农民同化的堪称“打成一片”典范的作品中,仍然可见五四思想启蒙的余绪,是五四问题小说的农村版。
现代文学也是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体制的大输入和大实验,现代文学的创造者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在外国文学中汲取与自己性之相近的养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代主义思潮和技巧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了知音。在鲁迅的作品中,读者可见较明显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与尼采哲学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学说为郭沫若、郁达夫这样的创造社作家所赏识;20年代初,在法国学习雕塑、直接接受巴黎象征主义艺术氛围熏陶的李金发以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的诗人姿态出现在诗坛上,同时带动了穆木天、冯乃超和王独清等人的诗歌创作;30年代,施蛰存和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团结了当时中国各路所谓“现代派”作家,他们是:成功地将象征主义诗艺中国化的诗人戴望舒,借鉴日本的“新感觉派”写作手法,反映上海都市市民生活的“新感觉派”小说作家穆时英和刘呐欧,京派作家中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以及诗人梁宗岱;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特殊环境中,又活跃着一批切磋现代主义诗艺的师生,其中著名的前辈诗人冯至、卞之琳和后来的“九叶诗人”的艺术影响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至于现代主义因素渗入艾青、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创作,更是数不胜数。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现实主义占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给读者带来了面目一新的审美享受,忧郁颓废的现代情绪、精神分析的变态心理,象征主义意象表达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意义阐释的多义与复杂,“新感觉派”小说的“蒙太奇”和通感手法的运用,无不向中国读者追求明晰连贯的阅读习惯提出严峻的挑战,强迫读者充分调动审美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参与作品意义的阐释和生成。将读者包括在创造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中,这是现代美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对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的直接总结。遗憾的是,由于现代中国血火交迸,实在无法长期给现代主义艺术提供宁静的田园和适宜的土壤,现代主义这一奇葩仅仅昙花一现。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种子一直深埋在地下,等待着另一个现代主义艺术繁荣期的来临。从这一角度,应该说,文革后期朦胧诗的迅速崛起和新时期文学现代派实验的一呼百应,都只是文学史另一轮循环在新的高起点的重新开始而已。
来稿时间:1999—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