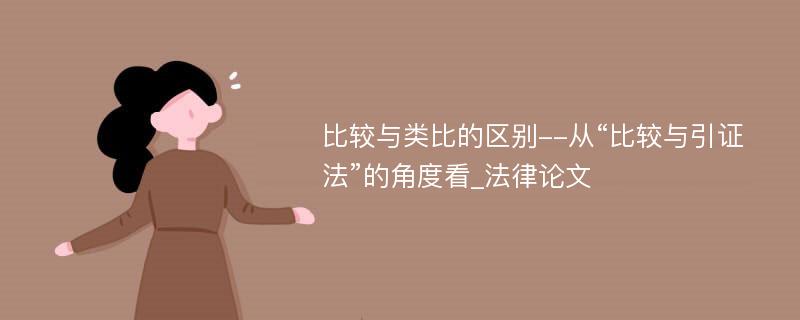
比附与类推之辨——从“比引律条”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律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比附是古代中国独特的法律推理方法,它以相似性问题为思考重心,与近代刑法所反对的类推① 有着某种家族类似性。清末时期,伴随《大清刑律》(通称为《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确立了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删除比附”正是该法着重彰显变革的要点之一,②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更有《断罪无正条》③ 长文,为此改革张本。他以托古改制的手法,论证传统中国本有罪刑法定的传统,并抨击比附之弊。因为沈氏巨大的影响力,比附作为罪刑法定的对立面被定型下来,传统中国的司法特质,也陷入了所谓法定与非法定这种似是而非的争论窠臼之中。
笔者以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应告别“西方有,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命题预设,而进入“是否不同”、“如何不同”、“为何不同”这样更中性、更心平气和,亦可能更有学术意义的层面进行探讨。本文试图在比附与类推的比较、辨析上作出这样的努力。
正如学者指出,类推的原理是一个宽广且难以界定的概念,④ 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界定为“因入罪之需要,为使规则涵摄当前之事实,依据‘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处理’之法理,超越规则中特定概念的文义之法律解释行为”。其经典的例子有:日本刑法第129条过失导致交通危险罪中的火车是否应包含汽车,盐酸是否属于德国刑法第250条加重强盗罪意义下的武器,电气是否属于盗窃罪意义上的物等。
在比附与类推的比较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先行著述,有如日本学者中村茂夫的《比附偺机能》⑤、滋贺秀三的《比附偲类推》⑥、德国学者陶安(Arnd Helmut Hafner)的《比附与类推:超越沈家本的时代约束》⑦、台湾地区学者张富美(Fu-mei Chang Chen)的On Analog in Ch’ing Law以及拙著[1]。在本文中,笔者将利用上述研究没有系统利用的史料:《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所收的“比引律条”——代表性的比附立法——作为分析的基础。“比引律条”源于明代的“比附律条”,其很可能是经刑部的判例而成之立法,数目处于变化之中,雍正朝更名为“比引律条”,删修而成三十条,直至清末。⑧ 这30条存续时间较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中更有成为律典正文中律条的小注⑨ 或条例者⑩,可以推定其代表着官方的认可态度,具有示范性,以其为分析蓝本,可以避免或减少如一般刑案中关于比附正确与否的争议。
本文将以比附为主线,兼与类推比较中进行论述,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展开:首先,从传统律典与近代刑法内在逻辑的不同入手,说明比附并不需要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上面临压力;其次,“比引律条”所见的比附,依行为相似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名分的比附、类推式的比附与特别的比附三种类型,可以看出,比附与类推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在名分的比附与特别的比附这两种类型中,比附有其特殊的面相;再次,从司法判例和律学家对“比引律条”的批评等角度入手,分析、反思比附在量刑及援引规则的可预期性上存在的问题。
在论证策略上,笔者试图以法律的内在视角,而不是诉诸外缘性的义理大道展开分析,原因在于深感后者常常会陷入某种“道理越‘深刻’,离事实真相越远”的窠臼。当然,前者亦非就是惟一或最优的方法,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分析法学”进路,更应该成为法史学研究的起点。
二、古今刑法的不同逻辑
本文所指的比附,出自于传统律典的“断罪无正条”,《大明律》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11)《大清律例》该条除个别措辞上稍加增修外,基本沿袭明律(12)。
关于此条,明代律学者张楷的解释,是笔者见过的诸多律学著作中最为详细的,其曰:
谓如有人犯罪,律令条款,或有其事而不曾细开,是为“该载不尽”;或迹其所犯,无有正当条目以断,是为“无正条”。凡若此,必当推察情理,援引他律以相比附。如京城锁钥,守门者失之,于律只有误不下锁钥,别无遗失之罪,是该载不尽也,则当以理推之,城门锁钥与印信、夜巡铜牌俱为关防之物,今既遗失,则比附遗失印信巡牌之律拟断。又如诈他人名字附水牌进入内府,出时故不勾销,及军官将带操军人,非理虐害,以致在逃,律无其款,是无正条也,则必援引别条以比附之。诈附水牌者,比依投匿名文书告言人罪律。虐害军人者,比依牧民官非理行事激变良民者律。(13)
依据其释义,第一个“若”字应作“或者”解,(14) 可见明律的比附,适用于两种情况:法律的“该载不尽”与“无正条”。前者接近于唐律的“举轻以明重”(15),即某一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其有罪,那么与之相似、但性质更为严重的行为自然更应该入罪。但明律比唐律有更明确的指示,其操作的全过程为:《大明律》“门禁锁钥”条对误不下京城门锁钥设有专款,与误不下锁相比,遗失锁钥行为的危害性显然更重,通过“举轻以明重”,经比较衡量决定入罪后,又以锁钥与印信、铜牌等同为关防之物,《大明律》“弃毁制书印信”条对遗失印信、铜牌的行为设有专款,遗失印信、铜牌与遗失锁钥事理相同,故可比照该款适用。
从关防之物的角度,将锁钥等同于印信、铜牌,与日本判例认为火车与汽车“因系行驶于轨道上,且俱为迅速、安全、并能运输多量客货之陆上交通工具”(16),颇为相似,具有类推之性质,“无正条”时所举的诈附水牌、虐害军人者的比附之例,其相似性问题,也颇值商榷,但我们或许不应混淆时空的差别,简单地以其违反罪刑法定主义来“以今非古”。
如果比附的载体——传统律典——因其以规范犯罪与刑罚为主,可视为刑法的话,我们需审慎地看到古今刑法内在逻辑(inner logic)的不同。
首先,是罪的标准问题。在何谓犯罪的问题上,传统律典的“不应得为”堪称底线条款,“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无罪名,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即以“常识性的衡平感”——情理——作为衡量“罪”之标准,这使得其不免混同于一般的社会道德感,起点甚低,与近代刑法认为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以法定类型为准有所不同。
其次,是去罪化的问题。在传统律典中,常可见“不坐”、“勿论”等标明行为(者)的非罪化的字样,以《大清律例》为例,有如“犯奸”中“强奸者,妇女不坐”(17);“略人略卖人”中“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奴婢),及略卖良人(与人)为奴婢者,皆(不分首从,未卖)杖一百,流三千里……被略之人不坐,给亲完聚”(18);“收留迷失子女”中“若得迷失奴婢而卖者,各减良人罪一等。被卖之人不坐,给亲完聚”(19);“娶部民妇女为妻妾”中“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者,杖八十……(恃势)强娶者,各加二等,女家不坐,(妇归前夫,女给亲)……”(20)。
上述条款中,强奸、拐卖等各种犯罪类型中的被害人,需要特别标明其“不坐”,以近代刑法的视角来看,这种提示式的“注意规定”似乎不可思议,但笔者认为,其存在并非毫无意义。以《唐律疏议》“违律为婚恐喝娶”条为例,“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21),按律疏解释,所谓“未成法”,是指“各减已成五等”,也就是按违律为婚已成减五等处罚,所以女方即便是被胁迫,只要是违背婚姻基本原则,诸如同姓通婚、亲属通婚、良贱通婚等情况下,也不能全身而退。其背后的立法考量可能是认为违律为婚的大错已经铸成,女方虽然是被胁迫,却非毫无反抗之机会,所以只能减轻刑罚,却无法去罪化。所以,古代刑律中的被害人(或无过错方),亦非全无责任。
或许正是因为古典“罪”的宽泛性,故立法者对于非罪之行为(者),需以“不坐”、“不论”之类之立法方式提醒审判官员,体现了一种“法有明文规定去罪化者不为罪”的思维。我们也可以窥得,传统律典的“断罪引律令”要求司法者具引律例,(22) 主要旨趣是要求其展示法律依据,它可以反映出传统司法“万事皆有法式”的法治倾向,却不能简单地等同近代的罪刑法定,进而纠缠其与“断罪无正条”中比附的吊桅并存。
古今刑法都面临着罪与非罪的判断与斟酌,在近代刑法中,因为罪刑法定之存在,类推的正当性颇受质疑,即便少数主张其合理性的学者,如认为“严格的禁止类推,结果正与禁止解释一样,历史经验已告诉我们,它完全没有作用”[2](P.13)的考夫曼氏,也不得不辩解道“有些批评者认为我根本怀疑刑法上的禁止类推,这对我是一种误解”(23),在惩治犯罪的驱动下,法学上的努力,无非是试图在其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中提出一定之标准,例如以类型来取代概念,作为可容许类推的界限(24),或者以扩张“解释”之名,与类推划清界限。
而就比附而言,无论是传统律典的罪之标准,还是其去罪化的立法方式,皆使得其无需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上承受过多的压力,“断罪无正条”与“断罪引律令”之间并没有实质的紧张关系。前提既然不同,比附的运用自然要比类推灵活得多。
三、比附的类型
先行研究中,中村茂夫从刑案出发,敏锐地指出:“类推是论理地分析法律规定,确定其意义,立足于为了推论某件事案是否包含在构成法律规范的语言里所进行的抽象化之思考过程……而比附似乎可以说是通过更大的视角捕捉事案的共同的本质部分,寻求其类似性。”(25) 管见以为这是相当独到的见解,但仍可进一步深入,例如:比附是在怎样的视角内展开?追求何种相似性?笔者以《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所收的“比引律条”为基础,依据行为的相似性程度之高低,将其分为名分的比附、类推式的比附与特别的比附三种类型。
(一)名分的比附
“比引律条”中,关于名分的比附有15条,占了50%。包括:
(第一条)僧道徒弟与师共犯罪,徒弟比依家人共犯律,免科。(第九条)妻之子打庶母伤者,比依弟妹殴兄姊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第十条)杀义子,比依杀兄弟之子律,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杖一百、流二千里。(第十二条)奸义子妇,比依奸缌麻以下亲之妻律,杖一百、徒三年;强者,斩。(第十三条)奸乞养子妇,比依奸妻前夫之女律,其子与妇断归本宗;强者,斩。(第十四条)奸义妹,比依奸同母异父姊妹律,杖一百,徒三年;强者,斩。(第十五条)奸妻之亲生母者,比依母之姊妹论。(第十六条)奸义女,比依奸妻前夫之女律,杖一百,徒三年;强者,斩。(第十八条)夫弃妻之尸,比依尊长弃毁缌麻以下卑幼之尸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第二十二条)弓兵奸职官妻,比依奴及雇工人奸家长期亲之妻律,绞。(第二十三条)伴当好舍人妻,比依奴及雇工人奸家长期亲之妻律,绞。(第二十七条)义子骂义父母,比依子孙骂祖父母律,立绞。(第二十八条)骂亲王,比依骂祖父母律,立绞。(第二十九条)义子奸义母,比依雇工人奸家长妻律,立斩。(第三十条)谋杀义父之期服兄弟,比依雇工人谋杀家长之期亲律,已行者,立斩;已杀者,凌迟。
传统社会是个身份社会,法律对家族中的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关系,社会上的贵贱、良贱范畴,结合特定的案件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并不厌繁琐、持续不断地制定细则规定。就司法官员而言,辨析、确定涉案当事人之间的名分关系,乃审判之要务。这15则“比引律条”,正反映出司法中面对某一类型案件中立法尚未规范的关系,如何通过比附来确定合适之名分之过程。比如关于亲属乱伦的上述第(15)条,发生于明代,律学家王肯堂在《律例笺释》中指出:“奸妻之亲母,律无文,宜比附确当上请,盖论服则缌麻以上亲,以义则亦伯叔母与母之姊妹比也。[3](P.708)”(笔者按:依《大明律》“亲属相奸”条,与伯叔母通奸是斩,母之姊妹是绞)。从明代的“比附律条”可窥得该案的处理结果:“女婿奸妻母,系败坏人伦,有伤风化,比依本条事例,各斩。”(26) 与明律相比,《大清律例》的“比引律条”在将名分关系明晰化的同时,更在律典正文的“亲属相奸”条中用律注标明:“若奸妻之亲生母者,以缌麻亲论之太轻。”(27)(笔者按:依《大清律例》“亲属相奸”条,与缌麻亲通奸,杖一百,徒三年),还比依母之姊妹论。
有必要指出,上述的比附类型,即便以当代视角观之,也不能说是为了入罪之需要,比如上述第(1)条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将僧道与徒弟的关系比附为家长和卑幼关系,即可依据“共犯罪分首从”条:“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长”,(28) 比附之目的在于使徒弟出罪。在其他例子中,如伤害、通奸、杀人、弃尸、骂詈等本来即法有明文惩罚之行为,依据不涉及名分之普通条款(比如“凡和奸,杖八十”)便可入罪。可见,古人的“无正条”与近代的“法无明文规定”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差距,在名分的比附类型中,其毋宁为“法律没有适当名分之规范”,近代对比附之批判,不无偏颇之处。当然,不可否认比附与直接适用普通条款相比,在量刑上显然不同。
(二)类推式的比附
“比引律条”中如下五例,可谓类推式的比附:
(第三条)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29),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杖八十。(第五条)打破信牌,比依毁官文书律,杖一百;(第八条)遗失京城门锁钥,比依遗失印信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第二十四条)奴婢诽谤家长,比依奴婢骂家长律,绞。(第二十六条)弃毁祖宗神主,比依弃毁父母死尸律,斩。
上述五例中,米麦与盐同为食物;信牌,作为置立于州县,拘提人犯,催督公事之物(30),与官文书同为记载官府事务之信物凭证;京城门锁钥与印信同为关防之物;“以不实之词毁人”的诽谤与“骂”这种“以恶言加人”之行为(两词解释见《汉语大词典》),性质相似(侵犯名誉罪);祖宗神主可以视为祖宗之化身。此类型之比附,似与类推并无二致。
(三)特别的比附
其余数条,似乎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类推之界限,不妨称之为特别的比附。如果说上述第(3)条中的另一种情况,发卖猪、羊肉灌水比附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律,以现代的视角,尚可说是属于同一犯罪类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话,下列诸条可以说超出了当代法律人的想象力,如:
(第二条)强、窃盗犯,捕役带同投首,有教令及贿求故捏情弊,比照受贿故纵律治罪。(第四条)男女订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第六条)运粮一半在逃,比依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律,杖一百;(第七条)既聘未娶子孙之妇,骂舅姑,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第十一条)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者,比照诈假官律治罪。(第十七条)偷盗所挂犯人首级,丢弃水中,比依拆毁申明亭板榜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第十九条)兄调戏弟妇,比依强奸未成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第二十条)拖累平人致死,比依诬告人因而致死一人律,绞。(第二十一条)官吏打死监候犯人,比依狱卒非理凌虐罪囚致死律,各绞。(第二十五条)奴婢放火烧家长房屋,比依奴婢骂家长律,绞。
笔者试图洞悉其些条款背后古人之独特的思维:如上述第(2)条,自首减免罪责是传统律典的基本准则,捕役本有缉盗之责,反带盗犯投首,使罪犯得以脱罪,难保其间无舞弊之嫌,与受贿故纵,似有异曲同工之效。如第(11)条,贡监生在国子监监满,经考职得任州同、州判、县丞,考职中假冒顶替者有成为官员之可能,其与被替代者之关系,正如假与人官者与知情受假官者。如第(17)条,古代将罪犯首级示众的酷刑,有威慑警诫世人之用,与申明亭中所立板榜之惩戒、教化功能有某种相似之处,故偷盗首级和拆毁申明亭的板榜,皆可被看成反抗教化之行为。
应该说,特别的比附很难说有构成要件的相似性,其毋宁是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这种特殊的思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忍俊不禁的是明代“比附律条”所收的鸡奸条款“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贼,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31) 此条所涉的鸡奸行为是双方合意(即后来清例所谓的“和同鸡奸),“秽物灌入人口”律则无疑为胁迫,主观方面差距甚大,客观方面的行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该条不免带有“造法”者极富想象力的直觉色彩。一言以蔽之,特别的比附之性质,不妨借用深谙德国概念法学的徐道邻对礼教法律观的看法予以概括,即“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形式主义的拘束。”(32)
四、比附的目标
与类推相比,比附在寻找相似规则之同时,因为传统立法的绝对确定法定刑之因素,亦基本决定了最终之刑罚(除了比附而加、减一等的情况),亦可以说,与近代的刑法采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定罪与量刑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不同,比附这种“找法”,同时包含了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仿照恩吉斯(Engisch的话来说,这一过程是在定罪和量刑之间“目光往返流盼”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援引适当的规则予以定罪并非不重要,正如学人指出,其有宣示犯人的罪行内容、予以非难之意义,(33) 清代的刑案中亦可见如“罪名虽无出入,引断殊未允协”——判决的刑罚/刑名虽然是适宜的,但引用裁断的法条并不适合(34) ——中央刑部批评地方的审拟意见的行文,皆可证对规则合理性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此类行文语气相对平和,也不妨可以看成传递着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即比起“情罪相符”的罪刑均衡来说,规则选择便成了相对次要的事务,这应该也是特别的比附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似性判断的不同,可能会使量刑出现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附者对罪刑均衡关系的把握,量刑的不妥当,亦会反过来引发对援引规则的合理性之质疑。下举司法中的代表性案例观之。
例一,《比照案件》“戏杀误杀过失杀”条下所收一案(35),李俸儿为救助被蛇咬的魏勋钊,忙乱中不慎用刀误伤其囟门致死,四川总督将李俸儿比照民人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施放枪箭杀伤人,仍依弓箭伤人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36) 刑部则改照庸医为人针刺因而致死,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论,收赎。
例二,《刑案汇览》所收“踏毁伊父灵牌故杀苟合继母”一案(37),案犯高名槐与继母戴氏因琐事争吵,戴氏捧其父灵牌欲控官,高名槐用刀砍死继母,并踏毁父亲灵牌。在其“踏毁灵牌”的问题上,地方对依“比引律条”第(26)条弃毁祖宗神主,比依弃毁父母死尸律拟斩候(38),还是比照“发冢”条例之“子发掘父母坟冢,见棺椁者斩立决”,抑或“开馆见尸并弃毁尸骸者凌迟处死”(39) 之间踌躇不决,其倾向第二种,并以“例无明文”,请刑部核示,刑部认为应按“比引律条”第(26)条定罪。
第一个案件中,在相似性的判断上,四川总督考虑的是“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例八“打射禽兽,不期杀伤人”这一字眼与案件事实的相似,关注的是用刀和施放枪剑皆具有同等的危险性,刑部比照的规则是“庸医杀伤人”律,关注的是当事人主观具有救人之心态,或可谓,地方关注“形似”,刑部则更重视“神似”,后者的意境无疑更高。抛开合理性问题不表,我们更要看到,前者的获刑是三等流刑中的最重者,后者则可以赎刑,轻重差距之大,令人感叹。
在第二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认为“例无明文,咨部核示”,实际上是在法有明文的情况下,试图比附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传统司法中并不鲜见,甚至曾经立法化予以认可,关键性的原因仍然是在罪刑均衡的把握上,而之所以不直接在引用正条的基础上修改刑罚,乃是因为从传统法理上讲,刑罚的变更需由皇权掌握,臣属只能议罪,具有“守法”之职的臣属最佳之方案就是通过比附列举法条进行论证[4](P.341-351)。在本案中,刑部的意见虽是用比引律条的正条定罪,但对地方有意规避正条的行为,并非特别反感,原因恐怕也是在此。而地方的踌躇不决,恐怕不是行为本身的定性问题,而是引用的正条和比附的规则所指向的刑罚:究竟是斩监候、还是斩立决,抑或凌迟处死,哪个才是符合“罪刑相符”这一实质正义目标的问题。在其内心世界的衡量中,“监候”稍轻,“凌迟”太重,所以才有“立决”的倾向。
司法中存在问题如斯,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已经立法化且存续时间甚长的“比引律条”自身,亦非毫无争议,此点也出乎笔者以比引律条为研究基础时的预设。
例如第(2)条,律学家指出:“原奏云:‘盗犯自首,律得减罪者,因该犯悔过,予以自新之路也。若准捕役带同投首,其中不无教令供词等弊。云云。’是以定有此例,所以防贿纵也……本犯无自首之心,因听旁人教令,始行投首,未闻将旁人治以重罪。因系捕役教令,始定此例,究嫌过重,亦与律意不符。”(40)
例如第(11)条,律学家指出:“乡会试外以考职为重,是以特立专条,而未及别项。顶名代考中式,不问死罪,此一经假冒顶替,即拟斩罪,似属参差,与处分则例参看。诈假官,假与人官者斩,知情受假者满流。贡监与官不同,转卖顶替,即照假官律治罪,似嫌太重。”(41)
例如第(17)条,《据会》(笔者按:《刑书据会》)云:“羞见父兄枭示而窃弃之者,引此毁板律,不可作弃尸论,凡人亦然,于义似合而实非。盖窃弃枭示,乃发于羞恶之心,且有不忍其观之意,岂得坐以流罪哉?即凡人亦不应若是之重也。”[5](P.934)
至于第(15)条,尽管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上看尚无争议,但明、清律实际比附不同的名分关系,前者比附伯叔母(42) 而为斩刑,后者比附母之姊妹而为绞。即便说两者的刑罚同为死罪,但执行方式的不同(身首异处与得保全尸),在古人的观念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究嫌过重”、“似嫌太重”、“不应若是之重”,讲的无非仍是量刑问题。因此,如果说类推面临的问题是罪与非罪的抉择,其被人诟病的原因是其使法律原本无法涵摄的行为入罪的话,比附的主要问题乃在量刑方面,极端的例子,正如前述“踏毁伊父灵牌故杀苟合继母”一案,试图规避正条,比附定罪。
古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比附带来的量刑危险之存在,除了通过覆审制度以及追究擅断者的责任来保障外,学理上也不乏总结。例如沈家本比较明、清律,对清律“(援)引(他)律比附”所增加的律注“他”字作出法理上的判断:“盖既为他律,其事未必相类,其义即不相通,牵就依违,狱多周内,重轻任意,冤滥难伸。此一字之误,其流弊正有不可胜言者矣。”(43) 司法中亦有这样的总结:“审理案件遇有例无明文原可比附他律定拟,然必所引之条与本案事理切合,即或事理不一而彼此情罪实无二致方可援照定谳,庶不失为平允。”(44) 皆可证古人试图将相似性问题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但正如“比引律条”第(15)条,无论比附伯叔母,还是比附母之姊妹,皆属于王肯堂所谓“义”之范畴,事理切合亦好、情罪一致也罢,仍然存在甚至并不缺乏复数之选择。
其实即便在当代,为了量刑标准的统一,有诸如《量刑指南》,甚至电脑量刑的出台,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立法再细则化,科技再发达,似乎也无法(或许亦无必要)保证不同的司法者会对同一个案件的同一罪犯给出完全一致的刑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会对古人比附时的援引规则之差异性有某种“同情的理解”,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传统法时代,这种建立在个人衡平感基础上的比附,可能很难确保援引规则之可预期性。
五、结语
相似问题应相同处理,类推乃出自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感。在西方刑法领域,其与经历启蒙运动洗礼,为社会契约、权力分立、人权保障等理论、观念所正当化论证的罪刑法定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就传统中国而言,权力的高度统一性,“以法为教”、“明刑弼教”之法律/刑罚功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种早熟的观念,“律例有限,情伪无穷”这类法律从业者的共识,法律在社会规范中的低层位阶(45) 等种种因素,皆使得古代中国虽不乏“守法”之传统与实践,却不会有近代罪刑法定的土壤。“断罪无正条”与“断罪引律令”之间亦没有实质的矛盾,甚至极端地讲,比附时要列明其援引之律例,无非是“断罪引律令”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来的要求。在传统律典中,以“不应得为”作为判断犯罪的底线条款,以情理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当类推需要与扩张解释辨析之时,比附则得以自由灵活地运用。
以“比引律条”为蓝本,根据行为相似性程度的高低,我们发现比附(至少)有名分的比附、类推式的比附与特别的比附三种类型,比附既包括类推,亦有其特殊的面相。从名分的比附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法中“正名”之重要性,而即便以当代视角观之,其也不能说是为了入罪之需要。从此角度讲,古人的“无正条”,包含无适当名分的规范之意,与近代的“法无明文规定”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差距。从特别的比附中,我们则可以看到比附超越构成要件的相似性,“不受严格形式主义拘束”的一面。
因为传统司法“情罪相符”之要求以及立法上绝对确定法定刑之设置,与类推的寻找最相似规则予以入罪相比,比附这种“找法”,同时包含了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规则的适当性固然重要,但量刑上的妥当才是最终目标,这也是特别的比附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似性判断的不同,可能会使量刑出现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附者对罪刑均衡关系的把握,因此比附的主要问题是在量刑方面。同时,建立在个人衡平感基础上的比附,可能很难确保援引规则之可预期性。
注释:
① 有必要指出,传统律典、律学著作和刑案中亦有“类推”一词,关于其具体运用,笔者将另撰文讨论。
②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收入《大清光绪新法令》的第19册,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二月初版。
③ 沈家本:《明律目笺一·断罪无正条》,收于氏著:《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册。
④ See Fu-mei Chang Chen(张富美),On Analogy in Ching Law,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1970.
⑤ [日]中村茂夫,收入氏著:《清代刑法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
⑥ 载《东洋法制史研究会通信》第15号,2006年8月21日。
⑦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⑧ 黄彰健:《明代律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考》,收入氏编著:《明代律例汇编》(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35-1037页。
⑨ 如第15条“奸妻之亲母”,成为“亲属相奸”条之律注,《大清律例》,卷三十三,郑秦、田涛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第524页。(“比引律条”的序号为笔者所加)
⑩ 如第1条“强窃盗犯,捕役带同投首”成为“自首”条之条例的一部分。《大清律例》,卷五,第115页;第11条“考职贡生假冒顶替”成为“贡举非其人”条之条例的一部分。《大清律例》,卷六,第147页;第20条“拖累平人致死”,成为“诬告”条之条例的一部分。《大清律例》,卷三十,第483页。
(11) 《大明律》,卷一,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周礼·秋官·大司寇》注疏“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也”(《周礼注疏》,卷第三十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09页),可谓古典文献中阐明“无(正)条”与“比附”关系之最早记载。传统立法中两者明确地建立联系,最早出现在唐朝。《宋刑统》“断狱律”所收的唐长兴二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规定:“律、格及后敕内,并无正条,即比附定刑。”(《宋刑统》,卷三十,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第551页),黄彰健认为其乃明律断罪无正条者,可“引律比附”所本。(黄彰健:《明代律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考》,第1027页)。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断狱敕”有:“诸断罪无正条者,比附定刑,虑不中者,奏裁。”(《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三,戴建国点校,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1页)。从明代起,比附开始进入律典名例律的“断罪无正条”中。
(12) “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援)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申该上司)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大清律例》,卷五,第127页。
(13) 张楷:《律条疏议》,卷一,收入《中国律学文献》第1辑第2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004年版,第245、246页。
(14) “若”字是传统律学的“律母”,依“例分八字之义”:若者,文虽殊而会上意。谓如犯罪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以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大清律例》,卷一,第41页。但“断罪无正条”的第一个“若”字显然不是此意。传统律典中“若”字作“或者”解释的例子有如“亲属相为容隐”:凡同居,(同谓同财共居亲属,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亦是。)若大功以上亲,(谓另居大功以上亲属,系服重。)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系恩重。)有罪,(彼此得)相为容隐……。《大清律例》,卷五,第120、121页。
(15)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疏]议曰:断罪无正条者,一部律内,犯无罪名。“其应出罪者”,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又条:“盗缌麻以上财物,节级减犯盗之罪。”若犯诈欺及坐赃之类,在律虽无减文,盗罪尚得减科,余犯明从减法。此并“举重明轻”之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议曰:案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又例云:“殴告大功尊长、小功尊属,不得以荫论。”若有殴告期亲尊长,举大功是轻,期亲是重,亦不得用荫。是“举轻明重”之类。《唐律疏议》,卷六,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第145、146页。
(16) 《日本刑法判例评释选集》,洪福增译,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17)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第522页。
(18) 《大清律例》,卷二十五,第405页。
(19) 《大清律例》,卷八,第80页。
(20) 《大清律例》,卷十,第210页。
(21) 《唐律疏议》,卷十四,第295页。
(22) 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大清律例》,卷三十七,第595页。
(23) [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后记”,第143-145页。
(24) 考夫曼指出“当我们把盐酸视为武器时,这并非从武器的概念得出,而是从加重强盗罪的类型得出的。”(《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第119页)但他后来似乎推翻了自己的某些主张,认为盐酸可视为武器,电气可视为物是错误的。(《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后记”,第159-161页)。
(25) [日]中村茂夫:《比附の机能》,收入氏著:《清代刑法研究》,第177、178页。
(26) 黄彰健:《明代律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考》,第1043页。
(27)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第524页。
(28) 《大清律例》,卷五,第118页。
(29) 该条尚有另一种情况:“发卖猪、羊肉灌水”,笔者将其归入特别的比附之类型。
(30) 参见《大清律例》“信牌”条,卷六,第145页。
(31) 黄彰健:《明代律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考》,第1068页。清代有关于鸡奸罪非常具体的条例,其中“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大清律例》,卷三十三,第522、523页。薛允升则对其比附定罪不以为然:“即如威逼人致死,男子和同鸡奸,有犯即可照不应为科断。可知后来增添之例,皆不应也。”薛允升:《唐明律合编》,第731页。
(32) 徐道邻:《中国法律制度》,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第160页。
(33) 庄以馨:《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案件为中心》,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年版。
(34) 对此段古文理解的关键在于“罪名”一词应作“刑罚/刑名”解,具体的分析,参见拙著:《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2页。
(35) 收入《历代判例判牍》第8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531、532页。该案亦可见《刑案汇览》(三编),卷三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第1139、1140页。
(36) 该处规则出自“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的条例八,完整的表达应为“若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施放枪剑,打射禽兽,不期杀伤人者,仍依弓箭杀人本律科断”,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十四,第4册,第852页。不管是《比照案件》还是《刑案汇览》,对该处法条都有所省略。
(37) 《刑案汇览》(三编),卷四十四,第1608、1609页。2005年笔者博士论文答辩时,杨一凡先生曾提问比引律条的实效性问题,当时只能从学理上回应,该案例之发现,正可以作为实证资料的例证。
(38) 需要指出,“比引律条”该条源自明代,刑罚为斩刑。清代斩刑细分为斩立决和斩监候,弃毁父母死尸律为斩监候,所以依据《大清律例》,比引律条第(26)条的刑罚实际应为斩监候。
(39) 该条是“发冢”条例二,比较完整的表达为“凡子孙发掘祖父母、父母坟墓……见棺椁者,皆斩立决;开棺见尸并毁弃尸骸者,皆凌迟处死”,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三十一,第4册,第740页。
(40) 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四,第2册,第109、110页。吴坛指出:“此条系仍雍正七年原例改定。乾隆五年馆修,以原议将捕役照知人犯罪事发藏匿家律治罪(笔者按:减罪人所犯罪一等),殊未允协,故改为受财故纵律治罪(笔者按:与囚之最重者同罪),纂如前例。”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马建石、杨育裳编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第281页。
(41) 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四第2册,第193页。
(42) 尽管明代的“比附律条”只是说“比附本条事例”,但结合王肯堂的意见不难得出其比附的名分关系。
(43) 沈家本:《明律目笺一·断罪无正条》,第1816页。有必要指出,明代的律学作品已经出现了“他”字,沈氏对史实的判断不无问题。
(44) 沈家本编:《刑案汇览三编》,卷四十三(下)“刑律·杂犯·不应为”所收光绪十年“儒师引诱学徒为非”之案。
(45) 如学者指出:中国人心中有一整体规范的概念,道、德、礼、法、习俗、乡约等,均为规范概念,但存在上下阶层。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隘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而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适地适用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则以谋求解决。参见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与法学》,《法制史研究》第九期,2006,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