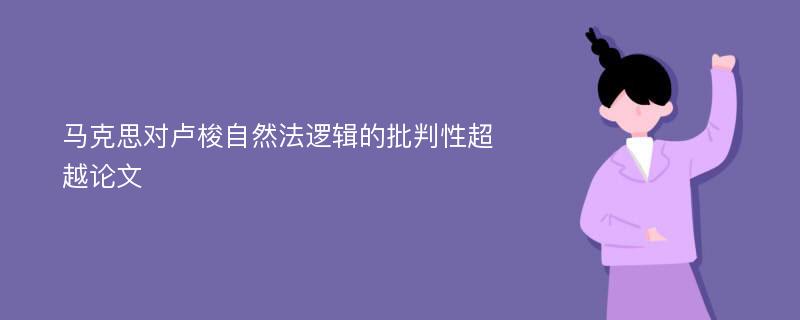
马克思对卢梭自然法逻辑的批判性超越
杨臻煌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卢梭自然法以自我保存、怜悯他人的自然人性与人类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作为基本逻辑支点,演绎并论证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自然法阐释了人在自然状态下逐渐异化的过程、表达了重构政治秩序的诉求、反对理性主义泛滥,但是其逻辑推演也存在跳跃式论证、忽视实然存在、将中性之物人格化等缺陷。马克思在异化思想、实践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方面,以唯物史观视角对卢梭自然法进行全面超越,实现了批判继承。
关键词: 马克思; 卢梭; 自然法思想; 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曾在《论蒲鲁东》《哥达纲领批判》中肯定了卢梭的革命精神,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1]马克思继承了卢梭思想合理的精神内核,但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超越。
一、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支点和逻辑路径
卢梭自然法有两个逻辑支点——自然人性和物质条件。自然人性是卢梭自然法的内在驱动力,物质条件是自然法发展的外在推动力,这两者无疑是相互支撑的逻辑关系。
(一)自然人性是卢梭自然法的内在驱动力
卢梭强调对人性的正确把握,认为“自然法的真正的定义之所以难于确定而且模糊不清,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人的本性的缘故”[2]64。 所以,卢梭的自然法以“自我保存”“怜悯他人”的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认为人在起初不知何为恶,凭着天良的怜悯行事为人。他们“无意加害于人,更注意防范可能遭到的侵害”[2]103,这种“防范”只能称之为“粗野”。“自我保存”是“怜悯他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自爱才有他爱,自爱在前,他爱在后。与此同时,“怜悯他人”的人类情感又反过来限制了自我的无限膨胀。
主要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观察。焦虑、抑郁评分由专业人员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观察。日常生活能力由专业人员对两组患者的正常、不同程度功能障碍、明显功能障碍进行记录。
怀有浓厚道德情怀的卢梭认为情感并非恶的存在。卢梭的自然人性论不是偏执一隅的性恶论或性善论,而是非常容易深入人心的自然人性的假设,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方面,“自我保存”是出于人性对死亡的天然恐惧,它本身合理且正义,但是在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它又为人们在产生冲突后必然进行的维护和反抗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怜悯他人”的顺利实现是由于早期有富足的资源,“怜悯他人”对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威胁。随着资源的逐渐匮乏,人们就渐渐泯灭怜悯之心,虚荣、骄傲等“恶”也逐步滋生。这样,卢梭对现代社会发展路径的分析变得顺理成章。
置于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中,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推演为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
(二)物质条件是卢梭自然法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卢梭承继洛克的思想,认为自然状态完备无缺,即具有足够辽阔的土地和资源,这是自然法推理的另一个逻辑支点。原始状态的人们只要拥有简单的生存技能就能健康幸福、与世无争地生活。之所以与世无争,是因为没有争的必要,每家每户都能自给自足。
卢梭并不否认由于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第一种不平等”,但是,当这样的不平等置于足够敞阔丰富的环境中时,就变得不值一提,因为“大地到处都会供给各种动物以食物仓库与避难所”[2]75。他认为“第二种不平等”,即特权与权势,是伴随着日益膨胀的人口和日渐紧缺的资源而产生的。换言之,人性的堕落正是由物质的匮乏激发出来的。日渐发展的政治环境给原始人类带来了情感的改变,虚荣和骄傲也由此而生。回归自然正是卢梭自然法的愿景。
长石矿物量较少(<5%),但矿物种类繁多,主要为钾长石,偶见有条纹长石、微斜长石和钠长石等。现主要对钾长石的嵌布特征描述如下:
(三)卢梭自然法的逻辑路径
卢梭自然法认为,原始状态中,由于自然环境优越、资源广阔,人们生活富足、无忧无虑、不争不抢, 野蛮人没有关于“名望”“权势”这些词语的概念,自然状态中除了天然生理上的不同,彼此之间没有差别。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环境的恶化,人们出现了疾病,发明了语言,实现了耕种,陷入了沉思,彼此之间由于资源的有限不得不划分界限。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确立之后,成为永恒的合法现象[3]。
二、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推演贡献及缺陷
2014年1月4—5日,水利部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召开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总结2013年水利工作,部署水利改革攻坚和加快发展任务,安排2014年水利重点工作。
(一)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推演贡献
虽然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仍然存在合理内核,马克思在人的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阐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论证等方面与卢梭思想有着继承关系,但是马克思突破了卢梭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了卢梭的自然法逻辑。
3.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病情复发情况:2组CP患者定期随访1年,观察组复发2例,复发率1.4%;对照组复发15例,复发率10.9%。观察组CP患者病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卢梭阐述了人类社会物化的过程,认为公民社会对象化之后,并不优于自然状态。从卢梭的行文当中,不难察觉其对现代性的反感和对过去的怀念,试图在人类社会成为异己力量之前停留在“异化”的起点。不同于古典自然法的“超克自然”,卢梭以过去反观现在,以人为追溯天然。卢梭希望人类从虚伪、功利的文明社会返璞归真,认为自然状态才是人类的“黄金状态”。当代人认为,人类的发展正是对自然状态缺陷的不断补偿。当卢梭关注人类关于“公平”的政治进步时,分工配合所带来的“效率”几乎成了盲点,所以在他看来,人们所认为的文明实际上成了自身的枷锁。卢梭的根本意图在于回归自然人的自由与善良,自然状态实则已经一去不复返。
2.卢梭自然法注重“应然”理念,忽视“实然”存在
文学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学和文化内容,不仅视角独特新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培养教师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个性,使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社会实际。
人性之复古,在于托古建制。诚如意大利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所言:“自然法之基本假定,是法律与道德的密切结合,但并不排斥两者区分的可能。”[4]自然法是哲学家表达对于道德与历史的看法的最终逆推,自然法之基本思路是哲学家为达至善与至美的论证过程,目的在于勾勒其政治愿景,并不是要对陈述内容的科学性进行论证,而是对政治现状进行反思。虽然卢梭与霍布斯均以情感为前提,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卢梭探求的是现有不平等制度的起源、不平等秩序的基础,抨击现代性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世的不平等,为重构政治秩序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正如朱学勤所说:“他们对此岸已然的批判,是对此岸应该重建的开始。”[5]卢梭希望达到“公共的大我”——实现人民的“公意”,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进而阐述他的政治构想,不仅驱逐霍布斯的专制集权,也反对其他自然法学家的资产阶级代议制。
卢梭不仅在“异己”命题上存在两难悖论,而且其关于个体与社会及个别公民意志、普遍意志、全体意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讨论也存在悖论和操作性难题。马克思继承了卢梭的共同体思想,以唯物史观重新释读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转向共产主义。卢梭认为,社会契约在私有制的解构之下歪曲了,追溯现代性社会的不平等的起源就在于私有制及少数人所占据的大部分资源。卢梭由个体到社会的发展进路最终被马克思所放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是明晰了这一观点: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逻辑起点,从生活、生产抽象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从现实的个人劳动推演出了共产主义的自主劳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于共同体思想和卢梭一样都怀有积极的自由倾向,但不同于卢梭公共政体和公民的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公共权威统管下的公共教育,马克思在卢梭道德的共同体和集体的共同体之上进行了更高阶段上的回复。共产主义,才是作为马克思思想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卢梭视感性冲动为道德的源泉,不希望人们的道德热情被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所辖制,将文明视为自然的遮掩,认为是意见裹挟了自然本性。赫尔岑认为:“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6]区分情感与理性,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开创性的,波普认为正是从卢梭开始悟出人主要的并不是理性。在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启蒙时代,卢梭对理性的批判难能可贵,是其个性魅力之所在。理性在启蒙时代登上至尊的宝座,作为工具的理性成为终极目的。人们为理性欢呼,尊崇理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理性将成为新的奴役形式。”[7]卢梭更是抨击了理性独尊的迷信。如果说,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时代构架了理性的骨骼,卢梭就是以传统的“宗教救赎”和不泯的道德情怀组合成理性骨架上的血肉。
1936年,袁家骝赴美求学。他不似父亲那样爱好诗词,更不像父亲喜欢倚红偎翠、拈花惹草,花钱如流水。相反,他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务实而节俭,对感情认真执着,遗传基因到他这里是物极必反还是变异?赴美留学的袁家骝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得到了国际学舍奖学金,不仅免缴学费,还管吃住,这使他的留学生活才不至于拮据。
2.2.1 稻瘟病药剂防治∶大田分蘖期开始每隔3天调查一次,主要查看植株上部三片叶,如发现发病中心或叶上急性型病斑,即应施药防治;预防穗瘟根据病情预报,以感病品种,多肥田为对象,掌握破口期分别抽穗时打药。施药种类和剂量,每亩用20%三环唑可湿性粉剂100克,重病田喷药2次,间隔7~10天。
(二)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推演缺陷
1.卢梭的自然法推演为跳跃式论证,显得急促而缺乏论证
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宗教体系和经院哲学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轰然倒塌。人们突然对历史的一切积累弃之如敝屣,以偏概全地要摧毁一切传统的堡垒,欧洲大陆迅速出现“道德真空”和“价值饥渴”,人们又转而急切地要建造一个一劳永逸的理性王国。原始的野蛮人被卢梭描绘得过于离群索居。野蛮人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怡然自得,人与人之间天然存在种种如不需要语言、不容易创造语言等联结的障碍,且不存在爱的关怀,只有性欲的简单满足、肉体的短暂结合,甚至任其孩子自生自灭。对于后来人们的团结配合、相助相爱等群居生活的转变过程都在“偶然事件”“意外原因”中一带而过。事实上,戴上卢梭口中的“枷锁”的过程应该十分艰难,显得卢梭自然法的论证不够充分。
2.人在现世与今生的“解放”诉求
卢梭认为,每一次人类的发展,都是一次不平等的加深。他视语言的起源、耕作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为人类对于“恶”的不断退让。卢梭的复古主义表现在个人品德和集体道德的理想上,希望建立如同日内瓦那样的道德共同体。古典政治哲学追求个人和集体的完整、高尚,在政治秩序的实际操作中难以实行,纯粹的民主制也是不可能的,政治构想容易沦为乌托邦。由“应然”直接导向的“实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卢梭之所以将现代社会与自然社会尖锐地对立起来,忽略了自然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发展环节,主要是因为卢梭以静止的观点将动态发展的历史停滞于政治秩序的构造之中。卢梭试图在他的纯然观念中阻止万物皆动的事实。
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将社会建设问题向前推进,免于陷入卢梭宗教情怀式的乌托邦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超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解释已经显示出了唯物史观的印迹。卢梭的宗教情感对于天真自然形态的溯源必然导致历史目的论,试图通过人的改造重返“伊甸乐园”,与先前的西方哲学家殊途同归。万物皆流,卢梭以静止的观点停滞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卢梭所提倡的道德性政治解决方案属于纯粹理性计划,相较于卢梭将社会人重返自然人的期望寄托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彼岸世界,马克思则将个人精神引入实践哲学,扎根于物质世界。马克思抛却了过去以道德形而上的视觉评判形而下的生产关系的路径,客观看待事物的运动,在其唯物史观的视野下,超越了包括卢梭在内的唯灵论的资产阶级方法,故而超越了卢梭政治哲学理论的克服路径。
卢梭将现代性攻击得体无完肤,将不平等的所有罪责都归咎于知识、艺术等日益精巧的科学,认为科学或哲学同德性是不相容的。科学本是无生命之物,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选择善恶。卢梭自然法的逻辑无疑是将科学、知识等不带情感属性的本体人格化。卢梭的自然法推演逻辑不知不觉将科学与道德进行了对立,最终容易得出科学与道德不可兼得的结论。“异化”虽然作为历史性存在,但是卢梭自然辩证法的逻辑推演却存在着历史性“悖论”。照这样推理下去,自由的社会要以德行为前提,就需要摒弃一切知识,就会出现反智倾向。善的传播依赖于知识的媒介,卢梭索性认为自然状态人人为善,也不需要善的传播。卢梭之所以将物质人格化,乃是因其自身具有浓厚的自然神论的宗教情怀,将自然与文明混为一谈了。
三、马克思对卢梭自然法逻辑的合理继承与创新发展
1.人在自然状态下的逐渐“异化”阐释
(一)“异化”的解释:否定之否定
卢梭作为异化思想的先驱者,意识到了人类主体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异性,但是其异化思想仍然处于初始萌芽阶段,所以在自然法逻辑推演中出现了上述的悖论,因为卢梭关于解决“对象化”的方式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形式,即回归过去。在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后,马克思赞同异化理论的现实存在性,扬弃了卢梭思想简单的交叉反差,以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维解释了卢梭未能解决的异己难题,深入剖析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异化,解释了人类与个人相异化的过程。马克思一方面诠释了社会形态的演变,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测;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过程。这一异化过程首先从劳动成为工人异己的存在物开始,逐步走向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对立,资本与劳动分离之后,劳动者的类本质被对象化。马克思解决了卢梭的异己难题,并突破了卢梭的两极悖论,以发展的眼光在更高的阶段上看待这一现象。
3.将中性之物人格化
3.人在理性独尊旗号下的“感性”回归
(二)实然解释世界,实践改造世界
马克思不仅从唯物史观视角重新释读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隐含在其中的规律,进行了“解释世界”的批判实践活动,还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积极“改造世界”。
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马克思实然地解释了世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根源入手,彻底否定了卢梭的道德政治。首先,卢梭的自然法主要是基于保护私利、建构政制的西方传统,其改造社会思路在于调节私利冲突 ,实则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制度保障人的嗜欲是人在社会中丧失自由的原因。马克思早在反对《林木盗窃法》的过程中就发现,公共财产是在私有制的利益要求下被侵犯的。后来确认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资本和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来源。其次,卢梭试图建立具有公意的共同体以实现社会契约的缔结,试图突破社会秩序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则指出,在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出现了商品交换,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及真正的共同体是蜕变于史前社会的,是消灭了阶级的、代替了阶级对立的共同体。再次,卢梭虽然藐视传统权威,不愿屈服于现存政权,但是其政治权力转移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脱离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事实,通过道德进行政治立法。但是全体意志中难以进行全面的道德建构,甚至在个人意志上都难以实行。脱离了实践的政治解释活动固然能够为改造活动提供愿景性的参考意见,但在改造世界中十分乏力。
为建设共产主义,马克思参加、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改造世界,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和平变革方式。马克思的政治创制思想具有实践性,在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方式破产后,暴力革命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必然途径。卢梭注重人的政治品性的养成,从而构建文明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纯粹观念的社会情感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合理的政治创制,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更为彻底地建立持久制度。为实现政治普遍性,马克思明确了暴力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强力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有效回应。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确立了政治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吸取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为缩短社会形态过渡时间,实现政治形式的变迁,推翻特定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日趋完善了革命的关键要素、革命的集中组织性、革命的实现方式等革命思想。
(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既是卢梭也是马克思的核心关切,但是什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何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由,两者存在思想分野。
卢梭理论严重割裂了自然人与社会人属性,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是抽象出人格的产物,以经验质料为基础自然导向外在目的规定,悬空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落入唯心主义先验方法的泥淖。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超越了卢梭的“自然人”。“人”不能孤立存在,社会关系的创造来源于实践,社会关系的实存内蕴于历史发展,既有自然性的需求,又有社会性的需求。
卢梭“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保障私有财产制度,甚至认为这比自由更重要,他批判的只是财产的不平等。马克思汲取了卢梭“私有制是不平等制度的根源”的思想内核,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这一传统伦理学主题进行说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可能性不能局限在伦理范畴,实现这一宏大命题必须通过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经济不平等来源于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分离,最终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仅加深了解释力,而且揭去了以洛克等西方思想家以保护私有财产为面具的,严重违背了平等自由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颠覆了西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所有权概念。
卢梭希望破坏现存物质世界而返璞归真,但这对于应对现代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壮大是无济于事的。卢梭自然法推演的终极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回归自然式的道德实现的基础之上的,仍然囿于西方传统哲学遵循的传统路径。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诸如贫富分化、利润率下降等问题,但是马克思十分客观地对待这一植根于物质基础的历史现实。马克思客观看待生产力的发展,扎根历史,立足现实,充分肯定科技的力量,以生产力作为解放全人类的内在根据,充分应用社会发展的先进产物。马克思较于卢梭更为激进,并不满足于政权结构的改善,而是提出废除私有制。
但说到了李红的心坎上,她高兴地说:“你都请我看电影了,我请你吃瓜子。”说着跑去买了两毛钱的瓜子,隔着报纸折成的瓜子包,热乎乎的。
马克思在异化思想、实践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方面对卢梭自然法逻辑实现了批判性超越。马克思的这一超越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实现了学理上的分野。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7-148.
[2] 让-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李常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3] 让-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高修娟,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125.
[4] 登特列夫. 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M]. 李日章, 梁捷, 王利,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99-100.
[5]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47.
[6] 恩斯特·卡西尔. 启蒙哲学[M]. 顾伟铭, 杨光仲, 郑楚宣,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11.
[7]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文集:第九卷[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59.
Marx ’s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Rousseau ’s Logic of Natural Law
YANG Zhenhu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 Rousseau’s natural law deduces and demonstrates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human inequality by taking self-preservation, compassion for others’ natural huma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al material conditions as its basic logical fulcrum. Rousseau’s natural law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human’s gradual alienation in the natural state, expresses the demand of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order, and opposes the overflow of rationalism. However, its logical deduction also has some defects, such as jumping argument, ignoring the existence of reality, and personifying neutral things. Marx transcended the alienation thought, the practical viewpoint,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alized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 Marx; Rousseau; natural law philosophy; critically transcendence
DOI: 10.19724/j.cnki.jmju.2019.03.004
收稿日期 :2019-04-11
作者简介 : 杨臻煌(1992— ),女,福建平和人,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821(2019)03-0024-06
[责任编辑: 陈小诗]
标签:马克思论文; 卢梭论文; 自然法思想论文; 批判性超越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