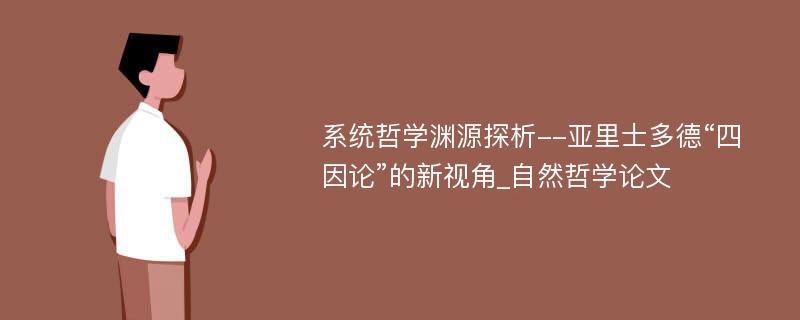
系统哲学探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透视论文,哲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旨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进行一种新的透视,以表明其中所包含但尚未很好发掘的丰富的系统思想。本文试图阐明,“四因说”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系统哲学。其基本问题——“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实质上是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论是“四因说”中真正的合理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并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四因说 整体论 系统哲学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系统思想的始祖,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1〕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公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通常学者们只是把这种系统思想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些闪光点,而笔者却认为它是贯穿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条红线,特别是其“四因说”的真正灵魂。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及自然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透视,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的“格式塔变换”。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以阐明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及自然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系统思想。
一、出发点:集大成的“四因说”
学界公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然而具体来讲,“四因说”是怎样集大成的?在学界还缺少一种清晰的说法。笔者提出,“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流派及随后思想发展的一种独到的概括和总结,一种全新的提炼和升华。
关于“四因”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实际上有所提及〔2〕。首先,“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来源于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显然,从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谟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都是“质料”的始基作用。其次,“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毫无疑问,以“火”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其善变的动力作用,而“爱憎说”进一步把动力划分为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不难看出,以“数”和“理念”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可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因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趋向性。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似乎都在寻找我在《物理学》中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其它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是模糊的;他们有些象是说到了,又象全没说到。”〔3〕可见,通过“四因说”可以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各流派和学说,进行一种“对号入座”的整理。这一点在学界尚未引起注意。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质料”、“动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难想象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则颇有争议。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无论在技艺制造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和在技术产物里是一样的。”“如果因为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不承认产生有目的,这是错误的。”〔4〕从亚里士多德的辩解来看,目的性与产生、发展的过程相关,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而在于是否存在不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最终结果。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道出了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称之为“动态目的论”的“等结果性”。贝塔朗菲证明,开放系统的稳定状态具有“等结果性”(即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稳定的状态)。因为开放系统并非人和生命特有,所以目的性也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目的论过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现在成了科学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5〕这至少表明了应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进行重新的认识。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还在于阐明了“四因”的相关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已分别涉及到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们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难以对自然界的整体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解释。比如,水性不变何以说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释各种事物确定的形式?“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何来相对稳定的组成、形式和趋势?何以对其进行认识?抽象的“数”、“形”怎么能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立存在?单一的“存在”又如何说明自然界多样性的来源?可见,任何的偏颇都会带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难。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6〕以房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建筑师、建筑术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其它任何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按此类推。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集大成的“四因说”确比以前的自然哲学理论更全面,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如果允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赋予现代含义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质料”相当于组成;“形式”相当于结构;“动力”相当于相互作用;“目的”相当于功能。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及描述都离不开组成、结构、相互作用和功能这四个要素。从这个含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确实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系统哲学。
二、主旋律:整体性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而“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认识”〔7〕。所以“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四因”当中“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统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8〕。所以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便归结为“质料”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中体现出来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学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评价,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充满矛盾:当他指出“质料”的“基础”和“底层”作用时是唯物主义的;而当他强调“形式”的“本体”地位时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质料”和“形式”相互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第二,“质料”和“形式”皆为“本体”的矛盾实质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把它归结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不恰当的。首先,从定义来看,“质料”(物因)表示“所从出”,这姑且可以看成物质;而“形式”(本因)表示“怎是”,即存在方式,这又怎么能等同于意识呢?其次,从属性来看,“质料”被认为具有“潜在性”(亦此亦彼的多种可能性);“形式”则被认为具有“现实性”(非此即彼的相对稳定性)。难道说“潜在”和“现实”能够区分物质和意识吗?再次,从事例来看,土是砖的“质料”,砖是土的“形式”;而砖是房的“质料”,房是砖的“形式”。这里哪来的意识呢?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四因说”贴上唯物或唯心的标签。
“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与其说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还不如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指出:“字母是音节的原因,材料是技术的原因,部分是整体的原因,前提是结论的原因,意思都是‘所从出’。在这些对偶中,前一类为基础质料(和部分);后一类为本质——或为整体,或为综合,或为形式。”〔9〕
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旧的问题,认识上的“格式塔变换”就发生了。原有的一些难题得到了新的解答。比如:“形式”(结构)、“目的”(功能)、“动力”(相互作用)这三者都是整体的属性,所以可以“归一”;“质料”作为部分有多种结合的可能,所以具有“潜在性”,而“形式”作为整体一经产生便相对确定,所以具有“现实性”;“形式”和“质料”相对不同的层次而言,所以砖瓦相对泥土是“形式”,而相对房屋却是“质料”;“纯质料”是最低层次的客体,所以它不再成为任何“形式”,“纯形式”则代表最高层次的客体,因此它不再充当任何“质料”;至于说“纯形式”、“至善神”和“第一推动”的统一,也不过是表明了一种自然神论的观点,即最高层次的自然界是以自身为目的、自己推动自己的。这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唯心主义。
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把它看成是简单的逻辑矛盾也不妥当。关键在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本体’可有二义:(甲)凡属于最低层次而无须再以别的事物来为之说明的,(乙)那些既然成为一个‘这个’也就可以分离而独立的”〔10〕。按笔者的理解:前一“本体”指“本源”;后一“本体”指“本质”。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都不可缺: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另一方面整体不能还原为部分,没有整体部分不足以决定事物的质。由于整体同时具有数量上的“加和性”与性质上的“非加和性”,所以它一方面不是“本体”,另一方面又是“本体”。这里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所谓的“动摇”和“悖理”只不过是它的表现形式。列宁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他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11〕只有透过这些表面的意见分歧,才能把握住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辩证法的主旋律。
三、里程碑:整体论的先行者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加以探讨的人。在探讨过程中他毫不掩饰其鲜明的整体论倾向,即把整体摆到第一位。从逻辑上来看,“整体在先”包含两层意识:第一,在定义上部分往往要借助于整体来进行说明。比如“弧是圆的部分”、“手是人的器官”等等。第二,在程序上认识总是先把握住整体再深入到部分。比如,先把握房子整体再细看其组成部分。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我们来说,明白易知的起初是一些未经分析的整体事物。而元素和本源是在从这些整体事物里把它们分析出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12〕这样一种从整体出发,又不限于整体,而深入到部分的方法论,可说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
亚里士多德在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其中以生物学方面的建树最为突出。为什么会这样?科学史家丹皮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所以在生物学方面成功,是因为生物学直到近年来为止,一直主要是一门观察的科学。”〔13〕笔者认为,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命在自然界中具有最明显的整体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这个整体论者在生物学中,能够如鱼得水,大显身手。确实,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同他的整体论自然哲学密不可分。他的四部生物学著作:《论灵魂(生命)》、《动物自然史》、《动物的组成部分》、《动物的生殖》,恰好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现实到潜在而排列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整体论自然哲学的思想。
关于生命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灵魂”的作用。他指出:“灵魂作为躯体的原因,是用在我们已区分过的三种意义上:它是躯体运动的始点;是躯体的目的;是一切拥有灵魂的躯体的主体。”〔14〕那么,“灵魂”作为躯体的“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又有什么具体的特点呢?首先,在“动力因”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看到了“一”、“多”对应的非线性。他指出:“潜能明显地将分作无理知与有理知之别……且有理知公式的各种能力可起相对反作用,而每一无理知能力只会起一种作用。”〔15〕确实,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中无生命可言,只有在“一多对应”的非线性关系中才有生物的“活性”。其次,在“目的因”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看到了控制的作用,只是对其机理还不能加以肯定。所以他这样指出:“灵魂作为躯体的现实性和舵手作为船舶的现实性是否有意义相同还不十分清楚。”〔16〕意味深长的是在两千多年后,维纳把机器与生命作类比创立了控制论(Cybernetics)。该词正是由希腊文“舵手”(kubernētēs)演变而 来的。最后,在“形式因”上,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了整体的不可分性。他指出:“当灵魂一旦离开了一个活动物,这些动物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只是形状如前,而实际上已不复是原来的部分了。”〔17〕同样,离开了躯体的手已不是真正的手,只能是空有其名姑相称呼而已。这一点在黑格尔、恩格斯、列宁等辩证法大师的有关著作中一再被引用和肯定。
关于生物的分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两分法”的自然分类原则,前者的分类依据是“水生与陆生”、“有翅和无翅”等外在属性;而后者的分类依据则是生殖方式等内在属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两分法中诸动物的天然组合已被拆散,以致种属失序是不可避免的。”〔18〕比如蝙蝠和老鼠被人为地分开,鲸和鱼则被混为一谈。如此为分类而进行的分类,掩盖了生物间的内在联系。反之,依据自然分类,亚里士多德却得到一个低等植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甲壳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的连续阶梯,并得到许多可贵而超前的思想火花。比如:“自然界的发展由无生命界进到有生命的动物界是积微而渐进的。”〔19〕对此达尔文非常佩服,并说他崇拜的林耐和居维叶在亚里士多德面前只配称小学生〔20〕。另一方面:“后于生成的总是先于本性,凡最后发育完成的,在本性上最先存在。”〔21〕对此黑格尔心领神会,他指出:“为了理解低级阶段,我们就必须认识发达的有机体。因为发达的有机体是不发达的有机体的尺度和原型。”〔22〕这里关键在于进化,发育的实质是信息量的增加,所以自上而下,将今论古自然更合乎逻辑。实际上这也是“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的另一种表述。
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杰出典范,即便从整个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来看,它也并没有因其古朴的风格而失去自身的影响。在黑格尔的辩证法自然哲学和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自然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黑格尔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宝藏,许多世纪以来,差不多完全不被人所知悉。”进而指出:“假使一个人要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23〕恩格斯同样认为:“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24〕罗素则指出,评价黑格尔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整体比部分是不是更实在?是不是更有价值?黑格尔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5〕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处在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有机时代”,他本人也被称为“进化论者哲学家”〔26〕。笔者认为,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最大特点便把是“有机性”本体化,从而得出“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27〕
继黑格尔之后,贝塔朗菲把一般系统论叫作“新的自然哲学”〔28〕。新就新在借助数学方法来研究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般系统论对‘整体’和‘整体性’进行科学探索,而这在不久以前还是超出科学的各个边界的形而上学观念。”〔29〕毫无疑问,就整体论的倾向而言,贝塔朗菲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观点。贝塔朗菲处在一个科学整体化的新时代,作为一个理论生物学家,他看到了以生命科学为制高点而深入探索复杂性的科学前景,并且深深体会到整体论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今天的系统哲学。如果说系统哲学是未来科学的一棵常青树,那么其根却深扎于悠久的历史土壤之中。正是通过贝塔朗菲,亚里士多德的“宝藏”再一次被人重新发现。这对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当今的系统哲学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1994年12月21日收到。
注释:
〔1〕庞元正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2〕〔3〕〔7〕〔10〕〔1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19、31、3、95、172页。
〔4〕〔6〕〔8〕〔9〕〔1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65、48、48、51、15页。
〔5〕〔28〕〔29〕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秋同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0、9页。
〔11〕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页。
〔13〕〔26〕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370页。
〔14〕〔16〕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487、482页。
〔17〕〔18〕〔21〕亚里士多德:《动物四篇》,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25、34页。
〔19〕王大庆:《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集》(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20〕周帮立:《达尔文年谱》,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见“达尔文1882年致奥格尔信”。
〔22〕〔27〕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1、34页。
〔2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34、28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页。
〔25〕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0页。
标签:自然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