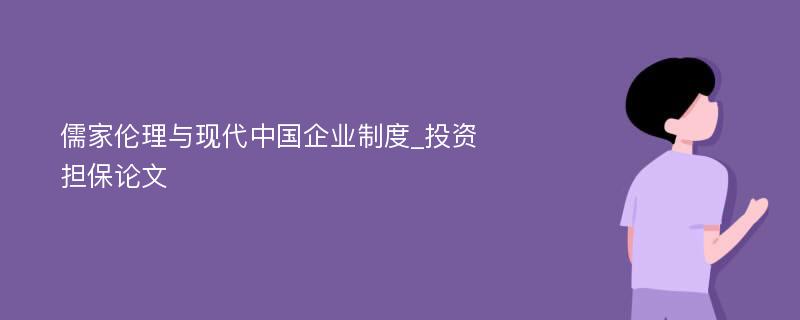
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企业制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1-0072-10
关于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问题笔者以往基本上是从正面的合理性来考察两者的关系(注:拙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论述了儒家伦理并没有构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而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和市场特色的内在依据;拙文《简论中国近代儒家伦理之转化为经济制度》 (载刘小枫、林立伟编《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版)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述了家族企业和若干市场制度的合理性。),而对儒家伦理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负面影响关注不够,本文根据新的认识,准备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个论题进行阐述。
一、企业制度的目标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企业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会遵循节省交易成本的总目标。企业和市场不过是经济组织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交易无论是在企业内部通过等级制来组织,还是在企业之间通过市场自发地进行,都是一种决策变量,具体采取哪种方式,则要在比较两种交易成本的高低之后决定(注:[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11页。)。每一种企业制度形态及相关制度的产生都是人们寻求最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因为企业和市场可以相互替代,人们往往根据历史条件的演变,在企业和市场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到底应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企业制度的演变既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相关,也与市场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密切关联,因此,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研究企业制度。
根据威廉姆森的总结,在非专用性投资向专用性投资转化的过程中,企业制度和相关制度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非专用性投资是指可以较自由地改变投资形态的投资;而专用性投资是指专为生产某种产品所作的投资,很难改变形态。前者如商业投资,后者如技术要求很高的规模很大的工业投资。
在非专用性投资的状况下,可以主要依赖市场,这时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而在专用性投资的状况下,完全依赖市场则很容易造成过度竞争,或产销脱节,也不易筹集大规模的资金,因此,企业制度和相关制度会逐渐发生深刻的改变。
民营企业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由道德背景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上涨问题。一个社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由道德背景很容易诱发各种交易成本上涨的事件。由道德背景诱发交易成本上涨,既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
大隆机器厂是1902年由严裕棠和褚小毛合作开设的,严、褚二人的分工是:严负责对外兜揽生意,褚负责对内管理生产。大隆厂开办后的几年内生意很好,但每年年终结算,除了开销,并不赚什么钱,有时还有亏损。这就引起褚小毛的不满,认为是严裕棠在外接业务时有舞弊,要严退伙,并诉诸公堂。官司从1905年打到1906年,终因查无实据而无法使严的舞弊指控坐实。结果是褚小毛退出大隆,另开新厂(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大隆厂的这次分裂是褚小毛不满严裕棠的道德品行而引起的,严的道德问题造成了大隆厂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涨。而这种情况在以后严裕棠一人当家时却没有发生。这说明交易成本与企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把管理费用视同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
190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荣瑞馨、张石君等共7人发起创办无锡振新纱厂。1911年沪上刮起橡皮股票风潮,牵连甚广。作为振新大股东和实力人物的荣瑞馨在风潮中亏累巨款,便暗中打起振新的主意来。振新地契存在董事唐水臣处,唐与荣瑞馨是姻亲,荣瑞馨私自从唐处取走地契,以向汇丰银行进行抵押借款。他又通过荣宗敬兄弟企业茂新批发所中的熟人,私用茂新印鉴为自己向汇丰银行借款作担保。荣瑞馨还款无力,事情终于败露,汇丰向担保人茂新追讨,险些将茂新厂房查封(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43年油印本,1905年纪事,1910年纪事。)。荣瑞馨一个人的道德品行,竟然差点拖垮产销经营都正常的两家企业。
洋行在雇佣买办或买办在效力于洋行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个道德背景问题,前者并会因此而涉及企业的交易成本。1864年丽如银行在上海的买办冯兴,欠下中外商人10万多两银子债务潜逃(注:North China Herald.4 June 1864,91.)。1884年太古洋行在上海的买办杨桂轩欠下中外商人10万多两银子债务潜逃。(注:North China Herald,29 October 1884,473.)这样,银行和洋行就不得不为逃走的买办还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大班卡梅伦爵士因中国商人的诚实而说了称赞的话,可20年后,这家银行的北京分行却蒙受了或许是买办贪污史上最惨重的损失,北京分行买办邓君翔于1927年挪用行款,欠下400多万两银子的债务。(注:《华字日报》(香港),1927年5月4日、6日、11日。)
反过来看,买办也常常有被洋人欺骗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到上海等通商口岸来淘金的洋人,不少是穷光蛋和流氓无赖,“几乎都没有钱,没有大产业”(注:郝延平著,李荣昌、沈祖炜、杜恂诚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他们利用买办的押金办企业,如果企业失败,买办就难以追回他的押金。
由道德背景引发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而且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场行为中。信口雌黄,名实不符;言不由衷,诱人上钩;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如此等等,都会使真实的信息变得十分昂贵,会使谈判、履约变得十,分艰难。这就会使双方在谈判、交易和诉讼过程中花费许多额外的费用,使成功的概率降低,失败的概率提高,也就是提高了交易费用。
近代中国火柴业大王刘鸿生是作为推销开滦煤的买办起家的。1925年至1930年间,刘鸿生在同义泰兴煤号老板杜家坤合作推销开滦煤的过程中,两个合作伙伴始终明争暗斗,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人间义泰兴的一个董事:“他们(指开滦售品处)同我们有密切关系,何以竟同我们竞争得如此激烈?”该董事回答:“我们所有的开滦售品处的股权可能被排除。”(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这样的“合作”无异于同床异梦。“合作”的结果,彼此增进的不是友谊,而是不信任、疑忌,进而发展到彼此大动干戈。交易成本当然也就随之而水涨船高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道德背景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在一些情况下,某某人的道德优劣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并不存在真凭实据,只是出于对他人道德品行的怀疑,便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爆发诡计大战、损人大战,各方都陷入背离道德的泥潭,并都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儒家伦理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影响
由于道德背景同交易成本紧密相关,民间商人在创办企业时,就会去寻找一种企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道德背景刺激交易成本上涨的机会最小。人们找到了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而在这种企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儒家伦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族企业并非是中国特产,西方也有。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除了家族企业外,合伙制也是非常普遍的,很难说家族企业就是西方早期民间企业制度的主流。而中国家族企业的覆盖面之广和延续时间之长,却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
之所以说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是民间企业的企业制度,有以下三点理由:其一,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不是政府硬性规定的,而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其二,家族企业是中国近代民间企业制度发展的趋势和必经阶段;其三,这是一种社会规范,绝大多数企业都循此规律,不管是独资、无限责任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不管是否有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形式,绝大多数中国私人企业是由家族控制的,或者说其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同时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的。
家族企业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儒家伦理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有两方面的涵义:
第一,希望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企业主要管理层模式。这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缩小企业经营者圈子的措施。深受儒家传统伦理熏陶的中国近代企业家,总是信不过别人,生怕与他人合作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其结果只能安排自己的子侄、亲属在企业的高层要津上做事。这样,由家族控制企业这一点是做到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道德危机。族中子侄尽管在形式上都会听命于家长,但难保不会出现人品道德问题。所以企业家为了逃避一种道德危机而陷入另一种道德危机。当然,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宁可选择家族企业,毕竟血浓于水,血亲与外姓相比,前者毕竟更容易获得信任。而且,家族企业出现道德危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问题在第一代在位时未必就会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使出现苗子,第一代的心理也往往希望通过加强管束和提倡中国合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来加以遏制,不像同外姓的关系那样容易迅速地彻底破裂。
在这一层面上,企业家对儒家伦理的重视,一是为了正心修身,二是为了齐家。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对上海十里洋场的“道德沦亡”感慨系之。他说他自己“平居省俭如在乡村”,而“看得洋场习气,奢靡成风,教育无方,殊非久传之道。历观富贵之家,无传二三代者,十年三反复,于今尤甚”。(注:朱德生:《乐农自订行年民纪事续编》,1949年油印本,1940年纪事。)他把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上升到企业成败、家道延续的高度来认识。
企业家还希望用儒家伦理来协调家族企业中家族管理层的内部关系。家族管理层的父子矛盾和兄弟矛盾,除了人的道德品质因素外,主要源于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为了缓解家族内的矛盾,家族中人或家族会议就往往强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劝导儿子孝顺父母,弟兄间各方相互谦让,勤俭克己,安于本分,而不要兄弟阋于墙。例如:1926年9月间,恒丰纱厂聂氏家族,鉴于聂潞生的独断专行,聂云台捧出母亲曾氏,组织了一个“聂氏家庭集益会”来协调各房兄弟的利益和行为。该集益会制定了“简章”,强调“以道德礼义为标准”,遇事“衡以圣贤古训”,要做到“大家明澈谅解,齐心合德,凡事不求勉强执行”(注: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 45—16页。)。即使是那些家族内和谐融洽的企业家,为了防患于未然,也要特别强调树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如荣德生曾为了“重振旧道德”而印行《人道须知》(注: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2年纪事。)。
因而,重视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说教就是为了搞好家族企业,要搞好家族企业就要遵行这些伦理规范,这已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家族企业制度规范之带有儒家伦理的印记,是明明白白的。
第二,把企业当作放大的家族,企业当家人也就成了这个大家族的家长。
大成纱厂厂主刘国钧用儒家伦理引导工人热爱工厂,树立“公司大家庭”的思想。他以“忠信笃敬”作为“厂训”,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如建造宿舍,办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组织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搞公墓,建造公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企业有功之臣立碑入堂(注:魏明康等主编:《中国近代实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3页。)。
陈光甫是一个很跟得上时代的银行家,他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是比较西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然是少数非家族企业之一,但陈光甫仍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并用儒学来规范大家的认识。他说:“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注:陈光甫:《三十四年十月陈先生在纽约发致告同人之立命寄言》,载《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印制,第207页。)陈光甫所谓的“忠”,是指“为理想,为事业,为团体”(注:陈光甫:《三十四年十月陈先生在纽约发致告同人之立命寄言》,载《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印制,第207页。),陈光甫是从企业大家庭的角度来尊儒的。中国近代企业的这一特色,我们至今在东亚许多国家仍可见到。
三、儒家伦理对市场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影响
儒家伦理所具有的影响力,只是关系到市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市场制度的全部。
儒家伦理重视家族关系、氏族关系,而同乡观念则是家族氏族观念的放大或延伸,或者说同乡观念是家族观念在社会关系上的放大或二次投射。因而,尽管孔子没有直接论述过同乡关系,但同乡观念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重视同乡关系的出发点,和重视家族关系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一个家族可以控制一个企业,但不可能把整个市场都控制起来,不可能只同本家族的人做生意,因而势必要有一个非家族的交易网。同时,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须尽可能地限制这个交易网,避免同不知底里的人打交道,而以诚信为基础的同乡观念则引导人们去完成各自交易网络的编织工作。
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中,做生意的人都以同乡关系结成“帮”:广东人在一起结成“广东帮”,宁波人在一起结成“宁波帮”,苏州人在一起形成“苏州帮”,无锡人结成“无锡帮”……同乡之间抱成一团,尽可能地互相帮助,互给优惠。
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观念是认钱不认人的,只有以利害关系结帮,而没有以同乡关系结帮的。一个新式商人或实业家,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同乡意识,实在是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特点之一。
一般来说,以诚信为基础的同乡商帮是市场各种交易活动的基础。当然,非同乡之间也可以有交易活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容量的扩大,非同乡之间势必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但这后一步只是在有了同乡合作的起点才得以迈出的。因而,同乡交易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市场制度的基础之一。
买办制度和担保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相关制度。这两种制度也部分是由家族观念和同乡观念转化而形成的。
买办是一种象征权力和财产的职位。但是要进洋行当买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著名商人或别的买办为之担保。在某些情况下,担保人自己可以由别人再担保,这样就构成了一种双重担保。还有一种联合作保的方式,即由二至四个担保人联合为一个买办担保。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故丧失了履约的能力,那么其担保责任就由其余的人分担。为此保证人也能从他所担保的买办那里按年取得一定份额的回报。保证人要为所担保的买办立下保单,保单上特别注重说明被保人的忠实可信。担保人所负的责任很大,因而人们不肯轻易为他人当买办作保。在一般情况下,担保人首先挑最信得过的家属成员担保,因此会发生家族买办网的情况。例如: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20世纪30年代止,在约50余年的时间里,洞庭山帮席氏家族共有23人担任过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职位,有5人担任2家洋行的买办。几乎所有上海著名的外商银行的买办职位,均为席氏家族囊括。(注: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9页。)天津人王铭槐家族中当买办的,除了他自己外,有3个儿子、9个孙子、4个内侄、1个外孙、2个姻亲,由他介绍当买办的同乡和朋友有6人(注: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
洋行每每偏向于雇佣来自同一家族的成员。早期太古洋行的上海买办都来自陈家,而其香港买办都来自莫家(注:Sheila Marriner and Francis E.Hyde,The Senior John Samuel Swire,1825~1895,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67:37.)。1860年琼记洋行的5个买办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注:Stephen 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962,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Harvard University,1971:40.)。无论从担保人还是从洋行方面看,这样的安排都比较靠得住,交易成本低。
进洋行当买办要有人担保,就更一般的情形而言,在近代中国,进任何企业做事都要有人担保,或有店铺为之担保(铺保),有的中国企业还要求雇员交付押金。同为买办担保的情形相似,担保人一般只愿意为自己的亲属或熟知的同乡担保,形成家族雇员和同乡雇员的普遍现象。一个企业的大多数雇员来自同一城镇、乡村的情况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某个行业主要由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的人所经营。这种担保制度使用工的交易成本减至最低。
完全可以这样说,家族观念和同乡观念奠定了买办制度和担保制度的部分基础,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在这两种企业相关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1935年以前,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来进行行业治理的同业组织,同乡观念在行业治理中竟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上海钱业公会的人会钱庄按股东或经理的籍贯可分成很多帮派(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69~771页。),在帮助陷入资金周转困难的会员钱庄时,同乡钱庄有时义不容辞地肩担重任。1929年2月,上海钱业公会会员裕成钱庄陷入资金困难,公会决定帮助,具体办法是:由公会名义筹垫现银20万两,其中一半即10万两由裕成的同乡钱庄“山帮”协助,另外10万两主要由公会执行委员各庄垫出(注:上海钱业公会通知执行委员各庄函,1929年2月24日。上档S174-2-90。)。所谓“山帮”,据考证,即为苏州洞庭山帮,从1929年2月24日上海钱业公会致垫款经手庄敦余庄的信中看,山帮8庄中6庄各垫款1.1万两,2庄各垫款1.7万两,合成10万两之数(注:上海钱业公会致敦余庄函,1929年2月24日。上档S174-2-90。)。
在为会员追讨欠款时,有时以同乡出面晓以利害,较易相互沟通。1931年1月,公会会员信裕钱庄与林庆记发生欠款纠葛,公会请三山福宁会馆以乡谊开导林庆记,“从速理了,以免纠结”(注:上海钱业公会致沪北三山福宁会馆函,1931年1月8日。上档S174-2-198。)。1929年6月江西吉安益记申庄倒闭,欠下公会会员裕大等庄8万余两,公会写信给上海江西会馆,要求该会馆诸董事主持公道,妥善处理吉安益记申庄倒闭事(注:上海钱业公会致上海江西会馆函,1929年6月6日。上档S174-2-53。)。
四、分家析产和对异姓的不信任:家族企业及传统观念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专用性投资的退出成本很高,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横向兼并、扩大企业规模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当然会引起企业管理方式的改变。同时,有的企业实行多元化投资,这也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是两个比较突出的案例。
荣家企业涉及纺织和面粉两个行业,随着企业兼并和新设企业数量的增加,其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1年设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总公司设庶务、文牍、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各部。原来的体制是各厂各自生产、销售和资金调度,而在新体制下,各厂的经理、厂长对工厂负责,着重生产管理,总公司则集中掌握各厂的购料、产品销售和资金调度。在业务方面,面粉和纱布是分别进行的,犹如两个事业部(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97页。)。
刘鸿生的企业分属火柴、水泥、煤矿、毛纺、运输、码头仓库、金融等各个领域,规模越来越大,其所属企业中,有的企业有时积余资金,但不一定亟需扩充,而有的企业需要扩充,却缺乏资金。刘鸿生认为,如果实行集中管理,以盈济虚,统一调度,肯定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因此于1930年筹划组织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正式成立,该公司以法人资格对刘鸿生所属各企业行使管理全权(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9页。)。
但是,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的集中管理都遭遇挫折。尽管两者的挫折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找到内在的关联。荣家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荣氏二兄弟除掌握总公司外,各厂负责人绝大多数是荣氏家族的子侄或亲戚,间有无锡同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289页。)。荣宗敬逝世后,荣氏家族缺少凝聚核心,抗战胜利后荣鸿元、荣尔仁都对企业提出了改革计划,可惜的是,荣鸿元和荣尔仁互相拒绝对方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荣尔仁的计划甚至得不到他的父亲荣德生的支持。家族企业在缺少凝聚核心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分家析产的现象,许多家族企业二代而亡,就是因为分家析产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分家析产可以有多种形式,当时的荣家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是企业控制权的分化导致企业总体实力的下降:“长房一支以荣鸿元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一、六、七、九厂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厂:二房一支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的二、三、五厂,茂新的一、二、三、四厂和天元、合丰等厂:另外后方一支,在李国伟掌握之下,管辖申四、福五等厂。而长房一支内,王禹卿掌握福新各厂自成一脉,吴昆生掌握申九,渐渐趋向独立。”(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页。)
刘鸿生企业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企业经营公司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各企业对刘鸿生所想培植的高层职业经理华润泉等人的不信任,各企业担心华润泉等高层职业经理“通过集中管理办法,全面掌握刘氏企业,因此各有戒心”(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这也同时反映出刘鸿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坚决的。对非家族、非同乡的彼此猜忌,使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成长举步维艰。
美国学者钱德勒在他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论旺了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和经理人员支配地位的形成。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的发展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中国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还不是非常迫切。这除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之外,家族企业和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很不发达,企业公众比程度很低,企业很容易因家族因素而导致分裂。1916年上海证券市场上公司股票才12只,20世纪20年代上海等地的证券交易以政府公债为主,“公司事业,尚未发达,股票之流通,为数极少。其营业良好者,大都稳藏于股东之手。价格固定,难成市面。若信用不佳者,虽贬价亦少人过问;且涨落过巨,负险极大”,因此上海证券市场并不能“实现公司股票之交易”。至于公司债券,就更无从谈起了。(注: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2年版,第369页。)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美国股票拥有者的数量从1900年的50万增至1920年的200万,再增至1930年的300万,从单个公司来看,规模也在迅速壮大,美国AT&T公司,1900年共有7500个股东,到1931年股东数量增至64.2万人(注:[澳]戈登·鲍易斯等:《现代商务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股票交易量也有了同样的快速增长,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公司从1907年的569个增加到1939年的1712个,并且它们的市价总值增加了5倍还多(注:[澳]戈登·鲍易斯等:《现代商务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发达的资本市场成为美、英等国企业兼并和扩大规模的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注:[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437~438页。)。中国的企业规模是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相匹配的。企业规模小,家族企业就很难实现向经理人层级管理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