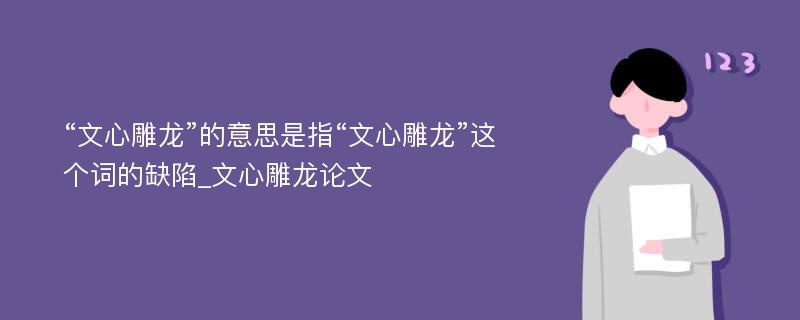
《文心雕龙》辞意指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意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3)01-0069-04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不朽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的确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怪乎被章学诚誉为“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1]之作,然而,所谓白璧微瑕,《文心雕龙》一书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乃至抵牾的地方。
我们且从刘勰的文学史观谈起。人们的文学观念时常会在他们对前代文学的评价中体现出来,刘勰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历代文学之递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精到之论,但亦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这里不妨将《通变》与《时序》中的两段相关文字加以比较。刘勰在《通变》篇中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在这段话里,刘勰对上古三代的文风持肯定态度,其中尤其推崇商周,认为是“丽而雅”。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引述刘禹昌语:“刘勰认为象《诗经》的‘风’、‘雅’诗篇,是思想既雅正,艺术又丽则的‘文质彬彬’的代表作,因此那是最合乎标准的诗作,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2](P1090)就刘勰的文学思想、审美倾向而言,刘禹昌的这段话概括得是非常准确的,换言之,这也就是刘勰的评价标准。《定势》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这里的“典雅”、“清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刘勰对楚骚之后的文学则颇有微辞,我们看到,上面那段话对周以后文学的评价便完全不同了,认为楚汉以至刘宋都是一味模仿前代、忽略和疏离古代,从“侈而艳”到“浅而绮”,甚而至于“讹而新”,“从质及讹”,一代不如一代,愈来愈淡乎寡味,终于造成文风衰落的局面。范文澜先生也曾提到这一点,范注云:“彦和于商周以前,不称‘后模前代’……至楚汉以下,则谓矩式影写,顾慕瞻望,而终之曰‘竞今疏古,风昧气衰’,据此以观,文章须顺自然,不可过重模拟。”认为刘勰以文章贵在自然为标准,对楚汉以后的文章是持否定态度的。
对此,《时序》篇的观点则明显有别,看法更加客观中允,不再极力突出商周,指出历代文学“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对楚汉之后不再一概予以否定,而是就每一时代的文学实际作辩证的评价,这便是和《通变》的主要区别之所在。《时序》篇说,战国时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西汉“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遗风余采,莫与比盛”;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及至西晋,依然是“人才实盛”的状况,“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只是到了东晋之后,因“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受清谈风气的影响,才使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3],“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不难看出,刘勰的矛头显然是指向此的。通篇观之,这番话公允客观,符合文学发展实际,与《通变》篇对楚汉之后历代均加贬斥的态度是有显著区别的。
然而,从总体看,《文心雕龙》中所体现的刘勰的文学史观基本上还是贵古贱今的,即《通变》所谓“从质及讹,弥近弥淡”。除上述两篇之外,其他篇章也不乏类似的表述,如《才略》篇开篇即云:“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对上古之颂赞可谓不惮其繁。《程器》篇亦然:“《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斵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也是首先肯定上古,在肯定虞夏周书的同时,又对近世以来“务华弃实”的文风提出了批评。《定势》篇在对文章风格体势的内在规定性进行正面分析之后,又从反面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并特别批判了近世文人过分强调文辞之巧的错误倾向,指出“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刻意讲求文章的形式与技巧,以实现其求新的目的,而这种一味追求新巧的做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近世的文体之弊:“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
再看《情采》篇中的一段: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以及《指瑕》中的一段: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而晋末篇章,依稀其旨,……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
毋庸赘言,我们便不难从中见出刘勰这种贱今贵古的文学观念来。这并不奇怪,它与刘勰宗经征圣的思想一脉相承,略无二致。除去上述几段较为明确的言语之外,在其他一些篇章的文意的缝隙之间也时常可以体味出这种倾向。然而,只有一处例外,那便是《时序》篇中人们为证此书之写作年代而多所引述的一段话:“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时序》篇里,刘勰在将历代文学演变的规律加以客观总结之后说了这段话,设若我们把它放回《时序》篇中,再次将全文乃至全书通读一过,便会发现这段话与书中其他部分的语言在措辞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语气上完全是尽善尽美的称颂,言语之间对齐皇的溢美之辞可谓极矣至矣,对比来看,这与前述种种贬抑“近代辞人”的言辞颇不相类。
刘勰对上古圣哲之文推崇备至,所谓“夫子文章”、“圣人之情”,“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3],是雅而正的典范;对“近代辞人”之文则多有訾议,或隐或显,不一而足。如上所述,那么多贬抑近世的言辞,为什么偏偏这一处不同了呢?这是《文心雕龙》一书中又一处作者观点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和上述《通变》与《时序》的差异相比,此一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矛盾、抵牾了。那么,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或许是最好的解释。对辞人文士,所言不妨率意一些,对圣上天子则万万不可。《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近年来新说颇多,我们认为此事还宜慎重。《诗品》叙陶渊明在中品,众人异说亦多,钱钟书力驳其非,《谈艺录》云:“……记室之评渊明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又标其‘风华清靡’之句。此岂上品考语。固非一字之差,所可矫夺。”对照钱说,反观“皇齐驭宝”云云一段,称颂之意彰显无隐,“齐末说”恐难移易。当然,《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解决和所能解决的,这里只是对涉及到的问题作一个臆测。此外,《文心雕龙》一书对另外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观点不一,文意相悖的矛盾。例如,在建安乐府诗的评价方面,《明诗》与《乐府》两篇中的观点即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而言,《明诗》篇中的看法较为客观,情感上大体是褒大于贬的;《乐府》一篇态度则完全不同,情感上基本呈现为贬意,葛晓音先生对此早有察觉,她在《论南北朝惰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4]一文中说:“刘勰对楚骚到建安以后文风的分析颇多精辟之见,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主要反映在对楚骚、建安文学与风雅正声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他……在《明诗》篇里客观评述了建安五言诗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然而刘勰在《乐府》篇里又指责魏之三祖的某些篇章‘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子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可见刘勰对建安乐府诗的看法仍有儒家的偏见,与他对《离骚》和建安五言诗的评价相矛盾。”显然,刘勰对建安文人、特别是三曹的评价在上述两篇中的确是不完全相同的。
另外,书中关于玄学“言意之辨”这一问题的看法前后也不尽一致。对此,刘勰似乎是倾向于言不尽意论的,他在《神思》篇论构思与创作时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墅乎篇成,半折心始”,这段有关艺术想象活动特点的描述与陆机《文赋》中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可谓异曲同工。他认为,作者的观念、思想、意图很难在文章中得到完全表达,毫无疑问,这一概括是符合创作实践的,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勰“言不尽意”的玄学主张;《隐秀》篇也有类似的话,“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指出“隐”是文外所含的言外之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序志》篇亦云:“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镬。”尽管刘勰说这话时或许意不在玄,但对于现在讨论这一命题的我们而言则不啻是明确地亮明观点的“把柄”了。然而,有了这样几个证据是否就可断言刘勰是言不尽意论者呢?情况或许并不这么简单。《物色》篇的一段话便有所不同,刘勰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这段话中,刘勰认为物象是可以无隐地描绘的,《诗经》的语言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一言穷理”,而使“情貌无遗”,甚而至于因其对景物特征的切中“要害”的把握,而使“后进锐笔,怯于争锋”。《夸饰》篇又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这段话讲得比较明白,就是说形而上的“道”人们是无法尽言其意的,形而下的“器”则不难道尽其“真”。“文以明道”是《文心雕龙》一书的基本观点之一,在刘勰看来,至高至上的“道”只能借助“文”来表现;其自身是无法言说的,而外物器用就不同了,人们的言辞能够对其加以充分的描摹。因此,从这两段话来看,刘勰对言尽意的观点还是有所认同的,这就使我们听到了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关于“言意之辨”这一问题的不同声音。
那么,《文心雕龙》一书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矛盾呢?本文不拟解决这一问题,这里只能作一些猜测。是刘勰的才学不够吗,恐怕不是。刘勰是齐梁时期极富远见卓识的学者、文学理论家,对文学艺术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序例中说,“……深感作者刘勰熟读群经,博览子史,于齐梁以前文集无不洞晓,而又深通内典,思想绵密。”因此,学识的问题大约不是导致上述矛盾的原因。可能的一种推测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所用时间较短,书成之后对全部内容未做细致巡检和打磨,从而导致了个别篇章矛盾的产生;然而,问题的答案或者也可以恰恰相反,即由于作者写作该书花费了较长的时间而使篇章之间观点相异。这里的假设便是,或许早在定林寺整理经藏之时刘勰即已开始该书的写作,而生活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又使其难以摒弃一切外务来专力于此,因此,各篇内容是作者长期思考,铢积寸累而陆续写成的,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导致作者已经有所变化的观念、看法在不同篇目中得以留存。也就是说,创作上的时断时续、历时多年是上述矛盾产生的根源。但是这还不大说得通,因为,对博通古籍的刘勰而言,完全可能在最后成书时做系统的检查和修正,以避免上述矛盾的产生。其中有一种可能性也许可以成为托辞:在各篇即将完成的最后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或许他为了将其投之权贵而来不及细细推敲,于是,只得仓促间定稿,于是,才有后来干谒沈约之事。当然,这更是完全凭空的推想了。
综上所述,刘勰关于文学史观、建安乐府诗、言意之辨等问题的看法在不同篇章中隐含着若干不一致的地方,可见《文心雕龙》一书内容上的确存在一些矛盾和抵牾。(本文为2002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七界年会大会交流论文)
[收稿日期]2002-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