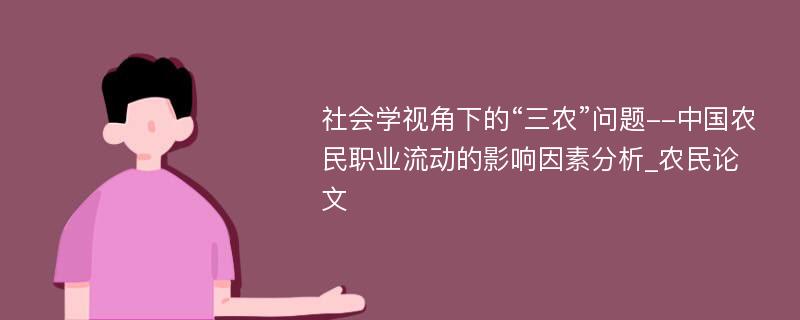
社会学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笔谈)——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三农论文,社会学论文,视野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意义的农民的职业流动最显著,最引人关注。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职业流动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进行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职业流动理论,而且可以澄清长期以来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和政策歧视。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始终象征着一种身份,隐含着传统和落后。尽管改革以来,传统意义的均质农民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从事非农工作,实现了职业流动。但其阶层属性和社会身份却没有改变,而只有使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的同步变化,才能实现农民流动的社会目标。在实践上,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民职业流动进行述评,不仅可以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职业流动的动因、方式、特征和影响农民流动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而且可以为加快农民身份转化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参考。
一、国内外关子农民职业流动的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者关于农民职业流动的理论非常丰富。在经济学界,如发展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拉文斯坦等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的“三态论”、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等等。在社会学界,索罗金早在1927年就编制了有关职业流动的23个表。此后关于职业流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1979年邓肯提出了统一联系模型,布里格、雅马库奇和芬根等对该模型做了应用和发展。展现了多变量分析方法在推动职业流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从此,对职业流动与年代、同龄群体、种族、教育等因素进行交互分析,就成为分析研究不同外界因素是如何影响职业流动的有力工具。(注: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此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则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民职业流动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的职业流动非常关注。美、英、法国等国都相继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国外民间组织和基金会都曾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国内,对农民职业流动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纵观近20年来的研究,可发现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人类学日益交叉、渗透和融合,已成为一个多学科、多理论、多角度参与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二是研究视角和理论的本土化。学者们逐渐摆脱了学术西化的影响,努力运用本土的经验材料,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理架构,如黄平的“生存理性”、文军的“理想选择”理论、王春光的“新生代农村人口”、李培林等学者则最早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农民的流动等等,都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三是研究主题和内容的深入化。如袁亚愚、李强等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孙立平、王春光、赵树凯等都对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做了不同视角的探讨。王春光的《中国职业流动中的不平等问题》着重对农民职业流动中的不平等与政策歧视进行了探讨。四是研究队伍的庞大和成果的丰硕。近些年来,由于农民职业流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把研究的侧重点转向了农民,研究队伍日益庞大,研究成果如汗牛充栋。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刘精明的《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民的职业流动研究》、王春光的《新生代农村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等都是一些精品。五是研究还存在不足。有些研究往往忽视农民流动这一重要的社会结构性现象与农村其他问题的联系,研究成果不能在现实社会政策中发挥应有作用,更不能对日益弱势化的农民群体的利益起到维护作用。而弥补研究的不足,是学界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分析
农民从本源上是一个职业概念,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却始终象征着一种身份,隐含着传统和落后。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意义的均质农民改变了职业,从事非农工作,实现了职业流动。但是其阶层属性和社会身份却很难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有了提高,但社会地位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独特的社会现象。而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制度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重工业发展的资本、资源得到保证,也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在国家的绝对权威下,一方面形成了全部社会资源集中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线。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这种界限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居民严格区隔开来,(注: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就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这种制度下,农村人口无法自由流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按照“比较利益”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农民职业转换受到制度性约束。
第二,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社会因素。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以及改变自身阶层属性方式的特殊性。在较少国家干预的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的改变,主要通过职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注: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而二元构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则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虽然已经走出了农村,脱离了农业,但是其身份却还是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而且,由于长期的文化偏见,农民又经常为城市人所排斥,他们与城市人有着深刻的社会隔阂,这就决定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影响了职业的流动。
第三,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像其他资本一样,也是投资的结果。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都属于人力资本要素。他列举了五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即“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能力、进行各种文娱体育的能力、创造能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注:张莹玉《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和信息等多种形式。”(注: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于流动的农民而言,其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年龄、性别、职业经历、家庭背景等等,都会成为重要因素,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事实上,中国农民无论在受教育的程度、个人综合素质以及健康等方面都无法与城市人相比较,这就决定离了他们无力进行投资,也无法获取回报,因而只能处于不利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解决农民问题,加快农民职业流动和身份转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一种推动身份变革以逐步减少农民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的核心是要把农民由单一的农民转为农业生产者、经营者、非农生产者、经营者和城市市民,特别是必须使一批不需要以土地为生者与土地彻底决裂,变成为农产品的纯商品消费者。而只有通过制度创新、社会改良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措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减少农民,使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同步变化,才能实现农民流动的社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