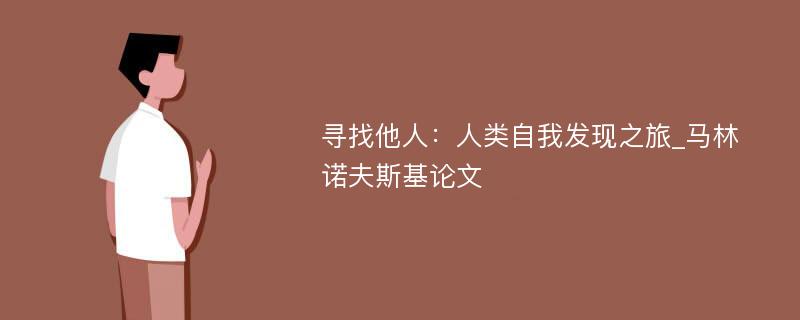
寻找他者:人类的自我发现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人类论文,自我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0)11—0049—06
一、人类学:研究他者,绕道理解自我
20世纪60年代,一位当代神学界颇负盛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为促使人们更理性地理解与接受基督思想和信仰,曾颇费心机地为基督神学找来了一个对话者——人类学,力图借由人类学使基督神学参与到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对话之中,而他为神学与人类学对话设定的中心话题,即为:人是什么。人类学何以能担当此重任?在其著作中,潘能伯格开宗明义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1](P.2)人类学,顾名思义,一门研究人的学科,潘能伯格更进一步,认为现代人类学“研究人对世界的开放性”——人总具有对新奇事物、新鲜体验开放的特殊本性。
以人的开放性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本身即不可能不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人类学对其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确认上:“人类学是对他者(the other)的系统研究,而其他所有社会科学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the self)的研究。只有人类学家敢于宣称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限于研究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2](P.1)研究自己,我们能了解到由我们的个人经验所能感知到的人类生活,但是这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绝不可能涵盖人类事象的全部图谱。以对他者的研究伴随并补充对自我的研究,我们也许能获致所有学科的最高目标,也是达致人之为人的必经之途—认识自我。
然而,就在人类学致力于穿越“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① 这一漫长却令人兴奋的旅途时,却发现这一旅途并不是想象的浪漫,而是艰难重重。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叹道:“我是一个闯入他们的生活而招致他们厌憎的家伙”,“我跑够了,再也不想伸长鼻子去探究异族的事情。”[3](P.11)另一方面,这个学科还招致了无情的批评与质疑,德里达曾认为:“人类学的‘暴力’产生于那一刻:异文化的空间由外人的一瞥而塑成并重新定位……在此过程中,人们在自我的认知对抗中重构异文化。就此看来,人类学的历史无异于是在以己文化之短进行的文字游戏中发生的、误述他者的历史。”[4](P.176)通往寻找他者的路上,人类学家不仅要迎击来自于外界的质疑声,同时,他还必须聆听自己心中的疑惑:何谓他者?我们是否能真正认识他者?我们知道,人的智识与成长有赖于反思与对话,因此,人类学家首先必须直面回荡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质询。
二、他者是谁:片面的解释
尽管并非本人意愿,马林诺夫斯基身后出版的田野日记《严格词义上的日记》(1955,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揭开了人类学家有意无意地向世人隐瞒遮蔽的双(多)重人格面纱的序幕。在这部用波兰语写作的关于特罗布里恩岛田野秘密日记里,马林诺夫斯基用混乱而断续的呓语式文体记录了自己的欲望、厌恶、无聊与野心。被人广为引用的证词是:“Gomaya,我给他一些草烟,他乞求更多……Gomaya像狗一样忠实的脸孔娱乐和吸引了我。他对我的感情是功利性而非情感性的。至于民族学:照我看来,土著的生活完全没有兴味和意义,它和一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那么遥远”[5](P.142-143)。
在最初的震惊、嘲笑、指责逐渐平息之后,人们开始理解、分析与研究这位专注于自己忧郁的人类学家那些粗糙和未加修饰的心灵独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里福德这样写道:“日记是一本创造性的,含有多种声音的书,它是人类学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不是因为揭示了人类学的经历的真实,而是它迫使我们紧紧抓住这类经历的复杂性并把所有根据这一类实地研究的文字叙述当作片面的解释。”[6](P.260)
倘若对人类学学科史上的“他者”认识观简单回顾并摘举几例,也许我们会对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文字叙述只是一种片面的解释”有更深的认同。
“落后的野蛮人”:人类学进化论者如摩尔根、泰勒等人相信人类生活在三种高低不同的状态中:蒙昧状态、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人类历史遵循这三种状态的顺序依次向前行进,且随时代会变得越来越好。在进化论者眼中,原始人(他者)从社会性来看,是野蛮的、杂交的,在文化上,他们只能从宗教仪式中寻求解释自然与世界的秘密。因此,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中,他者被视为落后、原始、野蛮的代名词,是落后的前身。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评论“野蛮”(savage)一词时指出的:“无论原义如何,‘野蛮’总是暗示着随心所欲、无规无矩、稀奇古怪。②
“高贵的野蛮人”:与进化论相反,原始论思想由于产生与风行于不稳定和动荡时期,总是带着悲观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在自我谴责与浪漫想象中建构出“高贵的野蛮人”、“幸福的孩子”等关于他者的理想化形象。第一个用土著语言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写道:“(土著)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缺乏一定的一致性,而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足以指导他们进行很多冒险事业的活动。而且,他们的艺术品同样不缺乏意义和美感……现代民族志者…展示了一幅土著人严格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图画,相比之下,凡尔赛宫或埃斯库里尔的生活却是散漫和随便的。”[7](P.7)
“他者是我们自己”:在崇尚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普世论的博厄斯学派(Franz Boas)看来,对他者的研究,其终极目的是要通过经验的方法找出众多文化形式中的共同点,在多样性中发现一致性。博厄斯断言:“这些分析表明,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区别。由于其特殊性,这种社会条件很容易给人一种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与我们大为不同的印象,而事实上他们与文明人的基本智力特征是相同的。”[8](P.63)结构主义人类学亦致力于发现人类思维相同的内在逻辑并为人类文化的规律性寻求解释,因此他们把“他者”视为我们自己。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写道:“我们的学科让西方人开始理解到,只要在地球表面上还有一个种族或一个人群将被他作为研究对象来看待,他就不可能理解他自己的时候,它达到了成熟。只是到那时,人类学才得以肯定自己是一项使文艺复兴更趋完满并为之做出补偿的事业,从而使人道主义扩展为人性的标准”。[9](P.21)在人道主义的道德力量驱动下强调人类的共性,把他者视为我们自己,但这样的道德驱动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难以解答的疑惑:我们实际怎样认识(how to do)和我们应该怎样认识(ought to do)他者,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可以依凭人类学家的理性道德力量调和的吗?
“他者是他们自己”:持文化特殊论的人类学者既相信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同等重要性,也承认文化与文化之间有着天然区别与鸿沟。人类学家阿莫瑞(Deborah Amory)在《美国协会的非洲研究》一文里,坦承“如同我所了解的非洲研究的复杂历史,我吃惊地发现当代美国人在非洲的经历多么忠实地再复制与描述黑/白,真实/客观,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些对立历史地建构了非洲研究领域。”[10](P.119)人类学中的环境决定论者,亦确信环境对人与人差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中国古语所言,性相近,习相远。正是不同的环境,使得山地之民性情独立,丰谷居民注重安居乐业,而海洋民族好动而崇尚远征。文化形貌论者如本尼迪克特对日神型、酒神型等民族精神的区分以及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等文化模式的鉴定,以及玛格丽特·米德表述的萨摩亚人那“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等,无不阐明:“他者”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他者是他们自己。
“面具化的他者”:面具化的他者形象由早期的探险者、征服者、传教士、旅游者等人基于异文化游历与浪漫想象建构而来,他们写作的作品(游记、书信、报告等)在道德激情之外同时具备一定的知识性与学术性,可谓研究他者的“准民族志作品”。他们将自己对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偏好或憎恶渗透于对他者的表述中,书写者鲜明的个性化与主观性色彩投射到他者形象里,他者即具有了面具化色彩。以对印第安人的描述为例,“印第安的概念不仅仅是单独的,而且也是特殊的、丰富多彩的、神圣的,有时有些英雄主义的或卑怯的。总而言之,印第安人有其特殊的神秘气息”。[2](P.188)这种神秘气息,在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康拉德对非洲人的描述中均可见一斑。然而随着现代人类学对异文化由窥视到观察再到凝视的了解和认知,这些他者逐渐被“去神秘化”,被视作是普遍性的人类中的一员,“面具化的他者”形象也随即淡出人类学的他者形象建构谱系。
摘举以上人类学对试图理解他者的种种努力与他者的不同形象建构,我们发现,即便是最聪明最富有“世界良心”的学者,也不能说自己完全和准确地理解了他者(因为谁能截然否定别人的观点呢?)。诚然,寻求学科一元论的企图是徒劳而无益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只是“礨空之在大泽,稊米之在大仓”,因此也只能够掌握人间智识的一小部分,不能也不必为整个大泽大仓而焦虑。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我们自己在寻找他者之途中的种种困惑与危机,理解这个绕道他者而认识的自我,理解“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发展至今,并不像许多人误以为的那样仍是把原始民族作为猎奇对象的一种自我粉饰和自我扩张,而已变为在多元文化中相互借鉴和自我重新定位的必要途径”[11]这样一种学科定位。虽然要让一位生活于土著人中间并宣称能科学客观地观察、描述和解释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心智特征的人类学家接受他只是一种“片面的解释”,是多么勉为其难,然而,不管承认与否,人类学“客观、科学、理性”地认识他者的困难已昭然示现,对之置若罔闻只能欲盖弥彰。
三、他者之惑即我之惑
人类学研究他者,而我们已然发现,他者这个概念不是孤立而静态地存在“那儿”,它只有在与“自我”相对应的时候才有意义。自我与他者实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我者”到“他者”,再回到“我者”,如果说,我是认识他者的一盏探照灯,而他者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那这盏探照灯和这面镜子都并非是用“科学而纯粹”的材料铸成,正如一句谚语所云:“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what matters most is how you see yourself)。如何看待自己,决定我者和他者之间爱恨交织、喜忧相伴的心路历程。
在拉丁语中,“人”(persona)的定义是:“它是面具、悲剧的面具、仪式面具与祖宗的面具”。[12](P.285)探求这个“面具”的真相之路让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同时即便今天专门研究人的各种社会科学也深感力所不能及,德国哲学家与神学家马克思·舍勒叹道:“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科学如何有价值,它们却掩去了人的本质,而不是去照亮它…故而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13](P.14)诚然,人之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都是如此难以测量,“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而我们也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14](P.8)
让我们不要再沉溺于空幻的思辨中,重新回想人类学那令人心动的承诺:通过绕道他者来理解自我。也让我们再重新审问自己:为什么人类学不能完全和准确地理解他者,甚至在认识他者的旅途中会出现自我认知的危机?③ 在他者的镜像中,问题渐渐浮现:人总是难以避免地把自己的小圈子看成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与体验当做宇宙的标准。希罗多德曾断言:“如果有人让人们选择世界上最适合他们的习俗的话,他们会查遍世界上所有的习俗,而最终还是会选择自己的习俗,并且确信他们的习俗是最好的。”[3](P.24)。
阻碍人全面认识自己与认识他者的正是这种小圈子中心观,也可称为人的唯我性或自我中心性。也即是说,人固有一种坚持自己的目的、观念和习惯的倾向,固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封闭自身的倾向,而不是进入开放的倾向。[1](P.53)自我中心性不能够仅仅依靠内省(或者说主要不是依靠内省)来摆脱,更不能通过抛弃自我(试图放逐自我的人,只会陷入空想)来解决,而只能够通过把自我投射或开放到一个更广大的生活时空中来克服。对于人类学来说,这个更大的时空就是他者所生活的异域空间,在这样一个“由地方、国家和跨国的力量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空间,他就在这个空间的一部分中旅行。[10](P.204)
然而,即使自我开放到更广大时空中,自我也总是要参与其中,因为人是自身目的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体,他会在自身存在的地方,把自我的时间与空间、把自身的生活经验携带进去。另一方面,我们已知,“他者”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文化,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让研究他者成为一个既是智慧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更是情感性的问题:由于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和中心性,他头脑里不可避免地安置着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④ 又由于“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15](P.56),因此,自我(确定无疑地具有道德判断)试图不对他者有任何道德判断地做研究的人类学其实“是将他者当作动物一样来研究。”[2](P.384)这样的研究视角,其实正如生物学家面对研究对象时,所抱持的观察者那种具有优越感却不愿作出道德判断的心态。把他者当作动物,这也许并非人类学家本意,然而这难道不正是马林诺夫斯基不断警醒自己却难以完全达到一个“科学、同情、审慎、理性”的完美人格的注解吗?难道这不是可以解开为何寻找他者寻求自我认识的道路如此迷雾重重的原因吗?
正是通过“绕道”,我们已经从纯粹的追问“人是什么”转变到了“怎样认识人”这一新的思想方式,这种新的思想方式要求人类学家在保有学术伦理、道德规范与原则的情况下深掘自己洞察与表述他者之智慧,同时,它允许人类学家有适度而可理解的感情参与。怎样认识人,如何使人类学家的感情、道德以及智慧超越唯我性与中心性,如何以对世界开放、对未来开放的胸怀,在积累深度的文化理解基础上,踏上寻找他者、认识自我的通途?拉比诺写道:“在我费心地琢磨要如何去观察和参与时,困惑也随之增长。在那些寒冷而孤寂的夜晚和那些炎热而孤寂的白天,对困惑的反思成了慰藉的来源。”[16](P.4)
四、反思:另一种旅行的起点
19世纪一个夏天的黄昏,一位名叫马洛的水手盘腿坐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的一条名叫“奈莉号”的巡航小艇上,用低沉的声音缓慢地讲述着自己的寻找“他者”之旅。在通往非洲一“这块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的航程中,马洛看到,在殖民者的奴役下,“一些黑色的人形的东西蜷缩着,躺卧着,背靠树干坐在树丛间,他们紧紧地依附着大地,一半露出来,一半遮没在昏暗的光线里,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17](P.503)对这些旅途中的“他者”同情之心溢于言表之时,马洛却无法掩盖自己与生俱来的殖民者的优越感:“他(野人司炉工)是一个经过教育得到提高的标本;他能点燃一只锅炉。他就在我的下面,说真话,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一只穿条学人样的马裤、戴顶皮帽子、用两条后腿走路的狗一样令你获益匪浅。”[17](P.486)
对于这部由英语世界里“最杰出的小说家”康拉德讲述的马洛非洲探险历程小说《黑暗的心》,爱德华·W·萨义德如此评论道,“《黑暗的心》不可能只是马洛的冒险历程的坦率再现:它也是马洛这个人的戏剧化再现”[18](P.28)。马洛的戏剧化再现也是康拉德的戏剧化再现:康拉德既是反帝国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这部有着双重视角的小说,后来被当作一篇出自人类学专业之外作者的人类学文献来读。马林诺夫斯基对这位与自己有着诸多共同点的前辈(都是波兰人,都背井离乡成为世界的流浪者,都用非母语—英语写作,都共同怀着“人类大同的理想”,更重要的,他们具有共同的书写对象:异域他者)敬重有加,他曾叹言:我应该是人类学中的康拉德!然而,一位晚近的人类学者詹姆斯·克里福德却直言道:人类学仍在等待他的康拉德。[6](P.263)
人类学仍在等待他的康拉德,虽然康拉德自己内心也对他者的态度充满矛盾,并且,在帝国主义与自己的身份认同中充满尴尬与无奈,但他非常有意识地把马洛的故事通过循环的叙述形式,通过马洛向世人讲述那被库尔兹“撕掉”的实话⑤,在敞开—遮蔽—再敞开的叙述策略中,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在西方文明的束缚与反叛中抗争的过程,展示了他对谴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反思自己“中心性”的能力的怀疑,展示了一个人类学主体性在场的典型文本。有学者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日记》里体现的言行不一,“不是个人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必然性。”[19]这种必然性是否正是康拉德与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区别呢?“重要的区别在康拉德对于尊重具体真实是一种讽刺的态度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只有一种不怀疑的态度”。[6](P.263)
康拉德在1901年给《纽约时报》写的一封信里如此写道:“创造性作品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对所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勇敢承认: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使我们的生活如此深不可测、负累重重、魅惑诱人、危机四伏……却又如此充满希望!”[20](P.11)在种种困惑与矛盾中,我们并没有停止寻找他者的脚步。人类即在这种追寻中昭示了自己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人,无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还是整个人类,可以说是还未发展成熟就早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有很长的幼儿期与青青期,而这也意味着人有巨大的可塑造性与成长性。同是,“人类根深蒂固地追求新鲜事物的本性将保证我们的想象力会有永远驰骋的机会”[21](P.149)。正是这种可塑性、成长性与想象力,人便能在克服自我中心、在对世界开放、对未来开放中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林诺夫斯基与康拉德的寻找他者之旅是最真实的发现自我之旅,是让后来者通过他们,把他们作为他者,可以得以照见自我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另一种镜像。
以康拉德和马林诺夫斯基为镜像,今天的人类学家在寻找他者、发现自我的旅途中,不断地在反思中前行。相比《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直接将他者介绍到我们面前,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学家寻找他者的过程,而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纳文》则将对他者的书写与建构之密钥也交给我们,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姊妹篇在幽默诙谐中解构他者与自我,在玛丽亚·肖斯塔克的《尼萨》中,我们看到他者作为主体性登场,当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s's point of view)熔炼为人类学的再次“自我形成”。甚至,在时间和空间的置换中,欧美人类学界的“他者”之旅已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要外出到“非西方”的世界,相反,“西方”自己已然变成了研究的主题……所有这些在他者之路上的探索之作,都让我们在学习如何观察他者、如何表述他者的实践与审思中,慢慢地认识到他者中的我性,我者中的他性。正如拉比诺最后所发现的,世界上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彼此而言,我们都是深层的他者:“人类学家和他的资讯人都是生活在一个经文化调适过的世界,陷于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6](P.144)
他者是谁?我是谁?人类永不停歇地寻找与追问。人是待完成的生命,是向着未知领域延伸的X,只有真正地探寻过了,我们才能告慰自己说: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人类学家斯蒂芬·A·泰勒认为:“我将民族志称为沉思的工具,因为我们既不是将它当作知识地图也不是将它视为行动指南来理解,甚至也不是为了娱乐来理解它。我们视其为另外一种旅行的起点。”[22](P.181)寻找他者,发现自我,我们永远在路上。
收稿日期:2010-09-06
注释:
① 此语系保罗·拉比诺借保罗·利科的话来对解释学问题进行的界定,而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认为这也是保罗·拉比诺对自己著作的一种阐释。参见(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25页。
②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著作中还提到一位“权威”对土著人习惯和风俗的理解:“风俗吗?没有。习惯?像野兽一样”。参见马林诺夫斯基著,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 在《日记》中,马林诺夫斯基最后写道:诚然,我缺乏真正的性格。”参见:Bronislaw Malinowski: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7年,P.298。
④ 普罗克拉斯蒂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非常残暴的强盗,他开设黑店,并设置一长一短两张铁床,捉到旅客后,便将旅客缚在床上,身矮者睡长床,身高者睡短床,或砍其腿,或将其拉长,以适合其睡的床。
⑤ 这句实话为库尔兹在为禁止野蛮习俗协会起草的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消灭这些畜生”,马洛将这份报告交给出版公司时,撕掉了这句话。在马林诺夫基的《日记》里,也写下相似的一句话:“总的说来我对这些土著人的总的感觉倾向于:消灭这些畜生。”参见康拉德《黑暗的心》与马林诺夫斯基《日记》。
标签:马林诺夫斯基论文; 人类学论文; 康拉德论文; 他者论文; 发现之旅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日记论文; 黑暗的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