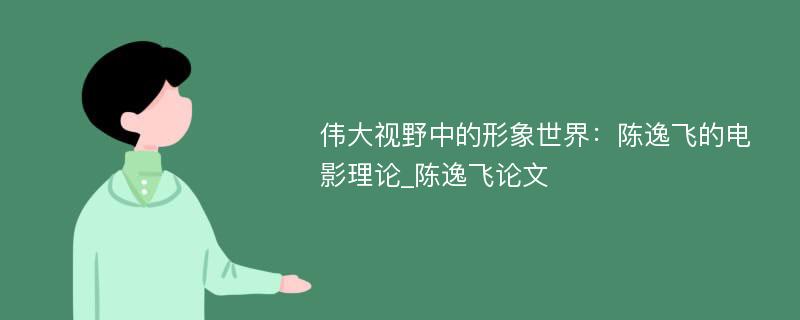
“大视觉”中的影像世界——陈逸飞电影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逸飞论文,影像论文,视觉论文,电影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故著名画家陈逸飞先生率先在国内提出“大视觉”这一艺术理念。所谓“大视觉”,用陈逸飞的话来说就是:“视觉艺术不是仅仅指平面的美术作品。作为从事美术的工作者,我们有种责任,把我们在造型艺术中对美的感悟通过各种手段和载体使城市变得更加美好,这是‘大视觉’的涵义。”[1] 在这种“大视觉”理念的统领之下,陈逸飞广泛涉猎,在美术、出版、模特、服装、景观和电影等领域积极探索,收获颇丰。或许因为电影最能体现其“大视觉”理念的精髓,所以陈氏对电影更是情有独钟,不但耗资千万,而且呕心沥血。因此,对陈氏电影的分析,既可洞察其电影艺术成就之高低,又可窥其“大视觉”理念之堂奥。
一、“诗化电影”的寂寞之旅
陈逸飞生前共拍过四部影片,即《海上旧梦》(1993)、《人约黄昏》(1995)、《逃亡上海》(1999)和《理发师》(2006)。其中《逃亡上海》是一部纪录片,反映了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油画艺术家,陈逸飞对电影画面的构图、色彩和光线等视觉元素极为敏感,也驾轻就熟,他常说每当自己拍到一个好的镜头,就像画了一幅好画一样激动不已。因此不少观众和学者称陈氏电影为“诗化电影”,确实,观看陈氏电影,可以感觉到其镜头语言油画般的唯美效果,尤其是那种弥漫于精致影像之间的感伤怀旧情调,一如观赏陈氏油画作品,让人难于释怀。美术与电影的联姻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了法国先锋派电影艺术家手中更是一片繁荣景象。活跃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法国左翼电影导演,因其先锋派的创作风格被人们称为“银幕诗人”,他们主张电影语言应该像诗的语言一样,要否定情节、避免“叙事和小说性”,从而凸现视觉形象的中心位置。为此,先锋派导演倡导一种脱离文学和戏剧的“纯电影”——充分运用可见的形式和节奏的变化,在运动和空间中寻找一种“情绪和激情”。正如先锋派代表人物安德烈·莫鲁阿所言:“可以创造一种纯电影,它将由一系列画面构成,而这些画面只是按照一定的节奏联结起来,没有任何纠葛……[2] 于是,对人物的梦境或迷醉状态的刻画和渲染就成为先锋派电影创作的主题,因为借助于游荡者恍惚不定的视线,可以将许多没有情节、缺乏逻辑顺序的离奇景象联系起来,使观众对此产生自由而主观的想象。除了营造这种神秘的氛围,先锋派电影还常常在影片中插入大量无生命之物的特写镜头,对不常见的景象和非常微小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爱。因此,物象与人有了同等价值,甚至超越于人而独立存在——一种典型的对物象的迷恋和崇拜,这种“拜物主义是与他们力图把叙述、情节和时间这些领域排除于‘纯粹的’、‘诗的’电影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倾向相适应的。”[2]
陈逸飞游学欧美多年,曾广泛考察包括电影在内的西方现代艺术的流变,也亲身参与了不少艺术实践活动,西方艺术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何在“大视觉”的范畴里将美术与电影这两种介质不同的艺术门类有机的结合起来,一直是陈逸飞思索的重大课题,而法国先锋派“纯电影”或“诗化电影”的观念对他的电影创作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陈氏刻意淡化电影的叙事性而极力营造一种感伤情调。《海上旧梦》表现一位当代画家在梦境中追寻一位身着旗袍的少女,对旧上海市井民俗的散漫影像作了富有诗意的平行剪辑。扑朔迷离、时隐时现的少女形象,成为沟通现实与过去,展示都市昔日浮华的“灵媒”,而作为“寻觅者”出现的画家,其流露出来的感伤怀旧之情则成为贯穿影片的主线,除此之外,该片的确毫无情节可言。这部影片很大程度上是从陈氏早年油画作品《踱步》(1979)中获取灵感的。《踱步》表现的是一位画家(也是陈逸飞本人的形象)背对观众,在一组反映五四运动的照片前陷入思考。陈逸飞在创作此画时大胆移用了电影的文本格式,把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回顾与反思全部浓缩于同一画幅之中,体现了陈氏一直极力倡导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情绪化”的创作主张。在《人约黄昏》这部影片中,陈氏再次塑造了一个城市漫游者的形象——旧上海某报馆记者徐先生,通过他与一个自称为“女鬼”的神秘女子的交往,展现了旧上海的风物民情。然而,尽管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人鬼恋”的故事,影像当中也确有古宅荒墓、鬼影憧憧,但观众似乎并未感到有多少恐怖与悬念,因为影片中的“人鬼恋”不过是一个噱头而已,所谓“女鬼”不过是一个为亡夫报仇的普通女子。情节单薄不说,对红色革命荒诞离奇的“爱情化”演绎几乎成为观众的笑柄。或许陈氏也察觉到自己在电影叙事上的欠缺,因而在其遗作《理发师》中,有意识将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戏剧化”,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异常坎坷,亡命天涯的爱情相当凄美,但由于叙事时空跨度太大,而陈氏显然又缺乏驾驭庞大历史题材的能力,所以这部影片的情节单调沉闷,叙事依旧乏力。
当然,叙事上的不足,并没有妨碍陈氏在影片中对景观物象的着意刻画,三部影片都体现了陈氏把镜头画面当作油画构图一样来经营的良苦用心。影片除了展示大量的自然景观,还竭力设置了一些让观众记忆犹深的道具,如《海上旧梦》中斑斓多姿的旗袍、《人约黄昏》里充满异国情调的ERA牌香烟、《理发师》里古色古香的留声机。陈氏不但亲自对这些道具加于精心设计,而且还在影片中赋予它们重要的叙事作用,使之起着连接画面意象、绵延心绪情感、甚至见证人物命运变迁的作用,如《理发师》中的留声机就目睹了男女主人公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当影片结尾男女主人公重逢时,这部留声机再次出现在银幕上,静静地流淌着昔日感伤的旋律。
作为一名推崇人文精神的艺术家,陈氏对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理性统治下日益抽象的思维方式深表担忧,他力图通过摄影机来帮助观众重新经验这个世界,让观众克服对物质现实的冷漠之情,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所以陈氏对物象的迷恋,显然和他追求诗化的电影语言有关,“电影似乎在它迷恋于事物的表面时,才成为真正的电影”。[3] 然而,对物象的偏爱使得陈氏在电影叙事和视觉画面之间进退维谷,最后他还是本能地将重心更多放在了视觉层面上。陈氏的困惑涉及到何谓电影本性这一难解之谜,他对视觉的偏执在其他电影导演身上也时有体现。令人玩味的是,陈氏电影尽管耗资巨大,但往往反响平平,多沦为“小众”电影,这与陈逸飞的“大视觉”理念似有冲突——陈逸飞在谈及“大视觉”理念时曾呼吁艺术家应该让视觉艺术走出自命高雅的画室和孤芳自赏的沙龙,要将自己的艺术感悟和美学理念贡献给社会和公众,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作为电影导演的陈逸飞,其电影作品显然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大视觉”艺术主张。或许,陈氏电影的真正价值更多只存在于其艺术探索性之中。
二、走不出的后殖民记忆误区
陈逸飞曾经于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经历了一番生活和艺术上的双重磨炼之后,陈氏画风突变。出国前的陈逸飞,其油画创作以笔力雄健、色彩鲜明、画风粗犷、富有气势以及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著称,《黄河颂》(1972)和《攻占总统府》(1976)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两幅作品。画风转向后的陈逸飞,不但在绘画题材上从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的宏大叙事转变为江南水乡、古典仕女和西藏风情一类的小品创作,而且在技法上也判若两人,色彩关系柔和沉着,线条细腻流畅,笔触朦胧圆润。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生存上的考虑,主要应归于西方文化对画家潜移默化的影响。陈氏曾回忆说:“每两周我会去苏豪区,五十七街和麦迪逊大街所有的画廊转一圈,让眼睛不只盯住一点而是全方位的,包括电影和戏剧,我乐此不疲。我的画风之所以会有变化,不是抄袭其他风格,而是慢慢来自心灵深处的转变。”[4] 在西方商品社会的洗礼和文化艺术的浸淫之下,陈逸飞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和艺术市场策略的重塑,加上受近代以来欧洲绵延不绝的东方主义绘画传统的启示,陈氏穷则思变,终大获成功。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最早发现并赏识陈逸飞,认为陈逸飞已经“渐渐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4] 而美国康科兰博物馆馆长米歇尔·波特文尼更是盛赞陈逸飞“是为他的民族恢复与西方对话的第一位艺术家。”[5] 1982年陈氏与哈默画廊正式签约,从此开启了他辉煌的“东方风格”的油画创作期,并迅速成为西方华人艺术家的领军人物,一再刷新由自己保持的华人绘画作品在西方艺术品市场的销售数量和价位纪录。其间,陈氏先后创作了大量具有东方色彩的油画作品,如表现江南水乡的《古桥》和《寂静的运河》,表现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浔阳旧梦》、《罂粟花》、《西厢待月》和《恋歌》及上海旧梦系列《黄金岁月》、《玉堂春暖》和《春风沉醉》等。风格转向后的陈氏油画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西方主体性的视觉来观照作为客体的东方意象,用西方照相写实主义的技法来表现一种东方神韵,使西方的细致酽丽和东方的朦胧典雅融为一体。
陈氏的电影创作风格与其转向后的画风极为相似,《海上旧梦》通过表现画家对一个高贵典雅、身着美丽旗袍的神秘少女的追寻,在静谧之中展示了一个世纪以来旧上海的人情风貌,借助于画家窥寻视点的游移,观众如在诗情画意中穿行。如果说《海上旧梦》还缺少必要的情节,仅仅是将一幅幅静态的城市众生相组合成流动的影像,那么《人约黄昏》和《理发师》就开始借具体人物的情感经历和命运变迁来演绎时代风云和展示旧上海的风貌了。《人约黄昏》通过一个离奇“女鬼”的故事,在恐怖和梦幻般的影像画面中表现了30年代老上海的风俗民情,诸如旧货市场、租界建筑、有轨电车等等。《理发师》则时空跨越更大,从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到湿润的江南水乡,再到大漠戈壁的劳改农场,战乱与和平、正义与背叛、爱情与仇恨,无不构成色彩斑斓的视觉奇观。三部影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展示昔日一个东方都市的浮华与美丽,同时也暴露其畸形与丑陋。观众通过影像世界里的建筑、语言、服饰、当然还有爱情这类漂浮的能指符号,可以强烈感受到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的碰撞与纠结。在陈氏精心营造的影像世界里,除了西方古典写实的画风一如既往,陈氏同时还沿用了自己在绘画创作中的诸多表意元素,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东方主义风格的电影视觉语言符号:怀旧意识、老上海情结、浪漫写实主义、幽怨女子和江南水乡等等。其中班驳的建筑、暗淡的街道和匆忙的人流,是陈氏影片最偏爱的场景,它渲染了一种奇特而忧郁的“东方式”生活形态,因为“街道就其广义来说,不仅是转瞬即逝的景象和偶然事件的荟萃之所,而且也是生活流得到必然表现的地方。”[3] 而影片中众多以宁静优雅又不乏凄美的神态出现的年轻女子,更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象征——她们对观众静穆的凝视往往诱惑西方观众克服影片情节的单薄和叙事的乏力,尽情地去想象这些神秘的异域女性之命运,去寻觅一个遥远的“他者”中国,因为她们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观念中静态凝滞的东方文化不谋而合,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6] 因此,尽管陈氏电影在西方的影响力远不如其画作来得广泛,但仍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热评,《人约黄昏》1995年曾入选戛纳电影节“特别推荐单元”,陈逸飞也受到电影节主席的亲自接见。
因为在不同文化碰撞中必然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所以文化身份的问题也随即产生,频繁往来于东西方的陈逸飞对此自然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切的体会,因为“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将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所取代。”[7] 或许,凭借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和东方人特有的悟性,陈逸飞在无意识中体味出了某种能与国际接轨的审美情趣,因此从绘画到电影,他都尽力营造出一个充满后殖民主义色彩的时空,让他的人物和景观浸淫其中,从而促使东西方艺术产生某种对话的可能性,因为“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文化自我的界定总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和生活方式的区分。”[7] 然而,成也“东方”,败也“东方”,陈氏的这一套影像话语渐渐构成一个他无法挣脱的后殖民记忆误区。在“东方风格”束缚下,陈氏电影的故事题材和审美趣味日益单一重复,影像画面徒增匠气,同时也暴露出他在全球化背景下自我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彷徨与焦虑。
三、文化和商业的浪漫史
陈氏生前常常被称为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陈氏究竟是艺术家还是商人的争论甚至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陈氏在艺术和商业领域的传奇经历和巨大成功也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几年前,国内艺术市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临摹陈逸飞或效仿陈逸飞画风的油画作品。毫无疑问,陈逸飞的“大视觉”理念也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逸飞”已不单纯是他的一个服饰品牌,而是其“大视觉”理念所涉及的任何一个项目——陈逸飞要让他所有的艺术产品都深深地烙上“逸飞制造”的商标。
陈逸飞的“大视觉”理念并非仅仅寻求各种视觉艺术媒介之间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积极的后工业社会的美学实践,这种美学实践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致力于将艺术从高雅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出象牙塔。应该说陈氏的“大视觉”理念与当下这个以视觉文化为主流的消费社会是非常吻合的。法国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居伊·德波就将这个时代命名为“形象充斥的世界”;美国学者C·伯格则不无悲哀地断定在这个连广告都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社会里,美学上的现代主义内涵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F·杰姆逊也感叹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了,“艺术品和文化产品变得越来越相似,对许多大众艺术作品来说,差别实际上已经只剩下艺术家的签名了。”[8] ——杰姆逊可能没有发现,现在连设计签名也已经成为一项时髦的文化产业了。总之,在后现代社会中,审美观念已逾越了艺术的界线,渗入到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而陈逸飞的“大视觉”理念正是这种具有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美学理念。因此,尽管陈氏的电影作品在市场上一再受挫,如耗资300万的《海上旧梦》就因未能上演而血本无归,像资料片一样尘封已久,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坦言投资拍电影是“交学费”,希望以此了解电影产业和创作的特性。所以,如果把“大视觉”理念和“逸飞”品牌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陈逸飞生前如此执着于对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因为维系着陈逸飞“大视觉”六大分支品牌运转的除了资金链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无形资产的纽带——必须确保其信誉不断增值的“陈逸飞”这一个人品牌之链——因为无论是电影,还是出版或服饰等,任何一个分支所取得的成就,都能增加“陈逸飞”这个总品牌形象的含金量,并对其他分支品牌产生积极效应,正如陈逸飞所坦言:“视觉恰恰是一个商机无限的产业,一个没钱可以生钱的产业。”[1] 因此,拍电影对于陈逸飞来说,绝非某些人所说的只是玩票而已。陈氏电影之所以在商业上不尽人意,与其说是陈氏的投资思路有违于电影行业的惯例,不如说是目前中国电影行业不规范操作的现状阻碍了陈氏的成功。总之,对日常生活审美欲望的关注、对影像视觉符号的强调是陈氏“大视觉”理念的核心,他雄心勃勃,想以亲身经历来编写一部当代中国“商业和文化的浪漫史”,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这也是“大视觉”理念的真正价值所在。
尽管陈氏的三部影片构成了对昔日城市的一次感伤缅怀之旅,但其“大视觉”理念却是建构于城市现代性的审美趣味之上。这位积极倡导发展城市视觉产业、主张从城市视觉形象的每一个“细节”着手,进行一场全民“视觉补课”从而迅速提升国民素质的艺术家,与他常年生活的城市——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陈逸飞是真正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他通过精致细腻的影像语言,传达了上海潜藏于人们记忆深处的暧昧。或许,陈氏的电影在叙事上还多有欠缺,但他却牢牢地把握住了昔日上海的韵味和质感,这是当代其他电影导演难于企及的。而上海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殖民地历史的大都会,其商业社会的实利主义、中西交融的人文底蕴、艺术与时尚的奇妙结合,又作为一种海派文化的背景,哺育了陈逸飞并为他日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
斯人已去,空留影像。对陈氏的电影作品,人们自可加于评说,但是,对陈氏及其“大视觉”理念,我们却必须保持一份敬意,因为对不同品位和表达方式持宽容态度是当代文化的基本价值。尽管陈逸飞的“大视觉”理念具有浓郁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色彩,但其对“诗化电影”的追求,无意间又成为一曲悲壮的现代主义美学绝唱;陈氏一心想打造其“视觉产业”的商业王国,然而他的纪录片《逃亡上海》又充满了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悲悯;在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之间的游离,使陈氏不可避免地陷入困惑且疲惫不堪,而所有这些恰好构成了在“大视觉”理论背景下陈逸飞电影的某些特质。文化宽容的核心原则就是尊重差异,正如鲍曼所说,“如今势不可挡的趋势是把文化视为人类永恒的、无可化约的差异性的基础。”[9] 显然,对陈逸飞的电影也应如此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