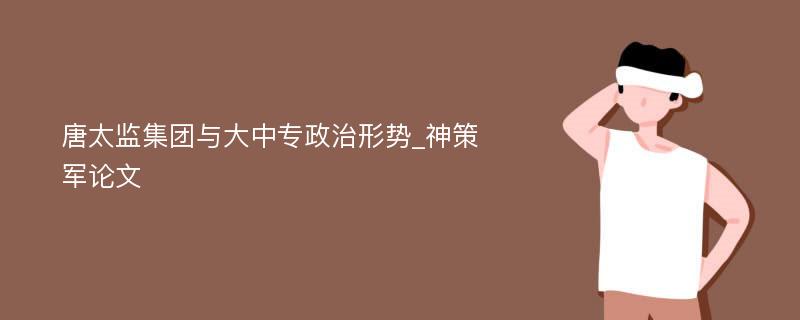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宦官论文,政局论文,大中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之势愈演愈烈,成为中晚唐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瞩目的重要的历史现象。长期以来,中外学人曾从不同侧面对之有所探讨,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史料的限制以及切入点的差异,以往的研究大都以通论性的或长时段的考察为主,因此,不少关涉中晚唐具体历史时段的宦官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政治经济问题悬而未决。本文拟在前人已有涉及的基础上,参据传世文献与墓志资料,对唐宣宗朝宦官集团及其与大中政局之关系加以探讨。讨论的问题约有三端:一是宦官集团与宣宗之立;二是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三是大中末年的宫廷政变。其中不少内容是对具体史实甚至某些细节的考订,可能有失于繁琐。我们的目的乃是企图通过对若干史实的梳理和辨析,揭示唐宣宗时期政治史上的疑点,以期有助于中晚唐政治史的进一步研讨。
一、唐宦官集团与宣宗之立
中唐以后,宦官擅政,诸帝多为宦官所立,宣宗亦然。《资治通鉴》(以下略称《通鉴》)卷247武宗会昌六年(846)三月条载: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号曰光叔。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两唐书《宣宗纪》所载与之略同。据本条,宣宗为“光王”时,善自“韬匿”,以“不慧”自掩,不仅成功地躲避了文、武诸帝之猜忌,而且诸宦官亦贪其庸下易制而矫诏立之,直到视事后其“隐德”才为外人所知。
如果仅从本条所言,宣宗之立似乎事出偶然。其本人并未预谋其事,自属意外得立。然而,我们知道,武宗本有皇子,而宣宗为武宗皇叔,并非帝位的当然人选,但宦官集团为何却偏偏选择了他?难道真的是认为他庸下易制吗?再联系到宣宗即位后与宦官集团的特殊关系(说见下),则宣宗得立似另有隐情。
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某些史乘有意讳言,史学界对于唐宣宗即位之真相一直不甚了了。而近些年来,有关唐武、宣之际仇氏、杨氏等宦官家族的墓志相继发现并予以刊布,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透过墓志所提供的若干线索,可以对宣宗得立之真相略窥一斑。其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三五所收《唐故振武麟胜等州监军使孟秀荣墓志》尤值重视。志略云:
府君大夫讳秀荣……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会昌三年正月六日,从(徙?)湖南监军,着蕃(番?)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军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赐绿,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内养。
志主孟秀荣于武宗会昌五年(845)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内中所言“王妃”事件,此不拟详说(王妃为武宗才人,因“忏旨”赐死,然其死因诸书所记互有歧疑,故暂置不论),总之,这是一次宫廷事件,宦官孟秀荣曾因之“连累”遭贬。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会昌五年九月,当时,武宗病重,据《通鉴》所说,“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1](卷248,会昌五年九月条)。武宗病重与王妃事件几乎同时,二者之间当有密切联系。
会昌六年(846)四月宣宗始听政,据志文,是月底宣宗即将孟秀荣召回,明年正月又进一步除其为“内养”,此后孟秀荣连获超擢。值得注意的是,志文提到所谓“追赐绿”一语,“追”,表明宣宗赏赐孟秀荣为追录前功。但会昌五年九月孟秀荣已被贬东都恭陵,宣宗即位时并不在长安。如果孟秀荣对宣宗有前功,只能指墓志中含糊其辞的“为王妃连累”之事,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孟秀荣之贬同宣宗之立有着一定的关联。假如这一推断可以成立,则宣宗之为宦官所立,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曾积极地预谋其事,并同武宗势力有过激烈冲突,王妃事件或孟秀荣之被“连累”事便可视为当时皇位之争的重要一环。
另据此志,孟秀荣元和三年(808)曾任“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宪宗时凤翔镇并无仇姓节度使,因孟秀荣本人即是宦官,故这里所云之“仇将军”当指某仇姓监军使。《新唐书·仇士良传》载士良,“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则可据以推知墓志中之“仇将军”或即武宗朝之权宦仇士良。志云会昌三年(843)正月六日,孟秀荣被仇士良拔擢为湖南监军,两日后又擢为判官,置于左右,显然,秀荣必为士良旧党。又秀荣被贬前,为左军中尉都判官、武德副使,属左军中尉之高级僚佐。当时的左军中尉是马元贽,王妃事件之发生,恐亦与之有关。我们知道,早在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马元贽为閤门使,为仇士良的主要帮凶,会昌三年六月仇士良主动引退时所安排的后继者即为此人。因此,同孟秀荣一样,马元贽同仇士良也渊源甚深。会昌五年的王妃事件,因都判官孟秀荣承担罪责,马元贽得以逃脱追究,并最终在拥戴宣宗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据称“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贽有力焉,由是宠冠诸宦”[1](卷249,大中四年四月条),因孟秀荣掩护之功对宣宗之立至为重要,故宣宗即位后“追赐”其“绿”亦理所当然。十分清楚,从志文所透露的情况看,仇氏宦官势力在宣宗夺位过程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
除上揭《孟秀荣墓志》外,宣宗同仇氏宦官世家(中唐以后上层宦官通过提携子弟,援引亲族,形成不少绵亘数十年的宦官世家)(注:关于宦官世家的问题,可参陈仲安先生《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2期。杜文在论及仇氏家族时将大中五年郑薰《仇士良神道碑》误附于会昌三年,故对仇氏家族的考述或有不实。)的暖昧关系在仇氏家族墓志中也有更为直接的反映。《文苑英华》卷932 收有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据此碑所载,大中五年(851),宣宗公然为仇士良“平反昭雪”,并树碑纪功。是时仇士良长子仇从广为宣徽使,次子仇亢宗曹州刺史,三子仇从源内府局丞,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仇士良嫡系假子俨然已经恢复昔日的权势。又《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五五收有宣宗御制《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此志由宣宗亲自撰写,仇氏所受恩遇显非普通后宫所及。墓志自言“仇氏簪缨,蝉联在昔”,唐代并无仇姓高门,宣宗所指显为仇姓宦官家族。仇氏卒于大中五年(851),仇士良平反亦在大中五年,二者之间似乎亦有密切关联。
如所周知,仇士良是唐文宗时期最为跋扈的权宦,《新唐书》本传称其“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武宗虽为其所立,亦不甘受其摆布,曾暗中对其权势进行裁抑。会昌三年(843)六月廿五日,亦即仇士良卒后的第二日,武宗诛仇士良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2](卷4,会昌三年六月廿五日条);次年六月,又在仇士良私第搜得兵仗数千,遂削其官爵,籍没其家,诸仇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从墓志所反映的情况看,至宣宗大中中期,诸仇并已身居荣秩,其官爵显然为宣宗即位后所超擢。宣宗非但不继续执行武宗打击仇氏势力的政策,反而为双手沾满朝臣和皇室鲜血的阉宦树碑纪功,荫其亲族。若非仇氏宦官势力在皇位争夺中对宣宗立有大功,断不会有如此礼遇。
我们还注意到,以往宦官擅立新君时往往会伴有不同宦官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穆、文、武诸宗莫不如此。前已提到,唐宣宗为武宗皇叔,并非帝位的当然人选,但是宣宗之立,宦官集团却表现得相当一致,这似乎暗示了当时除仇氏家族外,大部分宦官都已相继为宣宗笼络。这里可以略举几例。枢密使杨钦义笃信佛教,对会昌末武宗灭佛多有不满。《宋高僧传》云:“属宣宗龙飞,杨公自内枢统左禁军,以册定功高,请复兴天竺教。”[3](卷6,知玄传)则杨钦义亦为宣宗之党无疑。杨钦义二子杨玄略、杨玄价颇为宣宗重用,大中初杨玄略两任总监使之职[4](咸通○二○,杨玄略墓志)。另一枢密使刘行深在宣宗之立中也没有受到冲击,宣宗即位后拜其为右军中尉,并以其第五子刘遵礼为宣徽北院使[5](咸通○七二,刘遵礼墓志)。又军器使李敬实在武宗朝宣掌密令,宣宗即位后亦受命创迎銮寺,恩宠不衰,估计也曾预谋其事[4](大中○七八,李敬实墓志)。
与朝中宦官集团继享富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昌末外镇监军的宦官却多遭罢弃。如陕虢监军师全介曾深得武宗信赖,会昌末师氏在陕府监军,直到大中六年(852)才得以归朝,而且返朝后17年都罢黜不用[4](咸通○一九,师全介墓志)。又如义昌军监军高克从,本出自高力士家族,尤为武宗信赖[4](大中○○六,高克从墓志),会昌末高克从在义昌监军,也无缘参与其事,其二养子公球、公玙大中朝皆无显宦。公球卒于大中四年(852),其墓志但云“公讳可方”,而不书公球之名,并且对会昌时曾任义昌军押衙的经历避而不提[4](大中○二六,高可方墓志),似乎与躲避宣宗打击有关。总之,仇氏、王氏、杨氏等大部分上层宦官世家续享荣华,而外出监军无缘参预拥立的师氏、高氏等则倍受压抑。二者境遇的天壤之别是宣宗与宦官集团早有勾结的又一力证。
如上所说,唐武宗会昌末宫廷皇位之争的真相,由于史籍记载的缺漏或有意讳言而疑点重重,但业已刊布的诸多宦官墓志却提供了相关的线索。透过这批墓志所记述的某些尽管带有隐晦或含糊的史实,仍得以约略窥见唐宣宗即位之隐情。志文表明,宣宗之立,乃是他与马元贽、孟秀荣等仇氏残存势力及其他宦官世家阴相勾结的结果,而决非如《通鉴》等史籍所言,系因其“不慧”而为宦官所“误立”。这一真相之揭示,为我们研究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二、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唐宣宗在长达14年的统治中,其威权经历了一个由脆弱到逐渐巩固的发展过程,宦官集团对政局的影响亦随皇权的不同需要而有所变化。
因宣宗与朝臣素无渊源,大中前期皇权极为脆弱,国家大事也不得不继续仰仗宦官,宦官集团得以广泛参与各种政治事务,颇为跋扈。
大中初,党项内扰,宣宗征讨党项主要仰仗宦官集团的支持。大中五年(851),宣宗拜白敏中为都统西讨党项,敏中虽有都统之名,“既握兵外去,每一事,非关请不得专则不自专”[4](咸通○○五,白敏中墓志),真正起作用的却为宦官集团。长武、崇信等镇行营由宦官杨居实等监戍[4](咸通○○九,杨居实墓志),往河东联络沙陀援兵及押运粮草等重大军事使命,则由宣宗所亲信的宦官吴全缋综理之[4](乾符○一九,吴全缋墓志),是年宣宗又以宣徽南院使刘遵礼兼充京西北制置堡戍使,在西北增置堡垒约40余所[5](咸通○七二,刘遵礼墓志)。通过讨伐党项,宦官集团强化了对藩镇的控制。
仇士良引退时,曾传授诸宦固宠之术,云:“为诸君计,莫若繁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6](卷207,仇士良传)大中初仇氏之党得势,仇士良“繁殖财货”之计竟颇为奏效。《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载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未改元)九月敕有云:
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权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曲,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沽酒。
榷酒钱和官置沽是安史乱后朝廷和地方竭力争夺的税源之一,其中官沽对百姓的盘剥尤为严重,非军用紧迫朝廷一般不许官沽。新君即位通常都要大赦天下,而宣宗却不恤黎民,公然敕令八道设置官沽,显然有违常理。又《新唐书》卷182《李珏传》载:
及(李珏)疾亟,官属见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方论奏,未见报为恨,一不及家事。
前条所引会昌六年九月敕,声称置官沽的主要用途乃“以充军用”,而本条所言从中渔利的却是神策军,二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据旧唐纪,宣宗自即位起,神策军便在宫内大兴土木,营造不已。为纪其迎立之功,神策中尉创意在皇城内建迎銮寺,仅此一寺即耗时二年之久。大中元年(847)八月,神策军奏修百福殿成,凡廊舍屋宇700间;大中二年(848)神策军又修左银台门楼、屋宇及南面城墙,至睿武楼。当日神策军兴修不已,耗费巨大,也正是亟须财赋“以充军用”之时。唐代宫殿修缮,职归将作监,神策军侵其职权,其目的无非就是以修造为名而“繁殖财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会昌六年(846)九月敕淮南等地置官沽之主要目的,即为弥补当日神策军之所谓“军用不足”。
大中早期宦官集团权势的扩张,是以其拥戴之功为前提的。而大中中期,宣宗的统治已逐渐稳固,对宦官权势过重的情况已有所不满,开始有意识地抑制不法宦官。大中八年(854),有中使经过硖石驿,怒饼黑,鞭驿吏见血,为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所奏,宣宗将其谪配恭陵[1](卷249,大中八年九月丙戌条)。大中九年(855),浙东观察使李讷为乱军所逐,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1](卷249,大中九年九月乙亥条)。是年杨处约,由于“姻族失旨”,也被罢去“内养”,终宣宗世不被起用[4](咸通○○九,杨居实墓志)。大中十一年(857)内园使李敬实恃宠遇宰臣郑朗不避马,宣宗剥其品色,贬配南衙(注:《东观奏记》卷下,126页。《通鉴》卷249附其事于大中十年十一月条,据《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七八《李敬实墓志》,李敬实大中十一年冬始为内园使,《通鉴》误。)。又高品吴居中为固宠,听信术者之言,书宣宗尊号于袜底,事发后宣宗将其弃市[7](卷中,第113页)。除抑制跋扈的宦官外,对宦官所操纵的神策军势力宣宗也不再姑息。大中中期,河南县令杨牢不畏宦官权势,追冒军百姓入籍,责其差科,宣宗特意赐绯鱼袋(注:《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三七题《杨松年墓志》。按:此墓志原作“公讳□□松年”,《新唐书》卷118《李甘传》中有孝童杨牢葬父之事。杨牢,河南人,字松年,父茂卿,与墓志皆合,故知所缺二字分别为“牢”、“字”。)。大中十年(856)京兆府有厌蛊之狱,涉案者郭群属飞龙厩,三牒不可取,京兆尹韦澳入奏宣宗,次日即被押解送府[8](卷2第94页)。在宣宗的震慑之下,神策军横行无忌及百姓假托军籍逃避税役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故大中八年前后可视为宦官集团相对收敛的时期。
大中十一年之后,宣宗疏于政事,并沉溺于长生术。史称“上晚节颇好神仙”[1](卷249,大中十一年十月壬申条)。因宣宗惑于左右,疏远朝臣,宦官集团很快又故态复萌。荆南节度使杨汉公大中中期以贪鄙而被其征入朝堂,不复委以方面之任。但是杨汉公生性险谀,厚赂宣宗左右宦官,在宦官集团的蛊惑下,大中十二年(858)宣宗不顾郑裔绰等三驳制书,坚持授其同州刺史。是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擅杀刺史刘皋,宣宗虽然最终“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7](卷下,第128页),但杨玄价后于咸通初接替王宗实为左军中尉,则知其当日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宦官集团势力的回升很快对当时政局产生影响。杨汉公等因阉竖得官,各地藩镇竞相仿效,纷纷向宦官贿官。大中十一年以后,容管、岭南、湖南、江西、宣歙、武宁等藩镇相继爆发军士逐帅事件。右补阙张潜论军乱缘由时称:“籓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籓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4](卷249,大中十二年七月条)中晚唐时期的“羡余”由宦官把持的内库收管。大中末期朝廷竟以“羡余”多寡作为课绩标准,这显然是宦官经济势力扩张的重要表现。
三、大中末的宫廷政变
大中十三年六月,宣宗因长期吞服丹药疽发而亡。宣宗崩后,宦官擅立的情况再次发生。《通鉴》卷249大中十三年(859)六月条下载:
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漼。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
对于此次政变,胡三省等认为“宣宗不早定国本,使王宗实得以立长而窃定策之功。”[1](卷249,大中十二年二月条胡注)。事实上,大中末宣宗虽然对自己躁渴不适之事讳忌甚深,但已在悄悄开始安排身后之事。《东观奏记》卷下载: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郓王已下侍读。时郓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数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读,五日一入乾符门讲读。郓王即位后,其事遂停。
大中十二年皇子侍读之选,明显带有培养储君的目的。郑漳等由侍读郓王到侍读夔王,这一转变表明宣宗一度欲以长子郓王为太子,但是最后还是从私爱出发,选择了夔王。郓王居长,具有作太子的合法身分,而且郓王之母早薨,庸下易制,宦官亦多属心于郓王。宣宗自然深知宦官不喜夔王得立,在任命朝臣侍读的同时,也悄悄在宦官中为夔王清扫障碍。大中十二年宣宗刻意纵容宦官也许含有此方面的考虑。杨氏家族在神策军中颇有势力,大中十二年宣宗刻意包庇杨玄价等似乎意在笼络杨氏诸宦,以换取他们在自己身后对夔王的默许。因此,笼统地将政变归罪于宣宗不预立太子显然并非的论。
据《唐语林》所云:“故事:每罢左护军,由右军出;罢右护军,由左出;盖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驭下,每罢去,辄令自本军出,中外不能测。”[8](卷2,第90页)宣宗为宦官所立,两军中尉权势尤重,甚至连两军交换中尉的旧制宣宗都不能贯彻,只能小心翼翼地用“法”来驭制。大中九年(855)左军中尉为王宗实,王宗实此前不见于记载,大中八年(854)宣宗同韦澳论驾驭宦官之策时,称自己曾提拔一批宦官,“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1](卷249,大中八年十月条)。宣宗素惜服色之赐,有资格赐紫的宦官寥寥无几,宣宗所指或即此人。大中九年宣宗借浙东逐帅事件,贬其兄弟王宗景守恭陵,即有剪除王宗实党羽的意图,史谓宣宗不厚王宗实是有事实根据的。
宣宗无法真正控制两军中尉,只能将控制宦官的重点转向左右两枢密使。武宗朝抑制宦官,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等“愿悫”不敢预事,老宦尤之为“堕败旧风”[1](卷247,会昌三年五月壬寅条)。因武宗朝枢密使久不预政,宣宗控制枢密使的阻力相对较小。据称,“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1](卷262,天复元年正月条下胡注)。枢密使无法预闻宰相奏议,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大中时还有枢密承旨一职,大中九年(855)五月,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私改之,宣宗以擅改章奏罪论处[1](卷249,大中九年五月条)。枢密承旨不见于此前,疑亦为宣宗分枢密之权所创。宣宗对枢密使与宰相勾结的防范也十分严密。大中十年十二月,宣宗欲命萧邺为相,诏枢密院指挥翰林学士拟旨,因诏意不明,王归长复奏是否继判度支,宣宗疑其袒护萧邺,骤改以崔慎由为相,以示惩戒[7](卷中,第105页)。总之,在宣宗的严密监视下,大中时期枢密使相当于传达宣宗旨意的小吏,擅政的机会极为有限。
宣宗抑制枢密使非但没有巩固皇权,反而造成神策中尉权力独强的局面,为其身后的政变埋下祸根。宣宗平日即对左军中尉颇有疑惮,对右军中尉亦不甚放心,故病重之时将夔王托付给一贯驯服的两枢密使。王宗实同宣宗貌合神离,对大中末宣宗拉拢部分宦官的举动必然会有所警觉,如今又无故被剥夺兵权,自然不肯拱手让出神策军兵权,情急之下,宫廷政变也就在所难免了。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宗实之入,恐不免凭藉兵力,必非徒一亓元实翼导之也。不然,王归长等安肯束手受缚邪?”[9](第450页)这也就是说,即便宣宗未崩,亦有可能为乱兵所害,因此政变貌似突然,实则为宣宗同左军中尉积怨的总爆发。宣宗所提拔的王归长等皆懦弱听命之辈,权势又有很大的收缩,不足以控制全局,对王宗实等虽预有防范,仍然无济于事,兵变一起,只能捧足乞命而已。
四、结语
关于唐大中之政,旧史多有赞溢之辞。本文主要对宣宗朝宦官问题上的几个疑点进行辨析。
其一,受《通鉴》等史籍之影响,后世习惯上认为宣宗为躲避文、武诸帝迫害,长期韬光养晦,结果却因祸得福,为宦官所误立。今以碑刻墓志考之,宣宗即位前同仇氏等宦官家族早有渊源,会昌末曾同武宗势力发生激烈斗争。故宣宗得立,乃是他与宦官集团长期以来阴相勾结之结果。
其二,《旧唐书·宣宗纪》“史臣”言:“洎大中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所谓宣宗朝宦官“詟气”之说影响甚深。今亦以碑刻及其它史料考之,我们发现,宦官集团除大中八年前后稍有收敛外,在大中前期、后期不仅没有所谓“詟气”,反而在宣宗的纵容下,广泛介入各种政治事务,甚至还从东南财赋之地攫取大量的经济特权。大中时期实乃宦官权势扩大巩固的重要阶段。
我们知道,宦官擅政的程度与深度,同皇权的强弱及其需要是密切相关的。唐大中时期宦官集团与政治局势的关系,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中前期,唐宣宗统治基础薄弱,不得不继续仰仗宦官,宦官集团在西讨党项等军事行动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舞台上亦至为跋扈。大中中期,宣宗统治已相当巩固,开始着手打击宦官之不法行为,故在其抑制下有所收敛。但宦官擅政的根源却基本上未被触及。而大中末期,宣宗进取心衰退,并沉溺于长生术,在其纵容下,宦官权势又呈复兴之势。大中末期南方诸镇军乱屡起与宦官集团大肆收取诸镇“羡余”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中之政在宦官擅立中开始,又在宦官擅立中结束。过去,曾有学人将擅立新君视为宦官擅政的一种表现,这固然不错,但却未审立君、弑君、废君正是宦官集团得以逐步扩大其权势的中心环节。唐会昌时武宗君臣抑制宦官,籍没仇士良之家,朝纲稍振。会昌末,宦官集团则通过擅立宣宗,权势复炽,不仅武宗君臣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宦官集团还进一步“繁殖财货”,地位更为巩固。宣宗喜以权术驾驭宦官,最终却为权术所害,大中末王宗实等擅立懿宗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宦官集团的权势。据载,宦官立懿宗后入中书商议,当时的宰臣夏侯孜径称:“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8](卷7,第659页)所言尽管十分荒唐,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宦官集团通过擅立新君,其“内大臣”之地位首次得到外朝宰相的正式承认。从这一意义上说,宣宗大中时期是唐代宦官专权问题上的分水岭,它意味着中唐以来围绕着中枢权力,宦官集团与皇权以及宰相之间较为公开的权力之争已告一段落,中央朝政进入懿、僖时期“内”、“外”大臣共同执掌的新阶段。
标签:神策军论文; 会昌论文; 宦官专权论文; 枢密使论文; 历史论文; 新唐书论文; 仇士良论文; 唐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