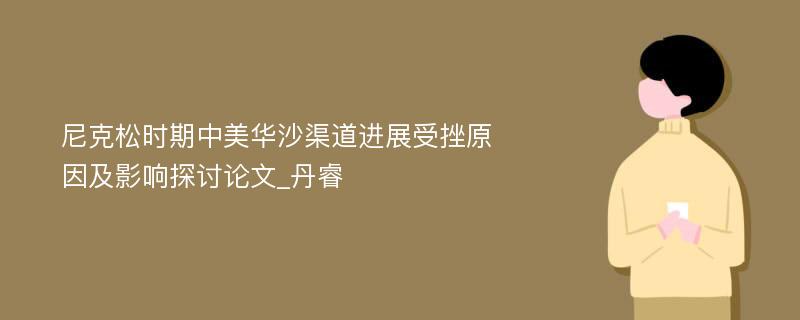
资助情况:本文受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8BS15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SWU1809698。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不承认政策,双方相互敌视,仅靠华沙大使级会谈维持联系。但随着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华沙会谈也因此中断。尼克松上台后,华沙会谈一度重开,在台湾问题和派遣高级代表上取得一定程度进展。受限于会谈级别、保密性、美政府内部政策评估分歧等原因,华沙会谈最终未能发挥更大作用。客观上,华沙会谈在中美互通信息、管控危机以及促进中美正常化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美关系;正常化;华沙渠道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都不予承认,并对华采取孤立与遏制政策,进行包围和封锁。尼克松上台后,逐渐开始寻求双边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在推进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充分利用了多种渠道,终于成功实现上述目标。对于相关渠道研究,国内已经有不少成果。既有对罗马尼亚渠道、巴基斯坦渠道、巴黎渠道、纽约渠道单独的个案研究,也有将上述渠道综合的整体研究[1]。然而对华沙渠道的研究,因其最终未发挥重大作用而研究者不多,有的是带回顾性叙述性质[2],有的虽从决策内幕考虑,但是对华沙渠道停止原因及其积极作用分析不够[3]。事实上,华沙渠道是中美双方最早也是接触时间最长的渠道,作为官方渠道在改善双方关系初期,也一直是中方希望和乐于使用的渠道。然而华沙渠道却未能发挥更大作用,其中原因值得深究。随着华沙渠道失效,促使尼克松加紧其他与中国联系渠道的利用,在吸收此前经验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与中方高层直接地秘密接触,成功开启通往中国大门。
一、华沙会谈重启波折与隐患
美国对新中国孤立政策导致长时期两国联系隔绝,1955年两国方才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1958年后会谈地点移至华沙,此后近10年时间双方前后共开展了134次会谈。1968年5月28日,由于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中方向美方郑重指出“美国最近加大了对中国人民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同时以各种手段欺骗世界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会谈没有任何意义,”[4]原定的第135次会谈被推迟。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就何时恢复第135次会谈进行了多轮协商,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9月17日,即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约一个月后,当美国再次向中方提出,建议恢复华沙会谈时,中方很快予以回复,在信中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一贯是同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友好关系。”[5]在当时中苏论战激烈以及文革高潮时,中方此种表态无疑是对美国友好的暗示,但在具体会期上并未明确答复。
之后在美方再三交涉下,中方于12月25日对其进行了正式回复,建议“明年2月20日开展华沙会谈。届时新总统上台一个月,应该做好决定了。”回复中还特别强调了中方会谈一直以来坚持的两项原则“一是,要求美国立即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所有军队,并拆除一切军事设施;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6]美国于12月29日指示驻波兰大使馆同意中方建议。
为应对即将恢复的华沙会谈,美国内部积极地准备着会谈方针与草案。根据基辛格2月11日准备的备忘录[7]记载,他认为“过去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讨论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这在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两边都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政策;华沙会谈带给我们一个转变政策重心的机会,可以既不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与立场,又不损害亚洲盟国利益(主要是日本)前提下,为了更稳定的东亚而与中共妥协。更具体地说,与北京达成实质的、可实行的安排,给和平共处赋予实际内容,而非停留在口头上。”
备忘录还初步拟定了华沙会谈四项备选方案:一是,明确表明准备就关系正常化谈判,但不影响对中华民国的关系和承诺;二是,表明除了对台湾承诺外,我们准备就政策进行认真讨论或谈判。同时可以暗示如果中国放弃武力解决争端,我们愿意审视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三是,可以按中方的愿望提出和平共处并询问他们是否有具体建议,而我们只是表明乐于倾听他们的建议,不主动提出任何具体的一般性措施;四是,采取主动,痛斥中国过去的非法行为。
备忘录中比较偏向第三项方案,认为其优势在于“强调了我们有兴趣在东亚发展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而不需要在当前采取新行动;不会引起盟国担心,实际可能会受欢迎;可以试探北京的意图。”当然文件中也指出了该方案可能存在的不足,即“不太可能在短期或长期引起北京的积极反应;北京和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我们仍停留在当前立场而stoessel没有新的举措。”
该备忘录第三项方案得到了美国决策层一致认可。国务院认为该方案还能“减轻‘中华民国’的担心,它现在很敏感因为当前加拿大和意大利正准备承认北京;减轻有些国家误以为由于加拿大对北京的承认,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将会有根本转变的风险;避免在国安会3月对中国政策全面审查前[8]就产生偏见。”最终,尼克松同意了第三种方案,2月15日该方案作为会谈指示发送给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馆。
然而事实上会谈进展并不顺利,就在美国方案准备期间,2月4日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出逃事件,廖通过荷兰当局被送往美国,并有消息称他将可能被送往台湾。2月6日中国国内指示大使馆以代办名义向美国发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勾结荷兰政府蓄意制造的严重反华事件;美国政府必须将廖和叔交还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9]然而美国似乎对此事并不在意,2月10日罕见地要求中方上门领取复信[10],另一方面还在与中方使馆商议大使级会谈的业务事宜。
不过就在2月18日,中方以代办名义再次向美方表示了抗议,“美国政府不仅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在目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中,按照预定日期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不适宜的。”[11]至此,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重启计划再次搁浅。
中方虽然在会谈前两天取消了预定安排,但从对美方回复的措辞上,仍可以看出中方对会谈的总体态度保持着积极性。一是,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这是中苏论战及文革背景下对美友好的重要暗示。二是,在廖出逃事件中,中方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是以“代办”名义向美国使馆发出抗议;对事件责任也并未全部归咎美国,而是由荷兰政府与美国政府共担;对会谈停摆处理上,实际也只是表明按期举行不适宜,暗含了可以择期再开的意味。
从美国对会谈的准备来看,1969年尼克松上台初期会谈政策偏向保守,基辛格虽有意给“和平共处”赋予实际性内容,但是在首次会谈方案上与国务院意见比较一致,倾向稳健保守方案,着重倾听中方建议,己方不提出具体措施,既顾及了可能对盟国产生的影响,又试探中方反应,对自身底牌则不愿提前透露。
如上所述,中方在外交官事件当中多有克制,但会谈的取消毕竟造成了中美缓和由热转冷,在基辛格看来,“到1969年3月,中美关系似乎又冻结在这20年来的相互不理解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了。”[12]不过随后3月份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以及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让中美关系再次出现转机。
中国方面,在中共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正式重新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根据当时助理熊向晖记述[13],在7月11日报送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元帅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9月到11月期间的后续多次讨论会上,还作出了“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四位元帅并未谈及廖和叔叛逃一事对华沙会谈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1969年2月份的会谈延期并非中方故意为之,更可能是由于内部原因导致政策临时调整。关于此后华沙会谈的处置上,元帅们作出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的政策建议。
9月11日,柯西金借吊唁胡志明后绕道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面后,四位元帅又于17日紧急报送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陈毅还专门提到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他设想“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而后华沙会谈的进展恰好印证了陈毅这一大胆设想。
美国在中苏冲突后,也重新评估了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认为与中缓和有利于战略上牵制苏联。尤其是尼克松7月环球访问中,在关岛发布的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有关讲话,明确表示了在亚洲进行收缩的意向。之后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领导人时,明确表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通过中间国建立联系渠道的愿望。美国还单方面放松对赴中旅游和对中贸易的限制。
9月9日,尼克松、基辛格专程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进行了一次谈话。要求大使能够在中立国家使馆直接向中国外交官传达“我已经在华盛顿见过总统,他对于同中国进行具体问题讨论具有浓厚兴趣,”并叮嘱其“中国外交官的任何反应都具有重大意义。”[14]不过斯托塞尔进展缓慢,10月初到11月下旬,基辛格在尼克松授权下,三次电令斯托塞尔“在下一个方便的外交场合去找最高级的中国外交代表,向他建议恢复华沙会谈。”[15]基辛格甚至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让愿意照办的人来办了。”
终于在12月3日,斯托塞尔在一次南斯拉夫政府举办的活动中找到机会向中方外交人员转达了尼克松的消息。之后双方在1970年1月8日正式会见并确定于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
就在华沙会谈停摆期间,尼克松政府内部在华沙会谈的准备上,开始由最初的基本一致开始显现分歧,主要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白宫核心工作圈和以国务卿罗杰斯为代表的国务院官僚系统。有关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霍尔德里奇评价“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国处理美中关系这整个问题的方式是,由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牢牢掌握决策大权,国务院被排除在所有的重大决策之外,国务院的作用限制在白宫作出重要决定后,在次要事务上给白宫支持。”[16]
而当时白宫与国务院的最初分歧出现在华沙会谈的保密性上。国务院偏向认为“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让苏联怀疑我们与中共联手对抗它的可能性。”基辛格却提醒罗杰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告诉多勃雷宁会谈内容。如果他问到,我们应该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关注的只是互相感兴趣的话题,没有超越这一点。总统关心下级工作人员在非正式谈话中不要超越这一点。”尼克松本人也强调“华沙会谈以及与苏联的谈话都应该在秘密的基础上处理。”[17]基辛格还特别向国务院转达了尼克松的担心并命令“有关华沙会谈和中美关系的所有电报、公开声明、新闻稿或者参考资料都由白宫审查。我们与中共的会谈不应对苏联有任何解释,也不应对苏联的相关反应有任何推测。”[18]
然而白宫官僚系统并未按照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要求严格保密,“在白宫奇妙的系统里,各种行政部门和外国政府或多或少自动被告知了重要的情况。”[19]对此,罗杰斯却解释道“我们在东京,台北和莫斯科的大使馆和驻香港总领事馆因为他们对此事的特殊兴趣而被通知。‘蒋总统’是作为有必要的礼貌性通知,佐藤首相是为了会谈结束后好与他一起共同应对公众意见。”[20]他还为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等国政府甚至是美国之音等公众媒体了解情况进行了诸多辩解。基辛格对于难以保密的现状只有无奈地表示“我想,总统应该也会这么想,我们在华沙会谈上处理得很差。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去建立它,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大使馆都知道了。”在基辛格看来,有关华沙会谈内容“我们说得越少,我们得到的就越多。”尼克松在收到基辛格汇报后,也叹息道“孩子未出生就将被我们扼杀了。”[21]
一次外交官事件,延缓了华沙会谈重启的时间,但中美这一联络通道并未因此中断。一方面,在互相利益需求的驱动下,双方最终同意恢复会谈。此时虽然尼克松也尝试通过其他方式建立联络渠道,但中方显然更加偏向直接在华沙会谈上谈判,周恩来就曾在1969年9月7日和12月12日分别会见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代表时,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22]。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对会谈的分歧和矛盾冲突逐渐显现,权力之争与意见之争交织混杂,甚至已经直接影响到会谈的准备与进行。斯托塞尔作为政府驻外人员对于来自白宫的直接指示执行力和执行意愿不强;而总统一再强调保密性,国务院却主动或是放任消息在官僚系统内流转,保密意识的缺失也暴露了华沙会谈失败的隐患。
二、重启后初次会谈与美国内部变化
在第135次会谈日期确定后,美国内部的会谈准备工作随即展开。由于196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年初为第135次会谈准备的备选方案显然已不合时宜,美国策略开始由伺机而动转为主动出击,这也显示了四元帅在判断重开会谈时机上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1970年1月14日,罗杰斯向总统提交了新的华沙会谈指导方案。这项方案最大的亮点是不再沿用年初第三方案中消极等待的态度,而是提议积极向中方强调中美关系的新开始和这届政府在亚洲推行的新政策,并传达此前未向中方表达过的立场[23]:
1、关岛主义。虽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但私底下再传给中国有利于关系改善。
2、美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打算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公然侵略。这有助于消除中国的潜在威胁。
3、我们打算减少在东南亚和中国南部边境的军事存在。这向中国表明我们不寻求永久军事存在,缓解其对被包围的忧虑。
4、提议讨论我们在该地区的目标和限制。
5、提议讨论整体贸易问题以及相关义务。
6、台湾问题的3个新提法。
(1)美国不打算将他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一方,也不打算干涉双方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
(2)承诺不支持台湾对大陆的反攻。
(3)表达希望随着亚洲局势变得和平稳定,可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
7、提议进行裁军的双边讨论。
8、提议派遣特别代表赴华盛顿或北京进行上述任意观点的讨论。
此次方案大胆提出美方关切点,在诸多敏感问题上并未选择回避,展现了力图把握会谈主动权的意图。在这个方案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单方面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与以往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有所不同;二是,主动提出派遣特别代表,与之前一直强调需要现在大使级会谈取得实质性成果态度发生了转变。虽然这份方案仍主要立足于美国利益诉求,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还有较大差距,但为促进华沙会谈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基辛格也对这份草案总体比较满意,认为需要修改的问题主要出在语气上。他希望用更为温和的方式提出,这样会对中方更有吸引力。
在1月20日的正式会谈中[24],斯托塞尔首先根据国务院指示,表明了美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不会孤立或联合敌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能够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的表态;最后提出派遣或接受特使进行双方直接会谈。中方主要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原则表态,中方也表示可以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亦可通过更高级别会谈或双方都同意的其他渠道开展对话。
斯托塞尔会后给国务院汇报[25]中认为“中方表态是非争论性的,愿意和平谈判解决与美国的争端。”同时他也提醒道“我相信中方为确保会议安全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任何泄露中国宽松的表态以及对于会议气氛的乐观描述将会让今后的联系尴尬,并致使中方强硬的防御姿态。”
尼克松上台后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为双方提供了了解互相立场的渠道,虽然在核心关切的台湾问题上双方在基本立场上存在分歧,但并未以此作为进一步接触和谈判的前提条件,双方在更高级代表和其他接触渠道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可以说第135次华沙会谈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相向而行。
(二)开辟其他渠道的尝试
基辛格显然注意到了中方在华沙会谈中态度的积极变化,会谈后第二天,他就会谈的变化情况向尼克松作了整理汇报[26]。他特别指出“中方重申了台湾立场但未要求我们明确行动;中方避免提及第七舰队、美苏勾结、越南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对此他评论道“中方的语言无疑是我们在华沙会谈历史上听到的最愉快的话,他们想继续会谈,现在问题是我们想如何利用这种转变?美国想完成的都是过渡性问题。这些都是以前谈过的,中方没有多大反应,他们坚持首先解决台湾问题。他们仍然坚持,但对于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也许会更加灵活。我们可能不得不适应他们去谈论台湾,但是我们需要小心翼翼不要扰乱台湾当前稳定而给他们意外收获。”最后他提出“对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同意斯托塞尔的关注,我们不要向朋友讲的太多,任何关于会谈的简报都要在这里审查。”
此时基辛格敏锐地把握住了中方的态度变化动向,一方面注意到中方积极转变,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难缠。在没有具体对策之前,他的态度比较谨慎,再次强调了保密性的重要。
对保密性的一再重申反映出基辛格对国务院安全工作表现出的不信任,实际上他也开始尝试建立能绕开国务院的其他联络渠道。在一份2月5日的备忘录中,他向尼克松汇报了荷兰负责对中国事务代办德克森的相关事宜[27]。德克森于1月30日以个人身份来到波士顿拜访了洛奇,并向洛奇提出如下建议:
1、提议他本人作为美国与北京政府沟通的渠道。
2、保持绝对秘密,只会向本国总理报告与美国协商好的内容,不会向外交部长透露。
3、周恩来在北京能全权指挥,他比较容易通过外交部副部长接触到。
4、他曾在1月13日被告知华沙会谈恢复,并收到如果美国想改善关系,那么一切都将变得简单的保证。
5、德克森判断周恩来希望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相对苏联人更偏向美国人。
6、德克森认为给他指派启动美方高级代表与周恩来会谈的任务是十分有用的,可以让双方关系有真正的进展。
基辛格认为德克森可以给中共提供安全感,而国务院内的亲苏派有可能不仅仅向多勃雷宁提供华沙会谈的内容,让苏联有机会通过恐吓中共来破坏会谈。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为此,基辛格还专门准备了一份给周恩来的备忘录草案:
美国政府希望在华沙大使级会谈重开后继续交换意见。然而由于公众的兴趣、会谈的级别以及牵涉的众多官员,使在此处会谈很难保证完全秘密。如果中国政府想让会谈不被他国知晓,总统准备建立一个备用渠道来处理最为敏感的事务。[28]
基辛格还在备忘录中详细提供了该渠道联系方式,并说明是直接与白宫联系,会谈内容只有总统身边小范围最亲近的人知晓。基辛格最后建议总统批准此备忘录并将消息控制在总统、洛奇、德克森和基辛格4人范围内。
据2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29]显示,基辛格在与洛奇和德克森的会见中传递了上述消息,由此可以推断是得到了尼克松的授权。虽然此后中美秘密联系主要依靠巴基斯坦渠道实现,但上述文件说明国务院主导的对中接触工作早已经不被尼克松所完全信任,尼克松—基辛格尝试着利用各种方式建立与北京的直接联系。
三、再次会谈及美内部政策的对立
(一)第136次会谈的进展
虽然基辛格已经在筹划通过其他秘密渠道取得与中方直接联系,但在渠道正式建立前,国务院作为美国政府官方外交机构,仍然直接承担着中美华沙会谈的具体交涉工作。2月3日,基辛格在尼克松授权下要求罗杰斯“根据华沙会谈的变化制定一份计划,计划应该包含我们在会谈的目标以及适应该目标国务院准备使用的策略。”[30]
2月6日国务院准备好了指导草案,该方案指示斯托塞尔:
1、表明我们准备与中国讨论一份联合声明,包含我们不干涉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以及重申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表明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缓和,我们打算减少在台湾军事设施。
3、表明我们准备放弃对赴大陆旅游的剩余限制。
4、提议专门讨论并解决封闭账户以及有关扩大贸易关系的问题。
5、授权我们大使讨论关于两年内将刑满的美国人理查德的特赦问题。
对于这份方案,虽然基辛格认为当前的策略和指导在总的方向上没问题,但国务院的方案从美国之前自己提出的派遣代表意见中有所后退。他还提醒尼克松,从1955年会谈开始不久中方就提出提高会谈级别而美国坚持在此之前大使级会谈要有进展,这种负面反应或许就是谈判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他最后建议总统,授权其通知国务院对该草案中有关回应中方在北京或华盛顿对话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进行回应。
总统批准了基辛格的建议,最终会谈指示分别于2月18日和2月19日以电报形式发送给了斯托塞尔。而值得注意的是,2月19日当天,斯托塞尔还收到了一封提醒其采取积极态度回应中方有关高级别会谈的来信,信中特别突出了这个意见是来自白宫的,可见白宫与国务院在围绕是否应该派遣高级别特使上分歧日渐凸显。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大局和战略利益出发,希望会谈能够稳步推进;然而罗杰斯则局限于外交一时一处得失,在推进会谈态度上保守甚至退后。国务院官员自身也曾表示“从国务院的角度看,对互派高级使者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之处,不过,存在着一种忧虑,唯恐在得不到相应的汇报的情况下,美国人会失去得太多,会对美国同其东亚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31]另外,从国务院向大使单独以信件方式告知白宫意见一事上看,罗杰斯当时对基辛格已心怀不满,只是碍于总统权威不得不照章执行。
1970年2月20日,中美双方代表在美国驻华沙大使馆进行了第136次正式会谈也是最后一次华沙会谈。根据美方会谈记录[32],中方在会谈中表示注意到了美方没有回避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并再次重申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中方也指出在两国大使级会谈上完成这个任务有诸多困难,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会谈。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遣部长级或总统特使代表来探讨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关于这次会议的发言稿,周恩来还专门在2月10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后他建议将最初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考虑”一词换为“接待”,获得毛泽东批准。[33]显然周恩来希望通过词语的表达,向美国暗示中方的积极意向。
美方大使在会谈上回应了中方有关台湾问题的关切,继续表明了该问题由相关方直接解决,美方坚持应该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付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不打算干涉双方任何和平解决方案。不过在台湾驻军问题上,美国也从言语上透露了积极态度,由上次会谈中“希望”转变为“打算”随着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在有关派遣代表一事上,斯托塞尔按照白宫意见,积极向中方表示了“美国正准备和你们一起考虑派遣代表的可能性”[34]。
从会谈记录来看,中美双方此次会谈较上次又有了进展,斯托塞尔向国务院的汇报[35]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他指出雷阳在20分钟的开场白中只关注两件事即台湾问题的首要地位和高层会谈的兴趣。他认为中方声明比上次会议甚至更加温和、非争论性,没有指控美国军事介入台湾,也避免提及无人机事件[36]。同时他也提醒中方明显准备在下次会谈中只讨论高级别会谈本身。
(二)美国政府内部分歧
基辛格对第136次华沙会谈内容十分重视,会议结束当天就向尼克松提交备忘录谈及此事。在备忘录[37]中他指出,中方现在从我们谈判立场中选取了最容易在外界产生轰动效应的元素。在回应我们建议时中方应该已经在头脑内考虑到了所有影响。但是他们也必须考虑调整对美国以及美国在台湾角色问题上的立场以避免高级别接触的失败,这种失败会鼓励苏联人相信中国寻求美国的探索失败,他们现在需要独自面对苏联。备忘录还观察到中方在这次会议上避免了争论和提及有可能伤害会议气氛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应该积极回应中方,小心选取代表并对他在北京的谈话设置底线。他还表示,由于下次会谈时间由我们提出,主动权在我方,我们不必急于指定代表,但也不应拖延太久,以免产生负面印象。
与基辛格建议派遣高级代表赴北京会谈的积极态度不同,罗杰斯对此提出了截然相对的看法。他在3月10日给尼克松的备忘录[38]中提道,由于北京希望的高层会议仅仅是服务于对抗苏联,破坏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削弱联合国内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因此只有当大使级会谈取得成果后才同意开展更高级别会议。他还进一步提出,最初的方式应该是有机会更深入试探中国意向,看他们对高级别会议有多强烈愿望以及是否愿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他还建议向中方提出3月19日举行下一次会谈,并表示美方希望在华沙进一步讨论高级别会谈前的共识基础。
罗杰斯的态度较之前可谓大幅度倒退,不仅试图将高级别会谈又定义回试探中方意向,而且不顾此前正因为美方一直要求在大使级会谈取得所谓成果,才导致华沙会谈迟迟没有进展的历史教训,又开始为会谈设置障碍。此外在会谈举行的时间上,罗杰斯居然在3月10日的备忘录中向尼克松建议于3月19日举行下一次会谈,基辛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允许总统有48小时考虑,这个备忘录明显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这么短时间内准备会议。”[39]
尼克松对罗杰斯在华沙会谈中采取的这种保守态度十分不满,根据美方档案[40],3月13日他在电话中向基辛格抱怨道“我一直在想中国的事情。他们提议在华沙举行会谈吗?我要的是在北京会谈。我不同意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建议他们告诉中方在本质上我们同意。谁在负责这件事?告诉他们,总统已经决定,我们要这样做。我想确保他们不会搞砸。”
基辛格在3月20日将总统的这一想法委婉地向罗杰斯进行了传达,从基辛格选择通知的时间点上其实已经表明否定了罗杰斯3月19日举行下一次会谈的建议。基辛格一方面转达了,总统认为会谈从大使级上升到更高级前确立双方立场的共同点是可取的;另一方面,总统相信以积极的方式应对提高会谈级别问题是重要的,并且应避免让中国感觉我们正在从1月20日会谈自己提出的建议上后退。因此总统指示斯托塞尔在下次会谈时提出我们积极寻找双方共同点的立场,以充分表明我们寻求高级会谈的意向。此外,在下次会谈时提出讨论北京高级会议的模式问题,比如外交豁免、安全通信等。
基辛格转达的此番总统意见,虽然原则上没有否定国务院有关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上寻求共同基础的建议,但实际上已经在命令国务院于下一次会谈中就高级别会谈细节问题开始和中方协商。
关于下一次会谈的时间安排,基辛格最初期望在3月23日至27日之间,但由于国务院的方案与设想差距较大,传达总统新意见后,国务院又声称需要更多时间准备,因而又被迫推延。而此前罗杰斯自己提出的时间安排却是备忘录后的一周左右,很难说罗杰斯没有借故拖延之嫌。随后的4月至6月期间,中美双方又因蒋经国访美,美国入侵柬埔寨等事件一再推迟。在下一次会谈日期迟迟不得确定之,国务院内部也有人在4月22日曾建议主动向中方表明“我们想继续对话,我们不认为东南亚的事态发展会影响华沙会议。”[40]罗杰斯则坚决地表态“不同意,我们为什么要表现得这么焦急。”[41]
会谈时间的一再拖延最终造成了华沙渠道的彻底关闭。6月20日,中方外交人员向美方人员正式通告“我被指示向你通知如下内容:鉴于双方都清楚知道的当前形势,中国政府认为不宜讨论和决定目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下次会议的日期。至于将来什么时候适合举行,可以由双方的联络人员在适当的时候讨论。我们这边会发布有关消息。”[42]然而此后中方再也未向美方华沙渠道发布消息,第136次会谈成为中美华沙会谈的绝唱,尼克松政府试图通过正式的华沙渠道打开中美关系的外交尝试也以挫折告终。
四、结语
华沙会谈长期以来作为中美交流的唯一正式渠道在尼克松上台前已举办了134次,在基辛格看来,华沙会谈“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议。”[43]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恢复会谈并试图使其在改善中美关系上发挥作用,中方也注意到美方在华沙会谈上态度的转变,对华沙会谈十分重视。然而就在第135次以及第136次会谈取得明显进展之时,下一次会谈时间却在双方反复博弈中不了了之,不得不说是重大遗憾。
华沙渠道在中美关系最为敌对,会谈最无进展之际尚能延续;反而在中美缓和,成果初显之时戛然而止,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一,级别不够,反应迟缓。十几年来华沙会谈一直徘徊不前,针对中方提出的提高会谈级别的建议,美方始终坚持在大使级会谈取得成果之前不予考虑。美方负责大使也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大使在会上就是宣读发言稿,所得到的回答无疑也是这类文稿。在下一次会谈里,照旧宣读在各自首都经过冗长准备的对答。”[44]这种低级别低授权的会谈,导致双方始终拘泥于事务性互相陈述,事事需请示缺乏临机决断之权,也注定会谈在迁延日久的程序性进程中错失良机。
第二,自行其是,难以保密。会谈选址位于波兰,由第三国提供双方会面场地,很容易受到监听泄露危险,再加之中美关系本身敏感,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尼克松上台后,会谈开始交替在两国使馆进行,然而美国国务院却对保密工作不太重视,不仅在官僚体系内放任使馆间互通消息,对各相关国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也纷纷进行通告,国务院内亲苏派甚至会做出某些出格之举。
第三,情报分散,政策不一。在华沙会谈进行的同时,尼克松基辛格也在利用各种其他渠道收集和向中方传递信息,而这些秘密渠道进展情况国务院毫不知情。因此白宫和国务院在对华沙会谈的政策起草和形势判断上出现信息不对称,政策不统一。
第四,权力掣肘,因小失大。基辛格与罗杰斯在决策层内互相博弈角力,争夺外交主导权,试图向总统施加更多个人影响。先是有基辛格三次电令大使仍无行动,后又有罗杰斯在会谈日期上一再拖延。国际谈判通过运用外交技巧让己方处于谈判优势地位本无可厚非,但过于倚赖或不择时机则适得其反。在第136和第137次会谈取得一定成果后,国务院政策又转向保守,即使总统决断后,又在会谈时间上贻误时机,为了所谓外交颜面不顾大局。
虽然华沙渠道未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有力作用,但也不应忽视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史上的积极影响。
首先,会谈为中美双方提供了互通信息和危机管控的渠道。自朝鲜战争之后,虽然中美又多次面临紧张危机,但再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其次,长时间的交涉也使双方互相了解了基本立场和谈判风格,在会谈中也提出了一定建设性意见,为推动台湾问题解决,促成高级别会谈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虽然通过华沙会谈实现互派大使的计划落空,但双方就此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华沙渠道的搁浅客观上也促使尼克松基辛格彻底绕开国务院,加紧其他秘密渠道的建设,最终通过巴基斯坦渠道顺利实现破冰之旅。
参考文献
[1]参见 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史学集刊,2008(3);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4);栗广.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纽约渠道.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4).
[2]参见 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4).
[3]参加 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2).
[4]FRUS,1964–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311.
[5]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1.
[6]FRUS,1964–1968,Volume XXX,China,Document 311.
[7]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
[8]2月5日,国安会NSSM14号文件要求全面评估对中政策,此时评估报告还未形成。
[9]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4).
[10]一般情况下,中美双方信件都由美方到中方使馆领取。
[11]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4).
[12]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171.
[1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75-201.
[14]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31.
尚辛.尼克遜回憶錄(中國部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78:79-80.
[15]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9-40.
[16]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51.
[17]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53.
[18]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190.
[19]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53.
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190.
[20]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4).
[21]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1.
FRUS,1969–1976,Volume E–13,Documents on China,1969–1972,Document 3.
[22]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2.
[23]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3.
[24]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6.
[25]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6.
[26]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6.
[27]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7.
[28]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5.
[29]FRUS,Volume E–13,Documents on China,1969–1972,Document 4.
[30]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48.
[31]FRUS,1969–1976,Volume E–13,Documents on China,1969–1972,Document 4.
[32]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8.
[33]2月10日,美国一架侦察机在海南岛坠落。中方宣称被击落,美方宣称由于航油耗尽。
[34]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69.
[35]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72.
[36]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690.
[37]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73.
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80.
[38]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80.
[39]FRUS,1969–1976,Volume XVII,China,1969–1972,Document 80.
[40]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684.
[41]HENRY A,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686.
作者简介:丹睿,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论文作者:丹睿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9
标签:华沙论文; 基辛格论文; 尼克松论文; 中方论文; 美国论文; 国务院论文; 中美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2期论文;
